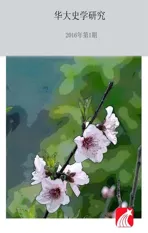重寻“现代”历程
——对孔飞力近代中国演进中根本议题的思索
2016-02-02李君生
重寻“现代”历程
——对孔飞力近代中国演进中根本议题的思索
李君生
对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的学人来说,孔飞力(Philip A.Kuhn)的名字并不陌生。作为一名杰出的历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及《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二书颇受中国学者重视。孔飞力在这两部著作中将关注重点定位于地方及社会下层,通过描述某种社会现象在基层的表现来透视整个帝国背后社会控制所潜藏的危机,这种研究取向启发并影响了众多学者。
与地方或区域性的社会史研究有所不同,关注地方或底层是孔飞力思考“全国性问题”中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视角。不过孔飞力学术关怀的重要一环,还在于持之以恒地探讨中国传统资源对现代转型的影响。孔飞力的著作《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直接将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作为论题,探究其何以是一种“中国的过程”,他的治学宗旨因而在此书中将得到更为直接的呈现。在当下学术界反思现代性的潮流下,此著对中国走向现代性历程的意见更是不能被轻视的。
全书就结构而言,共分五个部分,除导言外,其余分为四章;就内容而言,对根本性议题的探讨是全书的核心。第一章论及魏源著作中体现的有关政治参与的意识,第二章探讨了晚清几位官员对冯桂芬政治竞争问题建议的反应,第三章考察了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后一个世纪以来国家为强化乡村控制所做出的不懈努力,第四章论析了代际传承的思想家们对根本性议题的不断探寻。其中前三章分别对应着孔飞力提出的近代中国演进中三个具有根本性质的议题: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政治竞争如何同公众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第四章具有综括性。
尽管只有短短四章的篇幅,《起源》却展现出了孔飞力明确的问题意识与宏大的学术视野,通常这也是海外中国研究的优点。一般而言,没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便没有一定价值的学术研究。一本扎实的研究著作,存在有意义的“真”问题同时,也需要一定理论方法的建构与学术视野上的开拓。
孔飞力的问题意识,便在于他探讨中国现代国家时,发现历史传统对于中国现代国家特殊性的形成过程所做出的贡献仍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在他看来,中国“内在文化”特殊性并不是一种“中国性质”的宿命,反而是决定着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性。种种由中国“内在文化特质”导致“中国永远是中国”的研究方式,只是一种没有意义的循环论证。他认为摆脱这种循环论证的方法,便是要处理每一代人所要应对的根本性问题。这些根本性问题会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出现,但在新的环境下,在中国现代历程的种种表象中,孔飞力相信这些根本性议题会继续存在,而中国现代国家的演进,便可以通过考察不同时代对这些根本性议程的改造与再改造发现。
如前所述,根本议题围绕近代中国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展开。孔飞力所探讨的问题,时间断线设定于18世纪90年代的危机。如其所述,他认为正是这场危机使得“一些过去看来似乎具有偶然性的现象,此时在人们眼里都具有了全局性意义。一些过去看来只是属于地方性的现象,则被视为具有了全国性的意义”*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导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8页。。这场危机留下了三道具有关键性意义的难题:第一,如何对抗权力的滥用;第二,怎样才能充分利用文化精英们的政治能量;第三,如何用狭小的官僚机构统治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孔飞力历史性的思索从危机留下的这三道难题出发,认为这即是近代将要面对的根本性议题之所在。
根本性议题的选取与探讨,体现着孔飞力强烈的“内部叙事”取向。不过孔飞力并没有矫枉过正,否认“外部”方面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意义。他只是认为“要回答现代国家何以会具有形形色色的宪政结构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仅仅依靠外部史观便不能说明问题”*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文版序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页。。这种从中国自身出发理解现代中国的方法,被柯文定义为“中国中心观”,直接回应了欧洲中心观“外部”取向的理论框架,区别于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反应论,列文森提出的传统—现代论和一些学者的帝国主义论*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孔飞力相信,认识到不同国家可以经由不同方式走向“现代”的实例,有利于将现代化发生的“内部”与“外部”史观统一起来。
在讨论现代性的演进中统一“内部”与“外部”史观,是孔飞力本书的诉求之一,而一本学术著作值得肯定之处,恰也应该落脚于本书自身的优点以及对学术界的贡献。不过本书除了问题清晰、视野宏大外,对根本性议题的思索,还在于在既定的问题意识下用旧材料解决新问题,并阐述了三个方面的新观点。
其一,相对于魏源既有研究成果,孔飞力更加关注魏源思想中与现代国家建制发展有关的部分,探讨魏源扩大政治参与、促进政治竞争可以同国家权力的加强结合在一起的部分。如其所述,这为我们找到了现代国家起源的独特性和本土性。其二,冯桂芬作为魏源根本性议题的继承者,孔飞力利用清宫档案中京官们传阅并批注的《校邠庐抗议》,发现《抗议》的批判者们与美国早期联邦党人相比缺乏对公共利益的乐观,向我们说明近代士人为什么对于政治竞争实现公共利益的概念始终无法协调。第三,从耒阳暴乱到集体农业化,孔飞力对国家在税收中与中间掮客一个多世纪斗争的跨越性描述,论证了历史的演进中,旧政府原先未解决的财政需求议程不会因为新政府的出现被搁置,而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一再表现出来,对旧议程的不断改造,在财税改革中体现了现代国家建设的演进。
只可惜,《起源》毕竟是孔飞力以系列讲座为基础修订成的论文集而非专著,无论是全书构架或是由翻译导致的文字流畅程度,均要比《叛乱》和《叫魂》略逊一筹,仅以一百二十余页的篇幅来论证现代国家的议题,内容不够深入,因而出现了不少问题。
首先,作者苦于寻求的“中国经验”之特殊性依然摆脱不了西方标准。尽管孔飞力一再强调中国“内在导向”,避免将中国历史进程以西方为标准,但仍免不了将根本议程的构建以西方价值为标准,且不论近代中国是否真的存在着根本性议程,即使存在,选择作为议程的标准是什么?孔飞力选取了现代性的政治参与、竞争,中央与地方的财税纠葛为议程,但为什么不是现代军队、现代外交?这一点,孔飞力似乎并没有逃脱西方标准的局限。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为其中根本议程,孔飞力明显受到美国政治架构中以议会、多党背景下政治参与等为标准衡量中国走向现代所需要的政治条件,而中央与地方的财税竞争也不排除在英国求学时受到近代以英国王室与纳税人之间的斗争为背景的影响。
第二,作者对现代性的讨论不足。孔飞力把“现代”一词解释为“现实的存在”,此定义未免简单,忽略了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意涵,所以根本问题恐怕还在于如何定义国家的现代性。正如作者一直所强调的,我们不能忽略现代的差异性,可是在操作中,现代性若真如孔飞力所指出的那样仅仅理解为现实的存在,那他无疑消解了讨论现代性的意义。孔飞力构建现代性的标准即为根本性议程,且不论其见解有多少后见之明,即以此议程为标准,中国就具有现代性了吗?在现代性的进程上是越当代越现代吗?新中国成立后对统购统销的实行确实打压了中间掮客,靠着强力政权无偿榨取农业生产利润,也确实能够证明中央集权性越来越大,但能说这是一种现代性吗?在探讨过去时,孔飞力设定的标准又如何避免对知识分子对传统的思考人为赋予现代性?如果对现代性的理解缺乏恰当的阐释,则近代中国历史演进中有没有现代或如何现代都不重要;不恰当地解释现代性,还会让今人对时人产生一种误解,如此一来对当下也缺乏意义。事实上作者也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他在中文版序言中意识到对现代一词的理解是难以完全令人信服的。不过本书围绕根本议题的讨论与现代性的矛盾还在于,孔飞力始终关注的是晚清以来代际相承的问题,而时人面对同样问题给出的回答背后是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如何更好在代际相承中体现中国演进中的现代性,无可讳言,孔飞力的叙述并不是十分令人满意。
第三,作者对某些问题的分析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孔飞力围绕魏源进行的根本议题的讨论就有以论代史之嫌,魏源主张更广泛的政治参反映了帝国晚期根本性议题的应有之义,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应注意到传统士人“仁以为己任”及“明道救世”的文化传统,广开言路并不为近世所罕见,如果这一点不加区别,则魏源与古代士大夫政治参与意识有何区别就难以说清。孔飞力在耒阳暴乱一章将近代财政改革归结于国家对中间掮客抵制,显然存在失实,中间掮客确实与国家利益存在对立,但绝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零和博弈,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存在众多合作。综观全书,仅仅依据少量知识精英思想和一些地方经验来解释“现代国家”问题,也未免过于简单化处理,更何况思想家的意识,一般超脱于时代,这种根本性议程多大程度上是代表时代的议程,也是一个问题。譬如孔飞力讨论冯桂芬的民治思索,但思索与史实并不是一回事,如果思索也可作为现代性,那中国现代性起源最起码恐怕也要追索到明末,黄宗羲对封建君主的批判,主张对执政者们权力的监督是魏源、冯桂芬能比的吗?
第四,作者对中国现代性演进中的横向比较还有进一步拓展的余地。孔飞力曾在对中国晚清官员同联邦党人对比中曾提出一种观点,帝国官员们与联邦党人对公共利益的看法不同,正是这种悲观主义排除了代表权实行的可能性。不过要继续深究这种差别,很可能还要回到中国儒学传统上来。张灏提出一种解释,认为是西方自由主义背后的幽暗意识孕育了西方的民主传统,而儒家思想相反,却是对人性过度乐观*张灏对幽暗意识的解释是“发自对人性中或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醒悟”,《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第24页,具体阐释参见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在耒阳暴乱到集体农业化的地方税制探讨中,必须注意到近代欧洲国家抗税暴动长期存在,而中国抗税暴动变得普遍是20世纪初附加税增加之后才有的现象,在近代中国对外战争带来压力之前,传统中国国家政权一直满足于对地方的有限渗透,李怀印对晚清和民国时期河北获鹿县的研究表明了这一点*参见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第十二章结论部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95页。。
不过,我们不能对一本提要式的著作作出面面俱到的苛求。综观孔飞力全书的探讨,更倾向于现代性政府的制度运作,而非现代民族国家,相较于后者而言,前者仅仅是后者的一环而已。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位具有深刻人文关怀的史学大家,孔飞力的著作总是能留下太多启示,《起源》一书亦如此。《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未尽的探讨不会始终无果,缺憾也是创新的空间,孔飞力对中国现代历程的追索,将会继续延伸出新课题与新认识,对于一本著作而言,这也是值得称赞的贡献。
本书的最后,孔飞力最终并没有依据他所提出的根本性议题为中国现代国家的未来走向给出明确回答,只是指出困扰当下的问题其实在历史中已经长久存在。他认为,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能否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实现,只能是一个由时间才能回答的问题。充分认识过去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下,孔飞力思索中国近代一个世纪的根本性议题至少提醒我们,认清历史从哪里开始,会使我们走向哪里更富远见。
(李君生,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