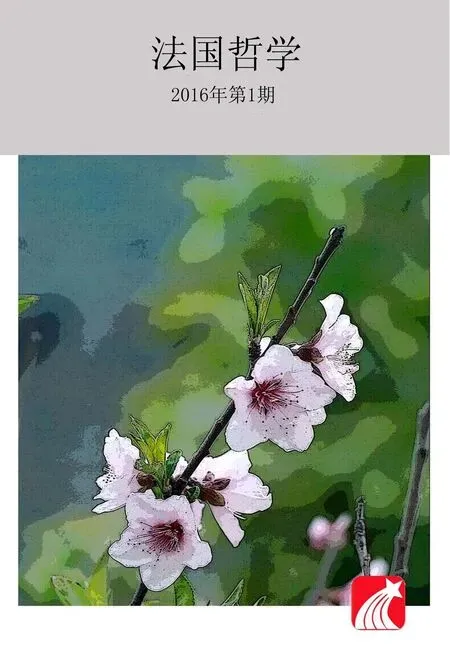以“罪”替“错”*—辨析《第一哲学沉思集》中对错误来源的回答
2016-02-01李琍
李 琍
(同济大学哲学系)
以“罪”替“错”*—辨析《第一哲学沉思集》中对错误来源的回答
李 琍
(同济大学哲学系)
早在1619年,笛卡尔在第一部未公开手稿《指导心灵的原则》中开篇就写道:“研究的目的是使心灵对世上呈现的一切事物形成确凿真实(solida& vera)的判断。”①Descartes,Regulæ ad Directionem Ingenii,inŒuvres de Descartes,publiées par Charles Adam et Paul Tannery, 1897-1910, Vol.X, p.359; 英译见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translated by John Cottingham, Robert Stoothoff, Dugald Murdo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Vol.I, p.9 ;中译见《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管震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页。本文对笛卡尔著作的引用,首先标国际笛卡尔研究通用的权威本《笛卡尔全集》(由Aham 和Tannery编,简称AT)的卷数及页码,然后标剑桥英译本(简称CSM)的卷数及页码,最后给中译本的页码。此处所引的这本书,笔者没有采用管震湖中译本的书名,但采用了他对这句话的翻译。20年之后他在《第一哲学沉思集》开篇又提到:“如果我想要在科学上建立起某种坚定可靠、经久不变(frmum & mansurum)的东西的话,我就非在我有生之日认真地把我历来信以为真的一切见解统统清除出去,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不可。”①Descartes,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in AT VII 17, AT IX 7; CSM II 12; 中译见《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4页。笛卡尔最初用拉丁文撰写《第一哲学沉思集》,收在AT版《笛卡尔全集》第9卷,该书在笛卡尔生前就有一个法文译本,收在AT版《笛卡尔全集》第9卷,庞景仁先生的中译本就译自这个法文本。本文引用《第一哲学沉思集》的注释先标拉丁文本即AT VII的页码,再标法文本即AT IX的页码,然后标剑桥英译本即CSM II 的页码,最后标庞先生中译本的页码。在采纳庞先生中译的时候直接标中译本页码,有些中译不甚恰当的地方笔者根据英译本重译,在这种情况下则写“参见中译本”。由此可见,追求稳固可靠的知识在笛卡尔哲学思考中始终占据着核心位置。从逻辑上而言,为了获得稳固可靠的知识,首先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人的认识何以会犯错呢?因为只有找到了犯错的根源,才有可能找到避免犯错的方法,然后才有可能获得确切无疑的知识。那么,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笛卡尔又是如何回答错误的来源的问题呢?
一、《第一哲学沉思集》中对错误来源的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
直接看来,在《第一哲学沉思集》的第三沉思与第四沉思中笛卡尔两度涉及人的认识犯错的问题。
在第三沉思第六自然段,笛卡尔对我的思维进行分类:“我的一些思维是关于事物的影像,并且仅在这些情况下‘观念’这个术语才严格适用,比如,当我想起一个人,或一个怪物,或天空,或天使,或上帝。我的其他思维则包含各种附加的形式:当我想要,或害怕,或肯定,或否定的时候,总是存在一个被我当作我的思维之对象的某个特殊事物,但是我的思维中所包含的不仅仅是与该物相似的东西,在这个范畴之内的某些思想被称为意愿或情感,而另一些则被称为判断。”②AT VII 37; AT IX 37; CSM II 25-26;参见中译本第36—37页。显然,我的思维在此被分成三类:观念,意志或情感,判断。前一类思维中仅包含赤裸裸的观念,后两类思维之中除了包含观念还有其他东西。
在接下来第七、八、九三个自然段中笛卡尔说道:“至于观念,如果只就其本身而不把它们牵涉到别的东西上去,真正说来,它们不能是假的;因为不管我想象一只山羊或一个怪物,在我想象上同样都是真实的。也不要害怕在情感或意志里边会有假的;即使我可以希望一些坏事情,或者甚至这些事情永远不存在,但是不能因此就说我对这些事情的希望不是真的。这样,就只剩下判断了。在判断里我应该小心谨慎以免弄错。”①AT VII 37; AT IX 37; CSM II 26;参见中译本第37页。显然,在此笛卡尔的态度很明确,在第一类思维观念里以及在第二类思维意志或情感里都无所谓对错,只有在第三类思维判断里才会有对错。
不管笛卡尔在第三沉思里根据什么原则将我的思维进行分类,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意志与判断分属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类型,在前者里面不可能存在错误,只在后者里面才会有错误。从逻辑上说,我们完全可以由此推出:源于我内心的意志能力是不可能导致错误的,只有我的判断能力才会导致错误。可是,到了第四沉思,笛卡尔对于错误的来源的说法不再如此清晰而是变得扑朔迷离了。
第四沉思的标题就是“论真理与错误”,讨论人的认识何以会犯错显然是这个沉思的主要任务之一。首先在第四自然段笛卡尔说道:“我体验到在我自己的心里有某一种判断能力,这种能力和我所具有的其他一切东西一样,无疑是我从上帝那里接受过来的;而且,因为他不想骗我,所以他肯定没有给我那样的一种判断能力,让我在正当使用它的时候总是弄错。”②AT VII 53-54; AT IX 61-62; CSM II 37-38;中译本第56页。这个说法显然就与第三沉思中的说法不同了,强调我心里的判断能力本身不可能犯错误。我们很自然地要追问:既然判断能力不是认识出错的原因,那认识错误源于何种能力呢?
在第九、十自然段笛卡尔说:“接下来,当我更仔细地检视自己,追问我的各种错误的本质(因为这些错误是我的不完满的唯一证据),我注意到它们取决于两个共同起作用的原因,即我心里的认识能力,还有我心里的选择能力或自由意志;也就是说,它们既取决于理智同时也取决于意志。既然理智所做的就是使我领会那些将要接受判断的观念,而不是肯定或否定任何事情;如果从这个角度严格考察的话,结果就会是,理智不会包含严格意义上所谓的错误。……意志仅仅在于我们做或不做(即去肯定或否定,去追逐或躲避)某事的能力;或者说,意志仅仅在于这一个事实:当理智提出了某些需要肯定或否定,或需要追逐或躲避的事情时,我们的倾向总是如此发挥作用以致我们不会感到我们是被某种外在力量所决定。……我认识到,我错误的原因既不是意志的能力本身……也不是理解的能力或领会的能力……那么我的错误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是从这里产生的,即既然意志比理智大得多、广得多,而我却没有把意志加以同样的限制,反而把它扩展到我所理解不到的东西上去,意志对这些东西既然是无所谓的,于是我就很容易陷于迷惘,并且把恶的当成善的,或者把假的当成真的来选取了。这就使我弄错并且犯了罪。”①AT VII 56-58; AT IX 65-68; CSM II 39-41;参见中译本第59—61页。
这两段话里包含着很多非常奇怪的说法,不过我们暂不仔细分辨,只需指出两点:首先,笛卡尔在这里明确指出理智能力本身不执行下判断的活动因此不必为认识出错负责;其次,他暗示了意志能力与判断活动有密切关系因此对认识出错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说法与第三沉思中将意志与判断划分为不同的思维类型并强调在意志中不可能存在错误的说法明显是相互冲突的。②霍布斯在针对《第一哲学沉思集》的反驳中也指出第四沉思中这个说法与之前的内容有矛盾。可惜的是他并没有深入地追究这个矛盾,只提了一笔,而笛卡尔本人在回应他的反驳时选择性地忽视了他的这个指责。参见AT VII 190-191; AT IX 247-248; CSM II 133-134;中译本第192—193页。于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就认识何以出错这个问题,笛卡尔似乎设了一个迷局,他似乎不想让读者轻易看透他的真实态度。
二、西方知识论传统中的判断
从字面上看,笛卡尔唯一明确承认的只是,认识出错源于判断活动。看来,我们首先必须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何为判断?下判断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活动?
这个问题必须追究到亚里士多德那里才有可能获得比较明确的答案。根据W.D.罗斯的解释,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判断被描述成不是对现实联系的了解,而是在心灵的那些感应之间建立联系(或者在否定判断的情况下,建立划分)。心灵的那些感应也叫‘概念’……在《论灵魂》中所有肯定和否定的判断,都被描述成是‘概念的结合,好像它们是一体’,就好像概念在心灵中是松散的,把它们联系起来就构成判断”。①W.D.罗斯著:《亚里士多德》,王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9页。罗斯还指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命题就是判断的语言表达。②同上书,第30页。
关于命题,我们来看亚里士多德在《解释篇》中的相关说法。第一条:“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有时,我们心中的思想并无正确和错误可言,有时则必然正确或者必然错误。语言也是这样,通过结合与分离它才会产生正确和错误。名词和动词自身,正像没有结合或分离的思想一样,如‘人’,或‘白’,如若不再增加什么,那它便既不是正确的,也不是错误的。”③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9页(原文翻译参照亚里士多德《解释篇》,16a1-15)。第四条:“所有的句子都有意义……并非任何句子都是命题,只有那些自身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句子才是命题。真实或虚假并不为任何句子所有,例如祈祷就是既无真实也无虚假可言的句子。”④同上书,第52页(《解释篇》17a1-5)。第五条:“所有命题都含有一个动词或一种动词的时态,甚至‘人’的定义,如若不增加‘现在是’、‘过去是’、‘将来是’或某些这一类的词,那么它就根本无法形成命题。”⑤同上书,第52页(《解释篇》17a10-15)。第九条,“关于现在或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判断,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的,必然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⑥同上书,第57页(《解释篇》18a25-30)。
结合亚里士多德本人的说法与罗斯的解释,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当一个个独立的概念或观念相互之间没有关联、毫无秩序地共存于我们的意识中的时候,我们就处于混乱无知的状态;只有当我们用系词“是”将指称某物的名词与表达谓述的各种词语联系起来我们才对某物下了判断,也就是说出了一个命题,这样我们才拥有了关于某物的知识,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关于某物的说法才有可能是对的或错的;有些时候我们为了表达自己的情感或愿望或出于其他的目的也会说出各种句子,也会将名词与各种其他的词相连接,但只要我们没有对事物下判断,我们说出来的就不是命题,也就无所谓对错。
仔细琢磨亚里士多德这里的说法,我们不难发现这与笛卡尔在第三沉思第七、八、九三个自然段所说的意思几乎完全一样。亚里士多德说一个个单独的词如“人”、“白”等等是无所谓对错的,这相当于笛卡尔说观念本身无所谓真假。亚里士多德说表达祈祷的句子无所谓真假,就相当于笛卡尔说在情感与意志里不会有假。而亚里士多德与笛卡尔都明确说到在只有在判断里才会有真假对错。
在西方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的重要地位就在于它规定了科学语言的根本格式。从此之后,凡研究讨论知识的人都一致公认,关于某物的知识应该借助命题来表达,所有的命题都以一个关于对象的判断活动为前提,所有的命题中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了系词“是”。对于这样一个在西方知识论讨论中根本无须重申的前提,笛卡尔显然心知肚明,我们可以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找到明显的证据。在第三沉思的第二自然段中,笛卡尔说过这样一句话:“在这个知识的首个条目中,仅仅存在一个关于我所断定的东西的清楚明白的知觉”①AT VII 35; AT IX 34; CSM II 24;参见中译本第35页。。这句话的英文是:In this frst item of knowledge there is simply a clear and distinct perception of what I am asserting.拉丁文是 :Nempe in hac primà cognition nilil alind est, quàm clara quædam &distinct perception ejus quod affrmo.这里的英文 asserting和拉丁文 affrmo显然指的都是下判断的活动。
三、第二沉思中的理智能力与判断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在笛卡尔这里,下判断的活动到底来自人心的哪种能力?下判断分明是我们形成知识的一个必要程序,难道它真的不是源于人心中的理智能力?
在第二沉思讨论我们如何获得关于蜡的知识的时候,笛卡尔有些说法对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问题很有参考价值。第十三自然段中他说道:“我必须承认这一块蜡的本性根本不是被我的想象揭示出来,而是仅仅被我的心灵知觉到的……在此最为关键的是,我所拥有的关于它的知觉既不是视觉,也不是触觉、也不是想象知觉—不是曾经所是的任何一种知觉,尽管以前看上去像是—而是一种心灵检查的知觉。”①AT VII 31; AT IX 28; CSM II 21;参见中译本第31页。紧接着在第十四自然段又说:“但是当我得到这个结论时,我很惊讶我的精神是如何容易犯错。因为,即使我内心中正在思考这些事情,未发一言地沉默进行,但是那熏陶培养我的现实语言却有缺陷,我几乎要被平常的说话方式欺骗了。如果蜡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总说我们看见了蜡本身,却不说我们根据其色彩形状而判断它在那儿;这很可能导致我立即下结论说关于蜡的知识来自眼睛所看到的东西,而不是仅仅来自心灵的审视。但是,此刻如果我往窗外看去并且看见人们穿过广场,正如我刚才碰巧所做的那样,通常我会说我看见了这些人本身,就如同我说我看见了蜡那样。可是,除了可以遮盖住一些自动机的帽子和外套,难道我还看见了别的什么?我判断他们是一些人。因此,那些我以为我正在用我的眼睛观看的东西,事实上只是被我心灵中的判断能力把握了。”②AT VII 31-32; AT IX 28-29; CSM II 21;参见中译本第31页。第十五自然段还有:“当我将蜡与它的外在形式相区别—就好像脱掉衣服那样,并且赤裸裸地考虑它—的时候,尽管我的判断仍然可能包含错误,不过至少我的知觉现在需要一个人类心灵。”③AT VII 32; AT IX 29-30; CSM II 21-22;参见中译本第32页。
显然在这里笛卡尔反反复复地强调,我不是借助于感官,也不是借助于想象,而是借助于心灵中判断能力获得关于外物的知识,也即对外物下判断。在这些讨论中笛卡尔根本就没有说我的判断活动与意志能力有任何关系。核对笛卡尔本人的用词,我们发现,第二沉思中“心灵”一词,拉丁文都是mens,法文大多数是esprit,有时是entendement,英文统一译成mind。而我们上文所引的第四沉思第九自然段中与意志能力并列的那个“理智”能力,拉丁文是intellectus,法文是entendement。在第四沉思第十自然段与意志能力并列那个“理解”能力,一处拉丁文是intelligendi,法文是la puissance d’entendre;一处拉丁文是intellectus,法文是entendement。我们看到,法文entendement这个词在第二沉思与第四沉思中都用过,由法文用词似乎可以推出:笛卡尔在第二沉思中所说的那个执行下判断活动的“心灵”就是第四沉思中的那个他号称不下判断的“理智”。不过两个沉思中拉丁文用词似乎并不相同。好在我们还可以找到另外一些佐证,在第二沉思第七自然段关于我的本质下了一个定义:“严格意义上我只是一个思维的东西,也即,我是一个心灵、智力、理智、理性,这些词的意思我以前是不知道的。”①AT VII 27; AT IX 22; CSM II 18;参见中译本第26页。为解释“思维的东西”笛卡尔给出了四个同位语,拉丁文是:mens, animus, intellectus, ratio。由此可以推出,在笛卡尔这里,拉丁文的mens与intellectus很可能是可以互换的,至少二者的功能、发挥的作用应该是相同的。
通过这番考察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第二沉思中笛卡尔确实认为是我的理智能力执行了下判断的活动使我获得了知识。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轻易相信第四沉思中理智不下判断的说法了。看来,我们必须对第四沉思中的下判断活动进行一番仔细的考察了。
四、意志的选择活动中所包含的判断活动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笛卡尔在第四沉思中到底如何描述意志能力与下判断活动之间的关系。为此必须再次仔细检查第四沉思第九自然段:“当我更仔细地检视自己,追问我的各种错误的本质(因为这些错误是我的不完满的唯一证据),我注意到它们取决于两个共同起作用的原因,即我心里的认识能力,还有我心里的选择能力或自由意志;也就是说,它们既取决于理智同时也取决于意志。既然理智所做的就是使我领会那些将要接受判断的观念,而不是肯定或否定任何事情;如果从这个角度严格考察的话,结果就会是,理智不会包含严格意义上所谓的错误。……意志仅仅在于我们做或不做(即去肯定或否定,去追逐或躲避)某事的能力;或者说,意志仅仅在于这一个事实:当理智提出了某些需要肯定或否定,或需要追逐或躲避的事情时,我们的倾向总是如此发挥作用以致我们不会感到我们是被某种外在力量所决定。”①AT VII 56-57; AT IX 65-67; CSM II 39-40;参见中译本第59—60页。在这段话中,笛卡尔对理智能力的界定是:“理智所做的就是使我领会那些将要接受判断的观念,而不是肯定或否定任何事情”,由此看来判断活动似乎就等同为肯定或否定的活动。他对意志能力的描述则是:“意志仅仅在于我们做或不做(即去肯定或否定,去追逐或躲避)某事的能力”。这样一来,读者很容易认为意志能力就是肯定或否定某事的能力,也就是说意志能力在执行下判断的活动。
可是,如果我们仔细推敲的话,就会发现这里有些不对劲。在这段话中,笛卡尔第一次提及意志的时候就明确交代了这是一种选择能力,然后他用三个短语来描述意志能力:“做或不做某事”、“肯定或否定某事”、“追逐或躲避某事”。这其中“做或不做某事”与“追逐或躲避某事”显然都只是行动层面的选择活动,不是认知层面的下判断活动。只剩下“肯定或否定某事”与下判断活动似乎有关。可是,意志这种明明是在行动层面发挥作用的选择能力如何又能执行在认识层面上所必需的下判断的活动呢?如果我们将笛卡尔在描述意志时所说的“肯定或否定”与“做或不做某事”、“追逐或躲避某事”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发现这里更应该是一种价值判断:断定某事是好的即肯定某事,于是我们就决定去做、去追逐,断定某事是不好的即否定某事,我们就不做、就躲避。也就是说,意志在行动层面上的选择活动必须以价值判断为前提。或者也可以说,意志在行动层面上的选择活动中包含了一个价值判断。
既然笛卡尔在这里所暗示的意志下判断活动其实只是一个价值判断而非纯粹知识判断,那么由此可以推出,笛卡尔所说的由意志不加节制地肯定或否定而导致的错误也应该是行动层面上的错而不是知识层面的错了。果然,第十自然段对于错误来源的最正式的总结是这样的:“那么我的错误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是从这里产生的,即既然意志比理智大得多、广得多,而我却没有把意志加以同样的限制,反而把它扩展到我所理解不到的东西上去,意志对这些东西既然是无所谓的,于是我就很容易陷于迷惘,并且把恶的当成善的,或者把假的当成真的来选取了。这就使我弄错并且犯了罪。”①AT VII 58; AT IX 68; CSM II 40-41;中译本第61页。此处拉丁文本与法文本不完全相同,本文此处采用了法文本及庞先生的中译本。在这里,说到意志不加节制地肯定或否定而导致错误的时候,迫于逻辑的需要,笛卡尔首先必须说意志“把恶的当成善的”,这显然是由于价值判断失误而导致的行动层面的犯罪,后面才顺便加上“把假的当成真的”这个知识层面的犯错,在最后下结论的时候他又巧妙地把“弄错”放在“犯罪”的前面,这样就显得他已经回答了认识犯错源于何处,虽然实际上他回答的只是行动犯罪源于何处。
我们已经看清了,在第四沉思中第九、十两个自然段,笛卡尔非常狡猾地将意志选择活动所必需的价值判断偷换为认识层面上的判断,这样他就制造出一个似乎由意志能力执行下判断活动的假象。不过,制造了这个假象的笛卡尔本人并不糊涂:其实他从未明确地说意志能力执行了下判断活动,他只是说意志肯定或否定某事;并且他从未说过意志能力是判断能力,相反他一再强调意志能力是选择能力。哪怕在得出意志能力必须为认识犯错负一定责任的结论之时,他仍然没有忘记把意志能力正在进行的活动描述为选择活动。比如第十自然段的结尾:“意志对这些东西既然是无所谓的,于是我就很容易陷于迷惘,并且把恶的当成善的,或者把假的当成真的来选取了。这就使我弄错并且犯了罪。”还有第十三自然段:“如果在我并没有足够清楚明白地领会到真理的情况下我限制自己下判断,那么很明显我行事正确并且避免了错误。但是,如果我或者肯定或者否定,那么我就没有正确地使用我的自由意志了。如果我赞成那本是错误的选项,那么显然我将会犯错;如果我选了另外一方,那也不过碰巧达到了真理,我仍然犯了错误,因为由自然之光理智的领会明显应该总是先于意志的决定。”①AT VII 59-60; AT IX 70; CSM II 41;参见中译本第62—63页。
五、认识中的判断活动被打扮成选择活动
笛卡尔在第四沉思中之所以能制造出作为选择能力的意志却执行了判断活动的假象,一方面固然归因于他将意志的选择活动中所包含价值判断偷换成认识判断,更关键的还是取决于他将认识中的判断活动打扮成选择活动。
这个工作在第四沉思第九自然段开头界定理智能力时其实已经开始了。他说“理智所做的就是使我领会那些将要接受判断的观念,而不是肯定或否定任何事情”,这样的说法诱使读者以为判断活动就等同为肯定或否定的活动。可是,认识中的判断活动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活动呢?上文已经指出过,根据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知识论传统,只有当我们用系词“是”将指称某物的名词与表达谓述的各种词语联系起来我们才对某物下了判断,也就是说,认识活动中的判断只是断定“某物是……”。判断分为很多种,亚里士多德本人对判断是这样分类的:按照质将判断分为肯定判断与否定判断,按照量将判断分为全称判断、特称判断、不确定判断;按照模态将判断分为现实判断、可能判断、必然判断三类。亚里士多德在说到判断时,有时为方便简单起见,只罗列出肯定或否定这两类判断,比如在上文所引《解释篇》第九条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判断只有肯定与否定这两类,下判断的活动只是说“某物是……”或“某物不是……”。搞清楚了在亚里士多德以来知识论传统中判断所指为何之后,我们也就明白了笛卡尔其实刻意将认识过程中的判断活动简化为肯定或否定的活动,这种做法的好处就是使得判断活动与选择活动有一些表面的相似。
不过这个打扮工作主要发生在第十一自然段。我们已经说过,在第十自然段最后总结意志的不加节制的肯定或否定行为如何导致认识出错的时候,笛卡尔迫于逻辑的需要不得不先说行动层面的犯罪再说认识层面的犯错。也就是说,此刻他暴露了自己将价值判断偷换为认识判断的做法。于是接下来他要努力清洗掉自己所提供的这个错误产生机制中包含的价值判断的痕迹。换言之,他要努力证明自己这里所说的判断是纯粹的认识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
在第十一自然段他开始举例说明:“举例来说,过去这几天我检查了是否有什么东西在世界上存在,并且认识到仅仅由于我检查了这一问题,因而显然我自己是存在的,于是我就不得不做这样的判断,即我领会得如此清楚的一件事是真的,不是由于什么外部的原因强迫我这样做,而仅仅是因为在我的理智里边的一个巨大的清楚性,随之而来的就是在我的意志里边有一个强烈的倾向;并且我越是觉得不那么无所谓,我就越是自由地去相信。”①AT VII 58-59; AT IX 68-69; CSM II 41;参见中译本第61—62页。这里是一个正面的例子,描述了我如何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在这个过程中,不是理智能力本身下判断,理智只负责清楚地领会某物;也不是意志能力本身下判断,笛卡尔只是说理智里面的巨大的清楚性带来了意志里的一个强烈的倾向,似乎是意志里的这个倾向使得我下了判断。
他接着说:“相反,目前我不仅知道由于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什么东西因而我存在,而且在我心里出现某一种关于物体性的本性的观念,这使我怀疑在我之内的这个在思维着的本性,或者不如说,我之所以为我的那个东西是否与这个物体性的本性不同,或者是否二者是一个东西。我现在假定我还不认识有任何理由使我相信后一种而不相信前一种。因此对于否定它或肯定它,或者甚至不去加以任何判断,我都完全无所谓。”①AT VII 59; AT IX 69; CSM II 41;参见中译本第62页。这里说的是,当理智不能清楚明白地认识到某物或某事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随随便便地对它下判断。我们发现,在这个例子中,笛卡尔把下判断说成“认为思维的我与物体性相同”或“认为思维的我与物体性不同”,这样判断活动就被说成是或者“肯定某物是……”或者“否定某物是……”,最终下判断活动就被打扮成一种在肯定项或否定项之间进行选择的行为。上文已经指出,在我们的认识活动中,下判断不过是说“某物是……”,肯定判断和否定判断并不构成所有的判断,除此之外还有好多种判断类型。尤其是当我们还没有清楚明白地领会到某物的时候,正确的做法是我们根本不说“某物是……”,而不是不在“某物是A”与“某物不是A”之间做一个选择。
在经过了这一番仔细打扮之后,笛卡尔终于可以在第十三自然段就认识犯错的来源给出一个纯粹知识论版本而不掺杂丝毫价值色彩的解释了:“但是,如果在我并没有足够清楚明白地领会到真理的情况下我限制自己下判断,那么很明显我行事正确并且避免了错误。但是,如果我或者肯定或者否定,那么我就没有正确地使用我的自由意志了。如果我赞成那本是错误的选项,那么显然我将会犯错;如果我选了另外一方,那也不过碰巧达到了真理,我仍然犯了错误,因为由自然之光理智的领会明显应该总是先于意志的决定。”②AT VII 59-60; AT IX 70; CSM II 41;参见中译本第62—63页。这段话第一句说在理智没有获得清楚明白的知觉之前正确的做法是不下判断,第二句话说的是如果意志在此时进行了肯定或否定活动那就犯错误了,将这两句话联系起来这里的意思显然是肯定或否定活动就是下判断的活动了,然后第三句话再将意志的活动描述为在两个选项之间进行选择的活动。如果没有第九自然段在界定理智能力时所做的那个铺垫以及第十一自然段将判断活动打扮成选择活动,那么就不可能如此水到渠成地得出这里的结论了。这之后笛卡尔再顺理成章地加上一句最概括性的总结:“在自由意志的不正确的使用中可以找到那个构成错误之本质的缺陷。”①AT VII 60; AT IX 70; CSM II 41;参见中译本第63页。这样一来笛卡尔就让意志为认识犯错承担了主要责任。
六、第四沉思讨论认识犯错的语境
我们的分析已经表明,在第四沉思中笛卡尔之所以能制造出意志执行下判断活动的迷局,并且成功地让意志为认识犯错承担主要责任,取决于他在这个过程中做了两次“越轨”之举:一是将意志选择活动中所包含的价值判断偷换为认识判断,二是将认识活动中的下判断活动打扮成在两个认识结论之间做选择的活动。揭开了这个迷局的本来的面目之后,我们面临的下一个问题自然就是:如此陈仓暗度、处心积虑、费尽周折,到底又是为哪般?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搞清楚,进入第四沉思后,笛卡尔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考察认识犯错的来源问题。为此我们必须回到这本书开篇第一句:“由于很久以来我就感觉到我自从幼年时期起就把一大堆错误的见解当作真实的接受过来,而从那时以后我根据一些非常靠不住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东西都不能不是十分可疑、十分不可靠的,因此我认为,如果我想要在科学上建立起某种坚定可靠、经久不变的东西的话,我就非在我有生之日认真地把我历来信以为真的一切见解统统清除出去,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不可。”②AT VII 17; AT IX 7; CSM II 12;参见中译本第14页。这一句不仅表明笛卡尔的最终目的是要在知识上建立起某种经久不变的东西,也即所谓重建稳固的知识大厦,而且指出了第一沉思的目的是清除一切错误的旧见解,或者说摧毁旧的知识体系。那么笛卡尔认为一切旧见解都不可靠的理由是什么呢?
在第一沉思第十二自然段,笛卡尔说了这样一番话:“我要假定有某一个妖怪,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上帝(他是至上的真理的源泉),这个妖怪的狡诈和欺骗手段不亚于他本领的强大,他用尽了他的机智来骗我。我要认为天、空气、地、颜色、形状、声音以及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外界事物都不过是他用力骗取我轻信的一些假象和骗局。我要把我自己看成是本来就没有手,没有眼睛,没有血,什么感官都没有,而却错误地相信我有这些东西。”①AT VII 22; AT IX 15; CSM II 15;参见中译本第20页。这话的意思是,我以往关于外物的一切知识之所以是错误的乃是因为它们都是妖怪欺骗我的结果。
笛卡尔为何要假设一个骗人的妖怪呢?在《第一哲学沉思集》所附的第五组反驳中,伽森狄就明确地对此提出质疑:“为什么你不愿意直截了当用很少的几句话把你一直到那时所认识的全部事物都假定是不可靠的(以便然后再把你承认是真实的那些事物挑拣出来),而宁愿把它们都假定是错误的,不惜从一个旧成见中解脱出来,去采取一个另外的、完全新的成见。你看,为了得出这个结论,你如何不得不假想一个骗人的上帝或一个什么样的恶魔用了他的全部心机来捉弄你,虽然只要把你不信任的理由归之于人类精神的不明智和仅仅是本性的弱点似乎就行了……对事情直截了当,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地加以说明,而不是像人们将会反对你的那样,装腔作势,弄虚作假,追求拐弯抹角、稀奇古怪的东西,岂不是更适合于一个哲学家的坦率精神,更适合于追求真理的热诚态度吗?”②AT VII 257-258; CSM II 180;中译本第260—261页。伽森狄对笛卡尔的这一组反驳AT IX中没有收入。这一番诚恳而尖锐的批评表明伽森狄认为在这里假设妖怪是哗众取宠的败笔。
笛卡尔这样回答伽森狄的批评:“一个哲学家……不会说什么只要在这个地方把我们不信任的理由归之于人类精神的不明智或者我们本性的弱点就行了。因为,为了改正我们的错误,用不着说我们之所以犯错误就是由于我们的精神不很明智,或者由于我们的本性残缺不全;因为这和我们说我们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我们本来就好犯错误是一样的。”③AT VII 349; CSM II 242;中译本第352—353页。这个回答表明,笛卡尔并不认为我们的认识能力本身有缺陷,我们以往的认识犯错只是由于我们受到某个强大的骗子的欺骗罢了。那么这个强大的骗子所指为何呢?在第一沉思第十三自然段,笛卡尔还说强大的骗子和我们长期相处以致成为支配我们信念的主人,它们描画了许多愉快的幻象,我们受它们的支配就好像一个奴隶在睡梦中享受一种虚构的自由。根据这些说法,结合时代背景,不难推出那个强大的骗子就是《圣经》中所描述的那个至高无上的、拥有一切权力、决定世间万物当然也包括人类的命运的天父了。①这并非笔者的臆测,Hiram Caton也持同样的观点,参见Hiram Caton,The Origin of Subjectivity,an Essay on Descartes,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116。说得更明确一些,在第一沉思中,笛卡尔指出,我们的旧知识体系之所以错漏百出、摇摇欲坠是因为它建立在谎言与迷信的基础之上,我们只有把旧的知识体系连根摧毁才有可能找到一块稳固的基石重建新的知识大厦。
在第二沉思中笛卡尔确立了纯粹的思维的我是确实存在、不可怀疑的,然后在第三沉思第二自然段宣布“凡是我清楚明白地认识到的都是真的”,这就意味着将纯思的我确立为新知识大厦的基石。第三沉思第五自然段,笛卡尔决定要来证明存在一个完满的、绝不骗人的上帝,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终确保凡是我所清楚明白地认识到的都是真的。这就是第三沉思的主要工作,完成这个证明工作之后,笛卡尔在第三沉思第四十自然段以及第四沉思第三自然段宣布完满的上帝绝不会欺骗我们,然后笛卡尔正式开始讨论我们的认识何以犯错的问题。
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刻来讨论这个问题呢?这其中的奥秘在于“完满的上帝不会欺骗我们”这个宣言背后所蕴含的立场。笛卡尔本人虽然两度发布这个宣言,但都没有对此给出进一步的解释。可是上帝绝不骗人这个说法并不符合正统基督教的立场,因为基督教认为人类达不到上帝那样的全知,因此上帝完全可以出于对人类的善意而欺骗那根本无法认清真相的人类,就好像医生为了让身患绝症却又不敢直面死亡的病人能够活得更长、更安心一些而欺骗他,说他患的病并不严重,又好像父亲为了让那些无知鲁莽倔强的小孩远离危险而说出各种谎言。①事实上,针对笛卡尔这个上帝绝不骗人的说法,《第一哲学沉思集》后面所附的第二、第三、第六组反驳都进行了批评,参见AT VII 125-126, 195, 415; AT IX 161-162, 254, 346; CSM II 89-90,136, 279-280;中译本第129—130、197、400页。可以说,承认善意的谎言的前提是承认人类理智不可能达到与上帝理智同等的程度,认定完满的上帝绝不会骗人的前提则是认定人类理智已经完满到不可能受骗。当然,胆小谨慎的笛卡尔不可能直接亮出违背基督教传统的观点。退一万步讲,就算教会人士不去攻击笛卡尔认定人类认识能力本身完满无缺陷的做法是骄傲狂悖,仅从逻辑本身而言,笛卡尔也绝不敢直接夸口说只要排除了谎言与迷信的干扰,我们的认识就绝对不会犯错误。他必须先对我们的认识活动本身做一番原则性的考察,必须先说清楚我们的认识能力怎样行事就会犯错,只有说清这一点之后他才有可能保证我们绝不踏入犯错的歧途,然后才能宣布我们可以对自己清楚明白的认识持绝对的信心。
七、借用神义论的问题框架
一旦辨明了笛卡尔在什么样的前提下以及为了何种目的而讨论认识犯错的问题,我们就不难理解他在第四沉思中讨论这个问题时所采取的貌似奇怪的路径。
笛卡尔在这个沉思的第四自然段正式进入这个讨论主题,其实他在这段第一句就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态度:“我体验到在我自己的心里有某一种判断能力,这种能力和我所具有的其他一切东西一样,无疑是我从上帝那里接受过来的;而且,因为他不想骗我,所以他肯定没有给我那样的一种判断能力,让我在正当使用它的时候总是弄错。”②AT VII 53-54; AT IX 61-62; CSM II 37-38;参见中译本第56页。上文已经说过,人的认识活动中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下判断,因此判断能力构成人的认识能力中的最核心部分,断定人的判断能力在正常使用时不会出错其实就意味着认定人的认识能力在本性上完满没有缺陷。当然,为了表明自己恪守基督教传统,笛卡尔这里必须说判断能力来自上帝,上帝出于仁慈不会给人一种在正常使用时会出错的能力。
可是,正如上文分析过的,就算人的认识能力在本性是完满够用的,笛卡尔也不敢说人类在实际认识过程中就可以做到绝不犯错,因此第一句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态度之后第二句话又改变了口气:“如果不是我刚才所说的似乎包含着我根本不会犯错的意思,那么对这一点就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①AT VII 54; AT IX 62; CSM II 38;参见中译本第56页。于是他接下来就开始寻找认识犯错的原因了:“如果凡是我所有的都是来自上帝的,如果他没有给我弄错的能力,那么就应该说,我决不应该弄错。真的,当我单单想到上帝时,我想心里并没有发现什么错或假的原因;可是,后来,当我回到我自己身上来的时候,经验告诉我,我还是会犯无数错误的,而在仔细追寻这些错误的原因时,我注意到在我的思维中不仅出现一个实在的、肯定的上帝观念,或者一个至上完满的存在体的观念,同时,姑且这样说,也出现一个否定的、‘无’的观念,也就是说,与各种类型的完满性完全相反的观念;而我好像就是介乎上帝与无之间的,也就是说,我被放在至上存在体与非存在体之间,这使得我,就我是由一个至上存在体产生的而言,在我心里实在说来没有什么东西引导我到错误上去;但是,如果我把我看成是以某种方式分享了无或非存在体,也就是说,由于我自己并不是至上存在体,我处于一种无限缺陷的状态中,因此我不必奇怪我是会弄错的。”②AT VII 54; AT IX 62; CSM II 38;中译本第56—57页。
这些说法虽然强调上帝不能为人的错误认识负责并且谦虚地承认了人类理智的局限,但是与基督教的教义并不完全相符,因为这里明显是一种二元论的立场,带上了古代异教哲学的色彩,于是他在第五自然段不嫌麻烦地再来对自己的立场做一番总结:“这样一来,我认识到,就其作为错误而言,并不取决于上帝的什么实在的东西,而仅仅是一种缺陷,从而对于犯错误来说,我不需要有上帝专门为这个目的而给我什么能力,而是我所以有时弄错是由于上帝给了我去分辨真和假的能力对我来说并不是无限的。”①AT VII 54; AT IX 63; CSM II 37-38;中译本第57页。这个总结看上去更符合基督教传统,因为笛卡尔在这里抹去了古代哲学的痕迹,只是承认上帝给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
可是,我们已经详细分析过,“完满的上帝绝不欺骗我们”这个立场必然蕴含着“人类成熟到不可能被欺骗”这个前提,所以,从逻辑上说,笛卡尔绝不会主张人类理智在本质上是有局限性的,第四自然段第二句之后以及第五自然段那些谦虚的说法其实都是自保之词,在第六自然段笛卡尔最终还是想办法回到了自己的真实态度:“虽然如此,我还不完全满足;因为,错误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否定,也就是说,不是单纯的缺陷或者缺少我不应该有的什么完满性,而是缺少我似乎应该具有的什么认识。”②AT VII 55; AT IX 63; CSM II 38;中译本第57页。话虽说得有些绕口,但意思还是很明白的:完满的认识能力是我本性应该具有的能力,并不是我本性不配有的能力,所以犯错不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就我的本性而言我不应该犯错。真实的意思已经表达,当然还要尽量保持低调,小心不要被指控为骄傲僭越,必须将荣誉归于上帝,所以要宣布我所拥有的认识能力无论怎么完满都是源于上帝的恩赐:“而且,在考虑上帝的性质时,我认为,如果说他给了我某种在本性上就是不完满的或是缺少它应该具有的某种完满性的功能的话,这是不可能的。工匠越是精巧熟练,从他的手里做出来的作品就越是完满,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由一切事物的至高无上的创造者所产生的任何东西怎么可能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完全并完满呢?”③同上。
可是,就算全能、全善的上帝所创造的我在本性上就应该是完满、不会犯错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犯错误却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在第二次正式表达了自己对人类理智之完满性的坚定信念之后,笛卡尔还是得折回头来第二次追问人类认识犯错的根源。然而,这一次,笛卡尔没有像第一次那样直接“追寻这些错误的原因”,他换了一种提问方式:“而且,毫无疑问,上帝可以给我一种本性使得我从不犯错;加上,毫无疑问,上帝总希望最好的东西。那么,难道我可能犯错要好于我不应该犯错吗?”①AT VII 55; AT IX 63; CSM II 38;参见中译本第57—58页。句中标为黑体的那个分句,庞先生的中译是“毫无疑问,上帝没有能把我创造得永远不能弄错”,这句的法文是Et certes il n’y a point de doute que Dieu n’ait peu me créer tel que je ne me peusse jamais tromper;拉丁文是 Nec dubium est quin potuerit Deus me talem creare, ut nunquam fallerer;英译是 There is, moreover, no doubt that God could have given me a nature such that I was never mistaken。对比法文、拉丁文、英译,显然庞先生中译有误,严格根据法文本应该把这句译成:“当然,我们不能怀疑上帝能把我创造得永不犯错。”这个意思是指,上帝能够把我创造得永不犯错。表面上看来,狡猾的笛卡尔在这里将皮球踢到上帝那里去了:既然我是上帝的造物,既然全能全善的上帝有能力、也愿意赋予我完满的认识能力,那么他又怎么会让我常常犯错呢?稍加琢磨,我们就能发现,笛卡尔这里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改头换面的神义论问题。基督教神学中传统的神义论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那么出于他的知识、能力与善意,他都会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他又如何能够允许这个世界上出现各种自然灾难和邪恶的社会现象呢?
对于神义论问题,传统神学讨论中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回答就是:上帝的理智超越了人类的理智,人类不可能真正理解上帝的所有作为,在这些灾难丑恶最初出现的时候我们肯定理解不了,但我们应该凭着对上帝坚定信心忍耐这些苦难打击,在经历了所有这一切之后我们最终能够理解上帝的美意。神学讨论中对神义论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常见的回答:我们必须从宏观整体上来理解上帝的创世活动,有些事情从局部看来是灾难或丑恶,但对于整体则是有利的,就好比一个画家不会在画布的所有区域都涂上同样鲜艳明亮的色彩,他会让某些部分亮丽一些某些部分暗淡一些,这样才能保证整体的和谐。在第七、八两个自然段,笛卡尔对于“上帝何以会允许我犯错”这个问题提供了与这两种答案非常类似的回答。由于这里都没有涉及人类认识活动本身,在此就不详谈。
第九到第十三自然段是第四沉思的核心部分,上文已经分析过,笛卡尔在此做的主要工作是,将错误的产生归结为意志在理智尚未获得清楚明白的知觉的前提下就贸然地进行肯定或否定活动。在第十三自然段最终的结论是这样表达的:“在自由意志的不正确的使用中可以找到那个构成错误之本质的缺陷。这种缺陷,我以为,在于自由意志的运用,就这种运用来自我,而不是我从上帝那里获得的意志能力而言,这种缺陷甚至不在于其依赖上帝的那种运用。”①AT VII 60; AT IX 70; CSM II 41;参见中译本第63页。为什么笛卡尔最终要让自由意志为认识犯错负责呢?表面看来,这个结论是在回答第六自然段那个改头换面的神义论问题:全能全善的上帝原本可以把我创造得绝不犯错,他又为何让我常常犯错呢?对于正统的神义论问题“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中怎么会有恶存在?”,奥古斯丁的回答成为基督教神学中比较权威的版本:上帝不须为恶负责,恶源于人滥用上帝赋予的自由意志,如果自由意志促使人服从肉体欲望而不追求理智揭示出来的善,就会产生各种恶。当笛卡尔说错误不来自上帝,而是源于人误用了上帝赋予的自由意志的时候,他对错误来源的回答与奥古斯丁对恶的来源的回答几乎是一样的。面对如此中规中矩的回答,谁还忍心怀疑笛卡尔的谦卑与虔诚呢?
可是,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笛卡尔为什么非要把认识层面的犯错与行动层面的犯罪纠缠在一起呢?为什么他一定要借用神义论的问题框架来讨论错误认识的来源?到此为止,我们应该不难辨认出他这样做的真实动机了。我们看到,笛卡尔这番讨论的直接结论是人的认识犯错不是由于上帝给人的认识能力不够用而是由于人误用上帝给予的自由意志。这个结论其实意味着在承认人之为人的局限的前提下不让人的理智能力为认识犯错承担直接的、主要的责任。这个结果恰恰是笛卡尔最需要的。上文已经说过,在第四沉思开始讨论认识何以犯错的问题之前,笛卡尔已经公开宣布过“完满的上帝不会骗人”,而这个宣言其实蕴含着“人类理智本身是完满够用的”这个前提。但是,在没有仔细考察认识何以犯错之前,笛卡尔绝不敢宣布我们可以对自己的理智能力持绝对的信心。如今,在经过第四沉思这一番仔细的探讨之后笛卡尔成功地将认识犯错的责任推到了意志头上,这样他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宣布我们可以绝对相信自己的理智能力了。事实上,第四沉思就是这样结尾的:“今天我不但知道了必须避免什么才能不致犯错误,而且也知道了我必须做什么才能认识真理。因为,如果我把我的注意力充分地放在凡是我领会得完满的事物上,如果我把这些事物从其余的、我所理解得糊里糊涂的事物中分别出来,我当然就会认识真理。这就是我今后将要认真加以注意的。”①AT VII 62; AT IX 74; CSM II 43;中译本第65—66页。这个结尾其实就是在宣布:从此以后,我们对于自己清楚明白地认识到的东西再也不必持怀疑的态度了。第一沉思中提出来的普遍怀疑的态度在此被彻底终结了。
八、不合法的借用
我们已经查明,为了不让人的理智能力为错误的认识负责,笛卡尔在第四沉思中借用了神义论的问题框架来讨论认识犯错的来源问题,他最终的结论是认识犯错源于我们误用了上帝给予的自由意志,这就使得他对错误来源的回答与奥古斯丁对恶的来源的回答几乎是一样的。留给本文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这种借用在逻辑上是否合法?上文已经指出,在笛卡尔制造意志为错误负责的迷局的过程中最关键的一个手法就是将意志选择行为所需要的价值判断偷换为认识判断。可是,如果价值判断与认识判断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那我们甚至都没有理由指责笛卡尔在这里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
那么,认识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区别何在?简单地说,认识判断只是声称“某物是……”,这个判断使我们获得关于对象的客观的知识,在我们就对象本身下一个认识判断的过程中,我们根本不必也不能考虑对象与这个下判断的我之间的关系,而且也不能将我个人对这个对象的主观情感掺杂进来。价值判断则是声称“某物是好的”或“某物是坏的”,这个好或坏的标准常常由下判断的我来决定,尤其是在意志对某物或某事进行选择的时候所需要的价值判断常常就只是考虑这个事或物对自己是好的还是坏的。
仅从原则上抽象地分析价值判断与认识判断的区别还不足以揭示笛卡尔是在玩偷换概念的把戏,我们还必须将行动层面上犯罪的内在机制与认识层面上犯错的内在机制做一番具体的分析比较。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被迫在做某事与不做某事之间进行选择,这个时候如果你判断做某事对你是好的你就会去做,如果你判断做某事对你是坏的你就不会做。这个时候如果你下了一个错误的价值判断,即把那个对你是坏的事情当作对你是好的事情去做了,那么你就犯罪了,或者相反,把那个对你是好的事情当作对你是坏的而拒绝了,那么你其实也是犯了罪,只是带来的恶劣后果可能相对小一些。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你会下一个错误的价值判断?按照奥古斯丁的说法,上帝给予人类自由意志是为了让人类利用它来追求理智揭示出来的善,但如果人类却利用自由意志追求各种低级欲望的满足,那么人类就误用了上帝给予的自由意志,于是就犯了罪。举个具体的例子:如果你现在非常饿又没有钱买食物,你走进一家食品店,发现售货员非常忙碌好像根本没有注意你,这个时候你就面临着偷食物还是不偷食物的选择。如果你认识到偷盗很可能被人发现,被发现的结果或是进监狱或是被人痛打或唾骂,就算侥幸没有被发现暂时救了你的身体,可是偷盗的人在身体消亡之后灵魂很可能下地狱受苦,这样一想的话偷盗带来的所有结果都是你无法忍受的,于是你就认定偷盗是坏的,就坚决不去偷盗,哪怕是饿死。相反,如果你此刻实在是难以忍受腹中的饥饿,于是就告诉自己说再不偷一口东西吃就会被饿死,而人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了,死亡才是最可怕的,于是你就会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偷一口食物不是什么十恶不赦之罪而是一种权宜之计,于是你就下定决心去偷了。很显然,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是出于满足生理欲望的需要而做出了错误的价值判断并进一步犯了罪。当然,在日常生活中并非所有错误的价值判断都是为了满足生理欲望,许多时候人们是为了追逐眼前的利益或是今生的荣耀而做出错误的价值判断。但无论如何,人们肯定是在某个动机的驱使之下才会做出错误的价值判断并进一步犯了罪。
再来看看在笛卡尔这里错误的认识是如何发生的。简单地说,在我们的理智尚未获得关于某物的清楚明白的知觉的时候,我们的意志就贸然地肯定或否定某物,于是我们就犯了错。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如果意志肯定或否定某物的行为只不过为了获取关于某物的知识,那么在我们的理智尚未获得关于某物清楚明白的知觉的情况下,意志又出于何种目的而急着去肯定或否定某物呢?前面已经说过,在我们获取关于某物的知识的过程中丝毫不能考虑这个物体与我们自己之间的利益关系,既然如此,那么在理智没有获得关于外物清楚明白的知觉之前,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急着去下判断。只要我们处在一个纯粹求知的活动环境中,那就不会有人逼着我们仓促下判断,急着下判断也不能带给我们生理的快感或即刻的利益。显然,按照奥古斯丁的理论,意志做出错误的价值判断并且因此犯罪是有明确的动机与驱动力的,但在笛卡尔这里,根本不存在任何一种动力驱使意志贸然地下判断或做选择。由此看来,从逻辑上说,笛卡尔不可能将奥古斯丁那里的恶源于自由意志的误用成功地转换为错误源于自由意志的误用。
至此我们可以这样解释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关于错误来源的各种奇怪说法:从根本上说,笛卡尔对人的理智能力持充分的信心,他认为只要我们正确地运用自己的理智能力我们的认识就不会犯错;但是,为了向教会人士表现自己的谦卑态度,他宣布我们的理智来自上帝的恩赐,上帝赐予的理智本身是完满的,错误源于我们对这种能力的不正确使用,这样一来笛卡尔就可以借用基督教的神义论问题框架来讨论错误认识的来源问题;在进一步分析我们如何误用了上帝赐予的认识能力的过程中,笛卡尔还是不愿意让我们的理智能力为错误认识承担责任,于是他就刻意制造出理智能力不下判断而是意志能力下判断的迷局,并且说错误源于在理智尚未获得关于外物清楚明白的知觉的情况下意志就贸然地肯定或否定外物,这样他就顺理成章地让自由意志为错误认识承担了主要责任。笛卡尔认为认识犯错源于自由意志的误用,奥古斯丁说恶源于自由意志的滥用,虽然这两个说法显得非常相似,可是在笛卡尔这里认识犯错并不像在奥古
斯丁那里行为犯罪那样有明确的驱动力,因此,笛卡尔不可能真正成功地借奥古斯丁回答恶源于何处的答案来回答错误源于何处,不过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法却使得他可以在掩盖自己对人类理智能力的绝对信心的同时,口头上向基督教传统宣布效忠。
* 本文已发表在《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