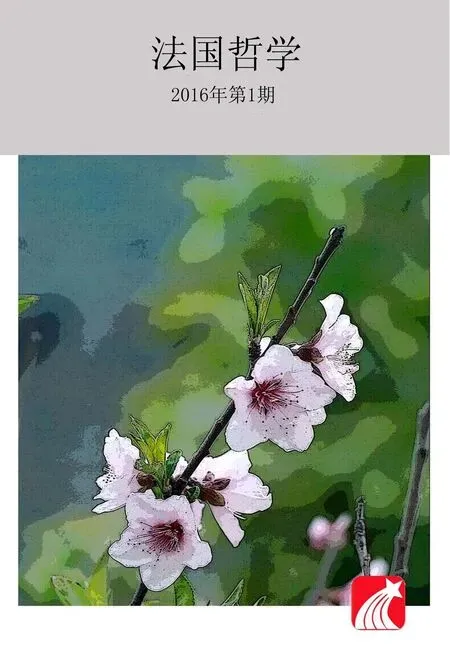我x故我在—读笛卡尔《形而上学的沉思》
2016-02-01尚杰
尚 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回到笛卡尔
我x故我在—读笛卡尔《形而上学的沉思》
尚 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一
笛卡尔与康德不同,康德把知识和自由意志区分开了,康德认为自由意志超越了人的理解能力,这是康德哲学中最杰出的思想,是他超出笛卡尔哲学的最关键之处。
笛卡尔并没有像康德那样在思想内部清晰地划定“理解”与“自由意志”之间的界限,更没有从自由意志方面理解康德的自在之物,从后一个思路中走来了叔本华和尼采,乃至现当代的欧洲大陆哲学。
古代哲学家并没有明确引入“意志”这个思想维度,即使在笛卡尔那里,意志的重要性也被“我思”取代了。在重新解读中,我试图将“我思”理解为“我要”,这个“我要”也就是意志,个人意志、意志自由。“我要”不同于“我应该”,古代哲学家只注意到“我应该”并使之成为道德与宗教的律令。但这是蒙昧而不是启蒙,因为在“我应该”中其实是没有我的。笛卡尔的我思之所以有我,不仅在于是我在思,而且这个思是不由自主的“我要”,否则,我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把“我思”还原为“我要”,这个思路超越了习惯上理解的笛卡尔“形而上学的沉思”。传统的解释是,笛卡尔为了确立无可怀疑的清楚明白的观念,先胡乱怀疑一通。也就是说,胡思乱想只是一个方法,或者叫过河的桥。但我觉得事实不是这样,笛卡尔无意中揭示了人不讲道理的天性,也就是无视事实、无视知识、由着性子来。这个天性,就是“我要”的意志不可阻挡,这个意志具有破坏性、原创性、癫狂性、孤独性、抑郁性,甚至由于不由自主地总朝着某个毫无道理或根本没有现实意义的方向想问题,具有精神上的强迫性。这是黑色的光,黑的启蒙,这种彻底返回内在性灵的情形后来在卢梭、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德勒兹等人的思想中被不断开拓出来。
笛卡尔在确立“我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的过程中怀疑一切,这些怀疑具有故意不赞成或睁眼说瞎话的性质。在这个过程中,常识和逻辑都被搁置起来了。换句话说,这个过程拒绝辩论。这个过程的语言,绝对不是在常识、知识和逻辑意义上的真话,但它们是意志意义上的真话,潜台词是“我就要这样想”,我控制不住自己去那样想,这时我根本不管什么根据或因果关系之类。这暴露出作为人与生俱来的天性,自由意志的力量比讲道理更为强大。
笛卡尔的用意,是说“我要独立思考”,但事实上在“我要思”时,每个人能想到什么,在能力上有着天壤之别。但这个差别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返回“我要”的意志。纯粹返回“我要”的情景,是野蛮的、危险的、意外的、偶然的,也是瞬间的,就像划过光明的黑暗。
在笛卡尔的沉思中,自由意志体现为怀疑一切、怀疑本身没有禁区。在这里,自由意志,就是相信“不相信”的权利。就是说,你说得再有道理,我也不相信。自由意志就是这种极端固执的精神状态。自由意志的态度,不是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笛卡尔是这样说的:“好像是我突然陷入深不见底的海洋之中……直到我遭遇到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①Descartes,Méditations métaphysiques,Garnier-Flammarion, 1979, p.71.世界现存的一切都值得怀疑,不可怀疑的明亮的东西只存在于心灵,这就是笛卡尔想告诉我们的真理—精神世界的阿基米德点就在这里,不仅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交流靠这个,宗教、哲学、科学真理的创造发明靠的也是这个,即思考那些现存世界原本不曾存在、现在也不存在的东西。这个“东西”,宗教称上帝,哲学称观念,科学称真理—它们与自由意志并不矛盾,它们共同构成支撑心灵世界的阿基米德点。
奇妙的是,为了解决宗教、哲学、科学乃至人与人之间的各种问题,首先应该抱着无视这个目的的态度。也就是说,在某个问题上我放任我的自由意志,顺着兴趣走,哪怕是偏离所要解决的问题或目的,于是我会创造出很多想法,问题在无意中竟然解决了。这个过程中,妨碍创造性的竟然是以往的记忆,因为记忆会喋喋不休地在我耳边说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就妨碍当下的幸福而言,记忆所带给人的痛苦要远远大于曾经留给人的幸福。
我所面临的一切现实事物在以下意义上是不存在的,即我可以任意地把A感受想象为B或C,而B或者C是我虚构出来的,它们只存在于我的内心深处。这里没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物是心的,心是物的。没有心,物就什么都不是;没有物,心也什么都不是。自由意志最神奇的地方在于,我会冒出无法与别人共享的念头,我无法解释某个念头为什么会产生以及怎样产生。笛卡尔是这样说的:“我的灵感只来自我的天性,这时我说我存在……心灵是极其稀缺而微妙的,像风、像火、像谵妄的空气。”②Ibid., p.75.当笛卡尔这样说的时候,很像是在用诗的语言描述思想。他对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不能说的心灵状态并没有保持沉默,打破沉默或显示心灵的途径,是使用隐喻,笛卡尔用具有物质行为的风和火形容心灵之无形与热烈。
我不思的时候我也在,比如我沉浸于物质行为之中,这个时候思是隐藏着的,思想化为行动,而且这个时候行为比思想还快。
我是谁?在思想的这个“我”是什么样子?看来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是我所不知道的东西,因此“我”不等同于判断。如果一定要回答,那只能像笛卡尔说的,我是在思想的东西—在怀疑、在理解、在肯定、在否定、在想象、在感受,如此等等。因此,我思故我在包含了我做故我在、我感受故我在、我爱故我在,等等。这里有精神的微妙性。所谓微妙,就是有很多意思虽然说不出来但感受得到。我这里并不是想逃避,因为我不可能脱离世俗生活里的人与事情。这些人与事是一些事实,这些事实本身既是俗气的也是美的—当我只有世俗的目的时,我的感受缺乏艺术感,但是当我沉迷于俗气之事的同时以转换的感受把这些事想象为任意超越现实的感受时,熟悉且平庸的日常生活瞬间会美丽起来。我不知道我在别人眼中的样子,但即使在我厌烦自己时,也能欣赏到自己的美,如此等等。
所谓“言不尽意”不是故意的,它的思想艺术价值,其实在于人要始终保持在好奇、欲望,以及不知道而想去知道的状态。语言的界限在于,语言永远追不上。我在说一句话的时候其实要有另一句话加以补充,但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因此,在效果上与人们想到的相反,“言不尽意”所导致的并不是少言,却是喋喋不休,但这并不像老太太似的总是唠叨同样的话,而是在极力填补好奇思想之新的欲望、不停地转换精神视角、不断地“换句话说”、无尽地超越自我。精神以语言为媒介极尽奢华自身之能事—“言不尽意”,就是说,还有话要说,还有更多的意思。
“言不尽意”并不是要抛弃语言,而是要以更有效的方式使用语言。当我察觉到语言无力表达感受时,我终究还要通过语言把这个观点表达出来,这就是语言的魔力与怪圈。语言是人的生命居所,当我没有能力去表达去描述的时候,我在精神上就死掉了,这与笛卡尔的意思是一样的:我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只是笛卡尔没有补充说,思想与语言其实是一回事。在哲学家与文学家那里,精神的微妙性是通过语言的微妙性体现出来的。如何读出哲学家语言中的未解之意呢?关键在于哲学家使用的术语往往不是字面上的意思(这一点很像诗人),尼采以这样的方式揭示基督教“道德”的真正名字叫怯懦。换句话说,基督教“道德”的情形也是一种“言未尽意”,“道德”背后其实是不道德。笛卡尔以他独特的智慧谈到同样的情形,他描述同样的蜡块在燃烧变成液体时还被叫作“蜡”,这很像是在同一个名称下隐藏着不同的货色。他说:“我几乎上了普通语言名词的当,因为我们说我们看见了同样的蜡……人们只通过眼睛而不是心灵的审视识别蜡。”①Descartes,Méditations métaphysiques,p.87.卢梭也曾经说过,他笔下词语的意思经常不是普通人所想到的那样,他是用自己的心灵写作,而这颗心是独一无二的。
笛卡尔太在乎思想的正确性了,他称之为“清楚明白的观念”。他怀疑一切是为了引出正确的思想,在我看这大可不必。不与是非或判断建立起联系的心思,仍旧是思想,而且可能是更重要的思想。要把“更重要”与“更正确”区分开来。比如,一个人活着的价值,并不在于他活得更正确、更有道德,因为究竟怎样才算正确或有道德地活着,是一个永远没有标准答案的话题。一个人只要把自己活出来,这就算没有虚度一生。但是,如果当一个人在“活自己”的过程是以使别人放弃“活自己”为代价的,那么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缺乏道德与教养的人。
笛卡尔在“我的依存性”中发现了“我的独立性”。“我的依存性”就是我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即我是不完满的;“我的独立性”就是我纯粹的心灵生活可以无视外部世界的存在,即我是完满的。这是他的《形而上学的沉思》中最宝贵的思想。从学理上考察,之后的卢梭、康德、叔本华都是沿着这个思路思考的,即我是一个具有主动的创造性思考和感受能力的独立存在者,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出发点的存在与虚无,其实是一回事。就像我想抬起胳膊,并写出这句话,胳膊就起来了,句子就出来了,这看似非常简单的事情其实是天大的创举,全部人类文明都是如此构成的。
当笛卡尔说“我存在”,不是我对外部世界的依存性存在,甚至也不是指身体的存在,而是指原本不存在的东西、只是在思想里存在的东西。这些与世界保持距离的存在,西方哲学往往也叫“形式”,中国传统往往称之为“意象”,赋比兴之“兴”。用现代汉语来讲,可称作不能用语言确切表达的“思想气氛”,比如喜庆、亲切、尴尬、害羞、惭愧—这些术语当然具有形成概念的趋势,但它们同时必须保留感性的光芒,使之具有美感。
想象是自由的,但要把有情景的想象与想象中的理解区别开来。笛卡尔说他可以想象任意一个三角形的样子,却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一个千边形的样子,我替笛卡尔继续说几句:他可以从概念上理解一个由一千条边构成的形状。纯粹的三角形靠的是精神的眼睛,但千边形靠的是精神的眼睛背后的精神的眼睛,近似于更深层次的理智直觉。千边形即使在思想中也无法完全在场,也就是说,当笛卡尔说清楚明白的观念时,指的是他的内心完全被理解所充满,而不是指某形状或形象能在他的想象中呈现。
但在我看来,这里的情形并不能证明理解高于想象,理解总是与形成概念有关的思考能力,缺乏概念的思考,就难以形成深刻的理解力。理解,就是澄清与梳理概念的工作,但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我们忽略了一个细节,就是说往往要把概念植入某种思想情景中去考察。为了引入思想情景,就得融入想象成分,而想象力与直觉能力是不可分的,是相互解释的。我对这种不可分性非常有兴趣,因为它不仅涉及科学,还涉及信仰与艺术。我不能仅仅满足于当一个科学人,更要做一个艺术人,艺术比科学更接近人的天性,更能说明人的本质,其情形就像一个有趣的人比一个有知识的人更受人们欢迎一样。
二
笛卡尔在区分心灵与身体时,注意到精神的不可分性,身体各部分有各自的名称,比如胳膊、腿、脚。但心灵不可以如此机械地划分为各个部分,心灵领域诸因素之间是相互包含的,以众所周知的康德术语为例:哪有什么纯粹的感性、知性、理性呢?给它们划定各自的界限只是为了理解的方便,事实上就像不能从人的身体上割下一块不流血的肉一样,肉与血总是连在一起的。一个人全神贯注沉浸于某件事情时似乎已经听不见别人说话,但这种听见的能力只是暂时被遮蔽了,而不是没有能力。纯粹的疯话也是人们虚构出来的,事实上并不存在,福柯写了《癫狂的历史》,德里达说,你不是疯子,怎么有资格做疯子的代言人呢?笛卡尔在怀疑一切时,也是在装疯。
但是,与其说人具有一种表演某种感情的能力或说谎的能力,不如说人有一种强迫自己不做自己的能力,这倒不一定是为了讨好、骗人或达到某种功利性目的,而是出于像卢梭那样的无法克制自己朝向某个方向去想问题的抽象冲动。康德没有注意到人的这种故意不讲理的本能,其实这可能是人类至今为止仍旧没有发现的被掩藏起来的智慧金矿,人们不去从积极方面开拓它,而只是简单地将它视为某种病态,斥之为抑郁症或者“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这就使得天生具有这种精神才华倾向的人严重被别人轻视与误解,导致这种才华的抑郁—他们不敢在不讲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而失去了精神发明的机会,这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巨大损失。
要写疯子,某人自己得先疯,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这个人真疯时,就已经写不出人话了。有才华的作家几乎无人真的体验过他们笔下人物的角色,这对文字来说,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我们只是沉醉于文字本身而已。感性、知性、理性,这不过就是六个字而已。认识这六个字的人在心灵上会有不同的反应,并非一定是康德式的反应,康德的反应只是众反应之一而已,即使他是一个思想天才。我可以暂时同意康德的划分,过一会由于某个念头袭来我又变卦了、不同意康德了,这是我的正常反应,心灵生活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用笛卡尔的话说,我只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如此而已。不应该将我活生生的思想灵动过程生硬地加以分割,说某时某刻的“我”是唯一真实的我。不是的,它们都是我。画出我在不同时刻的精神风貌,不时会暴露出各种面孔。
换句话说,事情的真相不是在当下,而是在别处,例如表面上地铁车厢里两个人为争座位而吵架,其实是没有教养。快乐也是在别处的,你给你的朋友一件小小的礼物,礼物本身并不值钱,但你朋友的快乐在于他由此联想到别的,联想到他在你心里有位置;生活也是在别处的,因为人并不想过日复一日的日子,想遭遇点新鲜事儿,即使要冒风险。如果一个人对一件事的反应总是可以被别人事先猜到,那么这个人至少在这件事上是一个乏味无趣的平庸之人。平庸的人再多,只等于有一个脑子或一个心眼:在脑子里只知道服从习惯。
回到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表面上似乎建立在一个暗含的三段论推论基础上,似乎其中有某种因果关系,但这只是一个假象:我思可以意味着我在,但我思与我在之间不是因果关系,而是“换句话说”的关系。这种关系甚至可以任意连接起来,因此,费希特批评笛卡尔,说我行动故我在,而以无意识消解意识的拉康,则把“我思”等同于无意识即“我不思”或者“我没有自主地意识到我在思”。拉康调侃说:“因为我不在的场所才有我思,故我不思的场所才有我在。”①Jaques Lacan, “L’instance de la lettre dans l’inconscient”, inÉcritsI, 转引自François Dosse,Histoire du structuralisme,Editions La Découverte, 1991, p.138。其实无论费希特还是拉康,并没有背离笛卡尔,他们在笛卡尔开辟的道路上极力开拓,他们的意思只是说关于什么是“我”或什么是“思”并不是预先确定好了的。
换句话说,“我”是破碎的,“我x故我在”。
没有什么比令人难以理解又令人兴奋异常更伟大的事情了,但我不做我既不理解又毫无感觉的事情,我只做虽然难以理解但使我的心灵有所触动的事情。为什么不重视“理解”呢?因为“理解”一词,就像“存在”一样,其意思是完全空洞的、大而无当、悬而未决。“理解”经常陷入独断,尤其是当我们事先确立起一个抽象空洞正确的概念或判断的时候,即预先就设定了某个脱离我们实际感受的定义是真的,这种预先性意义上的“先验性”是要不得的,它没有接触到最实在的东西,即叔本华所欣赏的康德意义上的自在之物。
认识论意义上的先验性无法触及自在之物,但自由意志意义上的任意性时刻沉浸其中的,正是实在本身或自在之物。在我看来,这种任意性,可能就是“先验性”最纯粹、最本真的含义,即第一次、创见、撞见、难以理解而兴奋异常,此刻降临的或海德格尔所谓的“此在”或者“亲在”,不同于西方哲学传统上讲的“经验”,因为“经验”一词首先意味着是一个概念,其意思已经完成了,而且它本身已经意味着可重复性,因此它在传统上不是指具体的感受,而是空洞的一般性。现在我们使“经验”回到其本来面目—亲在、感受—不要任何间接因素,不要推理性质的反思因素。这样就搁置了从前抽象而独断的思维,转到了具体而贴己的思维。
也就是说,当我们读到一个词语时,首先要破除的,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有现成意思的概念”这样的思维习惯。可以尝试着把这个现成的意思搁置起来,就像我们偶然发现一张熟悉的脸很陌生,这情景很少见,这感觉是艺术的,值得珍惜;但同样的情形换句话说就不少见了,即我们经常说得到做不到,这在很多情况下并非缘于我们故意说谎,而是人们误解了我们那些话其实并不是在做承诺,而不过是表示当时当场的某种不由自主的情绪而已。
要以激情而不是爱情的方式读书与写作,激情的表现不是一样的,既可以像圣埃克絮佩里写的童话《小王子》里的小王子那样①以下摘自《小王子》:“泪水的世界是多么神秘啊!”“大人们喜欢数字,他们从来不问实质问题。如果你对大人们说,‘我看到了一幢漂亮的粉红砖房’,他们是无法想象这幢房屋的。你得对他们说:‘我看到了一幢价值十万法郎的房屋。’于是,他们就会惊叹道:‘多么漂亮啊!’”“人们不应该听花说什么,只要欣赏她们,闻闻花就够了。”“如果你爱上了某个星球的一朵花。那么,只要在夜晚仰望星空,就会觉得漫天的繁星就像一朵朵盛开的花。”“驯养的意思:‘这是常常被人遗忘的事情。’狐狸说道,‘它的意思就是建立关系。’”“狐狸说:‘对我而言,你只不过是个小男孩,就像其他千万个小男孩一样。我不需要你,你也同样用不着我。对你来说。我也只不过是只狐狸,就跟其他千万只狐狸一样。然而,如果你驯养我。我们将会彼此需要,对我而言,你将是宇宙唯一的了,我对你来说,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了。’”,也可以像卢梭、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那样在抽象而悖谬的心情中孤独地感受自己的世界。激情是这样一种精神能量,它像小王子一样不回答问题却抓住某个问题直率而天真地死抠到底,直到突然出现另一个值得死抠到底的问题—成人的世界中的一切正经问题,例如权力金钱虚荣等等,到了小王子这里一概变异为有趣或值得惊奇。在这个基础上,小王子开始提问,但小王子始终惦记的只是他的花。换句话说,在激情的瞬间,激情将自身所放射出的独一无二性贯彻到所接触的一切事物,在这个时刻一切事物都与自己具有独特能量的想法相像,而不是让自己的想法顺应世界本来的样子。
对于这同样的意思,笛卡尔是这样说的:“有一种如此巨大而不可穷尽的力量,这力量独自存在着,绝不求助于任何其他的事物。”①Descartes,Méditations métaphysiques,p.234.显然,笛卡尔在这里指的是上帝,而我要说,这精神的力量既强大又孤独,它因孤独而强大,越孤独就越强大。并不是说它不怕孤独,而是说它自己是自己思想力量的发动机,是一切创造之源。没有这孤独就没有独特,一旦依存于别人的思想,独创性就不存在了。因此,每个孤独者内心深不可测的独特自我,就是使孤独者沉浸其中的上帝,在这里,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自生而滔滔不绝,这里有一个任性或充满自由意志的上帝、自由自在者随时且到处都自由自在,在这里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去理解概念,自由不是概念而是精神的实质。换句话说,实在或事物本身呈现为浑然自由流动状态,而不是任何一个意思已经被完成了的概念。
所谓创造性之母,就是说,她是其他一切事物(物质的、精神的、生命的)得以存在的原因,而它自己的存在并不需要原因,这种情形并不一定存在于人之外的关于上帝的观念之中,而是更真实地存在于人心之中,我敬仰、惊叹、畏惧、陶醉其中,我赞叹—为何有如此之多的自寻烦恼、杞人忧天之想?我为什么无法控制它们的出现?人们所在乎的事情之差异为何如此巨大?为什么人们欢迎平庸而排斥才华?在什么意义上那不需要原因而自存的东西高于需要原因而存在的东西?为什么人们安静而不动心地听那些煞有介事的谎言而从不站起来反驳?同样的语言为什么写在书里就容易被人相信?“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个表达为什么比“空前绝后”更具有美感?它是文言还是白话?为什么人们都极力想知道别人的隐私而把自己的隐私捂得严严的?为什么人们只看重“礼物”值多少钱而不看重礼物本身?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坚定认为只有攀上权力才有个人价值?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毫不重视纯粹属于个人的想法?为什么人们自发地倾向于服从而不愿意在头脑中充满问题?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不理睬别人的感受却会被别人喜欢?我的意思是说,写作的时候就像内心独白而绝不考虑读者是否接受,但读者却可能喜欢,就像读者更喜欢偷窥别人的隐私而不愿意听此人在大会上的发言。为什么呢?因为隐私更具有个别性和真实性,而真实的个别性由于独一无二从而具有了他人无法替代的价值。
三
一旦建立起依存关系,我所依存的东西在我眼里的性质就顿时改变了,变得十分亲切,就像某一本我着急要阅读的书籍,但这书在不感兴趣的人那里,不过一堆废纸而已。投入了感情,我所投入的东西就被我赋予了生命,而这东西原本不知道自己还有如此美丽的价值,反之亦然,我的新生命也会被我所经历的东西唤醒,而那东西自己并不知道它对我有如此美丽的价值,就像灵魂中的海市蜃楼。卞之琳在《断章》中写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可见,依存关系无处不在,而且并不一定相互依存,很可能是单方面的沉浸,不对称的爱。关键的不是被爱,而是有去爱的能力。心中有爱,心情就总是甜美的,即使周围环境险恶。在一切爱恋之中,最重要的是热爱自由。自由的价值甚至高于生命与爱情。
自由只能是精神上的,而不可能是行为上的。那么,既然在任何情况之下谁都无法阻拦某个人在心里想什么,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在法律上规定言论自由呢?因为把心里想的落实到公开的语言中并自由传播,与“只是在心里想”之间,是有天壤之别的。只有保证言论自由,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精神自由,否则,精神自由走不了多远。精神自由本身,肯定是天然的自由,任何人也管不着、想管也管不住。精神自由的性质是形而上的。既管不着也管不住精神自由的情形,也就是信仰自由。说白了,也就是自由想象或“胡思乱想”的自由,这些自由之所以是天然的,是因为我不需要任何权力事先给予我任意想的权利。换句话说,任何强大的权力都控制不住我最微小的胡思乱想,即使我自己的意志也控制不了。当然,各种各样的外来压力都在遏制胡思乱想,这却反而表明它对人的精神生命有多么宝贵。
如此看来,精神自由或信仰自由似乎是一句“废话”,因为人的精神本来就已经处于如此状态。但是,这是一句非常伟大的“废话”!它解放了人的思想,或者说它启发人彻底脱离精神的蒙昧状态。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人总是控制自己不去胡思乱想,人习惯于总是依赖自身之外的精神,而不相信自己的精神。一句话,“奴在心者”是自觉自愿的,因此这样的人即使处于“胡思乱想”状态,其想象的空间也很有限,会自觉地止步于某个界限。“奴在心者”其实是没有心灵生活的人,他总是处于恐惧之中。
对精神生活本身的恐惧以及由此导致的精神生活的简单枯燥、精神质量的低下以及对精神本身的贬低,是人类一切不幸中最大的不幸。人类历史的最大奇观不是种种科技创造发明,而是一方面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极少一部分有统治权力的人极力用法律力量控制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人们在自己的世俗生活中根本忽略了精神自由的问题,不知道它事关人的根本尊严与幸福,不知道它事关生命的根本质量。笛卡尔说,人是一个始终在思想的东西。考虑到在那么多个世纪里正是人使自己成为不是在自由思想的东西,笛卡尔说出了一句伟大的话!当笛卡尔怀疑一切时,他处于思想自由状态。
当然,很多话笛卡尔没有说透,比如我在思想,但我并没有在思考任何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说我在思想吗?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没有了吗?如果有,我跑到哪里去了呢?笛卡尔没有说到这种无意识的情形。从卢梭开始,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勒维纳斯、拉康、德勒兹都把思想延伸到无意识的他者维度,极大拓展了思想启蒙的空间。自由意志是无意识而不是自我意识,自由意志没有能力识别自身。
“我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并不等于自动回答了“在思想的我是什么”或“我是谁”,“我”和“思想”之间不能划全等号。从“思想”与“我”之间的这种不对称性中,能激发起对无意识的思考。进一步说,能在对这种无意识的思考过程中消解“我”。当然,这样的思考已经超越了笛卡尔的思想。
但问题还是没有完,“小王子”的精神气质是:一旦提出问题就绝不放弃,哪怕中途会勾起一连串其他问题,也要死盯住问题。对无意识的思考不也是思想吗?我们还是没有从笛卡尔的思想圈子里跳出来吗?但是,我觉得无意识已经跳出笛卡尔的“意识”了。
德勒兹说,哲学就是创造概念。他这么说容易造成误解,因为当人们一想到某个概念,就会下意识地琢磨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而事实上很多人一方面总是自以为已经知道了某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另一方面这所谓“已经知道”的情形在不同人那里又是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写文章争论某个概念,意义不大,因为如果是在自己已经知道了其意思的概念下讨论问题,说得再多也无非是同义反复;如果对某一概念大家想法不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概念等于悬而未决,因为彼此说的根本不是同样的意思。
因此,如果一定要说哲学就是创造概念,那么应该是创造出一个从前没有人想过的新的意思。这太难了,如果要使自己的想法没有被别人想过,那么必要的前提是根本不管(不管,不是不知道)别人曾经有过什么想法,在这个基础上创造新的概念,就是在彼此陌生的精神因素之间建立关系,例如人原来就是鱼变的,“人鱼”的联想就形成了,这当然只是关于人的无数联想之一。就像我看见一个人拿着一支笔在纸上划,这个事实可以引起我无数方向的联想,这些联想并不存在正确与否的问题,衡量这些联想质量的,应该是“是否曾经有人像我这样想?”或者说“我的联想是否能打动人心?”
思想和艺术一样,是在被激发基础上的自由联想的产物。人随时都在被激发,不仅与外部世界的事物接触、与他人的相遇会激发我们,人在独处时总会默默地想心事,也会为突然降临的念头而兴奋或伤感……自由联想过程最忌讳的是死心眼或者“目标始终如一”,自由联想的畅快在于思想和心情一样,总是处于走神中的凝视过程之中—每当我试图去用语言抓住某个意思时,这个意思总是变化为别的意思,我只是在享受思想感受的过程。
关于上帝的感受首先是艺术的,而不是正确的。我把原来总是在一起的或引起自然联想的意思分开,我觉得这样既有趣又深刻。分开之后,我试图建立不管思维习惯的原本各个孤立的念头之间的思想连接,这不仅是有趣的、深刻的,而且伴有焦躁不安,因为我的精神在冒险,我也许并不能一下子理解这些连接的意思,但我的直觉告诉我,它们很有意思。于是,我破天荒地把“理解”这个概念与“意义”分开了。此情此景的神秘,甚至超过了思辨哲学的晦涩,因为思辨哲学还是要人去理解的,但我这里却抗拒理解。或者说,我去制造很多比“理解”还快的精神刺激。虽然可能最终还是没有发生理解,但我已经享受过了精神刺激,获得了道德上的崇高感与幸福感,或许这种情形本身就是“正确的”,但如此一来,“正确”就与“理解”之间不发生关系了,那么我就更改了“正确”一词的词义,就像我以上说过的“人”=鱼。
这思想着的我只能来自我的大脑而不能来自我的皮肤吗?在什么意义上我的身体可以自己思考?我的身体知道而我不知道,我身体的感觉启发我的思想,总之我确实不认识我自己。在笛卡尔《形而上学的沉思》发表后,他的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发问的:“你怎么证明身体不能思想?你怎么证明身体的运动不是思想本身呢?”①转引自Descartes,Méditations métaphysiques,p.248。当然,这个身体也是物体。这两句问话的实质是说,无论物体还是身体,都有自身的生命。既然有生命就潜伏着精神或思想—当然,这里没有语言,这里有“没有语言的思想”,因而显得神秘。但我也可以反问:难道我们不是太重视语言里的思想了吗?或者说,思想绝不应该停止在语言保持沉默的地方。无法用语言陈述的思想,可以用别的手段表达,比如音乐、图画、舞蹈等等,虽然没有发生语言,但我们可以理解与欣赏,这是感受中的理解,它比光秃秃的概念理解更像是理解。
笛卡尔明确否定“我思故我在”中暗含着演绎三段论推理:“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时,这并不是任何一个三段论的大前提。当有人说‘我思想所以我是或所以我存在’,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思想依靠某种三段论的力量而存在,而是意味着他的思想已经在他自身之中了,这一点凭精神的简单内省就可以察觉得到。”①Descartes,Méditations métaphysiques,p.266.笛卡尔这段话里含有排斥二分法的味道,不能把他说的“思想”还原为所谓“主体”,因为“主体”已经意味着有一个与主体对立的客体。这客体其实并没有在主体之外(即“客体”与“主体”概念是相互依存的),但却已经在暗中将思想二分了。思想不是主体,因此思想并不是朝着某个对象的思想—令人遗憾的是,在哲学史后来的发展中,哲学家们恰恰从主体—客体二分的思路上发展笛卡尔的思想,一直到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还在说“一切意识都是朝向某个对象的意识”。由于有“思想对象”的存在,思想状态便陷入了二元论,这个思路甚至影响了康德,以至于在我看来,康德的认识论是他的思想中价值最小的部分,而他关于自在之物的描述,则是他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笛卡尔反复强调人是一个有思想能力的东西。思想能力是人自身已经具有的能力,这与后来康德的自在之物、叔本华的自由意志已经有所契合了。在思想能力的极限,笛卡尔与上帝遭遇,这也许并不意味着笛卡尔走向保守,而意味着他在思考思想如何被创造出来、思想是如何出场的。换句话说,在这里思想遇到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即“超越”。笛卡尔说,我们不能怀疑“怀疑本身”,意思是说,我们不能怀疑自己身上已经具有的思想能力。后来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是以“换句话说”的方式继续笛
卡尔已经说出的思想,即我不需要他人的引导,自己已经具有思想能力。这个与别人不同的“我”意味着思想的独特性与差异性。思想是以独特性与差异性的方式存在着的,因此当一听到“大家一致认为”,我就警惕接下来听到的可能是一句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