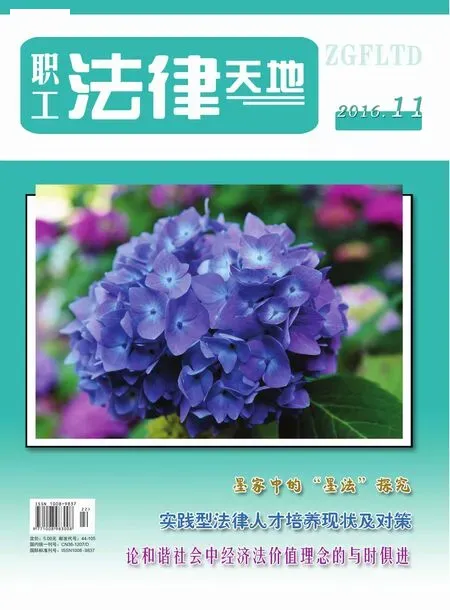诉讼专门性问题的研究意义
2016-01-31梁贺
梁 贺
(100089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北京)
诉讼专门性问题的研究意义
梁 贺
(100089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北京)
人类劳动的无限多样性和个人劳动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而社会分工则导致了在司法活动中,法官个人的知识无法了解日益精细化的其他领域的专门知识,司法鉴定以及专家辅助人制度应运而生。而启动鉴定或者引入专家证人的前提是面临专门性问题。然而尽管我国三大诉讼法以及其他一些部门法甚至部门规章等均规定了对专门性问题的处理办法,但是何谓专门性问题法律并无规定,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不多,对该问题的研究意义并未重视,本文即通过简单的梳理揭示诉讼专门性问题的研究意义。
专门性问题;研究现状;研究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6.20宝马肇事案自一开始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尤其是肇事者被认定为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的鉴定结果公布之后,更是引起轩然大波,网民几乎一边倒的对此表示怀疑、嘲讽:“不能让坏人以精神病为由来逃避法律责任”、“什么时候精神病证明变成免死金牌了”(康熙微服私访记里面有一记就是讲免死金牌的问题。)、“第三十七计装精神病”等等不绝于耳。如果一起案件的结果都是如此怨声载道,那么我们还谈什么公平正义?谈什么法律或司法的社会效果?
1972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戴维.罗森汉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安排九个正常的人家装精神病人前往美国各家精神病院就诊,就真旗舰的表现和平常毫无差别。结果,这九个人中有八个人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一人被诊断为躁狂抑郁症。后来,罗森含教授做了另一项实验,他对某精神病一员宣称,自己将派正常人假装精神病去该医院就诊。一年后,该医院称罗森汉至少派来了41名假病人。但事实上,罗森汉一个人都没有派。可见所谓的鉴定是多么荒唐。这些年来,虽然精神病的鉴定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本质上仍然只是停留在一句症状做判断的层面。解决这一问题是当务之急,而此一问题的先决问题乃是专门性问题的界定:精神病鉴定或者说司法鉴定的前提是专门性问题的确定,鉴定的目的是为了“事实裁判者在专门问题上认识能力的不足”。
二、专门性问题的法律规定
承上,专门性问题的界定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且事实上,专门性问题所涉及的内容极为繁杂,可是我国现行法律系统中对该问题规定的并不清晰。
《刑事诉讼法》第144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民事诉讼法》第72条:“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行政诉讼法》第35条:“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认为对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此外,三大诉讼法的相关司法解释也有诸多关于专门性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解释》第59条:“对鉴定结论有疑问的,人民法院可以指派或者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或者鉴定机构,对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1条:“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1—2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询问、对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8条:“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当事人可以向法庭申请由专业人员出庭进行说明,法庭也可以通知专业人员除同说明。”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
此外,在一些“小法”中也有专门性问题的模糊规定:2013年施行的《两高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使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对案件所涉的环境污染专门性问题难以确定的,由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或者由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指定的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林业部颁布的《林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30条规定:“未解决林业行政处罚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指派或者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
这些法律基本上都规定了启动司法鉴定的前提、原因以及主体,或者说规定了解决专门性问题的办法,但是对于至关重要的一点也就是到底什么是专门性问题,这些法律都没有规定。
三、专门性问题的研究现状
专门性问题的在如此之多的法律中规定,其恰当界定对于公正的处理案件又是如此重要,然而关于专门性问题的界定的研究却非常之少,这实在令人颇感遗憾。笔者在中国知网以“专门性问题”为关键词进行文献搜索,结果是以“专门性问题”为题的论文少于十篇。刘振红老师的博士论文《司法鉴定:诉讼专门性问题的展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对专门性问题进行了非常全面的解读,该书第一章为“何谓诉讼专门性问题”,从诉讼专门性问题的内涵、属性、特征以及相关概念的比较等角度进行研究,然而最终并未清楚揭示诉讼专门性问题的含义。
此外,在司法鉴定的研究和专家辅助人制度的研究,也有提到专门性问题的。这些研究的前提都是要恰当的界定专门性问题的内涵,因为只有遇到专门性问题,才有司法鉴定的必要,也才有专家辅助人的必要,因此,在此类的研究中也能找到一些对于专门性问题的界定有一定借鉴意义的观点。如有学者认为,“鉴定结论应仅仅针对案件事实中有关的专门性问题作出,至于属于普通的常识性问题范围之内的事实认定,鉴定人在认识能力上并不占有任何优势,所有应当属于事实裁判者的职责,鉴定人不得干预。”据此,所谓专门性问题也就是相对于常识性问题的事实问题。在后文具体论述专门性问题与常识性问题的界限时,作者称:“所谓专门知识和技能也不是一个拥有固定范围的概念,它与普通知识之间难以进行一清二白的区别,二者之间的迷糊状态,在英美国家,由于其诉讼模式的特点,可以不必深究,因为无论普通证人还是专家证人都是由控辩双方提供的……但在大陆法系国家,鉴定决定权与当事人举证权分离的现状决定了必须在专门知识技能与普通知识之间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明确区分,以划定鉴定权与举证权的界限……绝大多数法律法系国家都把鉴定的决定权交给法院,这意味着,在是否属于专门知识和技能的问题上,由法院行使判断权。”
关于诉讼专门性问题的研究,目前的共识主要就是所谓诉讼专门性问题,首先是一个事实问题。如陈光中老师认为,“专门性问题属于案件证明对象范围内的事实,不是公安司法人员可以直接做出肯定或否定回答的常识性问题或一般性法律问题”。在这里,即使不是一般性法律问题,其他更为复杂的法律问题也不属于此处的诉讼专门性问题。但是对于清楚地界定诉讼专门性问题,这还不够,因为在事实问题的范畴下,仍然有非常庞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举一个例子,我国刑法第49条第一款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因此,如果一个妇女面临被判处死刑的可能,则有判断该妇女是否怀孕的必要。而妇女是否怀孕,显然是一个事实问题,这是无需争议的,但这是否就是诉讼专门性问题呢?结合陈光中老师关于诉讼专门性问题的定义,诉讼专门性问题“不是公安司法人员可以直接做出肯定或否定回答的常识性问题”,那么一个人是否怀孕的问题能否由我们直接根据常识来回答呢?比如我们如果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个具有突出怀孕特征的妇女,我们会根据常识认为此人怀孕进而为其让座。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诉讼专门性问题呢?这些均有进一步研究之意义。
四、研究意义
承上,法律对专门性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学者们似乎对专门性问题的关注也较少。而专门性问题的界定确实是个复杂的问题,其困难在于无法确立一个相对固定的判断标准,将所谓“专门知识和技能”与普通知识进行区分,而且更困难的是,“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并不具有固定的概念涵盖范围,在不同的案件可能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因此,专门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如上所述并不多。即便如此,专门性问题的界定仍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
1.专门性问题的界定有助于防止鉴定人越权进行实体判决
笔者认为,有分工就会有分权,不当的分工导致越权的产生。实践中,随着证据科学化以及纠纷的日益多样化、复杂化,越来越多的案件需要借助司法鉴定来证明案件事实以及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力。尤其在一些鉴定意见涉及的事项是最后的、终局性的案件中,由于鉴定人具有天然的科学上的权威性,鉴定意见被认为可信度较高,法官往往直接甚至仅仅根据鉴定意见进行判决。这样,技术权威已经由原先解决案件中专门性问题的工具上升为一种在某些案件中解决纠纷的决定性力量,这使得鉴定人间接行使了审判权,在实质上已经构成了对审判权力的分割。判决往往主要甚至完全取决于鉴定意见,使得法官这一唯一的审判主体在部分案件中变成了鉴定人的附庸。而在大陆法系国家,鉴定人理应是“帮助法院进行认识的人”,是“法官的科学辅助人”。诚然,针对上述问题有学者建议应改革或完善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不过在现行制度下,专门性问题的界定可以明确司法鉴定的范围,明确鉴定人的职责范围,防止专家对不属于其权利范围内的事务进行实体判断,侵蚀审判权利。
2.专门性问题是司法鉴定程序的前提和对象
由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44条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2条规定可以看出,专门性问题是司法鉴定程序启动的前提,是司法鉴定的对象,试问如果连前提、对象都界定不清,又何谈司法鉴定程序的正当启动呢?因此,笔者认为正确解决上述问题对司法鉴定概念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理解司法鉴定对象和范围以及司法鉴定制度的构建都有重要的启示。
3.专门性问题的界定有助于避免同案不同判
从公平公正角度出发,为了避免同案不同判也应对专门性问题进行界定。笔者对近年来发生的几起特大故意杀人案进行了粗略的梳理,同样是恶性杀人案,行为人同样都具有某些可能患有精神病的表现,马加爵、杨佳、黄义文等人得到了司法鉴定的机会,而邱兴华、熊振林等人则被法院驳回精神病鉴定申请。这反映了此类问题在实践中仍处于模糊的地带。笔者试图在以上案件的判决书中找到司法机关同意或者驳回司法鉴定申请的依据,可惜结果不如人意。那么,司法机关在面对此类问题时,是根据什么原则来决定的呢?
4.恰当界定专门性问题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和政府公信力
2010年2月19日,河南省泌阳县板桥镇敬老院五保供养人胡炳旺手持菜刀等凶器,先后将5名供养人员杀害致死。归案2天后胡炳旺离奇死亡,政府的说法是其因精神病发而杀人并且自杀。2010年2月22日,甘肃一民警打车300公里拒付车费,还威胁车主。事后,甘肃省公安厅发布公告称该民警患有精神病,已经被送至精神病院。去年6月发生在南京的宝马车肇事案致两人死亡、一人受伤,最后南京市交警局认定肇事者王季进患有“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
这一系列案件都曾引起群众的质疑:“什么时候精神病证明变成免死金牌了”?政府为了自己的形象、为了隐瞒和掩饰真相可以随便将人塑造成精神病,“精神病”似乎成为政府部门公信力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而长此以往,司法权威将荡然无存。
[1]汪建成,孙远.《刑事鉴定结论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2期.
[2]陈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制稿》,中国法治出版,2004年版,第277页.
[3]汪建成.《司法鉴定基础理论研究》,载《法学家》,2009年第5期.
[4]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2条规定:“司法鉴定是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
[5]赵天水.《精神鉴定何时出现“珍贵范本”——重大命案中的精神病鉴定现状》,2016年6月4日.
梁贺(1990~),女,汉族,北京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