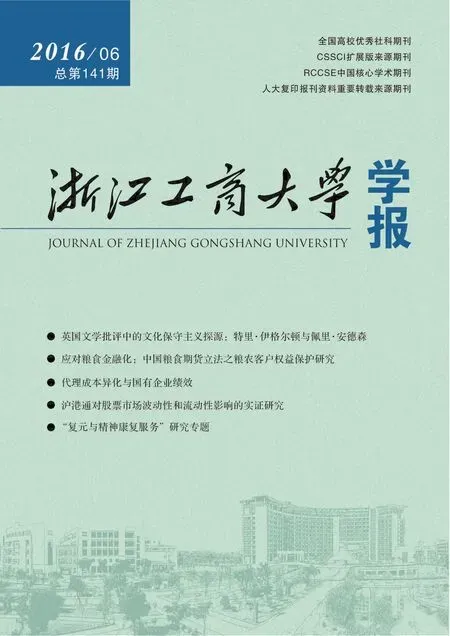英国文学批评中的文化保守主义探源:特里·伊格尔顿与佩里·安德森
2016-01-23赵国新
赵国新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北京 100089)
英国文学批评中的文化保守主义探源:特里·伊格尔顿与佩里·安德森
赵国新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北京 100089)
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的文论著作深受欧陆及本国诸多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影响,前人对此多有研讨。然而,史学家佩里·安德森对他的重要影响,至今尚未有人明确指出,遑论考察辨析。本文认为,安德森对于17世纪的英国革命以及近代英国资本主义独特性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的英国文学批评史观,为他考察文学研究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内在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和历史参考框架。伊格尔顿对近代英国文学批评中暗含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发掘和剖析,主要得益于安德森对现代英国社会盛行的政治保守主义的精彩解释。本文还指出,二者的相关著述也有助于解释18和19世纪英国小说中一个常被忽略的现象:与同时代的欧陆长篇小说相比,英国小说一直在回护本国的贵族阶级,它们从未像欧陆主要国家的长篇小说那样,激烈批判乃至彻底否定本国贵族阶级的思想和统治。
马克思主义;新左派;“文化与社会”的传统
特里·伊格尔顿是继雷蒙·威廉斯之后欧洲的头号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在中西方学界声望隆重,荣位高耸,不过,他还称不上是一位很有原创性的理论家,因为他既没有演绎出一种可以推广的思想框架,也没有创造出一个普适性的理论概念。客观地讲,他是文采灿然的批评家和目光如炬的批评史家。在移用他人的时新理论、成就自家斐然篇章的同时,他在英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也卓有成就,并体现出一种独到的学术眼光:他经常在人们习焉不察之处,出人意料地发现批评实践与现实政治的隐秘联系,令人顿觉耳目一新。这种异常敏锐的洞察力的产生,得益于他旁观约取、左右采获的治学方式。
其著书为文,以植根本土、旁采欧陆为主要特色。F.R.利维斯的细绎式批评和威廉斯的左翼文化理论,既是他行文立论的基本方法,也是他时常辩难的主要对象,欧洲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为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灵感,塑造了他的批评视角:乔治·卢卡奇的总体性理念,路易·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吕西安·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米歇尔·福柯的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瓦尔特·本雅明的文化批评,于日尔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研究,凡此种种,在他各个时期的著述中时有闪现。这些人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前人已有探索,[1-4]然而,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源头,由于十分隐蔽而为研究者所忽略。此人便是他的同时代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1938—)。
安德森对英国社会保守主义特性的历史研究,塑造了伊格尔顿的英国文学批评史观,为他考察文学研究与现实政治之间的隐蔽联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框架。伊格尔顿对现代英国文学批评中暗含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发掘剖析,主要得益于安德森对现代英国社会中显在的政治保守主义的历史解释。这种至关重要的思想启迪集中体现在伊格尔顿的三部著作当中,它们分别是《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5]《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6]和《文学批评的功能》[7]。
一、 佩里·安德森:英国社会保守主义的历史根源
1964年,佩里·安德森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了成名作《当代危机的起源》,探讨了英国社会何以保守成性、社会主义革命何以无法实现的历史根源。在他看来,这些问题肇始于17世纪英国革命的不彻底以及英国独特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这篇长文中,他主要依据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分析了17世纪革命的性质以及英国社会的阶级结构,进而论证英国独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对保守主义民族文化的塑造作用。[8]
与传统史家不同——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家,还是辉格党史家——安德森认为,17世纪的英国革命既不是标准的资产阶级革命,即所谓上升的资产阶级与没落贵族之间的搏斗,也不是什么宗教革命,即新教徒与天主教势力的对决,而是英国土地贵族内部两个集团的角力,其中一方为大搞商业投资的地主,另一方是专事土地租赁的地主。严格来讲,它不像是一场革命,更像一场政变。彼时工业革命尚未发生,资产阶级主要集中在商业和金融业,而非制造业,他们的政治能量和经济实力还十分微弱,他们既无心也无力领导革命,更不是革命的主力军,他们只是依附于从事商业投资的地主阶级,跟着摇旗呐喊、以壮声威而已,结果因缘时会,搭上了这班历史顺风车,轻而易举地成为这次革命的最大受益者。这场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清除了制度障碍,但它丝毫没有改变统治集团的人事布局,在革命之后,真正主宰国家命运的依然是大大小小的土地贵族。在思想上,这场革命也未能产生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意识形态,例如法国革命产生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精神。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来说,这场革命只改变了英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却没有改变其封建色彩浓厚的上层建筑。在此后的三百年里,大权在手的土地贵族与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逐渐融合,形成了一个复合型的统治集团,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霸权阶级。土地贵族的阶级意识成为英国社会的霸权意识形态,保守成性的“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和因袭旧俗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至于资产阶级,既屈从土地贵族的声威,又害怕法国革命和本国工人运动,益发丧失了挑战土地贵族的意愿和胆气,他们无意另起炉灶,而是固守支离破碎的经验主义,不愿通盘重新审视社会,只满足于内部的改良折中,零打碎敲地改造社会制度,以保护自己的最大利益。按照安德森的分析,这就是现代英国在文化上因循守旧、在政治上寂静无为的症结所在。
在研究英国社会保守主义成因的著述中,这是最早的一篇马克思主义论作,它与安德森后来发表的两篇长文《民族文化的构成》(1968)和《逆流中的文化》(1992)一道*PERRY ANDERSON. “Components of the National Culture”(1968); “ A Culture in Contraflow”(1990),in Perry Anderson.English Ques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1992: 48-104,193-301.,为解读英国国民性和社会文化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钥匙,在史学和文学领域均有一定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风行一时的文化史名著马丁·威纳的《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就明显带有安德森的上述思想印记,这本书甚至影响了撒切尔政府新保守主义的经济决策,[9]在文学领域,安德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伊格尔顿的英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当中。
二、 《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文学研究的政治使命
1976年出版的《批评与意识形态》是伊格尔顿的成名作,争议最多,影响甚大。该书尖锐地批评了20世纪英国的三股文学批评思潮:以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批评、利维斯的细绎派批评和雷蒙·威廉斯的“左翼-利维斯式”批评。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文学功能论:文学的主要作用不在于产生审美愉悦,如传统的人文主义批评之所论,也不在于反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如传统马克思主义批评之所见,文学的主要功能就是产生审美意识形态,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发掘文学中暗含的意识形态话语规律。
此书的一大亮点是,作者从社会思想史的角度重新阐释了威廉斯发掘的“文化与社会”的传统。这是威廉斯在文学批评名著《文化与社会》一书中首次揭橥的现代英国所独有的一股人文主义思潮。[10]从18世纪到20世纪中叶,从英国现代保守主义的鼻祖伯克(Edmund Burke)开始,直到20世纪的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这一百多年间的大部分作家、思想家和社会改良者,都是这个传统中的思想要角。威廉斯没有系统地归纳出这个传统的核心观点,但细读此书之后,我们还是可以大致总结出其基本要义: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有着一种自然和谐、自成一体的有机文化(organic culture),然而,自从工业革命勃兴以来,这种有机和谐的社会文化,遭到了人为造就的工业文明的侵蚀,整个社会变得唯利是图,人心不古,道德缺失,人的心灵也变得机械麻木,文化水准江河日下,文化欣赏品味也今不如昔,社会的精神和思想危机也由此而产生。若想摆脱这个危机,出路只有两个,一个是文化保守派的方案,重建有机社会(organic community),重申文化价值,对抗机械性的资本主义文明;另一个是政治激进派的方案,推翻工业资本主义,另建新的文化与社会形态,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在文化与社会的传统中,文化保守主义者占据大多数。威廉斯对这个传统有发现之功,也有深入反思,尤其对它美化中世纪的做法的批判,很见思辨功力,但作者在写作此书之时,尚未摆脱利维斯的影响,因此,他的行文论述还是以细绎派的经验式考察为主,重在寻章摘句、文本分析,缺少系统连贯的理论思辨,他既没有为这个传统归纳出一条清晰的思想主线,也没有解释它的社会历史成因,好在伊格尔顿替他完成了后面这项任务:
“19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面临着一个严重问题。由于它生长在思想贫瘠的功利主义土壤中,无法生发出一套具有强烈感染力的神话,曲尽人们对英国社会的切身体验,因此,它只好经常求助于浪漫派的人文主义遗产,它把伯克式保守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混杂在一起——后者是科尔律治晚年从德国舶来的,传给了卡莱尔、迪斯累里、阿诺德和罗斯金,这就是所谓文化与社会的传统。这种传统从唯心主义角度批判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但同时又神化了私有制。19世纪英国意识形态特有的复杂性就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安东尼奥·葛兰西所说的“有机”因素与“传统”因素的矛盾统一体当中。19世纪的英国意识形态建立在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在统治集团内部复杂联合的基础上。思想贫困的经验主义,无法上升到真正的意识形态层面,不得已,它只好去利用浪漫派丰富的人文主义象征资源,援引它抽象的思想认可和准封建制的社会模式,以确认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文化与社会的传统就是这种意识形态联盟的文学记录。”[5]102-103
这段阐述文字简短,但内涵颇丰。如果读者不太了解上述人物及其思想,是很难理解其中的奥义的。现根据《文化与社会》中的相关论述,对这段文字略作申说。按照伊格尔顿的理解,“文化与社会”的传统有两个思想来源,一是埃德蒙·伯克的贵族式政治保守主义,二是科尔律治从德国浪漫派那里引进的“有机论”思想;它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分工,强烈抨击以金钱交易为基础的工业社会。二者对工业文明的严词批判,深刻影响了一系列英国作家和学者。卡莱尔说,机器生产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也改变了人的心灵状态,使人的思想日益机械化;保守党政客、小说家迪斯累利在小说《两国论》中控诉说,工业革命造成了惊人的贫富分化,英国俨然已经分裂为穷人和富人这两个国度;罗斯金为了表达他对工业文明的厌恶,转而热捧中世纪哥特艺术;马修·阿诺德批判英国中产阶级禁欲克制,崇尚实利,俗不可耐,认为他们急需理性、雅致的思想文化的陶冶,涤除市侩习气。19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塑造者是由两拨人构成的,一派是资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为资产阶级张目的有机知识分子,另一派是依附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传统知识分子,这两派貌似水火不容,但在英国却殊途同归,站在了一面大旗之下,一边攻击唯利是图的工业主义,一边维护财产私有制。换句话说,“文化与社会”的传统中的大多数人,固然批判工业资本主义,但他们多从贵族式的保守主义立场和浪漫派理想主义出发的,他们所推崇的前工业时代的有机社会,实质是一个等级制度分明的社会。这种有机论观念的潜台词是:社会各阶级要各司其职,安于身份和财产的不平等现状。在19世纪新出现的功利主义,由于浅陋粗疏,缺少精深的思辨,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辩护过于露骨,很难成为一套让人信服、赢得社会共识的意识形态,而英国传统的经验主义,因其就事论事、支离破碎的思想缺陷,缺少系统性、条理性和前瞻性,显得目光短浅、思想贫血,也无法上升到深刻的意识形态层面,这样一来,“文化与社会”的传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主导意识形态的替代物。
对照安德森的《当前危机的起源》,就不难看出,这套保守主义底色浓重的意识形态,自有其历史和现实的社会基础,那就是作者所揭示的近代英国独有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种以政治妥协、思想融合为特征的资本主义路线图,造就了商业、金融资产阶级和商业贵族的历史大联合,决定了近代英国统治集团的人士布局,赋予其社会文化思想以保守主义性质,就此而言,“文化与社会”的传统就是英式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折射。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在这本书中,伊格尔顿既没有提到安德森的名字,也没有提到他的任何著述,只见他反复引用葛兰西,既然如此,是否可以认为:影响他的只有葛兰西,而无安德森?有这种疑问是非常正常的,尤其是因为,伊格尔顿又引用了葛兰西关于英国土地贵族与工业资本家思想媾和的论述:“有一种广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们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经济集团而出现,但是,在更高层次的领域内,我们发现,旧有的地主阶级几乎还保持着垄断地位,它失去了经济领导权,但它被新兴的统治集团当作传统知识分子接纳吸收,为其出谋划策。旧式土地贵族与工业家的这种结合方式,在其他国家,体现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新兴统治阶级站在了一起。”[5]103
显然,伊格尔顿在这里继续强化读者的印象:影响他的分析的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不过,检视他所援引的葛兰西的《狱中札记选》后,[11]即会发现,在这部零散的思想笔记中,只有这么一小段涉及到英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复杂性,遑论深入探讨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成因。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读过安德森的《当前危机的起源》,如果没有它所提供的历史框架的话,仅凭葛兰西的这寥寥数语,是很难做出内涵如此丰富、历史感如此强烈的分析的;况且,伊格尔顿提到的经验主义的思想缺陷,也正是安德森在文中极力论证和指出的。
书中还有一个亮点,那就是作者对马修·阿诺德文学批评的政治解读。作为现代英国文学批评的奠基人,阿诺德并不是追求系统的理论家,他从来没有演绎出一套批评模式,供人依样画葫芦,但他的一些零散的批评观念却影响很大,流传久远。像人们熟知的“文学指导人生”这类说法,就肇始于阿诺德。在他的批评名篇《当代批评的功能》以及名著《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12-13]阿诺德坚持不懈地宣扬,文学就是人生的批评,大文豪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以遒劲的笔法、优美的形式,用思想观念去指导生活,解决人生在世如何安身立命这一问题;至于文学批评家,理应实事求是地看待事物(see the object as it really is),以客观中正、不偏不倚的态度去赞赏和发扬古今思想和言论的精华(the best that is said and thought)。他的其他批评理念,例如,“希腊精神”“希伯来精神”“无功利性”“美好与光明”等等,常被人不加引用地采纳,渐次成为共识,读者耳濡目染既久,也就无暇追溯其渊源所自了。从T.S.艾略特、I.A.瑞恰慈到F.R.利维斯,这一脉自由派批评人士,无不受这套自由人文主义的熏陶;从雷蒙·威廉斯到特里·伊格尔顿,这一干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在钦敬之余,也经常与他进行思想商榷、隔代交锋。
从马修·阿诺德文学和社会评论中,伊格尔顿看出了其中蕴含的文化政治用意,并加以系统分析,这在英国文学批评史上,尚属首次。从他的分析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念兹在兹的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安德森的近代英国历史独特论:英国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在政治和文化上日益融合而非断然决裂。阿诺德看到,英国贵族阶级在政治上逐渐失势,而资产阶级只管闷声发财,忽视精神修养,缺乏接班的文化资本,于是,他就严厉敦促资产阶级加强思想修养,继承贵族阶级的文化霸权,进而收编无产阶级,成为社会的共主:“资产阶级缺乏曾经赋予贵族阶级统治合法性的那种无处不在的精神主导地位;除非它能够迅速取得这种文化主导权,使自己作为一个真正的全民阶级安然处在社会的‘思想中心’,否则它就无法完成在政治上收编被剥削阶级的历史使命。”[5]105在建立文化霸权过程中,资产阶级必须借鉴贵族高雅精致文学审美情趣,只有这样,它才能占领文化制高点,造就振臂一呼、普罗云从的喜人局面:“资产阶级必须吸收没落贵族文明的审美遗产,以便为自己配备一种能够打入大众之中的意识形态。在一个‘温文尔雅、思想自由、受人尊敬、脱胎换骨的中产阶级身上’,无产阶级会找到‘欣然向往的目标’。”[5]106不言而喻,在这种文化“勾兑”过程中,贵族阶级的保守主义价值观和审美情趣必然会见缝插针,悄无声息地渗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中。阿诺德本人厕身其中的“文化与社会”的传统,就是这种思想渗透的明证,就此而言,“文化与社会”的传统也为安德森的史论提供了形象有力的文学证据。
三、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英国文学研究的制度化
20世纪西方文论以文本中心论起家,以形式研究为主导,以揭示作品的“文学性”为己任。然而,自60年代结构主义兴起以来,形式主义批评自身的“文学性”却大大降低,理论性增强,可读性弱化,几乎沦为哲学和社会理论的婢女。个别极端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和批评,文字生涩,术语满纸,仿佛恶鬼画符,令人无法卒读,其曲折含义,即便是行家里手,也很难心领神会。在此情势之下,从70年代开始,专事解说当代文论、进行理论稀释的各式“导论”便应运而生。
在这类著述中,影响最大、流布最广的莫过于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自1983年初版面世以来,该书不断重印,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对于当代文论的普及居功厥伟;如果说雷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的《文学理论》是新批评的圣经,这本“导论”堪称当代西方文论的圣经。由于成书较早,它只覆盖了20世纪西方文论的半壁江山:英美新批评、现象学和阐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读者无法在正文中审视作者对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述评,只能在1996年的第2版后记中窥视其精彩点评了。不过,本书的价值并未因此而降低。首先,它不是那种入门级的浮泛之作,而是面向研究者的高端之作,多有新颖独到之见;其次,文字洗练流畅,插科打诨、讽刺幽默一时俱来,在亦庄亦谐之中,表露出作者深厚的思辨功力。
写的最出彩的是第一章“英国文学(研究)的兴起”,[6]常被收入各式批评文选。它主要讲述了英国文学研究如何在大学成为一门常设学科,揭露它如何与现实政治暗通款曲,批判了自由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虚伪的去政治化主张。在英国文学研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前,英国的大学,尤其是像牛津、剑桥这样的老牌大学,主要研究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以及语文学(历史比较语言学),英国文学研究固然存在,但并非大学中的常设学科;文学史研究只是学者在书斋中的个人爱好,文学批评也不过是作家业余遣兴的漫笔。直到19世纪末,英国文学研究才在大学迅速崛起,独立成系,尤其在综合性大学里,它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一门学科。
在伊格尔顿看来,英国文学研究在高校中地位陡然上升,是宗教的社会影响力日渐式微的结果。长期以来,宗教一直是维系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统治的有效意识形态。作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安抚力量,它致力于培养民众的服从、奉献和内省精神。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由于科学的进步和历史的变迁,宗教的社会功能开始减弱。在这种形势下,英国文学顺理成章地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填补宗教衰落后留下的意识形态真空,开始发挥宗教的社会功能。他还发现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最早设立英文专业的院校,还不是英国统治阶级的摇篮——牛津和剑桥,而是工人阶级子弟就读的“技工学院”、工人院校和大学附属夜校。原因很简单,统治阶级在利用英文研究来施行文化政治,从思想上收编工人阶级。伊格尔顿不无戏谑地写道,自从诞生之日起,这门“穷人的古典文学”就不断地给学生们洗脑:社会各阶级要和谐团结,要培养同情心,要有民族自豪感。不惟如此,英文研究还被纳入公务员考试范围,成为统治阶级界定自身的重要标准。精通英国文学成了帝国官员的标准配置,帝国文化“软实力”的体现,海外殖民的重要手段,经过文学文化的包装之后,大英帝国的官员就可以带着民族自信感奔赴海外,向殖民地人民炫耀这种文化的优越性。[6]28
细察之下,不难看出,伊格尔顿的这番制度揭秘,是在批判自阿诺德以降直至利维斯的自由人文主义批评路线,虽然作者没有明说,但我们不难领会其言外之意:文学批评始终是一桩隐蔽的政治事业,自由人文主义所谓客观中正、不偏不倚的论调,本身就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手腕,它悄无声息地完成了自己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共谋,完美地诠释了文学批评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此外,文学研究的制度化,也是贵族与资产阶级实现阶级融合的重要手段:“由于需要将势力日益强大而精神粗鄙的中产阶级与占统治地位的贵族结合起来,由于需要传播温文尔雅的社会行为举止、‘正确的’趣味习惯和共同的文化标准,文学获得了某种新的重要性。”[6]16作为文学研究制度化的重要推手,阿诺德是最早倡导这种阶级-文化融合的英国批评家。作为中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阿诺德已经看出,贵族阶级已经无力承担统治阶级的使命,而这个国家的新主人资产阶级,又缺乏一种精妙的意识形态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在这方面,他们只好求助于传统贵族,“这些贵族,阿诺德敏锐地认识到,已经不再是英国的统治阶级,但他们还是有一些意识形态库存,可以资助他们的中产阶级主人。”[6]23而这两大阶级在政治和文化融合过程中体现出的社会保守主义特性,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英国文学研究的制度化。
其实,早在阿诺德发出这番倡导之前,这种阶级-文化的融合就已经悄然进行了,新古典主义文学就曾经担当过这样的历史重任。18世纪的新古典主义文学理念即体现出贵族阶级的政治诉求。18世纪新古典主义中的理性、自然、秩序以及得体(propriety)等概念的产生,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它们折射出的是,在经历过17世纪的血腥内战以及一系列动乱后,英国统治阶级寻求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心理。[6]16在他的下一本书中,伊格尔顿更为详细地论述新古典主义文学理论如何服务于贵族与资产阶级的文化媾和事业。
四、 《文学批评的功能》:社会评论与政治妥协
1985年出版的《文学批评的功能》,仅有一百多页,但内容却相当的丰富,其中论述18世纪英国文学批评兴起的那一章最见思想功力,毕竟18世纪文学也是他的研究专长,也正是在这一部分,安德森的阶级融合论体现得至为明显。书中既没有谈英国文学批评的具体策略,也不去讲它的理论源流,而是大写特写18世纪以来英国文学批评的政治思想史。其核心观点是:当代英国文学批评已经与日常生活完全脱节,批评家不再去指点江山、擘划社会走向,文学批评也因而丧失了其原有的社会批评功能,它要么蜕变为文学产业的公关手段,要么偏安于高校文学系,成为教授兼批评家的谋生手段。[7]8
然而,在现代英国文学批评诞生之际,情况却与此完全相反。现代欧洲文学批评产生于资产阶级反对绝对主义国家的斗争中。当时资产阶级血气方刚,冉冉上升,面对依旧强大的封建势力,义无反顾地去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话语空间,进行理性评论和启蒙批判。这就是于日尔根·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它处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由俱乐部、报刊杂志、咖啡馆组成,吸引了一批文人雅士。他们在此坐而论道,指点江山,评说宦海风云,议论市井新闻,宣扬礼俗政教,品鉴文学艺术,陶冶思想情趣。有资格进入公共领域、进行平等交流的,来自社会各个阶层,这里的入场券不是贵族身份,也不是万贯家财,而是理性的思辨能力。随着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出现,文学探讨走出了贵族沙龙的小圈子,近代欧洲文学批评由此而产生。
在欧洲诸国当中,英国的公共领域出现得最早,但与欧陆大国不同的是,英国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不是封建贵族的死敌,而是它耿直的“诤友”:“鉴于英国民族的独特性,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因为追随政治绝对主义而得到巩固,而不是从内部去抵制政治绝对主义。”[7]10显而易见,英国公共领域的这种反常特性,成因于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历史融合。在18世纪初,期刊杂志是英国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主要组成部分,斯蒂尔主编的《闲谈者》和艾迪生主编的《观察者》为其中的翘楚,它们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塑造公共舆论,进而影响政府的一些政治决策。从二者的办刊宗旨和行文风格可以看出,英国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在努力制造社会共识,而非革命性决裂。它们一边挖苦讽刺生活放荡的贵族阶级,矫正其道德品行;一边仿效贵族的仪礼风尚,为资产阶级暴发户制定端庄得体的行为法则,培养其文化品位,进而推动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结盟,形成一个新的统治集团。例如,约瑟夫·艾迪生的文风“谑而不虐”,一边斥责传统的统治阶级,一边与其步调一致,避免烈性谩骂,体现出建立社会共识的良苦用心。
现代英国文学批评就诞生于这样一种政治妥协和社会共识的氛围之中。散文作家、小册子作者彼此舌剑唇枪,貌似无比激烈,但他们都是有政治底线的;哪些可以说,哪些不可以说,说到什么程度,大家心里一清二楚,而且,犯忌可能遭到严办,笛福就曾因言获罪,被当街示众。伊格尔顿举例说,在18世纪的法国,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文人与公共舆论截然对立,但在同时代的英国,塞缪尔·约翰逊这类批评家却与公众观点一致。这对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批评来说,绝对是一个讽刺。它打着反对绝对主义的旗号,但实际行为却是保守的、矫正性的,而不是颠覆性的。换句话说,它是社会改良性质的。在理性臣民之中传播文雅话语,在符号层面上弥合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差距,这是文学批评的历史任务,而完成这项历史任务的旗手就是斯蒂尔和艾迪生这样的文学批评家。
斯蒂尔的评论文章通常是就事论事和印象式的,缺少理论结构和主导原则;艾迪生的评论更具分析性,但他的文学批评,本质上还是经验主义的,走的是霍布斯和洛克的路数,追求打动人心的效果,很在意文学对读者的心理影响,而不是探讨技术性或理论性很强的问题。此时,文学批评还没有形成一种自主性的专业化话语,它只是广义上的人文主义伦理学的分支。就内容来说,《漫谈者》和《观察者》主要是评论艺术、伦理、宗教、哲学以及日常生活,文学评论还是很边缘的。严格来讲,它们的批评还不是文学的,而是文化的,本质上是提高资产阶级个人修养、为社会制定行为规范的一项文化工程。
伊格尔顿的上述评论和分析显示,与欧陆现代文学批评不同的是,现代英国文学批评在兴起过程中,就带有浓厚的保守主义特色,它非但不是反封建主义的利器,反而是弥合新旧阶级差异的文化粘合剂,它反映并且强化了当时的英国现实,即安德森所论述的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日益融合的趋向。在这本小书中,安德森的名字一次也没有出现,但是,从他的这些论述中可以感觉到,安德森的阶级融合论简直无处不在。
五、 启 迪
在阅读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长篇小说的时候,如果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样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欧陆长篇小说汲汲于丑化和抨击封建贵族,而英国小说却忙于讽刺和批评资产阶级,从而有意或无意地去回护贵族阶级。18和19世纪的欧洲文学,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史诗——长篇小说——以反映该阶级的思想心声、反抗封建贵族为主潮。揭露封建贵族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批判其保守陈旧的价值观念,这类主题在18、19世纪的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的文学中是屡见不鲜的,但在同时代的英国文学中却是凤毛麟角的,几乎没有一部英国小说名著全盘否定贵族统治和思想,美化贵族和乡绅生活的长篇小说和田园诗歌反倒层出不穷。在英国小说家中,描写封建贵族最多的非瓦特·司各特莫属。这位中世纪主义的文学代表,在他卷帙浩繁的历史小说中,不遗余力地颂扬骑士理想,而他本人在现实生活中也竭力模仿贵族的做派。按照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拉尔夫·福克斯的分析,司各特笔下的贵族人物实际上是他心目中的资产阶级的理想形象;[14]套用雪莱在《为诗辩护》中的名言,[15]司各特就是在为世人立法。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在18世纪英国哥特小说中,不是有大量的恶魔式贵族主人公吗?作者不是在丑化他们吗?然而,稍加留意,即会发现,英国哥特小说的故事背景大多设在欧洲大陆的天主教盛行的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在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国家都是英国的政治、经济竞争对手,也是清教的敌人,也就是说,这些邪恶的贵族多是外国人,且为天主教徒,就此而言,英国哥特小说简直是英国民族主义和宗教斗争的文学白手套。在19世纪的英国小说名著中,狄更斯的《双城记》对贵族的批判是最严厉的,但其中罪大恶极的贵族可不是英国人,而是法国人。在小说创作中,曲意回护贵族的做法俨然已经成为18和19世纪英国文学的传统,甚至到20世纪还绵延不绝。在工人阶级出身的小说家D·H·劳伦斯的笔下,《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中的克利福德男爵固然被描写成负面人物,他的门第观念和自私做派尤其招人厌恶,但是,对于他在那场帝国主义战争中的不幸遭遇,作者还是给予深切同情的,而他对康妮的死看硬守,也有一往情深的成分在内。
英国小说的这一显著特色,尤其是英国与欧洲大陆小说之间的这种显著差异,迄今尚未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其实,它们非常值得英国文学研究者、尤其是比较文学的研究者进行平行研究,系统考察,而安德森对英国近代社会性质和英国资本主义特色的历史探索,伊格尔顿对近代英国批评的政治思考,无疑会为这种视野宏阔的比较研究提供不可或缺的历史背景和极为重要的思想框架。
近二十年来,中国学界非常推崇文史互证的方法,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钱钟书的《管锥编》和《谈艺录》,常被奉为这种方法的典范。其要义与优势约略可以归纳为:以诗证史,弥补史笔之缺失,以史释文,曲尽作者之隐衷。但文史互证的范围,应不止于材料的补充、背景的还原和内容的互释,也应包括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借鉴。在这方面,伊格尔顿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他的英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袭用了安德森的史学研究思路,成功地揭示和阐释了英国文学研究中的保守主义特性及其历史起源,当然,他在上述研究中列举的大量案例,也为相关的历史研究补充了文学方面的佐证,有助于拓宽其思想视域。
[1]DAVID ALDERSON.Terry Eagleton[M].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04.
[2]JAMES SMITH.Terry Eaglet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M].Cambridge: Polity Press,2008.
[3]VICTOR N PAANANEN.British Marxist Criticism[M].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2000.
[4]TERRY EAGLETON,MATTHEW BEAUMONT.The Task of the Critic: Terry Eagleton in Dialogue[M].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09.
[5]TERRY EAGLETON.Criticism and Ideology: A Study i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M].London: New Left Books,1976.
[6]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2版.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7]TERRY EAGLETON.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from the Spector to Post-Structuralism[M].London: Verso,1984.
[8]PERRY ANDERSON.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1964)[M]//PERRY ANDERSON.English Questions.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1992:15-47.
[9]赵国新.英国工业资本主义衰落的文化起因说[J].外国文学,2014(2):143-149.
[10]RAYMOND WILLIAMS.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1958)[M].London:Penguin Books,1961.
[11]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M].London: Lawrence & Wishart,1971.
[12]MATTHEW ARNOLD.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M]// VINCENT B LEITCH.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New York and London: W.W.Norton & Company,2001.
[13]马修·阿诺德.文化和无政府状态[M].修订版.韩敏中,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
[14]拉尔夫·福克斯.小说与人民[M].何家槐,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61.
[15]PERCY BYSSHE SHELLEY.A Defence of Poetry[M]// VINCENT B LEITCH.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New York and London: W.W.Norton & Company,2001:717.
(责任编辑 杨文欢)
Origins of Cultural Conservatism in English Literary Criticism:Terry Eagleton and Perry Anderson
ZHAO Guo-xin
(SchoolofEnglishandInternationalStudies,BeijingForeignStudiesUniversity,Beijing100089,China)
Terry Eagleton’s critical works have been under multiple influences from various critics and theorist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which have been recognized and discussed in details in some relevant studies. However, another source of influence, the historical studies by Perry Anderson, has never been identified, much less examined up to the present day. The paper attempts to argue that, Perry Anderson’s insightful critical account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and the particularities of English capitalism shaped to some extent Eagleton’s fundamental view of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ry criticism, and provided him with an important socio-historical framework for reference to examine the inner connection between critical practice and real politics. Actually, Eagleton’s illuminating analyses of the cultural conservatism hidden in modern English literary criticism was greatly indebted to Anderson’s convincing explanation for the political conservatism explicit in modern English society. The paper also suggests that their works could be used for explaining an often-neglected phenomenon in the 18th and 19th English classical novels: unlike their counterparts of the same periods in major Euro-continental countries, they tend to avoid severely criticizing let alone completely negating the aristocratic thoughts and ruling at home.
Marxism; New Left; the “culture and society” tradition
2016-07-1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2JYC752047);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1WYB010)
赵国新,男,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文论及英国文学研究。
I06
A
1009-1505(2016)06-000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