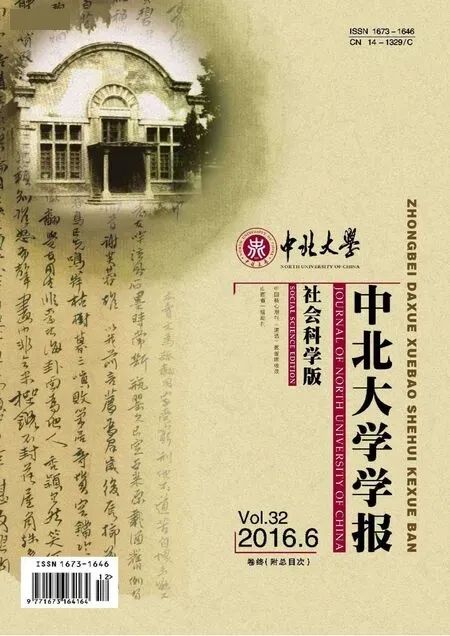走向疯癫还是实现自我?——论吉尔曼的女性主义叙事
2016-01-15温安琪
温安琪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
走向疯癫还是实现自我?
——论吉尔曼的女性主义叙事
温安琪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
以女性主义叙事学为理论基础, 探讨美国知名作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女权主义思想发展脉络及其现实意义。 吉尔曼在她的两部作品《黄色糊墙纸》和《她乡》中分别采用男女两种不同的叙述声音和叙述视角, 这是她女权意识不断觉醒, 女权主义思想不断发展的表现: 从要求给予女性话语权, 追求两性平等到承认两性差异, 强调女性价值, 推崇女性文化。 作者根据特定的社会现实和不同的写作意图采用不同的叙事手法, 使她的女权主义思想更易被读者接受, 从而产生极大的社会反响和现实意义: 女性只有夺回话语权, 树立话语权威和独立自主的意识, 才能消除偏见, 得到男性尊重, 打破二元对立思维, 与男性携手共创更高的社会价值, 共建多元化的和谐社会。
吉尔曼; 《黄色糊墙纸》; 《她乡》; 女性主义叙事学; 女权主义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女性主义文评与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相结合的产物, 是聚焦于叙事结构和叙事技巧的性别政治。[1]女性主义传叙事学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苏珊·S·兰瑟(Susan S. Lanser)和罗宾·沃霍尔(Robin R. Warhol)等。 兰瑟认为文学是两种系统的结合: 既可把文学视为对现实生活的模仿与再现, 也可从符号学角度将它视为对语言的建构。[1]2因此女性主义叙事学家会借叙事学的术语和模式来研究女性作家的叙事手法, 指出她们的作品有哪些结构上的特征, 采用了哪些技巧, 推翻由阅读印象来探讨女性写作的模式, 使分析更为精确和系统。
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是知名的女权运动先驱, 她一生不懈地为争取女性权力与自由而写作, 创作出了许多经典作品。 对于她的作品, 国内外的批评学家多从女性主义视角进行解读。 《黄色糊墙纸》(TheYellowWallpaper, 下文简称《黄》)是吉尔曼的女权主义代表作, 我国最早研究吉尔曼的学者朱虹认为《黄》是“在精神上非常接近当代的作品”[2]18。 其他学者则多从女性主义角度研究故事中的女性形象、 疯癫意象、 叙事策略, 认为这些都体现出吉尔曼反对父权制压迫, 争取女性解放的先进思想。 《她乡》(Herland)是吉尔曼创作的乌托邦小说, 吉尔· 拉德(Jill Ladd)、 托马斯·高尔特·珀塞(Thomas Galt Peyser)等国外学者多关注小说的女性社会性别、 思想内涵、 叙事角度等。 到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 有关吉尔曼的乌托邦小说的研究在中国兴起。 但国内对于《她乡》的研究较少, 且多从女性主义角度和文化角度研究书中的母职文化、 女性形象、 后殖民主义思想等, 或将《她乡》与《西游记》 《镜花缘》等古典小说进行比较研究。[3]学者们多认为书中建构的女性理想国是对父权社会的挑战, 为今天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借鉴。
吉尔曼的作品反响之大, 影响之深,其原因不仅在于她新颖的题材和内容, 更在于她独特的叙事手法: 革新叙事视角, 运用多层叙事结构, 使用象征和反讽等。 因此, 本文将从叙事学角度出发, 以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为基础, 对比分析两部作品的叙事手法, 探讨不同的叙事技巧下作者的女性主义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1 《黄色糊墙纸》与《她乡》中的叙事手法
1.1 女性叙述声音: 建构与强化女性话语权威
“声音”在叙述学中指叙事讲述者, 女性主义多用它指代身份和权力。 兰瑟在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中则认为叙述声音和被叙述的外部世界成互构关系。[1]她将叙事模式与社会身份结合, 关注性别化的作者权威, 注重探讨女作家是如何批判、 抵制、 颠覆男性权威及建构自我权威的。
《黄》和《她乡》采用的“个人型叙述声音”, 是故事叙述者和主人公为同一人的第一人称叙事。 作者视叙述者为其代言人, 通过主人公的语言和行为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形态。 《黄》中, 我们听到的是女性叙述声音, 《她乡》的故事则是由一位男性来讲述。 作为一名积极的女权主义者, 为什么吉尔曼会选择不同的叙述声音?著名叙述学家布思说过“在任何阅读经验中都存在着读者、 叙述者, 其他角色和读者之间的一种隐性对话”, 因此, 这是作者借不同的叙述者之口与读者交流, 以达到传达不同的女权主义思想的目的。
《黄》中的主人公——无名者“我”, 是名知识女性, 生产后患上抑郁症, 被丈夫带到乡村疗养, “在身体复原以前绝对不允许她‘工作’”[2]69。 作为女性, 尤其是一个“疯女人”, 她成为“弱者中的弱者”[2]78, 失去了“说话”的权利。 所以, 作者用个人型叙述声音, 赋予“失语”的主人公站出来为自己讲话的机会, 用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经历: “想方设法地把我所想到的和感受到的讲出来——讲出来了我才觉得轻松”[2]78, 这不仅生动地展示了她为挣脱父权制枷锁而走向疯癫的过程, 也表达了作者的女性抗争意识及对当时男权社会压迫女性的批判。 这种叙事模式也建构出某种以女性身体为形式的女性主体的权威。[4]24
通过主人公的叙述, 读者知道了老宅“是一座殖民时期的大厦……我还是要自负地断言, 这座大厦使人感到有点古怪”[2]68。 丈夫约翰则“是个极端现实派。 ……不喜欢我写哪怕一个字, 告诫我不要被幻想俘虏”[2]68-69。 约翰的妹妹“那么关心我……我完全相信, 她以为我是因为写作才得病的”[2]75。 还有那令她发狂的“窗子上……装有栏杆, 墙上还装着铁环”[2]71的育婴室和“颜色令人讨厌, 令人恶心的”[2]71糊墙纸。 作品还运用通感, 从视觉转到嗅觉, “那墙纸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它的气味!……一种黄色的气味”[2]85。 她将所看所感毫无保留地告诉读者, 读者获得的信息都来自她的主观感受与判断, 在情感上更易与叙述者产生共鸣, 使叙述者在受叙者面前享有绝对的叙述权威。
然而, 小说采用日记体形式, 意味着即使主人公可以畅所欲言, 那些话语也只是她将其他人物阻隔在外的内心世界的偷偷表达, 对于象征男性权威的丈夫来说, 她的话语在他眼中是“有些精神质和歇斯底里的病人”[2]69发出的, 是微不足道的。 书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约翰他十分爱我, 不喜欢看见我生病, 有一天, 我试着和他进行一次真诚的谈话, ……在他面前我表现得很糟糕, 还没说完就放声哭泣。”[2]79吉尔曼虽然大力倡导女权和社会改革, 但她作品中的女性在有力度、 有权威的男性言语前, 依然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愿, 这暗示现实中女性话语权威在男性面前的崩溃瓦解。
1.2 男性叙述声音: 对男权文化的反思
作者在《她乡》中反常地使用了男性叙述声音。 不同于其他女性作家为了获得话语权, 匿名或模仿男性作家的叙述口吻来表达自己的意识, 吉尔曼以男性叙述声音这种隐退的方式掩藏自己的女性身份, 表面上似乎淡化了自己的作者权威, 实际上是避免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观点或偏见, 将权力下放给读者。[5]笔者认为其原因是由于男性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 享有话语权, 代表的是智慧、 理智和权威, 女性则代表感性, 她们的声音是不可信甚至是“听不见”的。 因此让男人说话, 掌握叙述权, 可使故事更具说服力。 作品中颇具地位的三名男性从继承社会既成的偏见到认可和赞扬女性的价值、 自我检讨传统社会以男性为主体的价值观的这种转变, 让作品传达的思想更容易被社会大众接受。
作为吉尔曼乌托邦三部曲的第二部, 吉尔曼推崇的女性理论是“强调性别差异, 颂扬女性文化, 彰显女性价值观”[6]。 小说中, 吉尔曼积极建构着“她乡”这个神奇的国度, 批判现实中的男权中心文化, 男人在她乡学会欣赏女性文化的历史, 尽显女性话语和文化的辉煌。 书中, 三个男人被囚禁在一个房间里, 学习她乡的语言。[1]39并且“对这门语言是很感兴趣的。 看到她们有书, 就迫切想要读懂并深入了解她们的历史, 如果她们确有历史的话。 她们的语言不难说, 听起来通顺悦耳, 而且读写非常简单”[7]47。 吉尔曼对男权文化的解构与对新话语和新文化的建构并非一蹴而就, 叙述者慢慢地接受并使用她乡的语言, 男权话语逐渐式微, 并最终被一种“母性的语言”所代替[5], 说明父权制社会和母权制社会的矛盾被淡化, 女性话语也可以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
1.3 叙述视角: 疯癫叙事与理性叙事
1.3.1 女性主义叙事学下的叙述视角
叙述视角指叙述时观察故事的角度。[8]88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多关注叙述视角与性别政治的联系, 将注意力集中在叙述视角所体现的性别政治上。 他们认为叙述视角(聚焦者)与观察对象(聚焦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意识形态关系或权力关系。[8]215传统文学作品多采用男性视角, 使女性成为被凝视的对象, 在宣扬男性意识形态的同时压制女性意识。 而《黄》与《她乡》中, 作者虽采用了不同的叙述视角, 却都体现出先进的女性意识, 塑造出独立自主, 追求平等的女性形象。
女性主义叙事学领军人物罗宾·沃霍尔认为“看”和“被看”反映出一种带有性别色彩的权力争夺。 女性必须认清自身性别身份, 由被“凝视”的客体变成主动“观察”的主体, 以解构男性话语, 掌控叙事行为, 通过叙述话语传递女性观点与意识形态, 获得叙述主动权, 确立话语权威, 提升她们在文本中的地位。[9]书中女主人公被照顾她的妹妹, 一个“十全十美的女管家”[2]75约束, 丈夫也总是默默观察着她的状况, 这种“照顾”对于她就是“被监视、 被观察”。 她成为被“凝视”的客体, 无法掌控自己的身体和思想。 但作者也赋予了主人公“观察”别人的权力。 通过第一人称经验视角, 用女主人公的眼睛来推动故事的发展, 让她拥有了叙事主导权, 成为聚焦者。 丈夫、 房子、 墙纸则成为聚焦对象。
观察丈夫时, 她“总是在他不知道我在看他的时候注视着他”[2]83, 在她眼中有时候约翰“显得很古怪, 甚至连珍妮的表情也有点莫测高深”[2]83, 最后甚至发展成“有点害怕约翰”[2]83。 简单几句话, 便让约翰典型的父权制家长的形象深入人心, 让读者感受到丈夫代表的父权文化在主人公内心造成的压力。 对最具象征意义的黄墙纸, 主人公也是“一连好几个钟头都盯着这些图案……那些图案在有些地方没有褪色, 当阳光正好照射在它上面的时候, 我就看见一种奇怪的、 使人烦恼的不成形的人影, 在那可笑的惹人瞩目的正面图案背后悄悄地移动着”[2]76-77, 那模糊的人形是个女人, “她一直企图爬出来, 但谁也穿不过那图案”[2]87。 读者正是透过这些叙述察觉主人公日渐疯癫的精神状态, 对她产生怜悯与同情。
女主人公既是叙述者也是聚焦者, 叙述者把视界局限在自己身上, 没有任何参照, 如文中丈夫的话语大多以间接引语的形式出现, 读者没有判断的依据, 不免让人觉得主人公的叙述混乱, 不合逻辑甚至不可靠。 但是叙述者让读者通过主人公的眼睛来观察她周围的人和事物, 直接的内心独白充满主体性, 更加真切地再现了主人公的意识活动。 她看待事物的眼光和感受也投射到自己身上, 这是聚焦者与读者之间潜在的对话与交流, 主人公的种种情感读者都能够切身体会, 通过她的叙述读者参与了她心理崩溃的全过程, 走进了主人公的内心。 虽然叙述者最后走向疯癫, 但是读者却明白她想要在艰难的环境中生存, 只有建构疯癫这样的“特殊策略”。 这激发了读者对她的理解与同情, 以及对丈夫所代表的父权制社会对女性压迫的强烈控诉与谴责[10]。 作者通过一个疯女人的视角, 利用疯癫及其疯癫叙事者的叙事, 抨击父权文化对女性身份的定义、 推翻父权制男性思维和话语对女性思维与话语的统治, 抵制父权文化对女性文学创作压制, 让女性争夺原本属于男性的叙述主体地位。
1.3.2 《她乡》中的男性叙事视角
在男权文化中心社会, 女性被认为是男性的附属, 没有表达权。 在以男性视角讲述的小说中, 女性形象任由男性塑造, 这使失语又失真的女性形象在男性作家的作品中极为常见。 《她乡》通过社会学家Van的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 让现在的“我”回忆当时的“我”的故事。 虽然聚焦者是男性, 聚焦对象是她乡及她乡里的女人们, 女人们仍是“被观察”“被凝视”的对象, 但作者通过聚焦者前后视角的对比, 及故事人物不同视角的对比颠覆了传统的女性形象与两性关系。
故事开头, 叙事者仍用传统视角看待她乡和女性。 当他们看到她乡的全貌, 有“很多可爱的街道及其里里外外的建筑物、 美丽的公园”, 以及那些“冷静, 严肃, 聪慧, 无所畏惧, 显然充满信心, 意志坚定”[7]27的女性时, 他们认定有男人存在, 否则这里不可能出现进步和发明。 主人公的怀疑暗示了他们对女性创造文明的不信任, 是从男性视角反映出的现实社会中女性受压迫的真实情况: 女性是附属品, 是第二性。[11]
但在她乡生活、 学习期间, 三位男性逐渐意识到她乡是个美丽整洁、 规划有序的“文明进化的国家”, 那些女性“在智慧和行为上, 确实展现出了很高的水平, 远超我们目前掌握的那些”[7]106。 他们原先的观念被颠覆, 正如叙事者后来所说: “在我越来越欣赏这些女人的成就的同时, 我对男性成就的骄傲也在一点点地丧失……那时, 我们在女性的问题上是一点都不进步的。”[7]83传统的眼光不再适用, 叙述者的反思表达出作者希望男性可以转变传统视角, 客观地看待女性, 检讨传统社会以男性为主题的价值观, 将女人当做“人”来看待, 认可女人作为“人”的价值。
女性主义叙述学对聚焦者眼光与人物眼光互为加强或互为对照的关系也很关注。[8]215男主人公Van除了从自己的角度观察周围的事物与人, 向读者传达自己的想法外, 还对比了其他故事人物的视角: “当杰夫说扎瓦小姐——总不忘加上——和蔼可亲。 但特里总是对他的老师冷嘲热讽。”[7]47当叙述者和杰夫由衷地欣赏这个国家的优点和管理时, 特里却“依旧很挑剔”[7]104。 三人视角的对比表明生活在父权制社会下的男性来到她乡, 男性权威得不到重视甚至受到威胁时, 男权意识和性别偏见依然根深蒂固。 这表明在现实生活中, 即使社会进步、 妇女意识逐步觉醒, 要消除不平等的性别观念任重而道远, 吉尔曼所建构的女性理想社会依然具有很强的乌托邦性。
对比更为强烈的是男性和女性看待事物的感受和体验。 首先, 他们对各自的性别身份定位不同, 她乡中不存在“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的二元对立, 女人也不是传统男权文化视域中的女性类型, 她们身手矫健, 在气质上个个才情横溢、 精明能干、 独立主动、 理性果断。 其次, 也没有社会分工的不同。 她乡中的女人, 穿着讲究实用, 不用取悦男性。 她们还与男性一样承担社会责任, 创造出相同甚至更高的社会价值。 这是作者对男权文化逻辑的一种挑战。 最后, 她乡的女人认为未来是充满希望的: “她们的理想是如此崇高!她们祈祷着美丽、 健康、 聪颖、 善良, 并为此不懈努力。 她们没有敌人, 彼此全是姐妹或朋友。 面对如画的江山, 一个美好的未来开始在她们脑海里构建。 ……她们真的准备相信我们那儿是个更好的世界。”[7]82反观现实的男权社会, 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冲突随处可见, 未来充满悬念。 作者在这里是想宣扬她乡互助友爱、 共建和谐社会的精神。 她结合女性主义理论前两阶段的观点, 试图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呼吁男性用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去看待女性、 接受女性, 最后男女之间呈现百家争鸣的多元化局面。
故事的结尾, 叙述者带着妻子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也带回去了她乡先进开化的社会意识, 她乡人民健康活力的标准、 冷静平和的脾气、 卓越的智慧与修养。 他们是和现代人共同建设如她乡般美好的社会, 还是最终被同化,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她乡的存在提供了一种途径, 这也是吉尔曼建构女性主义乌托邦的深远意义, 以一种理想的乌托邦社会作为目标并朝着目标大胆前进, 才能争取到自由, 建设充满前景的社会。
2 吉尔曼叙事手法的意义
《黄》和《她乡》中没有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或复杂多变的人物, 吉尔曼采取与传统小说不一样的叙事策略, 让作品产生极大的影响力。 《黄》中疯女人的叙事声音和叙述视角, 让读者深入了解主人公的内心世界、 生存方式与人生体验, 促使人们反思女性生活现状, 抨击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压迫。 而《她乡》中的男性叙述则体现了作者不拘泥于传统女性主义, 推崇更具包容性的女权主义思想, 对消除性别差异、 构建两性和谐的社会具有指导意义。
主题与叙述形式的完美结合, 使这两部作品在展现文本信息、 表现美学效果的同时, 又让读者产生共鸣, 更加深刻地领悟到作品体现的女权主义思想。
3 结 语
吉尔曼从女性立场出发, 运用不同的叙述技巧, 采用了不同的叙述声音和叙述视角, 在《黄色糊墙纸》和《她乡》中重新给予女性话语权威, 表现了她不断发展的女性意识。 从疯女人到独立自主的女性, 从向父权制社会提出挑战到建立一个女性主义乌托邦, 吉尔曼的女权主义思想对我们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1]Lanser S S. Toward a feminist narratology[J]. Style, 1991(3): 21.
[2]朱虹. 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3]曾桂娥. 结构与建构——吉尔曼女权主义乌托邦研究[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9.
[4][美]苏珊·S·兰瑟. 虚构的权威[M]. 黄必康,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5]刘英, 张建萍. 从“他乡”到“她乡”, 吉尔曼女性主义写作策略的转变[J].妇女研究论丛, 2006, 4(7): 67-72.
[6]Kristeva J, Blake H. Women’s time [J].Signs, 1981, 7(1): 13-35.
[7][美]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 她的国[M]. 朱巧蓓, 王骁双, 康宇扬, 等译.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
[8]申丹, 王丽亚. 西方叙事学: 《经典与后经典》[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9]Warhol R A. The look, the body, and the heroine of persuasion: a feminist-narratological view of Jane austen[J]. Novel A Forum on Fiction, 1993, 26(1): 5-19.
[10]肖向阳. 我们是如何相信一个“疯女人”的述说的?——论《黄色墙纸》的叙事技巧[J]. 语文学刊, 2009(8): 5-7.
[11]陈大为. 构建女性乌托邦——女性主义下《她乡》中的她者世界 [J].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13, 22(8): 69-71.
Going to Madness or Self-Realization——Charlotte Gilman’s Feminist Thoughts
WEN Anq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Founded on Feminist Narratology,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and realistic meaning of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s Feminism. In her famous representative works,TheYellowWallpaperandHerland, Gilman respectively used female and male narrative voices and angles, which represented her developing female consciousness and thoughts: from fighting for female discourse and gender equality to admitting gender differences, highlighting the values of woman and praising highly of female culture.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ocial realities and writing purposes, Gilman adopted different narrative techniques to make her Feminism more acceptable to readers so that it could have greater repercussions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which is that only if women recapture the right to speak, and establish authority discourse and independent feminine consciousness, can they erase social biases, win men’s respects, break binary oppositions and higher creative social values, and construct a harmonious pluralistic society.
Gilman;TheYellowWallpaper;Herland; feminist narratology; feminism
1673-1646(2016)06-0105-05
2016-06-13
安徽大学研究生学术创新研究扶持项目: 走向疯癫还是实现自我?——论吉尔女性主义叙事(yfc100086)
温安琪(1992-), 女, 硕士生, 从事专业: 美国文学。
I106.4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6.06.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