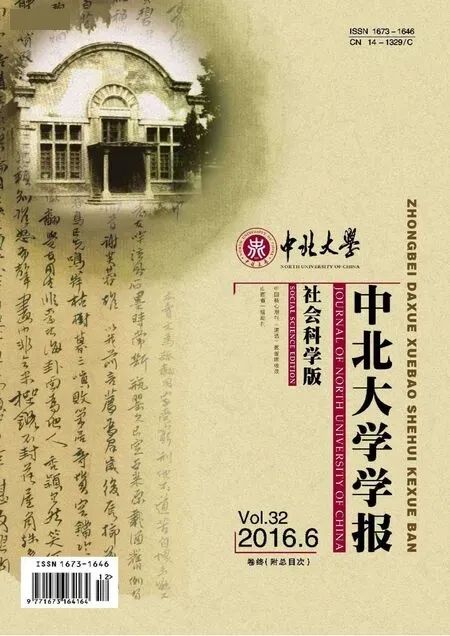试论新时期小说中的传教士形象
2016-01-15侯旭,王姮
侯 旭, 王 姮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1)
试论新时期小说中的传教士形象
侯 旭, 王 姮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1)
新时期以来许多小说中都出现了传教士的形象, 有些甚至直接以传教士为描写对象。 这些传教士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教, 在面临战争、 教派教义纷争、 发展不到信徒等各种困境之时, 仍然坚持传教, 执着于自己的信仰。 他们的形象既弥补了当代社会信仰缺失、 道德异位等现实问题, 又是作家直面人生、 反思人性、 塑造理想形象的主动选择, 给读者们带来了新的审美取向和价值标准。
新时期小说; 传教士形象; 价值与意义
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至唐朝, 习惯上, 我们把这些传教的神职人员统称为传教士。 建国后, 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迅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各类文学创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在新时期文学的小说创作中, 一大批以传教士为描写对象的作品纷纷出现, 如1994年莫言《丰乳肥臀》中的马洛亚神父, 2004年范稳《水乳大地》中的杜朗迪神父和其《大地雅歌》中的沙利士神父, 2009年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传教士老詹, 2011年严歌苓《金陵十三钗》中的英格曼神父和阿多那多神父, 2012年李锐《张马丁的第八天》中的高主教和张马丁等等。 无论是被称为“神父” “师父”, 或是“主教”, 这些角色本质上都是传教士, 都怀着把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最初希望。 这些传教士首先是“外国人”, 他们迥异于国人的外貌直接刺激了中国人的感官, 加之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的西方文化传统, 都为他们的传教带来困难。
1 新时期小说中传教士形象出现的原因
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中, 传教士大都以正面形象示人, 或至少是拥有令人动容的正面性格。 传教士所特有的异域文化特色, 注定了它带有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色彩。 所谓比较文学研究的形象学, “是三重的形象: 它是异国的形象, 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 文化)的形象, 最后, 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1]。 因此, 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大量地出现传教士的形象, 自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创作原因。
1.1 小说中人物的塑造是作家自主选择的结果
新时期以来, “传统意识形态的陈旧格局被打破……作家们不再依照对社会的共同理解来进行创作, 而是以个体的生命直面人生, 从每个人都不相同的个人体验与独特方式出发, 来描述自己眼中的世界”[2]。 社会环境的相对宽松, 作家创作的自由度相对提高, 可以自由书写自己的思绪和对世界的认识。 文学作品写什么、 怎么写, 很大程度上是作家在自身已有的知识经验、 生活阅历、 信念信仰的基础上进行的。 第一, 作家的知识储备是他们创作的源泉。 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中, 不只哥特式的尖顶天主教堂象征着基督教文化, “十三”这个数字也是颇有深意的。 有学者解释说, “十二”其实是指向了基督周围的十二使徒, 另一个人则是基督十二使徒之外的另一个使徒保罗。 “在基督教的文化之中, 保罗的关键的地位在于他给予了基督教关键的传播的机会。”[3]整部作品都在讲述着救赎与被救的故事, 其中的宗教意蕴不言而喻。 第二, 作家的心态也是影响创作的重要因素。 所谓作家心态, 是指“作家某一时期 , 或创作某一作品时的心理状态, 是作家的人生观、 创作动机、 审美理想、 艺术追求等多种心理因素交汇融合的产物, 是由客观的生存环境与主体生理机制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4]。 正如作家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深情地写道: “尽管美国人和意大利人正在欧洲互相残食, 但他们的神父在我的故乡却携手共进, 共同从事着慈善事业, 在尽力救着我多得不可数计的乡亲的命。”[5]传教士救命的恩情在作家刘震云的故乡广为流传, 传教士的正面形象也由此深入到作家的内心。 第三, 作家长久以来的文化信仰也决定了他们用什么样的笔调来塑造人物。 自古以来, 中国人就拥有对“神”的信仰, 相信在自我言说、 与他人对话的同时, 还有存在于高空中的神灵, 监督着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 这种“举头三尺有神明”的传统观念不在于中国人选择“信”什么, 而是什么值得去相信。 李锐在创作谈中说道: “在我的小说里东方和西方是同时登场的。 ……所有的生与死、 善和恶、 爱和恨、 沉沦和拯救、 忠诚和背叛、 高贵和卑贱, 都不仅超越了国家和民族, 也更超越了文化和宗教。”[6]中西方的神外在形态各异, 但大都是自己民族集体的想象, 寄寓着美好的民族理想。 作为神的旨意在人间的布道者, 传教士的形象便自然有其光辉的一面。
1.2 源自作家对历史的思考, 借助传教士这一历史形象, 表现对动荡年代的反思
历史上的传教士大批量入华主要是在清末明初,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 这是中国社会战争频繁、 灾害不断的时代, 人民生活痛苦不堪。 作家是否应该对残酷的历史进行反思, 历来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 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曾说:“奥斯辛威集中营之后的一切文化, 包括对它的迫切的批判都是垃圾……任何漂亮的空话、 甚至神学的空话都失去了权利。”[7]在超乎人类道德底线的残酷杀戮之后, 面对人性的灾难, 无论是对野蛮罪行的谴责或批判, 还是饱经沧桑后的沉重反思, 亦或是歌颂和平与自由的妙曼诗歌, 都无法最真实地还原苦难本身。 但是, 尽管痛苦彷徨, 作家还是要勇敢地执笔书写, 因为文学的职责之一, 就是反思苦难, 于痛定思痛中发现未来的曙光。 “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在牢笼已经被拆除很久之后, 去摧毁暴政使其受害者与观望者仍然沦为囚徒的潜力。”[8]从最丑恶的人性深处爆发出来的暴力、 冲突、 战争一次次登上历史的舞台, 从原始的木棍石块到现代的鱼雷导弹, 每一次都有看似正当、 正义的理由, 每一次都有“士可忍孰不可忍”的借口。 归根结底, 还是人性的贪欲和暴虐。 回忆苦难, 书写苦难, 反思苦难, 是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李锐笔下, 西方的基督教与中国本土的女娲信仰针锋相对, “神与神的较量, 流的却是人血”[9]。 教案冲突中满含人性的荒谬, “最让人无法释怀的, 就是你眼睁睁地看见同样的人类, 却因为不同的信仰而崇高无比、 义正言辞、 激情澎湃地杀人”[10]。 满含鲜血的历史激起了作家书写的愿望, 使得他们重新审视这些不远千里来到中国, 试图用自己的生命传播教义的传教士们。
1.3 文学作品承载着宗教、 道德、 情感、 心理等多方面的文化蕴涵
文学作品是作家关照社会现实、 表达思想情感、 阐发宗教道德和人生价值观念的艺术载体, 承载着宗教、 道德、 情感、 心理等多方面的文化蕴涵。 新时期以来的小说更是如此。 传教士表现出的爱与救赎, 执着与坚毅等新的文化精神, 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中国自古以来的实用主义态度, 带来了一种超越的审美特征。 新世纪以来, 经济迅速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改善。 然而, 物质消费的日趋丰盈, 却无法消解生命的焦虑, 每个人活跃的精神思维也无法取代个体生命孤寂的存在。 许多人在每日每夜的忙忙碌碌中随波逐流, 茫然生活, 惶然地寻找着心灵的栖息地。 人们在享受物质的土地上载歌载舞, 却突然发现信仰的天空一片阴霾。 道德缺失, 价值评估标准错乱, “信仰危机及其所导致的虚无主义阴影不断来袭, 困扰着那些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富足的当代人”[11]。 一部分作家开始怀着怜悯、 叩问的心情, 把笔触伸向宗教题材, 试图点燃信仰的火把, 找寻隐匿在纷繁的物质颗粒中的道德。 正如美国作家福克纳所说:“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 使他的勇气、 荣誉感、 希望、 自尊心、 同情心、 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昔日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 帮助他挺立起来。”[12]信仰的本质是“作为有限的个人与无限的上帝之间建立的一种生命关系, 是有限的个人不断破碎自己, 在永恒神性的关照下, 自我思索, 自我关照, 自我超越, 重建自我的过程”[13]。 这些传教士们在面对危机时的坚韧与坚持, 蕴含着浓厚的人文关怀, 给当下人们荒芜的精神园地带来新的生机, 带来了净化心灵、 救赎灵魂的希望。
2 新时期小说中传教士面临的危机
当代文学, 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 在描写传教士时较为集中地表现了他们作为“文明的归化者”[14]的形象。 小说中的传教士们, 不管是面临战争、 教义纷争, 还是在和平年代寂寞无闻, 都秉承着坚定的基督教信仰, 在危机面前坚持前行, 展现了自身美好的品质。
在战乱不断的年代, 人的基本生存遭遇挑战。 作家严歌苓的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就讲述了在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 十二位妓女为了躲避日本人的残害而躲进教堂, 后又为了保护教会女学生而从容赴日本人的“聚会”的故事。 然而自古以来, “戏子无情, 婊子无义”, 这些日日在秦淮河花船之上莺歌燕舞的妓女怎会如此轻易地放弃对人世的眷恋, 变得无私高尚起来呢?是残酷战争中人性的光辉闪现, 是流淌在中国人血液中的舍己救人品质, 还是对“商女不知亡国恨”说法的现身反驳……我们无法去猜测小说中人物的内心, 只能借助作家的描写来推断。 正因如此, 战乱中的传教士们以舍生忘死、 坚持传教的精神感化众生, 以及神圣的教堂中浓厚的基督教文化的气息, 才有可能带给这些原本贪生怕死、 眷恋荣华的妓女们以心灵的启迪。
首先, 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妓女是不知廉耻的代表、 理应受到惩罚的价值观念不同, 基督教文化对妓女持宽容的态度, 认为她们是可以被救赎的。 《圣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众人要用石块打死一个妓女, 耶稣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结果, 众人惭愧地低下头, 丢下石头离去。 兵荒马乱之时, 所有人都走投无路。 这些妓女们的内心深处也是诚惶诚恐, 她们深知自己会被遗弃, 无人愿意收留她们, 因此, 她们自救式的翻墙进入教堂, 以期寻求避难所。 自身难保的英格曼神父虽万般无奈但也算是收留了她们, 此时她们内心潜意识里其实充斥着满满的感激之情。 其次, 金陵教堂的传教士们在日军的刺刀前面不改色, 保护女学生和前来避难的妓女的英勇举动也给妓女们带来心灵的震撼。 “阿多纳多请他(戴教官)放心, 有英格曼神父和她, 豆蔻那样的事万一发生, 也只会在他们两个神父变成尸体之后。”[15]她们本是被人轻视且玩弄的社会底层, 在各自逃难的时代, 竟然有人愿意以生命为代价保护她们, 这使得她们的心灵受到震颤。 再次, 妓女和女学生避难的教堂具有浓厚的基督文化氛围。 “教堂想象着世界的诞生”[16], 这所饱经南京战火洗礼的教堂被布置为暖色调, 是一个温暖的象征。 它隔绝了战争和屠杀, 隔绝了南京城里惨绝人寰的嚎啕, 作为血雨腥风摧残下的南京城中最后一片绿洲, 在其安宁被打破之际, 唤起了妓女灵魂上的自我净化与救赎。 最后, 女学生们的圣歌也给这些妓女的心灵带来触动。 这些含苞待放的生命面临着可怕的威胁, 女孩们用静默代替哭喊, 用纯真的歌声唱诵圣经。 “火光和血光声中升起的圣经诗篇, 歌声清冽透明, 一个个音符圆润地滴进地狱般的都市, 犹如天堂的泪珠。”[15]学生们的歌声, 甚至可以让狼都立地成佛, 也陶醉了妓女们为脂粉酒色所玷污的心灵。 虽然在作品和电影中, 传教士都不是作为直接描写的主要对象, 但是他们所带来的基督教文化气氛却萦绕在整个故事之中, 给这段沉重的历史以温情的基调, 犹如影片中多重出现的教堂彩色玻璃一般。
较之残酷的国家战争, 在相对和平的年代, 传教士在宗教、 教义上出现纷争之时, 仍然坚持着虔诚的信仰, 坚守在这片硝烟弥漫的土地上。 范稳的《水乳大地》 《大地雅歌》都描写了入藏传教士在藏区的传教活动, 讲述了基督教传播中与东巴教、 佛教的冲突与融合。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杜朗迪神父是个复杂的角色, 一方面, 他怀着把圣十字插在神山上的执着愿望, 踏踏实实地来到藏区传教, 给藏民治病, 真心实意地帮助他们, 并希望感化他们。 另一方面, 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 加之他对中国的文化知之甚少, 甚至觉得无须尊重中国宗教, 会认为藏传佛教是落后的宗教, 会使人愚昧, 甚至认为应该杀了蒙蔽藏民灵魂的喇嘛。 由此, 基督教在西藏传教中教案不断。 杜朗迪神父不畏死亡, 他把自己当成走向十字架的耶稣, 从容面对殉道。 虽然, 他们炽热的鲜血最终难以唤起藏民对上帝的敬仰与崇敬, 但是这种为信仰而心甘情愿牺牲的奉献精神依旧为人敬佩。
李锐的《张马丁的第八天》同样描写了天主教与中国本土的女娲之间的信仰冲突。 “张马丁以耶稣、 教堂为营, 张王氏与菩萨、 娘娘庙为伍。 神与神的较量, 流的却是人血。”[9]小说中的莱高维诺主教(即高主教)带着为自己打做的棺材, 抱着有去无归的信念,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播教义, 坚决铲除异己张天赐, 最终心甘情愿地死于对教义的捍卫之中。 在高主教身上, 很难说他的虔诚是虚伪的, 他坚持着对上帝的忠诚, 执着传教, 坦然接受义和团“点天灯”方式的虐杀, 让其他教徒带着伤病员和育婴堂的孩子躲进秘密的地下室, 躲过了教堂的大屠杀。 小说的主人公张马丁也是个敢作敢当的传教士, 宁愿死也不愿做假证陷害人, 为了自己的良知, 敢于接受苦难。 作家李锐在接受采访时说: “传教士们从来都不是虚伪的, 哪有千里迢迢不顾艰难、 不顾生死的虚伪者。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近几百年基督教的传播史和西方血腥残酷的殖民史是剥离不开的。 这是西方人的罪与罚。 这件事情不能靠简单的妖魔化来解决。 可惜的是, 人们总是相互妖魔化一下就完事大吉, 过若干年再血腥残忍地来一次。 不是谁败在谁的脚下, 而是‘人’永远败在‘人’的脚下。”[6]宗教、 教义纠纷, 自基督教传入中国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 在信什么、 信与不信方面, 洒下了多少人血, 时至今日这种和平稳定的年代, 都难说是完全停止了。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里面虔诚的传教士老詹, 从二十多岁来到延津, 只发展了八个信徒, 每天坚持让帮手小赵用自行车驮着他满城转, 劝人信教。 他的困难不是生存遭遇挑战, 而是没有人愿意信他, 或者说是信主。 几乎所有人都对老詹讲:“你要能让主来帮我贩茶, 我就信他。” “你要能让主来帮我破竹子, 我就信他。”[17]177然而, 老詹最大的贡献, 不在于发展了几个信徒, 而在于没人去信了。 在物质现实吞噬了所有人的精神世界之后, 只有他还在信。 老詹死后, 主人公吴摩西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张图纸:“这是一座八层高的哥特式教堂, 中央穹隆。 直径四十点六米; 穹顶离地, 六十点八米; 钟塔高一百六十米, 塔顶上有座大钟, 直径六米; 教堂标明用大理石墙面, 七十二扇窗户, 窗上的玻璃是彩绘的, 门头上竖一根十字架, 直插云霄。 不但教堂雄伟, 教堂中的摆设, 也画在一旁, 件件精美。”[17]171这是老詹未完成的心愿, 也是他到死都执着的信仰, 非常令人感动。
3 新时期小说中传教士形象的价值和意义
新时期小说中, 传教士的正面形象显示了作家试图通过传教士这一外来者形象, 反思历史, 关照现实, 呼唤真善美的创作理念。 在不同的年代, 不同的危机面前, 作家笔下的传教士形象所具有的精神品质, 都给予了读者无限的思索。
狼烟四起的战争年代, 日军大规模侵入中国, 带来无尽的杀戮与死亡。 在严歌苓笔下, 金陵的教堂里, 拥有着西方人面孔的传教士们原本是安全的, 可是他们却宁愿冒着生命危险, 保护女学生和前来避难的妓女, 甚至还保护日军严禁庇护的中国伤兵们。 小说里的英格曼神父是一位慈祥的长者, 最终无奈地在女学生和妓女之间选择牺牲后者, 内心饱受煎熬。 这种“以次充好”的观念虽然不符合基督教历来遵循的众生平等的观念, 但也令人无法过多指责。 神父毕竟还是人, 有人的偏见和计较。 在古老的南京城被践踏和侮辱的时刻, 如果是女学生前去赴日本人的宴, 所有人都知道她们即将面临的是什么——强暴, 这是比屠杀更可怕的灾难。 “若说屠杀只是对肉体的消灭, 以及通过屠杀来进行征服, 那么‘Rape’则是以践踏一国尊严, 霸占、 亵渎一国最隐秘最脆弱的私处, 以彻底伤害一国人的心灵来实现最终的得逞和征服, 来实践残杀的……无论在何种文化里, 处女都象征一定程度的圣洁, 而占领者不践踏到神圣是不能算全盘占领的。”[18]张艺谋导演的同名电影中, 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 对情节进行了适量改编, 以减少信息含量, 使观众在电影播放的短短几个小时内, 更好地把握剧情和情感。 电影中的英格曼神父死于日军流弹中, 来教堂埋葬神父的入殓师约翰·米勒是一个爱钱如命的酒鬼, 为了给死去的英格曼神父化妆, 才进入了教堂, 却在日军袭击教堂之时挺身而出, 假装作神父保护了女学生和前来避难的妓女们。 电影自上映以来, 毁誉参半, 不少评论者认为影片中太多“被看”的成分, 是一道以女性身体为主元素的视觉盛宴, 企图用情色来换取票房回报的功利性目的, 缺乏人道的诚意。 可是, 当假神父约翰在神圣的教堂中穿上教袍, 一改往日酩酊大醉、 觊觎妓女美色的流氓相, 义正言辞地斥责日军入侵教堂和试图侵害女学生的无耻行径之时, 很多人都为他的正义动容, 甚至忘记了他是一个假神父。 当然, 传教士在面临生命威胁时也不全是无畏的。 20世纪90年代, 莫言在《丰乳肥臀》中塑造了上官金童的生身父亲马洛亚神父, 便是个相对弱势的传教士形象。 在村民眼里, “花椒树的辣味、 奶山羊的膻气、 马洛亚的臊味, 混成恶浊的气味团膨胀在艳阳天下, 毒害了半条街。”[19]上官鲁氏难产之时, 马洛亚神父虔诚地祈祷着上帝保佑, 却被前来接生的孙大姑一把推开:“孙大姑冷笑一声, 走上前去, 把马洛亚搡到一边去, 牧师身体趔趄着, 睁开眼睛, 吐出一个‘阿门’, 手指在胸前划个‘十’字, 结束了他的长篇祝祷。”[19]同样, 在上官寿喜与父亲被日本军残忍杀害的时候, 马洛亚神父依旧是满含深情地为他们祈祷, 却又被镇长打断: “司马亭镇长把马洛亚牧师从土堆上拉下来, 说: 老马, 您到边上歇会儿吧, 您也是死里逃生。”[19]马洛亚神父手无寸铁, 在鸟枪队队员霸道地占领教堂、 在婴儿面前强暴上官鲁氏时, 他痛苦无奈地从钟楼上一跃而下, 用死亡抵抗暴力。 虽然在莫言笔下, 马洛亚神父显示出不被接受的弱势, 在战乱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 可是他对孕妇、 死者发自内心的虔诚祝祷, 仍不乏善良。 传教士们在烽烟四起、 朝不保夕的时候仍然努力拯救着中国人民, 散发着人道主义的温暖光芒。
不止战争会带来流血与死亡, 教派与教义的纠纷也会带来牺牲。 在这样的纷争中, 传教士不断反思, 寻求着内心的救赎。 范稳的《水乳大地》与《大地雅歌》讲述了基督教在西藏与藏传佛教、 东巴教的教派纷争。 教派的纷争是关于“信什么”的问题, 传教士来到西藏, “多半挟有战争打出来的民族优势, 在19世纪盛行于西的所谓“进步”观念的支配下, 他们对中国的文化知之甚少, 甚至觉得无须尊重中国文化”[20]。 在《水乳大地》中, 沙利亚神父一直是基督教的坚定传播者, 他认为藏传佛教及藏族传统都是阻碍藏民接近上帝的绊脚石, 在与藏传佛教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之后, 遇到可怜的小女孩央珍。 然而当他满含关爱地试图将小女孩带回教堂抚养的时候, 却发现小女孩满面惊恐, 宁可靠近悬崖, 也不愿靠近他一步。 沙利亚神父面对满目疮痍的山谷深深地忏悔了: “主啊, 求你饶恕我们的罪。 即便是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时, 做得也没有他们过分。”[21]在传教过程中对暴力的忏悔与反思, 也存在于同一教派对教义的不同理解之中。 李锐的《张马丁的第八天》中, 高主教为传教不择手段, 甚至不惜枉死最激烈反抗传教的头目张天赐。 然而张马丁却坚持真相, 不允许自己对主、 对其他人说谎。 当高主教要求张马丁严守假死秘密, 张马丁困惑地问道:“神父……难道我们捧着《圣经》的时候需要学会用枪了吗?”[22]最终, 张马丁还是选择从高主教所谓的信仰的世界里出走, 走向天石村之路, 从第八天开始了自己的死而复生。 虽然传教士是宗教的代言人, 传播的是神的旨意, 但是这种对流血的忏悔, 试图对不同教派、 文化的尊重与理解, 对自身信仰的再思考, 舍生取义的坚守, 都显示出强大的人性光辉。
不单单是在战乱中, 即便在简单的生活中, 传教士依旧身处困境之中。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里的老詹, 身边全是三教九流的普通老百姓, 没几个人愿意花时间来听他说道, 可是, 他最大的成就在于, 所有人都不信教, 他却依然坚信着。 老詹死后, 遗物中的蝇头小字“恶魔的私语”, 无疑是对这个众声喧哗世界的咒骂。 嘈杂的世界中, 所有人都在说, 都在变着花样传播别人说的话语, 深思熟虑着如何去大放厥词地“喷空”来获得大家的关注, 却找不到几个心灵相通的可以说真心话的人。 然而咒骂过后, 老詹还是选择宽恕, 宽恕世界的冷漠与纷繁, 宽恕着无信仰的小人物们的蝇营狗苟, 宽恕着所有人对他的不信任和对主的不尊重, 所以老詹到死都是一派和蔼、 慈祥的模样, 没有激烈的言辞, 却成为主人公吴摩西心中那道柔和明亮的曙光, 照亮了他旁逸斜出的残败人生。
文学首先是人的文学, 新时期小说中传教士的正面形象代表了追求真善美的审美取向和价值标准, 传达了正义、 仁慈、 坚韧、 宽容等正能量, 给当代社会道德缺失的现状以温暖的启示, 引导着人们不断靠近神性、 摆脱兽性遗传, 和谐相处, 展现美好人性。
[1]孟华. 比较文学形象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2]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3]张颐武. 《金陵十三钗》: 民族的新生与救赎[J]. 当代电影, 2012(2): 27-31.
[4]杨守森. 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5]刘震云. 温故一九四二[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6]傅小平. 李锐: 来一次没有遮挡的“正面进攻”[N]. 文学报, 2011-08-11(003).
[7][德]西奥多·阿多诺. 否定的辩证法[M]. 张峰,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3.
[8]哈金. 南京安魂曲[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
[9]陈涛. 《张马丁的第八天》: 神与神的较量, 流的却是人血[N]. 中国新闻周刊, 2012(08): 78-79.
[10]李锐. 《张马丁的第八天》: 一个关于人的寓言[J]. 山西文学, 2012(3): 79-82.
[11]胡冬冬. 新时期以来小说中的基督徒形象研究[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12]福克纳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讲话[EB/OL]. 1950-12-10[2012-10-12]. http:∥www. doc88. com/p-950212516640. html.
[13]蔡军. 论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西方传教士形象[D]. 合肥: 安徽大学, 2014.
[14]方解石. 顺民与强盗——传教士在中国近代的角色[J]. 民主与科学, 2000(6): 40-42.
[15]严歌苓. 金陵十三钗[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
[16]埃尔·达米埃. 世界文化象征词典[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2.
[17]刘震云. 一句顶一万句[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
[18]严歌苓. 悲惨而绚烂的牺牲[J].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2011(4): 69.
[19]莫言. 丰乳肥臀[M].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2.
[20]顾卫民.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21]范稳. 水乳大地[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22]李锐. 张马丁的第八天[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
The Images of Missioners in the Novels of the New Period of China
HOU Xu, WANG Heng
(Chinese Department, Shaanxi Sci-tech University, Hanzhong 723001, China)
The images of missioners have been described in the novels of the new period of China. These missioners traveled thousands of miles to China to preach their religions. They persisted in doing missionary work even though they faced lots of difficulties such as warfare, church doctrine disputes, the lack of believers and so on. The missioners not only alleviated the realistic problem of the lack of people’s faith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other moral problems, but also represented writers’ choices in terms of building the ideal images to confront the life and reflect on human values, and showed new aesthetic orientation and value standards to readers.
Chinese new literature; images of missioners; value and meaning
1673-1646(2016)06-0100-05
2016-05-27
侯 旭(1992-), 女, 硕士生, 从事专业: 中国现当代文学。
I207.42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6.06.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