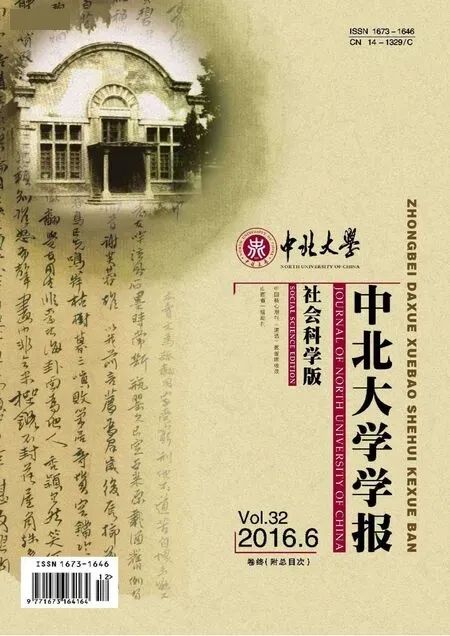本雅明作品中的隐喻和换喻
2016-01-15杨佳敏
杨佳敏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本雅明作品中的隐喻和换喻
杨佳敏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本雅明的著作向来被当作隐喻的范本加以研究, 戴维·弗里斯比、 理查德·沃林等理论家只着眼于隐喻的特殊地位, 而忽视了文本中换喻的价值与意义。 本文将以雅各布逊关于隐喻与换喻的定义为理论基础, 对本雅明作品中的隐喻和换喻进行分析研究, 并以他的代表作《柏林童年》 《单行道》等为例, 从创作经验、 呈现方式以及创作效果三方面对其作品中隐喻和换喻的存在进行论述。 一方面, 它们依然遵循着雅各布逊《隐喻和换喻的两极》中提出的相似性与毗连性特点, 另一方面, 被创作出来的隐喻与换喻因其所处的文本环境而呈现出独特的个人化风格。
本雅明; 隐喻; 换喻
从戴维森的三角模式的因果隐喻, 到塞尔的“S、 R、 P”隐喻话语, 直到二十世纪的俄国形式主义。 由于很大程度上受到符号学的影响, 以雅各布逊为代表的理论家往往遵循着从语言角度分析话语以及阐释文本信息的传统模式。 不同于戴维森与塞尔的隐喻理论, 雅各布逊将隐喻与换喻进行现代性意义上的分析比较, 通过沿袭索绪尔语言的共时性与历时性模式的二元对立观点, 从相似性以及相邻性角度论述了隐喻与换喻的不同之处。 在索绪尔语言学的基础上, 他提出失语症的产生无非是来源于隐喻和换喻两种极端的类型, 语言中替换功能出现毛病, 从而引起组合上的问题。 前者本着相似性的原则, 而后者则以毗邻性为基础。 因此, 隐喻表现为一种相似性关系, 换喻呈现出毗邻性的关系。[1]
以雅各布逊对隐喻与换喻的区分为基础来分析本雅明的创作, 可以发现, 本雅明创作中向来被当作散文集的《柏林童年》以及札记《单行道》, 存在着大量的以碎片化方式呈现的隐喻, 以及通过叙事呈现出的换喻。 不同于《拱廊街计划》和《单行道》的是, 《柏林童年》笔调更接近于散文, 因而一直以来被读者当作“最美的散文集”来欣赏。 按照雅各布逊的观点, 散文较之诗歌等其他题材多见换喻结构。 《柏林童年》中除了本雅明常用的象征手法外, 最为典型的是: 文本中隐喻与换喻如何相互和谐交织, 这种以碎片化形式呈现出的隐喻的主旨如何在换喻中得以彰显。
1 隐喻与换喻的创作实践
在《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中, 本雅明从隐喻的角度解读了古斯塔夫·卡恩将波德莱尔诗歌作为一种“体力活”的观点。 他以击剑者为喻, 提出波德莱尔在诗歌中充分发挥了击剑的搏斗因素与艺术表现之间的相似性。 作为“语言森林”遍布的象征主义诗人, 波德莱尔在诗歌创作中, 大量使用隐喻的手法。 同样, 在本雅明颇具现代性的创作中, 隐喻也成为其魅力的来源。
“梦”是本雅明创作中最为热衷的一个主题。 雅各布逊曾将弗洛伊德《释梦》中的“梦境”研究划分为隐喻和换喻两种形式。 隐喻式的梦幻使用的是象征意象的相似性, 而换喻使用的是象征与时间的毗连性, 这也正对应着梦的象征作用以及梦的转移作用。[1]
读者可以从相似性与相邻性两方面对本雅明的梦境进行解读。 在他的作品《地下工程施工》(《单行道》中的一篇短文)中, 梦境中的“教堂的尖塔”与“集市广场”分别象征着宗教教义与现代都市。 现代生活中宗教经验贫乏, 政治势力与资产阶级的物质生活使人们精神世界匮乏。 本雅明的创作正是致力于对经验贫乏的救赎, 而梦中出现的塔尖正是对心灵救赎的象征。 作者通过主体客体化的方式, 使自己的主观世界借助客体形式得以呈现。 然而, 对于读者来说, 隐喻涵义的明晰却又依靠于具有联系的语境, 需要通过上下文才能解读作为符号的物的所指。
不同于隐喻以意象、 格言等片段形式呈现于读者面前, 换喻存在于叙事性文学的情节中, 即存在于事情的变化与经过的表述中, 并通过文中的描写与叙述得以表现。 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对人物和事件的叙述, 以情节变化引发空间的位移。 即使本雅明在对现代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的界定中与卢卡奇产生很大分歧, 但不可否认的是, 本雅明的创作确实受到卢卡奇《小说理论》潜移默化的影响, 并表现为在其散文中对小说叙事原则的无意识使用。 雅各布逊在分析隐喻与换喻里提到, 诗歌多隐喻结构, 对于散文, 研究者多分析它的换喻。 不同于诗歌强调象征对诗意营造的作用, 本雅明的创作往往具有叙事性。
在对换喻的分析研究中, 雅各布逊提出了一种“事态场景”学说。 与以往分析话语中语法上的邻近性不同, “事态场景”分析着文本中的场景、 情节、 行为等。 一个事态包含以下三部分: 事态前提、 事态核心、 事态后果。[2]以《单行道》为例,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 文学创作是作家的白日梦, 那么登记簿上的名字同样也体现着作者的潜意识。 《113号》 由三部分组成, 也是由三个梦境构成。 第一个梦境是作者与小学同学重温往日友谊, 第二个梦境是进入歌德居所前的登记簿, 第三个梦境是与歌德用餐。 三个看似脱离的场景却是不断递进、 不断深入。 在第一部分中“我梦见和小学时的第一个伙伴迅速地重温了兄弟般的情谊, 虽然几十年来我已经不认得他, 在这个时期也几乎想不起他”[3]。 正是这个绝望的梦, 使得本雅明开始思考礼仪的缺失, 我们可以将其看作事态的前提。 于是作者开始通过拜谒歌德来试图唤起自己对古典主义的复归, 那么从登记簿的签名到与歌德餐厅见面便是事态的核心部分。 最后的痛哭流涕便是事态的后果。 第一次失落换喻性地指向作者的反省, 才会有第二个情节的发生, 因而与歌德见面的情节便与小学同学见面的情节具有了邻近关系。 最后当作者扶起歌德时的哭泣, 直指与歌德会面的核心事态, 在整个情节中形成了换喻的邻近性基础。
除此之外, 本雅明在创作中对于人物所处环境以及人物的外貌描写, 同样存在着换喻。 在《姆姆类人》中本雅明着重选取了集一切不适于一身的帽子: 左手以熟练的优雅动作拖着一顶巨大的墨西哥宽边草帽, 右手拿着一根拐杖正面可以看到拐杖向后倾斜的球形捏手, 捏手后端是一束在花园工作台上被安上去的鸵鸟毛。[4]表面上看, 这顶墨西哥羚羊胡帽子与阿尔卑斯山的亚热带地中海气候风景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实际上, 被强制性要求去契合周围环境的作者同样表现出对于这种盲目复制的机械化方式的不满。 在这一描写片段中, 作者左手擎起的帽子与作者的心理形成了邻近性基础上的换喻。 另外, 此时的画面与作者之前所提到的“我与居所、 家具和服装相像, 唯独从不与我自己想象”[4], 在概念上又形成了一组邻近性关系。
母亲是本雅明创作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一位女性形象, 然而他对母亲的容貌从来没有正面的描写, 相反只是常常着眼于人物的服饰、 装扮。 在散文《聚会》中, 母亲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 她已经系上的那块头巾的黑色尖角会触抚我的脸颊……我在她那块头巾的阴影中, 以及在与她胸前佩戴的那块黄色大宝石的贴近中体验到每个时辰, 都使我幸福无比,这种幸福感是在被她亲吻时从她嘴里得到硬糖的感觉无法媲美的。[4]黑色丝巾是犹太女性传统的宗教配饰, 因而头巾便是对佩戴者宗教信仰的暗示。 需要注意的是, 作者对母亲头巾的拟人化描写。 作者对母亲的喜爱以及母亲对他的关爱通过黑色头巾带来的触感形成了互相间的邻近性关系, 于是头巾成为作者情感的投射。 除此之外, 母亲胸前的黄色大宝石同样是作者回忆中的另一个重要物品。 与其说母亲身上佩戴的黄色宝石是家庭的护身符, 不如说在作者眼里母亲才是真正带给他安全感与幸福的角色。 作者没有对母亲这一人物形象进行细致的直接刻画, 只是将人物的形象特征投射给人物身上最具代表性的饰物, 利用配饰与人物的邻近性关系形成了创作中对于人物特征塑造的一组换喻。
2 隐喻与换喻的星丛关系
“星丛”本是天文学上的术语, 本雅明在《德国悲悼剧的起源》中首次将其作为哲学理论, 来探讨客体与理念间的关系。 在《德国悲悼剧的起源》这部著作中, 作者运用符号学中的能指与所指, 揭示悲悼剧中的隐喻价值。 除了作为理论外, 本雅明创作中的隐喻与换喻也呈现出如同星体与星丛般的关系。
星丛理念是本雅明认识论的哲学, “每一个理念就是一颗行星, 都像相互关联的行星一样, 与其他理念相关联”[5]。 真理的获取依靠各自和谐共处的单体, 这些单体便是认识的对象, 不论是对唯理论还是经验论者, 认识不可或缺的便是认识客体。 和宇宙星体相同的是如莱布尼茨《单子论》中所说的: 世界有着自在秩序, 事物之间普遍联系。 对事物的最终认识必须存在于一个必然实体之中, 实体存在的特殊事物也是相互联系的。[6]个体之间具有相互联系, 却因为各自的秩序而和谐运行从不触碰, 它们之间存在着与星体间相似的距离, 距离间的张力使它们保持独立性。 因而理念之于客体, 便是星座之于群星。[6]在整个系统中, 看似独立存在的个体之间存在着真正的永恒不变的隐喻关系。
正如本雅明创作中的隐喻常常表现为单个意象的形式。 格雷姆·吉洛希在《瓦尔特·本雅明批判星丛》的前言中, 对本雅明文化碎片如此介绍: 本雅明先锋性的批评解读以及文本表征形式是破碎的、 折中的、 现代性物力学的, 例如单体、 论文、 星丛 、 格言、 短暂的思考、 梦境、 辩证的‘意象 ’、 文本的‘影像’、 影视的蒙太奇手法。[7]一方面, 星丛观念本身是隐喻的哲学, 这种隐喻的产生借助星系间的关系、 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以及理念和客体之间关系的相似性。 另一方面, 在具体的创作中, “他毫无过渡地以一种叙事的一致性描述了一个又一个形象: 流浪汉、 密谋家、 路易·波拿巴及其走狗、 诗人、 拾垃圾的、 醉汉、 妓女、 人群、 大众、 商品、 拱廊街、 林荫大道”[8]。 这些原本独立或者难以解释的隐喻个体却是“从叙述中的毗邻世界中抽取出来的”[9], 那就意味着, 隐喻主旨的扩大依靠客体所处的空间环境。 虽然本雅明从未阐释过换喻的创作理论, 也从来没有研究者将他作品中的换喻置于与隐喻等价的地位进行研究, 但不可否认的是, 正如芭芭拉·约翰逊所言, 隐喻从来都不会是独立存在的, 它存在于所毗邻的空间。 一旦创作中的隐喻被放置于具体的叙事语境中, 伴随叙事而来的便是换喻的邻近性基础。 我们不难想象, 隐喻作为星丛中的星体, 叙事作为星体运行的轨道, 而在这一轨道中相邻的两个星体之间便形成了邻近性的关系, 原本同为隐喻的个体因为毗邻性而相互结成换喻。
3 隐喻与换喻双轴运动的创作效果
隐喻与换喻虽然作为语言中的两极, 但它们在概念上却没有明确的界限, 正如雅各布逊所言:“在正常的言语行为当中, 这两个过程是始终在发挥效用的。”[1]由此可见, 文本中从来都没有纯粹的隐喻创作或者换喻创作。 在本雅明的创作中, 隐喻与换喻互相发挥着作用, 相辅相成。 创作中这些“孜孜不倦地以语录片言的形式加进日常生活和读书所渔获的‘珍珠和珊瑚’”的隐喻[10], 正是本雅明创作呈现出碎片化的原因。 “设计换喻时的接近, 仅仅是为了揭示该诗的隐喻的主旨。”[9]本雅明创作中的换喻, 使原本零散在场景描写中的事物得到升华与统一。 伴随叙述与描写而来的换喻使原本在形式上呈现出碎片化特点的隐喻意象在意义上得到整合。
在《墨西哥大使馆》中, 作者这样描写一次大型的弥撒活动:
一位牧师对着洞窟一面墙上高高悬挂着的圣父半身木雕像。 举起一个墨西哥原始崇拜的偶像。 这时候圣父的头从右向左不赞成的摇动了三次。[3]
这无疑是本雅明宗教经验下的创作。 显然, 作者借用圣父的反应表达了自己的宗教理念。 一位做弥撒的牧师企图利用人们的信仰, 而圣父对这种拜物主义的崇拜是不以为然的。 圣父是基督教所信仰的弥赛亚, 但是这场弥撒却是假借圣父之明以达到意识形态统治。 显然, 在作者看来, 这已经代表着宗教信仰的缺失、 宗教礼仪的衰退, 也是原始的遵循教义的宗教经验的贫乏。 本雅明通过高处的圣象、 近处的牧师、 牧师手里的崇拜物、 以及圣父的摇晃三个不同画面表现自己对现代宗教的思考。 在整个场景的描写中, 一方面, 圣象及偶像各自具有隐喻意义, 同时圣父与其所举起的偶像又形成了伴随空间毗邻性而来的换喻。
由前厅再到餐厅, 随着地点的不断变化, 梦中本雅明与歌德的接触也逐步深入。 正如本雅明所提到的“我们早就忘却了礼仪, 我们所生活的大厦就是在这种礼仪下面建筑起来的”[3], 地点只是作为礼仪的符号。 例如在餐厅这一部分中, 本雅明写道:“在桌子右边的顶头, 我在歌德旁边就坐。”[3]本雅明一直致力于德国古典主义文化研究, 在此“我”正是歌德的追随者。 随着文章叙事中空间的不断推移, 原本零散的片段被整合, 原先碎片化的涵义也被“收藏者”整理起来而变得明晰。 结构与意义上的碎片化与哲学上强调连续性的传统观念分道扬镳, 但正如散文创作一般, 碎片之间形成“形散而神不散”的特征。 因而, 读者要善于发现本雅明作品里的秩序与线索。 碎片化的形式打破常规而具有迷宫般的创新性, 从而打破了传统创作中对连贯性的要求, 使读者耳目一新。 这种“破坏性”体现在他的哲学观念中, 便是对连续性的时间观念的解构。 然而, 在具体的创作中, 形式上的碎片化由于空间描写中的相互关系而趋于稳定, 原本看似独立无关的意义也被赋予完整。
本雅明的创作正如他所提出的星丛观念一般, 看似独立的个体却共同遵守着隐喻的规律。 在这种秩序中, 各个意象井然有序地发挥着不论是意义上还是理论上的作用。 在星丛中, 星体之间互相联系又相互独立。 在隐喻的星丛里, 每个因素同样遵循着星体间的秩序。 可是,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本雅明的“星丛”理解为天文学中星体的集合, 理念和真理也不是简单的隐喻对象的集合。 隐喻涵义的扩大依靠创作中双轴运动的相互扶持。 星丛的每个个体本身具有隐喻作用, 由这些看似互不联系的个体形成的整体是最凝练的更高级隐喻。 在整个统一体里, 邻近的星体使对方得以命名, 相邻的隐喻客体间便成了相对而言的换喻, 使对方意义得到突显。 这些零散的涵义便不断地在理解中加以整合, 形成作者最终的理念。 这也是为什么本雅明的创作总是深奥难解的原因。 因为对真理的捕获不在于一次创作或者创作中的某一部分。 正如汉娜·阿伦特对本雅明的理解——深海采珠人, 作者的创作是一次收藏, 将最凝练的思想搜集在一起, 于是提炼出最高层次的理念, 那便是真理。[11]
[1]朱立元, 李钧.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上)[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2]司建国. 认知隐喻、 转喻维度的曹禺戏剧研究[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8.
[3][德]瓦尔特·本雅明. 单行道[M]. 李士勋,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4][德]瓦尔特·本雅明. 柏林童年[M]. 王涌,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5][德]瓦尔特·本雅明. 德国悲剧的起源[M]. 陈永国, 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
[6]桑靖宇. 《单子论》翻译、 注释[EB/OL]. 2008-01-28[2016-02-29]. http:∥www.docin.com/p-1305650071.html.
[7]Graeme Gilloch. Walter Benjamin critical constellation[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2.
[8][德]瓦尔特·本雅明.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 张旭东, 译. 上海: 生活·读书·三联书店, 1989.
[9][美]芭芭拉·约翰逊. 《他们的目光注视着上帝》中的隐喻、 换喻及声音[J]. 贺彭, 译. 国外文学, 1993(4): 57-68.
[10][德]汉娜·阿伦特. 启迪[M]. 张旭东, 王斑, 译.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11][德]汉娜·阿伦特. 深海采珠人[G]∥西奥多·阿多诺, 雅克·德里达, 等著. 郭军, 曹雷雨, 译. 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 寓言和语言的种子.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
The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Benjamin’s Works
YANG Jiamin
(Chinese Department,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Benjamin’s works have been the model for metaphor study. Theorists focused only on the special status of metaphor, such as David Frisby and Clarisse Wallin, but ignored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metonymy. This article bases on the definitions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of Jacobson to analyze Benjamin's works. Taking Benjamin’s representative works,BerlinChildhoodandOneWayStreet, as examples, this paper discusses metaphor and metonymy from three aspects, constellation theory, creative experience and aesthetic experience. On one hand, metaphor and metonymy still foll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imilarity and adjacen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his article present a unique personal style for its textual environment.
Benjamin; metaphor; metonymy
1673-1646(2016)06-0096-04
2016-07-02
杨佳敏(1992-), 女, 硕士生, 从事专业: 文学理论。
I057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6.06.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