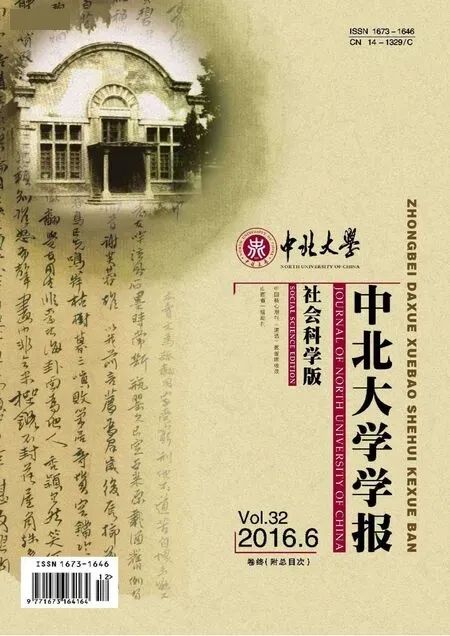伊壁鸠鲁对死亡的哲学考察
2016-01-15杨鹏
杨 鹏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伊壁鸠鲁对死亡的哲学考察
杨 鹏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伊壁鸠鲁对死亡的哲学思考完美地体现了希腊化时期自然哲学的伦理精神。 一方面, 他对于生死问题的研究视角和死亡事实的审视维度超越了单纯治疗哲学领域, 渗透到准则学、 物理学和伦理学在内的整个伊壁鸠鲁哲学体系之中, 使得对死亡哲学的考查成为理解其整个哲学体系的钥匙; 另一方面, 伊壁鸠鲁通过厘清原子聚散与个体生死的关系, 否定了以往哲学赋予死亡的现实感觉性和人生价值性, 批评了因惧怕死亡而膜拜神灵的愚蠢行为, 进而指出真正的幸福在于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 倡导人们以既不惧死又不厌生的态度, 实现有德性的理智生活。
伊壁鸠鲁; 死亡; 生存; 治疗哲学
1 哲学是“治疗灵魂的药剂”: 死亡研究的哲学视阈
长期以来, 学者们习惯将伊壁鸠鲁对死亡的哲学研究归于伦理学范畴, 笔者不否认死亡研究的伦理学意义, 但伊壁鸠鲁对死亡的思考严格意义上讲是以“治疗哲学”的进路展开的, 因为他着眼于对主体自身人生追求的关切, 而非人与人关系的协调。[1]272对死亡的思考贯穿了伊壁鸠鲁的整个哲学体系, 并成为理解伊壁鸠鲁哲学的钥匙。
1.1 死亡哲学与准则学
伊壁鸠鲁的准则学要解决“真理标准”问题, 这里的“真理”具有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双重指向。 伊壁鸠鲁提出的感觉、 前把握观念和情感三条准则, 兼具认识和实践的维度, 也就是说, 伊壁鸠鲁的准则已超越单纯抽象思维中的对错标准问题, 成为选择现实生活目标的指导。 死亡作为每个人生活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也是准则学探讨的应有之义。
作为感觉主义者的伊壁鸠鲁认为唯有感觉才绝对真实。 “必须完全遵循感觉, 也就是直接印象, 无论它是理智的还是其他某种感官的; 同样, 要遵循直接的(苦乐)感受, 以便在遇到有待证明的和不明白的事情时, 可以有解决它们的办法。”[2]4感觉作用的发挥具有双重意义: 感觉经验既作为清楚明白的感知对象之真理性标准, 又是某些感知对象实现“清楚明白”的依据。 感觉之所以具有无可置疑的可靠性并成为真理标准, 源于“外部事物连续不断地向我们发来印象”[2]8, 因此, 人们对死亡的种种感觉都基于死亡的影像, 然而伊壁鸠鲁对灵魂及其性质的思考却推导出了死亡事实本身是不存在影像的结论。 另一方面, 面对盛行一时的唯灵论思想, 伊壁鸠鲁告诫弟子们: “灵魂是感觉的重大原因; 但是, 如果灵魂不被有机体的其他部分包住, 就不能进行感觉……灵魂如果离去了, 有机体就失去感觉能力, 因为有机体自身并不拥有灵魂的能力。”[2]13尽管灵魂与肉体生命相互依存, 但伊壁鸠鲁强调肉体感性生命存在的基础性, 即灵魂必须基于有生命人而存在, 因为只有有生命的人才会有感觉, 才能获得感知对象的影像。
伊壁鸠鲁哲学总体上是排斥情感的。 “自然的研究不能依靠空洞的假设和习俗传统, 而应当遵从事实的自然启发。 因为非理性的和空洞的意见对于我们所需要的无烦扰的生活毫无帮助。”[2]21然而, 假设和习俗这些基于人情感的活动绝非不值一提, 这是基于伊壁鸠鲁“真理标准”的特殊内涵的考虑: 伊壁鸠鲁的准则学兼有认识和实践的成分, 以实践进路就不得不考虑人的情感体验, 情感作为三条准则之一无疑也体现了伊壁鸠鲁哲学思想的实践意味。 伊壁鸠鲁认为追求与人之本性相适应的快乐并规避作为其对立面的痛苦是人全部活动的根本准则, 人对自然的认识归根到底也都要为去苦求乐服务。 人们认为死亡是最大的痛苦, 然而死亡没有与之相对的影像, 这种痛苦不可能来自真切的感觉, 而只能来自人们的情感。
1.2 死亡哲学与物理学
伊壁鸠鲁物理学讨论的是传统意义上自然哲学的内容, 他对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原子论学说的继承, 成为其解决生死问题的自然哲学基础。 一方面, 伊壁鸠鲁强调物体和虚空构成了整个世界, 要考查生死问题就必须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 伊壁鸠鲁对传统的原子论进行了改造, 原子偏斜和对“虚空”概念的强调使其哲学思想中具有了更多向往自由的倾向。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些变化恰恰透露出伊壁鸠鲁对生死问题考查的新进路。
伊壁鸠鲁在《致希罗多德的信》中写道: “除了物体和虚空, 我们不能设想还有其他任何东西。”[3]1007所谓物体, 在伊壁鸠鲁看来无非是“感觉本身清楚地显示于所有人的”[3]1007。 笔者认为, 在对生死问题的讨论上, 不论是“物体”还是“原子”构成事物的本原, 最终都是归于原子的, 所以在此可以对二者不做区分。 与虚空相比, 原子具有无可争议的实在性和存在的永恒性。 根据原子论的基本原理, 生存就是原子间的相互聚合, 死亡就是原子间的相互分裂。 一个人而言, 他自身生存的过程也就是不断走向死亡的过程, 也就是各原子由分离到聚合, 最后再到分离的转化和演变。 然而现实中每个人的出生环境、 生存状态、 临终境遇都会不同, 对于这些从原子构成实体角度无法解释的问题, 伊壁鸠鲁引进了“虚空”概念并提出原子偏斜理论。
伊壁鸠鲁认为构成物体的基础是原子, 但原子之外还有“虚空”。 证明“虚空”不能像证明原子那样完全基于感觉, 而要采用理性加感性的双重路数[1]203: “如果不存在‘虚空’或‘地方’或我们称为‘无法接触者’的东西, 则物体将无处存在, 也无处可以运动; 然而, 很明显事物是在运动的。”[3]1007“虚空”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具有两层含义: 就动态而言, “虚空”是原子的处所, “物体在虚空里面, 以不同的方向在其中运动”; 就静态而言, “虚空”是原子间的间隔, 宇宙的构成就是原子及原子间的间隔。[4]52伊壁鸠鲁对“虚空”概念的强调是为了阐述原子偏离直线运动的原理。 “如果始基也不通过偏斜而开始新的运动以打破这—命运的铁律, 使原因不再无穷地跟着另—个原因, 那么大地上的生物怎么可能有其自由意志呢?”[2]98伊壁鸠鲁由此将作为偶然性的自由意志(偏斜运动)引入人类生活, 为思考生死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既然生的原因在于原子碰撞而聚合, 且聚合由偏斜运动而非垂直下降引起, 那么各类可感事物的生成就都有了哲学依据。[5]597其次, 死的原因是原子相互分离,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会死, 却无法选择自己死亡的方式, 从而对因信仰命定论而不努力从事的懒惰思想进行了有力回击。 最后, 伊壁鸠鲁通过对“虚空”概念和自由意志的强调, 高扬了人的自由意志和个体生命的价值意义, 为每个人努力追求自身幸福提供了有力的哲学支持。
1.3 死亡哲学与伦理学
伊壁鸠鲁将个人对快乐和痛苦的感受作为“最高的善”的标准, 并以目的论和道义论相互批判又相互证明的手法探讨了生死问题。 伊壁鸠鲁的死亡哲学虽名为谈死, 实乃谈生, 明显地具有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意义, 毋宁说死亡哲学是他人生哲学或生命哲学的一种深化、 延续和扩展。[6]2
伊壁鸠鲁认为人们之所以痛苦, 在于其过去使用的“加法式”治疗方法。[1]276为让学派成员掌握正确的治疗方法, 伊壁鸠鲁撰写了40条学说纲目, 最前的四条(又称“四重疗法”)分别从神灵、 死亡、 痛苦和欲望这些令人生畏的问题出发, 提出离苦求乐的良方。 “死亡与我们无关。 因为身体消解为原子后就不再有感觉, 而不再有感觉的东西与我们毫无关系。”[2]38对于我们自己的死, 由于自身感觉的丧失而无所谓痛苦。 只要人们换一种思路, 从原子聚散的角度观察自身, 便会坦然接受生命的有限性, 从而不再畏惧死亡。 “快乐增长的上限就是所有痛苦的去除。 当快乐存在时, 身体就没有痛苦, 心灵也没有悲伤, 或者二者都不会有。”[2]38既然对死都可以无所畏惧, 活着就更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了。 伊壁鸠鲁本人临终前的安详和福乐感, 正是对自己死亡哲学的积极践行。 由于“持续的痛苦在身体中不会存在很久, 相反, 极度的痛苦只会短暂地存在”[1]38, 这种“疗法”无疑是对感觉和情感的协调。 伊壁鸠鲁虽然承认一切最终还原于感觉, 但不是感觉主义者, 最高层的苦与乐不在肉体而在于内心。 只有以灵魂与肉体二分的观点为基础, 我们才能全面把握伊壁鸠鲁对“死亡”的真正思考。
快乐是伊壁鸠鲁伦理学的核心, 这种快乐不是昔勒尼学派快乐主义的翻版, 而是最大程度上对其质疑: 伊壁鸠鲁把对痛苦的规避和对幸福的追求建立在个体意志自由的基础上, 以期实现“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3]1069。 这种静态快乐是昔勒尼学派贪图享乐和追求肉欲的动态快乐所不能理解的, 尽管这种快乐可能是消极的[5]566, 但他恰恰使人得以区别于动物的当下体验。 伊壁鸠鲁一方面主张每个人努力追求快乐, 又不忘提醒人们对快乐加以甄别, 以期实现更深更久的快乐或避免更深更久的痛苦。 “没有任何快乐自身就是恶的。 但是某些享乐的事会带来比快乐大许多倍的烦恼。”[2]39死亡的确尽管是最大的恶, 但不应贪生惧死, 因为这种“生”给身体带来了更多痛苦, 或使灵魂受到更多纷扰。 对于每个个体而言, 生和死具有不确定性, 每个人只要对其泰然处之便是最大的快乐。
2 死亡与我们无关: 死亡事实的哲学审视
伊壁鸠鲁以感觉论和原子论的视角考查了死亡的事实, 认为“死亡——诸恶中最令人恐惧的东西, 与我们无关; 因为, 当我们在的时候, 死亡尚未来临, 而当死亡来临时, 我们却已经不在了。 所以, 无论对于生者, 还是对于死者, 死亡都与之无关; 因为对于前者, 死亡尚不存在, 至于那些死者, 他们自己已经不在了”[3]1065。 伊壁鸠鲁觉察到人的肉体存在和内心灵魂之间的矛盾, 对其死亡哲学的考查也必须遵从肉体死亡和精神死亡的双重路数。
2.1 没有感觉的东西与我们无关
基于对感觉的信任, 伊壁鸠鲁在《致美诺寇的信》中表达了对死亡的态度: “要习惯于相信死亡与我们无关。 所有的善和恶都为感觉所知晓, 而感觉的丧失就是死亡。”[3]1065可见, 死亡不仅仅是肉体感觉的丧失, 更是理性思考和追求幸福的能力的丧失。 进而他提醒人们秉承正确的善恶标准, 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主动且合理地追求幸福。
与斯多亚派不同, 伊壁鸠鲁的“前把握观念”不仅是感性知识的积累, 而且包含对知识的正确运用。 所以学界普遍认为, 这种“前把握观念”大致相当于概念(Preconception)。 尽管 “一说到‘人’, 我们马上就会按照这个先前储存的观念想到其形象, 有如感觉原来给我们报道过的那样。 每个这样的词的基本含义, 都是直接的、 清晰的”[3]1001, 我们却无法类比出“死”的前把握观念, 相反, 通过类比只能否定“死”的前把握观念的存在。 前把握观念并不涵盖全部概念, 它只作为与当下感觉不同的一种知识出现, 当人们把这些感觉存储在记忆中, 并用语词对这些感觉进行表述时, 前把握观念才会产生并随之发生作用。 毋庸置疑, 每个个体的死不能由感觉来证明: 任何生命体都不曾有过死的感觉, 相反, 不仅“死”不属于前把握观念, 而且死亡本身也不可能有与之对应的前把握观念。 至于人们将“死”的概念当作前把握观念的错误, 不过是感觉, 准确说是基于错觉而形成的判断而已。
人们之所以恐惧死亡, 是因为人们错误地把死亡这一事实同人生的价值意义联系起来, 伊壁鸠鲁认为要消除对死亡的恐惧必须通过研习哲学, 悟出“死亡和我们毫不相干”的道理。 人们对死的恐惧源于对生的无知: 从物理学角度看, 人和世间万物一样都是由原子偶然聚合而成的, 构成人的原子并不比构成其他事物的原子高明; 从准则学角度看, 生无非感觉器官的形成和感觉能力的获得。 既然生本身与人生意义毫不相干, 那么作为其对立面的死, 也不应具备人生价值。 每个人同自己的死是毫无关系的, 那么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便只能来自对他人死亡的感知。 然而伊壁鸠鲁认为: 死亡不仅和死者毫不相干, 而且和生者也毫不相干。[6]86从原子论角度看, 每个人都是由原子和虚空偶然聚合而成, 那么构成不同人的原子必然不同, 产生的感觉也就不同。 由于不具备通感的可能性, 死者个人的感受也是旁人无法获得的。 从伦理学的角度看, 伊壁鸠鲁根据亚里士多德“恐惧只属于近在眼前的最有破坏性的恶”的思想指出, 既然死亡对于死者或者濒死时都不可怕, 当他活着时死亡就更不可怕了。
2.2 向神祈求是毫无意义的蠢事
“感觉的丧失就是死亡”, 但死亡绝非单纯感觉的丧失。 感觉的丧失只能说明肉体的死亡, 以个体幸福为最高目标的伊壁鸠鲁更关注内心(或灵魂)死亡, 这一点正是基于他对神与灵魂的“影像”学说展开的。 在政治就是宗教的时代, 人们对灵魂的理解同获得幸福密切相关。 “如果构成灵魂本性的那些原子——尽管数量很小——消失了, 则余下的有机整体即使整个地或部分地持续下来, 也不可能有感觉了。”[2]13灵魂不可能在人死后独立存在, 没有灵魂的肉身也不会再有感觉, 这对柏拉图以来盛行的灵魂不灭论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灵魂是脆弱的, 如果它“不被有机体的其他部分包住, 就不能进行感觉”[2]13, 人的死亡就是构成灵魂的原子集团会迅速消散瓦解, 这种消散瓦解与构成肉体的原子集团的消散瓦解是没有差异的, 因此, 在伊壁鸠鲁看来, 不仅感觉的丧失是死亡, 灵魂的消散也是死亡。 只是人们常常贪图肉体的存在, 而忽视了内心灵魂的保养, 卢克来修提醒人们: “在身体患病时, 心灵也往往失常……既然身体上的疾病的确传染并渗入到心灵之中, 你必须承认, 此时心灵已经解体毁灭。”[1]237可见, 只有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并存的状态才是真正的幸福。
伊壁鸠鲁不仅讲神, 而且将对神的研究置于其学说的重要位置, 若仅凭“神是确实存在的, 因为这一知识是清楚明白的”[2]30, 认为伊壁鸠鲁是一位主张有神论的唯心主义者, 是对伊壁鸠鲁整个哲学体系的忽视。 伊壁鸠鲁笔下的神不是要人们像信仰宗教那样对其进行敬仰膜拜, 而是为灵魂的无纷扰提供了一条实现的途径。 “幸福和不朽的存在者自己不多事, 也不给别人带去操劳, 因此他不会感到愤怒和偏爱, 所有这些情绪都是软弱者才有的。”[2]38神不会干涉人们的现实生活, 宗教所要求的对神的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 既然不存在不朽的灵魂, 即使死亡本身是痛苦的, 人死后也感受不到任何痛苦。 神不会有愤怒和偏爱的个人感情, 那么宗教悬设的地狱和死后审判便不会存在, 换言之, 既然神不是永恒存在的, 人作为选择主体的地位便可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了。
3 好好地生与好好地死: 死亡态度的哲学意义
通过对生与死、 灵与肉、 感觉与理性、 原子与虚空的考查, 伊壁鸠鲁建立起了以死亡治疗哲学为主线, 囊括准则学、 物理学和伦理学在内的庞大哲学体系。 伊壁鸠鲁本人对为了理论而创造理论的态度是十分鄙视的, 因为研究哲学的目的在于, “老年人通过自己的阅历, 面对良善的事情时依然如年轻人一样行事, 年轻人则因不再对未来感到恐惧而变得成熟”[3]1063-1065, 进而使每个人都过上幸福的生活。
3.1 真正的幸福: 灵魂的无纷扰与生活的有德性
既然死亡与我们毫无相关, 我们便只需关注当下的生存, 伊壁鸠鲁并不提倡盲目生活而主张不断追求幸福, 而真正幸福只能通过研究哲学来获得: “对于那些导致幸福的东西, 我们应当努力钻研; 如果幸福已经降临, 那我们就拥有了一切; 如果它尚未降临, 那我们就要尽一切努力去赢得它。”[3]1065
通过细致的哲学研究, 伊壁鸠鲁得出了真正幸福生活的标准: “我们所有的选择和规避, 都指向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 因为这就是幸福生活的目的。”[3]1069伊壁鸠鲁依然坚持了肉体生命和内心灵魂二分的思路, 当人们身体有痛苦时自然不会感到幸福, 但相对于身体的痛苦, 伊壁鸠鲁更看重内心对幸福的感受。 “快乐不是无止境的狂欢滥饮……而是冷静的推理, 找出我们进行所有选择和规避的原因, 将那些让灵魂陷入最大纷乱的观念赶走。”[3]1069由于幸福只能作为主体内心感受, 在获得幸福方面, 灵魂无纷扰自然比身体无痛苦具有更大意义。 灵魂之所以会受到纷扰, 在于“总是推想或猜测存在着什么永久的坏事, 这或者是由于[地狱]神话, 或者由于害怕死后失去感觉, 就好像死亡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似的”[2]18, 推想和猜测本身并不会引起灵魂的纷扰, 问题在于推想和猜测违背感觉和前把握观念的准则, 即烦扰并不来自理性的参与, 而是来自对非理性的过分执着。 伊壁鸠鲁认为充满理性思考的天文学研究是安静灵魂的“减法疗方”: “除了带来心灵的无烦扰和坚定的信念之外, 再无其他目的”[2]20。 为了区别于传统快乐主义的主张, 伊壁鸠鲁强调“审慎”权衡一切感觉, 在明智的基础上追求身体无痛苦和灵魂无纷扰的真正幸福。
既然对死亡的恐惧造成了灵魂的纷扰, 那么获得幸福就必须消除恐惧。 伊壁鸠鲁果断否定了遁隐山林、 革除自我的做法, 指出只有保持明智(清楚明白地了解和呈现证据), 当惧怕和纷扰出现时才可以及时发现并当下消除。 人不仅是行为的主体, 更是价值的主体。 “所有这一切中首要和最大的善就是明智……一个人不可能快乐地生活, 除非他明智、 美好而正义地生活着; 一个人也不可能〈明智、 美好而正义地生活〉, 除非他快乐地生活着。 因为德性同快乐地生活结合为一, 而快乐地生活也同德性不相分离。”[3]1071明智不仅要了解许多具体知识, 更希望人们真切思考人生价值: 一方面, 贪恋生命的长度是不必要的, 因为它完全在我们把握范围之外, 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努力实现当下的幸福生活; 另一方面, 生存在世界上是不能全凭运气的, “运气不好但理智行事的人, 强过运气虽好但却愚蠢行事的人”[3]1073, 只有在理智指导下获得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
3.2 贤者既不畏惧死亡, 也不厌恶生存
面对古希腊晚期社会动荡的现实, 人们对死亡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许多人有时将死亡视为最大的恶事而加以逃避, 〈有时又将之视为对生活中各种恶事的解脱而加以选择。 而智慧的人既不会孜孜求生, 〉也不会对死亡感到恐惧。 因为对他而言, 生不是一种纠缠, 死也不会被他视为一种恶。”[3]1065-1067不论是死亡灾难说还是死亡避难说, 在伊壁鸠鲁看来都是虚妄的, 明智的贤人应当坦然面对生与死, 既不畏惧死亡, 也不厌恶生存。
同许多哲学家一样, 伊壁鸠鲁不是一位只会夸夸其谈的伪君子, 他一生都在践行自己的主张。 拉尔修曾经描述过伊壁鸠鲁临死前的镇定与从容: “别了, 请你们记住我的教导。 这就是伊壁鸠鲁临死前给朋友们的最后的话。 他洗了一个温水澡, 喝了一点纯酒, 然后就被冷酷的哈德斯带走。”[3]989结石症和胃病使临死前的伊壁鸠鲁痛不欲生, 然而, 他依然宣布: 他生命的最后一天是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伊壁鸠鲁并非第一位劝诫人们不要惧怕死亡的哲学家, 在伊壁鸠鲁之前, 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早已开始了这样的工作, 但他们要达到的目的却是截然相反的[6]86-87: 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劝人们不要惧怕死亡, 目的在于劝说人们追求死亡并走向死亡, 因而他们的死亡哲学就目的而言是一种劝死的哲学。 与此相反, 伊壁鸠鲁劝诫人们不要惧怕死亡, 是避免盲目地追求死亡和走向死亡, 进而唤醒人们的理智, 防范死亡恐惧对人生的各种“偷袭”, 让人们获得真正的幸福。 因此, 伊壁鸠鲁的死亡哲学乃是一种“劝生哲学”。
由于原子存在偏斜运动, 人们生存于其中的世界便是一个以各种偶然性构成的世界, 原子和虚空的组合不可能始终给每个人幸福, 身体有痛苦和灵魂受纷扰的状态总会出现。 尽管死亡之后就无所谓痛苦还是快乐, 伊壁鸠鲁仍坚决反对通过死亡来摆脱因偶然性导致的种种痛苦和纷扰。 正是从这样一种比较健全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出发, 伊壁鸠鲁能够在死亡未到来时“好好地活”, 当死亡到来时“好好地死”, 这就是我们从伊壁鸠鲁的哲学中所应汲取的最重要“教养”。
[1][古希腊]伊壁鸠鲁, [古罗马]卢克来修. 自然与快乐: 伊壁鸠鲁的哲学[M]. 包利民, 刘玉鹏, 王纬纬,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2]汪子嵩, 陈村富, 包利民, 等. 希腊哲学史(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3][古希腊]第欧根尼·拉尔修. 名哲言行录[M]. 徐开来, 溥林,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4]吴国盛. 希腊空间概念[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5]杨适. 古希腊哲学探本[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6]段德智. 死亡哲学[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
The Philosophy of Death of Epicurus
YANG Peng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The Philosophy of Epicurus perfectly reflects the ethical spirit of natural philosophy in the Hellenistic period. His per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existence and examine of death beyond pure therapeutic philosophy, and infiltrates into the whole philosophy system of Epicurus, including standards, physics and ethics. Investigating the philosophy of death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 the whole philosophy system of Epicurus. On the other hand, Epicurus clar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cumulation and dispersion of atom and the life and death of individual, denies the reality and value of death from the past philosophers, as well as criticizes worshiping the gods for the fear of death. Epicurus points out that the real happiness signifies the body without pain and soul without distractions, and advocates people not to fear death or detest life, which aims to live with virtue and intellect.
Epicurus; death; existence; therapeutic philosophy
1673-1646(2016)06-0055-05
2016-06-11
杨 鹏(1991-), 男, 硕士生, 从事专业:价值哲学。
B502.31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6.06.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