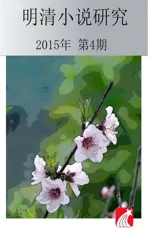疑而难信的传记——读《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
2016-01-06马成生
疑而难信的传记——读《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

·马成生·
摘要
蒲玉生先生著的《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是《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大型丛书之一。据该丛书编委会的《出版说明》,这是一项“原创的纪实体文学工程”,“必须在尊重史实基础上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反对戏说、颠覆和凭空捏造”。笔者就是遵循这些“说明”,阅读这部《施耐庵传》,感到有多处与“说明”并不相符。所谓“纪实”传记,实乃疑而难信。关键词
《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施耐庵施彦端一、把虚假不实的生卒年代写入《施耐庵传》
首先,看《施耐庵传·引言》的叙述:“元末明初的文学大师施耐庵,本名彦端,字子安,又名肇端,又字耐庵(或别号耐庵)。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生于泰州海陵县白驹场街市,明洪武三年(1370)病逝于淮安,享年七十五岁”。
这里,把“文学大师施耐庵”,说是“本名彦端”,“又字耐庵”。这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学术界就一直在争辩,并被多人否定的问题。此处暂且不谈。现在,只就其生、卒年代先考察一下。
这个“本名彦端”者,生于“元贞二年”(1296),卒于“洪武三年”(1370)。其根据是《兴化县续志》中的王道生《施耐庵墓志》(以下简称“王志”)。此志极有近人冒名伪作之嫌。它在1928年11月8日于上海《新闻报》发表之时,尚无这样的生卒年代。为何从无变有呢?1982年5月,兴化县施耐庵文物史料陈列室编印的《施耐庵资料一》中,有丁正华等《清理施让残墓文物及继续调查施耐庵史料报告》一文。其中对此有具体说明。原来在上世纪40年代,兴化人刘仲书(1880—1955),为修撰《兴化县续志》的“坐办”,即实际负责人。他为了把这个“本名彦端”的施耐庵编入县志,便对“王志”做了手脚,作了“改动”,于是,才有这个“生于元贞丙申岁”(元贞二年)、“殁于明洪武庚戌岁”(洪武三年)的生、卒年代。丁正华等说:“改动当在入志之时,改动者或即刘仲书,或为白驹施姓而刘参与其事。”此“改动”之时,相距明初已近六百年,并无确切根据,这么轻举妄动,当然是难有什么真实性的。
且看这个施彦端真实可信的文物史料。杨新作于明景泰四年(1453)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此铭的主人是施让,以下简称“施让铭”),其中明确记载着:“这个施彦端”于“洪武癸丑”(1373)生施让,字以谦。刻制于“嘉靖岁甲申”(1524)的出土文物《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也明确记载着:“(曾)祖彦端,会元季兵起口口口家之。及世平,怀故居兴化(还)白驹,生祖以谦。”这“世平”,即朱元璋平定天下,建立大明皇朝,建元“洪武”之时。可见,对施让的出生时间,两者的记载一致,其真实可信,自不待言。“施让铭”中还明确记载着:这个施彦端,两个“皆自名门”的媳妇,对他“始终弗怠”的“孝养”。这两个媳妇,大的顾妙善,生于“洪武辛亥”(1371),小的陈妙贞,生于“洪武戊辰”(1388)。那时婚龄较现在低些,一般是十六而后嫁。假定是十六虚岁就出嫁,那也要分别在1386年与1403年才能为施家媳妇。可见,这个施彦端自当于1403年尚生活在世。上述文物史料所记载的,自当是这个施彦端真实可信的生活年代。至今为止,尚未有任何文物史料能够纠正或推翻它。我们尊重事实,实事求是,自当要肯定它。
现在,就以此对照一下刘仲书“改动”出来的生、卒年代。自1296年到1403年,已是107年了,这个施彦端岂能如此长寿!再看,自1370年去世三年后的1373年,还生儿子,去世33年后的1403年还受到“始终弗怠”的“孝养”,古往今来,普天之下,岂有此事!分明可见,刘仲书的“改动”,不符史实,未免荒唐,自当摒弃!然而,浦先生的《施耐庵传》,恰恰置施彦端真实可信的生活年代于不顾,偏偏把刘仲书“改动”出来的这个虚假不实的生、卒年代写入传中。作为“纪实体文学工程”的传记,怎能这样?也许有人说,近六十余年来,也有不少人采信刘仲书“改动”出来的这个生、卒年代呢。这话固然不假,但是,我们研究古人,确定其生、卒年代,岂可以“不少人采信”为根据,而不以真实可信的文物史料为根据?
《施耐庵传》中,这个“本名彦端”的施耐庵,其生、卒年代既然与施彦端真实的生活年代牴牾,因此,按照这个生、卒年代而编排的一生行迹、种种事件自然也难免是虚假不实的。且看一例。
如施彦端的仕途问题。《施耐庵传》中说:“至顺二年辛未,1331年,36岁,赐进士。”(286页)“至元元年乙亥,1335年,40岁,约此年在钱塘县任县尹。”(287页)这个中进士、官钱塘的时间与年龄,就是根据上述虚假不实的生、卒年代而编排出来的。人们一看,立刻知道,根据这样编排的时间与年代,这个施彦端于1373年生儿子之时,就已经是78岁了。这自然就是不太可能之事。而根据文物史料,施彦端的生儿子时间是真实的,所以,传中编排的赐进士与任县尹就自然是不真实了。这一点,不妨再看《施让铭》《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这些真实可信的文物史料,其中也都丝毫未有提及这些进士、为官等大事。施族第十四世孙施封作的《施氏长门谱序》,开头就是“族本寒微”。如果这个施彦端真的有既中进士,又为官等大事,岂会这样!而且,这进士、为官不仅是一家的大事,一族的大事,也是一县的大事,而兴化县的系列旧志,如万历十九年的“欧志”、康熙二十四年的“张志”,咸丰二年的“梁志”,对大体与施彦端同时的顾成、顾逖等人的进士、官职、政绩等均有具体的记载,而对施彦端却是丝毫未有提及。所谓“钱塘县任县尹”,据明万历三十七年的《钱塘县志·纪官》,元代汉人任知县的有赵渊复,任县丞的有顾仲信,而施彦端,也是丝毫未有提及。据此,《施耐庵传》中的“赐进士”、“钱塘县任县尹”,实在难以肯定,也只能是疑而难信。
二、把荒诞不经的事迹写入《施耐庵传》
现沿着《施耐庵传》中,这个“本名彦端”的行迹,且举数例如下。
例一,这个“本名彦端”者,在郓城之事,且看浦先生的叙述:
至顺二年辛未,1331年……经国子监司业刘本善推荐,任郓城县训导。(286页)
在郓城的一、二年中,施耐庵搜集了若干梁山英雄故事……进行实地考察……做过细致的调查……且绘制成图。(53页)
对于这些叙述,不妨先与实际情况对照一下。
首先,“司业刘本善”有墓在郓城张营乡,其墓碑仍在,“首行字为‘刘司业先茔之志铭’”,“尾行字为‘大元泰定元年九月二十二日’”。请看,这个“司业刘本善”于“泰定元年”即1324年就已经去世了,怎么还能在七年之后即1331年去“推荐”人?世间岂有此事!再看《水浒传》中的实际描写。如“林冲雪夜上梁山”,正是严冰封河的时刻,而梁山边朱贵酒店的人却说:“若要去时,需用船去。”(11回)梁山在郓城东北数十里,宋江自郓城流放江州,向南已“行了一日”,次晨,“约莫也走了三十里”,此地北距梁山至少百里以上。然而,刘唐等在梁山泊边截住宋江,用船“当时载过山前大路”,很快便上断金亭、忠义堂,与晁盖等梁山头领“聚会”了。(36回)可见,这里把郓城、梁山一带的气候物象与地理态势,全都写错了。如果这个“本名彦端”者真在郓城住过“一二年”,更有“考察”“调查”之行动,岂会有这样的描写。分明可见,浦先生上面的种种叙述,经不起实际的检验,完全违背事实,未免是荒诞不经。
例二,这个“本名彦端”的施耐庵,于郓城之后,又自白驹跑到杭州来与施惠“合一”之事,且看浦先生的叙述:
1342年……定居杭州……以施惠笔名发表《幽闺记》。(288页)
施耐庵以施惠笔名,写过一篇曲子《咏剑》。(29页)
《录鬼簿》还向我们透露了施耐庵(施惠)的一批诗朋酒友:赵群卿……陈彦实……(82、83页)
他“坐贾为业”。(82页)
这里,分明让白驹那个“本名彦端”的施耐庵,居然跑到浙江来“定居杭州”了。并且,多次用“施耐庵(施惠)”来表述,既指定他“住西湖栖霞岭麓”(75页),又指定在吴山“坐贾为业”,还“说经浑经”,称“耐庵”(82页),完全把两人“合二为一”了。除此之外,浦先生还用自己创造的一句话语“钟嗣成《录鬼簿》介绍施耐庵”,而后,把钟嗣成《录鬼簿》介绍施惠的话接上;而且,还把无名氏(一说贾仲明)后来补写的《凌波仙》也合进去;不仅如此,还把施惠的朋友赵君卿、陈彦实作了颇为具体的介绍,说成是施彦端的朋友(81—83页)。这样,一般不了解的同志,可能真以为白驹的施彦端就是杭州的施惠了。然而,尽管浦先生如何多方面地介绍施惠,恰恰把《录鬼簿》卷下的开头,介绍施惠等19位作家时的一句话,即“方今已亡名公才人”这一句不作介绍了。《录鬼簿》作于至顺元年(1330)。这明确表示:施惠已于1330年就是“已亡”之人了。而白驹这个“本名彦端”者,于1403年尚在世。试问:这怎么能与73年之前就“已亡”的施惠“合一”!这样,浦先生所说的“施耐庵以施惠笔名”写《咏剑》、“1342年……定居杭州”“住西湖栖霞岭麓”之类,全是无稽之谈。
“当今已亡名公才人”一句,是“双施”不能“合一”的关键;然而,浦先生对之,正如上一节对待施彦端真实可信的生活年代一样,视若无物,弃之不顾。
附提一下。把钱塘施惠与钱塘施耐庵看成同一个人,把《幽闺记》与《水浒传》看成同一个作者,在晚清至民国时期曾有人提起过,但也只是片言只语,并无确切根据,尤其是这两书的主题、思想、语言风格迥异,且《水浒传》成书,远在1330年施惠“已亡”之后。施惠与施耐庵显然不是同一个人。用钟嗣成《录鬼簿》有关记载一对照,是非分明。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有《施耐庵、施惠与施彦端难以“合一”》《钱塘施耐庵与兴化施彦端难以“合一”》两文,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的《杭州与水浒》一书中,说明钱塘施惠、施耐庵(真正的《水浒传》作者)与兴化施彦端分明是三个人,不是一个人。此处,不再多提了。
总之,浦先生把那个于1373年尚生儿子的白驹“本名彦端”者,与1330年就“已亡”的杭州施惠“合一”起来,这也未免是一种荒诞不经之事。
例三,这个“本名彦端”的施耐庵,跑到杭州来取得“书面素材”之事,且看浦先生的叙述:
据蒋瑞藻《小说考证·卷一·水浒第十四》,其中所录笔记资料颇丰,有:记述“(六和塔)塔下旧有鲁智深像……进泷浦下有铁岭关……国初江浒人掘地得石碣,题曰‘武松之墓’。”钱塘之任,是施耐庵得到书面素材、踏勘传说古迹,接受水浒戏艺术熏陶的重要阶段。(12页)
上已提及,这个“本名彦端”的施耐庵不可能中进士,以至有“钱塘之任”,不可能在杭州“踏勘传说古迹”以至“受水浒戏艺术熏陶”之类。这且不说。这里,仅就他取得“书面素材”一事,辨析几句。蒋瑞藻《小说考证》卷一中,有关《水浒》的“书面素材”18则。浦先生所举的“书面素材”,在《湖壖杂记》中的《六和塔》条,其中,除浦先生删去一部分外,其余文字与浦先生所引的完全相同。这部《湖壖杂记》作者是陆次云,据光绪四年刊本影印本《江阴县志》:“康熙二十四年,海防同知陆次云,字云土,浙江钱塘人。”分明可见,这个陆次云,上距这个“本名彦端”的出生已三百多年了。试问:施彦端如何能够这么提前三百多年取得这些“书面素材”?这,显然又是一种荒诞不经之事。
例四,这个“本名彦端”的施耐庵送孙子入张士诚幕之事,且看浦先生的叙述:
卞元亨又一次来到施耐庵家,仍有劝他辅佐张士诚的意思。施耐庵……(说):“……我的孙儿施述元,能文能武,愿送入军中,报效大王。……张士诚任命施耐庵的孙子施述元一官半职,并拨给了一班人马。”(111—112页)
此时是张士诚刚起义的1353年。据前已提及的“施让铭”,这个施述元的父亲施让,出生于“洪武癸丑”(1373)年,其母亲顾妙善出生于洪武辛亥(1371)年。怎么在父母出生之前20年与18年,他就长大成人,“能文能武”,并能任官职,能带“一班人马”?这不是比前面已提及的父亲“去世三年”又生儿子更加荒诞不经吗?
例五,这个“本名彦端”的施耐庵暮年写作《古本水浒传》之事,且看浦先生的叙述:
明朝洪武初年……夏秋之交,梁山脚下朱家客店来了个清癯干瘦的老者,在客店住了一个多月……这人便是施耐庵。(196页)
一对梁山父子,向他讲述了宋江等义军的另一种结局……没有接受招安……义军全军覆没,全部壮烈牺牲。(197—198页)
据此,浦先生便认为,这个施耐庵“酝酿了两种结局:一种是血战到底的《古本水浒传》120回本。这部书的前70回与金圣叹评点的贯华堂本《水浒传》基本一致,而后五十回……梁山好汉没有受招安,直到第120回,他们还在与官军血战。后50回本曾由上海中西书局于1933年单独排印过”(198页)。
浦先生所讲的这种《古本水浒传》,就在1985年8月,由蒋祖钢先生校勘,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过。它一面市,就遭到许多学者的“辨伪”:因为其后50回与前70回风格就不一;后者情节结构也都比前者呆板平庸;后者每回文字都要比前者少三分之一左右,且都无诗词之类;人物结构也“走样”,最明显的如鲁智深,原是“遇江而止”,却变成五台山修行;更主要的是语言,如“没有”“没曾”“给”等近代的词语,前者均未见,而后者常用。总之,前后两者,不是出于一人之手。大家认为,把后者与前者合一,并非增光,而是添丑。当时,虽也有学者为之辩护,但缺乏力证。而今,浦先生作传,也未提出力证,怎么便把前后两者都归于一个人之作呢?这里,且不论其它,只提一个问题:这本《古本水浒传》究竟是哪一年写出来呢?
据浦先生叙述:这个“本名彦端”者,于“洪武初年”(1368)的“夏秋之交”上梁山,“住了一个多月”,该是八九月间了。之后,回到白驹,“补写”“朱贵开店的故事”与《水浒传》中别的“空白”(196页),还“常常在白驹北宝寺说书场说书”(243页)。这,又该是相当长的时间。之后,被捕。在牢中,光是续写《水浒传》后30回,就“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之前,已坐牢一段时间,之后,又“装疯卖傻”,“写起了‘姜子牙斩将封神’来”(248页)。这,自然又该是相当长的时间。然而,“一三六九年十月初二”,他却在淮安“祝寿”了。之前,他自南京大牢放出,到白驹已住了些时,而后才来淮安呢。据浦先生的安排去推测,这个“本名彦端”者,光是坐牢时间,就不够了,还有别的时间来写别的作品吗?而“祝寿”之时,他已“虚弱”“多病”,“一生好酒”的他已不能饮酒,“只吃一点点面条”(257页)。此后仅仅五个月,便“离开了人世”(258页)。试问:他怎能写出50回的《古本水浒传》?难道不需要应有的精力与相当的时间?他难道不是人而是神!如此荒诞,人们一看,难免惊讶!
以上,如让死人去“推荐”活人,让生活年代相距甚远的两人“合一”,让明代人去取得清代的“书面素材”,让父母远未出生而儿子便“能文能武”,让缺乏精力与时间的人写出50回《古本水浒传》等,都是这个“本名彦端”者的主要行迹,占了《施耐庵传》不少篇幅,而这些全是违背常情,荒诞不经之事,如何能使人相信?
三、把牵强附会的“原型”写入《施耐庵传》
且看浦先生的叙述:
《水浒传》是借宋江起义为名,述张士诚起义之实。(13页)
《水浒传》的故事,明写宋江,实写张士诚。(117页)
一部《水浒传》纯属是以宋江起义说事,而以张士诚起义为原型和背景的。(180页)
这里,竟把《水浒传》中的主角宋江形象说成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张士诚为“原型”,这是明显的牵强附会。不论从两者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思想倾向以至生活作风方面来看,都是相距甚大以至相违的。笔者已经写过一篇《孔、跖非同型——略说张士诚非宋江“原型”》,于2015年5月《现代语文》上发表。此处不多说了。然而,浦先生还有其他方面的类似论述:
施耐庵有感于吴王张士诚的农民起义,这里的洪太尉与张天师都是影射张士诚的:一是用了张士诚投降元朝时的官职,二是用张士诚的姓。(80—81页)
书中曾多次出现“小人姓张”、“张大哥”等张姓细节。(116页)
为何《水浒传》中至少七处写了张姓,而没有写其它李、王、曹等姓,说明施耐庵是有意识地将张士诚隐晦曲折地写入《水浒传》中。(117页)
现在,分别按次略析一下。
《水浒传》中多次出现“小人姓张”“张大哥”等张姓细节,究竟为什么?当燕青冒认为“张乙的儿子张闲”而进入李师师居处之时,《水浒传》作者就已直接出面来说明:“原来世上姓张姓李姓王的最多”(72回),自称姓张,容易蒙混,不易发觉。这与什么“施耐庵是有意识地将张士诚隐晦曲折地写入《水浒传》中”分明没有关系。在《水浒传》中还有浦先生未提及的“张千李万”呢(36回)。究其实际,这些姓张姓李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谓张三李四,张家长李家短,都是泛指。常说的“张冠李戴”,也并非是姓张的帽子,戴在姓李的头上。《施耐庵传》要把语言习惯中的“泛指”,说成“实指”,要借此与张士诚扯上关系,这也只能是牵强附会。
以上讲的是人事,以下讲的是地理。略举一例:
金沙滩。施耐庵在《水浒传》第十一回中写道:“小喽啰把船摇开,望泊子里去奔金沙滩来。”这泊子,乃是洪泽湖的泊子原型。(181页)
“这泊子”,即梁山水泊,怎么会以洪泽湖的泊子为原型?这里,需要引一点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中的描写:
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通巨野、金乡,北靠青、齐、兖、郓……
这位高文秀,是元代著名杂剧作家。据元代钟嗣成《录鬼簿》:“东平人,府学(生),早卒。”据《古州东平与历代名人》,他约生于1240年,卒于1290年。他所描写的梁山水泊,就是以东平旁边的现实中的梁山泊为“原型”,他所描写的梁山水泊旁边的城市,如巨野、济阳以及青、齐、兖、郓等至今仍在。这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与他同时或稍后的元人,如李致远在《大妇小妻还牢末杂剧》中写的“路打梁山泊所过”,无名氏《争报恩三虎下山杂剧》中写的“占下了八百里梁山泊”,无名氏在《鲁智深喜赏黄花峪杂剧》中说的“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等等。这都是高文秀以现实世界中的梁山水泊为“原型”而描写的梁山水泊。后来在《水浒传》中,柴进向林冲介绍梁山水泊(11回),宋江向燕顺等介绍梁山水泊(35回),也都是移用高文秀上述的描写,只是略改动数字而已。高文秀描写梁山泊,白驹施彦端尚未出世呢,而到浦先生笔下,怎么会突然夺掉高文秀的著作权,变成这个“本名彦端”者以“洪泽湖的泊子原型”而描写的梁山泊?这也未免太牵强附会了吧。
为什么在人事与地理描写方面有这样的牵强附会?
看来,是这个“本名彦端”者与张士诚同是白驹人,生活时代亦相及,借此似可以“就近取材”之类为由,为“白驹施彦端进士,字耐庵,为《水浒传》作者”这样一个观点添一个“内证”;然而,毕竟缺乏确切的内在联系,没有科学性,全凭牵强附会的所谓“原型”云云,自然也就不可能取信于人。
四、把缺乏史实性的传说写入《施耐庵传》
这种缺乏史实性的传说,主要就是指《施耐庵的传说》,共有两种版本:一种是马春阳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出版,共73篇;另一种是张袁祥、胡永林整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出版,共31篇。两个版本合起来,共104篇,内容大同小异,有的重复,都是讲这个“本名彦端”的施耐庵如何出世、成长、写《水浒传》等种种行迹。对这种传说,浦先生认为:“至少是施耐庵实有其人,在这些地方活动过的极重要的证据。”(8页)对浦先生的话,须要作些分析。试问:如果这些传说与史实牴牾,明显不符,这也能看成“极重要的证据”?
在此,先简要提一下这些传说的问世年代。且看,这些传说中所明白表露的这个“本名彦端”者的生、卒年代,不迟不早,恰恰就是刘仲书“改动”出来虚假不实的生、卒年代,同时几乎都是以“施耐庵”三字统率各篇。前已提及,刘仲书是在上世纪40年代“改动”出这个“本名彦端”的施耐庵生、卒年代的,而“耐庵”两字最早出现是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的“长门谱”中,是在谱中正文“彦端公”右下旁添的“字耐庵”三字(既是旁添,自当是在正文写成之后,但究竟是何时旁添,现无法考实)。再是在咸丰二年(1852)修的《施氏族谱》中,是把“施让铭”中的“先公彦端”窜改为“先公耐庵”。我们把刘仲书的“改动”时间与“耐庵”两字的出现时间结合起来看,这些传说的问世时间,自当不大可能是在乾隆四十二年以至咸丰二年之后(即使有,亦是少数),而更可能是上世纪40年代之后。其中,如《天罡地煞仿罗汉》,把1975年“评《水浒》”运动中公之于世的《毛主席语录》“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只把“反”字改为同义的“勿”字)也编制进去了。这分明是问世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施耐庵热”时代呢。总的看来,这些传说相距这个“本名彦端”者已经五六百年了,很难说有多少历史价值,很难以此证明这个“本名彦端”者“其人”及其“活动”情况。然而,浦先生却以此作为史料而写入《施耐庵传》的竟有50来处,有的照抄原文,一字不改。现就把这部分传说,分类略作辨析如下。
一类是把他人他事改制成施耐庵传说。
先看《施耐庵传》第二章《官场岁月》中,这个施耐庵“在钱塘当县尹“时的一件事:
施耐庵听一位说书人说《宋江征方腊》,说到宋江带兵在钱塘县与方腊展开血战,林冲手提单刀,一马当先,在杭州城东南候潮门与方腊交战,一连几个回合,林冲因年老体弱,打不过方腊,在石牌楼跌马,城头巷飞刀,最后到惠民坊跌入陷马坑,被乱刀砍死。当地居民就将林冲尸体葬在附近大柳树下。(75页)
这一段施耐庵所经历的事情,全抄自《施耐庵的传说》中的《柳下祭林冲》,只是个别词句略有改动。接着,又说施耐庵与当地一老人找到林冲坟墓,设祭,并议论林冲英雄事迹,终于施耐庵写了“林冲误入白虎堂”“刺配沧州”“大闹野猪林”等“十回书”。这些,也是来自上述这篇传说。(75—76页)
这段抄自传说的施耐庵的经历,难道真是施耐庵的史实吗?退一步说,难道真有如此的传说吗?勿!
那是清末民初,杭州说“水浒”有王(春镛)、郭(君朋)、陈(国昌)、张(锦鹏)四大派。其中的王派,从“宋江征方腊”说起,创作了19回《后水浒传》,就讲了宋江军与方腊军在杭州四眼井、涌金门、凤凰山一带的战斗,其中就有林冲在石牌楼跌马,城头巷飞刀,最后跌入惠民巷附近陷马坑等情节。杭州一些老“书迷”,至今尚记得。杨子华先生在《水浒民俗文化》中对此有详细论述,不妨参看。有人却把《后水浒》中说林冲这一段子,加以扩展,添枝加叶,“创造”成这么一个《柳下祭林冲》,成为“施耐庵的传说”,这实际就是造假。然而浦先生居然以这假传说,作为真史料,作为白驹这个“本名彦端”者写《水浒传》的真凭实据了。
再看《施耐庵传》第三章《书会才人》中,这个“本名彦端”的施耐庵在温州的一些叙述:
施耐庵同刘伯温来到温州……跨进了江心寺……惠月长老……便请他俩作诗题词留念……施耐庵望了望窗外……只写下“虫二”两个字。这惠月长老……一时不解其意。(89—90页)
接下来,刘伯温写了一首七绝,每句开头一字是“风、月、无、边”。惠月长老终于知道:“風、月”二字没有边,岂不就是“虫、二”?于是,高兴地喊出来:“妙,绝妙!绝妙!”(90页)
《施耐庵传》中,这一段关于“风月无边”的叙述,除个别文字有出入外,其余全抄录于《施耐庵的传说》中的《“风月无边”传佳话》。究其实际,这段传说也未必是有关《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传说。在杭州一带至今还常有人说,清代乾隆帝弘历与纪晓岚游览西湖湖心亭,弘历一见景物,便题了“虫、二”二字。周围的人都不晓其意。弘历问纪晓岚,纪只说“让我想想”,并未说明真意。这时,一位游客直率地说:“好一个风月无边”,弘历要他说个究竟,他便说:“風和月两字无有边缘,不就是虫、二?这里的风景真是太好了。”弘历很赏识他,便把他带到御书房工作。
这则“风月无边”的传说,其实还另有源头。据《鉏雨亭随笔》,明代妓女湘英的门匾上让唐伯虎题了“风月无边”四字,人们为之赞美。祝枝山却说:“风月无边,就是‘虫、二’,这不是笑料?”可是,湘英没有改掉,于是,便也流传开来,连绵不断。这个源于湘英的“风月无边”故事,也很可能是被改编而成为《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传说。
在第四章《军事生涯》中,类似事例还有。如“御花苑斩狐”(131页),说是张士诚宠爱两个美女——香香和珍珍,施耐庵耽心张士诚被女色所迷,便设计杀了一只狐狸,说是两个美女的真身。这也是《施耐庵的传说》中《锦春园“斩狐”》的移用,只是个别句子稍作改动。而这《锦春园“斩狐”》,又颇似《封神演义》中的“轩辕洞斩狐”,说是比干耽心纣王被女色所迷,便把轩辕洞中化为美女的狐狸杀了。看来,很难排除《锦春园“斩狐”》是《轩辕洞“斩狐”》的改造与利用。而浦先生的“御花苑斩狐”,又把这个与施耐庵未见有什么关系的传说,作为史实而写入《施耐庵传》了。
在第五章《著书劝世》中,浦先生还采用《施耐庵的传说》中的《酒菜活了》。说是施耐庵在常熟河阳山永庆寺当作酒菜的鱼、虾、螺狮,第二天又活了。鱼“游来游去”,虾“一跳一跳”,螺狮“就是屁股没有了”。在这里,浦先生公开表明:这是传说,但又扯上施耐庵,“这民间故事有夸大的成分,但谁也挡不住人民群众对施耐庵的喜欢”(138—140页)。
其实,在浙江杭州一带,这是广为人知的济公故事。清代吴本泰《西溪梵隐志》卷四《永兴寺碑记》中就有记载:“民将食螺已断尾,(济)颠乞放池中,遂活。至今,螺无尾。”看来,这也可能是上世纪80年代的“施耐庵热”中,有人“移”去而创造成施耐庵的故事,实际与施耐庵无关,未必是“人民群众对施耐庵的喜欢”。
又一类是把《水浒传》的现成文字改制成施耐庵传说。
且看第三章《书会才人》中《造访真人》的叙述:
施耐庵游了九天殿、紫微殿、太乙殿、三官殿……便问陪同的住持真人道:“道长,别处殿宇都富丽堂皇,为何此处衰败冷落?”真人回答道:“客官有所不知,此处原为大唐洞玄国师镇压魔王之殿,过去从不开放。”(79—80页)
这些,也是照抄《施耐庵的传说》中的《访真人》。接着,便叙述“北宋嘉祐年间,京师瘟疫盛行”,洪太尉来请龙虎山张天师祀禳天灾,因而游山,“打开殿门,挖开地穴”,放走了“一百零八个魔君”。这些也是基本照抄。有些句子,如“刮喇叭一声巨响,一股黑气冲天”,一字不改,只是象声词“唿”写成“刮”。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访真人》这样的传说,究竟其源头何在,究竟是怎么形成?
首先,《访真人》上述内容基本是今天所见的容与堂《水浒传》第一回“洪太尉游山”与第二回开头一节部分内容的概括。其次,这《访真人》中还说两句回目“张天师祀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只是“祈”字改为“祀”字,其他十三个字则与容与堂本完全一样。稍有版本知识的人大致都知道:施耐庵撰写《水浒传》的时候,是不可能有这样整齐的回目的。不妨与上世纪后期发现的《京本忠义传》两叶残叶的回目对比一下,如“石秀见杨雄被捉”,“祝彪与花荣战”,文与野,雅与俗,可谓档次分明。一般专家认为,这可能是正德或嘉靖间的版本,未必是施耐庵当时的版本呢。非常明白,《访真人》中这样整齐的回目是《水浒传》问世后经过许多人加工提炼的成果呢。无疑,这些整齐的回目表明这些传说问世于施耐庵之后甚远的时代,不能排除它们问世于上世纪“施耐庵热”中。从史实角度看,这与明初真正的《水浒传》作者没有关系。再次,《访真人》中还说“施耐庵游九天殿、紫微殿、太乙殿、三官殿……”。查对一下,清同治间杨长杰修、黄联玉纂的《贵溪县志》,龙虎山上只有寺观正一观、静应观、灵宝观等,并无九天殿之类,而容与本《水浒传》第一回中,洪太尉游山时,正是游了上述这些殿宇,其顺序也完全一致。从上面数方面来看,这篇《访真人》传说,极有可能是在上世纪40年代之后,到80年代的“施耐庵热”中,从容与堂本《水浒传》改编而来,也完全是为了张扬“白驹施彦端字耐庵为《水浒传》作者”这一目的而改编的。
还有一类,是无中生有,也是缺乏生活根据的无稽之谈。
且看第四章《军事生涯》中,浦先生对“四义士墓”的叙述:
施耐庵就是隐居于此著述《水浒传》的……
蓼儿洼的东北部紧靠淮城巽关……大洼内,原为官家的坟地,坟地中有几座高大的坟墓,所处位置地势高爽,是一块“风水地”,相传那几座高大的坟墓,就是宋江、李逵等四义士的冢穴。(107页)
这则“相传”,笔者未见其他文字记载,不知浦先生采自何处。但,从史实角度,可以略加分析。所谓“冢穴”当是尸骸埋葬处。这里的“宋江、李逵等四义士的冢穴”,自然包括吴用、花荣两位。据浦先生所说的“相传”看来,这“四义士的冢穴”远在施耐庵之前,在“淮城巽关”就有了的,如其不然,哪会有浦先生这样的“相传”。然而,历史上真有此事吗?
首先,北宋末年的宋江会埋尸于此?《宋史·张叔夜传》载有“江乃降”。王称《东都事略·徽宗记》载有“宣和三年……五月丙申,宋江就擒”。宋江于投降或“就擒”之后,于何地被处决,未见记载,但历史上这么一个曾为寇为盗的宋江,其尸骸会特意运送到“淮城巽关”“官家的坟地”,而且是“地势高爽”的“风水地”去埋葬吗?恐无此理。至于李逵,宋代史书上的记载,如《三朝北盟会编》卷114,说他是“密州军卒”,《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说他与吴顺一起杀却“权知密州杜彦”,“逵遂领州事”。《宋史·高宗本纪》说“逵以密州降金”,《三朝北盟会编》卷131,说“逵为(吴)顺所杀”。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尤其是降金一事,更为当时人们所不齿,与《水浒传》中的李逵绝不相称,难称“义士”,恐怕只是姓名相同而已。何况密州,在山东海滨,距“淮城巽关”路途遥远,其尸骸更不可能特意运到浦先生所“相传”的那种坟地上的。又如吴用与花荣,看来是“水浒故事”或《水浒传》所塑造的艺术形象罢了,怎么会有尸骸以至于“高大的坟墓”?
然而,蒲先生利用这个“相传”而大做文章,先说“施耐庵就是隐居于此著述《水浒传》”,更具体肯定“施耐庵流寓淮安西北土地祠”。此地距“淮城巽关”不远,自当了解上述“相传”的内容,这自然会把“宋江、李逵等四义士的冢穴”作为描写《水浒传》一百回中的“东西四丘”,即宋江、李逵、吴用、花荣四义士墓穴的“原型”的。浦先生还大加申说,施耐庵在《水浒传》中有意多次点出“楚州南门外有个去处……俨然似水浒寨一般”,与“梁山泊无异”,并认为“这个小环境是今楚州区的南门,大环境是楚水之南的兴化、大丰一带”。这分明又是要为“兴化、大丰一带的”“白驹施彦端字耐庵为《水浒传》作者”添一份有力的“证据”呢。这还不够,还要加上这么一条佐证:“这也是大丰市白驹镇施氏宗祠门联所说:‘吴兴锦世泽,楚水封明禋’的缘故”(107页),这么东拉西扯,只能是白费笔力。浦先生所利用的“相传”,是无稽之“传”,虚无缥缈,要把它看作史实而写入《施耐庵传》已属不当了,其他种种发挥还有什么意义?
在这《施耐庵传》第七章《牢狱之灾》中浦先生还说:“据《水浒传》中所述,宋江、李逵、吴用和花荣四将军死后就埋葬在楚州南门外蓼儿洼内。”并且,把上述“相传”内容又重述了一遍(257页)。其实,“《水浒传》中所述”,是艺术形象,而艺术形象并无尸骸,不可能在现实世界的“大洼子”“官家的坟地”上出现“宋江、李逵等四个义士的墓穴”的(如果是人们读了《水浒传》,为了对宋江等的思念,造了四座假墓,那是另一回事)。看来不论从史实角度,还是从艺术角度,要利用上述这样的“相传”来张扬“白驹施彦端,为《水浒传》作者”实在是很难说得通。
再看第七章《牢狱之灾》中的《金陵坐牢》:
施耐庵写的“宋江三打大名府”这几回书,太精彩动人,大家争着要先睹为快,施耐庵说:“大家不要争啦,让我来讲给诸位听……”(243页)
接下去,“刚巧一个官员”听到,便把施耐庵“押送金陵”。“刘伯温到大牢里探望”,说“你咋来,还咋走!”于是,施耐庵便续写“受招安”“打方腊、平辽”。朱元璋仍不放他,刘伯温等又出了“锦囊”妙计,于是,按“计”“装疯卖傻起来”,“写起了‘姜子牙斩将封神’来”。(243—248页)
这部分《施耐庵传》,是移用《施耐庵的传说》中的《狱中续写〈水浒传〉》与《一夜“封神”》,有的概括其大意,有的一字未改。其实,这两篇传说本身,就有不少明显的不实之处。如说施耐庵写了《呼延灼月夜赚关胜》《时迁火烧翠云楼》《吴用智取大名府》等,这些回目是《水浒传》完全定型了如天都外臣序本、容与堂本才有的,施耐庵初写《水浒传》时怎能有。这些传说的性质,在分析《访真人》时已说明了。又如,说施耐庵在狱中写了“征西辽、平王庆、田虎、方腊”,还在狱中装“疯”,封神,以致产生“民间传说的施耐庵千日写《水浒》,一夜写‘封神’”。这些,作为传说,任意扯淡,不必计较,无所谓真实不真实。然而,浦先生撰写《施耐庵传》却把上述这些不可能是施耐庵写的回目如数抄录,至于在狱中写的书,说是“在七十回《水浒传》的基础上,又写了宋江受招安,替宋王朝去打方腊,平辽……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248页)。试问,有这个可能吗?我们从实际出发,简单评析一下。
首先,一个作家,难道想写什么便能写什么吗?宋江受招安,平辽,平方腊共30回,约30万字。对此,施耐庵原来并无准备,现要创作,总得先收集些素材。光说“平辽”吧,发生在遥远的北方边界,自“滴泪斩小卒”“打蓟州”“战玉田”“取文安”,直至“战幽州”,逼“伪辽归降”,如果脑子里一片空白,如何下笔?退一步说,即使有了一定的素材,还有复杂的艺术构思呢?即使写出初稿,还得涂涂改改,琢磨修饰,既要送皇帝阅览,总还得誊抄清楚。试想,一支毛笔,繁体汉字,像施耐庵这样不足一年便去世的衰弱老人,有可能吗?就是一个健壮的作家,一年能创作多少字?《施耐庵传》,居然叙述这样一个施耐庵,在牢狱中完成这样的创作任务,有几分真实可言?
还有一类是颠倒时序,把后事提前而编制成传说。
如第二章《官场岁月》中的《愤而悬印》:说是施耐庵“很不得志……参拜过相传涌金门张顺归神的庙宇”(72页)。这是抄自《施耐庵的传说》中的《辞官》,只是在“参拜过”之后加“相传”两字。其实,这《辞官》本身就不符合实际,纯是胡编乱造。因为,张顺被射死涌金门,“敕封为‘金华将军’,庙食杭州”,这是《水浒传》第94—96回的描写。之后,人们把涌金门内原是祭祀曹杲的“金华将军庙”,移花接木,移接到张顺身上去了。之后,才有“张顺归神的庙宇”的“相传”。据《辞官》中的描述,这个施耐庵去“参拜”之时,正是他“为官钱塘”的元朝。这时,《水浒传》远未问世呢,哪有“涌金门张顺归神的庙宇”!这是把后事提前以至时序完全颠倒了,可见传说编制者的无知轻率。然而,浦先生也当作信史!
总之,关于施耐庵的传说,即使不计较其因某些意图而大量编制于上世纪中叶之后,以至难有历史价值这一特点,就看这些传说本身,或利用他人他事改制而成,或利用现成的《水浒传》内容改制而成,或无中生有而编制出来,或颠倒时序把后人后事提前而编制出来,等等。这些传说本身与这个“本名彦端”者并无关系,井水河水,各不相干,自然就不可能利用它们来“证明”这个“本名彦端”者的任何问题,然而,浦先生竟作为史料,大量搬入《施耐庵传》中了。自然还有其他许多传说,今天难以一一考实,但就其制作时间来看,相距“本名彦端”者实在太远,缺乏史实性,是不当轻率地作为史料使用的。
附提一下。《施耐庵传》中,还有些叙述混乱,说法不一处。如第三章《书会才人》中说:施惠在杭州吴山“也说经浑经,称‘耐庵’”(82页);在第五章《著书劝世》中,说是在江阴徐家教书,又“更名耐庵”(150—155页)。更一个名,何须两次?又如第二章《官场岁月》中说:“至顺四年(1333)……施耐庵实现了他‘雁塔题名’的宏愿,是赐进士”(60—61页);而《施耐庵年表》中说:“至顺二年辛未,1331年,36岁,赐进士”;又说:“至顺四年,元惠宗元统元年癸酉,1333年,38岁,再赴大都(北京)会试,应试不第”(286—287页)赐进士,为何两次?既已“雁塔题名”,为何又“应试不第”?又如,第五章《著书劝世》中说:“施耐庵的独生女施娟”(162页)表明施耐庵没有儿子;而在第八章《大师身后》中说:“施耐庵的长孙文昱”(259页)。既无儿子,哪来长孙?又如第六章《水浒原型》中说:“施耐庵,‘会元季兵起播浙’”(186页),这,自是1353年前后之事。然而,《施耐庵年表》中说:“1353年,58岁……施耐庵还是参加了张士诚幕”(289—290页)。同是一人,不是孙悟空,如何分身?又如第七章《牢狱之灾》中,在金陵坐牢之前,已两次提到倪邵庄这个村名(232页);而到了金陵坐牢之后,又说:“改名为倪邵庄”(251页)。前已有此名,何须又改。等等。这些,几乎都是为了作传的需要而任意编造,但难免使读者头脑紊乱。
结语
浦先生说:“研究施耐庵这样的人,他‘名不见经传’,所以也不会有碑铭志乘可据。”(8页)这话,明显是不符实际的。且看,出土文物《施让地照》、杨新作《故处士施公墓志铭》、出土文物《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以及施封作《施氏长门谱序》等,都是公认了的这个“本名彦端”的施耐庵有关文物史料,其中所记载的施彦端生子、两位“皆自名门”的媳妇对他的“孝养”等,分明可看出他真实可信的生活年代。以此还可鉴别其它一些资料,如早被人指为后人冒名伪作的王道生《施耐庵墓志》以及其他一些被窜改或者被添加的资料之类。以真比假,假难遁形,大家更不难借此辨别真伪的。同时,还有系列兴化县旧志、《钱塘县志》等与上述真实可信的文物史料联系起来,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然而,浦先生面对上述种种真实可信的或有参考价值的文物史料,基本是弃之不顾,反而说“不会有碑铭志乘可据”;不但如此,反而去采信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刘仲书毫无根据而“改动”出来的这个“本名彦端”的生、卒年,撰写荒诞不经的事迹,还有牵强附会的“原型”,更有缺乏史实性的传说,于是成就这么一部疑而难信的《施耐庵传》。也许有人说,不要把这本传记看作“纪实体文学工程”,而只看做艺术虚构的小说,或者更“开放”些,看作为“戏说”类作品,这不就可免去种种指责吗!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也不恰当。因为,《水浒传》作者是一位享誉全国、名扬世界的作家,为之作传,不能胡弄,应该以史实为据,实事求是,首先让大家看到一位真实的人。
本文,只是对《施耐庵传》的初读,更是粗读,也只是对该传部分内容提出如上看法。但是,其疑而难信的特点,已经相当突出了。在此,顺笔寄语文学专家白烨先生,你在《施耐庵传》封四上赞扬“作者不仅在史料收集上显示出了特别的功夫,而且在史实钩沉与艺术铺展的关系上也把握得当,尤以对环绕施耐庵的社会环境、人际关系的考察与梳理、考据和叙述,相当用心用力……”请问,你究竟有否认真看过这本《施耐庵传》与有关史料?
注:
① 浦玉生《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
② 王道生《施耐庵墓志》,学术界已有多人指其为近人冒名伪作。笔者于2014年9月《现代语文》上的《碑文难信“辨正”未正》一文,对此亦有论述。
③ 关于刘司业的墓地,已有好些学者作了论述。此处引自童力群《论施耐庵任郓城县训导的时间是元英宗至治三年早春》,见《水浒争鸣》第13期,团结出版社2012年版。
④ 程允俊、郭云策主编《古州东平与历代名人》,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⑤ 杨子华《水浒民俗文化》,华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⑥ 此文引自《古书典故辞典》,杭州大学中文系《古书典故辞典》编写组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魏文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