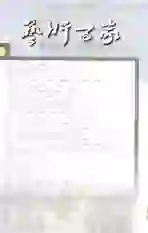当下文化语境与艺术学学科建构的现实问题
2015-12-25王德胜
摘 要: 艺术学学科正面临着由文化语境改变所导致的艺术指向性变迁。只有从当下文化语境的基本点出发,才能有效地将艺术学学科建构引向一个切合文化发展实际的方向。置身多元文化语境,在各种新的艺术现象、新的艺术经验和新的艺术阐释要求面前,能否走出既有知识传统,又走向开放性体系建构,是艺术学学科建构中最具有挑战性的现实问题。它要求把“开放的态度”具体化为学科理论的现实成果,突破有关艺术的知识传统的普遍性指向,进而完成从知识传统的封闭预设向当下艺术现实转换的学科前景。 关键词: 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文化语境;艺术学;学科建构;艺术指向性变迁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作为人文研究的艺术学学科,既包含着理论建构的持久性要求,又因艺术活动与具体文化观念、文化实践之间关系的特殊性,同时具有特定的“语境性”。文化存在语境制约着艺术发展的内在方向,也是引导和强化艺术学学科建设的现实出发点。因此,讨论艺术学学科建构,不能仅只局限于单一学科理论的内部。实际上,在各种学科建构思考的内部或背后,必定纠集着基于艺术的文化存在及其实践取向的诸方面判断理性。
当前,我们只有首先将艺术学学科建构问题置于文化存在的当下语境,从文化语境的基本点出发,才能有效地将艺术学学科建构引向一个切合文化发展实际的方向。
一 可以认为,当下文化语境的基本点,在于“四化”——“去中心化”、分层化、大众化和意义“微化”——呈现着当下文化生产与消费的总体征候,直接体现了当下文化价值指向的基本态势。第一,作为当下文化生产的意识形态特征,“去中心化”在总体上表达着文化活动的多元价值取向,以及现实文化感受作为人的生活价值经验的多元性。
它意味着,包括艺术活动及其审美经验在内,价值体验的唯一性、意义生产的确定性、文化经验的历史性不仅逐渐丧失了其在当下文化生产中的核心与主导位置,也已经难以完成其对于人的文化的现实阐释。文化生产在当下过程中不断脱开原有的价值归趋模式,转而主要依据人在日常实践中的直接感受及其所提供的经验模式,以便现实地完成文化生产的当下展开。具体到艺术、艺术活动来说,“去中心化”的文化生产现实,直接关涉艺术和艺术活动的既有知识传统,特别是有关艺术与人类文化关系的确定、艺术存在与人类精神关系的把握,以及我们对于艺术活动与现实生活感受的关系本质、艺术演变与社会进步的关系模式等的有效认定。如果说,我们曾经历史地、并且行之有效地保存了一套用以实现“艺术的”判断的美学话语,那么,在取消“中心”而演变为多元指向的当下文化生产语境中,我们实际已很难直接依据既有的文化意识和美学知识传统,对艺术的现实身份作出有效确认。这一点,也正像法国美学家吉姆内斯在《当代艺术之争》中所指出的:“鉴定的缺失自然而然地取消了一切‘反鉴定。”[1](p.93)这里,缺失的“鉴定”正是我们曾经持守的艺术底线,而“反鉴定”之“被”取消,则缘于作为“鉴定”根据的既有经验在现实文化语境中已无所适从,因而“反鉴定”便同样失掉了实施的依据。第二,作为当下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的具体实践形态,分层化所揭示出来的突出问题在于:一方面,当文化生产权力由原先的高度集中体制转向当下层面更具广泛性的多元分化体制之后,由于不同文化主体对于各自立场的坚守与张扬,不同文化利益之间开始出现重新分配的要求和趋势,进而导致了文化生产过程的分化,并在这一分化过程中实现着不同文化主体的利益归趋;另一方面,由于更加自由的文化生产权力的形成,分化的文化生产过程也同时带来对于文化意义的不同体认方式和指向,进而形成不同文化主体在文化感受、文化价值满足层面上的分野。
更具体一些来说,当下文化语境中,“分层化”在宏观方面呈现为体制性文化与非体制性文化的分化;而从具体层面上来看,即便体制性文化和非体制性文化的内部,也还同样存在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精英文化话语与大众文化话语的不同利益诉求和实践方式。特别是,由于当下文化的分层化又是趋于变化之中的,随着各种新的生活方式出现,在不同文化层面之间其实又存在着某种交替转换的形态。因此,考察当下文化语境,最主要的是要看到文化利益的分化、文化体认与价值满足的差异以及文化主体诉求形态的改变。第三,大众化或者说“草根化”,普遍构成为当下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发展情势。
一方面,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大众化,直接联系着分层化的文化语境。可以说,在特定意义上,作为当下文化价值指向的基本态势之一,大众化征候正是文化分层的显著结果;另一方面,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大众化,既突出实现着对于以“创造性”“精神深度”以及“崇高体验”为基本模式的文化价值观念与文化生产方式的具体消解,也更加突出地强调了文化消费实践之于文化价值确立的特殊地位,更加执着地寻求文化生产本身对于人的生活满足感受的直接功能实现。
值得指出的是,大众化的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同人在日常实践中的意义获取方式直接联系:日常生活本身不再是“无意义”或“低层次意义”的集合之地,它是人的日常感受的出发点,也是人以日常感受方式直接寻求和生产意义形象的过程;人对意义的获取将不再依赖生活反思能力的功能,而直接联系着人自身在日常实践中的满足感。也因此,普通大众的生活情绪与普遍欲求开始直接进入文化生产与消费的领域,而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功能实现也同样维系在普通大众生活满足的普遍利益之上——“草根”由此产生出前所未有的文化主动性,并且日益深刻地影响着包括艺术活动在内的文化生产方式的指向性变革。“艺术变得寻常,涉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它越来越不像艺术了。”[1](p.166)“不像艺术”的艺术带来了艺术生产的根本性改变。与其他文化生产形态一样,艺术活动不再仅仅服从于精神的美学律令,而是具体介入到人的日常生活领域,传达着人的日常感受及其意义满足。第四,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意义“微化”成为文化生产与消费活动的又一特殊征候。
由于移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技术能力,人们不仅随时随地身处芜杂多变的信息交互活动之中,而且也无力从海量信息中梳理和寻获必要的知识理性与持续积累。互联网信息交互的自由性、开放性和广泛性,在迅速催生文化意识的普遍民主化倾向的同时,也持续瓦解了人们原有的价值体验与生活信仰,在十分广泛的范围里重新确立起一种新的“意义”建构模式:通过共时性的信息交互,不断使“意义”呈现的过程趋于即时化、表象化和碎片化,并在总体上指向了某种“泛民主化”的社会共享。它不仅将意义的生产大面积散布在移动互联网信息的即时获取之中,而且使每一个微细具体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本身就成为“意义”所在。
可以说,意义深度的消失、意义生产的泛化及其即时化,在否定意义深度性的同时,更加凸显和强化了意义建构的“微化”效应。而这种“微化”的意义生产则进一步激化了人的日常感受的具体性和琐碎性,并将那种与移动互联网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微”意义传递活动纳入整个意义建构模式。就像互联网“微评论”的意义已然遮蔽了传统的知识性批评那样,对于直接依赖移动互联网信息生产与传播能力的当下文化而言,“意义”的生产同时是其传递活动与过程本身,因而“意义”无时无处不在[2]。在这一过程中,艺术、艺术家和艺术活动必定无法独善其身。
艾略特曾经对艺术变迁的整体性规律作过具体描述:“当一件新的艺术品被创作出来时,一切早于它的艺术品都同时受到了某种影响。现存的不朽作品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完美的体系。由于新的(真正新的)艺术品加入到它们的行列中,这个完美体系就会发生一些修改。在新作品来临之前,现有的体系是完整的。但当新鲜事物介入之后,体系若还要存在下去,那么整个现有体系必须有所修改。”[3]“现有体系”的完美性,体现并保持了作为一种知识传统的艺术观念、艺术实践以及艺术价值的历史完整性。它在遭遇“新的作品”——包括新的艺术观念、艺术实践和新的艺术理解方式等——的介入之后,其“存在”的现实可能性便理所当然地产生于那种依据“新的作品”所进行的必要调整或“修改”。借用艾略特的这一描述,我们可以将当下文化语境的“四化”征候,视为理解艺术、艺术活动现实“遭遇”的基本出发点。它们在总体呈现当下文化语境具体改变情状的同时,不仅向艺术、艺术家和大众提供了各种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也向艺术学学科提出了“新鲜事物”介入后的新的建构要求。事实上,当下文化语境中的艺术学学科建构,整体地面临着文化语境改变所导致的艺术指向性变迁。从宏观上看,这一指向性变迁主要体现为艺术体系内部既有力量的知识权威性及其价值表达模式不断碎片化或边缘化,而艺术、艺术活动在更加广泛和紧密联系人的日常生活的同时,则更加突出了对于人的日常感受方式、感受特性及其意义满足的直接传达。显然,这种艺术的指向性变迁,内在地呈现出艺术本身的“语境性”,同时也十分具体地表明了,在当下文化的实践性压力面前,“尽管‘高雅文化有其所谓的非物质的和超凡的本质,但它在事实上是与日常活动和关系紧紧缠绕在一起的”[4]。它不仅在“何为艺术”的知识性层面上引导着艺术活动的个体意识方向的调整,而且在实践层面直接改变了艺术的组织模式和结构及其大众的艺术消费能力,包括对艺术批评机制、批评范式的重建规划。应该说,这种艺术存在的现实指向,挑战了已有的艺术传统,要求艺术学学科能够基于统一的理论自觉,重构自身新的阐释方式和阐释形态,并具体确立其文化合法性。具体来讲,随着艺术的指向性变迁,艺术学学科建构面临两方面的现实问题:其一,在多元指向的艺术话语构建活动中,艺术学学科如何真正适应文化分化的现实语境,在理论层面上具体把握艺术活动与生活关系的意义特定性而非价值普适性。其二,在艺术生产与消费的日常实践中,艺术学学科如何能够有力地适应多元存在的艺术现实,在实践层面上有效实现自身的介入性能力,强化艺术批评的生产性功能。应该看到,这两方面现实问题在凸显当下文化语境中艺术存在的实质性改变之际,实际上已经更加明确地引入了对于艺术功能分化、艺术消费间关联性及其相互渗透影响的机制、艺术与生活关系的前瞻性维度、艺术审美体验的多变形式等实践转换问题的具体关注。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是艺术学学科面对艺术价值分化、统一性话语消解,又如何能够通过其自身内部新的“适应”以及适应能力的建构,来重建艺术实践的文化自信,重构艺术理论的阐释能力,进而使整个艺术理论、艺术批评活动能够真正实现对于当下文化语境中艺术生产与消费的引导性功能。
三 在艺术学学科建构的各种现实问题中,最具有挑战性的,是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学最终能否以开放性形态,在当下文化语境中现实地寻获自身的存在路向。换句话说,置身多元文化语境之中,在各种新的艺术现象、新的艺术经验、新的艺术阐释要求面前,艺术学学科是否能够走出既有的知识传统,真正走向一种开放性体系的建构。在《现代艺术的意义》一书中,拉塞尔曾经强调:“艺术从存在以来一直在给我们那种有关我们自己的意识”,“艺术在未来将以何种形式出现是谁也无法预言的,但没有哪个健全的社会会希望自己的存在可以不需要艺术”[5](p.433)。健全社会的发展固然为艺术的存在留下了必要位置,然而,艺术本身却始终并且也正在经历着许多巨大的改变。事实上,对于当下文化语境中的艺术学学科来说,在文化现实中直面并从容把握艺术给予我们的“有关我们自己的意识”,并非自然而然,而是一个需要理论变革勇气并实际地调整内在指向的建构性过程。在文化实践的广泛改变中,随着艺术、艺术活动向着社会公众的日常感受活动日益敞开,一切在理论上围绕艺术、艺术活动所进行的思想努力,无疑更需要我们拥有不同以往的建构智慧。可以认为,循着开放性建构的路向,艺术学学科其实正前行在一条新的美学精神的艰苦探索之路上。而艺术学学科建构的开放性,则“可能将会完成当代艺术之争未能达到的目标:结束精英主义对艺术界的垄断,结束官方体制的指令,在文化上另辟蹊径,开辟广阔的艺术体验,向所有希望并敢于尝试的人开放”[1](p.185)。于是,遵循吉姆内斯的思路,敢于在新的艺术事实面前通过“开辟广阔的艺术体验”,进而“在文化上另辟蹊径”,显然是艺术学学科在当下文化语境中走向开放性建构的总体路向。当然,不断走向开放建构的艺术学学科,在面对新问题、感受新现象、积累新经验的过程中,其最终目标显然不仅只是为那些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艺术、艺术活动确立阐释根据,更重要的是,它应该能够同时指向艺术发展的未来、艺术思考的未来,是在为正在到来或我们可能面对的艺术实践及其存在寻求一种更具文化包容性的理论架构,在理论重塑的过程中充分实现艺术、艺术活动的阐释能力。也因此,对于当下的艺术学学科建构而言,在何种程度上呈现学科的开放性维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开放学科建构的思想路径,便成为艺术学学科的一项迫切课题。进一步来说,这种学科建构的开放性,在根本上,是力图在学科建构的总体路向上,使艺术学学科从两个方面有效实现自己的现实能力:其一,能够充分体会艺术和艺术家在当下文化语境中的生存实际,纳入性地而非排除性地接受艺术生产与消费的当下现实。
也可以说,艺术学学科建构的开放性,其前提是对那些围绕在艺术和非艺术周围的知识传统进行必要的清理,将艺术、艺术活动从既有知识的限定性中释放出来,以便能够重新审视当下艺术存在的实际改变。即如拉塞尔提醒我们的,“假如我们要探讨一下在本世纪最后十年中什么才能被列入艺术的问题,我们就必须记住总体形势的两个基本方面:一个是技术力量的程度,它必然会更加强大。它赋予我们用前所未有的方式控制和改造环境”,“如果艺术不同这些新的可能性协商对话,那么就将不成其为艺术了”[5](p.28-429)。技术存在之所以有力地动摇了我们对于艺术的知识理性,不仅在于它切实改变了艺术家对于自身能力的要求,改变了艺术活动的具体形态,而且在于技术的高度发展和充分使用,通过广泛改变人的生活形态,同时现实地改变了艺术与人的活动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姆内斯断言:“艺术与新技术保持着多样的联系,例如对信息工具(数字化、信息图示)与日俱新的掌握,更广意义上与科技(生物、纳米技术)的联系,无不在打破学科间的传统边界。这些相互渗透有时会使艺术活动自身的特殊化难以实现。”[1](p.166)
在这里,如果说艺术的“特殊化”作为一种知识传统的要求,曾经让我们对艺术的“创造性能力”保持了一份精神信仰的话,那么,在技术发展不断瓦解艺术“特殊化”存在的过程中,对于艺术的“创造性”信仰便已然失去了它的现实前提。“当今的艺术在不同学科的相互关联与打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催生出多样的实践,并介入日常生活”,“让传统主义者失望的是,当今的艺术不再如过去人们理解的,只是崇高、美、完美和理想化的领域”[1](p.168)。“失望”起于知识传统与艺术现实之间的分裂或不相容。当艺术存在的现实及其具体实践已经“不再如过去人们理解的”——尽管它没有绝尘逃离“崇高、美、完美和理想化”,但却已经不能仅仅服从知识传统的阐释效力,那么,一种有“希望”的艺术学学科建构,便在于走出知识传统的既有认识方式和阐释阈限,将多元指向、多样实践的艺术可能性纳入自身视域,在充分“还原”艺术、艺术活动的当下实际之际,为自身铺就进入艺术现实的直接道路。其二,艺术学学科的建构过程能够直接面对当下,形成具体介入当下艺术生产与消费活动的能力,而不是独善其身地维护某种理论上的完整性以及阐释体系的超越性。
美国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的鲍里斯·格洛伊斯教授所讲的一段话,从艺术和艺术家的当下处境这一侧面,很好地启发了我们: 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一个不仅仅是大批量消费艺术,而且大批量的艺术生产的时代。录制一段录像并在互联网上展示成为一种几乎每个人都能操作的简单活动。自我记录已成为大众的做法,甚至是一种大众的迷恋。当代通讯与网络联系方式,如脸谱(Facebook)、我的空间(MySpace)、YouTube、第二人生(Second Life)和推特(Twitter)等网站给了全球人把他们的照片、录像和文本以一种不可从其他后观念主义作品(包括时间为基础的作品)区分开来的方式放置提供了可能。这意味着:当代艺术在今天已成为一种大众文化实践。所以问题来了:一位当代艺术家怎样能够从当代艺术在大众中的成功中幸存?或者说,艺术家怎样在一个人人都成了艺术家的世界中幸存?[6] 很显然,在一定的意义上,当下文化语境中的艺术学学科建构,其实是一件不得不为的工作。当文化生产与消费全面进入一个开放无限、个人民主与文化共享并行的互联网时代,艺术曾经拥有的知识传统及其设定的边界被纷纷打破。当一切人的活动、人的生活表达皆有可能成为艺术的活动和艺术存在的方式,现实本身就已经从观念上瓦解了艺术行为与日常生活满足之间的知识性差别。面对业已充分开放化的艺术生产与消费之境,艺术学学科当然不可能置身这一开放的艺术现实之外,而就存在于其中。因此,对于艺术学学科建构来说,其对于当下艺术生产与消费活动的介入能力,便必定脱开了既有的知识构造形态及其阐释效力,需要实际地转向一个新的维度。事实上,如果说当下文化语境中的艺术、艺术家必须思考“怎样在一个人人都成了艺术家的世界中幸存”,那么,这一艺术本身的“幸存”方式和“幸存”能力,也决定了围绕其上的艺术学学科建构同样正面临着这样的具体问题,即在理论把握与实践过程中,艺术学学科将如何在一个高度开放的生活世界里,为艺术、艺术家提供一种必要的意义指向?尤其是,在艺术功能分化的当下现实中,当艺术正在通过“成为一种大众文化实践”而不断强化自身的日常生活——文化消费能力之时,艺术学学科是否还有可能继续持守那种维系在知识传统之上的阐释效力?倘若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是不是就应该像拉塞尔所指出的:“如果一切东西都是艺术,再如果日常生活能够用艺术形式来检验,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再把‘不够好这个可怕的词语加在个人的努力创造上。因此,我们应该把目标放在唤起每个人的那种优良的意识上,这种意识本身就是一种创造的形式。”[5](p.429-430)“不够好”作为一种价值话语,其阐释前提在于艺术开放的有限性,以及艺术存在与人的日常活动之间的知识性差异。而毫无疑问,强调“每个人的那种优良的意识”,并且肯定这种意识本身所呈现的意义形式,其所要求的则是放弃“分别”艺术与非艺术的知识立场,突出表达了对于艺术存在与日常生活的共享性关系的认可。应该说,这也正是艺术学学科在当下文化语境中的建构目标。阿瑟·丹托在《艺术的终结》中曾言:“一个普遍的艺术定义,一种封闭的理论,应该考虑在事例种类方面有种开放的态度,而且应该把这种开放的态度解释为它的后果之一。”[7]强调艺术学学科在当下文化语境中的开放性建构,就是要求我们能够把这种“开放的态度”具体化为学科理论的现实成果。它所强调的,应该是一种突破有关艺术的知识传统的普遍性指向,完成从知识传统的封闭预设向当下艺术现实转换的学科前景。 (责任编辑:徐智本)
参考文献:
[1]马克·吉姆内斯著,王名男译.当代艺术之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王德胜.“微时代”的美学[J].社会科学辑刊,2014,(06).
[3]T.S.艾略特著,李赋宁译注.传统与个人才能[A].艾略特文学论文集[C].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3.
[4]戴维·英格利斯著,张秋月等译.文化与日常生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130.
[5]约翰·拉塞尔著,陈世怀等译.现代艺术的意义[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6.
[6]美国e-flux journal编,陈佩华等译.什么是当代艺术?[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30.
[7]阿瑟·丹托著,欧阳英译.艺术的终结[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