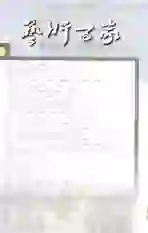20世纪中国艺术批评史的几个“主题范式”
2015-12-25陈旭光��
陈旭光��
摘 要: 20世纪中国艺术批评史,是整个中国艺术批评史的延续和有机组成,也是在延续承传的现代化进程中发生剧变的历史。在世纪百年艺术批评的风云起伏中,必然有一些基本的问题、矛盾、焦点是反复出现甚至贯穿始终的。文章认为:外来/本土、传统/创新:中西文化的对立与融合,主流/支流: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消长纠葛,正统/多元:马克思主义政治批评的沉浮即与其他批评流派或方法的关系,现代/后现代:超越、反叛与融合的混杂等基本问题或基本矛盾,也即一种基本的“主题范式”,构成为贯穿20世纪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之始终的重要线索,应该成为研究20世纪艺术批评的自觉参照。文章秉持一种全局的艺术批评视野和开放动态的历史意识,对20世纪艺术批评史的几个重要的主题范式进行了总结与阐述。
关键词: 艺术学理论;20世纪;艺术史;中国艺术批评史;主题范式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是中国社会、历史大变革,中西文化大碰撞、大融合的时期,是中华民族风云激荡、命运多舛但不断走向复兴和辉煌的世纪。20世纪的中国艺术批评史,与20世纪中国艺术发展史相呼应,是整个中国艺术批评史的延续和有机组成,也是在延续承传的现代化进程中发生新变甚至剧变的历史。
一个世纪的历史不算短,而由于20世纪中国文化、社会的特殊性更增其复杂性。百年中国艺术史和与艺术史密切相关的艺术批评史可谓头绪繁多、现象驳杂、内容宏富,不同的人物、作品、文章、话题、现象、事件在不同的时段互相交杂穿插或平行发展,有时旧话重提,反复出现,有时一个话题在某个艺术领域刚刚平息,又在另一相邻领域重新“开战”。但经过历史的沉淀,通过我们仔细的爬梳、辨析,其实不难发现也有规律可循。也就是说,在世纪百年的艺术批评的风云起伏中,必然有一些基本的问题、矛盾、焦点、核心或视角是反复出现甚至是贯穿始终的。
[JP2]本文认为:外来与本土、传统与创新:中西文化的对立与融合,主流与支流: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消长纠葛,正统与多元:马克思主义政治批评的沉浮即与其他批评流派或方法的关系,现代与后现代:超越、反叛与融合的混杂等基本问题或基本矛盾,也即一种基本的“主题范式”,构成为贯穿20世纪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之始终的重要线索,因而也成为我们研究、剖析20世纪艺术批评发展历史的几个自觉的参照系。
也许,只有在这几个参照之下,我们才能秉持一种全局的视野和整体的胸怀,在研究中贯彻开放动态的历史意识。
一、外来/本土、传统/创新:中西文化或中西艺术的对立与融合[JZ)][HS)]
20世纪的中国艺术是在近代国门打开之后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这里面,有完全“舶来”的艺术门类和体裁,蜂拥而入的众多新颖的艺术流派与创作方法,也有传统艺术在新的时势语境中的继续存在和发展。所以,艺术的传统与创新发展,艺术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如何对待传统与现代,是“西化”还是“民族化”,是“革新”还是“守旧”,是崇“古”还是尚“今”等问题,无疑是20世纪中国艺术发展和批评论争头等重要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还常常因为现实的功利性需求、主流意识形态的介入干扰而平添其复杂性。邓福星在谈到20世纪中国美术批评论争历史的时候试图用“继承与创新”这一对范畴来统摄20世纪的中国美术批评,他指出:“20世纪美术论辩自始至终都围绕着古今之争,围绕着中西之争,而古今与中西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统而言之,就是紧紧围绕着对传统的继承和时代创新的关系这个基本的核心问题。可以这样说,“继承与创新”是20世纪美术论辩的一条轴线,它像数学中的数轴,论辩中其他的许多问题都是上下波动的曲线,一些问题看似同继承与创新没有直接关系,但放在百年的全过程中来看却总是环绕这个核心问题,从未改变基本方向,更未远去。纵观美术论辩的百年历程,可以说,美术在转型中的继承和创新问题是美术论辩的轴线。”[1]当然,“继承与创新”也许还不尽涵盖一切。我们不妨在这一轴线或曰基本主题的统摄下,再大致梳理出这样一组中国艺术发展过程中常用的或我们常常听到的两两相对的二元对立范畴:
继承/创新,传统文化/外来文化,本土文化/外来文化,新文学/旧文学,守旧/创新,传统/现代, 民族化/西化,民族化/现代化,本土性/现代性,民族形式(民间形式)/外来形式,旧/新,古/今……这一组关于传统与现代的基本矛盾,贯穿20世纪社会历史的始终,也贯穿20世纪中国艺术史和艺术批评史的始终。在20世纪,电影、摄影、话剧、油画、西洋音乐、芭蕾舞以及20世纪末的种类繁多的后现代艺术(如装置艺术、行为艺术、摇滚乐等)都是某种“舶来品”,都是从西方传入的。它们的加入使艺术大家族扩大了艺术的族类,引起了传统艺术的变异或革新,也引发了与原来的艺术如何相处,与艺术传统是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它们自身的“民族化”、“本土化”(包括要不要以及如何民族化、本土化)等一系列相关问题。当然,这一组矛盾或二元对立并非是水火不相容、非此即彼、只能取其一的。事实上,这一组矛盾虽常常以对峙的姿态出现,但又往往在相互对立矛盾中相互融合统一。在这一组二元对立中,又往往派生出西化派、本土派、融合派、国粹派、现代派、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等不同但又常有交杂的文化价值取向。就艺术实践而言,应该说没有纯粹的“西化”,也没有纯粹的“民族化”。“西化”是中国人在中国本土进行的模仿、学习、借鉴和再创造,民族化也是在西方艺术大量传入中国本土之后因为有了西方艺术作为“他者”的存在之后进行的民族化。因而这实际上是在20世纪中国艺术发展中已经进行和正在进行的中西互动、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融合的艺术实践,是一种“现代化”。比如国画和油画这是一对“二元对立”,关于国画革新和油画“民族化”的论争几乎贯穿20世纪,但二者之间也在不断地互相影响、交融统一。正如英国著名中国艺术史家苏利文所言所见:“国画和西画之间古老的辩争并没有解决,也许它根本就不能解决。正是中国和西方绘画模式极富成果的接触,才产生了超乎寻常丰富的现代中国艺术。包括吴冠中、王怀庆(1944年生)、罗尔纯(1929年生)和毛栗子(张准立,1950年生)等主流艺术家从西方按其所需地习得技法和主题,却以他们自己的术语予以表达。”[2] 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在20世纪艺术史的这条历史河道中,它本身也在不断的艺术实践中生成自身的传统。传统是流动的,是不断生成、扩大、延续的。相较于20世纪,整个中国古典艺术和传统文化是我们的传统,但在20世纪之后的艺术创作也不断地以前面的艺术为传统。例如对于80年代中后期的新潮美术和后新潮美术的艺术家们来说,难道中国现代主义的先驱刘海粟、林风眠和“决澜社”的庞薰琹、倪贻德等的现代主义探索不是他们的传统吗?对于第五代、第六代导演来说,除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前苏联电影等之外,吴永刚、蔡楚生、马徐维邦、费穆等中国现代导演也都成为了他们难以逾越的传统。而这些20世纪的艺术传统都已经进行了有效的“本土化”或中西融合。另外还要指出的是,中西文化、传统与创新、外来与本土的矛盾对立虽然客观上是存在的,但有些时候则是因为20世纪国势处于弱势状态下的过激反应或特定时期中西冷战思维的表现,是夸大了的甚至是臆想出来的。事实上,在20世纪末,中国艺术家们对待这些问题的心态就平和了很多,他们会把中西文化的碰撞、中西艺术的互相影响、互相学习视为正常的交流、互补和互融。另外,对立与矛盾是表象的,融合则是根本的。在20世纪中国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创新与传统或“现代化”与“民族化”这一组矛盾实际上是互相纠葛彼此依存的,是两种同时发生、共存的文化变构意向。创新更多表现为对西方文化、现代意识、技巧手法的借用甚至横向移植,但条件是必须最终适应中国的土壤;传统或“民族化”表现为古典、传统的“现代转化”,但这种转化常常由于西方文化的诱发,而且也必须适应现实的需求,否则就可能成为已经僵死、徒有外形但没有功能的“遗形物”了。在20世纪中国艺术批评史的三个阶段①,艺术的传统/创新、外来/本土关系均有侧重不同、此消彼长的不同表现。在第一阶段,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文化的倡导者往往对传统持激进批判的态度。甚至被反思者称为五四新文学、新文化与民族文化传统的联系“仿佛被一刀腰斩”,因而形成了一个“民族文化之断裂带”[3]。所以在这一阶段,西化、现代化、革新、革命的呼声明显占了上风。当然,创新与传统的紧张、对峙和尖锐争议一直存在。如美术界,围绕“美术革命”的争议就非常激烈。以国画家“二高一陈”(高剑父、高奇峰、陈师曾)为代表的“岭南画派”也倡议“美术革新”,吸收西方写实技法,融合中西。但陈师曾(陈衡恪)对“文人画”的阐释代表了美术界经过“美术革命”对国画的否定挞伐之后的反省。但他对国画的有些评价过高,表现出对传统的留恋。戏剧界围绕中国戏剧的方向,则出现了不同文化价值取向的西洋派(胡适等《新青年》同仁)、本土派(张厚载、张次溪等)、国剧派(余上沅、赵太侔、熊佛西等)等。其中,国剧派思考和主张则颇有融合中西古今的文化意向。国剧派“构建中国现代戏剧的基本思路是贯通古今,融汇中外,站在当时的理论高度对现存戏剧文化进行宏观扫描,从而确定中国戏剧的理想形态”[4],虽然戏剧实践成果不多,但影响深远。在第二阶段,由于抗战救亡的现实需要,也由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渐渐获得了领导权,在中/西、本土文化/外来文化、传统/现代、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二元对立中,重心明显向民族、本土、大众一方倾斜。比如关于艺术形式的“民族化”还是“西化”之争,在20世纪的开端,在30年代“左联”时期就时有争议,一直是中国20世纪艺术实践和艺术批评的回避不了的重要问题所在。抗战时期“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是“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运动在抗战形势下的发展,其中心依然是探讨文艺如何与本民族特点结合,如何与工农兵大众结合,进而如何发挥抗战宣传的功能的问题。这一关于“民族形式”的文艺论争涉及了几乎所有的艺术门类。成为一个热点的艺术批评焦点话题。在抗战的形势下,这一论争颇有愈趋激烈之势。并最后在延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的介入后,论争渐趋统一,偏重于对民族形式、民间形式的继承的思想占据了上风。通过这一场论争,“左翼”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进一步取得了话语权。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民族化的强调升温。表现在国画领域,强调国画表现现实题材的写实主义画风。一些画家主张改造国画的内容,另一批画家则批评改革主张为民族虚无主义,虽然在笔墨等技法问题上尚有分歧和争议,对国画某些内容、风格的否定也有狭隘化的嫌疑,但在国画表现现实题材的写实主义画风方面还是取得了共识。
在第三阶段,在反思传统文化和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五四”传统得到承接,天平又向外来文化倾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潮美术几乎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把西方现代艺术乃至后现代艺术进行匆匆的演练。美术界“中国画危机”(李小山)、“笔墨等于零”(吴冠中)等口号的提出以及引发的争议就是这种文化取向的表现之一。在20世纪中国画领域,这种创新与守旧之争更是几乎贯穿始终。无论是“美术革命”论争,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民族虚无主义和保守主义之争,每一次都离不开创新与守旧或继承与创新的问题。这自然是因为“中国画承载了太多传统文化的理念和民族审美意识,它因为有太长的历史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表现观念和手法,而且,它培养了相应的中华民族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美术的其他门类和画种无法与之比肩。然而,所有这些既是它的优势也可能成为它的负担。随着中国画每发展一步,都会带来‘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从而便引起论争。”[1]
二 、主流/支流、中心/边缘: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消长纠葛[JZ)][HS)]
20世纪的艺术史中,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纠葛消长几乎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也是我们总结、梳理艺术批评史写作重要的有效线索。不仅仅因为围绕着两大“主义”的论争较量极为明显激烈,也相应形成了各自为自己进行阐发辩护的批评观、艺术观以及相应的批评模式和方法。学术史上,已有不少研究者对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中的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思潮流变、美学风格和创作原则手法等进行了宏观的研究。如邵大箴《写实主义和二十世纪中国画》[5]、王泽龙《1917-1987现实主义文学反思》[6]、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7]、陈思和《七十年外来思潮影响通论》[8]、陈旭光《论二十世纪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9]等。当然,在这里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创作方法,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创作流派,我们更应该理解成为某种创作倾向、走向、创作特点或艺术风格与追求等。以现实主义为例,它作为一种创作流派或思潮是指特定历史阶段有特定内涵的艺术史术语,但作为创作方法则有所泛化,可以说古已有之,甚至中外皆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作为思潮、流派不可能在中国本土上原原本本再现,但作为进入中国本土、本土化之后的创作追求形成某种风格、倾向却是有可能的。归根结底,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作为艺术思潮在西方就是庞杂的——不仅有一个时间维度上的演变,本身在流派团体的构成上也非常庞杂,在进入中国后的本土化过程中无疑愈益复杂化。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还有大量的“中间物”,现实主义还常常与写实主义或写实手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手法等部分重叠或总是捆绑在一起。现代主义不仅流派众多、构成复杂,而且本身与浪漫主义、后现代主义也颇多叠合,较难明确区分。在20世纪中国艺术的语境中,我们依据它们的原始意义,结合被人理解和使用的状况,可以大体归纳出它们主要的特征性差异,例如:
现实主义强调“写实原则”和真实性原则,塑造“典型”形象,往往要求创作主体客观冷静,强调理性意识;强调艺术社会功能的功利主义,追求大众化、通俗化、平民化的表达,主张追求民族形式、民族化……现代主义是偏主观的、激情的,极力追求表现自我意识、心理意识或潜意识心理,技巧上可以变形、扭曲、夸张、抽象,具有某种纯粹的形式主义倾向,偏向“艺术为艺术”或“艺术为自我”,更偏向西化、现代化……现实主义与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不少叠合或纠葛,现代主义则与浪漫主义尤其是消极浪漫主义、后现代主义有部分重叠或纠葛。比如,一般而言,从现代主义艺术的创作主体——艺术家来看,现代主义的艺术家,“是一批具有自身相对的独立性,承继了‘五四现代知识分子个性主义精神传统,在艺术表现上偏重自我和内心世界,尊重形式的独立性价值,表现出较大程度上的‘艺术至上和‘文的自觉精神,并因而与提倡‘大众化、‘民族形式方向、‘革命文学、‘两结合创作方法的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一定疏离和对抗关系的现代自由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选择或倾心于现代主义,自然有着耐人寻味的意识形态蕴含”[9](p.15)。
在“五四”新文化的发轫期,与其他西方文艺思潮相比,从时间上看,现实主义思潮进入中国并不算早。从影响力看,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美术上的“写实”追求、话剧中的现实主义追求,都很难说就占据了绝对的主流地位,现实主义往往几乎同时从西方传入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包括表现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野兽派等)同台竞技。这种状况至少在文学领域存在。[JP2]“五四”时期浪漫主义传入中国还早于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因为浪漫主义中蕴含的那种张扬个性、自我抒情、反抗社会等特征投合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狂飙突进的精神。但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到了抗战时期,尤其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由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地位愈益提升和强化,现实主义越来越得到了张扬并逐渐主流化。从某种角度说,就是道路越走越窄。为抗战服务演变成为工农兵服务、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功利性、阶级性愈加突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阶段,则从前苏联那里移植了某些创作原则)。 例如在美术领域,不仅从西方传入的油画以徐悲鸿等人的呼吁和亲力亲为为代表,以写实风格为主,在中国画领域,写实,也成为无论是改良论者还是革命论者改造中国画的不二法宝,是许多革新者、学人、艺术家为中国美术开出的一个重要处方。正如邵大箴指出的,“研究写实主义在中国画变革中的作用和影响,研究从西方引进写实主义的得和失,对于探讨中国画的现状和它的未来发展,不无意义”,“写实绘画不能概括20世纪中国画的全部面貌,但是写实主义的影响无所不在”[5]。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在20世纪艺术创作中的繁盛乃至占据主流性、主导性的地位,甚至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期成为不可动摇、无法逾越的创作原则、“铁律”,不外乎如下几个原因:
一是“五四”时期一代知识分子往往从艺术为社会、为人生的功利性角度出发来提倡现实主义,又在现实主义的高扬中强化这种功利性。在他们看来,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能保证艺术的社会功利性,只有真实地表现社会、人生、现实,“不语怪力乱神”,才能对受众发生良好的影响,才有利于世事人心、社会人生。
二是灾难深重、民族危机不断的20世纪现实的需要。正如陈思和在谈到中国作家的现实主义选择时说的,“当时中国正面临着一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争,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与社会责任感空前高涨,再加之世界上‘红色三十年代的左派思潮影响,除了小部分作家在有限的范围内试验着现代主义的创作外,极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8](p.146)在艺术领域显然也不例外。三是提倡践行者认为大众的易于接受的需要。1937年的中国抗日战争把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民投入了战争的熔炉。工农兵尤其是农民成为战争的主体。在农民的政治热情高涨的同时,以农民为主要宣传、动员、服务对象的战争文化规范悄悄取代了“五四”时期以来逐渐形成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现代文化规范。因为要强化文艺的宣传功能,要给工农兵“雪中送炭”,更要让工农兵“喜闻乐见”,就必须要走通俗易懂的通俗化道路,要利用“民族形式”和民间形式,这样确立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正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核心精神。四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20世纪下半世纪成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而马克思主义强调艺术的社会属性,艺术对现实、政治的反映和宣传、服务的功能,因而尊崇、提倡甚至独尊现实主义。[JP2]
相应地,现代主义也绝非在真空中生长,它极大地受制约于20世纪中国独特的社会政治形势和文化环境,更是常常受到冷落排斥甚至难免于受批判的“边缘化”命运,在这之中,现代主义的艺术家还常常或真诚或出于现实主义的威力而自我反思、自我批判。 与现实主义的逐渐主流化相反,现代主义则在与现实主义的相持相抗中越来越边缘化。在集中期几乎逐渐销声匿迹。但到70年代末至80年代又经“解冻”潮流而小心翼翼地复苏。并在“85新潮美术”、先锋派文学、实验戏剧等领域达到了一个高潮,高潮之后又因这种复杂原因而解体或被告别,迅即通过“89后新潮”等美术潮流而趋向后现代意味的实验艺术。在20世纪末,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无论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都无需借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而压制对方的较为自由宽松的艺术氛围。或者可以说,在一个商品化、市场经济的时代,意识形态的对抗性早已不再那么激烈,不同创作方法的意识形态含义也在大众性和商品化的氛围中消解了。更何况,秉持解构精神的后现代文化、后现代艺术崛起了,无论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都已经成为被“后”(颠覆、解构、讽刺、滑稽模仿等)的对象,早就自顾不暇了。
三、正统/多元:马克思主义与政治批评的沉浮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泽厚指出:“没有哪一种哲学或理论,能在现代世界史上留下如此深重的影响有如马克思主义;它在俄国和中国占据统治地位已数十年,从根本上影响、决定和支配了十几亿人和好几代人的命运,并从而影响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10]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中国的传播,对艺术创作、艺术发展的影响,与其他批评流派或方法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常常通过艺术批评或政治批评——是巨大的、绕不过去的。
[JP2]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表现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有学者曾将其主要的思想观点概括为,文艺是生活本质的形象化反映,生活实际上是耸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的表象,“文艺是政治本质的典型化反映,而反映者及创作主体实质上乃是处在一定的经济地位、从属于一定的阶级的创作主体”,“文艺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创作主体对政治本质的典型化反映”[11],等等。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对20世纪中国艺术发展史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对现实主义的独尊和强力推助。因为马克思主义强调对社会的改造,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乃至政治服务功能,因而必然选择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作为其推崇的创作方法。如果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知识分子对先后译介进中国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如表现主义、象征主义、野兽派、达达主义等)还是并未戴上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只是出于现实需要和艺术家个人需要自由选择的话,那么,30年代后,现实主义思潮则进一步马克思主义化了,因为在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已经取得了革命的成功,所以,前苏联国家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逐渐在中国通过30年代的“左联”文艺、40年代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文联、作协、美术家、电影家、音乐家协会等机构以文件、运动等方式进一步强化而越来越主流化,并定于一尊,奠定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二是对现代主义的制约和排斥。
[JP2]马克思主义在文艺基本观念上根本上是与现代主义文艺观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对现代主义始终持批判否定的态度。因而在20世纪的艺术史上,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代主义的艺术观念传播和艺术创作是起到遏制作用的。有学者论述马克思主义对现代主义等艺术思潮、艺术风格或创作手法的这种“遏制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西方反理性哲学的批判,削弱了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哲学基础”; “二是帮助一些作家摆脱精神上的危机,绕开走向现代主义之路”——这位学者显然是认同马克思主义对现代主义的先验性定位的,他还以鲁迅告别“苦闷的象征”时代,转而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例来说明;三是“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还促使中国作家在引进和借鉴外国文学上向俄苏文学倾斜”[12]。
三是批评方法的政治批评的倾向。[JP2]无疑,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主流化和意识形态化形成了一种政治批评的范式。其过于浓烈的意识形态性,一定程度上阻断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艺术生态,其对文艺反映现实的过于强调则一定程度上阻断了艺术创作方法上的自由和多元。尤其是20世纪中国艺术进入转折期后,“战前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那儿演化出来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倾向,现在适应了更大的时代需要,尤其到了40年代的后半期,几乎成为政治斗争和政治宣传的工具,现实主义精神——真正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真实地表现生活的本来面貌而不是为适应某种理论上的宣传需要去歪曲生活等原则都处于萎缩状态。现实主义正面临着政治实用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修正。”[8](p.151)
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苏联文艺中的某些庸俗社会学观点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中的机械影响几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形成了诸如“无冲突论”“唯题材论”“主题先行论”“三突出”等严重束缚艺术创作的教条。从艺术批评的角度说,则是一些艺术批评评价的不二标准了。 也正因如此,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对现实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思以及反思之后对其他批评流派和方法的引进和多元化、开放化,成为“新时期”艺术批评理论思考和批评实践的重要主题。
四、现代/后现代:超越、反叛与融合的混杂
20世纪80年代,当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还在纠缠争辩不休的时候,到90年代,一个“后现代”的幽灵开始在中国艺术界席卷而来。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批评家们熟用的西方学者名是叔本华、尼采、康德、弗洛伊德、萨特、克莱夫·贝尔等,那么,20世纪90年代则逐渐被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哈贝马斯、杰姆逊等所取代。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显然无法非常清晰地划出区分界限,后现代文化或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极为驳杂含混的术语,兼有文化、社会、时代、艺术、现象、精神等多种角度的含义和指涉。后现代的“后”的意思既可能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叛和反驳,也可能是既有背离、反叛也有对现代主义在时间维度和性质层面等的延续,某些现代主义特质的极端化发展。大体而言,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主义具有文化反叛性、策略手法的解构性、传播的大众文化性、日常生活化、世俗化等特性。例如在美术领域,新潮美术与后新潮美术的关系也类似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刘骁纯曾归纳过美术中现代艺术与后现代艺术的主要区别:为艺术—反艺术;架上艺术—非架上艺术,纯艺术—对纯艺术的彻底怀疑和解构;本质化的艺术—对艺术本质的彻底怀疑和解构;寻找艺术基本元素、建构元话语的艺术—对艺术基本元素和元话语的彻底怀疑和解构,以结构主义为语言哲学基础—以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为语言哲学基础等几个方面[13]。此归纳可为参考。然而,后新潮美术由于出现了大量如装置艺术、行为艺术、观念艺术、“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等新的艺术样式或新的艺术风格形态,现代主义的批评观念有时显得无法阐释,故而批评方法也相应地要进行某些变化才能适用。这个问题随着后现代艺术的蓬勃发展而显得愈益严峻。1994年的《江苏画刊》曾发起关于装置艺术作品意义的讨论,就如何阐释此类新艺术,是否能够或应该追寻此类作品的“明确的意义”等问题展开了探讨。编者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继前些年艺坛风行具有明确文化指向的‘玩世现实主义和‘波普风之后,近年随着非架上艺术,特别是相对数量的装置艺术出现后,许多人感到,如果理解、评价艺术品只是从文化针对性或艺术本身着眼的话,很多作品的意义不再是清晰的,亦称为‘意义的模糊。是作品本身模糊不清,还是我们评价的尺度没有跟上变化了的艺术状况?这个问题已开始困扰着艺术家与艺术批评。如果说批评与理论更多的是对艺术创作的一种追述与询问,那么这种现象意味着一种新的挑战。”随后,围绕此期杂志重点推介的易英的《力求明确的意义》[14]而展开了一场规模不小的关于实验艺术“意义”的论争, 这一论争的焦点实际上就是现代主义艺术观念与后现代主义艺术观念的争论。
五、结语
总而言之:外来/本土、传统/创新:中西文化或中西艺术的对立与融合,主流/支流: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消长纠葛,中心/多元:马克思主义与政治批评的沉浮即与其他批评流派或方法的关系,现代/后现代:超越、反叛与融合的混杂,这几个基本的“主题范式”,构成为贯穿20世纪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之始终的清晰的线索,是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20世纪艺术批评史之升沉流变的重要视角和参照系。
(责任编辑:徐智本)
① [ZK(#]笔者在《中国艺术批评史20世纪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中,把20世纪艺术批评史划分为前后相续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转型与建设期”,大约是19世纪20世纪之交到20世纪30年代末。第二个阶段是“转折与集中期”,大约是从30年代末抗战爆发到70年代中后期“文革”结束的这一漫长而特殊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开放与多元期”,大约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又一个新的世纪之交。[ZK)] 参考文献:
[1][ZK(#]邓福星.中国美术论辩绪论(上)[M].南昌:百花洲出版社,2007.8-9.
[2][英]苏利文.艺术中国[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249.
[3]郑义.跨越文化的断裂带[N].文艺报,1985-07-13.
[4]郭富民.插图本中国话剧史[M].济南:济南出版社,2003.90.
[5]邵大箴.写实主义和二十世纪中国画[J].美术史论,1993,(03).
[6]王泽龙.中国新文学思潮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
[7]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8]陈思和.七十年外来思潮影响通论[A].鸡鸣风雨[C].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9]陈旭光.中西诗学的会通——论二十世纪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0]李泽厚.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A].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8.150.
[11]昌切.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A].思之思——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论[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76.
[12]唐正序、陈厚诚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12.
[13]刘骁纯.何谓后现代?[A].贾方舟.20世纪末中国美术批批文萃批评的时代(卷一)[C].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7.239.
[14]易英.力求明确的意义[J].江苏画刊,199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