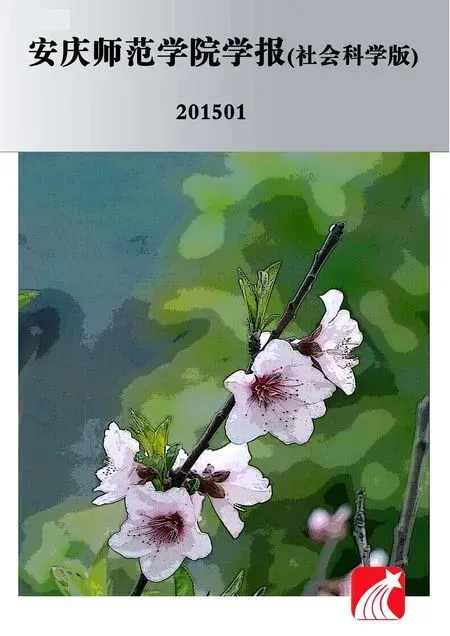严复《英文汉诂》与马建忠《马氏文通》比较论
2015-12-17欧梦越
欧 梦 越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 英国 伦敦)
严复《英文汉诂》与马建忠《马氏文通》比较论
欧 梦 越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福州350007;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英国伦敦)
摘要:严复的《英文汉诂》和马建忠的《马氏文通》皆为开创性的语法学著作。虽然手段、目的不同,但理念相近,皆是以西方语法学理论改造和建构汉语语法体系,以提高学习效率,进而中西学会通。他们皆受到西方普遍唯理语法理论的影响,认为各种语言的语法都有相通之处即普遍性,同时注重特殊性,开创了中国中西语言对比研究的先河。《马氏文通》由开始遭受批评、否定,越来越得到赞扬、肯定;《英文汉诂》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其蕴含的学术价值极不相称。
关键词:《英文汉诂》;《马氏文通》;语言对比研究
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5.01.014
严复和马建忠都是中国近代传播西学的先行者,严复的《英文汉诂》和马建忠的《马氏文通》皆为开创性的语法学著作。近百年来,《马氏文通》研究已成“显学”,而《英文汉诂》却没能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迄今为止,除个别论著偶然涉及外,仍无学者将两者进行系统的比较评价。因此,本文尝试从时代背景入手,先大体上比较两书编撰的动机和目的以及内容方面异同,接着重点分析他们借鉴西方语法理论来建构汉语语法体系并进行中西语言对比研究的异同,再从影响角度比较其价值,以期引起学界更多关注。
一
清末,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岌岌可危,特别是“甲午海战”失败,举国震惊。面对前所未有之变局,社会精英阶层深切认识到开启民智、学习西方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兴学重教,尤其是外语教育日益成为时代的潮流。马建忠和严复皆被“洋务派”派往欧洲学习,精通西学,极力呼吁国人学西语、通西学。严复《英文汉诂·卮言》说:“中国自甲午一创于东邻,庚子再困于八国,海内憬然,始知旧学之必不足恃,而人人以开瀹民智为不可以已。”[1]1正是在此背景下,《马氏文通》和《英文汉诂》应时而出,光绪二十四年(1898),商务印书馆出版《马氏文通》前六卷,1900年初出齐;《英文汉诂》于光绪三十年(1904)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发行。
中国古代没有西方观念的语法学著作,有之,自《马氏文通》始。《马氏文通·序》感叹传统教学弊在“就书衍说”,“循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2]2。又曰:“余特怪伊古以来,皆以文学有不可授受者在,并其可授受者而不一讲焉,爰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以成此编;盖将探夫自有文字以来至今未宣之秘奥,启其缄縢,导后人以先路。”[2]3他认为西方重视语法,语言文字有章可循,简单易学,遂决意编一部汉语语法著作,以便于国人学习,故前后花费十余年时间,仿照拉丁语法,研究古代汉语结构规律,编成《马氏文通》,开拓创新之功不可没。《马氏文通·例言》明确说:“此书系仿葛郎玛而作,后先次序,皆有定程。观是书者,稍一凌躐,必至无从领悟。如能自始至终,循序渐进,将逐条详加体味,不惟执笔学中国古文词即有左宜右有之妙,其于学泰西古今之一切文字,以视自来学西文者,盖事半功倍矣。”[2]1《马氏文通·后序》曰:“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而后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学文焉,其成就之速必无逊于西人。然后及其年力富强之时,以学道而明理焉,微特中国之书籍其理道可知,将由是而求西文所载之道,所明之理,亦不难精求而会通焉……则为此书者,正可谓识当时之务。”[2]2他期望学生能够借助此书高效学习汉语,学习西语也事半功倍,从而快速掌握中西文化知识,进而“学道而明理”,以强国富民。
严复也提倡西学,强调求西学的重要途径就是学习西文。《英文汉诂·卮言》曰:“使西学而不可不治,西史而不可不读,则术之最简而径者,固莫若先通其语言文字,而为之始基。”[1]7《英文汉诂·叙》感叹:“吾国之习英文者益众,然学者多苦其法之难通。”[1]卷首鉴于当时现状,他花了数月时间,以英国马孙、摩栗思等人著作为基础,编写出《英文汉诂》。书中《析辞》云:“中国文字最古,然先民从未为之律令,如西国之文规者,其正书Orthography、字论Etymology,固间见于小学诸书,顾独详于形义诂训。至于指部析辞之事,则寓于蒙学之属对,与前者经义之文,以无专书。故师弟皆知其当然,而能言其所以然者寡。今欲示学者以中西之相合,试取诗、古文中一二语为式,而驭以析辞之法,庶几可互相发明也。”[1]191强调西方语法知识对有效理解汉语的重要性,中西语法比较,可相互发明。《英文汉诂·叙》说自己编撰该书的意图,是“乃有以答海内学者之愤悱”,“有以解学者之惑而餍其意”[1]卷首。尽管《英文汉诂》只是一部给初学者介绍英语语法的书,严复自己却非常看重,光绪三十年(1904),《与熊季廉书》说:“继此学英文人,第令通晓中国文理者,即可触类旁通,不致为俗师所苦矣。”[3]247-248同年,《与熊季廉书》又说:“此书出后,凡读英文二三年,于国文有根柢者,当可无师自通。自谓于学界不无功德。”[3]251他希望阅读此书后,凡是于英文、国文有一定基础者,均能达到举一反三、无师自通的境界。
马建忠和严复有交往,志趣相投,观念开放,思想深刻。编写《马氏文通》和《英文汉诂》,一为有效学习汉语,一为有效学习英语,虽然手段、目的不同,但理念是相近的,皆是总结语言规律,注重以西方语法学理论改造和建构汉语语法体系,以提高学习效率,进而中西学会通,“识当时之务”,救亡图存。1933年,黎锦熙《比较文法》附注说《马氏文通》“算是比严氏《英文汉话》出版较早的一部《拉丁文法汉证》”[4]附注,即是看到两书性质上的一致性。
再看两书的具体内容,《马氏文通》共十章,重点是前九章,论“字类”即“词类”。马建忠借鉴西方词类划分方法的同时,注重继承中国传统小学对字词的研究成果,分析中西语言异同,将词类分为名词、代词、静词、动词、状词、介词、连词和助词叹词八类。《英文汉诂》对英语词类的划分与摩栗思Morris观点相同,分为八大类,即noun名物(名词)、adjective区别(形容词)、pronoun称代(代词)、verb云谓(动词)、adverb疏状(副词)、preposition介系(介词)、conjunction挈合(连词)、interjection嗟叹(感叹词),两者大同而小异。马建忠和严复从各自角度建构了比较完整的汉语词类系统。
关于词组,《马氏文通》用“读”指主谓短语,《英文汉诂》将英语phrase译作“仂语”,后来,许地山《语体文法大纲》、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吕叔湘《汉语学习》初版时,皆用 “仂语”概念,20世纪50年代,这一术语仍很流行,可见《英文汉诂》的影响力。后因“仂语”概念过于生僻,逐渐被淘汰,而代之以章士钊《中等国文典》(1907)首先使用的“词组”概念和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中使用的“短语”概念。
《马氏文通》和《英文汉诂》建立了汉语“复句”理论,汉语开始真正有了复句观念。《马氏文通》首次将复句问题引入汉语语法理论中,但没有使用“复句”概念,今人仅从句与句相联属断定所指为复句。《英文汉诂》比附英语语法来解释汉语语法,对句子进行分类,分为单简句(simple sentence)和繁句,繁句又分为合沓句(compound sentence)和包孕句(complex sentence),繁句实际上即是复句,严复仍没有明确使用“复句”概念。《马氏文通》仿效西方复句理论,但没有照搬,没有简单地移中就西,而是将复句理论与传统句读、虚词理论结合起来;《英文汉诂》中,句子分类基本上比附西方语法,模仿痕迹明显。现代汉语单句、复句的区分,正是在接受了西方语法的《马氏文通》和《英文汉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虽然比附西方语法构建汉语语法体系存在一些不足,但《马氏文通》和《英文汉诂》注重中西会通,促进了中西文化的直接对话和交流,应充分肯定其开创性价值。邵敬敏《汉语语法学史稿》将《马氏文通》归为模仿、修正派,将《英文汉诂》归入验证派,与《马氏文通》描述汉语语法不同,《英文汉诂》阐释英语语法,严复也表达了对汉语语法的独特认识。[5]
二
语言的普遍性特征为马建忠和严复借鉴西方语法理论来建构汉语语法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可能性,他们皆受到西方普遍唯理语法理论的影响,认为各种语言的语法都有相通之处即普遍性。《马氏文通·后序》曰:“而亘古今,塞宇宙,其种之或黄、或白、或紫、或黑之钧是人也,天皆赋之以此心之所以能意,此意之所以能达之理。则常探讨画革旁行诸国语言之源流,若希腊、若拉丁之文词而属比之,见其字别种,而句司字,所以声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吾经籍、子、史诸书,其大纲盖无不同。于是因所同以同夫所不同者,是则此编之所以成也。”[2]1《英文汉诂·叙》说:“故文法有二:有大同者焉,为一切言语文字之所公;有专国者焉,为一种之民所独用。而是二者,皆察于成迹,举其所会通以为之谱。”[1]卷首这是他们对中西语言共性与个性即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认识。
马建忠相信中西语法有相同规律,也注意到它们的差异。《马氏文通》将词划分为九类,在英语八大词类之外增加“助字”一类,强调是汉语的特点,这种划分大体上符合古代汉语的实际情况,后来的诸家汉语语法著作对词的分类或增或减,大都采纳马氏分类。马建忠将句法和词法结合起来,与专讲形态的西方语法有较大差异,而不是机械模仿。黎锦熙《比较文法·序》说:“偶忆王船山《俟解》中有句话‘不迷其所同,而亦不失其所以异’,真可用为比较文法研究的铁则。一般踢开拉丁文法而欲另建中华文法者,是‘迷其所同’也;一手把住拉丁文法而遂挪作中华文法者,是又‘失其所以异’也——《马氏文通》是已。”[4]卷首他认为王夫之的话可作为比较文法研究的原则,强调所谓“比较”,既要同中求异,又要异中求同,对《马氏文通》的批评自有其道理。但开创时离不开模仿,难免不足,其开创之功是必须充分肯定的。
严复强调中西语言同源,《政治讲义》说:“支那之语,求诸古音,其与西语同者,正复不少。如西云mola mill,吾则云磨;西云ear areare,吾则云犁……诸如此类,触处而遇。果使语言可凭,安见东黄西白不出同源?”[6]重视语言的普遍性,中西语言确有许多共同点。基于对语言普遍性的认识,严复直接借鉴英语语法体系来构建汉语语法体系,认为语法是由正书Orthography(按:今通译“正字法”)、字论Etymology(按:今通译“词源学”)、成文Syntax(按:今通译“句法”)三部分构成,“字论”部分,他用英语的八大词类来划分汉语词类。
《马氏文通》基本上模仿西方语法理论建构汉语语法体系,不过仍将关于句法的讨论置于传统“句读”概念下。严复在成文Syntax即“句法”部分,首次为汉语句子勾勒出一个明确的分类系统,指出句子的基本成分是句主(主语)和谓语合而成句,前者以实,后者以虚。句子又分单简句、合沓句、包孕句,“句法”的论述是《英文汉诂》对汉语语法体系建构的突出贡献,看到的正是中西语言的相同方面。从总体上看,严复强调两种语言之间,“同”多于“异”。甚至《马氏文通》认为的“异”,他也倾向于“同”,《马氏文通》在英语八大词类之外特别增加“助字”类,《英文汉诂》中《字论》却认为:“泰西文字,八部而止,惟中国若多一部,若语助之焉哉乎也是已。虽然,谛而审之,即以为未尝多亦可,盖语助之字,常函云谓、疏状之义,此如也字,实无异于英之is,法之est。”[1]12这是对英语词类的直接套用,完全按照英语的八大词类,将汉语特有的助词分别归入“verb”和“adverb”类,以为“助词”单独分类可有可无,此观点并不可取。“称代部”中,他甚至得出普遍结论:“中西古语多同,西人如艾约瑟等所言多与鄙人合者,可知欧、亚之民,古为同种,非傅会也。”[1]35过分强调“同”,有牵强附会之嫌。
严复强调在比较中学习语言,《英文汉诂·卮言》说:“夫将兴之国,诚必取其国语文字而厘正修明之,于此之时,其于外国之语言,且有相资之益焉。”[1]5《马氏文通要例启蒙·序》曰:“昔英学者穆勒有云:欲通本国之文辞而达其奥窔,非兼通数异国之文字言语不能办也。不佞尝以其言为无以易……欧人为学,未有孤习本国文字者也。夫道生于对待,得所比较,错综参互,而后原则公例见焉。”[7]卷首《英文汉诂》的许多章节里随处可见两种语言比较,比较时,严复既识同,也辨异。他力图通过比较来揭示中西语言的不同规律。他对《英文汉诂》有更高的期许,与弟子熊季廉信中说:“窃意此书出后,不独学英文者门径厘然;即中国之文字语言,亦当得其迥照之益也。”[3]244也就是说,该书不仅是学习英文的捷径,亦可深化对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理解和对传统文化的把握,体现了严复中西会通的先进思想。
中西语言自有其共同性一面,但又各有其特殊性,难免冲突,马建忠和严复力图用比较的方法调和这种矛盾,但两种语言的许多差异是无法调和的,所以他们难免“削足适履”,这是中国语法学草创时期不得不“模仿”而产生的先天不足。马建忠和严复的中西语言对比研究有明显不足,但他们开创了中国中西语言对比研究的先河,其先驱者地位应给予充分肯定。
三
《马氏文通》出版后的十多年里,因深奥难懂,受到读者冷落。严复《马氏文通要例启蒙·序》说:“特其文繁而征引旧籍多,今贤所束阁者,故不独喻之者寡,即寓目者亦已少矣。”[7]卷首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学界多批评它“简单模仿”“生搬硬套”。不过,《马氏文通》的影响是越来越大的,一直再版,到1930年,已印第21版,至今已有《马氏文通》的不同版本30多种。《马氏文通》也得到不少学者认同肯定,自出版以来,不少语法书跟着出版,有数十种之多,大都是对其进行修正和补充。1920年,梁启超始将《马氏文通》与《英文汉诂》相提并论,热情称赞:“清人以小学为治经之途径,嗜之甚笃,附庸遂蔚为大国……而马建忠学之以著《文通》,严复学之以著《英文汉诂》,为‘文典学’之椎轮焉。”[8]并尊二者为“文典学”的创始之作。赵尔巽等《清史稿·马建忠传》称赞《马氏文通》“为古今特创之作”[9]。黎锦熙《比较文法》称赞《马氏文通》“是第一部沟通中西之大规模的创作”[4]卷首。近现代,西方文化成为强势文化,中国传统学术皆逐渐纳入西方学术体系中,国人有一心理适应过程,从拒斥到逐渐接受,《马氏文通》由开始的遭受批评、否定,越来越得到赞扬、肯定。《马氏文通》在中国语法学史上影响深远,备受学界重视,被后人推崇为中国第一部完整、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是中国语法学的奠基之作,至今仍没有任何一部同类著作的影响超过它。百年来的中国语法学史,几乎就是对《马氏文通》的评论史,研究《马氏文通》成为一门“显学”。
《英文汉诂》出版后,引起多方关注,教育界、学术界皆不吝赞美。到20世纪30年代,已再版20余次,作为学部审定的“国家级”教材,其地位和价值不言而喻。[10]相比《马氏文通》,《英文汉诂》的受众更多一些。缪子才《〈马氏文通〉问答》比较说:“《英文汉诂》《马氏文通》并行中国三十年矣,读《汉诂》者鼓舞欢欣,读《文通》者倦而欲睡。此何故也?以饴饧和乳汁,爱其滋养者多,用稻黍烘面包,癖其味者少也。”[11]第11卷20世纪前三十年间,《英文汉诂》影响较大,受到读者欢迎。研究方面,《英文汉诂》后来则沉寂无闻,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百余年来,它只是在外语教育领域作为一本教科书被提及,与其蕴含的学术价值以及严复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相比,显然极不相称。
《马氏文通》和《英文汉诂》坚持使用“雅驯”的文言而不使用白话文,旨在强化对传统文化的崇敬和承继,不使母语“破碎”。两书的编撰初衷都是为教学而用,但由于取材仅限于文言文,过于深奥难解,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
参考文献:
[1]严复.英文汉诂[M].上海:商务印书馆,1904.
[2]吕叔湘,王海棻.马氏文通读本[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3]孙应祥,皮后锋.严复集补编[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4]黎锦熙.比较文法[M].北京:著者书店,1933.
[5]文贵良.以严复为中心:汉语的实用理性与“国语”的现代性发生[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7).
[6]王栻.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1246.
[7]陶奎.马氏文通要例启蒙[M].天津:华新印刷局,1916.
[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51.
[9]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12482.
[10]欧梦越.论严复英文汉诂的写作出版过程及社会反响[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4(3).
[11]缪子才.马氏文通问答[J].厦大周刊,1931(1).
责任编校:汪长林
网络出版时间:2015-03-02 2:51:25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50302.0952.014.html
中图分类号:H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15)01-0057-04
作者简介:欧梦越,女,安徽蚌埠人,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学术访问学生。
基金项目:福建师范大学胡国赞研究生出国(境)访学资助项目(Hu Guozan Study-Abroad Grant for Graduates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收稿日期:2014-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