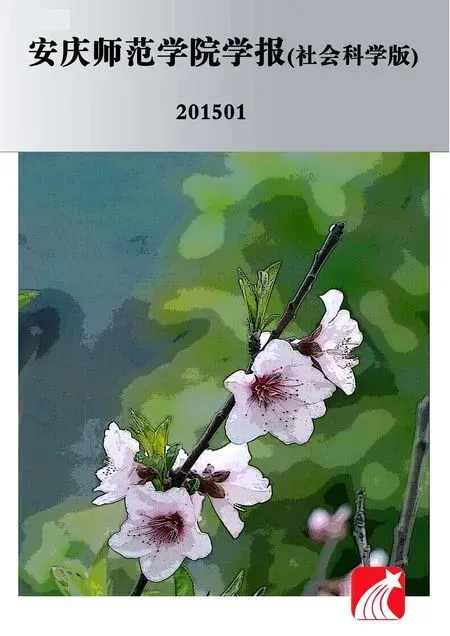海外回归医籍《风科集验名方》疑难字词考辨
2015-12-17刘敬林
刘 敬 林
(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海外回归医籍《风科集验名方》疑难字词考辨
刘 敬 林
(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安徽安庆246133)
摘要:《风科集验名方》是近年从日本回归的我国元代刻刊的一部精品中医方书。由于学者们初涉研究的缘故,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此书校点本,对“铃、珪、校、戾、敬、宗、扬、检、萆、较”等字词的考释存在一些问题,很有商榷之必要。
关键词:中医古籍;《风科集验名方》;疑难字词
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5.01.011
由金末太医赵大中原编,元人赵素补缺(约1236年)及左斗元校补(1298年)而成的《风科集验名方》,是一部精品中医方书。该书自1306年刻刊之后,未有翻刻本。由于历史的原因,该书在国内失传而独存于日本。近年国家中医研究院将其复制回国,在将其校点后于2010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校点所据底本元刊本刻板精良,文字辨认无甚大碍[1]675,而校点者郑金生、真柳诚(日本)二先生,又都是中日两国中医古籍文献的行家里手,故校点堪称精当。然由于学者们初涉研究的缘故,其中对有些疑难字语的考释,似尚偶存些许可议之处。今不揣浅陋,斗胆将鄙见公之于众,以向校点者及同好求教。
本文每条讨论,先引《风科集验名方》原文及校注,然后提行以“按”字标出笔者考订辨析之意。为方便读者覆按引文,下文凡引《风科集验名方》者皆用页码如“P.××”标明出处。
1.若夫述《内经》之旨要,究病证之根源,列圣贤之治法,具古今之方论,广记而备言,有条而不紊,所谓药疾之司南,医学之铃键欤!(P.3)
按,“铃键”不词,当是“钤键”。古人刻写以“今”为构件之字,俗体多作“令”形。对此,《敦煌俗字典》收有多个字例[2]200,此容不赘。而《疑难字考释与研究》亦有“‘今’旁俗书多与‘令’旁相乱”之论[3]492。校注者或因拘于底本“钤”构件“今”为“令”形,则未审构词理据而误录作“铃键”。“钤”指锁;“键”指钥匙。后“钤键”连语可喻指事物的核心或关键。晋·郭璞《〈尔雅〉序》:“夫《尔雅》者,……诚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钤键。”邢昺疏:“《说文》云:‘钤,锁也。’《方言》云:‘户钥,自关之东,陈楚之间谓之键。’《小尔雅》云:‘键谓之钥。’言此书为六艺之锁钥,必开通之,然后得其微旨也。”《隋书·天文志中》:“又北二小星曰钩钤,房之钤键,天之管钥。”此指锁钥。清·钱谦益《〈琅环类纂〉序》:“居今之世……导九流之津涉,开六艺之钤键。”于省吾《双剑誃诸子新证·淮南子新证序》:“《淮南》一书,撷传记之精英,为百家之钤键。”此二例为比喻义“核心”、“关键”。皆可为证。“医学之钤键”,翻成白话就是:(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医学的关键。
2. 予不敏,载念自幼多疾,视人之疾,犹己之疾。今既不得如王焘、陆宣公,达以行其志,独不能推二公当时辑《秘要》、裒《集验方》之心以淑诸人乎?校注:焘:原作“珪”。王珪乃元代《泰定养生主论》的作者。据此句后称《秘要》,则当为唐代《外台秘要》作者王焘,故改。(P.11)
按,上引为《风科集验名方》补校者左斗元“自叙”中的一段文字。校注“据此句后称《秘要》”而校原文“珪”为“焘”,从《秘要》作者确为“王焘”而非“王珪”言,应该说是对的。但校注者将校改理由说成“王珪乃元代《泰定养生主论》的作者”,则误。据褚玄仁《王珪先生年表》载,《泰定养生主论》作者王珪生于南宋理宗景定五年(1264年),南宋祥兴元年(1278年)十五岁时因家乡流行疾疫而初涉医学,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二十三岁时,以“材异”辟为辰州(今湖南省沅陵地区)同知。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弃官归里,隐居养亲,屏绝世累,一心事医;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年)六十一岁时,开始撰写《泰定养生主论》,泰定四年(1327年)六十四岁时成书并作自叙,元惠宗至元四年(1338年)七十五岁时,《泰定养生主论》刊行[4]215-222。而上引叙文末作者所示“自叙”所写时间为“大德戊戌端阳日(后学庐陵左斗元辰叟自叙)”。“大德”为元成宗年号,“戊戌”年即大德二年(1298年)。其时,元人王珪尚在辰州同知任所,并未事医而有成就,早于元人王珪的左斗元的笔下,不可能把唐代著名医家王焘误为尚未专事医的同朝晚辈“王珪”。
再从文意看,底本“王珪”决非元人“王珪”。“今既不得如王珪、陆宣公,达以行其志,独不能推二公当时辑《秘要》、裒《集验方》之心以淑诸人乎”,是作为论据以证文章论点即开篇语:“先正有言:达则愿为良相,不达愿为良医”的。其中,居于“王珪”之后的陆宣公指唐代政治家、文学家、医家陆贽(754年—805年)。陆贽祖籍苏州嘉兴(今属浙江),大历八年(773年)进士,贞元八年(792年)出任宰相,贞元十一年春贬忠州别驾。在别驾任上,因见当地气候恶劣,疾疫流行,遂编录《陆氏集验方》50卷,供人们治病使用。永贞元年(805年)卒于任所,谥号“宣”。而元人王珪一生官仅为辰州同知——辰州知州的佐官,其所任职在封建社会说不上“达”,根本无法同担任过宰相的陆贽平列同作论据以证论点,更不要说“位次”能排在陆贽之前了。
既然叙文中的“王珪”不可能是元人“王珪”,那应是哪个“王珪”呢?我们认为,此乃王焘的祖父“王珪”。《外台秘要》作者王焘的祖父王珪,乃初唐著名政治家,《新唐书·王珪传》说,王珪为太宗“诏谏官随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入阁”,与“(房)玄龄、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征同辅政”。此可谓“达则愿为良相”者。而王焘在有唐史书中没有单独立“传”,而是作为“附传”尾附于其祖父王珪之《王珪传》,且仅整六十个字。这六十字,除简介王焘“为徐州司马”、“历给事中,邺郡太守,治闻于时”的从政事外,余多简述其从医及《外台秘要》成书事。若“王珪”确是左斗元笔下或记忆之误,那最大的可能也只能是因爷孙同传于一文所致。
左斗元自叙本书编纂过程曰:“取《素问》、《灵枢》、《难经》、《中藏》、巢《源》、《千金》、《外台》、《圣惠》、《医说》等书,及《南北经验名方》,并《说文》字书”,“又取经子史集、古今圣贤名医治风药品、治理制度、动风食忌”,“研精披究”,“逐一参订”,“庶成全书”。由此可知左氏不仅确实精通医学文献,长于医书校雠与编纂,亦精于“经史子集”。博学如此者,岂能对王珪、王焘祖孙史事不清楚而不知《秘要》的作者为谁?
据此,我们推测,“焘”冠“珪”戴,是作者左斗元为说明自己增补此书原因时的心知肚明的有意之为。文章开篇提出叙文观点:“先正有言:达则愿为良相,不达愿为良医。”接着简述官医提举刘君卿请他校雠《风科》,进而述自己愿意校雠《风科》的动因说:“予不敏,载念自幼多疾,视人之疾,犹己之疾。今既不得如王珪、陆宣公,达以行其志,独不能推二公当时辑《秘要》、裒《集验方》之心以淑诸人乎?遂不复辞让,乃研精披究于是。”这里,叙文以王珪、陆宣公二人为据,说他们“达”时作良相,“不达”为良医,而自己原本未“达”,故只能做“良医”而从刘君卿之议。如若左氏据《秘要》而作“王焘”,那就无法使文章论点与论据统一,也就无以表明自己“研精披究于是”的动机,而整篇叙文“自身”也就无法形成一体。
据上所论,我们认为此“王珪”乃唐人王珪无疑,对其只需注明为《外台秘要》作者王焘的祖父“王珪”即可。
3.《药总诀》 梁·陶隐居撰。论次药品五味寒热之性,主疗疾病,及采畜时月之法。凡二卷。一本题云《药像敩诀》,不着撰人名氏,文字并相类。校注:敩:原作“校”,据《证类本草·序例上·补注所引书传》改。(P.73)
按,此校有违自身体例。本书校点“凡例”八云:“对原书的古今字、通假字,一般不加改动,以存原貌。”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小部》:“校:假借又为‘敩’。”准此,则“校”、“敩”于此乃通假关系,不必校改以自乱体例。
又及:检《四库全书·子部·证类本草·序例上》作“《药像口诀》”,而《四库全书·子部·本草纲目·序例上》则作“《药象口诀》”。看来校点古籍,凡底本可通者,一般不可据他本易之,否则,真是改不胜改。
4.《药性论》 不着撰人名氏。集众药品类,分其性味、君臣、主病之效。凡四卷。一本题曰陶隐居撰。然所记药性功效与本草有相戾者,疑非隐居所为。校注:戾:原作“类”,义正相反,据改同上。(P.74)
按,将“类”校作“戾”,从今人角度看,直观明白,但有违原文本意。其实,此“类”义即“戾”。《说文·犬部》“类”朱骏声《通训定声》:“类,假借又为戾。”《逸周书·史记》:“昔縠平之君,愎类无亲。”孔晁注:“类,戾也。”俞樾《群经平议·毛诗四》按,“类,与戾通。”孙诒让《札迻·荀子杨倞注·不苟篇第三》:“夫富贵者则类傲之”按,“类,与戾通。”此还可证之于跟“类”有通用关系的“颣”。《老子》第四十一章:“夷道若颣。”陆德明释文:“河上作类。”《说文·糸部》“颣”段玉裁注:“颣,亦假‘类’为之。《昭十六年传》曰‘刑之颇类’服虔读‘类’为‘颣’。”《管子·地员》:“大者不类,小者则治。”王念孙《读书杂志·管子第九·地员·不类》:“颣、类古字通。”《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贪惏无厌,忿颣无期。”陆德明释文:“颣,本又作类。”杜预注:“颣,戾也。”《说文·糸部》“颣”朱骏声《通训定声》:“颣,假借为戾。”
训诂学有“反训”术语,其定义为“一个词有两种‘反向’的意义”,如:“售”,既可训作“卖”,也可训作“买”。“乞”既可表“求”义,也可表“与”义。“假”既可释为“借入”,又能解作“借出”[5]110-127。“类”或属“反训”词,自身含有“戾”义,故不必改“类”为“戾”。
5.唐《新修本草》 唐司空英国公勣等奉敕修。初,陶隐居因《神农本经》三卷,增修为七卷。显庆中,监门府长史苏敬表请修定,因命太尉赵国公长孙无忌、尚药奉御许孝崇与敬等二十人重广,定为二十卷。今谓之《唐本草》。校注:敬:原因避宋太祖赵匡胤之祖名讳作“恭”,今据《旧唐书·经籍志》改回。下同。(P.74)
按,将唐代医家“苏敬”的又名“苏恭”说成为“避宋太祖赵匡胤之祖名讳”而成,非仅校注者一家看法。然我们以为,这种说法似有讨论的余地。而以《旧唐书》为据改“恭”为“敬”,亦欠说服力。《新唐书·艺文志》:“苏敬《新修本草》二十一卷。”宋·王钦若《册府元龟·总录部·医术第二》:“时右监门长史苏敬上言:陶弘景所撰《本草》事多舛缪。诏中书令许敬宗与才及李淳风,礼部郎中孔志约,并诸名医增损旧本,仍令司空李勣总监定之。”宋·唐慎微《证类本草·木部下品总九十九种》:“(楸木)生山谷间,亦植园林以为材用,与梓树本同末异,若柏叶之有松身,苏敬以二木为一,误也。”而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六、卷六十三,“苏敬”并五见。《旧唐书》为早于宋朝的后晋人所撰,可不受后来的宋太祖赵匡胤之祖名讳而径作“敬”,那为何宋人欧阳修、王钦若、唐慎微等都不避讳,而元人左斗元却讳而避之呢?
而且,支持此疑问的一个最直接的证据是唐人王焘(670年—755年)的《外台秘要》。王焘《外台秘要》博采众家之长,“上自神农,下及唐世,无不采摭”,引用前代医籍达60部之多。其中,引用唐人苏敬用药方剂凡十六则——卷十八五则、卷十九十一则——并作“苏恭”。若“苏恭”为“苏敬”“避宋太祖赵匡胤之祖名讳”所致,则如何解释唐人笔下的“苏恭”呢?
宋初确有过避宋太祖赵匡胤之祖名讳“敬”的“庙讳”之规定,但哲宗时就将其“改迁夹室”,不再避讳了,更何况宋人有“临文不讳”之习。这也就是为何宋人笔下多径作“敬”,的缘故。据沈澍农先生研究,宋本医籍有避宋太祖赵匡胤祖父名敬的,但其方法是采用“缺末笔”讳,而非近同义词代字讳[6]139。看来,说“恭”为避宋太祖赵匡胤之祖名“敬”之“庙讳”而改,未必确切。
那么,“敬”与“恭”的异文关系当为何?因史书对“苏敬”没能提供更多的材料供研究,这里只能据一般事理提出个人一点看法,以供参考。作为唐右监门长史的“苏敬”,“敬”是其名,而“恭”或是其字。《礼记·乐记》:“庄敬恭顺,礼之制也。”名“敬”、字“恭”或本于此。《玉篇·苟部》:“敬,恭也。”名与字义近同,可互释。这就犹如唐诗人李白字太白、杜甫字子美一样:“白”“(太)白”同义,“甫”“(子)美”义近同可互释,而字中“太”、“子”则为衬字。后世或作“敬”,或作“恭”只是称名与称字的缘故。
6.显庆中,监门府长史苏敬表请修定,因命太尉赵国公长孙无忌、尚药奉御许孝崇与敬等二十人重广,定为二十卷。今谓之《唐本草》。校注:崇:原作“宗”,据《新唐书·艺文志》改。(P.74)
按,检四库全书《新唐书·艺文志》、及中华书局校点本《新唐书·艺文志》,字均作“许孝宗”[7]1573,不知校者“崇”字所据为哪一版本《新唐书》?而实际情况也是,底本“宗”字不误,不必据他本“崇”而校改。在传世文献中,“尚药奉御许孝宗”,与“尚药奉御许孝崇”并见。作“许孝宗”者,除元人《风科集验名方》、及《新唐书》外,还有元人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四《历代医师·唐》、李时珍《本草纲目·序例上》。而作“许孝崇”者有:《证类本草·序例上》、宋·张杲《医说》卷一、宋·王应麟《玉海》卷六十三、清《钦定历代职官表》卷三十六《太医院表》等。同一人名,为何有“宗”“崇”两种写法呢?究其因,乃古人眼里二字通用。《管子·正篇》:“万特崇一。”俞樾平议:“崇,读为宗。《尚书·牧誓篇》:‘是崇是长。’《汉书·谷永传》‘崇’作‘宗’。是古字通也。”《诗经·大雅·思齐》:“惠于宗公”马瑞辰传笺通释:“宗、崇古通用。”《墨子·非儒》下:“宗丧循哀”孙诒让间诂引毕云:“《孔丛》、《史记》‘宗’作‘崇’。宗、崇字通。”又《尚同中》:“宗于父兄故旧”孙诒让间诂引戴云:“宗,读为崇。”孙诒让《札迻》卷五:“我欲伐宗、脍、胥敖”按,“宗,盖崇之假字。”《书·顾命》:“恤宅宗”刘逢禄今古文集解引庄云:“宗,当作崇。”
若从汉字的本字本用看,底本中人名“孝宗”较异文“孝崇”为长。《书·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孔安国传:“继先祖之志为孝。”《礼记·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周礼·地官·师氏》:“三曰孝德。”郑玄注引孔子曰:“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孝宗”之名本自“能继先人之志”义,而作“(孝)崇”或是“(孝)宗”的借字,否则,义嫌迂曲。
7.《删繁本草》 唐润州医博士兼节度随军扬损之撰。以本草诸书所载药类颇繁,难于看捡,删去其不急并有名未用之类,为五卷。不着年代,疑开元后人。校注:损:原误作“振”,据《证类本草·序例上·补注所引书传》改。(P.74)
按,校“振”为“损”,是。但上引文字尚有两字因形近而误录。其一,“扬”乃“杨”字之误。除校注者所参之本《证类本草·序例上》作“杨”外,他书亦多有证。《宋史·艺文志六》:“杨损之《删繁本草》五卷。”宋·郑樵《通志·艺文略》第七:“《删繁本草》五卷,杨损之撰。”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序例上》:“《删繁本草》禹锡曰:唐润州医博士兼节度随军杨损之撰。”其二,“捡”乃“检”字之误。“检”义为查,今人常说的“检字表”、“检索”、“检查”就是其常见用法,而字作“捡”,则不可通。
古人书字,以“木”作左边偏旁的,极易与“手”混同,对此,张涌泉先生《汉语俗字丛考》“木部”论曰“扌旁木旁相乱为俗书通例”[8]546。“扬”“捡”二字,正是张先生所讲之类。今人录文当以正字为准。
又及:同书第129页:“斑猫一个,去头、翅、足,以针札住,灯焰上烧,米醋内淬,如此三两次,就烧成。”又第134页:“一月,尚柱拐而行。”其中,“札”乃“扎”、“柱”及“拄”混同例。前者将“杨”误录为“扬”,而此则将“扎”、“拄”误录为“札”、“柱”。误虽相反,然可互为证。
8.菝葜 《本草》云:味甘平,温,无毒。主腰背寒痛,风痹。校注:菝葜:原作“萆拨”。考《证类》其性味主治乃属菝葜,而非荜茇,因改。(P.94)
按,从今人理解方便说,将底本“萆拨”校作“菝葜”,可从。但从校注古籍通例看,此校尚有讨论的余地。具体地说,就是底本“拨”是“葜”之误,当出校;但“萆”恐非“菝”误字,而是“菝”的异写词。《礼记·月令》:“(孟夏之月)王瓜生,苦菜秀。”郑玄注:“王瓜,萆挈也。”《本草经考注》:“今《月令》注作王瓜,萆挈也。《正义》云:王瓜,萆挈。《鲁本草》文据此则以王瓜为菝葜,本草家别有此说,张揖、郑玄共从之也。”[9]446《广雅·释草》“王瓜”王念孙疏证:“《月令》郑注云:‘王瓜,萆挈也。’萆挈与菝葜同。正义云‘王瓜,萆挈’,《鲁本草》文。是萆挈一名王瓜,本草家即有是说。草木多异物而同名者,此类是也。”[10]328可见,在记录[菝葜]这一语词时,“萆挈”与“菝葜”同,而“萆”与“菝”亦当同。对“萆”不烦校改。
9.朱真人治风坑汤 《野人闲话·朱真人灵验篇》云:有病者,患风疾数年不效,掘坑,令患者解衣,坐于坑内,遂以热汤淋之。良久,复以簟盖之,差。校注:效:原作“较”,据《普济方》卷89改。(P.111)
按,底本“较”不是“效”的误字,是“较”的常见义。而明人《普济方》“效”实是“较”同词异写。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二:“较,犹瘥也。”[11]244“瘥”即病好。《玉篇·疒部》:“瘥,疾愈也。”明·汤显祖《牡丹亭·拾画》:“日来病患较些,闷坐不过。”徐朔方等校注:“较,病好一些。”《外台秘要》卷二十五:“又疗痢,初较脓血或变纯白,或成鱼脑。”唐·薛能《黄蜀葵》诗:“记得玉人初病较,道家妆束厌禳时。”宋·欧阳修《与梅圣俞书》:“小儿子伤寒已较,因劳复发。”又《与王懿恪书》之五:“某自过年,儿女多病,小女患目,殆今未较,日颇忧煎。”宋·杨万里《久病小愈雨中端午试笔》:“病较欣逢五五辰,宫衣忽忆拜天恩。”元·关汉卿《拜月亭》第二折:“但较些呵,郎中行别有酬劳。”又第三折“这一炷香,愿俺抛闪的男儿较些。”又“你哥哥暑湿风寒从较些。”皆其例。因“较”义为病痊,故可与“痊”同义连语作“痊较”。金·董解元《西厢记》第五卷:“小诗便是得效药,读罢顿然痊较。”又可倒作“较痊”。元·关汉卿《拜月亭》第四折“你而今病疾儿都较痊,你而今身体儿全康健。”《汉语大字典·口部》:“可:⑧病愈。”[12]615“较”义同“可”,故又能与“可”连语作“较可”。元·王实甫《西厢记》第二本第三折:“我相思为他,他相思为我,从今后两下里相思都较可。”言两人的相思病都好了。元·武汉臣《生金阁》第一折:“来到这半途中,染了一场冻天行的病证,方才较可。”人们常把病愈称作病“好”。而此“好”与表病好的“较”亦近同,因此又有人将“较”与“好”连语作“较好”,以称病愈。元·郑光祖《倩女离魂》第三折:“[夫人上云]来到孩儿房门首也。梅香,您姐姐较好些么?……[夫人见科云]孩儿,你病体如何?”元·无名氏《争报恩》第三折:“到权家店支家口,不幸染了一场重病,不甫能将息的身子较好,要回梁山去。”字又作“校”。《汉语大字典·木部》:“校:病愈。唐张籍《患眼》:‘三年患眼今年校,免与风光便隔生。’唐白居易《病中赠南邻觅酒》:‘头痛牙疼三日卧,妻看煎药婢来扶。今朝似校抬头语,先问南邻有酒无?’”[12]1291他书例多,不烦引。“较”“校”为何可表病愈义?蒋礼鸿认为是由其“比较”“校量”义引申而为“差减”,而疾病的差减就是病愈[13]229-232。
“朱真人治风坑汤”方,是说有病人,患风疾好多年都不好,后来用了治风坑汤后就痊愈(差)了。上文“不较”,与下文“差”相对为文,相反为义,“较”即好,指病愈。根本无需校改。至于《普济方》作“效”,从元人作“较”而明人改作“效”看,只能看作是原文“较”的同词异写字,而不可作为校改原文的依据。又:同书第388页:“万安丸治一切风痫发搐,多时不较,并宜服之。”此“较”与上论“较”并同。
参考文献:
[1]曹洪欣.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第一册[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
[2]黄征.敦煌俗字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3]杨宝忠.疑难字考释与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王珪.泰定养生主论[M].褚玄仁,校注.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5]蒋绍愚.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沈澍农.中医古籍用字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7]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张涌泉.汉语俗字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0.
[9]森立之.本草经考注[M].吉文辉等,校点.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10]王念孙.广雅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M].北京:中华书局1953.
[12]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第二版)[M].武汉:崇文书局,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
[13]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第四次增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责任编校:汪长林
网络出版时间:2015-03-02 2:51:25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50302.0952.010.html
A Discussion of Difficult Words in the Medical Book Fengke Jiyan Mingfang Returned Overseas
LIU Jing-l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Anqing Teachers College,Anqing 246133,Anhui,China)
Abstract:FengkeJiyanMingfang is a medical book of high quality printed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returned from Japan recently.However, because relevant studies are just at an initial stage, there exist some problems about such difficult words as “qian (钤), gui (珪), xiao (校), li (戾), jing (敬), zong (宗), yang (扬), jian (检), bi (萆) and jiao (较)” in the edition published by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in 2010, hence the necessity of discussion.
Key words:returned overseas; FengkeJiyanMingfang; difficult words; discussion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15)01-0045-05
作者简介:刘敬林,男,河南镇平人,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14BYY103)。 国家社会科学
收稿日期:2014-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