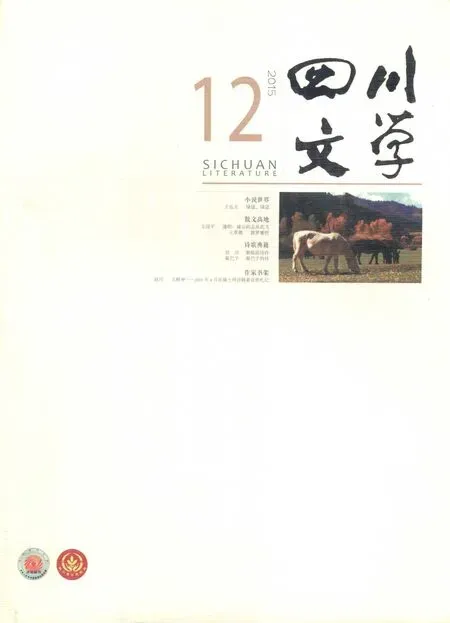事无空言说皇木
2015-12-16○邹蓉
○ 邹 蓉
好久以前就想去皇木,还专门为此筹划过几次,总以为我很快就要去了,实际上也是遥遥无期。即便人已经到了汉源,还是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始终不能成行。
这些年没少听人说皇木,有人说皇木的腊肉好吃,也有人说皇木的竹子坪风景如何优美……我曾经在大渡河峡峪听人说,最佳的观景点就在皇木的三合村。如若仅仅是这些,不能对一个地方有更详尽的说法,终归还是让人意犹未尽。我是一个喜欢刨根问底的人,想必“皇木”的地名还是有讲究的。一个“皇”字,免不了又要和古代的皇帝扯上关系,比如汉源的花椒之所以称之为“贡椒”,亦是如此。有史料记载:“皇木古为夷人之大堡子……明建文帝朱允炆居南京皇城,因此处森林茂密,多产上等杉木、楠木等,被列为采伐地……所以称为皇木厂。”还有史可证,500多年前,汉源帽壳山的确为北京紫禁城提供了木料。有人说如果没有中国西南的皇木,就没有今天的紫禁城,也没有明清时候的北京。汉源的皇木是中国西南采伐皇家用木最重要的地方,也是迄今发掘出实物,唯一能够证明皇木存在的地点。
我对所有的史料都抱有一定的警惕性,免得混淆视听。如此,我自己对“皇木”实际上还是没有概念。
当年,我在汉源县第四中学上了一年的学。寝室里住有一个隔壁班的女生,我现在还能想起她的模样,就是忘记她叫什么名字,连姓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一个爱运动的高个子女生,模样俊俏,一说话就笑,篮球场上还很拼命……我记得最初认识时,她说自己是皇木人。我第一次听人说“皇木”,就是从她那里得知汉源还有这么一个地方,倒不是觉得诧异,就是觉得新奇。我去过的地方不多,听说过的地名也不多,自己也知道世界之大,还有很多地方我闻所未闻。也听人说过一些地名,过一段时间就忘记了,主要是缺少一些关联。恍惚记得她说要带我去她家玩,还说皇木离大树有好几十里路,得挑个周末才行。我以为她说的是真的,心里记着这事。有一段时间,我接连几个周末都不回家,总以为她看见我在,就会邀我去皇木玩。我没想到的是,她后来就再没提这件事情,有可能是她忘记了,也有可能就是随口说说而已,并不是真的想邀我去耍。即便是这样,我还是一等再等,满心希望她有一天想起这事,然后我就跟她去皇木了。我小时候脸皮薄,没好意思提醒她,这事就不了了之。后来再听人说皇木,我都无一例外地想起那个女生,以及她对我说的话。
真要去皇木,并不是一件难事。就因为没有去成,又说来说去都说了好几回,后来就不大好意思再说。所有没有做成的事,都不过是想法,人生最不缺少的就是想法,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但是,基本上我所有的想法都在,不会自己消失,总有契机给它溜出来,时不时撩得人心猿意马。人要活到一定的年龄才能明白,不能把想干的事停留在嘴上。还是让我逮着了机会,和一些写作的人去采风——于是,我在这个秋天去了皇木。
我坐诗人何文的车,车上还有杨兴中老师,我们一共就三个人。他们两个是天全人。天全和汉源同属于雅安地区,说起来也不算远。很凑巧的是,我们三个人都没有去过皇木。对于这一点,相互都不用作过多的解释。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如果总是惦记着远方,难免会忽略近处。就何文的话来说,因为大家都没有去过,前面的路才极富诱惑,每前行一米都是一个新的纪元……
开车从汉源县城出来往东,有很长一段公路是沿着大渡河顺流而下,过了乌斯河火车站,在某个分路口以后,车就往山里去了。大渡河也就越来越远了,但时不时还是能看见,不过真的是有点远了,看上去已经不敢相信是大渡河了,倒像是一股细流,又或者说是成了山与山的分界线。
何文的车开得极平稳,不紧不慢地跟着前面的车,在崎岖的山路上缓缓前行。沿途的景和物与汉源别的地方相似,或者说就是农村与农村的相似,我不能马上神而往之。放眼望去,漫山遍野长着高的树,以及矮的灌木丛,道路在中间绕来绕去,加之山中有薄雾飘散游走,四下变得扑朔迷离。还是能看得见远处的山,却看不到更长的路,前面的车突然就不见了,恍惚我们便这样迷了路,从此要与世界隔绝了。鸟儿清脆的叫声,忽左忽右,总觉得它们在旁边跳来跳去,像是在故意逗我,可惜我听不懂。隐约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兴奋,抑或假装迷路倒是很开心的事,有一点小刺激。看似每一段路即将消失,它还是要往前一点一点地延展,就像是路载着我们往前蹭。
无论如何,还是应了那句话: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前面突然就出现了一片开阔地。公路两边的地里种着红苕,红苕藤爬了一地,长得铺天盖地。离公路远一点的地里长有青菜、包心菜,排列整齐,长势喜人,看上去有一些规模,应该是蔬菜种植基地。坡上坡下的地里稀稀拉拉地立着苞谷杆。这个季节,苞谷已经收了有一段时间了,留在地里的苞谷杆不过是一些“光杆司令”,大概还没来得及收拾。近年去过的农村,农民只忙着收粮食,收过以后较长一段时间,地里还是一片狼藉。
每次看见这样的情形,就不由得想起我曾经的乡村生活。当年,我们家也要种苞谷,而且每年都种,种出来的苞谷磨成粉给猪食。母亲才收完苞谷,又要拿镰刀去地里砍苞谷杆,她是要把地里收拾亮堂。母亲总说“只有把天亮出来,地里的庄稼才长得好”。那些秋天,我也是要跟着母亲下地干活,苞谷杆背回家立在晒楼边的空地里,太阳晒得到,风也吹得到,要不了多长时间,苞谷杆就脱水干透。然后再折成一截一截的,每次煮饭的时候用它来生火,等火烧旺了再往里放柴禾,火就这样烧起来了,燃后的灰烬撒在地里作肥料。
凡是看见收了苞谷的地里还立着苞谷杆,我都恨不得抓一把镰刀,亲自下到地里去把余下的事情做完……尔后惊觉,这事与我并无关系,倒像是某种强迫症在作祟。我害怕看见别人没做完的事情摆在那里,我就会很认真地思考,而事情确实与我不相干,我不过就是想想而已,并不会真的去做,还是感觉到累,一种力不从心的累。我想着当年的母亲,想着她那些种地的日子,她作为一个农民,那么多年一直都很是尽职。
算起来,我离开汉源有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还真是有点久了。这样长的时间,新生儿也能长大成人。在这样长的时间里,我曾经生活过的农村,还有我现在居住的城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称得上是翻天覆地。现代交通的日新月异,新农村的建设初见成效,有过半的乡村已经实现路路通、村村通,农村与城市的距离在逐渐缩小。著名诗人李白写的《蜀道难》: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诗句里的描述,已然成为过去。所有的变化,已经不能单纯地说是好与坏,凡事皆有两面性,常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现代城市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过去的农村是人多地少,现在是人少地多,劳动力的限制,以至部分土地板结,田地荒芜。路过那些长着过膝蒿草的田地,风吹野花显凄婉,都不忍心多看几眼,看着看着就难过。
我小时候看见过有人为争一点地,大打出手,还有人为给自己家田里多灌点水被砍死在水沟里……我吃自己家地里种的粮食长大,自小就知道土地的珍贵。家里的田地不多,只有母亲和我分有土地,父亲和兄长有工作,户口不在农村,分不到土地。我也有童年的忧伤,小小年纪就要担心田里地里的收成,害怕地里长的粮食不够一家人吃。看别人家田大地多,心里总有一些羡慕。我曾经梦想拥有大片的土地,成为名符其实的“地主”,如果这个都不能实现,那我就要远远地离开。归根到底是不忍心看母亲患得患失,担惊受怕,还是希望生活富足,能够让母亲过得好些。
每个人的心里都长着欲望。
虽然我无法拥有大片的土地,虽然我也是按我设想的那样,远离了那块只能养活我和母亲的田地,对土地还是有割舍不下的情怀。有时候我都觉得可笑,也很幼稚,面对别人的田地,我要去估算它的收成,评估它是不是已经物尽其能。看着一些空在那里的田和地,想着母亲那一辈农民的勤劳,每一家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死心塌地地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
近年有些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报道,身强力壮的都跑城里打工挣钱去了,唯有老人和孩子还守着乡下的日子。这便是我这些年觉得,农村再不是我熟悉的农村了。
前面的车停了,我们也跟着停下来。旁边有一个湖,听人说是松坪湖。
松坪湖是皇木松坪土司地的人工湖,湖里长满水葫芦,也不知道那水里有没有鱼在游。几只白鹭在湖上面交差盘旋、飞翔、栖息,从自己过去的记忆中慢慢回到现实中,心情异常平静。从湖的这边看湖的那边,湖水宁静而澄澈,湖那边的亭子里有几位老人,他们围坐在一起,看样子可能在打川牌,也可能是在抽烟、聊天,或只是坐在一起,什么也没有做,样子很是闲适。
近处的农舍有人推门,能听见院子里的鸡鸣狗叫,还闻到空气中家禽的味道……农村生活又缕缕涌现,仿佛也还是熟悉。这个时候有一种冲动,想去拍人家的门,进到院子里去讨要一口水喝。所有的想法都很隐秘,只要不说出来,就不会有人觉察,自己却很容易就融入这样的氛围中。
沿着湖边新修的公路徒步前行,我也不清楚是要往哪里去。突然就有人指着旁边一片林子说是土司古墓,我跟着驻足观望。土和石头堆砌而成的土司古墓异常质朴,如果不是有人指引,我可能不会注意到这一片林子。树长在土司的坟头上,中间荒草丛生,也不知道那些树长了多少年,长到现在树冠甚是茂密,已是遮天蔽日,想必此地是福地,抑或是风水宝地。还是觉得土司古墓太过朴素,实在是跟平常百姓以往的坟茔没什么两样。一边在说松坪土司的一些生平过往,另一边秋蝉在树上一刻也不消停,叫声尖锐刺耳,如利器或铁丝般“嗞嗞嗞”地要长进脑子里去,保不准耳膜会在下一刻 “噗”一声破掉。有点烦心,下意识要寻它,却一直不能发现它所在的位置,即便是借助声音也不能。
关于松坪土司,《汉源县志》有专门的记载:明时有土司世居松坪,直至明终清至。康熙四十三年,因松坪土司马比必招抚发难彝民有功,即荣升其为土千户,即第一代松坪土司。道光十三年,土千户马林因“反叛”罪名,被清廷处死于成都。松坪土司历时130年。而民间传说土司居松坪是为避战乱,在此狩猎为生。
由松坪土司说松坪,过去整个松坪是一个大型的建筑群落,全是四合院,呈七星抱月之势,还设计有五福捧寿的造型……想必那是松坪土司地过去的盛况,就如大树的张家盐店也是如此。如今松坪土司地尚存甚少,除去土司古墓,还有一截大约三十米长的土司城墙。我看到的松坪是4·20芦山地震后重建的。基本上所有的灾后重建都是旧貌换新颜,是按现代新农村规划建设。现在农村的房屋修建非常讲究,不管是远看还是近看,都跟小别墅似的。我不得不说,自己对新农村的认识极为模糊,好像整个国家都在努力把农村建设成城市。另外,新农村与新农村的建筑模式又都差不多,识别度不高,这就跟城市与城市的千篇一律是一个道理。
——或许,习惯了就好。
看过松坪土司地,我还是坐回先前的车继续往前行。是我先问要去哪里,何文和杨兴中也是一脸茫然,原来他们也不知道具体的行程安排。一个车上三个人,就没一个明白人,我们竟然为此哈哈大笑。其实这样也挺好,越是对未来的事情无所知,就越是新奇。
说话间,不经意瞥见右前方有一个路牌:皇木镇。我当时就愣住了,居然忘记刚刚想要说的话,有点傻傻的。一直以来,我脑子里只有“皇木”,并没有“皇木镇”。可能是我对文字的记忆出现了问题,这个着实让我吓了一跳。好在事情也不难理解,皇木——皇木厂——皇木镇,它们大概就是以这样的线性方式出现的。我来之前听人说过,现在皇木还住有当年的伐木工人的后代。
镇口的公路边有一块空地,有几辆车已经停在那里。地上能清楚地看见车辙,泥泞和积水显得这里昨夜像是才下过大雨。也还是在镇口,有几个摆摊卖东西的,衣服和鞋子都有,还有一些廉价的塑料玩具……一看便知是遇上赶场天,还以为镇上有多热闹,多走几步就发现镇子其实很安静,不少人家还关门闭户,也就只有场口那一点热闹,好像是专门迎接我们似的。或许是因为我们到得晚了些,想必上午还是要比现在热闹些。山里面的镇子都不会大,要走完整个镇子,估计也不会花多少时间。到镇上赶场无非就是卖东西和买东西,买东西的人买了东西就回去了,不会无故在场镇上多停留,毕竟屋里屋外的事情繁多,总有一些牵肠挂肚的事情。卖东西的人自然要回得晚些,只要还有东西可卖,即便赶场的人都散了,也舍不得马上收摊走人,总觉得还有买卖要来。
我小时候喜欢去一些热闹的地方,不放过任何机会,总想往镇上、城里去,没钱买东西,看热闹也是好的。长大了以后,我喜欢去一些不那么热闹的地方,为的就是从城里挤出去,到乡下去透透气,过一些短暂而闲散的时光。现在看来,镇子小没有什么不好,所见的生活质朴而真实,毕竟日子不是过给别人看的。
皇木镇所处的位置在海拔两千多的高山上。我们一来就遇上难得的阴天,自嘲是因为我把成都的坏天气带到皇木山上来了,听见的人都同意了这个说法,虽然说的是玩笑话,我真以为逃出城市的雾霾,在这里我会看到蓝天白云,事情还真是始料未及。当然,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有晴天,有阴天,也会有雨天,冬天皇木山上还要下大雪,路上要结暗冰,这个成都不会有。
没有太阳的皇木,下午有点冷。从包里翻一件厚衣服出来穿在身上,从山下到山上,前后十多度的温差,有点分不清季节了。需要喝点热水,再吃点东西,身体会很快适应这里的冷空气。
我是真的不知道下午要去参观果园。我要是知道,也不会吃菜喝汤,还要吃两个土豆。浑然不觉就跟人进了果园,看人家房前屋后都是果树,树上那些油绿的桔子、青绿的梨子、洇红的苹果,还有紫红的李子,我马上就懊悔了。还是没有预见性,饭有什么好吃的,夹点菜吃就算了,还要吃什么土豆?即便是要吃土豆,吃一个就好了,居然还吃两个,一点余地都没留。这下好了,什么都吃不下了,只能在果园里瞎逛,眼睁睁地看着一树的果子,我是不想指指点点,更不想评头论足。听见有人在后面说苹果的果形和色泽,这样的话题要继续的话,估计会牵扯到修枝和疏果的农技问题。修枝不难理解,疏果的说法对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来说,稍微有点难懂。其实就是在挂果的初期,须要按一定的密度去人工疏果,把多余的果子摘掉,保证足够的营养供给余下的果子生长,同时也是保证它们的生长空间。一想到空间,我生怕有人踩到树下的青菜,以前我母亲就是这样叮嘱我的,现在仍然清楚地记得,一进到田地里,就紧张这个。
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果香味,我分得清楚苹果的味道,也分得清楚梨子的味道,我记得所有吃过的水果味道。我尽量踩着田埂前行,现在就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我停下来,恍惚我就这样走进别人的梦里面,也不知道谁在前面等我……
我还是来得早了些,虽说已经是秋天,但还是初秋。果园里的苹果开始红了,但是色泽还没有出来,还须要再等些时日。等秋天的太阳多晒几回,昼夜的温差再大些,苹果自然红透,色泽和味道俱佳。就我个人而言,喜欢红苹果的同时,更偏爱青苹果一些。当地与我们同行的老者摘了一个大苹果给我,直径有八、九公分,这样大的苹果我是吃不完的,但是不能不接。其实所有的水果不是越大越好吃,直径七公分左右的苹果口感极佳。我倒是没有想到,老人家竟然给我摘的是青苹果,不是都觉得红苹果更好看些吗?我都没有说话,他已经洞悉一切,给了我一个青苹果,而不是一个红苹果,这个让人心里觉得温暖。没有水,拿着苹果在衣服上擦了几下,直接用嘴啃着吃。听到自己清脆地咬破苹果皮,马上就有丰富的果汁涌到嘴里,甜与酸的混合交错,丝丝缕缕从舌尖到舌根,味道极为丰富,还是层次分明。我说:“这是我今年吃过最好吃的青苹果”。不管有没有人相信,我说的是真话。今年春天,我在九乡的申家沟看桃花、梨花、苹果花的时候说过类似的话,我当时说“这是我活到现在最美丽的一个春天”,事无虚言。我还是不自觉地把汉源不同的两个地方关联起来,仿佛我一路从申家沟的春天走过来,在皇木山上的果园里进入了秋天。
我原本是想吃完这个苹果的,还是力不从心。实际上,我从来就吃不完一整个苹果,这慢慢就成为一种障碍。我再怎么努力也不能吃掉整个苹果,心里有些歉疚,总觉得有点对不起人。看到地上落了不少苹果,也迟迟不敢把手里啃了一半的苹果扔掉,握在手里又走了很长一段路。后面还有人在摘苹果,也不知道是谁的苹果掉在地上,从我旁边的沟渠骨碌碌地滚下去了,我差点开口喊停,以为它会听我话的。还有人给我苹果,我说没法拿了,他们就兀自往我的小背包里塞,虽然装不了几个,心意却是满满的。后来又遇上糖心苹果,我都不敢多看,害怕再有人给我苹果,我根本腾不出手去接。
路边有一棵不大的李子树,树干也就大姆指般粗细,却密密地结了一串紫色的李子。我吃过这样的李子,许多地方称之为“鸡血李”,我是觉得这名字不贴切,鸡血怎么可能是紫红色,更像是葡萄汁。我是吃过这种李子,却没有看见它长在树枝上的样子。现在看见了,紫色的李子长在绿色的枝头,还真是好看得不得了。于是,我悄悄地扔掉手里的半个苹果,想着它这样烂在地里也是有机肥,这样便是自我宽慰,心里稍稍心安了。吃李子的时候,又遇上农家门口有几棵很大的核桃树,核桃外面一层绿色的皮已经裂开,看得见里面的核桃壳。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找来的竹竿,有人跃跃欲试要打核桃。这个让我想起小时候,遇上打核桃,我便躲到旁边去,等核桃都掉在地上了,我才跑出来捡。现在看见有人要打核桃,我还是和小时候一样,跑到远一点的地方,免得核桃从树上掉下来砸到头。
核桃从树上掉下来,“啪”地落在地上,面上那层绿色的皮本来就已经裂了,落下来就散开了,裹在中间的核桃从里面滚出来,手劲大的捡两个放在手心,用力一挤,核桃壳就破了……
当晚,夜宿皇木镇。一夜雨声“嘀嘀嗒嗒”,再听不见别的声音。人的意识变得异常清楚,生命的存在突然间被放大了许多倍,所有的执念都无足轻重,可以抛得一干二净,仿佛这样就得到某种新生,一切重新开始。
离我们住的客栈不远处有一座天主教堂,昨天就有人已经去看过了,我还没来得及。客栈是当地人自己修的房子,开的客栈。在我入住的整个过程中,没看见有外人帮忙,凡事都是主人家亲力亲为。客栈的主人是一位五十来岁的阿姨,我闲来无事与她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问镇上有没有可以喝茶打麻将的地方。她马上就摆手摇头说:“我家是不打麻将的。”这话她一连大声说了好几遍,弄得我很不好意思。第二天走的时候,还有人要往我的背包里装两个苹果,说是供奉教堂的水果,才知道老板还要照管镇上的天主教堂。
我头一天就错过时间,没有看成教堂,想着第二天早上先去看了教堂才吃早饭。谁知道早上起来,我还是没有看成教堂。就因为听说客栈旁边的学校里有一棵千年老树,我就跟人看树去了,这样一来我又没有看成教堂。
果然如他们说的那样,皇木初中的操场上还真是有一棵老树。我认得的树不少,还是叫不出那树的名字,是问了别人才知道是“柯楠树”。据说北京故宫大殿的柱子用的就是此木,也是从汉源的皇木运进京城。我们之所以还能看见这棵柯楠树长在这里,是因为它当年长姿不佳,才 被嫌弃,要不然今天也是故宫里的一根柱子了。按长者们的说法,看见老树是福气。至于它有没有千年之久,我不敢乱说,但无论如何,它看上去确实很有龄感。目测这样一棵树,需十几个人合抱。树干里面风化、腐烂形成的空洞,大概能塞十几、二十个学生进去。想着小孩子可能在这里藏猫猫,心里就莫名愉悦。还想着夏天可能会有人在那里面纳凉,仿佛人这样也是可以成神仙的。
柯楠树紧挨着学校的围墙,围墙外面有一口老井,整个皇木镇的人饮水全靠它。我仔细看过那口井,严格来说,那不算是井,应该是泉眼。泉水清澈见底,满而不溢。人蹲在前面的石阶上就可以用勺取水,老弱妇嬬皆无危险。这样看来,千年的柯楠树是长在泉水之上,依山傍水,可谓是一块灵地,难怪它能如此长寿。
我便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始终没有去教堂,或许也是要留点遗憾下次再来,这样想想也就觉得没什么了。只是心里不免还是有些诧异,按理说皇木镇所处的位置还是有点偏僻,但是这个地方竟然有天主教堂,这多少有点让人匪夷所思。就因为皇木境内有一段“乐西”(乐山——西昌)公路,就误以为两者是有关系的。既然皇木镇当时地处交通要道,有传教士落脚皇木镇也就是情理中的事情了。其实不然。皇木的天主教堂建于清朝同治年间,由法籍传教士勃拉布依·比纳特所建,早于乐西公路的修建。乐西公路没有那么长的历史,修建于抗日战争爆发初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乐西公路是四川通往缅甸国际公路最直接的通道,一方面是为了方便陪都与战区之间运送物资,另一方面国民政府还另有打算,万一重庆失守,又可以迁都西昌。此次皇木之行,我走了一段乐西公路,在蓑衣岭还能看见当年乐西公路的一点旧貌,悬崖上有一段木料和混凝土筑的路基,下面用圆木支撑和加固,至今仍然还很牢固。另外,皇木镇和许多地方一样,还有自己的“城隍庙”。为此我专门打听,据说早年有伐木的将军死于此地,皇帝封赏,让其可享人间烟火,建庙于此,便于后人祭奠和祈求护佑。
我走“乐西”公路去二道坪观大渡河峡峪,就是没有去三合村,想必许多事不能一次做完,有念想不是什么坏事。但是,我吃到地道的皇木腊肉,对我这种吃货级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吃肉之前先在养猪场看猪跑,看它们在树林里啃草,在泥地里打滚……养猪场的狗与猪关系和谐,同在一处抢食,这很符合乡村气质。有一些类似的情形还留在记忆里,现在能一点一点地找回来。听到口哨声,猪便从树林里三五成群地钻出来,步态笨拙还要摇头晃脑,聚到一起大概有两百来头。我忍不住要帮人出主意,在猪圈的房檐下挂个大喇叭,给一首音乐专门用来召唤它们进食,那岂不是更省心?我话说得很诚恳,还是要惹人笑,就好像我说得不当真,不过是在开玩笑逗人,我也就没再继续往下说。若是再往下说,我还真会说一些玩笑话,各种奇怪的想法,除去给猪听音乐,还可以对着猪读书、写字,或者每天给它们念几首诗也不是不可以,那些猪可能会长出一些文艺气质出来。后来想想,这话说不得,会产生歧义,让人误会。
七拉八扯的谈话,拐弯抹角地知道养猪的老板是我小表姐的同学,这么说就多了一层关系,彼此也就没那么生分了。再聊,又知道她并非是老板,养猪场是食品厂的一部分,她的儿子才是食品厂的法人。我感兴趣的是,她的儿子大学毕业后为何放弃在城里发展,要知道他已经在城里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她还在城里给儿子买了房子。自己放弃城市的舒适,到农村养猪做食品,这个需要多种精神。
我佩服所有勇敢的人,总之我是下不了这样的决心,所以自愧不如。我所谓的故乡,不过是一种情结,并不会有实质的行为。我那些关于土地的情愫,也不过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意识形态,只能停留在一种经历,一段回忆。时间养成我对城市的依赖,农村只是我城市生活的镇静剂,我并不能像当初离开时那样义无反顾地回去找我的土地。
离开皇木的时候,我不确定还会不会再来。一些感悟和思索,让我不敢面对自己,我必须端正态度,重新认识自己。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我又想起当年隔壁班的那个女生,也不知道她如今身在何处,想必她已经成为别人的妻子,还成为了别人的母亲——而我,记住了她少女的青春模样。猛然惊觉这些年,皇木在我这里是与她联系在一起的。
皇木在我这里是有性别的,
皇木是一女的,
而且,皇木就是一年轻的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