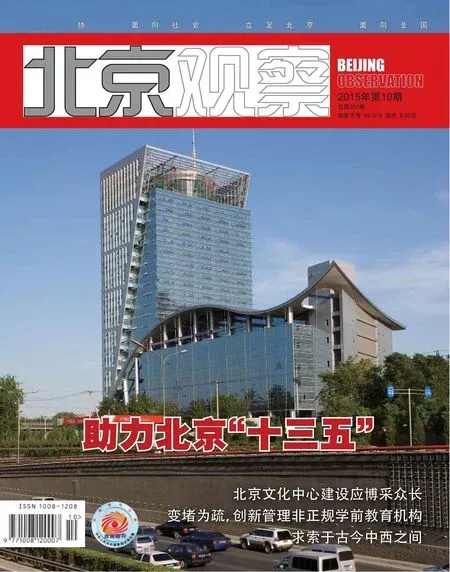写在鲁迅书边
2015-12-07文李乔
文 李 乔
不管东方西方,不问姓资姓社,不拘古代现代,苟利国家之革新,人民之福祉,只要是好东西,统统可以拿来。但又必以中国为本位,以革命为依归。这就是鲁迅的拿来主义,何其正确,何其精警!
鲁迅是民族魂,他的魂魄会长留天地间,不会散去。他的文字,常读而常新。平日读鲁,每有新收获、新体会,辄书为札记。
鲁迅口述拿来主义
改革开放已三十年,但排外思想并未尽除,晚清徐桐和拳民的幽灵仍时常游荡在世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某些蹩脚理论家仍以此为圭臬,爱国贼们更是砸车伤人,大闹街市。心有所感,我便在中央编译局举行的一次出版座谈会上发言:“应将鲁迅先生的杂文《拿来主义》,印成大字本,普遍发给机关、团体和基层。”这当然不是正规建议,是在呼吁应该学习鲁迅的拿来主义,因为这个精彩思想可以醒脑、开智、祛愚。
鲁迅不仅写过杂文《拿来主义》,还在口头上简述过拿来主义思想。1933年,鲁迅与斯诺有过一席谈,有云:
“我对苏俄不了解,但我读过不少俄国革命以前的作品,他们同中国很有些相似之处。我们肯定有可以向俄国学习的地方。此外,我们也可以向美国学习。但是,对中国来说,只能够有一种革命——中国的革命。我们也有可以从自己的历史中吸取的教训。”(《新华文摘》2012年第4期《斯诺与西行漫记前奏》)
细读这段话,可以发现这真是片言缩写的《拿来主义》。不管东方西方,不问姓资姓社,不拘古代现代,苟利国家之革新,人民之福祉,只要是好东西,统统可以拿来。但又必以中国为本位,以革命为依归。这就是鲁迅的拿来主义,何其正确,何其精警!这段话知者甚少,故录此以广之。
梁鲁论读书角度
“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绛洞花主》小引)鲁迅论《红楼梦》此名言,吾赞佩至极。近读梁启超《慧观》一文,推测迅翁之言恐由梁氏文启发而来。
梁氏曰:“同一书也,考据家读之,所触者无一非考据之材料;词章家读之,所触者无一非词章之材料;好作灯谜酒令之人读之,所触者无一非灯谜酒令之材料;经世家读之,所触者无一非经世之材料。”(引自何香久主编《中国历代名家散文大系之清卷》,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898页)此文刊于1900年3月1日《清议报》,早于鲁迅《绛洞花主》小引。
对比梁鲁二语,可见其相同处:皆揭示读书者因身份不同而眼光与角度各异。红学家冯其庸授课,常告学生读书可用“八面受敌法”,即一本书,每读一次换一角度,多次变换则全书尽知矣。此法颇类似梁鲁所言不同身份之多角度也。
迅翁之发明,在于察知读《红楼梦》者之具体视角,梁氏所言则泛论读书角度之不同。梁氏发明在先也。文化相续,互相启发,乃学术文化之常态,无足诧异,更无损迅翁之发明。然亦不应埋没梁氏。故记此一笔。
点天灯
古有“火刑”,也称“焚刑”,即把人烧死。但怎么烧,却有讲究,能烧出花样来。普通火刑是把人捆于木桩或树干,脚下累积木柴,然后点火焚之。弄出花样,便有远焙法、饮醋法、点天灯之类。这些都要比普通火刑残酷得多。鲁迅在给友人杨霁云的一封信里说:“五六年前考虐杀法,见日本书记彼国杀基督徒时,火刑之法,与别国不同,乃远远以火焙之,已大叹其苛酷。后见唐人笔记,则云有官杀盗,亦用火缓焙,渴则饮以醋,此又日本人所不及者也。”(《鲁迅全集·书信·致杨霁云》)五六年前,指1927年、1928年。鲁迅有感于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屠戮之凶”,遂考史上之虐杀法。日式之远焙法,意在细细折磨。唐人之饮醋法,乃令被刑人内脏如焚。
然火刑之最酷者,还当数“点天灯”。鲁迅似未谈过此刑。兹补说之。何谓点天灯?清人胡恩燮《患难一家言》释曰:“束绵浸膏倒燃之,名曰‘点天灯’。”(《太平天国史料简辑》第2册第327页)就是将人以麻布缠紧,浸在油膏里,浸透后将人倒挂起来,从脚跟点燃,让火慢慢往下烧,直至烧死。此种烧法可延时几个时辰,人痛极而不死。故远焙、食醋比起点天灯,显得温柔多了。此刑起于何时无确考,我所见最早资料为太平天国施用此刑。张德坚《贼情汇纂》记:“凡有人私带妖魔入城或妖示张贴谋反诸事,自有天父指出,定将此人点天灯”,“凡犯第七天条,如系老兄弟定点天灯”。(《太平天国丛刊》第3册第231页)《太平刑律》记:“凡典圣库、圣粮及各典官,如有藏匿盗卖等弊,即属反草变妖,即治以点天灯之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卷三十《刑律》)其时,封建官府之正刑,火刑已基本不用,更无点天灯,但洪天王青睐此刑,遂写入天国法典。军师洪仁看不下去,提出废止点天灯,但洪天王不干,批道:“爷今圣旨斩邪留正,杀妖、杀有罪,不能免也。”还曾看到一条材料,谓民国某地农民恨极县长,遂施以点天灯。乃天国之遗意也。点天灯之创意,非仅大增其残酷性,更增加观赏性、侮辱性及警示性。被刑者悬于高空,挣扎惨叫,施刑者大快,吓猴之力度亦更大。
鲁迅“考虐杀法”,意在痛诋国民党的虐杀。但有“左”爷却大骂鲁迅倡扬“人道主义”。其批判文字未得见,想来也就是“对杀人要做阶级分析”之类。依此论,则太平天国之点天灯便属正义,杀敌人嘛,至多稍嫌过分。有论文云:点天灯“表明了太平天国领导人反对清王朝的坚定立场和对大逆不道罪斗争的鲜明态度”,“也反映出农民的狭隘性与落后性”。本质是点赞,是“酷刑有理”。“左”祸之酷刑不断,或与此类歪论有关。
不悟自己之为奴
鲁迅给郑振铎的一封信里说:“顷读《清代文字狱档》第八本,见有山西秀才欲取二表妹不得,乃上书于乾隆,请其出力,结果几乎杀头。真像明清之际的才子佳人小说,惜结末大不相同耳。清时,许多中国人似并不悟自己之为奴,一叹。”
若不是鲁迅把此事写出,怎会想到清朝竟还有这等事,清人竟还有这等人!此真乃才子佳人小说之历史版。若非鲁迅告以档案所载,人若向我讲此事,我一定以为他在编故事,说八卦。然而这却是真事无疑。但这是一桩文字狱吗?不大像啊。但载于文字狱档,应该是的。然而又大异于常见的那种政治性的触犯逆鳞或违碍时忌所酿成的文字狱。那么,这算是哪种文字狱呢?我看是“蝎子拉屎独一份”的文字狱,是文字狱的奇葩。酿成这起文字狱的原因,不是这位秀才政治上不谨慎,或是笔下对皇上不恭敬,而是由于他拿皇帝“不当外人儿”,混淆了主奴关系。区区一个小秀才,竟敢麻烦皇帝帮自己追女人,可笑亦可怪也。为什么会这样?就是鲁迅说的,他“并不悟自己之为奴”。鲁迅为此而“一叹”。
鲁迅所叹息者,当然并非这秀才一人,而是天下许多中国人。鲁迅慨叹清代的中国人在清廷二百多年软硬兼施的统治下,已经浑然不觉自己是奴隶了。“不悟自己之为奴”,实乃奴性之最深者。不悟,自然也就不图改变,“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便会延长下去,直至延长到“欲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作者系北京日报原编委、理论部主任,第十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