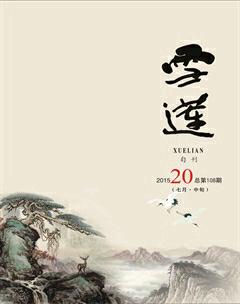鲍照《拟行路难》中的生命意识
2015-11-25刘振宇
刘振宇
【摘 要】生命意识是每一个现存的生命个体对自己生命的自觉认识,这在鲍照的《拟行路难》十八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本文就诗中的三种生命意识,即生存意识、主体意识和死亡意识,进行分析。
【关键词】鲍照;拟行路难;生命意识
一、生存意识:积极入世
一切有生命的生物都有生存意识,生存意识简而言之就是想要存在的意愿。人的生存意识是其中最为强烈和鲜明的。人类的生存意识除了基本的物质满足,更重要的是力求在世界上实现自身的存在感,也就是实现自身理想。对于鲍照来说,生存意识即是想要建功立业的汲汲心态,故而他选择了积极入世。
这样的豪言壮志,在鲍照早期的其他诗歌中也有很多,特别是一些边塞类诗,像《代出自蓟北门行》就写道“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疡”,好不豪迈!虽然鲍照没有从军的经历,但是表现了他不甘平凡,认为生命应该在更大的舞台上发光发热,同时对自己的才能也表现了极大的自信和肯定。
这种积极入世的存在意识在《拟行路难》有所体现。《拟行路难》其十曰“君不见蕣华不终朝。须臾淹冉零落销。盛年妖艳浮华辈。不久亦当诣冢头。一去无还期。千秋万岁无音词。孤魂茕茕空陇间。独魄徘徊遶坟基。”作者通过对自然界草木凋谢的观察,联想到人生亦是如此,年华易逝,但人生在世,不能终日无所事事,死后无名,劝诫人们应该把握当下,在有限的岁月中奋发图强,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在死后的“千秋万岁”历史长河中,留下自己的一笔。《拟行路难》其十一曰:“君不见枯箨走阶庭,何时复青着故茎。君不见亡灵蒙享祀,何时倾杯竭壶罂。君当见此起忧思,及得与时人争。人生倐忽如绝电,华年盛德几时见?”作者以两个“君不见”发语,引出两个反问,力度极强,让人们面对作者设定的情境,对时光以及人生进行思考,即作者所说的“起忧思”。时光流逝,如白驹过隙,“绝电”的比喻极言生命之短,在这样短暂生命中我们应该如何度过?作者给出了一个答案:“及得与时人争”,也就是积极入世,相信自己,不甘心庸庸碌碌地度过。《拟行路难》其十三曰“春禽喈喈旦暮鸣,最伤君子忧思情。我初辞家从军侨,荣志溢气干云霄。”诗中作者描写了一个从军征人的形象,春日里征人离开家乡,心中除了对家乡亲人的留恋,更多的是满怀壮志想要在沙场建功立业的拳拳爱国之心。这样的自信与豪气,与后人李白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如出一辙。虽然写的是征人,但作者何尝不是怀抱着这样的理想,想要积极入世,想要在仕途上证明自己。《拟行路难》其十八中“诸君莫叹贫,富贵不由人。丈夫四十强而仕,余当二十弱冠辰。莫言草木委冬雪,会应苏息遇阳春。”“莫叹贫”表达了作者对困境的乐观与豁达,后面几句更是直抒胸臆,对于眼下不合理的现状,作者表現出的,不是退缩自卑,也不是自暴自弃,而是一种勇于冲撞的勇气,尽管外部的大环境对他的压抑犹如冬雪,但是他仍然对未来充满希望,相信这些压力不会永远存在,相信自己可以冲破一切阻力,走向人生的春天。
鲍照的这些诗歌中,个人的存在意识极为突出,有着一种初生牛犊的闯劲,这种自信和热情是年轻人共有的。之前的年轻的曹植也曾斗志昂扬:“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后来年轻的李贺也曾呐喊:“男儿何不带越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如此强烈的生存意识是因为,未来对于年轻人来说总是光明的,偶尔出现的黑暗总是可以被克服的。但是,鲍照在《拟行路难》中这些积极入世充满着光明和希望的诗歌相对较少的,当他真的进入了南朝社会这个深不见底的泥淖处处碰壁后,他的生命意识又转向了第二个阶段。
二、主体意识:愤慨不平
主体意识是指主体的自我意识。它是“人对于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是人之所以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根据” 。当鲍照步入仕途,自我价值和主体能力面对社会的严峻挑战时,他表现出了极大的主体意识。在《拟行路难》十八首的许多作品中,他用外放而激烈的方式抒发情感,显露出极为强烈的愤慨不平。萧子显《南齐书》中对其的评论:“发唱惊挺,操调险急”,是再恰当不过了。
下面主要就《拟行路难》其四进行分析。《拟行路难》其四:“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诗歌开头,作者用一个水流因地势高低而流向各处的现象,反映了当时寒门学子的悲哀处境,也表达了作者的无比愤怒。在南朝“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的大环境下,作为“孤门贱生”但有真才实学的鲍照,心中的苦痛与无奈达到极点。对这样的不公无法扭转,“行叹复坐愁”也不是办法,只能借酒浇愁,殊不知“借酒浇愁愁更愁”,一切的愤慨不能道出,让全诗笼罩在欲诉无人、欲哭无泪的气氛之中。可谓一切尽在不言中。鲍照的暴风骤雨式抒情形成一种神奇的力量,让读者跟着他的情感上下起伏,仿佛透过纸背,就能听到他愤怒的呐喊,或是沉重的叹息。
除上面所说两首外,其三中“人生几时得为乐。宁做野中之双凫,不做云间之别鹤”,也直抒胸臆,“去亲为客”追逐黑暗重重的功名,功名未立,容颜先老,让他感触颇深,想如隐者般远离仕途的纷扰,不愿仰人鼻息,作者的正气跃然纸上。此外其七中“人生不得恒称意,惆怅徒倚至夜半。”“惆怅”“倚”这一系列动作,作者的愤慨不平虽然没有像其六一样激烈,但也是抒发不平之气的另一个略微平和的渠道。其八中“还君金钗玳瑁簪,不忍见之益愁思。”,作者以弃妇的口吻,倾吐了孤直之士对于等级制度的强烈不满和抑郁之情。
主体意识的激烈迸发,让鲍照的诗歌中有声嘶力竭的怒吼,而当愤懑逐渐平息,又出现了另一种生命意识。
三、死亡意识:无奈倦客
死亡意识指的是人作为生命的主体对死亡的认识和体验,这是每一个生命个体都存在的普遍意识,它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而死亡意识的“具体所指则是丰富多样的,也难以有一个固定的内涵,它具有高度的主体性,每个不同的个体基于自己的主体情况都有不同的死亡意识”。
在鲍照的诗歌中死亡意识主要有两种表现:首先,时光流逝感增强。这一点在鲍照之前的诗人中有很多表达,孔子就曾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鲍照感慨岁月易逝的诗歌中,更赋予一种时光易逝而个人的人生价值还没有实现的揪心与无奈。在《拟行路难》十八首中,经过统计,有七处关于感时伤逝的表述,此外还两次提到“白发”意象。在这里取“白发”两例进行分析。
第一处是《拟行路难》其十三:“流浪渐冉经三龄。忽有白发素髭生。今暮临水拔已尽。明日对镜复已盈。”诗中的主人公是从军的征人,应召入伍时也曾意气风发,但在无尽的战争中,那些昂扬的理想早已不见,心中只留下对故乡的无限怀恋和对自己身死他乡的满心悲伤。这几句诗构建了一个极具悲剧气氛的画面:经过三年的颠沛流離,忽然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年轻,两鬓生出了白发,对着水面不甘心地揪掉,结果第二天白发就像心中的苦痛一样挥之不去,早就又生了出来,剪不断理还乱,早年的理想已经随时间的流逝慢慢变质,后来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与其何其相似。第二处是《行路难》其十六:“年去年来自如削。白发零落不胜冠。”这首诗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杜甫的“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两者都充满了对国家和个人的无限愁怨。鲍照这句诗的前一句用“削”这个动词来形容时光的匆匆,让人唏嘘。时间真像一把刻刀,削去我们的年轻,也削去我们曾经指点江山的激昂豪情,现如今只剩满头白发和满心的无奈。这两句诗感染力极强,足见鲍照高手妙笔。
其次,是天命感增强。鲍照乃一介寒士,虽有远大抱负和过人才学,但是人力却无法扭转社会的不公和命运的跌宕,不甘心沉沦下僚但挣扎却屡屡失败。在理想与现实的不可调和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存亡贵贱付皇天”这样的宿命思想,这是很好理解的。据统计,在《拟行路难》十八首中,提到宿命论的有六处,借酒浇愁字眼有四处。现在简单取几处进行分析。
《拟行路难》其五很典型:“人生苦多欢乐少,意气敷腴在盛年。且愿得志数相就,床头恒有沽酒钱。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贵贱付皇天。”字里行间渗透的是将生命的价值交付上天判定。功名是作者一生所追逐的,如今各种碰壁后只得发出“付皇天”的叹息。在无可奈何时,只能饮酒作为慰藉,想到床头的买酒钱起码是不缺的,似乎也算是个人生满足的标准了。这其中透露出的,是无比的苦涩和无奈。在社会中,个人力量是何其渺小!也许对于普通人,这样的生活虽平淡也是过得去的,但是对于鲍照,这个对自己有着无比自信、不甘平凡的人来说,这样的说法背后是他无法言明的悲哀,这应该是作者抑郁不得志的另一种宣泄。这两首诗在表面上劝人及时行乐,实则承载了自己的年命之悲,这样的抒情很有破坏性,像先累积一个美好的梦,又毫不留情地打破,似乎获得了一种报复性的快感,更突显悲剧性。
以上两种都是其死亡意识的表现,第一种属于直接表现,通过时间的流逝来直观地表现死亡意识;第二种属于间接表现,通过无力回天的“天命感”来作为其个人价值死亡的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