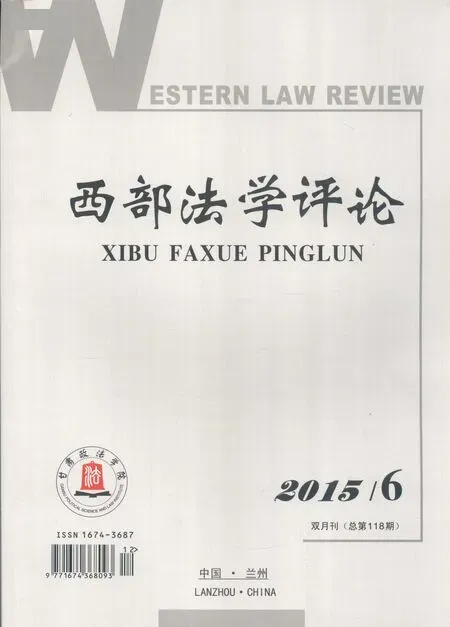十字路口的环境法:回顾过去的25年,展望未来的25年
2015-11-25理查德拉扎勒斯何颖莹
[美]理查德·拉扎勒斯 (著),王 慧,何颖莹 (译)
十字路口的环境法:回顾过去的25年,展望未来的25年
[美]理查德·拉扎勒斯 (著),王 慧,何颖莹 (译)
本文围绕三个主题探讨了环境法与环境立法所经历的变化。第一主题涉及国会与环境法的政治学。第二主题关注法院以及宪法和环境法之间的变化关系。最后,本文比较了今天的环境法人和环境法与25年前的环境法人和环境法所面临的本质上截然不同的挑战。
环境法 国会 法院 宪法 挑战
导言
二十五年,通常看似是一段极长的时间。当我刚从法学院毕业且不足25岁时,情况确实如此。不过,我对时间的理解已有变化,环境法及环绕其左右的争议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
25年前的环境法和今天的环境法存在鲜明的反差,环境法及其立法在过去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借助回顾才能得以彰显。确定无疑的是,国内环境法的法律文本保持惊人的相似。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停滞状态突显了变化到底有多大。
上一代环境法学者通常主要论述环境法中唯一永恒的内容 (动态本质)如何变化。〔1〕See Daniel A.Farber,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a Learning Experience,27LOY.L.A.L.REV.791,791(1994);Daniel P.Selmi,Experimentation and the“New”Environmental Law,27LOY.L.A.L.REV.1061,1062–68(1994).国会通过当时极具建设性的立法程序 (涉及联邦和州层面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法院)不断通过重大的环境法修正案。有人曾担心变化太大,以至于被规制的对象难以进行调整和投资。〔2〕正如我曾写道,环境法的动态特性可能会与将违反环保标准的行为予以刑事化的努力形成张力,因为 “刑法强调确定的规则,而环境法不断变化且寻求根本性的巨变”。Richard J.Lazarus,Meeting the Demands of Integration in the Evolution of Environmental Law:Reforming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aw,83GEO.L.J.2407,2445(1995).不管这种担忧当时是否具有正当性可以置之不理,现在人们的担忧已截然不同:变化太少而不是变化太多。美国国内环境立法的停滞和全球环境立法的活跃形成鲜明对比。〔3〕Tseming Yang &Robert V.Percival,The Emergence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Law,36ECOLOGY L.Q.615,645–49(2009).美国,这个曾广受赞誉的先锋正面临掉队的风险。
本文旨在庆祝密西根大学法学院召开的第25届全国环境法学会年会,并纪念1988年密西根大学法学院举办的协会创立大会。本文围绕三个主题来探讨首次协会会议后环境法与环境立法所经历的变化。第一主题涉及国会与环境法的政治学。第二主题关注法院以及宪法和环境法之间的变化关系。最后,本文比较了今天的环境法人和环境法与25年前的环境法人和环境法所面临的本质上截然不同的挑战。
一、国会与环境政治学
25年前,美国可以自诩它有一个全身投入环境立法的国会。〔4〕Richard J.Lazarus,Congressional Descent:The Demise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Environmental Law,94 GEO.L.J.619,625–29(2006).民主党和共和党齐心协力制定全面的、雄心勃勃的联邦环境法律。在1988年协会创立大会以来,过去十几年见证了联邦环境保护法的激增。这些法律从抱负和潜在影响来说完全称得上是革命性的法律。这些法律旨在颠覆当时流行的人与自然的观念,它们包含严格的新污染控制标准,适用于大气废气排放、〔6〕Clean Air Act,42U.S.C.§§7401,7409(2006).通航水域排污〔7〕Clean Water Act,33U.S.C.§§1251,1311(2006).和土地危险废物倾倒〔8〕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Recovery Act,42U.S.C.§§6901,6924–6925(2006).。

20世纪70年代以来联邦环境法清单〔5〕
而且,联邦环境法不仅仅是污染控制法。它们还包括自然资源管理、保护和保全法律,可用于调整公共土地〔9〕Federal Land Policy and Management Act,43U.S.C.§§1701–1787(2006 &Supp.II 2008).、沿海地带〔10〕Coastal Zone Management Act,16U.S.C.§§1451–1466(2006).、濒危物种〔11〕Endangered Species Act,16U.S.C.§§1531–1544(2006).、渔业〔12〕Magnuson Fishery Conservation Act,16U.S.C.§§1801–1891D(2006).、国家森林〔13〕National Forest Management Act,16U.S.C.§§1600–1614(2006).和煤炭土地〔14〕Surface Mining Control and Reclamation Act o f 1977,30U.S.C.§§1201–79(2006).。这些法律几乎全部都以两党多数投票在两院通过。〔15〕Richard J.Lazarus,The Tragedy of Distrust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Federal Environmental Law,54LAW &CONTEMP.PROBS.311,323(1991).(“20世纪70年代参议院和众议院支持主要联邦环境立法的平均投票比例分别为76:5和331:30。”)
20世纪80年代这种模式也没有势微。恰恰相反,1980年是现代环境法第二个十年的元年。国会在1980年12月通过了两个法律:《综合环境应对补偿、责任法》(CERCLA)〔16〕42U.S.C.§§9601–9675(2006);Pub.L.No.96-510,94Stat.2767(1980).和《阿拉斯加国家利益土地保护法》(ANILCA)〔17〕16U.S.C.§§3101–3233(2006);Pub.L.No.96-487,94Stat.2374(1980).。理论上,国会决不会颁布上述任何一个法律。为什么呢?因为就在法律颁布的几周前,美国诞生了一位新总统——罗纳德·里根,他在竞选时恰恰反对这类联邦法律。〔18〕Hedrick Smith,President Concedes:Republican Gains Victories in All Areas and Vows to Act on Economy,N.Y.TIMES,Nov.5,1980,at A1;Philip Shabecoff,Major Environment Leaders Back Carter Re-election Bid,N.Y.TIMES,Sept.28,1980,§1at 36;Editorial,The Environment and the Stump,N.Y.TIMES,Oct.22,1980,at A30.同样重要的是,民主党失去了参议院多数席位,共和党几周后将在几十年来第一次控制参议院。这是一个无实权的国会。它具有注定要失败的国会的全部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重大立法都不可能通过,因为即将掌管白宫的政党和参议院领导人会极力阻碍其通过,在我们的政治体系下这不难做到。
CERCLA是国会曾颁布的最严厉的污染控制和环境污染责任法之一,ANILCA是最全面的自然资源保护法律之一。〔19〕同前引〔4〕,第626页。但是,这两部法律均顺利通过,因为共和党党魁最终支持它们通过。〔20〕Philip Shabecoff,Compromise on‘Superfund,’N.Y.TIMES,Nov.24,1980,at D9;Joanne Omang,Senate Approves Fund to Clean Up Hazardous Wastes,WASH.POST,Nov.25,1980,at A1;Seth S.King,Compromise Bill to Preserve Alaskan Lands Approved,N.Y.TIMES,Nov.13,1980,at A1.这些党魁包括来自田纳西州的即将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参议员霍华德·贝克,来自佛蒙特州的即将成为参议院环境和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席的参议员罗伯特·斯坦福。〔21〕同前引〔20〕。他们没有阻挠相关立法,而是与民主党领导层和一个无实权的总统达成确保CERCLA和ANILCA通过所必需的妥协。〔22〕同前引〔20〕。参议员斯坦福尤其大力推动危险废物法的通过。〔23〕同前引〔20〕。
接下来的十年,国会制定了更多的法律。〔24〕同前引〔4〕,第626–28页。这些新的法律越来越详细,越来越谐调。〔25〕同前引〔24〕。换句话说,国会做了国会应该做的事:从经验中学习,根据经验修改法律,进而进入一个充满思考、反思和迭代的立法进程。
1988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乔治·布什竞选总统,宣称他将是美国第一个 “环境总统”。〔26〕See John Holusha,Bush Pledges Efforts to Clean Up Air and Water,N.Y.TIMES,Sept.1,1988,at B9;Mark Green,How Dukakis Can Overcome Bush’s‘Slur du Jour,’N.Y.TIMES,Sept.17,1988,§1,at 27.他对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的马萨诸塞州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提出了非常有名的批评,指责他未能完全清理波士顿港水污染。〔27〕Robin Toner,Bush,in Enemy Waters,Says Rival Hindered Cleanup of Boston Harbor,N.Y.TIMES,Sept.2,1988,at A16.当选之后,布什总统至少在他任期的前两年试图实现他的竞选承诺。〔28〕See Philip Shabecoff,E.P.A.Nominee Says He Will Urge Law to Cut Acid Rain,N.Y.TIMES,Feb.1,1989,at A1.他任命威廉·莱利作为环境保护署署长,莱利毫无疑问是该职位的最佳人选。〔29〕﹞同前引〔26〕。白宫与环保署一道支持通过全面的清洁空气法修正案,打破了十三年来该修正案迟迟不得颁布的僵局。〔30〕Keith Schneider,How Clean Air Became Part of the Bottom Line,N.Y.TIMES,Oct.28,1990,§4,at E4.政府密切地与环境保护基金等环保团体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人乔治·米切尔合作。〔31〕Keith Schneider,Ambitious Air Pollution Bill Sent to White House,N.Y.TIMES,Oct.28,1990,§1,at 38.两党间毫无偏见的合作结果便是一部完全修订的联邦空气污染控制法,它因在改善国家空气质量中所取得的显著成效而受到广泛赞誉。〔32〕E.g.,U.S.EPA,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THE CLEAN AIR ACT FROM 1990TO 2020,7-1to 7-10(2011).
1990年,没有人会想到 《清洁空气法》实际上是国会最后的努力。基于1990年的成功,人们有理由相信大的趋势将是国会加大参与力度和两党不断减少分歧。毕竟,十三年的僵局已被成功打破。二十多年后,我们才发现 《清洁空气法》是国会两党最后一次合作。当然,那之后也有过一些插曲式的立法时刻,但再也没有1990年时的立法规模,也没有前二十年的立法态势。如果说第一个二十年国会在环境立法中的作用明显 “上升”,最近二十年以来则可以称之为明显 “下降”。〔33〕同前引〔4〕,第629–32页。
国会山或许外表依然,但内在迥异。它不是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或是1990年的国会,而是一个基本放弃了环境法立法职责的立法机构。这并不是因为现在对新法和修正案的需要减少了。如今,新信息和新挑战需要法律关注。我们身边的整个世界正发生多维度的变化:经济上的变化,政治上的变化,以及当下与气候变化相随的生态上的变化。
然而,放弃职责会付出巨大代价。虽然缺乏必要的法律修改和补充,行政机构却不得不解决当下的问题而非过去的问题。但是,当受限于那些为了应对过去的问题而制定的法律时,行政机构势必被迫在现行立法授权框架内活动,有时甚至会超越授权,进而引发旷日持久,扰人心神并且往往成功的诉讼。例如,环保署如今正努力在现行的 《清洁空气法》的条款内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一些问题容易解决,譬如温室气体是否是该法所规定的空气污染物。〔34〕Massachusetts v.EPA,549U.S.497,528–32(2007).有些问题则如行政机构所说的那样非常困难,譬如针对本法文本所包含的所有温室气体源适用重大退化预防程序和第六章规定的许可程序。〔35〕Prevention of Significant Deterioration and Title V Greenhouse Gas Tailoring Rule,75Fed.Reg.31513,31516(June 3,2010)(法典位置编号为40C.F.R.§§51–52,70–71)(描述了EPA在有关温室气体的规章制定中对 “行政必要”原则的依赖,它授权环保署以规避本不可能出现的行政后果的方式来实施法定要求。”)。2012年6月26日,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以缺乏起诉资格为由驳回了工业界对这一规定的挑战。See Coalition for Responsible Regulation v.EPA,684F.3d102(D.C.Cir.2012).
更糟糕的是,最近国会唯一采取的行动是通过拨款法案:综合预算法案可以有成千上万页。人们几乎没有机会阅读这一法案,通常故意为之,它能被隐藏在各种附文中,更不用说引发有意义的辩论和讨论了。这是最糟的立法。附文本身总是代表短期的、未经深思的利益,而非长远眼光和专业知识。〔36〕同前引〔4〕,第638–48页。
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国会1995年讨论和颁布的救助林业工人附文〔37〕Pub.L.No.104–19,§§2001–2002,109Stat.194,240–47(1995).。该紧急拨款法案旨在为克拉荷马城轰炸中的受害者提供基金。〔38〕同前引〔37〕。但附文插入后,投票支持帮助轰炸受害者的人同时也得支持在太平洋西北地区的原始森林中进行森林采伐。〔39〕同前引〔37〕。作为法律的附文产生如下法律效果:推翻法院就森林砍伐行为违反 《国家环境政策法》和 《濒危物种法》而颁发的禁令。〔40〕同前引〔37〕,at§2001(c)(9);同前引〔4〕,第643页。
但这就是国会近来立法努力的始末及趋势。因此,国会山近来的大多数努力似乎旨在阻止国会做欠考虑的事,而不是通过国家需要的新法律,这与20世纪80年代末第一届全国环境法学会协会在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承办时大相径庭。
二、法院、宪法和环境法之间的变化关系
二十五年前,美国的各级法院因为在促进和发展国家的环保法中发挥的积极巨大、建设性的作用而广受爱戴。他们早期的判决通过将新的、扩张的理论用于污染控制法,助力了当时全国上下出现的立法努力。法院把目光投向看似极为较为陈旧的法律,如1899年 《河流和港口法》〔41〕33U.S.C.§403(2006);30Stat.1151(1899).(该法导致 〈清洁水法〉〔42〕Federal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Act Amendments of 1972,Pub.L.No.92-500,86Stat.816(1972);See Oliver A.Houck,The Water,the Trees,and the Land:Three Nearly Forgotten Cases that Changed the American Landscape,70TUL.L.REV.2279,2282–91(1996).的诞生)和1897年 《组织管理法》〔43〕16U.S.C.§§473–482(2006).(该法创立了林务局)〔44〕30Stat.11,35(1897).,后者几乎在八十年后推动 《国家森林管理法》〔45〕Pub.L.No.94-588,90Stat.2949(1976);see Houck,supra note 42,at 2291–2301.的通过。法院不仅推动了这些新法律,而且当时还十分欢迎这些新法。〔46〕例如,Richard J.Lazarus,Judging Environmental Law,18TUL.ENVTL L.J.201,205–06,208–11(2004).一些法官把保障这些法律视为他们的司法职责。〔47〕例如,同上注。
没有法官比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史盖利·莱特法官更好地诠释了这一点。〔48〕同前引〔46〕。史盖利·莱特特法官从位于新奥尔良的上诉法院来到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49〕Peter Braestrup,Wright is Named to Appeals Court,N.Y.TIMES,Dec.16,1961,at 18.讽刺的是,他不是因为自己卓越的工作获得提拔。〔50〕同前引〔49〕,参见Jurist in Racial Dispute:James Skelly Wright,N.Y.TIMES,Nov.16,1960,at 23;同时参见同前引〔46〕,第204页。他工作变动的真实原因是,因为他的裁决有人试图将他赶出司法界。〔51〕Braestrup,同前引〔49〕;Jurist in Racial Dispute,同前引〔50〕。或至少把他赶出新奥尔良、路易斯安那州和南方。〔52〕Braestrup,同前引〔49〕;Jurist in Racial Dispute,同前引〔50〕。
莱特冒犯了什么?通过命令废除新奥尔良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以实施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中的判决。〔53〕Braestrup,同前引〔50〕;Jurist in Racial Dispute,前注50;See Bill Monroe,In Memoriam:J Skelly Wright,102HARV.L.REV.361,363–64,371–72(1988).据说南部民主党参议员告诉当时的总统约翰·F·肯尼迪,他们希望莱特法官走人。〔54〕See David Halberstam,Judge Is Opposed by Senator Long,N.Y.TIMES,June 1,1961,at 22.所以,总统肯尼迪通过任命法官莱特到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任职进行妥协。〔55〕同前引〔46〕,第204页;Monroe,同前引〔53〕,第371–72页.〔56〕同前引〔46〕,第204–05页.
一到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莱特法官便感知公民权利法律和环境法律之间存在联系:需要保护那些未出场的人,他们缺乏政治和经济力量。〔〕在公民权利语境下,这意味保护遭受了数十年歧视和隔离的少数民族,虽然大部分歧视和隔离曾得到法律的支持。〔57〕同前引〔53〕,第371–72页.现在,在地处首府的联邦上诉法院所审理的环保案件中,莱特法官自然将他的关注对象扩大那些缺乏政治和经济力量的人 (特别是后代人),他们正是环境保护法试图保护之人。〔58〕同前引〔46〕,第204–05页.
莱特法官最著名的有关法院在联邦环境法中的作用的表述呈现在1971年他在卡尔弗特·克里夫斯协调委员会公司诉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一案中做出的裁决意见。〔59〕449F.2d1109(D.C.Cir.1971).在把刚出台的 《国家环境政策法》适用于原子能委员会的许可程序时,莱特法官的意见从字面上改变了该法,以至于看似远远超出起草该法的议员 (斯库普·杰克逊)和签署该法的总统 (理查德·尼克松)的个人预期。〔60〕A.Dan Tarlock,The Story of Calvert Cliffs:A Court Construes 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 to Create a Powerful Cause of Action,in ENVIRONMENTAL LAW STORIES 77,82–83(Richard J.Lazarus &Oliver A.Houck eds.,2005).卡尔弗特·克里夫斯案裁决书的第一段开门见山表明了莱特法官的意图:
这些案子只是可以预见的大量新型诉讼 (这种诉讼寻求司法帮助来保护自然环境)的开端。几个最近出台的法规试图让政府承担责任来控制物质 “生产”这台破坏性引擎。但这一立法的承诺能否成为现实还有待观察。其中司法的作用不容忽视……我们的职责,简而言之,就是确保那在国会大厅里被预示的重要立法目的,不会在大量的联邦官僚机构走廊里丢失或被误导。〔61〕Calvert Cliffs,449F.2dat 1111.
仅仅思考该意见的第一段的第一句吧。在描述 《国家环境政策法》这类法律时,莱特法官提到 “大量诉讼”“可以预见”。〔62〕同前引〔61〕。然而,大量诉讼不应该是一种 “预见”,而是一种 “威胁”。但对莱特法官并非如此。正如裁决意见进一步所披露的那样,莱特法官所设想 “司法的作用”便是确保新的环境法律中的 “重要的政策”得到实现。〔63〕同前引〔61〕。他清楚地知道这些政策会在 “巨大的联邦官僚机构走廊”中被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加以 “丢失”或 “误导”,因为他已亲眼目睹民权法在南方和州政府机构中的遭遇。〔64〕同前引〔61〕。此外,如莱特法官所言,“司法的作用”便是确保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65〕同前引〔61〕。
这是司法能动主义?绝对不假。对司法武器强硬、有力的呼唤可能是更贴切的描述。对莱特法官和其他一些人来说,环境法几乎带有准宪法的维度。虽然法院从未承认环境保护属于联邦宪法权范畴,但他们显然认为环境保护问题应得到特别的司法保护,其价值在司法衡平中不断提升。
这一司法态度催生了其他判决。有些裁决扩大了依据公民诉讼提起环境诉讼的原告的范围。〔66〕例如,参见United States v.Students Challenging Agency Regulatory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412U.S.669(1973).(支持环境原告具有宪法第三条所规定的起诉资格,尽管因果关系的指控被减弱。)大量的裁决支持更有力的环境保护,比如,在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下根据 《清洁空气法》创设严重恶化预防计划。〔67〕Sierra Club v.Ruckelshaus,344F.Supp.253(D.D.C.),aff’d,No.72-1528(D.C.Cir.1983),aff’d by an equally divided Court,Fri v.Sierra Club,412U.S.541(1973).类似地,法院支持普遍使用 《联邦超级基金法》所规定的连带责任。〔68〕U.S.v.Chem-Dyne,572F.Supp.802,809–11(1983).当时标志性的事件是,1986年最高法院以9比0在美国诉河滨湾景案中裁定支持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和环境保护局对可航水域概念的扩张解释,进而拓宽了 《联邦清洁水法》的适用地域范围。〔69〕474U.S.121,122(1985).法院支持这些机构对立法语言意图使用功能方法来解释,因为这种解释方法是解决国会已认定的水污染问题所必需的,尽管这种方法对国会规定的 “可航水域”这一术语的书面含义重视不够。〔70〕同前引〔69〕,第132–35页。
但在全国环境法学会协会首次会议结束短短几个月后,在联邦法院工作了四十年的莱特法官去世了。〔71〕Marjorie Hunter,Judge J.Skelly Wright,Segregation Foe,Dies at 77,N.Y.TIMES,Aug.8,1988,at D10.同时,在相当程度上,环境保护权利应该得到特别的司法保护的观点也随他而逝了。25年前,一个全然不同的新的司法观念正在酝酿并抵达国家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大楼也许外表依然,但内在迥异。这一差异反映在一位新的最高法院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法官的司法哲学中,他在河滨湾景案做出裁决后的短短几个月后以及全国环境法学会协会首届会议召开18个月前升迁到联邦最高法院。〔72〕Stuart Taylor,Jr.,Rehnquist and Scalia Take Their Places on Court,N.Y.TIMES,Sept.27,1986,§1,at 8.
在斯卡利亚法官的批准听证会上,没有人关注他对环境法的态度。那并不是因为没有相关记录。斯卡利亚法官在很多方面是个史盖利·莱特的反对者,并以此为豪。无论如何他都不是一个低调的提名者。1983年,即在他1986年9月宣誓就任最高法院法官的三年前,时任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的斯卡利亚发表法律评论文章,明确反对莱特法官的司法哲学。〔73〕Antonin Scalia,The Doctrine of Standing as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17SUFFOLK L.REV.881(1983).在为提高环境诉讼原告的司法壁垒辩护时,斯卡利亚法官不仅批评莱特法官有关保护自然环境是司法新的功能的声明。他嘲笑莱特法官。斯卡利亚法官明确将卡尔弗特·克里夫斯案视为 “司法与环保诉讼间长期的不正当关系。”〔74〕同前引〔73〕,第884–85页。当被问到他的观点是否意味将出现莱特法官所指的 “在国会大厅里预示的重要立法目的,会不会在巨大的联邦官僚机构走廊里丢失或被误导”时,他进一步承认自己的观点。〔75〕同前引〔73〕,第897页。他没有拐弯抹角,他强硬地回应到:“当然会,而且还是一件好事。”〔76〕同前引〔75〕。参议院以98比0的投票确认斯卡利亚的大法官身份。〔77〕132CONG.REC.23,813(1986).整个听证程序中没有一次提到环境法。〔78〕同前引〔77〕,第23页,第803–13页;See also Nomination of Judge Antonin Scalia,To Be Associate Justice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S.Comm.on the Judiciary,99th Cong.(1986).关于斯卡利亚提名的委员会报告只有76字。〔79〕Linda Greenhouse,Reporter’s Notebook:Senators vs.Rehnquist,N.Y.TIMES,Sept.18,1986,at A24.
一到最高法院,斯卡利亚法官便颠覆了宪法和环境的关系。在环境法发展的早期,许多人已经开始提出环境保护是否已经或应该是一项宪法权利这样的疑问。斯卡利亚法官在最高法院内就20世纪70、80年代严格的环保法律是否明智带来一股新的质疑主义,他通过推动各种质疑环境法及其私人执法的合宪性的法律辩论为怀疑主义开道。在诺拉诉加利福尼亚沿海委员会案〔80〕483U.S.825(1987).和卢卡斯诉南卡罗来纳海岸委员会案〔81〕505U.S.1003(1992).中,争议焦点是环保法律是否构成对私人财产未做合理补偿的违宪征收。在鲁建诉国家野生动物联盟案〔82〕497U.S.871(1990).和鲁建诉野生动物守护者案〔83〕504U.S.555(1992).中,诉求是环境公民诉讼中的原告缺乏宪法第3条规定的起诉资格。在拉帕诺斯诉美国案中,斯卡利亚法官主张狭义解释 《清洁水法案》,一定程度是为了回应他对国会贸易条款权限的狭义观点。〔84〕547U.S.715(2006).尤其是最后这个判决,它与法院在河边湾景案中的一致意见简直是天壤之别,河边湾景案对 《清洁水法案》适用地域范围的观点本有拓展的潜能,且该案仅仅是斯卡利亚法官进入最高院几个月前做出的。〔85〕474U.S.121,132–35(1985).
三、环境法律的挑战:当下与25年前的比较
现在是环境法和环境保护的艰难时期。最近,我们目睹了国家遭遇的最严重的石油泄漏事件——2010年春季至夏季英国石油公司深水地平线墨西哥湾石油泄漏。〔86〕See NAT’L COMM’N ON THE BP DEEPWATER HORIZON OIL SPILL AND OFFSHORE DRILLING,DEEP WATER:THE GULF OIL DISASTER AND THE FUTURE OF OFFSHORE DRILLING 173–78(2011).而且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潜在的环境灾难:全球气候变化。然而,在著此文之际,即海湾石油泄漏两年多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宣布有 “明确”的证据 表明全球变暖正在发生且大部分的变暖“很有可能”是大气中人为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导致的声明的五年后,〔87〕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CLIMATE CHANGE 2007:SYNTHESIS REPORT 30,37(2007).国会还没有颁布任何有显著意义的立法来预防未来的石油泄漏或解决全球气候变化因或果。
可以肯定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环境立法变得越来越难,但仍然有一个不可否认的公理:没有任何事情能像环境灾难一样可以打破一个立法僵局。这样的例子在现代环境法的历史中比比皆是。20世纪60年代,雷切尔·卡森的 《寂静的春天》所发出的可怕警告促成了杀虫剂的管制以及20世纪70年代第一波联邦环境法的出现。〔88〕RICHARD J.LAZARUS,THE MAKING OF ENVIRONMENTAL LAW 58–60(2004).1969年凯霍加河的大火和圣芭芭拉石油泄漏,成为通过1972年 《联邦水污染控制法》的战斗口号。〔89〕同前引〔88〕,第59页;See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Legislation:Part 1;Hearings on S.75,S.192,S.280,S.281,S.523,S.573,S.601,S.679,S.927,S.1011,S.1012,S.1013,S.1014,S.1015and S.1017 Before the Subcomm.on Air and Water Pollution of the S.Comm.on Pub.Works,92nd Cong.374(1971)(statement of Rep.Charles A.Vanik);see also 118CONG.REC.10,218(1972).1978年核电站堆芯熔毁的骇人灾难触发了联邦核能管制体制的改革。〔90〕例如,参见Nuclear Regulatory Comm.—The Rogovin Rep.:Hearing Before Subcomm.on Env’t,Energy,and Natural Res.of the H.Comm.on Gov’t Operations,96th Cong.(1980).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对拉夫运河和德拉姆谷等有害垃圾场的广泛宣传,促使国会在1980年颁布CERCLA。〔91〕同前引〔88〕,第108页;参见Pub.L.No.96-510,94Stat.2767(1980);see also 126CONG.REC.26337,26340,26347(1980);see also Hazardous and Toxic Waste Disposal:Administration Testimony on S.1480to the Subcomm.on Envtl.Pollution and Resource Prot.of the S.Comm.on Env’t and Pub.Works,96th Cong.(1979).1989年,“埃克森·瓦尔迪兹”号油轮使我们有了1990年 《石油泄漏污染法》。〔92〕See S.REP.NO.101-99(1989).这些法律曾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被提议、讨论和考虑过,最后在国会休眠长达十年,因为它们得到法律通过所需的政治动力和支持。〔93〕See Tanker Safety in Alaska:Part 3;Hearings on S.182,S.568,S.682,S.715,and S.898Before the S.Comm.On Commerce,Sci.,and Transp.,95th Cong.(1977);See also Comprehensive Oil Pollution Liab.and Comp.Act:Hearing on H.R.85Before the Subcomm.on Water Res.of the H.Comm.on Pub.Works and Transp.,96th Cong.(1979);see also Leo H.Carney,For Environmentalists,The Battle Goes On,N.Y.TIMES,Jan.4,1981,§11,at NJ22.然而,在阿拉斯加原油泄漏几个月后,国会通过了这些姗姗来迟的法律。〔94〕136CONG.REC.21,726,22,299(1990);Philip Shabecoff,Largest U.S.Tanker Spill Spews 270,000 Barrels of Oil Off Alaska,N.Y.TIMES,Mar.25,1989,§1,at 1.
但到了2010年,甚至一场灾难都不能促成社会所需的法律。墨西哥湾石油泄漏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墨西哥湾深处的马孔多油井泄露,深水地平线石油钻机沉没,钻井平台上的11位工人的惨痛丧生,溢出的数百万加仑的石油流入这个国家乃至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生态系统——墨西哥海湾,在这里,墨西哥湾海岸线正摆出像海绵一样吸油的态势,至关重要的环境和经济资源可能遭受长期的破坏。〔95〕NAT’L COMM’N ON THE BP DEEPWATER HORIZON OIL SPILL AND OFFSHORE DRILLING,supra note 86,at 173–78.
墨西哥湾石油泄漏后的两年多国会制定了什么法律?1989年,国会花了一年时间通过了全面的石油泄漏立法。〔96〕Schneider,同前引〔30〕,第4页。两年多后的现在,这个国家依然在等待。国会无所作为,没有为政府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帮助它们更加仔细规划深水钻探作业,实施价格有效的政府监管和风险管理,也未向内务部、海岸警卫队、美国环境保护暑、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提供他们在泄露发生时能及时做出应对所需要的资源。
这些都是容易实现的目标,并且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石油公司,海湾所在的州,这些州里的商业利益和公民个人。没有输家只有赢家。但我们没有看到必要的法律得以通过,而是看到持久的立法僵局。〔97〕Editorial,The Big Spill,Two Years Later,N.Y.TIMES,Apr.18,2012,at A26.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包含在修法议案中的法律是这样一种法律:抵触现有的保障措施,在缺乏必要的监督下加速钻井平台作业,这显然提高而不是减少泄漏发生的风险。〔98〕See JONATHAN L.RAMSEUR,CONG.RESEARCH SERV.,R41684,Summary of OIL SPILL LEGISLATION IN THE 112TH CONGRESS(2011).国会颁布的唯一立法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在州和联邦政府之间 (它们强烈要求获得自己应得的份额)瓜分泄漏带来的战利品,BP因为造成泄漏不得不支付数十亿美元的民事处罚金。〔99〕国会在2012年6月29日通过了众议院4348号决议会议报告,奥巴马总统在2012年7月6日签署了法案。参见Pub.L.No.112-141,§§1601–1608。新的法律创建了海湾海岸恢复基金,由2010年的海湾石油泄漏中百分之八十的民事处罚,罚款和其他理赔资助。同上注。毫无疑问,这些金钱确能带来一些益处,但是没有一项好处可以根本解决泄漏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漏油事件两周年纪念日之际,总统领导的石油泄漏委员会,基于国会立法职责的完全缺位 (未能用有效的立法预防将来发生石油泄漏)而给它 “D”级评分。〔100〕OIL SPILL COMMISSION ACTION,ASSESSING PROGRESS:IMPLEMENTING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NATIONAL OIL SPILL COMMISSION 2(2012).(给国会在“提高海上钻探的安全性和改善国家应对可能出现的漏油的能力的努力中打了 “D”级。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国会没有为这些努力提供领导或支持。”)
如果美国国会不能解决一些如石油钻井泄露一样简单的问题,又怎能期望国会来解决21世纪最重要的环境问题:气候变化。正如我 (和其他人)之前所描述的那样,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立法噩梦,一个 “超级难办”的问题。〔101〕Richard J.Lazarus,Super Wicked Problems and Climate Change—Restraining the Present to Liberate the Future,94CORNELL L.REV.1153,1160(2009).问题的根源是气候变化的原因和结果在时间和空间上较为分散,在任一维度都没有对应的可信赖的立法机构。〔102〕同前引〔101〕,第1166–87页。全球气候变化这个问题,关注短期利益的民选官员不关心,关注特定空间利益的政府也不关心。而且,许多美国人的短期思维得以助长。〔103〕同前引〔102〕。
然而,近在2009年,制定国家综合性的气候变化立法在政治上确定无疑。〔104〕同前引〔101〕,第1155–56页。国家似乎已对这一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立法时刻做好准备。〔105〕同前引〔104〕。所有要素似乎同时到位。作为曾在竞选时提到该议题的新当选的总统,在他就职一周内便提到此类立法的迫切需要。〔106〕Barack Hussein Obama,Inaugural Address(Jan.20,2009),available at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president-barack-obamas-inaugural-address.新总统相应地在行政机构领导职位上任命了那些旨在将推动气候变化立法通过作为行政机构首要任务的提名人:环保署署长莉萨·杰克逊〔107〕John M.Broder,Cabinet Choices Answer Questions from Senators,N.Y.TIMES,Jan.15,2009,at A22.、能源秘书朱棣文〔108〕David M.Herszenhorn and Helene Cooper,2Confirmed for Economy and for National Security,N.Y.TIMES,Jan.21,2009,at P14.、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的行政主管简·卢布琴科〔109〕Cornelia Dean,NOAA Chief Believes in Science as Social Contract,N.Y.TIMES,Mar.24,2009,at D2.、白宫科学顾问约翰·霍尔德伦〔110〕Edward Wong &Andrew C.Revkin,Experts in U.S.and China See a Chance for Cooperation Against Climate Change,N.Y.TIMES,Feb.5,2009,at A14.、环境质量委员会主席南希萨特利〔111〕同前引〔107〕,第A22.,当然还有白宫能源和气候变化办公室主任布朗尼·卡罗尔〔112〕John M.Broder,E.P.A.Pick Vows to Put Science First,NYTIMES.COM(Jan.14,2009),http://www.nytimes.com/2009/01/15/us/politics/15webjackson.html?_r=1.。同样重要的是,国会山也蓄势待发。各个关键点上均已到位的领袖。在参议院里,有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113〕‘Obama’s People’:A Who’s Who,N.Y.TIMES,Jan.18,2009,at MM53.、环境和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席芭芭拉·鲍克斯〔114〕S.18,111th Cong.(2009).和能源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主席杰夫·宾格曼。〔115〕同前引〔114〕。在众议院,有发言人南希佩罗西〔116〕H.R.2,111th Cong.(2009).、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主席亨利·韦克斯曼。〔117〕H.R.8,111th Cong.(2009).议员韦克斯曼特别强调了推动气候立法动力的严肃性。〔118〕Lyndsey Layton,Californians Shape Up as Force on Environmental Policy,WASH.POST,Dec.29,2008,at A3.来自密歇根的约翰·丁格尔基于他的资历应可担任主席,长期以来他一直是议会中最有权势的成员之一,确实是一个不易挑战的人。〔119〕同前引〔118〕。但韦克斯曼却在主席一职上挑战丁格尔且获胜,因为很多民主党人担心丁格尔先生不会全力支持气候变化立法,因为他和汽车行业长期存在关系。〔120〕同前引〔118〕。
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支持并不局限于白宫和国会里的民主党,抑或环保人士。〔121〕Andrew Revkin,Climate,N.Y.TIMES,Oct.26,2008,§Week in Review,at 6.(描述麦凯恩参议员支持2003年的气候变化立法。)它得到两党的支持。〔122〕同前引〔121〕。共和党领袖也强调全国立法的必要性,这包括2008年大选中共和党总统提名人〔123〕同前引〔121〕。以及2012年大选时共和党总统提名人中的两位突出候选人:罗姆尼和纽特·金里奇。〔124〕Ezra Klein,Obama,Romney and Gingrich Share A Lot—Except in Courage,WASH.POST,Nov.29,2011,at A8;Dan Eggen,‘08Shift on Energy Was Boon to Gingrich Group,WASH.POST,Dec.29 2011,at A4.工业领袖同样站出来支持制定综合性的气候变化法。〔125〕Steve Mufson,Push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es Would Put a Price on Emitting Pollution,WASH.POST,Mar.13,2009,at D1.(描述在美国气候行动合作中行业领导者对重要的国家气候变化立法的支持。)
但是白宫和国会有可以展示的立法成就吗?没有。或者比什么也没有更糟的是。国家气候变化立法问题已经成为政治毒药。没有人会触碰全球气候变化这个议题。工业领袖们背弃了他们早期作出的承诺。曾表露支持立场的共和党领袖现在也否定了他们之前的立场。〔126〕E.g.,Klein,前注124,第A8;Eggen,前注124,第A4.
即使是在2008年竞选时提及这个问题,在2009年和2010年明确指出指出该问题明显具有紧迫性的奥巴马总统,在任期的后两年回避了这个问题。和他总统任期一开始至2011年的说辞形成鲜明对比。这是总统2009年上台一个星期后说的:“气候变化的长期威胁加剧了我们的国家和经济安全所面临的紧急危险,如果不加以控制,可能导致暴力冲突,可怕的风暴,萎缩的海岸线,和不可逆转的灾难。这些都是美国人众所周知的事实”。〔127〕Remarks o f the President o f the United States on Energy,Public Papers o f the President(Jan.26,2009).
但后来,即便是那个内心确信危险存在紧迫性和威胁性的灾难具有不可逆性的总统,嘴上也不再提及气候变化或全球变暖。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的演讲和讲话中,说了63次 “全球气候变化”或 “全球变暖”。在2010年他说了73次。2011年他有说出这些词次数是多少呢?一次。〔128〕2009、2010和2011的统计数据都是基于WESTLAW搜索中这三年“总统文件”的档案,搜索“全球变暖”或 “气候变化”两词。这个档案包含总统发表的所有评论和演讲。总统唯一提到气候变化是在2011年1月19日和中国国家主席的一个联合新闻发布会上。〔129〕Press Conference with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Hu o 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Jan.19,2011).而且,那是为了回应中国国家主席提到气候变化可作为中美合作的一个领域。〔130〕同前引〔129〕。1月19日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1年一次都未提及气候变化。全球气候变化成了伏地魔:一种总统至少在连任前都不敢提到的威胁。
然而,为了回应中国主席而促使美国总统发出那些很快从他的公共词汇中消失的词语这一事实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过去二十五年国际和全球环境法律的出现。这段时间内,国外环境法律的发展可能大体相当于20世纪70、80年代的美国国内环境法律的发展。〔131〕例如,参见Yang &Percival,supra note 3,第617–19页,第628–30页,第637页。世界范围内,环境法有了一次爆发。而且,正当美国让出通过新法或新技术来扮演气候变化领导者的角色时,中国或许恰恰开始推动解决全球气候变化的重大新技术和新法律,这包括碳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132〕See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China’s Policies and Actions for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Nov.2011,http://www.gov.cn/english/official/2011-11/22/content_2000272.htm(last visited June 26,2012).
当今的环境法律人,必须将目光远远伸出我们的国界。只专注于美国法律无法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在现在的立法僵局下尤其如此。只关注我们领土管辖内的活动产生的风险无法使墨西哥湾免于深水钻井的风险,也无法确保在如此苛刻、难以接近的环境下不断增多的钻井活动不给给北极带来环境风险。气候变化,就其本质而言,显然只有在前所未有的国际协调与合作下才能有效地解决。古巴和墨西哥对墨西哥湾内以及俄罗斯对北极境内的近海石油钻探活动进行监管的必要性毫不低于美国政府施加的监管。
结语
二十五年前,包括我在内的参加2012年3月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全国环境法学会协会年会的每位发言人具有不同的身份。我当时是美国副检察长助理,处理斯卡利亚法官刚加入的最高法院所受理的环境案件。路易斯·希弗,现在的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总法律顾问,当时是全国公共广播的总法律顾问,几年后成为美国司法部环境和自然资源部门历史上任职最长的副检察长。鲍勃·珀西瓦尔教授,为拜伦·怀特法官做助理后在美国环保基金工作了六年,当时刚刚开始他在马里兰大学的学术生涯,在那里他创建了一个全美优秀的环境法项目。霍莉·多雷姆斯教授,获得康奈尔大学植物学博士学位后,成为了一个朝着向全国领先的环境法学者前进的一年级法律系学生。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过去25年在环境法的躬身耕耘是收获巨大、令人振奋、极具挑战性的。可以实践、参与和教授这个国家真正伟大和建设性的法律革命是多么大的荣幸!下一代环境法人所面临的挑战同样意义重大或充满回报。环境法人已经做了很多,但还有更多的事情等待环境法人去做。风险之大,令人不安。不独美国,全世界皆然。
理查德·拉扎勒斯(Richard J.Lazarus),哈佛大学法学院霍华德与凱瑟琳阿贝尔法学教授(Howard and Katherine Aibel Professor of Law);王慧,法学博士,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何颖莹,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本文受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项目编号:14PJC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