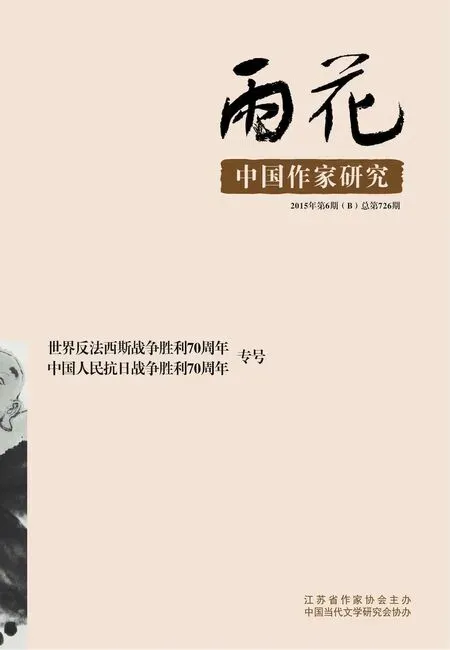墨即是色
——李敬泽的批评世界
2015-11-18杨晓帆
■杨晓帆
读《致理想读者》,竟会想到“色情”与“情色”之分别,当越来越多的文学批评陶醉于华丽辞藻的意淫,或是以供给“硬货”为名堆砌起“干巴巴”的术语高见时,李敬泽像一位真正的情色大师,重新定义着批评家笔下的“活色生香”。
“感觉”是第一位的。关于作家作品的洞见,首先来源于批评家最原初的感官体验,甚至连表达方式本身也是基于感官的修辞。李敬泽的批评,常常像是与作家两三人饮酒唱诗,真知灼见固然重要,但此时更看重氛围与格调。就像评毕飞宇一文,题为《声音、恐惧与历史》。当各类文学批评、学术研究从“权力”、“微观政治”等大词忙不可遏地给毕飞宇带上“福柯”面具时,李敬泽只是有点漫不经心地说,毕飞宇的语言是“有声音的”,“有肉的”,“他是人类生活的力学家”;而这种深入权力毛细血管的写作方式究竟是什么,李敬泽则用莫言做比,“莫言是一个超级动物,小动物的细微感触不在他的世界尺度之内,即使是小动物在他笔下也像是庞然大物”。这样的批评恐怕难以提供精准的意见和知识,但它提供了一个触媒,让读者重新在批评文字中体会毕飞宇小说中让人后背发凉的故事,理解莫言小说的恣意汪洋。而李敬泽自己也像一个有着细微感官的小动物,以身体的方式去阅读,以身体的方式把他所看到文学世界里细小的东西呈现出来。于是,作家或文本不再是解剖台上的死尸或帆布上的一堆静物,他们和批评家一样,是对世界敞开的感官动物,时刻准备去捕捉万物花开的一刹那。
这种包裹在鲜活感兴体验中的文学观,是非常现代的。尽管受学院体制规训的我们,熟稔于伊格尔顿、福柯,谈现代性,谈后学,看起来在使用一套现代知识,但关于文学的理解却可能是非常传统陈旧的。相反,《致理想读者》里从未专门论述过“现代”,但“个人”、“内面”等关键词却在批评与作品相遇时自然而然地随意赋形。比如李敬泽对中短篇小说的格外关注。当大多数批评认为中国文学的失利在于缺乏好长篇时,李敬泽明确指出肇始于18、19世纪“现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已经过时了。这种判断是对文学体制寄居于时代变动的理论把握,小说篇幅不仅仅是写作者能力的问题,在丧失总体性的世界图景中,长篇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只能是反经典的,而中短篇才是对应我们时代之“现代感”的最恰当形式。
“现代感”的核心是语言和人的内在性。《致理想读者》的第一篇《1976年后的短篇小说:脉络辨》格外精彩,它几乎改写了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基本判断。在李敬泽看来,新时期小说的起点不是思想解放的《班主任》,应当是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因为“我”的声音终于被从宏大历史和人群中区别出来。如果说这一判断还只是将80年代中期“文学主体性”、“文学向内转”的文学史叙述往前推,那么在对现代派、先锋小说等85新潮的认识上,李敬泽则给出了更加大胆激进的解释。有别于将一切归因于“语言论转向”看似深刻实属偷懒的知识概述,李敬泽仍旧从挖掘作家的感性表达开始——“马原在本质上隐于密室,另一些人则桀骜不驯地走在大街上——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中,主人公一直在大街上晃荡,随时准备接受冷眼和白眼,随时准备还以冷眼和白眼。”当马原自己恐怕都已经被“叙事圈套”迷惑得洋洋自得时,李敬泽竟想到用“密室”来重新定位马原的写作状态。“隐于密室”或“走上大街”,这无疑是80年代中期人们面对崭新生活世界时最为突出的体验方式,而先锋派的叙事实验或现代派的语言狂化,都只是这些非常个人化的身体性经验在语言层面的外化。于是,“它的声音自怜自赏,有一种北京的、精神贵族般的优越感”,“在1985年,这个声音具有震撼性力量,它表达了‘颓’的、不求上进的姿态”,“相应地,一个新的语言区域被打开:语言从口头、从边缘、从被禁止和遗忘在书面之外的地方解放出来,语言可以不得体,语言不仅是为了说得对,还可以为了说得爽……”这些描述让人联想到本雅明笔下的波德莱尔和巴黎,波德莱尔笔下的浪荡子和黑夜,关于“现代性”的理论洞察一定只发生在个体生命与语言或现实世界发生关联的时刻,而李敬泽的批评首先完成的就是现场还原。这种观察进一步丰富了作为脉络起点的张承志的“我”。“我”不再仅仅是“前三十年”当代文学中“我们”的对立面,而是在新的日常生活体验中、在新的城市空间中,要求以新的方式完成自我表达的内在世界。这个脉络自然走向90年代的个人化、身体化写作,它提示我们去思考,看似毫不搭界的马原的“密室”与陈染们的“浴缸”,是否存在着关于“我是谁”的共同疑问?而在语言层面,正如李敬泽对朱文的精彩断语——“提高了汉语的力比多水平”,无论是莫言“沉溺感官”的语言,池莉小说中“炙热的、肉体的”气息,还是90年代小说中“强壮蛮横的身体”,李敬泽用这些力比多扩张的重复性修辞,让我们不仅认识到、也感受到了80年代以来这股文学中“内在性力量”的生长。
这个脉络确实在80年代展开了,但这种展开是不是真的被文学史家、批评家、作家和理想读者把握到了呢?所谓更具内在性力量的文学,难道就是80年代以来被各种理论知识充实绑定了的那个“纯文学”观么?“纯文学”必须因为基于对语言、形式、技术的关注,而承担使文学丧失现实穿透力的责任么?当记者询问李敬泽如何看待读图时代里文学影响力的衰落时,李敬泽显示出他对此类问题的不屑一顾,似乎这根本不是他所认为文学遭遇的问题。什么是理想读者,什么是理想文学?如果参照雷蒙德·威廉斯关于“文化”的三层定义,我们今天很多文学研究者都致力于在文献意义上拣选那些在数十年后仍然应当被收藏和模仿的“典范性文本”,一般读者则在社会生活的文化层面从阅读中获得情感净化,而李敬泽对“理想读者”和“理想文学”的要求显然更高。文学生活不是记忆经典,不是心灵鸡汤,文学不仅仅是一堆纸质书籍和修辞术,理想文学追求的是文学内部的精神气质,是格调,是对于人类完善过程具有绝对和普遍价值的文化。批评家作为理想读者,首先要完成的就是一个高难度动作,他必须有极强的现场感,把这个部分中最好的东西拣选出来,而这种现场感还要能够被进一步理论化、历史化,能够被最终整理为我们伟大“传统”的一部分。
如何体会现代,如何接续传统?这些被讨论强调无数次的命题,仍然有待在批评实践中去完成。写出《小春秋》的李敬泽,在他的《庄之蝶论》、对莫言《生死疲劳》的解读中,继续执着于他对古典传统的体会与发现,我们已经可以隐约看到另一条脉络——我们的现代感要如何接续到中国古典的语文形式与中国人自身的生命状态中去,这可能是关于“内在性力量”的另一种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