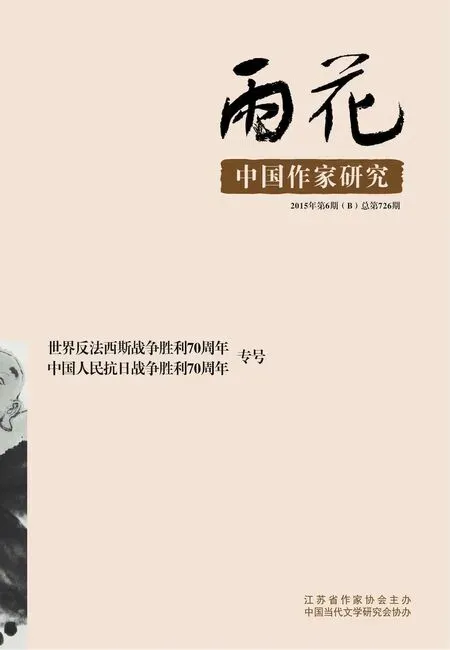刀客与“雅痞”
——谈李敬泽
2015-11-18■李壮
■李 壮
相较于小说诗歌等狭义的文学作品,谈论评论家的评论文章似乎难度更大。当我试图谈论文学评论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柏拉图。柏拉图对世界的理解是,最先有一个超验的“理念”,现实之物是对理念的模仿,艺术作品表现事物,则是对模仿的模仿。相类似地,我们常把文学称作对生活的阐释,那么文学评论则是对阐释的阐释,我们今天再来讨论李敬泽的评论文章,那就成了“阐释之阐释之阐释”——许多西南地区的朋友发音平翘舌不分,大概单是念出这个句子都会疯掉。更要命的是,在文学实验和先锋革命退潮之后,我们所谓的“纯文学”似乎在总体上进入了一种波澜不惊的状态;我们眼中的文学图景已经渐渐变成了一面巨大的玻璃幕墙,明亮、光滑、棱角渐少。特异功能往往是骗人的,要在玻璃上立足,或者像蜘蛛一样吐得出通黏万物的蛛丝,或者要拥有复杂而敏锐的感官,能够在玻璃貌似平滑的体表上寻找到隐秘的裂缝,进而将足或喙深深地插进去。总而言之,在今天做一个文学评论家,多少要具备些在玻璃上飞檐走壁、无中见有的本领。这本领里带有些昆虫的特色,如果嫌昆虫的比喻不够高大,那么至少也得是蜘蛛侠。
李敬泽是能够在玻璃上立足的人。不仅如此,他还是少数那种能够身姿潇洒地在玻璃上来回游走的评论家。或者说得更直白一些,他属于那种能够一眼看出问题所在、还能把问题分析得漂亮的评论家。李敬泽的文章常能够呈现出某种“复眼”式的效果。昆虫的复眼结构使它们能够同时捕捉数百个独立的视觉影像,这些影像在大脑中组合为一,最终形成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的外界感知。李敬泽的评论文章最令人叹服的一点,便是那种视野的层次感和思想的穿透力:他善于以自己的方式捕捉、重组文学场域的多重影像,进而准确地找到作品内部那些幽微秘藏的穴位,由此单刀突进到文本背后更大的问题中去。这是一种极其可贵的素质。我们身边已经充斥着太多四平八稳、老生常谈的评论文章,那些置之四海而皆准的论断分析在我们心中滋生着持续的疲倦;一次又一次地,那些看起来既安全又重要的话语在滔滔雄辩之后最终抵达了无效性——因为看似“安全”和“重要”的东西往往是廉价和通用的,它可以被完好地安放于对任何文本的论述之中,作品的独特价值也势必随之淹没。在我看来,当下文学评论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评奖思维”及“研讨会思维”的泛滥。这类思维的特点是,在一个潜在设定的标准或价值体系之下对具体的文本加以关照,并以之为坐标,进行一系列轻车熟路的“打分”或“定位”。并不是说这种思维不好,关键在于思维的顺位问题必须厘清:应当先有具备独立问题意识的文学评论思维,然后再衍伸出定位性的评奖评价思维,而不是相反,否则文学评论很容易变成一种脱水蔬菜般有料无活力的东西。而李敬泽文章的可贵之处正在于,那是一种具有原始活力的理想的评论文章:小处起水花、洇入大问题,从极富个人见地的文本发现接通对整体文学发展脉络的理解。例如在《1976年后的短篇小说:脉络辨》一文中,李敬泽谈到王蒙80年代初的小说,并没有从那种“可疑甚至反叛的气味”滑向“意识流”与“现代主义艺术手法”的文学史概念考,而是笔锋一转,从语言形式的本体切进:“王蒙创造了一种语言,这种语言预示着正在来临的时代的某些根本特质,人们将身处一个混杂、矛盾、生机勃勃的世界,将面临多端的、相互冲突的价值……一切都汇集于一个人的内部。”因此,“在这语言的多端流动中,短篇小说的张力不再依赖于叙事……它是自我与世界的应对周旋——小说的内在性之门由此开启”。从幽微的形式切口介入文学主潮的莫测变幻,这是优秀批评家的秘传武功,李敬泽对这门功夫的化用可谓得心应手。类似的处理还见于该文对铁凝《哦,香雪》的分析:李敬泽在小说看似纯净的情感体验背后发现了更其幽隐的秘密,“她只是对历史、对浩大降临的事物怀有复杂的态度……她的情感和理智很难平衡,克服困难的结果就是如此诗意的、注意细节的语言”。这里面又涉及到更大的问题——“中国作家如何应对和表现他们所感受的巨大社会变化”。
类似于小说诗歌,好的文学评论也应是“创作”之一种,自觉、自足、自洽、风格浓烈,带给读者有力的审美冲击。我们所期待的是那种酣畅淋漓、令人于身于心产生应激反应的评论文章,成就这一切的必是写作者强大的主体性,或者说“文气”。李敬泽正属于那种风格鲜明、文气充沛的评论家。玩游戏的人都知道,电脑游戏中不同的角色会有不同的攻击属性,评论家写文章也与此类似。有的人是物理攻击,手舞大锤,百米冲刺过来,一锤一锤地抡你。这类评论家大概要数那些1234点列出来然后密密匝匝铺开论证的人,他们以扎实厚重取胜。有的人是魔法攻击,站在远处念念有词,冰火光电炫目特技一拥而上,对应于那类理论功底深厚、通吃中西思想史的研究者。李敬泽则更像穿刺攻击,使用弓箭或快刀,潇洒、精确、穿透力十足。这是顶级刺客的素质,也是优秀评论家素质之一种:举重若轻、不留痕迹、一针见血。他从万千文本之中掠身而过,你不会看见他动作夸张地放大招,但一转身,就会发现身上溢出一线红色:他已经戳中了要害。这又不是蜘蛛侠了,而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漠刀客。
这种感觉在李敬泽的文章中俯仰皆是。我至今记得求学时代初读《庄之蝶论》时那种震惊而激动的心情:这种震撼不仅来自于作者在马克思与福柯、曹雪芹与托尔斯泰、文坛争论与时代语境、东方古典美学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困境之间从容游走、大开大阖的气度,更因为这种信马由缰的游走与开阖其实已在不知不觉之中结构出一个漩涡力场,将更驳杂的信息、更浩大的困惑以及我们自身对“哀”与“颓”的复杂体验裹挟其中——“当他让庄之蝶从‘□□□’中溜走时,他和他的批评者们一样,是把人的责任交给了其环境和时代,但当他在无着无落的火车站上把庄之蝶交付给痛苦的无言、付与生死时,他又确认了庄之蝶的‘存在’,而把存在之难局严峻地交给了我们。”当诗人的自由、名士的潇洒、学者的深刻、哲人的悲悯不着痕迹地汇融于同一篇文章,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被它击中、击倒呢?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对阿乙小说集《春天在哪里》的推荐,直接从“好小说具有某种气味”的感性经验入手,把我们带入对文本的体感认知之中;为甫跃辉小说集《动物园》作序,以“甫跃辉真是郁达夫的转世灵童”这样一句“玩笑话”开始,而后通过对比两人面对都市经验时的反应,迅速接通了两个时代之间地缘政治学的共通与差异,把甫跃辉的写作放进了一个有效而具体的坐标系;谈到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李敬泽从一个私人性的事件——建议不要叫这样一个不严肃的名字——入手,最终却谈到了“小说”与“大说”、公共话题与经验可能性等重大命题。
这里,刘震云的例子又显示出李敬泽评论文章的另一个特点:词语的魔术。在他的评论文章里,出现的往往是常规词汇,却总能够在精心的排列和易容之中呈现出魔法般的戏剧性和准确性。“小说”这个词语已经被我们使用得毫无感觉了,说到与之对应的概念,我们会想到诗歌、散文、非虚构;但李敬泽突然抛出一个“大说”来,一下子就把整个概念给陌生化了,并且确乎贴合于文章所论。这种手法在李敬泽笔下来得出其不意,但又往往使用得十分准确,其实已经是一种诗歌思维。如同一个语言的魔术师,李敬泽的笔锋灵动、飘忽,总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现身,甚至常常跨越学科的边界。以《2012,我的阅读笔记》一篇为例。说到马原的《牛鬼蛇神》,李敬泽评曰“老实得如同记流水账,而且坚决不做假账”——这是会计学。论到经验之为负担,则是“医学上有一种病叫‘肌无力’,我们的病是‘心无力’,被洪水猛兽般的至高无上的经验压垮了”——这是临床医学。及至话语同内心生活之关系,便说“建立一种内心生活,找到内心生活的表意系统,这是中国小说自现代以来的基本志业,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又成了文学的革命历史学。这样敏捷生动的语言和词汇系统,显示出一种内在的自由。“人们用普通话说大话办大事,用方言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当小说家用方言时,他看世界的眼光必定有变,不变不行,因为人就活在语言里。”这是李敬泽自己的话。语言绑定着看世界的眼光,方言与普通话之辨如此,拘束或自在的评论语言亦如是。
语言问题深究到根子上,其实都是姿态的问题。在这里我想吐槽一下评论界的某些风气。现在很多时候,评论界、作者、读者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互动,看似一团和气,其实自说自话。有时遇到把握不住的文本又实在绕不过去,就搬来“福柯”、“伊格尔顿”之类的名字来虚晃一枪。我相信我们身边都出现过这样的人,他们理论功底很厚,越钻越深越远,但一张嘴说话谁都听不懂,恨不得分析梅西踢球都用上几套流行的思想理论。化用沈浩波的一句话,他们真的是在通往大师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了。理论建树的高人当然需要,但如果大家都这么狂奔,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你可以跑得很高、跑得很远,但最后大家只看见你的屁股,看不见你的脸。理论阐释终究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艺术判断,而不是相反;往屁股上装大灯的专利属于汽车而不是评论家——不分场合地秀背影最终只会导致批评的失效。李敬泽的文章之所以特别耐读,就是因为李敬泽的文章能让我们看得见他的表情。他也站得高,也看得远,但是他不是拿屁股朝着读者,他是拿脸对着我们。在《庄之蝶论》中,李敬泽说《废都》那些著名的空格方块是一种“精心为之的败笔”,因为在这些方块之中,庄之蝶这个人物溜走了。李敬泽自己的评论文章恰恰相反,在那些嬉笑怒骂的文字之中,李敬泽是在场的。透过这些文字,我们仿佛能够看到他口衔烟斗、手翻书页、脸上略带戏谑却深藏忧患的表情,这使他的文章充满了情绪与生命的质感。李敬泽的文章中时时可见潇洒的戏仿、调笑、以及关乎阅读感受和情绪体验的坦诚剖白;他的言说腔调独一无二,从身心体验或灵感细节进入文本的本事极其了得。那些文字铺开得如此率性、机敏而自然,有时甚至会给我们这样的错觉,即李敬泽的文章几乎就是从那一个个玩笑、妙喻或特殊的表达里产生的,它们仅仅借助着词语甚至语气的动力势能就足以一路奔涌裹挟出滚滚洪流,浩浩汤汤直入沧海。这看上去简单,其实困难极了——没有充足的自信和才情,一个写作者怎敢把自家表情暴露于外?又如何能天马行空举重若轻?还是躲在那些大概念大理论以及八股文风的后面安全一些。
这种潇洒与率性,使得李敬泽的文章中透露出一股子“痞”气。当然,不是骂街打架那种痞,而是酷酷的痞、有范儿的痞、西装革履的痞,是一种“雅痞”。这种“雅痞”如同幽默,需要才情,需要性情,更需要智力才识层面的底气和优越感。李敬泽在文字之中表情鲜明,然而不装。换言之,他有姿态,但不会故作姿态。归根到底是两个字:真诚。
当然,评论家的“真诚”绝不是小卖部老板式的笑脸敦厚、和气生财,相反,评论家的“真诚”往往会构建出另一种场景,那便是直言厉语,甚至抉心自食。好的评论家不仅要做伯乐,有时还要扮演那个道破国王裸体的孩子;他不仅负责为好的作品鼓与呼,还有责任撕毁那些伪造的和谐。这里便见出李敬泽厉害的一面。其最新评论集《致理想读者》中收录了一篇名为《“短篇衰微”之另一解》的文章,文中不留情面地道出了作者对“短篇衰微”说法的另一重解读:“短篇小说确实面临恶劣的生态”,因为供它行走的只有一条单一狭窄的路径,而“这个路径最终只对某些特定判断下的作品开放”。这篇文章读来痛快,我认为它直接点出了当今文坛亟待清理的病毒之一:审美趣味上那种狂妄、僵硬、缺少省思的“过度自信”。对此我深有同感,我们眼见着一茬又一茬涌现的青年作家们正变得越发成熟、越发老练,但这种“成熟”和“老练”的背后有没有普适性“期刊腔”、“选本腔”的影子?有多少作家和作品是以自我磨灭的代价换得了所谓的“被接受”?我们的文坛是不是一定要变成产业化管理流水线生产的大棚蔬菜培育场?对此李敬泽说得更狠:“是得多么庸常的作品才能让这个意见纷纭的时代的人们感到完美啊?”还有一篇类似的文章叫《视角与“花岗岩脑袋”》,主旨从题目便可大致揣摩。视角与趣味的局限是当下文坛及评论界面临的大问题之一。事实上李敬泽自己的视野很宽,他长期致力于发掘有潜力的青年作家,而且一直在尝试从新的作家和文本的上面发现时代赋予的独特性。李敬泽把那些口味单一、视域狭窄、思维老化的编辑和评论家们形容为“花岗岩脑袋”——他说这些石头脑袋急需破开。这让我想起了我的家乡。我在青岛长大,青岛盛产花岗岩,由于靠海,也多礁石,至于礁石是不是花岗岩质地,我没有考证过。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海滩上遍地的沙子,都是从那些坚硬无比的岩石身上破碎下来的。海浪一遍一遍地拍打,花岗岩也好、海礁也罢,最后都得破碎。这跟文学的革新之路大致相似。问题是今天,80年代那样冲天涤日的文学大潮已经不可能重现了,那么在一个文学革命总体“退潮”的时代,我们如何打破那些“花岗岩脑袋”?我想,答案或许在于“种子”。如同我们所知道的,种子能够从内部顶裂死者的颅骨、从石缝里撕开整块山岩:外力难以打破的东西,植物的种子常常能够以生长的力量从内部打开缺口。这颗种子,这种内在性的力量,就是我前面反复提到的、在李敬泽身上不断显现的东西:发现的眼光、在场的语言、真诚的品质,以及优秀评论家的良心和尊严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