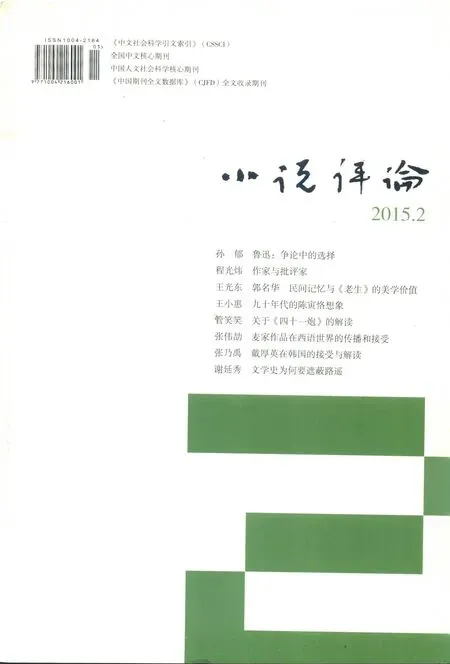论叶梅小说的生态书写
2015-11-14曾娟
曾 娟
论叶梅小说的生态书写
曾 娟
土家族女作家叶梅以其执著、自信的笔力为我们构筑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桃源之地——鄂西世界。在她的笔下不仅有神奇秀美、雄浑险峻的自然风光,还有对土家儿女的生存境况、精神品格及其独特的生命意识的书写与观照。她的作品恰如“那博大深邃而又变幻无穷的大海,在每个时段里,它都有令人心动的颜色,在每个视角里,它都有值得珍存的构图。……经得起人们在不同的期待视野中做出不同的解读和阐释,从中得到立体的多元的启示”。正因如此,论者对叶梅的小说有多种界定,比如鄂西风情小说、土家文化小说、新乡土小说等,并从地域文化、民俗学、民族文化、女性意识、叙事风格等视角对其文本进行解读。毫无疑问,这些研究拓宽了读者的视野,让我们领略到了一个丰富、别样的艺术世界。但是,叶梅小说中还有一些有用的活性资源不应忽略,那就是她小说中的生态书写。只是,她的作品并不直接揭示生态危机现状,而是通过对神奇秀美的自然生态的书写、健康自然的生命形式的表现,展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的和谐统一。叶梅的写作表达了对诗意栖居生存理想的守望与忧思,呈现出鲜明的生态意识。
一、神奇秀美的自然生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直是人类向往与追求的理想的生存境界,这也是生态文学考察和表现的重要内容。在叶梅的作品中,人与自然诗意融合的生存空间就是鄂西世界,一个宁静、祥和、神奇的自然王国。那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大山区,是叶梅出生和成长的地方,那里的山山水水养育了她,也给了她创作的灵感与素材。即使后来工作在城市,“那山、那水,一根竹管,一朵山花,一泓泉水,都化作了一种情绪,”融进了叶梅的作品中。在叶梅的所有作品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她对鄂西自然山水的书写与赞叹,这种自然景物的描写已成为她写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其他作家将写景作为故事或人物、主题的陪衬地位的做法不同,叶梅小说中的生态环境已不是一般的风景描写,它有着蓬勃的生命力,是作家情感与灵魂的寄托之地。
叶梅的小说多集中描写恩施境内清江、长江三峡流域一带土家人的生活。这一片地方高山环绕,峡谷幽深,山崖陡峭,水流湍急,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原生态”地区。龙船河、野山关、神龙溪、宝塔河、九畹溪、通天洞……这些自然景观时时出现在叶梅笔下,成为作品的重要特色。龙船河蜿蜒伸展在群山之间,时而凶险,时而恬静,时而狰狞,时而温柔,充满着野性与生命活力。《撒忧的龙船河》是这样描述它的雄奇壮美:
那河面百二十里,起源于龙船寨头一处无名山洞,沸腾泉水在苔藓密布的石洞之外积成深潭,继而跌宕出三道百丈悬崖,蜿蜒九滩十八弯,依次经过苦竹、夫妻、老鹰三峡,最后汇入长江。那河看是纤细实际奇险刁钻,河上礁石如水怪獠牙狰狞参差不齐,水流变幻莫测,时而深沉回旋织出串串漩涡,时而奔腾狂躁如一束束雪青的箭簇。
河两岸青山相对而出,“间或有血红点点,三两猴儿于茂林嬉戏”,一派盎然生机。而恩施一带的山峦奇妙无穷,在《回到恩施》中叶梅将其与张家界相对比,认为:“处在鄂西的野山关更为浑厚苍茫更为神秘粗野,山间的小径总是若有若无,不时被纠缠不清的藤蔓所阻碍,当你好不容易钻出一片密林,面前不是豁然开朗,相反倒是一面笔直陡峭的石壁或是一道汹涌的小溪。”读来犹如丛林探险般神秘莫测,妙趣无穷。鄂西的山水也有它恬静、温和的一面,“那水的深厚与碧绿,柔软地须着船弦滑过,绸缎一般悄无声息,”“山也是碧绿的,一沓一沓地浸透了看不见的远处,仿佛只要用手一拧,那山便可淌出浓浓的绿色浆汁来。”“河两边的岩石上有好多悬棺,还有古栈道,橘子树”,每到橘子成熟之季,满山遍野的金黄美不胜收。山上的溶洞神秘险要,粉白的鸽子花开满山头,漫山遍野的青竹林,麂子奔跑在陡峭的山崖。就连三峡的黄昏都充满着诗情画意,“残红晚霞,一江碧水泛散粼粼金光,倦鸟泼剌剌归林,峡谷峭壁深沉了颜色,如墨如黛。”如此神奇秀美、充满灵性的生态环境怎不令人向往?
有人说,叶梅笔下的故乡山水已被灵性化了,成为作品中的角色,成为一种精神实体。的确,土家山寨的山山水水已构成一个自足的生态世界,寄托着作者的情感。除却龙船河、野山关、吊脚楼,“洞”也是叶梅故乡山水的独特代表。她怀着无比崇敬之情描述故乡的溶洞,“长江三峡沿岸高低起伏的大山里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溶洞,它们是崇山峻岭中一只只睁大的眼睛,长久地不动声色地凝视着天和地,是是非非,风风雨雨,爱恨情仇,沧海桑田,一代又一代,人老洞未老。”土家人从他们的祖先巴人开始就对洞穴有着深刻的感情,特别是对祖先曾住过的洞穴敬仰有加。《青云衣》中由于三峡大南坝建设,向怀田的屋场将被淹埋,搬迁之前,他将先人一一安置进岩洞,并交待自己死后也睡进幽深的岩洞,与三峡的高山、绿水、清风做伴。《山中有个洞》更是将“洞”与三代土家儿女联系起来。山上的通天洞“与世隔绝,风光秀美,本是一个让人断绝尘念修身养性的绝妙所在,且紫气东来,冬暧夏凉,真所谓洞天福地。”田土司将小儿子安排在山洞读书,小王子却在山洞前产生了爱情,最终田土司为成全皇帝“改土归流”制血溅通天洞。多年后田快活的爷爷田红军(田大胆),作为大部队撤离湘鄂西留下的伤员之一,藏进通天洞坚守了七七四十九天,有幸逃过清匪团的攻击存活下来。子孙田快活为寻宝进入通天洞,结果九死一生,虽空手而归,入洞的经历却使他明白活着的意义。在这里溶洞已不仅仅是主人公栖息的地方、故事发生的背景,它同主人公一样成为作品中的重要角色,展示了土家山寨的文化内涵。它不仅是一代又一代土家人的历史见证,也是土家儿女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力的表征。叶梅对溶洞的描写,既展示了“洞”在土家文化中的深刻的历史内涵,也表达了作者对“洞”的土家文化意蕴的热爱与崇拜之情。
二、健康、自然的生命形式
“健康、自然的生命形式”指未经现代文明浸染和玷污的生命的本然状态,蕴含着自然的人性;充满野性的生命力;淳朴的民俗风情;达观超脱等多层意义。生活在长江三峡崇山峻岭之中的土家族,依顺自然的法则,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里的人既质朴、简单、纯真,又勇武刚烈,笃信鬼神,充满了神秘气息。
1.敬畏天地、自然;崇拜祖先、神灵
湖北恩施地处巫山山脉和武陵山脉的交汇之外,方圆数百里峰峦迭障,云雾遮罩。这里是巴文化的发源地,又汇集着楚文化与巫文化,处处充满着神奇与玄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土家族信仰万物有灵,其宗教信仰有对大自然的崇拜、动植物崇拜和祖先、鬼神崇拜。“土家族是多神教……他们主要生活在人烟稀少的大山里,生存现状决定了他们要学会与大山对话,与天地对话,与神交流。否则,他们就无法在那样一种时空环境中生存下来。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对世界万物的理解,是‘天人合一’的某种体现。”所以,他们时时以一种敬畏之心对待天地、自然万物。
在《青云衣》中,叶梅描述了峡江人对山鬼的情感。山民认为向怀田的父母连同门前的橘树、屋后的翠竹以及那三明两暗的房子消失在江水中后留下的“呛鼻的土腥味”就是山鬼的气息。在他们看来“山的幽灵,忽大忽小,忽隐忽现的。一会儿是风,带着呼呼的叫声掠过山头;一会儿可能藏匿在漫山遍野的白雾之中,化作一只小小的狐狸,嗖地从雾中穿过;更多的时候,它沉睡在大山的深处,就像这些深埋地底的狰狞巨石,一动不动。但是,说不定什么时候突然惊醒,一撑腰站起来,山的衣裳就崩裂了,哗啦啦落下无数挂饰。……山鬼可以藏在山的任何一处,它的突然发作,谁也无法制止。”“山是不能没有山鬼的。山鬼是山的魂魄。”面对山体滑坡这种自然灾害,峡江人在悲伤无奈之中选择坦然面对。这种生活态度正是土家人顺其自然,尊重自然规律的思想意识的体现。
土家人相信天上有一座灵魂聚居的拗花山,山上的千万种花儿与地上的千万个人儿命运相联,一花一生命,一花一命运,谁也躲不掉。所以,凡遇妇女生育之际,必请巫师上天去请七仙女,找到代表命相的花树。《花树花树》一开篇就描述了巫师覃老二请七仙女的场面:
龙船寨的巫师覃老二双眼紧闭,去上天请出七仙女。一缕香魂入体,核桃似的覃老二顿时婀娜多姿,沙哑声音也如清晨翠鸟婉转,飘飘然往前行走。耳听得婴儿啼哭,田家老太急切问道:“看见了吗?看见我孙女的花树了吗?”
七姑娘凝神聚气,闪动明眸,在那云蒸霞蔚之中终于找到灵魂聚居的拗花山。只见满山遍野春来冬云,千万种花儿是那千万个人儿的命运,姹紫嫣红繁茂调零各异。七姑娘看准田家老太新添孙女的命树,一树骨嘟嘟雪白小花,莹湛透明。正待仔细,眼前突地红光灼灼,格外伸出一枝娇嫩的粉红花儿来,耀眼得紧。七姑娘失声叫道:“又是一棵?”
七姑娘轻移莲步,长裙摇曳,飘飘然回天而去。覃老二一个跟头栽倒在地上,口吐白沫长睡不醒,红日西沉才被太唤醒过来。
这是土家人的梯玛信仰,承载着土家人万物有灵观念、泛自然神论思想,隐藏在土家族人的仪式、风俗、口头文学等文化形态中。梯玛(巫师)是人与神沟通的中介,梯玛信仰实质就是对巫术的信仰。“对巫术的信仰乃是深深地植根于生命一体化的信念之中的。”这种信仰背后不正是土家人对生命和自然的敬畏吗?
2.从容、豁达的生死观
土家族人对待生、死的态度与看法蕴含着“天人合一”的生态内涵。“土家族文化是一个开放式的,他们对待生死的态度从容而又达观。在他们看来,死亡不过是从一个门坎跨入到另一个门坎。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念,在土家族对待生死的态度上表现得很充分,他们不是以悲哀、哭泣,而是以歌舞,来送亡者上路。”恩施土家人独特的自然生存环境造就了他们独特的生存方式与生命体验。
在《撒忧的龙船河》中,覃老大一家三代人以在长江三峡上行船谋生——“走豌豆角”,这是他们无法选择的生存方式。覃老大活着时常说两句话“该死的卵朝天,不该死的万万年”,“要死卵朝天,不死好过年”,看似消极宿命又粗鄙,其实恰恰表现了他面对生死的坦然态度。面对死神的威胁,龙船河的挑战,不仅需要强健的体魄、高超的行船技术,还要有征服自然的勇气,更要有面对生死的从容态度。对于长期生活在雄奇壮美又险峻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死只是一线之隔,这样的生存环境孕育了土家人从容、豁达的生死观。他们热爱生活、敬畏生命,珍惜生命。当生命真正终结时,他们泰然自若,不悲不泣,以欢快的“跳丧”仪式高兴地送死者上路。
“跳丧”(撒儿嗬)是土家人相沿已久的文化习俗,至今仍广泛流行。每逢土家人有长者过逝,其亲人特别是子孙后代要邀集族人一起热闹地庆祝。他们围绕在死者的灵柩旁,一边吟唱“撒儿嗬”歌谣,一边跳驱鬼避邪的舞蹈,以这种方式向死者告别,将亡灵导入极乐之乡。在《撒忧的龙船河》中,覃老大年过六十寿终时,乡民以欢乐的舞蹈为他送行。叶梅用生花妙笔具象地描绘了这一活动场面:“老二掌鼓,巴茶掌灯,十几条包着头帕的土家汉子开始跳丧。场坝里灯火辉煌如白昼,大坛的酒搬上来了,大碗的肉盛上来了,寨子里的人密密地围坐在堂屋、场坝和白果树下,笑逐颜开气势非凡地为覃老大送行。”土家人“对知天命而善终的亡灵从不用悲伤的眼泪”,所以他们用热烈欢乐的舞蹈送行。这种“跳丧”活动折射出土家人的生命意识和他们对人生幸福、意义的本真地理解。
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豁达、乐观的生死观念包含着遵从自然规律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当下的生态思想十分契合。
3.推崇自然情感,张扬生命激情
“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土家人也不例外,情感是他们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反映出他们本真、自然的人性。恩施这一带,“婚姻习俗自古以来并不封闭,满山此起彼伏的情歌便是见证,三月三女儿会时,年轻未嫁的女子更是可以自由与男子对歌约会,进而订下终身。”(《回到恩施》)正因为有这样的民族心理土壤,土家女子对爱情的追求全没有汉族女子那种扭捏、矜持、犹豫不决,倒是相当果敢、大胆。如,土家妹子谭青秀(《回到恩施》)对“父亲”一样的解放军干部一见钟情,大胆地追求,主动为其量脚做鞋;清江边上的女子妲儿(《青云衣》,主动接近向天生向其表白爱情,并结为夫妻;巴茶(《撒忧的龙船河》)在女儿会上对覃老大产生好感,将自己亲手扎成的千层鞋底作为定情之物送出,并为自己定下婚姻;昭女(《花树花树》大胆向乡长示爱,终因男人的功利,又主动分手;李玉霞(《乡姑李玉霞的婚事》)自已给自己找对象,看中卖鱼的乱毛……这些女子对爱情大胆自主地追求,正是一种生命自由、自主性的展示,也是一种自然人性的复归。叶梅正是通过对土家儿女婚俗的动情描写,凸显他们独特的情感体验与态度。
土家男女推崇自然的情爱,对待情感率性而为,未掺杂任何物质与功利色彩。与当下那种建立在各种利益、欲望基础上的爱情相比,这些是最纯粹、最自然、最健康的情感。叶梅在这种健康、自然的生命形式的书写中展示了人性美、人情美。
三、诗意栖居的守望与忧思
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其诗美论中曾引用诗人荷尔德林的一句诗歌描绘了人类最理想的生存状态:诗意地栖居。“人居天地之间,上可以仰望天空,下可以俯瞰大地,承日月光辉,沐流岚虹霓,拥抱自然,与人亲亲,即是一种诗意栖居的状态。”这是海德格尔对现代性及其批判时所憧憬的“审美的生存”,一种桃花源梦境。叶梅小说展示的美好自然、淳朴人性、人际和谐正是作家理想的生存方式的文学表现。
她笔下的鄂西世界平和、安宁、质朴、自然,景色秀美,众生和融,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达到和谐统一的境界。与喧闹、功利、物欲横流、人性异化的当代城市形成鲜明对比。然而,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美丽的恩施也未能阻挡现代化的步伐。就像《青云衣》中描述的那样,随着三峡大坝的建设,向怀田依山傍水而建的屋场将全部消失在电站建设的轰鸣声中。眼看着自己生长的那片美丽故土随着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发生着令人痛心的变化,叶梅不无伤感地写道:“那条小溪(龙船河)却在不断地变化着。由于三峡工程的进行,大坝蓄水的时候,回水将进入这条小溪,旅游中引以为特色的乘坐‘碗豆角’漂流将不可能在下游进行,而沿途的峡谷景点也会相应消失或者变矮,悬棺、栈道,将会没入水底,觅食的猴子也将会搬到更高的山上……”这种变化引起作家深沉的忧思与焦虑。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叶梅并没有沉浸在自己构建的理想王国,而是在现实面前做出了理性的反思。《歌棒》、《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五月飞蛾》等作品,与其说这些作品关注的是土家乡民进城后的生存状态,意欲表现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矛盾冲突,不如说是作者对土家山地文化特有魅力的展现,更是对自然生态失衡、人的异化、生命力的萎缩、道德伦理的滑坡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思考。
作为从乡村步入都市的少数民族作家,面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叶梅的心情是无比复杂的,既对现实颇感无奈,又对鄂西那片土地充满怀念与忧虑。这种心境恰如其分地体现在她笔下进城的土家儿女身上,龙船寨的农民歌手沙鲁(《歌棒》,因其原生态的歌声被电视台邀到北京参演晚会,却因丢了歌棒,不告而别回到三峡。当芳罗问他为什么不在北京找?沙鲁回答:“那不是我的地方,我一天也呆不下去了。”他是属于三峡龙船河的,北京的环境、北京人容不下他这个真正的原生态的三峡人。主持人芳罗自然不明白沙鲁的心境,但是当她为寻找沙鲁来到三峡的时候,秀美的自然风光、淳朴的原著民使她有了一种别样的心境,那是长久呆在都市中体会不到的感受。龙船寨拥有宁静的夜,“夜色发黑,树叶被风吹得沙沙直响,小河那边,一轮弯弯的月儿升了起来,山里村庄真安静。”相比之下,“北京这会儿,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她和杨金戈常去朋友聚会,有时候到后海吃涮肉、划船,随后又到酒吧喝红酒、唱歌,不知不觉间就通宵未眠。第二天早晨接着就赶去上班,真的是起早睡晚,车堵成一片,人筋疲力尽。”所以,在龙船寨的安宁中芳罗一身轻松,睡了个好觉。而与质朴的沙鲁相处的过程中芳罗更是感受到三峡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最终她放弃了劝沙鲁回北京的计划。“诗意地栖居”远比名利重要。无业游民马松(《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这个从三峡来到城市的乡民,夜晚来临时总在别墅区转悠寻找栖居所。之所以喜欢这个都市之外的高贵小区,是因为“在一些杨树和大槐树的簇拥之中,四处飘荡着田园的气息,庄稼呀马粪呀,还有难得一闻的柴火味儿,城市的喧闹被筛子似的田野一格格过滤了,让他想起三峡大山里的种种。”居无定所的马松躲在别墅区的小楼上,从他的视角观察到了城市的病态以及对人的异化。他在不自主的对比中怀念起三峡的种种,比如城市污染导致的雾霾,“沉闷浓重的灰色雾团就遮蔽了四周的绿树,咳嗽一声都被雾给吸了进去,短促得连鼻子里的回声都没有。”雾像铅块一样挡住人们前行的脚步,而“三峡的雾是白的,雪白雪白,轻飘飘的,在人的身边绸带一般飘动。”马松认为三峡的包谷酒、三峡的狗、“人大戏”、三峡的姑娘都比城市里的好。多么令人神往的地方,一切是那么美,一切是那么和谐。难怪二妹(《五月飞蛾》)看到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都市景象,心生困惑:“为什么在石板坡,方圆几十里大山只有几十户人家,但随时能感觉到人的存在,某人唱支山歌某家争个嘴大家都知道,某人去砍柴某人去走人家大家也都看得明白,而在城市里却感觉不到人呢?密密麻麻走来走去的人是不是都汇到那层网里去了呢?”在走进城市的路途中,二妹既向往城市生活,又抗拒城市文化,既接受城市文明,又守望着自己的心灵。对于进城的土家儿女来说,这是一种普遍的焦灼的心境,它是理想与现实无法相契合而产生的精神困窘与无奈感。
结 语
面对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各民族的作家将自己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与反思以文学的形式呈现,如姜戎的《狼图腾》、周大新的《湖光山色》、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藏族阿来的《空山》、土家族李传峰的《红豺》、蒙古族郭雪波的《沙狐》等等。土家族作家叶梅也是其中的一位,她坚守本民族的“经验”,为我们展示土家儿女在大自然面前的生存智慧。正如她自己所说,“我的小说植根于长江三峡流域的民族地域生活,高山峡谷的三峡人对世界万物和人生的理解,体现了巴楚文化中从庄子到屈原浓烈的诗意美,对我来说都是极为珍贵的财富。我想表现各色人等的生存状态及命运,并试图诊释民族的文化母体,有力寻译民族文化的秘密,对土家人刚烈勇武、多情重义、豁达坦荡等民族性格与文化精神的展示,对西部山地少数民族地方与民间文化资源的发掘,来寻找救治现代文明之弊的某些有用的活性资源。”所以,她构建神奇秀美、淳朴宁静、安然自若的鄂西世界来抗衡现代文明之弊。
从生态批评的视角看,叶梅小说的生态书写显得格外有意义和有价值。第一,随着工业文明的入侵,人与自然之间那种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被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改变。人类为了追求无止境的欲望肆意掠夺、毁坏大自然资源,从而导致生态危机与生态灾难频频发生。在人类对待大自然的病态心理面前,叶梅笔下的土家族人敬畏天地自然,崇拜祖先、神灵的生命意识与人生姿态给自高自大的人类以警醒。第二,生老病死是大自然的规律,一切顺其自然方能保持生态和谐。但当今社会的人类要么轻易放弃生命,要么耽于不死神话,叶梅笔下土家族人豁达、乐观的生死观能给人以启发。第三,在物欲横流的当下社会,两性关系充满功利、物质色彩,而叶梅笔下健康、本真的绿色爱情给游戏爱情的青年男女以精神启示。叶梅作品对自然生态、自然人性、生命意识、两性关系、生存方式的思考,体现了她独特的生命体验与生态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当下倡导的生态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讲,她的创作延续了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创作精神,丰富了民族文学的内容。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14C0232);益阳市社科联课题(2013YS020)。
曾 娟 湖南城市学院
注释:
①严英秀:《趟过男人河的女人:论叶梅小说的女性书写》,《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5期。
②这方面的代表论文有:张守仁《鄂西无处不是情——关于叶梅的小说》、樊星《叶梅的“恩施文化小说”——读〈回到恩施〉》、道毅《寻索土家族文化的秘密——论叶梅的土家族文化小说》、《论叶梅小说的叙事风格》、彭卫鸿《论叶梅小说的女性意识》、严英秀《趟过男人河的女人:论叶梅小说的女性书写》等。
③张守仁:《鄂西无处不是情——关于叶梅的小说》,《叶梅研究专集》,北京:中央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37页。
④⑤⑨⑪⑫⑮㉔叶梅:《妹娃要过河》,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49页,第202页,第72页,第242页,第240页,第47页,第147页。
⑥叶梅:《最后的土司》,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11页。
⑦⑧叶梅:《歌棒》,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第16页,第17页。
⑩⑭李俊国,叶梅:《诗性,在生命与文化的碰撞中绽放——叶梅访谈录》,《民族文学》2005年第4期。
⑬[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42页。
⑯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9页。
⑰刘秀珍:《论沈从文作品中的生态美》,《江汉论坛》2010年第2期。
⑱叶梅:《我的西兰卡普》,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⑲⑳㉑㉒㉓叶梅:《歌棒》,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第23页,第23页,第50页,第76页,第76页。
㉕杨文,叶梅:《展现土家人的民族性格》,《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