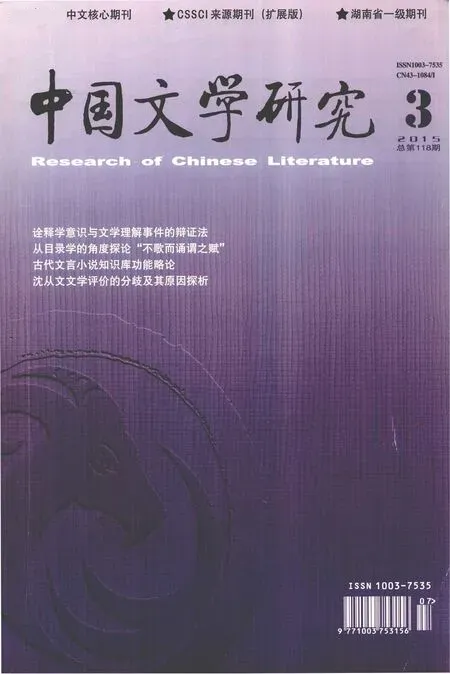“永王东巡”和“永嘉南渡”——从李白政治判断中历史经验的失灵说起
2015-11-14郭硕
郭 硕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 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叛军一路长驱直入,到第二年六月,攻占潼关,玄宗仓皇幸蜀。不久,玄宗第十六子永王璘出镇江陵,随即起兵东下,迅速成为长江流域的一大军事势力。李白亦参与永王幕府,今存诗作中尚有《永王东巡歌》十一首,是这一事件最重要的原始文献,也为研究者多所征引,研究的指向多在于李白的文学生涯与“从逆”性质。不过这些诗句所能提供的历史信息,不仅仅是关涉李白生平和诗作的重要关节,还是安史之乱变局中各种政治风云最直接的反映。与此同时,诗歌中所见典故背后的历史经验,也是李白所作政治选择的直接认识来源。这种历史认知背后的逻辑以及其对安史之乱前后政治格局变化的影响,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重点所在。
一、永王东巡与“永嘉南渡”:李白诗句中的政治意象
李白《永王东巡歌》之二:“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此诗中两处以晋事用典,即永嘉南渡之仓皇,谢安抗击苻坚之风度。至于“三川北虏乱如麻”句,所描绘的历史背景也与永嘉之乱极为相似,安禄山与刘渊同为胡人出身,亦同样起兵叛乱并先后占领了洛阳、长安,造成了天下“乱如麻”的历史影响。李白从规模和性质两方面,对历史上的永嘉之乱和现实上的安史之乱进行了类比。后句利用谢安的典故,前人认为“其时邺侯、汾阳均未显用,殆有所指,非自况也”,此理解可能并不准确。有一点很清楚,李白使用谢安以江南为基地抗击“北虏”的历史背景为典,新的“谢安石”得以抗击安史叛军自然也离不开永王为主的唐王朝江东势力。全诗合读,还有一番隐含的意义可以开解,即是永嘉之乱反映的是安史之乱的现实,而谢安抗秦之典则包含着李白对辅佐江南的永王担负起抗击叛军重任的期待,让东晋中兴的历史得以重写。
从现有资料看,李白自天保三年(744 年)离京南下,其后虽也曾短暂停留安禄山的巢穴幽州,但绝大多数时间都是长期流离于南方的金陵、扬州等地,远离了当时政治的中心。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更是不曾离开过南方。安史之乱造成中原的破坏以及玄肃二帝仓皇流徙的悲惨境遇,身在南方的李白其实是没有亲眼目睹的。李白诗中对于安史之乱的描写,其来源大约有两种:第一是在亲历者描述的基础上进行的事实重构,第二是基于某种知识背景下的历史想象。永嘉故事与安史之乱的高度相似性,也成为李白诗作中意境构建的渊源。此类例证在李诗中并非个例,如《赠张相镐二首》其二亦云:“想像晋末时,崩腾胡尘起,衣冠陷锋镝,戎虏盈朝市。石勒窥神州,刘聪劫天子”。除《永王东巡歌》之二明确用永嘉之乱之典外,另外几首也具有类似永嘉故事的寓指。如其五云:“二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所谓“二帝巡游俱未回”自可指代玄宗、肃宗二帝,不过西晋愍、怀二帝沦陷非所亦是似曾相识;“五陵松柏使人哀”的意象,现实中无疑是指称京都不守,诸帝陵墓沦于异类的悲凉,也不难想见傅亮《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所说的永嘉之乱西晋五陵“坟茔幽沦,百年荒翳”之悲怆景象的历史重演。铺垫之后,“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两句,则确凿无疑地以永王托寄兴复中原的重任了。
值得注意的是,李白诗中的王业寓指也是很明显的。“龙盘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故丘”、“初从云梦开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数句,皆以金陵为依托。东晋的王业正是以江南的建康为基地建立起来的,“金陵有天子气”正是东晋南朝时代最重要的帝业象征。瞿蜕园、朱金城分析《永王东巡歌》组诗说:“综观此诗次第,第十首以前皆写永王东巡为据金陵以图恢复,第九首最为一篇之警策,其主张永王用舟师泛海直取幽燕,意已昭然可睹,然欲行此策,必以金陵为根本。”李白诗中所用的金陵典故,“龙盘虎踞帝王州”与“更取金陵作小山”,当然符合李白诗一贯的风格。李白在《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中,也仍对唐王朝定都金陵之可能性念念不忘。其文起首便云:“臣闻社稷无常奉,明者守之;君臣无定位,暗者失之。所以父作子述,重光叠辉。天未绝晋,人惟戴唐。”又说“臣伏见金陵旧都,地称天险。龙盘虎踞,开扃自然。六代皇居,五福斯在。雄图霸迹,隐轸由存。咽喉控带,萦错如绣。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
从李白的思想来看,以金陵为基地兴复中原的用意确实非常明显的。而此时玄、肃二帝却远遁西蜀、朔方,都不在江南,能够在金陵代表大唐“王气”者非永王莫属。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即云“若非赞其逆谋,则必无是语矣”,自当是得当之言。另外,《东巡歌》之一“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一句,实际上永王东巡的时间并非是正月,按《春秋繁露》对“正月”解说云:“何以谓之王正月?王者必受命而后王”,元人萧士赟早已注意到李白此处的用意是“夫子作《春秋》而书王之意也”。
从“永嘉”、“谢安”的明指到金陵王气的暗寓,李白在《永王东巡歌》中以“永嘉南渡”的历史记忆作为政治托寓的对象,也是李白在政治判断中汲取历史经验的来源。“永嘉南渡”指的不仅仅是安史之乱对中原故都的破坏,也喻涵李白对唐王业依傍金陵的王气得以保存和中兴的期盼,能够担负这一重任的,正是李白的府主永王璘。
二、永王出镇与“永嘉南渡”想象生成的现实背景
李白组诗用“永嘉南渡”的典故,古典今事之间必然会有相似的成分。诗歌中所托寄的思想,都是诗人所生活的时代的反映,都不可能脱离其得以生成的历史背景。李白从璘的动机和对永王的期待,需要从李白对当时政治局势的判断入手进行分析。李白为何认为永嘉南渡的历史会在永王身上重演呢?这一点还需要从永王出镇的历史背景来考察。
结合诸史记载,永王出镇江陵的时间在马嵬之变以后。太子李亨分兵北上,随后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遥尊玄宗为太上皇。大约同时,尚在入蜀途中的玄宗下诏,以太子李亨充天下兵马元帅,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兵马;同时又以其第十六子永王璘为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等四道节度大使,出镇江陵。此时唐军与安禄山叛军在北方战场上的争夺中正处于最低潮的时期,在北方的唐军实力基本保存完整的只剩下朔方军了。此前参与对安禄山叛军作战的唐军主要将领或败或死或降,加之京城陷落,唐王朝失去了一大政治优势,对唐玄宗来说,朔方军将领的态度是否会因此而改变尚未可知。另一方面,即算朔方军对唐王朝的态度忠诚,它先前也只是作为偏师出击河北,并未用作抗击叛军的主力投入正面作战,其战斗力如何也还是个未知数。因而在玄宗的角度考虑,朔方军的可靠性大成问题。因而贾二强先生便已指出此时“玄宗对朔方军已毫无信任可言。”而太子李亨离去时,玄宗曾谕之云:“汝勉之,勿以吾为念。西北诸胡,吾抚之甚厚,汝必得其用。”似乎是玄宗认为当时西北少数民族势力能够成为抗击安禄山的主要力量。实际上,玄宗对所谓西北诸胡(主要是吐蕃与回纥)“抚之甚厚”,其程度无论如何应当是比不上同是胡人的安禄山的,而且二者在玄宗时期还都与唐王朝进行过长期在边境战争。所谓“抚之甚厚”似乎不太符合实际情况,而西北诸族势力的态度更是一个未知数,太子能否集合力量卷土重来甚至其生命安全能否得到保障都还是一个未知数。
在永王出镇时间这一点上我们还注意到一个关节,就是玄宗下制当时根本不知道太子去向,更不知道他已经在灵武即位。而且玄宗本人的所在也不为人所知,“四方闻潼关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舆所在”。这时候玄宗对形势处于失控状态,各地对中枢机构的情况也一无所知。因此,仓皇逃往西南一隅的玄宗一方面需要控制最重要的根据地江南地区作为反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分散诸皇子以防止被安禄山一网打尽的意图。在玄宗仓皇逃亡蜀地的时候,如果安禄山乘胜追击,玄宗的处境将是非常危险的,而此时玄宗诸皇子均在玄宗身边,存在被安禄山一网打尽的危险。事实上玄宗逃离长安时,便有公主、皇孙不及跟上而遭毒手者。李德裕曾经提及:“向使天宝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处方州,虽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为安禄山、朱泚所鱼肉者,由聚于一宫故也。”此时的玄宗其实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以诸王出镇即是应对之策。另一个事实是,玄宗欲以永王控御江南似乎早有打算。早在天宝十四年十二月,玄宗即以永王璘为山南节度使,以江陵长史源洧为副,而此时距离长安陷落还有半年之久,这也说明在当时玄宗早就已经有派永王出镇的打算了。
永王璘作为唯一一位玄宗钦点的派往江南这一富庶地带的皇子,同时也成为最高级别的地方长官,似乎有足够的据有江南地区的资本。而这时,唐玄宗正苟安于蜀郡西南偏僻之地;肃宗则仓皇辗转于贫瘠荒寒的西北一隅。此时北方各地都已经残破不堪,而南方一带则得以保全,它的富饶能够最大限度地成为平叛的财富来源,因而成为关系到全局的一个关键因素。永王所出镇的江南地区则控制着唐王朝的经济命脉,无论从控制范围、人力的丰厚还是经济实力各方面来看,都要比西北和蜀地强大得多,因而使它成为唐政府最重要的后方基地。永王出镇后,“七月至襄阳,九月至江陵,召募士将数万人,态情补署,江淮租赋,山积转江陵,破用拒亿。以薛谬、李台卿、蔡晌为谋主。”而且其召募士将、补署官吏、积聚江淮财赋等举措,甚至都获得了玄宗诏制的授权,因而有许多人包括李白都对其寄予了无限期望。
在这样的背景下,永嘉南渡晋元帝中兴晋室的历史记忆也在江南地区的士人中不断泛起。与李白同时代的萧颖士虽然不曾参与永王集团,但他在给宰相崔圆上书中曾提出:“今兵食所资在东南,但楚、越重山复江,自古中原扰则盗先起,宜时遣王以捍镇江淮。”据崔圆本传,他正是在马嵬之变以后被玄宗任命为宰相的,萧颖士的上书时间也当在此后不久。也正是萧颖士,提出过一种以南朝正统论,“乃黜陈闰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学者指出萧颖士之所以独尊萧梁,主要是出于个人感情,自是的论;不过南朝正统论本身,却与“遣王以捍镇江淮”以江南为基地复兴唐室的思想颇为合契。与萧颖士持有类似的南朝正统观的,还有今存的一部重要的唐代史书《建康实录》。许嵩其人生平不见记载,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考其成书时间云:“第四卷末识云‘吴大帝黄武元年壬寅至唐至德元年丙申,五百三十五年’,第十卷末又识晋元帝太兴元年至至德年数,此当是其成书之岁。”此说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值得注意的是,至德元年恰恰就是永王东巡的同一年。南朝正统论在这一时期突然出现并且流行,绝不是偶然的。实际上,以江南的建康接续中原正统,在此前的历史上仅仅只有永嘉南渡后的东晋唯一一次。可以说,南朝正统论的历史意识与李白将永王东巡比作永嘉南渡,在思想脉络上是完全一致的。
三、历史结局大相径庭:永王东巡的迅速失败
历史的发展过程并未如李白等人所期望的那样,而逆转这一局面的,恰好是在临武即位的唐肃宗。永王东下是出自玄宗的诏书,这一举措无疑对肃宗的皇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至德元年七月以后,肃宗在朔方军的支持下于西北立足;而叛军占领长安之后,已经力不从心,再也没有发动大规模的攻击行动。可以说平叛战争已经进人一个相持阶段,这种相持阶段的存在也避免了永嘉之乱怀、愍二帝先后被掳的情况重演。在这样的背景下,肃宗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迅速发起了对永王的行动,江南的局势也就此逆转。
永王璘于至德元年七月至襄阳,九月至江陵,十二月即举兵东下,虽然速度也不慢,但是,他可能没有料到,肃宗的动作已经走到了前面。在灵武即位以后,肃宗立即设法将消息传达到了江南地区,以稳定江南地区的士心民心。即位当月,玄宗尚未知道肃宗即位的消息之时,肃宗即“以(颜)真卿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讨、采访、处置使,并致赦书,亦以蜡丸达之。真卿颁下河北诸郡,又遣人颁于河南、江、淮。由是诸道始知上即位于灵武,徇国之心益坚矣。”肃宗在即位以后立即以皇帝身份号令江南,无疑起到了坚凝人心的作用。虽然号令到达江南需要一定的时间,肃宗对江南地区行事的速度之快,应该是起到了作用的。要知道永王出兵东巡已经是在五个月以后了,毫无疑问肃宗以皇帝的身份号令江南,时间上肯定是走在永王前面,而且握有皇帝身份的政治优势,永王在江南号令不灵,应该也与肃宗事先已经有所准备有关。
肃宗利用政治上的优势,向江南地区安插亲信、策动和利用地方势力对抗永王。在永王璘到达江南地区时,肃宗已经完成了江南到江淮一线关键的人事安排,这一地区的地方实力人物,也已做好了联合对付的准备。肃宗灵武即位后,曾下诏命令永王璘去成都朝见,但永王拒不从命。这就给了肃宗以打击的借口。趁此机会,在永王从江陵出兵的几乎同时,肃宗于“十二月,置淮南节度使,领广陵等十二郡,以(高)适为之;置淮南西道节度使,领汝南等五郡,以来瑱为之;使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共图璘。”而韦陟为江东节度使也是肃宗任命以控制江南的:“肃宗即位于灵武,起为吴郡太守,兼江南东道采访使……会江东永王擅起兵,令陟招谕,除御史大夫,兼江东节度使”。韦陟等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平叛的军事行动,但也在瓦解永王璘势力,击灭永王军队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此前的十一月,肃宗还曾“诏宰相崔涣巡抚江南,补授官吏”,加强江南的人事控制。通过这一系列的人事安排,肃宗已经在人事上做好了应对永王的准备,肃宗任命的地方官员也已将江淮一带牢牢的控制在自己手中。
而且我们还不能忽略一点,就是肃宗及时采取措施,使江南的财政收入未全数落入永王手中。肃宗即位之后即利用皇帝之名通过第五琦开辟了汉水—洋州运输线,并得到了江淮租赋的支持。至德元年十月,也就是永王璘抵达江陵后的第二个月,先从蜀地见过玄宗时任监察御史、江淮租庸使的第五琦“见上于彭原,请以江淮租庸市轻货,泝江汉而上至洋川,令汉中王瑀陆运至扶风以助军;上从之,寻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史载,至德二年二月,肃宗到凤翔,“旬日,陇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汇,江淮庸调亦至洋川、汉中。”由此可知,在永王败死的当月,至少有一批江南的庸调已经运抵洋川和汉中。那么这一批庸调的启运则在永王失败之前很久了,因为此时漕运不通,庸调是由新开辟的曲折的陆上通道运抵的。对江南的经济情况了如指掌的刘晏,也于此时由肃宗任命为兼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领江淮租庸事,为肃宗控制江南财富。永王经略江南时,刘晏却拒绝支持,“永王璘署晏右职,固辞”。他还“与采访使李希言谋拒之。希言假晏守余杭,会战不利,走依晏。晏为陈可守计,因发义兵坚壁。会王败,欲转略州县,闻晏有备,自西陵西走。”这正说明在永王二月败死之前,肃宗已经获得当时江淮一带的财富支持,或者说江淮一带的财政已基本被肃宗控制。
永王璘举兵东下,肃宗已经在江淮一线构建了完善的军事布局,并迅速向永王璘发起了攻击。永王璘本无多少军事才能,手下将领临阵背离,仓皇之间又误判军情,草木皆兵,短短数月时间便一溃千里。永王本人也在兵败后欲南逃岭南,于途中被江西采访使皇甫侁诛杀。李白辅佐永王璘以成就“永嘉南渡”中兴唐室的政治理想,也就如流星一般坠入黑暗之中。
四、历史想象已无回响:再现“永嘉南渡”可能性的消除
永王败死对安史之乱前期的全国战局发展及安史之乱的平定进程,均造成了重要的影响。历史的发展确凿无疑地显示,唐王朝镇压这场叛乱最终所倚仗的,还是西北的朔方军以及回纥等部的军事力量。终唐一代,虽然江南的经济地位不断提升,但始终没有成为政治角逐的中心地带,永嘉南渡的历史也终究没有得到重演,这一发展趋势对永王的迅速处理相关,也与肃宗及其之后的政策相关。
一方面,唐中央王朝在永王之乱中加强了对江南一带的控制。虽然其后仍不乏有试图占据江南地区以图自立者,但影响力不及永王之乱,最后均以失败告终。安史之乱时期出现的较大规模的叛乱事件还有刘展之乱、袁晁之乱,均被迅速扑灭。此后一直到宣宗末年的裘甫之乱,江淮到江南一带的局势基本稳定,再未出现大规模的叛乱事件。这与唐朝后期北方藩镇林立,叛乱蜂起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贾二强先生注意到一个问题,唐王朝对安、史手下重要将领采用了招抚为主的政策,是河北藩镇之滥觞,而这一政策实际上在对付永王璘起兵时已露端倪。对唐朝廷来说,保持南方的稳定有利于保证稳定的赋税供给,维持政府的运转。当时朝廷所能有效控制的地区,主要为关中、淮南、江南东西、剑南、山南、岭南等道,大多数都在南方地区,可以说南方控制着唐朝廷的命脉。安史之乱以后主管过财政的权臣如刘晏、第五琦、元载等人多与平定永王之乱有关,这也很能说明熟悉南方情况的人在国家财政方面起的作用。唐宪宗时削除藩镇,也是先一举平定江淮,再削平河北势力,其他便望风而归,也正是因为江淮地位重要,需要首先平定。对于南方来说,维持稳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学界一般将唐朝后期南方经济的发展归结于人口南移因而有大规模的土地开垦及大修水利,或者圩田等生产方式促进了南方农业的发展,等等,但江南政治的稳定则是人口会南移的最大的吸引因素,也是能够安定地进行农业生产的基础。
另一方面,永王的失败标志着玄宗以宗室诸王抗击安史叛军的尝试破产,也标志着唐代诸侯王势力的彻底消失。肃宗以后,没有了独立的太子和亲王,也没有了独立的东宫、王府官设置。永王璘败死以后直到唐亡,再也没有宗室在地方发动过大规模的反叛行动,也没有宗室成员真正控制过地方军政。唐代后期地方的叛乱,多与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等社会政治问题结合在一起,而极少与诸王有关。随着藩镇力量的膨胀,李德裕曾经建议以宗室来限制藩镇势力:“制书听宗室年高者出阁,且除诸州上佐,使携共男女出外婚嫁”,然则这一建议“竟以议所除官不决而罢。”直到《新唐书》的作者,还在感叹唐代后期应该使用分封制来解决藩镇问题:“救土崩之难,莫如建诸侯;削尾大之势,莫如置守宰。”当然这样的观点也有不少的反对者,柳宗元的《封建论》更为人们所熟知。直到唐末昭宗时期,又提出以诸王典兵来限制藩镇的做法,但此时的皇帝已经成了藩镇手中的傀儡。这时候,韩建要求撤销命制的重要理由就是永王之乱:“玄宗之末,永王璘暂出江南,遽谋不轨。代宗时吐蕃入寇,光启中朱玫乱常,皆援立宗支以系人望。今诸王衔命四方者,乞皆召还。”从此之后,唐宗室、皇子一直被养在深宫,直到最后被梁太祖朱温一网打尽。五代十国时期,打着唐王朝旗号的两个政权后唐和南唐,其君主事实上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李唐宗室或后代。
通过扼杀“永嘉南渡”的两个要件,即防止江南势力的坐大和控制能够号令江南的宗室成员,唐王朝顺利地实现了控御江南的目的。因此,永王璘事件成为了安史之乱过程中的一个插曲,同时也是唐代政治史上的一个插曲。肃宗对永王璘的快速处置,随之带来的江南地区的稳定与宗室诸王力量的消歇,终于使得永嘉南渡重演的可能性就此消失。永王璘事件没能在历史上留下如同安史之乱一般的记载,也不曾留下藩镇割据这般影响深远的政治局面,李白将永王东巡比作永嘉南渡的历史意识,也就再也没有在史书上出现了。《旧五代史》记载南唐先主李昪“自云唐明皇第六子永王璘之裔”,则成为这一事件最后泛起的一点涟漪,也仅仅如此了。
五、结语:李白的政治判断与“从逆”的历史评价
唐代历史的发展对重现“永嘉南渡”的可能性判了死刑,而主持其事的永王也以被肃宗宣布为“叛逆”为标志而打入历史的冷宫。史家认为,李璘身为皇子,“不能立忠孝之节,为社稷之谋,而乃聚兵江上,规为己利,不义不昵,以灾其身”,从道德方面谴责其不忠不义的悖逆行为,这一批评也一直延续。永嘉南渡的历史不再重演,永王事件的在史书中的痕迹也渐渐淡化,甚至对这一道德评判争议都极少出现。虽有现代学者指出所谓永王璘“叛逆”案纯属唐肃宗制造的冤案,应予彻底推翻,但这种呼吁已在千年之后了。历史终究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叛逆”与“中兴”之间隔着成王败寇的逻辑。
永王璘的败死无疑也是李白政治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次转折。对于李白从璘事件,朱熹批评说:“李白见永王璘反,便从臾之,文人之没头脑乃尔!”朱子的话是从永王璘失败后的历史进行“倒放电影”式的观照而说的。如果对历史的解读不能获得现实政治发展的验证,那么后世的史家以及其他政治行为体很可能对这种解释失去兴趣,因而不再关注这类历史可能性的存在。永王既已在道德上被打入了“叛逆”的标签,永嘉南渡的历史也不再重演,李白的政治选择不免要被后人看得幼稚而荒诞。不过若是站在古人的立场上细致地分析这种判断产生的历史背景,注意历史进程中的各种偶然因素和突发事件,就能理解李白的政治选择在当时也未必就没有合理性。
〔注释〕
①关于李白从永王璘事的研究很多,代表性的论著可参见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 年,第80—106 页;张天来:《李白“从璘”事辨析》,《社会科学研究》,1981 年,第2 期;寇养厚:《永王东巡与〈永王东巡歌〉》,《山西大学学报》,1984 年,第3 期;邓小军:《永王璘案真相——并释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文学遗产》,2010 年,第5 期等。
②肃宗七月甲子日即位,玄宗当月丁卯日下诏永王出镇,中间只隔三天,在当时的条件下,玄宗也不大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知道肃宗即位的消息。史料也明确记载,直到八月癸巳,灵武使者至蜀,玄宗方才得到太子亨已即位的明确信息。
③参见《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第一册,第230 页;又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第十五册,第6940 页。玄宗以皇子出镇犹在此之前,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禄山反于范阳当月,玄宗即“以荣王琬(玄宗第六子)为元帅,命高仙芝副之,于京城招募,号曰天武军,其众十万”,随即开赴前线,参见《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第一册,第230 页;“制以琬为征讨元帅,高仙芝为副,令仙芝征河、陇兵募屯于陕郡以御之。”参见《旧唐书》卷一百七《靖恭太子琬传》,第十册,第3261—3262 页。
④参见张忱石:《建康实录·点校说明》,中华书局,1986 年,第3-6 页;谢秉洪:《<建康实录>作者与成书时代新论》,《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5 期。二著均对王鸣盛的观点有深入考证和补充。
〔1〕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
〔3〕(梁)萧统.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宋)葛立方.韵语阳秋(何文焕《历代诗话》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6〕贾二强.唐永王李璘起兵事发微[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1).
〔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8〕(五代)刘煦.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唐)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0〕刘浦江.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J].文史,2013(2).
〔11〕(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12〕(宋)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3〕邓小军.永王璘案真相——并释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J].文学遗产,2010(5).
〔14〕(宋)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