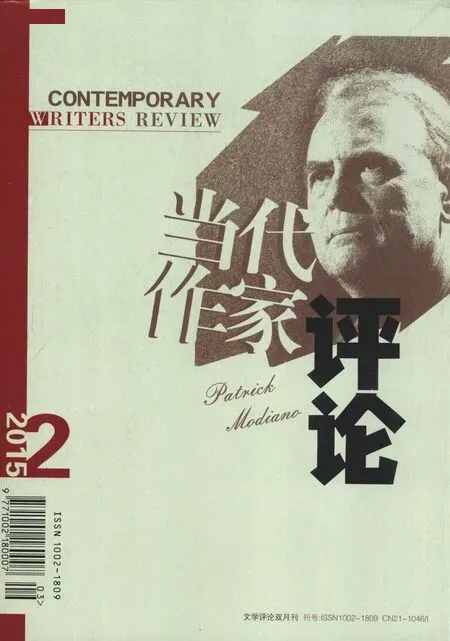作为历史编纂元小说的《星形广场》
2015-11-14张志玮
张志玮
“我未出生便有了记忆”,这是莫迪亚诺小说中一句经典的悖论。二○一四年诺奖组委会为莫里亚诺准备的颁奖词正是“他以记忆之艺术唤醒了那最不可捉摸的人类命运并揭示了二战中占领时期的生活世界”。而事实上一九四五年才出生的莫迪亚诺,对于二战的记忆又从何谈起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二战的过往对于莫迪亚诺而言只能以一种被加工的方式被知晓,因为他不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但与此同时,作为拥有一半犹太血统的战后一代,莫迪亚诺却始终感觉历史如幽灵一样与他如影随形。他的处女作《星形广场》(一九六八)就是这样一部被历史施了魔的作品,而小说中典型的后现代叙事特点也为后现代小说的发展开创了先河。
本文将以加拿大后现代理论学者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在其著作《后现代诗学》(一九八八)中提出的“历史编纂元小说”(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概念为主要理论依据来解读《星形广场》。莫里亚诺的《星形广场》发表于一九六八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佩里·安德森在描述六十年代的法国思想界是这样总结的:“主体消亡”成为了这“十年的口号”。当然一九六○-一九七○年代正值后结构主义奠基人——宣称“人已死”的福柯与宣称“哲学已死”的德里达最为多产的时期。不过即使是在前福柯、德里达时代,法语世界也仍旧不乏撼动欧洲思想界甚至世界思想界的强大声音。从开创现代语言学的索绪尔(瑞士法语区),到结构主义人类学奠基人列维施特劳斯;从传承与改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拉康,再到为马克思主义注入新血液的阿尔都塞,一种被传统人文主义所笃信的“人类中心主义”甚至在后现代主义到来之前就已遭到了来自不同知识领域的质疑。这些皆用法语写作的学者无疑将这个国家推上了这场挑战传统人文主义的主战场,法兰西这片独特的知识土壤不仅滋养了随之而来的后现代精神,也为莫迪亚诺在文学领域的探索提供了温床。
然而与流行于一九五○-一九六○年代的法国新小说不同,莫迪亚诺的《星形广场》不仅将二战时期巴黎被占领的历史作为了小说的背景,更把对这段历史精妙地糅合进了作品的叙述之中。这与主张“由重视历史和社会现实转而重视意识”的法国新小说迥然不同。法国新小说在歌颂文学的原创性与作者自主性的同时将现代文学带入了一种为创新而创新,为形式而形式的尴尬之境。才从现实主义宏大叙事中逃脱出来的文学,却在新一轮现代主义的激进试验中沦为了文字游戏。然而,随着后结构主义对于主体的解构和对形而上人类意识(或无意识)的批判,已处在象牙塔中的现代文学连最后根基也随之松动了——人类意识(或无意识)无法再为文学提供一个安稳的落脚点。曾经构筑在逻各斯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根基之上的西方文学圣殿正面临崩塌。西方文学开始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型,而莫迪亚诺的《星形广场》正是这个历史时期的产物。
后现代主义历史观与历史编纂元小说
随着后结构主义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接受,后德里达与福柯时期的学者们对于大写历史的虚妄性有了明显的批判意识。其中以格林布拉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就对历史做了新的注解。如王宁教授所讲:“按照新历史主义者的看法,历史的叙述并不等同与历史的事件本身,任何一种对历史的文字描述都只能是一种历史的叙述(historical narrative)或编纂史(historiography),或元历史(metahistory),或文本话的历史,其科学性和客观性是大值得怀疑的。因为在撰史的背后起到主宰作用的是一种强势话语的霸权和权力的运作机制。”美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通过对历史叙述进行修辞学分析得出了结论,即历史叙述与文学叙述在话语结构上并无实质差别。总之,后现代的历史哲学观正在经历从“本体论”走向“认识论”的过程。当然形而上的宏大历史叙述尽管被拉下了神坛却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相反,后现代学者更加强调了我们重访历史的必要,但这种重访必须带着一种批判性的自省意识。即在了解历史叙述不可靠的同时意识到自己是这种不可靠的历史叙述的产物。如格林布拉特的那句名言“我的声音是那些已逝者的声音”同样莫迪亚诺所称的“我未出生就有了记忆”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在这两种叙述中,“我”这个主体已经不再重要,记忆与已逝者的声音已经将我表达。
然而面对一切已经被历史化的事实,后现代文学又将何去何从呢?悲观者如詹明信,他认为文学作品曾经的深度已被后现代的表面化替代,肤浅的拼凑(pastiche)成为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标志。而乐观者如琳达哈琴,她并不完全认同后现代小说仅是肤浅拼凑,相反在她的著作《后现代诗学》中,哈琴不仅为后现代小说予以正名,更提出了“历史编纂元小说”(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的概念。她认为后现代小说的深邃之处正在于它对文学创作所面临的后现代悖论有着深刻的认识。依照哈琴的定义,这类小说通常指那些“知名的流行小说,它们既包含深刻的自我反映(self-reflective),又悖论式地引入了历史事件与人物”。这些历史编纂元小说的作者深谙后现代理论关于模糊历史与文学边界的论述,并对“文学与历史皆为人造物有着明确的自省”,因此他们对于小说的处理形式通常是,既提及到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或人物,又出于对历史叙述的不信任而混以讽刺的戏仿。同时,这类作品也对自己的创作进行批判,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小说亦是历史叙述的产物,是“被历史化”的文本,因此他们会有意无意暴露小说被编写的过程,或是为读者揭示出小说叙述的不可信性。历史编纂元小说的作者正是用自己的文学实践着对于“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深刻认识。然而在这种实践中,他们也必须面对一种矛盾,如哈琴所描述的,“后现代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文化事业。它深陷其所指责的体系和价值却又试图通过使用和妄用它来与之较量。”因此历史编纂元小说,并非表面上看来的那样是仅仅是对过去进行碎片式的拼凑,而是一种兼具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后现代小说类型。
这类被哈琴归于临时编纂元小说的作品包括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艾柯的《玫瑰之名》、汤婷婷的《女勇士》、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和巴斯的《烟草经纪人》等。很显然这种分类并不属于某位作家的特权,而是针对文学作品的具体叙述形式来进行的归纳。尽管在哈琴的列表中并没有包含莫迪亚诺的作品。但细读莫迪亚诺的《星形广场》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小说具备明显的后现代历史编纂元小说的特征。但或许由于英译本的缺失,这部优秀作品的流通范围和知晓程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限制。
《星形广场》中“小写的历史”与“反英雄”
历史的回归可以说是文学由现代转向后现代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历史的这次回归却失去了它曾经稳定的本质根基。后现代对于历史叙述的矛盾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它在强调历史叙述强大建构力的同时,又揭示了历史叙述本身被建构的事实。大写的历史尽管正在失去它的合法性,却不可否定地仍旧在操控它所建构的体系。因此对于大写历史的审判不能是缄默置之,而是要在新的语境下重提历史,而重提的意义在于引入小写的历史——那些被掩盖的或是徘徊在中心之外的边缘历史,并通过小写历史对抗形而上的宏大叙事。《星形广场》中我们正看到了拉法埃尔·什勒米洛维奇——这个在二战占领时期混迹在巴黎并靠通敌和拉皮条苟且营生的犹太主人公。小说以引用一大段辱骂拉法埃尔的信件开篇:“……什勒米洛维奇?……哼!犹太人街区的烂货,臭气熏天!……毛坑里的大蛆!……黎巴嫩加纳克的流氓!……”这种道德败坏的主人公一出场便颠覆了本该属于那段历史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叙述。拉法埃尔这种无德小人物的故事打破了某种“常规且合理”的历史叙述。同样的文学手法我们也可以在约瑟夫·海勒的后现代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看到。两部小说都是通过这类反英雄揭示了整个二战的荒谬性,无论是法西斯轴心国还是反法西斯同盟,正义不属于任何一方,因为战争的正义根本不存在。
小说的主人公“我”拉法埃尔是一个成长在巴黎的犹太人,然而“我”的犹太身份始终把“我”排斥在法国的主流社会之外。尽管“我”比法国人更熟稔这个国家的文学和历史,然而我“不是这个国家的孩子”,“我的行为举止也同培养法国人的品德背道而驰:他们弘扬谨慎、节俭和勤劳。我的祖先是东方人,黑眼睛,喜欢张扬和排场,并且懒惰成性”。身为犹太人的“我”在一个存在着严重种族歧视的法国,只是一个二等公民,一只丧家犬”。然而也只有通过“我”这样一个反英雄,反法西斯正义光环下肮脏和虚伪的巴黎社会才能被揭露。小说不断在历史与虚构间穿插闪回。在小说中“我”的故事被构建在种种真实的历史事件上,如在法国甚至世界造成巨大影响的德雷福斯事件。“我”一个犹太人,只能从德雷福斯的事件中吸取教训,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纳粹通敌者,一个拐卖白人妇女的皮条客,因为“我”被剥夺了效忠法国的资格。
尽管“我”曾经试图融入这个国家,但“我”最终无法摆脱自己异族身份的历史与梦魇。曾经在T镇,一个远离肮脏与堕落城市的法国外省,当“我”在行使一个“拐卖白人少女卖淫”的任务途中,“我”犹豫了。“不,我绝不能将天真烂漫的洛依佳提供给巴西色情业。我要扎下来,在T镇隐居了。我就当小学老师,过平静而普通的生活。”然而当“我满怀如此美好的决心,开始起飞了,动身去教授法国历史。我给学生上的一堂课,毫无节制地赞扬贞德。我投身每一次的十字军征战,在布维讷,罗克鲁瓦和阿科尔桥战斗。唉!我很快发觉,我没有那种 furia francese(法兰西愤怒)。”“我”更无法赞美十字军屠戮犹太人的历史。因此“我”必须放弃这个“美好的决心”,“我”写下忏悔书谴责自己对法国的手软,并最终交出了洛依佳。“写完这份忏悔书,世界又恢复了我喜爱的颜色。”拉法埃尔无法摆脱的是被西方历史书写的身份,在这部历史中,犹太人只能是叛徒、仇人、骗子、流浪者。然而拉法埃尔却清楚“也仅仅始于十五世纪,我是犹太人。他们是高卢人。他们一直在迫害我”。对于这种民族身份的虚构性和虚伪性,小说中本就有了交代。“并不存在犹太人,这是雅利安人的一种编造。”但即使知道犹太民族被建构的身份,拉法埃尔也无力反抗那纵然是编造却一直行使有效的历史叙述。作为一个被边缘化、被歧视的少数族裔,拉法埃尔无法冲破自己被书写的历史命运。“我憎恨害得我好苦的谎言”,但“我”却只能在这个谎言中感到,“世界又恢复了我喜爱的颜色”。这种辛辣的讽刺正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在面对他所批判的庞大体系时感到的矛盾与无力。
《星形广场》中的互文与戏仿
在《星形广场》并不算长的篇幅中,充斥着许多对文学作品的互文和对历史事件的戏仿。很多时候莫迪亚诺笔下的拉法埃尔正是在借用历史文人的话语叙述自己的故事。这种互文手法的运用充分体现了作品的后现代特点。与现代主义不同,后现代主义放弃了对“新形式”与“原创性”的追求,而转向了“过去的在场(The Presence of the Past)”。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一切所谓的“原创”都只不过是对过去文本的某种互文,真正的原创根本不存在。后现代作家安伯托艾柯认为对于后现代作家而言,“过去是无法避免的,它只能以一种不再天真的,讽刺的,戏仿的手段被再现和再使用”。在《星形广场》中,主人公拉法埃尔不断提及如拉辛、普鲁斯特、萨特、热内、蒙田、卡夫卡、歌德等作家的作品。一方面,这种互文体现了后现代作家对德里达“文本之外无他物”的某种认可,并揭示了自己只能在前人文本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事实;另一方面,这种互文也是对已存在的文本进行一种批判式的重读。小说中拉法埃尔无法从法国的文学中找到自己的归属。“而我,拉法埃尔·什勒米洛维奇,除了一个无国籍的穷苦少年,我还能谈论什么少年呢?我既不可能成为杰拉尔·德·涅瓦尔,也不可能成为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更不可能成为马塞尔·普鲁斯特。我没有什么瓦卢瓦那种地方温暖我的心灵,也没有吉耶讷地区,也没有康布雷镇。”就连在因为肺结核而想到自杀的时候“我”似乎都不够资格。“我倒是可以自杀。经过三思,我决定不能留下俊美的仪容。遗容那么美,他们又该把我比作雏鹰或者维特了。”(《雏鹰》是由法国作家罗斯唐创作的一部剧本,讲述的是死于肺结核的拿破仑二世短暂的一生)不难看出这种互文的目的在于嘲讽。这些被公认为人类最伟大的文学,无疑是经挑选的适合“他们”的文学,而对于“我”这个浪迹在社会边缘的犹太青年,却无法从“他们”的文学中获取安慰。
莫迪亚诺除了讽刺的引入互文作品之外,还戏仿了某些文学作品。如小说中,由拉法埃尔撰写的文章《雅各布X的忏悔》成为了萨特一篇文章的主要题材。小说中,萨特以一篇名为《圣雅各布 X,喜剧演员和殉道者》的文章为拉法埃尔虚构的“圣雅各布 X”做了辩护,并恳求雅各布 X公开自己的姓名。事实上,萨特确实写过一篇名为《喜剧演员和殉道者圣热内》的文章。文章本是关于法国的流浪作家让·热内的,但小说中却被偷梁换柱成了由拉法埃尔臆造出的一个人物。这种对于已存在的文本进行改写同样也是后现代小说的一种典型做法,如库切戏仿《鲁滨逊漂流记》的小说《福》。这种改写既基于后现代作者对于文本意义开放性的理解,又基于他们想要通过改写来实现对抗旧文本的目的。选择戏仿萨特的文章无疑表明了叙述者的某种立场,那就是对于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怀疑。尽管萨特作为一名著名知识分子曾在许多文章中宣扬了自己支持犹太人的立场和反种族歧视的观点。但萨特哲学所强调的“选择的自由”,在主人公拉法埃尔面前不过是“乌托邦”。牵绊这种自由的正是“过去”或是说历史。在历史的宏大叙述中,每个个人都被牵涉其中,无从选择。在小说的结尾,弗洛伊德强烈介意“我”看一看萨特的《关于犹太问题的思考》,因为他希望我能认同萨特的观点,即“犹太人并不存在”,从而治好我的“犹太妄想症”。而“我”即使认同萨特对于“犹太人没有本质的存在”的观点,却无法摆脱千百年来犹太人被书写的“存在”。这种被书写的历史就是莫迪亚诺所要控诉的“记忆”,它发生在“我出生前”,让我无法选择。
除了对已写文学的改写,小说中也充斥着对历史事件的改写。拉法埃尔时而会被描述成希特勒情人爱娃的情夫,并和希特勒一起在伯格霍夫别墅谈笑风生。“从一九三五年起,我成了爱娃·布莱恩的情夫。希特勒首相总是把她一个人丢在贝希特斯加登……我是在伯格霍夫别墅周围转悠时,头一次碰见爱娃。彼此一见钟情。希特勒每月来一次上萨尔兹堡。我们相处得很好。他诚心诚意接受,我在爱娃身边充当骑士的角色。这一切在他看来无足挂齿……晚间,他向我们谈论他的计划。我们就像两个孩子似的听他讲。”这种荒诞的历史重写,在重访历史的同时戏弄了历史。几乎可以断定莫迪亚诺在小说中对二战历史的重提,既不是为了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真相,更不是质疑二战中犹太人的惨痛遭遇。他的目的正是为了讽刺整场战争的恐怖与荒谬。当拉法埃尔宣称:“能从希特勒手中接过十字勋章的,也只有我这一个犹太人。”这种讽刺非但没有减轻这段历史的重量,反而加重了历史中犹太人物的悲情。“我的脑袋爆开,但不清楚是子弹打的,还是乐开了花。”而这种犹太式的笑,几乎伴随了所有小说中被杀害的犹太人物,而这种笑比哭更令人悲恸。
事实上,莫迪亚诺本人是一个非常尊重历史的作家,他尊重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记录,并小心地将这些记录复制在自己的小说中,尤其是在他的“占领”三部曲中,他对地点和历史事件描述的准确性几乎无可挑剔。在小说中二战中被杀害的“六百万犹太人”总被反复提起,对于莫迪亚诺而言,这个数字不但不可以被否定反而需要被铭记。他本人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质疑历史叙事的真实与公正。但他却从未否定过历史,相反他认为每个人都是他之前历史的产物。正如他在法国《读书》杂志的访谈中所讲到的:“我总觉得自己是污浊时代的产物,是战争的产物。人们总是在谈论‘占领时期’,可对我而言,却并非是无缘无故的。”
《星形广场》中的自我反映
当然除了对历史素材进行运用和重加工,历史编纂元小说的另一个特点则是它的自我反映,即小说必须对自己文本的虚构性进行揭露。换句话说,说它必须具有出某种元小说(metafiction)的特点。在小说的尾声,当小说中的“我”兼叙述者拉法埃尔被杀死后,另一个叙述者“我”又出现了。这位叙述者还是拉法埃尔吗?显然拉法埃尔已经死了,而这个“我”也并不是拉法埃尔的同龄人。这个“我”是在拉法埃尔被枪杀后醒来的,当时“我”床头站着弗洛伊德,他告诉“我”,“我”是被他的几名护士在码头救起来的,“我”不是犹太人,“我”仅仅是产生了幻觉。弗洛伊德告诉“我”,“希姆莱已经死了,当时您还没有出生,怎么可能记得这些事情。”虽然这个突然插入的身份不明的叙述者只出现在了小说的结尾处,但却足以颠覆整部小说叙事的可靠性。这个叙述者的介入让整个拉法埃尔的故事成为了一种幻觉或是一个梦,因为这个叙述者“我”根本无法拥有拉法埃尔的故事,“我”既不是犹太人,更没经历过那段历史。这种对于小说虚构性的自我反映,目的是为了揭示文学文本无非是一种历史化的叙述,因此在对历史叙事进行批判性揭露的同时,也必须要对自己的文本进行自我揭露。这种双重反映是后现代历史编纂元小说与现代主义元小说最大的不同处。
《星形广场》的发表让当时只有二十三岁的莫迪亚诺在法国瞬间成名。尽管《星形广场》是他在文学领域的第一次尝试,但其收获的反响和奖项都足以为这位年轻的作家带来巨大的信心和创作热情。在接下来的四十多年中,莫迪亚诺一直坚持着他的文学创作,并不断推出新的作品。莫迪亚诺的文学作品并不拘泥于一种固定的形式,其作品的深刻性与丰富性最终让他荣膺文学殿堂的最高殊荣——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