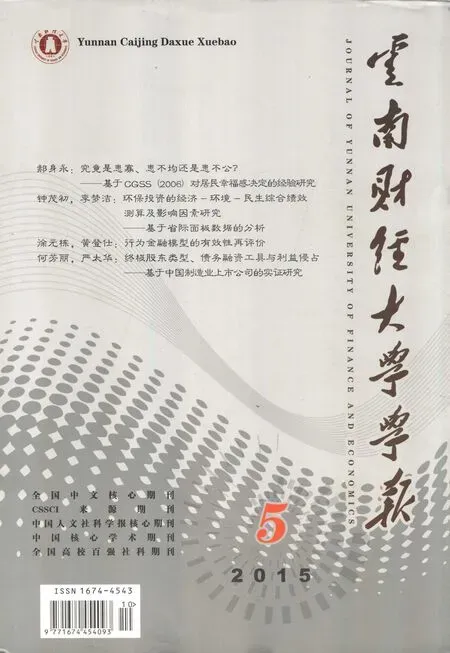终极股东类型、债务融资工具与利益侵占——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2015-11-13何芳丽严太华
何芳丽,严太华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400044)
一、引言
Claessens等(2000)发现超过2/3的东亚上市公司是由单一大股东控制,这些大股东通常利用双重持股、交叉持股或金字塔结构的方式建立控制权和现金流权之间的分离。[1]多数研究表明,这种新型的两权分离会促使控制股东对小股东进行利益侵占,[2~5]此时,债务融资不但不具有治理效应,反而为终极股东提供了可控的资源,方便了终极股东对上市公司进行利益侵占。[6~10]然而,不同的终极股东类型对上市公司实施的控制目的不尽相同,他们对上市公司实施的利益侵占程度也不同;另外,不同债务工具所对应的债权人,他们对债务人的监督和约束能力存在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类型的终极股东是如何通过不同类型的债务工具进行利益侵占的?或者,不同类型的债务工具在终极股东的侵占行为中起到了怎样的调节作用?相关的研究尚未发现,为此,本文将在金字塔控股结构下,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实证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同时考虑了终极股东类型和债务融资工具对终极股东侵占行为的影响,丰富了终极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的研究内容;(2)将具体的债务融资工具(银行债务、公司债券及商业信用)作为终极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实施利益侵占的一个调节变量引入研究模型中,更直接具体地度量了不同债务融资工具对终极控股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的调节作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终极控股股东类型与利益侵占
在参考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将终极控制股东的类型分为:中央政府控股、地方政府控股、家族控股和其他特殊法人控股,由于前三种控股类型比较典型且在我们的样本中约占94%,故本文主要探讨中央政府控股、地方政府控股和家族控股的利益侵占行为。不同类型的终极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目的存在差异,中央政府控股更注重国家稳定与发展,地方政府控股注重地方经济效益,家族控股注重自身私利,故地方政府控股和家族控股具有较强的掏空动机,而中央政府控股的掏空动机较弱。[4]夏立军和方秩强(2005)指出,由于行政分权,中央政府的角色更像是一个委托人,而地方政府的角色更类似于一个代理人,相对于中央政府控股,地方政府控股的终极股东侵占行为更严重。[11]冯旭南(2012)的研究发现,家族控制人侵占中小股东利益问题已经非常严重。[8]黎来芳等(2008)从资金占用角度研究终极股东的侵占行为,实证研究表明,相对于国家终极控制的上市公司,私人终极控制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规模更高,即私人终极控股股东的侵占行为比国家终极股东的侵占行为更严重。[12]白云霞等(2013)也认为,与国有大股东相比,私有大股东通过负债方式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程度较高。[9]为此,提出假设:
H1:相对来说,中央政府控股股东的侵占行为最弱,家族控股股东的侵占行为最强,地方政府控股股东的侵占行为居中。
(二)债务融资工具与治理效应
按照债务融资来源的主要方式,将债务融资工具分为:银行债务、公司债券及商业信用,不同的债务融资工具对债务人的监督约束方式不尽相同。
在有关银行债务治理效应的经典文献中,所讨论的主要是私有银行,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债务被认为是监督约束作用最强的债务,因为银行债务的所有权非常集中,且银行作为业内人士可以获取私人信息,这使得银行有动力也有能力发挥债权监督约束作用。[13]然而,在我国目前的借贷市场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集中了主要的信贷资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国有性质的商业银行充当了政府的政策性工具,其相应的贷款通常具有某些政治目的,并非都是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银行债务治理效应受到质疑。另外,在银行债务中普遍存在预算软约束现象,这进一步弱化了银行的监督约束作用,使得银行债务并未发挥应有的债务治理效应,反而表现出治理效应恶化现象。[14~15]
公司债券的所有权是分散的,搭便车问题导致单个债权人没有监管掠夺或投机活动的动力,即便是有债权者自愿去监管,但监管的成本会远远高于银行监管的成本,故公司债券的监管是无效率的。[16]然而,正是由于公司债券的所有者比较分散,使得公司面临债务违约时很难通过重新谈判方式避免清算,从而公司债券具有债务硬约束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挥债务治理效应。另外,我国实施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缓解了公司债券所有者过于分散带来的监管无效率现象。公司债券的硬约束作用及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的实施,使得公司债券具有明显正面的治理效应。[14]
商业信用的债权人比较分散,且单笔交易的金额一般较小,商业信用债权人对债务人基本上没有约束,主要表现在事前无保障、事中监控难、事后维权难等问题,[17]这很难说明商业信用具有较强的治理效应。然而,商业信用也有监督优势,在商业信用供给关系中,供给者一般是上游企业,获得者是下游企业,作为商业信用供应商的上游企业具有信息获取优势、对客户的控制力优势及财产挽回优势。[18]杨勇(2009)的研究表明,商业信用融资能够改善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15]
综上所述,各种债务融资工具都存在治理效应的一面,但这种治理效应的充分发挥依赖于债权人是否有能力和动力去实施监督约束。
(三)中央政府控股、债务融资工具与利益侵占
中央政府控股的公司主要涉及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且在行业中处于龙头地位,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服务。由于中央政府控股的目标是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相应的侵占动机较弱,所以通常银行债务和公司债券的治理效应应该都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挥,至少不会引起终极股东实施利益侵占。一方面,公司债券的硬约束可以约束具有较弱侵占动机的终极股东;另一方面,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控股股东也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没必要为了把“左边口袋”的财物放进“右边口袋”而实施利益侵占行为。但是,商业信用的治理效应却不一定得到发挥,因为中央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处于龙头地位,在商业信用供给关系中处于买方垄断地位,商业信用的卖方即商业信用的债权人有动力但没能力去实施监督约束。为此,提出假设:
H2:商业信用对中央政府控股股东的侵占行为影响较强,而公司债券、银行债务对侵占行为的影响较弱。
(四)地方政府控股、债务融资工具与利益侵占
地方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注重地方经济效益,由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资源竞争,因此,与中央政府控股股东相比,地方政府控股股东的侵占动机有所增强。此时,由于软预算约束,银行没有动力实施监督约束。一方面,由于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通常就是国有企业,这些公司享受政府隐性担保带来的融资便利,无需经过严格的审核程序就能获得银行贷款;另一方面,由于不存在债务违约风险,即便债务违约也会由政府买单,所以在放贷后,银行对借贷公司并不积极监督。从而,事先的不严格审核,事后的无监督状态,使得具有较强侵占动机的地方政府控股股东为了谋取私利而对中小股东或外部投资者实施利益侵占。类似的,由于地方政府控股股东具有较强的利益侵占动机,公司债券的硬约束得到弱化,而地方政府控股的国有性质使得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的监督机制得到弱化,产生弱制度效应,从而公司债券的治理效应未能得到发挥。然而,对于地方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来说,商业信用可能得到发挥,因为作为商业信用买方的地方政府控股公司,已经不再是行业龙头企业,其买方垄断地位较弱,或者,更多情况下在买卖中处于弱势地位,此时,商业信用的供给者有能力和动力实施监督约束。从而,如果地方政府控股股东通过债务融资实施利益侵占,那么终极股东最有可能通过银行债务和公司债券融资工具进行侵占,为此,提出假设:
H3:银行债务和公司债券对地方政府控股股东的侵占行为影响较强,商业信用对侵占行为的影响较弱。
(五)家族控股、债务融资工具与利益侵占
家族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控制的目的是获取自身私利,侵占动机非常强。面对家族控股股东存在强烈的侵占动机,银行债务并未发挥应有的债务治理效应,冯旭南(2012)的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用短期债务融资还是长期债务融资来衡量,银行借款行为都反映了家族终极控制人的掠夺动机。[8]类似的,商业信用的治理效应也很难得到发挥,尽管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在商业信用的买卖关系中不存在垄断地位,商业信用供应商具有信息获取优势、对客户的控制力优势及财产挽回优势,但我国法律制度环境薄弱,通常出现事中监控难、事后维权难等问题。然而,公司债券的治理效应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挥,因为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公司债券在发行前需要通过严格的审核,而且在发行时也具有约束条款,一般的公司,尤其是家族控制的民营企业,很难有机会发行公司债券,鉴于公司债券的来之不易,终极股东不会轻易通过公司债券实施利益侵占。另外,与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相比,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对家族控股公司的监督效应也更能得到发挥。为此,提出假设:
H4:银行债务和商业信用对家族控股股东的侵占行为影响较强,公司债券对侵占行为的影响较弱。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变量定义及描述
终极股东利益侵占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也是本文的关键变量,用Tunnel表示,现有文献对该变量的直接度量方式略有不同。比如,刘运国等(2009)使用“经营性资金净占用/总资产”和“非经营性资金净占用/总资产”及其之和来度量。[4]马曙光等(2005)及韩亮亮等(2013)使用“其他应收款/总资产”来度量。[19~20]陈红等(2012)使用“(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总资产”来度量。[5]由于刘运国等(2009)的经营性资金净占用包含“应收账款和预付账款”两个会计科目,而这两个科目也正好是本文所使用的解释变量(信用债务)的主要部分,故刘运国的度量方式不适合本文。马曙光等(2005)及韩亮亮等(2013)的度量方式仅仅考虑了终极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并未考虑终极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输血”等利益输入方面。为了较全面地度量终极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本文采用陈红等(2012)的度量方式,定义Tunnel=(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总资产,若Tunnel<0,则可视为终极股东为了自身长远利益所作出的支持行为,也称“负侵占行为”。[5]
相关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明细表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由于金字塔控股结构是我国上市公司的一个显著特征,并且上市公司中有较大比例是制造业(2007年约占60%),故本文的研究选取在上海和深圳两个交易所上市的具有金字塔控制结构的制造业公司在2007~2013之间的年度数据,并通过如下方式筛选样本:(1)剔除B股和H股公司;(2)剔除样本期间内有数据缺失的公司;(3)剔除样本期间内股票被特别处理的公司;(4)剔除无法找到终极控股股东的公司。最终得到3166个样本点,其中2007年321个样本,2008年 343个样本,2009年 382个样本,2010年476个样本,2011年515个样本,2012年573个样本,2013年556个样本。公司的特征数据均来源于CCERDATA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深圳国泰安CSMAR数据库。
(三)计量模型的建立
根据假设,建立以下模型:

其中,Debt是债务类型的统称,在本文中分别为银行债务(Bank)、公司债券(Bond)及商业信用(Tc);Ownership是终极控股股东类型的统称,在本文中分别为中央政府控股(Cstate)、地方政府控股(Lstate)及家族控股(Family);γ'=(γ1,……,γ12),是控制向量 Controls'=(Lev,Logassets,profit,Q,Tangibility,Z_score,Indou1,…,Indou9,Year1,…Year6)的回归系数向量,ε 为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将被解释变量及调节变量按照不同的样本组作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从全样本来看,Tunnel的最小值是-0.4322,最大值是0.4794,且均值和中位数都是负数,说明在样本中,大部分终极股东对上市公司是实施支持行为;不同终极股东类型对上市公司实施利益侵占的程度有所不同,家族控股的Tunnel变量的均值和中位数都大于政府控股的均值和中位数,说明家族控股的侵占程度高于政府控股。关于三种债务类型的使用情况,总体上,银行债务和商业信用的债务规模相差不大,公司债券的规模较小,由公司债券的中位数为零,说明样本中有一半以上的公司没有发行公司债券;按终极股东类型分组后,地方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其银行债务、公司债券及商业信用的使用量都居于首位;在银行债务和商业信用使用方面,中央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高于家族控股的上市公司;家族控股的上市公司使用公司债券水平高于中央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

表2 被解释变量及调节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二)计量模型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1.终极股东类型与利益侵占行为
表3检验了不同终极股东类型的侵占行为,表3中的第(1)~(4)列表明,不管是否有控制变量,中央政府控股、地方政府控股与Tunnel(利益侵占)都是显著负相关,说明政府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实施负侵占行为,即支持行为;而第(7)列和第(8)列中Lstate系数的绝对值小于Cstate系数的绝对值,说明地方政府控股的支持力度弱于中央政府控股的支持力度;第(5)列和第(6)列表明,不管是否有控制变量,家族控股与Tunnel(利益侵占)都是显著正相关,说明家族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实施侵占行为。综上分析,假设1得到验证。
2.中央政府控股、债务融资工具与利益侵占行为
表4主要是检验债务融资工具对中央政府控股股东利益侵占的调节效应。表4的第(1)列和(2)列表明,中央政府控股与银行债务及公司债券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说明银行债务及公司债券对中央政府控股的侵占行为没有调节效应;第(3)列中的中央政府控股与商业信用的交互作用显著为正,说明中央政府控股股东通过商业信用实施了利益侵占,商业信用削弱了中央政府控股的支持行为,假设2得到验证。

表3 终极股东类型与利益侵占的回归结果

表4 中央政府控股、债务工具与利益侵占的回归结果
3.地方政府控股、债务融资工具与利益侵占行为
表5主要是检验债务融资工具对地方政府控股股东利益侵占的调节效应。表5的第(1)列和第(2)列表明,地方政府控股与银行债务及公司债券的交互作用显著为正,说明银行债务及公司债券对地方政府控股的侵占行为有正的调节效应,即:地方政府控股股东通过银行债务和公司债券实施了利益侵占,银行债务和公司债券削弱了地方政府控股的支持行为;第(3)列中地方政府控股与商业信用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说明商业信用对地方政府控股的侵占行为不存在调节效应,假设3得到验证。

表5 地方政府控股、债务工具与利益侵占的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检验的标准误,***、**和*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4.家族控股、债务融资工具与利益侵占行为
表6主要是检验债务融资工具对家族控股股东利益侵占的调节效应。表6的第(1)列和第(3)列表明,家族控股与银行债务及商业信用的交互作用显著为正,说明银行债务及商业信用对家族控股的侵占行为有正的调节效应,即:家族控股股东通过银行债务和商业信用实施了利益侵占,银行债务和商业信用加剧了家族控股的侵占行为;第(2)列中家族控股与公司债券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说明公司债券对家族控股的侵占行为不存在调节效应,假设4得到验证。

表6 家族控股、债务工具与利益侵占的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检验的标准误,***、**和*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五、结语
在金字塔控股结构下,以中国制造业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不同类型终极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利益侵占行为,以及不同类型的债务融资工具在侵占行为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1)中央政府控股股东和地方政府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有支持行为(即负侵占行为),家族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有侵占行为;(2)商业信用削弱了中央政府控股股东的支持行为,银行债务和公司债券对中央政府控股股东侵占行为的调节效应不显著;(3)银行债务和公司债券削弱了地方政府控股股东的支持行为,商业信用对地方政府控股股东侵占行为的调节效应不显著;(4)银行债务和商业信用加剧了家族控股股东的侵占行为,公司债券对家族控股股东侵占行为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终极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利益侵占程度不同,不同类型的债务工具对终极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的调节效应存在差异。为了降低终极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利益侵占,建议采取如下措施:首先,进一步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市场化运作水平,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并降低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充分发挥银行债务的治理效应;其次,完善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加强受托管理人的监督机制,促进公司债券治理效应的充分发挥;再次,改善外部投资者保护环境,完善法律制度环境,促进商业信用治理效应的充分发挥。
[1]Claessens S,Djankov S,Lang L.The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in East Asian Corporation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0,(58):81 – 112.
[2]Johnson S,La Porta R,Lopez-de-Silances F,Sheleifer A.Tunneling[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90):22–27.
[3]Paligorova T,XU Z.Complex Ownership and Capital Structure[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2,(18):701–716.
[4]刘运国,吴小云.终极控制人、金字塔控制与控股股东掏空行为研究[J].管理学报,2009,(12):1661–1669.
[5]陈红,杨凌霄.金字塔股权结构、股权制衡与终极股东侵占[J].投资研究,2012,(3):101–113.
[6]Bany-Ariffin AN,Mat Nor F,McGowan Jr CB.Pyramidal Structure,Firm Capital Structure Exploitation and Ultimate Owners'Dominance[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2010,(19):151 –164.
[7]孙健.终极控制权与资本结构的选择——来自沪市的经验证据[J].管理科学,2008,(2):18 –25.
[8]冯旭南.债务融资和掠夺——来自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2,(3):943 -968.
[9]白云霞,林秉旋,王亚平,吴联生.所有权、负债与大股东利益侵占——来自中国控制权转移公司的证据[J].会计研究,2013,(4):66-72.
[10]宋小保.最终控制人、负债融资与利益侵占: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4,(7):1633 -1647.
[11]夏立军,方秩强.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J].经济研究,2005,(5):40 -51.
[12]黎来芳,王化成,张伟华.控制权、资金占用与掏空——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中国软科学 ,2008,(8):121-127.
[13]Diamond D.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Delegated Monitoring[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84,(51):393-414.
[14]刘清江.公司债券融资与银行债务治理效应的实证分析[J].开放导报 ,2009,(5):93-97.
[15]杨勇.银行贷款、商业信用融资及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J].南开管理评论 ,2009,(5):28-37.
[16]Houston J,James C.Bank Information Monopolies and the Mix of Private and Public Debt Claims[J].Journal of Finance,1996,(51):1863-1889.
[17]童盼,陆正飞.负债融资、负债来源与企业投资行为——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 ,2005,(5):75 -84.
[18]Petersen MA,Rajah RG.Trade Credit Theories and Evidence[J].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 - ies,1997,10(3):661 -691.
[19]马曙光,黄志忠,薛云奎.股权分置、资金侵占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J].会计研究,2005,(9):44-50.
[20]韩亮亮,闫雪.终极股东控制、债务资金占用与债权人利益保护[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69 -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