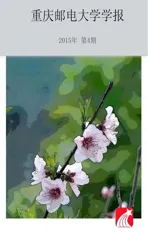行政处罚中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与限制*
2015-11-05徐信贵
徐信贵,康 勇
(重庆行政学院,重庆400041)
行政处罚中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与限制*
徐信贵,康 勇
(重庆行政学院,重庆400041)
行政处罚信息公开是政府不可逃避的义务,但是这种义务也应当存在某种程度的限制。限制的缘由不是基于政府的权力而是被处罚人的权益。行政处罚信息的公开范围应当是涉及公共领域以及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事项。政府对社会公众人物行政处罚信息的公开应当区分不同的公众人物而作区别对待。政府对还未明确证实的涉及公共利益的违法信息的公开应当保持克制。依申请公开的行政处罚信息一般情况下不应包括被处罚人的个人基本信息。行政处罚信息的公开不应当侵犯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此外,对政府的公开义务进行法律规范限制(相关法律对公开范围作明确规定)以及程序性限制(对信息公开进行程序控制)亦是维护被处罚人合法权益的有力工具。
行政处罚;信息公开;限制

伴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施行,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的行政义务已被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所肯定。在此之前以及在此之后各地方政府亦相继颁布了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政府的行政义务包括公开行政处罚信息不可置疑。但是,任何事物都存在一个度,超过这个度,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从而最终走向其反面。政府在信息公开中的义务亦是如此。行政处罚信息与一般的政府通过调查、收集、制作程序所保存的信息有所不同:前者涉及相对人的违法信息,政府机关一旦公布这类信息,对相对人的权益可能造成无法逆转的损害。因而,一方面,政府在实际履行公开行政处罚信息义务时应当事必躬亲,以将纸质上的义务转为行动上的义务;另一方面,政府应当有所保留、有所克制,面对一些公开与否对社会没有实际价值意义的,以及严重影响相对人人格权益的行政处罚信息,政府可以不向社会公开,或不主动向社会公开或者对公开的程序、内容等方面做一些限制。
一、学术界对公开范围的争论
由于行政处罚信息的特殊性,若政府毫无约束地公布该类信息,可能给相对人的诸如隐私权等权利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因而,学者们不再论证行政处罚信息应当被公开而是更倾向于关注何种类型的行政处罚信息不能被公开。的确,政府对自己所保存的信息是不能任意处分的,在对信息进行公布之前,需要考虑公布信息是否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以及对公开与否所带来的影响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以判断公开与否是否会出现价值失衡,继而确定公开的范围与限制。
莫于川教授认为,“应警惕过分扩大主动公开的范围,因为行政机关对行政执法结果给予公开可能会导致对相对人变相的‘二次处罚’,因而,主动公开的范围应当限于存在广泛社会需求的政府信息”[1]。这种“二次处罚”的概念也是其他学者所支持与认可的。章志远教授把行政违法事实的公布称为“声誉罚”,他认为“行政违法事实的公布包括可逆转的行政违法事实的公布与不可逆转的行政违法事实的公布,对于后者的适用应当更为慎重,需要遵循严格的条件与程序”。并且他特别强调人格尊严因素是限制行政违法事实公布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阻碍”[2]。亦有其他学者认为行政处罚信息的公开不能和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以及商业利益的保护相冲突,但公民隐私权以及商业利益的保护在面对公共利益时,应当退居二线,公共利益具有优先性。《关于依法公开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侵犯知识产权行政处罚案件信息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中的有关规定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与学者们对行政处罚案件政府信息公开义务限制的观点有所出入。因为侵犯知识产权的行政处罚信息并不是社会公众广泛需求的,人们不太关注一个企业是否侵犯另一个企业的知识产权。只要企业没有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以及有毒有害产品,公众对企业的关注度将变得很低。并且,公开此类信息可能会泄露其他企业的商业秘密以及知识产权。因此,政府在公开此类信息时应当作出适当的筛选,以防突破信息公开义务的限制因素,给相对人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学者们对行政处罚信息公开限制的观点各有独到之处,应当成为政府在公开此类信息时重要的考量因素。但是,学者们似乎主要针对的是政府主动公开的情况,对公众申请这一形式似乎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根据《条例》的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有关机关申请信息公开。学者们对之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是对“特殊需要”进行解释。但是,由于行政处罚信息自身的特殊性,政府应申请公布此类信息时受到的束缚因素与公开一般的信息可能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应当对申请行政处罚信息的公开这个问题给予特殊的关注。
在政府公开其所保存的信息已成为趋势时,我们再来探讨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的限制因素看似是不可取的。但是,作出这样限制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违法者、被处罚人的隐私权不遭受不正当的侵害。正如日本学者盐野宏所言:“关于个人信息的处理如果欠缺适切性的话,就会发生不当的侵害个人的权利利益的事情。”[3]在面对强大的公权力机器下,相对人的权利显得是如此的弱小,以致其只能在权力的细缝中“成长”。因此,在行政处罚信息公开层面,政府权力行使应当有所克制、有所缓和。
二、公开范围的再梳理
(一)主动公开与否的信息性质分析
在分析哪些行政处罚信息应当主动公开,哪些信息又应当有所保留时,我们需要根据信息的性质来做出判断,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行政处罚信息是否涉及公共领域或是社会公众普遍急需了解的信息。《条例》第10条第11项规定了有关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生产、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情况应当作为政府主动公开的信息。法律之所以做出如此规定,是因为这些信息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并且是社会公众急需了解的信息。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当政府通过监督检查手段收集到企业存在生产有毒有害食品问题时,必须立即向社会公布此应急信息,以免其对社会公众造成严重的生命健康威胁。在这些领域,公共利益相对于私人利益来说具有优先性。“公共利益不仅是国家社会存在之目的,也是法律赋予行政机关行政权力的目的所在,行政机关被视为公共利益的守护者或者监护人。”[4]因而,政府对行政处罚信息的公开不但没有侵犯私利,反而保障了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从而维护了特定领域的公共利益。实际上,亦有学者认为“《条例》虽然没有直接规定要公开此类行政处罚决定信息,但监督检查情况必然包含了监督检查结果的案件行政处罚决定信息”[5]。笔者赞同其观点,行政处罚信息包括处罚前信息收集阶段的行政执法信息以及处罚中的行政处罚结果信息。根据《意见》的规定,违反法律、法规或规章的主要事实被纳入应当公开的行政处罚信息的范围之内,这种“事实”即是行政执法阶段收集的信息。只有当这些行政处罚信息牵涉到公共利益以及公众的普遍需要时,政府才有义务公开。若这种信息完全只涉及到被处罚者个人自身的信息,与公共利益毫不相干,也不是公众所普遍需要的,那么这种信息就不应当存在于政府主动公开的范围之内。在现实执法过程中,“醉驾公开”成为执法机关普遍的做法。但是,这种公开的合法性以及合理性问题还有待商榷。因为,这种公开既与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公众的普遍需要不挂钩,也无法阻止相对人再次醉酒驾驶的行为发生,又侵犯了相对人的隐私权。这种百害而无一利的做法确实值得有关执法机关的深思。至少政府将违法者的个人信息完全暴露在社会公众的视野之下的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值得商榷。
当然,政府机关在公开此类信息时,应当将其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以及个人基本隐私信息分别处理。若需公开的信息与后者能够分割开来,那么执法机关应当只公布需要公开的信息。若是不能分割,政府应当作出利益权衡即将公开所带来的正面效益以及社会影响与负面的影响进行价值权衡,然后再来考虑是否公开该行政处罚信息。
第二,对社会公众人物的行政处罚信息公开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对于社会公众人物来说,应另当别论。有关公众人物的行政处罚信息既没涉及公共利益,又不是公众普遍关注的,那么其是否应当被排除在主动公开的范围之外呢?笔者认为,对此,应当区分公众人物是政府官员还是明星。若是政府官员,主动公开的信息应当包括“扫黄打非信息”在内的所有行政处罚信息。因为,一方面,作为政府官员,应当为其他公民遵纪守法树立良好的形象,自身的行为方式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另一方面,有利于加强社会对政府官员行为的监督,防止政府官员由行政处罚的对象演变成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而成为行政处分或刑事制裁的对象。对于明星来说,其行为虽然可能影响其他社会公众的行为方式,但是,因为其既不具有公权力的行使资格,其行为的影响作用又是有限的,所以政府没有必要也不应当将其受行政处罚的信息主动公开。在这方面,明星与一般公民一样,都享有隐私权不可侵犯的权利。
第三,还未明确证实的涉及公共利益的企业违法信息能否公开。当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发现企业具有环境破坏、食品安全等问题的端倪,但没有最终确切的证据证明其存在违法行为,或被证明的事实可能存在错误时,执法机关是否可以公开其违法信息?这个问题实际上属于“公共警告”的范畴。公共警告有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即“知识依赖性”和“消费者无知性”。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普通公众需要政府承担起信息告知的义务,以弥补公众在市场信息支配中处于的弱势地位。“公共警告既是一种警示风险的有效工具,又具有一般侵害行政行为的属性,具有双面特征,很多时候还构成一种重大的‘信息惩罚’。”[6]与之相比较的是欧盟行政法上的“风险预防原则”。风险预防原则的理念在于“当尚无确定科学证据的情况下,基于一定科学基础上的合理怀疑而采取预防性措施,于第一时间妥善处理环境、食品安全、生物安全等问题”[7]。风险预防原则当然要求执法机关公开相对人可能存在的违法信息。但它们存在不同之处:公共警告的前提是执法机关最终能够证明企业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只是在当前阶段无法明确证明或证明的事实可能存在错误;而风险预防原则的前提是无论是目前还是在作出行政处罚时都无法用科学证据证明其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公共警告具有存在错误的可能性,若政府对之加以毫无约束的滥用,可能会给相对人带来无法弥补的商业信誉以及可得盈利损失。因此,执法机关应当慎用之。笔者认为,若未明确证实的涉及公共利益的违法信息具有及时公开的必要时,如有毒有害食品信息,那么政府可以在行政处罚作出之前公布;反之,执法机关应当等到行政处罚作出时再一同公布。因为,由于缺乏信息公开的必要性以及及时性,说明公众对此信息的需求并不是那么的强烈。对于此类信息,政府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公布,既有利于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又避免了政府“公共警告权”的滥用。即使一般公众的权益由于信息的缺失受到损害,但是基于此种利益不具有急迫性,因而可以通过事后企业的补偿得以挽回。
总之,这种限制一方面可以督促行政机关及时履行信息公开的义务,避免社会大众由于处在信息不对称的弱势一端而受到严重的损害;另一方面,又可以防止违法者或被处罚人的人格信息、身份信息被公之于众,造成人格受侮辱、身份地位降低等“二次处罚”。
(二)依申请公开与否的信息范围分析
《行政处罚法》并没有规定公众是否可以向政府申请公开行政处罚信息。《条例》在规定了政府主动公开的信息范围之外,还规定了公众可以通过申请的渠道获得政府信息的条件,即“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的需要”。在行政处罚领域,如果涉及公共利益以及社会公众普遍需要的信息,政府需要主动公开,那么申请公开的行政处罚信息领域应当是单个公民自身所需要的信息,且与公共利益无关。如企业根据自身的生产需要申请公开某些企业的违法信息,避免走上同样的违法道路;某个科研机构申请公开某类的违法信息,以便科研活动能够顺利进行。但实际上,不涉及公众普遍需要的行政处罚信息对其他人的生产、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帮助。一般公众根据“科研”的需要申请公开行政处罚信息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以及现实意义。但是,由于这些信息具有私密性,尤其是“扫黄打非信息”涉及到被处罚者的基本人格利益。政府若毫无保留地将这些信息向被申请者公开,无疑对信息的承载对象是不合理的且是不公正的。因此,信息公开范围的限定就显得至关重要。
政府应当将行政处罚信息分割为违法事实信息以及个人基本信息。政府应申请所公布的信息属于违法事实信息,对个人基本信息应当有所保留,但是被处罚人同意公开其个人基本信息的除外。尤其是在公开关于“扫黄打非信息”等涉及人格利益信息时,政府机关要对之进行严格筛选。并且只要其他人根据该信息就能推定被处罚人的基本信息时,那么该信息亦应当被排除在公开范围之外。因为,涉及人格利益的信息一旦被公众所知晓,那么相对人的荣誉、名誉将遭受重大的损害,其经济利益亦可能间接地受到损失。亦有学者认为“……但是,因违法行为与其有关联,如果该个人身份信息对利益相关人是一种需要,以至于如果没有这些信息将足以造成不必要的不公正处理结果,或者自身会受到某种伤害,这时候该个人身份信息的公开就成为必要了”[8]。但是,该观点是建立在该类违法行为信息属于政府主动公开的信息范围之内的,且它对属于政府主动公开的信息范围的观点与本文存在不同,因此,该观点不适合本文应申请公开的信息领域。在涉及到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的情况下,政府应当区分行政处罚信息,将无关于前者的信息向申请者公开。若不能区分或区分后对申请者来说没有实际意义,那么政府机关应当拒绝申请人的申请,并应当合理说明理由。
三、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的法律规范与程序性限制
“虽然行政机关将行政处罚结果向当事人以及直接相关人员或者组织公开的执法模式不仅不能充分发挥社会对违法行为的监督,而且造成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处罚效应不能及时、有效地向社会和公众转达,使得行政处罚的应有功能无法发挥”[9],但是,无论政府对行政处罚信息的公开是否具有合法的、正当的理由,即使是这微不足道的处罚结果信息,都会对相对人造成“二次处罚”,尤其是对企业的经营利益以及公民的人格利益带来无形的损害。因此,就应当赋予被处罚人程序性权利以对抗政府的公权力。通过对信息公开进行法律以及程序性限制,既可以满足公众对信息的需求,又可以满足相对人对隐私利益保护的需要。
(一)法律规范约束
我国现有的法律并没有对哪些行政处罚信息应当公开,哪些行政处罚信息又不应当公开给予细致的规定,且《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没有对个人信息的公开坚持何种原则给予明确的答复。然而,“美国的《隐私权法》规定行政机关对个人的记录以不公开为原则,以公开为例外”[10]。虽然《条例》第10条第11项规定了有关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生产、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情况应当作为政府主动公开的信息,在此范围内的行政处罚信息亦应包括在内,但是,对其他涉及公共领域以及公众普遍关注事项的行政处罚信息的公开,法律并没有作出规定。根据重要事项保留说,凡是重要的行政活动都应当被纳入法律保留的范围。这些领域的行政处罚信息的公开实属重要事项,应当由法律加以规定。若法律没有规定此行政处罚信息可以被公开,那么政府就应当收缩自己的权力触角。这些行政处罚信息是否应当被公开既可以由单行法律加以规范性约束,又可以由《行政处罚法》进行统一性规定。比较适当的做法是,若存在对此领域的执法活动进行规定的单行法律,那么该领域的行政处罚信息的公开范围就应当由单行法律加以规定(如《环境保护法》、《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因为单行法律可以对此进行详细规定,并且这也可以避免法条的错位以及法律条文的不完整性;反之,可以由《行政处罚法》进行全面的概括性规定。无论是单行法律还是《行政处罚法》对该范围加以规定,都应当明确以不公开为原则,以公开为例外。
(二)程序性控制
从行政权行使的过程来看,程序性控制是为了弥补实体性控制的不足。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程序性控制比实体性控制更重要。……而职权行使却是经常性的,若无程序规则约束,则会时时构成对人们权利、自由的威胁”[11]。在程序性控制中,公众的知情权以及表达意见权是基础。由此可知,无论是主动公开型还是依公民申请型,政府在公开涉及第三方权益的行政处罚信息时,首先应当听取第三方的意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条例》第23条只是规定了公民申请型的政府听取意见的义务。行政处罚信息所具有的独特的性质决定了即使政府主动公开该信息,也应当听取被处罚人的意见。在这里,被处罚人可以进行充分辩护,对信息公开给被处罚人造成的不利影响与对社会带来的公益价值大小的权重进行说明,政府的最后决定应当充分建立在被处罚人辩护理由被充分听取的基础之上。但该意见只是作为政府决定的参考,其对政府的约束力还在于法院可能基于程序违法而撤销该行政决定。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若政府最终坚持违法公开行政处罚信息,即使法院判决政府撤销违法的行政行为,但是被处罚人的人格、隐私以及间接的财产等权益已经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失,被处罚人的胜诉已经没有了实际意义。鉴于此,我们可以借鉴预防性行政诉讼制度。如果被处罚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政府即将公布的信息是不合法的,且会对自己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那么其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以阻止政府不合法地公开自己的违法信息。这种事前的司法控制,可以有效地避免政府对被处罚人隐私信息的侵害。至于其中的程序设置问题,有待学者们的继续探讨。
对于政府应申请人的申请而作出的公开决定,本文对此进行额外的程序设置。首先,政府应当审查申请者的资格与目的是否符合《条例》第13条的规定,若不符合应当拒绝公开;其次,不同于一般的信息公开,政府应当对“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作出限制性解释,尽量缩小政府应申请公开的行政处罚信息的范围;最后,即使相对人同意公开其个人身份信息,政府也应当对申请人滥用该行政违法信息设置相应的行政责任,防止申请人将该信息服务于自己的不正当目的。有学者认为:“我国各级政府机构对依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准备不足,还没有完全走出秘密行政的传统;在制度层面,则存在申请主体范围受限、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狭窄、监督机制不足等局限。”[12]因此,可能有人怀疑在申请人申请政府公开信息已经困难的情况下,再对其进行程序性限制,会使申请人对政府保存信息的获取难度雪上加霜。然而,本文针对的是行政处罚信息,在该领域被处罚人的信息隐私权相对于申请人的知情权来说,应当具有价值上的优先性。
[1] 莫于川,林鸿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指南[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72.
[2] 章志远,鲍燕娇.作为声誉罚的行政违法事实公布[J].行政法学研究,2014(1):52-53.
[3] 盐野宏.行政法总论[M].杨建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31.
[4] 肖泽晟.非处罚性行政许可中止——从某环评批复行政复议“后语”说起[J].当代法学,2012(6):25.
[5] 刘健.工商行政处罚决定信息公开研究[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2(7):73.
[6] 朱春华.公共警告与“信息惩罚”之间的正义——“农夫山泉砒霜门事件”折射的法律命题[J].行政法学研究,2010(3):76.
[7] 王敬波.欧盟行政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93-95.
[8] 王军.行政处罚信息公开与隐私权保护[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1(1):105.
[9] 黄学贤.整合行政处罚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尝试[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5-21.
[10]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下[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1053.
[11]杨建顺.行政规制与权利保障[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548.
[12]陆幸福.论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之制度改进[J].法学,2013(4):74.Government’s Obligations and Lim itations of Adm inistrative Penalty Information Publicity
XU Xingui,KANG Yong
(Chongqing Adm inistration Institute,Chongqing 400041,China)
Administrative penalty information publicity is government’s inevitable duty,but this kind of duty should also be limited to a certain degree.The reasons of limitation are not based on the power of governmentbut the rightsand interests of the punished people.The publicity scope of administrative penalty information should be involved in social issues of the public domain and common concern to the public.Government should distinguish between different public figures so as to handle public administrative penalty information about social public figures.The government should refrain from illegal information,which has not been clearly confirmed and involves the public interest.Generally,the administrative penalty information which is based on application should not include the punished personal basic information.Government should not violate state secrets,commercial secrets and personal privacy.In addition,the government’s publicity obligations should be restricted by legal norms(Related law clearly stipulates the publicity scope)and procedures(Process control to the information publicity)and they are effective toolswhich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unished people.
administrative penalty;information publicity;lim itation
D912.1
A
1673-8268(2015)04-0046-05
10.3969/j.issn.1673-8268.2015.04.009
(编辑:刘仲秋)
2014-10-2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食品安全风险警示制度研究(13CFX028)
徐信贵(1982-),男,江西广丰人,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行政法学、信息规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