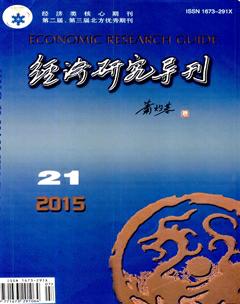从成本效用理论角度浅析中国“丁克”家庭模式
2015-11-03何蕾蕾
何蕾蕾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合肥 230601)
一、丁克家庭模式的兴起
所谓“丁克”,即为英文“Double in come and no kids”的缩写词DINK的汉译,字面意思就是夫妻双方都有收入但不生育子女的家庭模式,更主要指向的是夫妻有生育能力但主观上不愿意生育的家庭。澳大利亚的青年人群中最早出现这样的家庭相处模式,随后,这一“前卫”的家庭模式受到欧美等发达国家青年的推崇[1]。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浪潮的庇护下,丁克家庭模式传入中国,并在这个素来崇尚“多子多福”的传统国家盛行起来[2]。2002年2月零点调查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当时中国的大中城市已出现60万个丁克家庭[3]。2012年,上海市妇联针对全市家庭状况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丁克”家庭已经占上海家庭总数的12.4%。南京市一项抽样调查表明,有4%的夫妇自愿固守“丁克”家庭。总体上来看,“丁克”家庭在我国特别是大中城市明显地呈上升趋势[4]。
二、文献回顾
作为一种新型家庭结构,“丁克”家庭模式成为众多学者的热门研究对象。就已有相关研究而言,国内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丁克家庭形成的原因。许珂在《丁克家庭的成因及社会功能分析》中详细阐述了中国丁克家庭产生的主要原因包括孩子的生养成本高、婚育观念的变迁、生育动机的转变、外来文化的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等。另外,刘杰森在《社会学视野中的“丁克”家庭》一文中也发表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丁克家庭形成有其六大原因:工作、经济、晚婚、生理、婚姻和学习西方文化。
第二,丁克家庭的社会影响。林丛、石人炳在《浅论“丁克”家庭形成原因及其社会影响》一文中对相关文献的观点做了总结,丁克家庭的社会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传统家庭的冲击、对妇女地位的影响、对人口再生产和人口质量的影响等,并强调丁克家庭的社会影响不单单是负面或正面,应在考虑丁克家庭的规模和丁克家庭的演变趋势等两大因素的基础上做出中肯评价。
另外,相关文献的分析视角多有雷同,多从社会学和伦理学的角度分析丁克家庭,鲜有其他学科视角的加入。
就丁克家庭模式而言,对其形成原因和影响的讨论必不可少,但如何在固有框架下进行深层次的探讨,挖掘群体间、地区间“丁克”形成的本质原因,这成为文章出新的必要着眼点。
三、成本效用理论与丁克家庭模式
成本效用理论是微观人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分析丁克家庭模式的利器。从经济学角度,利用莱宾斯坦的孩子成本效用理论,赋予中国丁克家庭模式一个“存在即合理”的理由。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微观上,家庭生育行为取决于对孩子成本和效用的权衡。孩子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部分,直接成本指生养孩子所需要的一切花费,从怀胎十月到抚养,从衣食住行到各种教育等投入;间接成本指父母亲为生养子女而放弃的各种就业、升迁等机会,也称为机会成本,尤其在母亲身上体现明显。孩子的效用包括:经济效用,即孩子作为劳动力直接给家庭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保险效用,主要体现在养老方面;精神效用,孩子作为耐用“消费品”,可以满足父母感情和精神需要,能够带来“天伦之乐”;维系家庭地位的效用;安全保卫效用;扩展家庭效用,“多子多福”“子孙满堂”[5]。
丁克之所以成为丁克,应该就是孩子成本与效用权衡的结果。随着经济发展,物价上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生养孩子的成本会越来越高。另外,跟上重视教育的脚步,“赢在起跑线”,家长对子女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也会越来越多,周期也越来越长。相对的,孩子的效用并不能达到预期。父母不单单满足于孩子的精神效用,他们当然希望孩子会提供其他效用,如经济效用。但是残酷的现实给父母当头一棒,据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数据显示,我国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现象,有30%左右的成年人被老年人供养着[6]。子女尚不能生活自足,甚至还在啃老,又何来的条件为父母提供经济效用。再者,盛行的“421”家庭模式给子女带来繁重的赡养老人的压力,一个独生子女需要承担六个老人甚至12个老人的养老责任,父母也就不奢求子女的养老效用。父母与子女长期分隔两地的相处模式也让父母不再依赖于子女的安全保护效用。在大多数父母看来,仅精神效用、维护家庭地位效用和扩展家庭效用已略显微不足道。成本与效用较量过后,许多家庭便选择成为丁克,在他们看来,作为投资品和消费品的孩子,不足以让他们获得理想收益。
四、丁克家庭条件错位现象
(一)群体条件匹配错位
李银河教授通过对北京丁克族的调查发现,就本人职业来看,为干部、知识分子的比例占样本的73.7%;就教育程度看,男性具有大专以上教育水平的占65.8%,女性占68.4%[7]。自丁克理念被广泛传播以来,丁克人群主要表现出几大特征:第一,丁克家庭常见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城市;第二,夫妻双方的文化程度较高;第三,收入水平较高;第四,热衷旅游;第五,高智商人群[8]。这五大特征却披露一大错位,即抚养子女能力较强的家庭偏偏选择丁克,在丁克家庭生活条件匹配上出现错位。在家庭文化程度、收入水平、生活质量等各方面上,与其他普通家庭相比,大部分丁克家庭都不会存在生活资料短缺、无法培养优秀子女的成本问题。从孩子效用角度看,他们对孩子投资回报率应该更有把握,并且有理由期望比预期更高的回报。但是,他们却选择丁克。
(二)城乡条件匹配错位
2008年某调查显示,在20~29岁、30~39岁两个年龄段的城市女性理想子女数为0的比例分别为12.7%和1.7%,男性为6.2%和3.8%,农村男女均无“丁克”意向[9]。与以往相比,现在的农村条件有了明显提高,农村青年也希望提高子女的生活质量,现在农村生养孩子的成本已不再是“多一个人多双筷子”那么简单。无论在生活条件还是教育环境方面,农村享受资源远远不及城市,农村子女未来离开父母以谋求更好发展的可能性比城市子女更大,农村父母从子女身上获得效用的可能性更小。为了让子女在城市扎根,农村父母甚至会选择对子女二次投入,买房买车。偏偏抚育子女更困难的农村青年不选择丁克,而条件稍显优越的城市青年选择丁克,这就是城乡条件匹配上的错位。
出现两大错位的最主要原因应该是精神与经济的碰撞,现代文明与传统的较量。凤凰视频曾在《丁克一族成社会趋势人口老化问题亟待解决》一片中采访一对丁克夫妇,他们态度鲜明地表示,现在孩子课业压力这么大,父母可以决定是否生育但并不能确定子女未来的生活是快乐的。即使实力雄厚,在人的精神追求和经济回报之间,显然他们选择精神满足,选择尊重,子女也是需要尊重的个体,擅自做出生育决定可能对子女是一种伤害。这也是他们接受较高等教育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部分青年选择成为丁克的原因是对中国人口数量的担忧。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让他们开始思考自己的生育行为,丁克成为最终选择。他们认为,中国只有出现越来越多的丁克家庭才能加快人口从正增长往负增长的转变[10],中国才能成为“平均”的强国。
五、丁克家庭模式的人口经济学影响
(一)微观影响
丁克家庭对家庭本身存在影响,但该家庭不局限于核心家庭,也包括主干家庭。
从成本效用角度看,习惯上认为成本效用是针对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而言,但是隔代关系也应该存在成本效用关系。父母对子女的投资除了是对子女的培养,也应该是子嗣绵延的期盼,也希望从子女身上得到家庭扩展、子孙满堂的效用回报。
从婚姻代际责任角度看,子女对父母有精神赡养的责任,精神赡养当然应该包括孙子女的精神作用,这是丁克家庭在婚姻代际责任方面的欠缺。
从婚姻夫妻责任角度看,子女是夫妻间关系的天然桥梁,丁克夫妇属于享乐主义者,害怕承担婚姻责任,担心增加离婚成本。丁克家庭没有发挥家庭人口再生产的功能,称其为“合租者”也不为过,这样的家庭关系并不稳固。
(二)宏观影响
宏观上,丁克家庭的涌现会对社会产生影响。缓解人口压力等正面作用自不必多说,更需要关注的是其负面影响。
从成本效用角度看,社会对教育等各方面的投入必有其预期回报,如社会成员综合素质的提升、对工作能力的期望等,而且应该回报并不限于一代人,为子孙后代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应该是希望得到子孙后代连续不断的回报,包括经济硬指标和文化软指标。未来,丁克一代的养老问题也会成为社会负担,增加社会成本且没有回报。
从人口学角度看,丁克家庭的涌现势必对人口规模、质量和结构产生影响。丁克家庭最直接的就是对人口规模产生影响。若丁克家庭大量出现必然带来生育率的降低,直接影响到未来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劳动力数量会变得紧张。丁克主要集中于经济实力强且文化素质高的家庭,可见,这群高素质人才对后代的素质提升不会有太大作用,那么,无法保证对未来的劳动力素质不会产生消极影响。
六、小结
继“丁克”之后,“悔丁族”和“白丁”流行起来。顾名思义,“悔丁族”特指早年坚决不要孩子而到中年开始后悔的人群,最终他们开始艰难而尴尬的高龄备孕之路。他们想要孩子却错过最佳生育阶段[11]。“白丁”,白白当了一回丁克,从开始的坚持丁克到最后坚持生孩子,思想、行为的转变一定有其现实原因。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即双峰生育偏好。具有双峰偏好的家庭认为不生育或者生育两个孩子都要优于生育一个孩子[12],与其只能生育一个小孩,不如不生。求一双子女,求一个“好”字的家庭越来越多,摒除生理、经济实力等因素的影响,最应该做的就是政策调整。如今“单独二孩”政策的推行应该给众多双峰生育偏好家庭带来希望,更多的双峰生育偏好家庭也等待着全面二胎政策的到来,从而摆脱其丁克困境。
简单的好与不好、正面或负面并不能完整评价丁克家庭模式,存在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不合理之处,只希望选择“丁克”之前在利弊之间做好权衡,综合考虑对自我、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最终形成最合理的人口再生产模式。
[1]徐斌.“丁克”家庭的社会学考察[J].广西社会科学,2005,(1):160-162.
[2]马晓钰.从家庭经济学角度分析丁克家庭问题[J].学园,2012,(10):14-15.
[3]李爱芹.中国丁克家庭的社会学透视[J].西北人口,2006,(6):6-9.
[4]薛烨.当代中国婚姻责任研究[D].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5]朱群芳.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概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50-68.
[6] 陈奇娟.大学毕业生“啃老”现象原因探析[J].社会工作,2008,(5):51.
[7]姚蓓,但加成.当代中国丁克家庭的伦理审视[J].唯实,2008,(7):42-46.
[8]何瑛.丁克表情——丁克生活的理智与原罪[J].青年与社会,2012,(5):10-11.
[9]张亮.“丁克”只是少数青年的选择[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11-16(A08).
[10]姚晓凤.现代中国丁克家庭人口效应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11] 范领.尴尬的“悔丁族”[J].青年与社会,2012,(5):24.
[12] 李铮.生育意愿的双峰偏好研究[J].人口研究,2010,(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