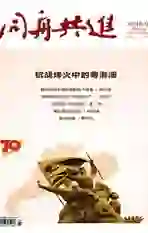历史上的偷书贼
2015-10-30孙玉祥
孙玉祥
据媒体报道:2015年7月21日,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原馆长萧元在广州中院受审。检方指控他贪污齐白石、张大千等名人的画作100多幅,涉案金额约亿元。
类似的盗窃事件,在历史上仅是个案,还是源远流长其来有自?它们又对文物保存乃至中华文明造成怎样不可挽回的损失?
【《永乐大典》的遇遭】
事实上,这样的内鬼、内行作案的情形古已有之。比如,一度被《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的《永乐大典》即遭此厄。
《永乐大典》系明成祖朱棣在位时所编,于永乐二年(1404年)首次成书,初名《文献集成》。书成后,明成祖精益求精,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于是再命太子少傅姚广孝、大学士解缙、礼部尚书郑赐等人重修。永乐五年(1407年),新版本定稿进呈,明成祖这次十分满意,并亲自命名为《永乐大典》。一年后,正本全部抄录完成。
此书的遭遇颇为坎坷: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永乐大典》也由南京搬往北京文渊阁。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皇宫失火波及文渊阁,嘉靖帝连下四道急令抢救《永乐大典》,大典得以完璧。经过这次火灾,嘉靖帝考虑一个保存大典的办法,由于刻印的工程和费用巨大,难以实施,嘉靖决定重录一本,以备万一。1562年,集朝廷大儒和各地善书者109人重录大典,用了4年时间,是谓嘉靖钞本,存放在另一个叫“皇史宬”的地方。
事实证明重录是对的,因为后来永乐原本突然全部失佚了——有的说毁于明末战乱,有的说毁于嘉庆年间乾清宫大火,还有人说其实是殉葬在明世宗的陵墓永陵中——众说纷纭,反正到清朝以后,能见到的就只有这个嘉靖钞本了。
康熙年间,在“皇史宬”找到了嘉靖钞本,经清点,已有少量残缺。清初藏在“皇史宬”的副本,到了雍正年间又移至翰林院。张廷玉在所著《澄怀园语》卷三曾提及此事。他说:“此书原贮皇史宬,雍正年间移置翰林院。予掌院时,因得寓目焉。书乃写本,字画端楷,装饰工致,纸墨皆发古香。”当时翰林院诸人肯留意这书的极少,何况是公家之物,卷帙众多,更无人去点查。直到乾隆准备编纂《四库全书》,有人献议从《永乐大典》中辑录遗书,这才认真地派员加以点查,这时才第一次发现存在翰林院的《永乐大典》早已失去两千多册了,也就是说,还剩下九千多册,也不算少。
但很快更大的厄运来了:经过修纂《四库全书》时对于《永乐大典》的一番利用,这书竟渐渐引起当时那些经常使用这套书的文臣的注意,他们很快由内行转为内鬼,开始对这套书上下其手。因为这套《大典》存在翰林院,这些堂堂的翰林院诸公就近水楼台先得月地做起了“雅贼”——专偷《永乐大典》。据清末藏书家、目录学家丁国均在《荷香馆琐言》中记载:“《永乐大典》原本万余册,陆续散出,光绪乙亥(光绪元年)检此书,不及五千。至癸巳(光绪十九年)仅存六百余册。相传翰林入院时,使仆预携衣一包, 出时尽穿其衣,而包书以出,人不觉也。又密迩各国使馆,闻每《大典》一册,外人辄以银十两购之,馆人秘密盗售,不可究诘,致散亡益速。”甚至像文廷式这样的学者词人,也做起了内鬼,居然通过这样的手法偷盗《永乐大典》,且数量多达100多册。光绪元年重修翰林院衙门时,清点《永乐大典》,只剩5000多册。20年后再清点,竟然只存800册——一部大书,几乎被偷光了。
【鲁迅:“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
民国时期,相同的事情又发生了——偷的是清朝的“大内档案”。
所谓“大内档案”,指中国清代紫禁城内内阁大库、方略馆大库、国史馆大库及宫中各处所藏档案的统称,包括明清两朝(主要是清朝)500多年间留下的总量约900多万件的历史档案,内容庞杂,是有关清朝历史的原始资料。民国建立后,这些东西被装为八千麻袋,塞在孔庙之中的敬一亭里。因为是前朝旧物,总让人对其生出无限遐想——比如,其中是否有值钱的宋版书之类,于是各种有资格接近它又比较内行的角色,就开始打它的主意了。
关于此事,鲁迅在发表于1928年1月28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上的《谈谈所谓“大内档案”》,有生动介绍。
这“大内档案”,据深通“国朝”掌故的罗遗老(指罗振玉)说,是他“国朝”时堆在内阁里的乱纸,大家原本主张焚弃,经他力争,这才保留下来的。等到他的“国朝”退位,满满地埋满了大半亭子。既然是公家的东西,就难免被私人偷盗了:先是工友偷,将书籍倒在地上,单拿麻袋去卖钱。接着,专家也出了手——这回是当教育总长的“F先生”(指傅增湘,藏书家。1917年12月至1919年5月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著有《藏园群书题记》等书),一位藏书和“考古”的名人。“F先生”估计是听到了什么谣言,以为麻袋里一定有上好的“海内孤本”,便命令手下(包括鲁迅)去查看麻袋里是否真有如此宝贝。鲁迅他们去查了查,只查出“破烂的半本,或是撕破的几张”的宋版书。于是,以考察欧美教育驰誉的“Y次长(指袁希涛,曾任江苏省教育会会长,1915年到1919年间先后两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等职)、以“满嘴跑火车”出名的“C参事”(指蒋维乔,1912年至1917年间先后三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倏忽间都变成了考古学家。这三位大人物都“念兹在兹”,于尘埃和破纸中流连忘返。凡有别人捡起放在桌上的,他们嘴上虽说看看,但等到送还时,往往要比原先少一点。
再后来,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的“YT处长”(指彦德,满洲正黄旗人,曾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郎中、京师学务局长)也插手其间,于是,八千麻袋便在午门上被“整理”,结果当然是大家顺手牵羊,毫不客气。最后,为了均摊责任,各部派员会同再行检查:“这宗公事是灵的,不到两星期,各部都派来了,从两个至四个,其中很多的是新从外洋回来的留学生,还穿着崭新的洋服。于是济济跄跄,又在灰土和废纸之间钻来钻去。但是,说也奇怪,好几个崭新的留学生又都忽然变了考古家了,将破烂的纸张,绢片,塞到洋裤袋里——但这是传闻之词,我没有目睹。”
鲁迅最后感慨道:“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这种感慨当然不限于“大内档案”,也不限于《永乐大典》,甚至也不限于萧元盗画——有人假设,如果现在将我们国家图书馆、博物院、美术馆里的所有名贵书画做个盘查的话,不知给那些内行兼内鬼掉包偷盗的有多少——总之,萧元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