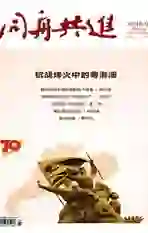澳门:“中立”状态下的另类抗战
2015-10-30贺越明
贺越明
从上世纪30年代初的局部抗战到后来的全面抗战,中华大地处处经受着战火洗礼,即使未被日寇铁蹄践踏的地区乃至大后方,也多受到程度不等的军事威胁。偏居华南一隅的澳门,是唯一不曾弥漫战争硝烟的城市。澳门当时处于葡萄牙管治下,背负着历史带来的侥幸和尴尬。在另一个外敌入侵中国时,出现了与内地以及香港不同的境遇和命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葡萄牙政府预感中、日战争不可避免。于是,葡萄牙外长费尔南多·阿乌古斯托·布朗克,于1932年3月5日在瑞士日内瓦国际联盟总部发表声明,表示“葡萄牙是中日两国世代的朋友”,在中日冲突事件中葡萄牙保持“中立”立场,以此取得中立国的法律地位。由此,澳门作为葡萄牙海外管治地区,也成为不受交战国任何一方侵犯的“中立区”。
救亡宣传有声有色
抗战期间,澳葡当局维持“中立”地位,但广大澳门同胞在祖国遭受外敌入侵的危亡之际,充满对日寇的极大愤慨,表现出炽热的爱国情感。早在“九一八”事变后的11月,当地一些商人就发起成立了澳门筹赈兵灾慈善会,召集各行各业的商家向内地抗日将士捐款捐物。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携手合作,澳门民众纷纷组织各种爱国社团,开展有计划、有步骤的救亡活动。由于澳葡当局标榜“中立”,却要维持与日方的良好关系,不准爱国社团公开打出“抗敌”“抗日”“救国”之类的旗号,不少社团都以救灾、慈善等名义成立。问世较早的有澳门各界救灾会、澳门学界体育界音乐界戏剧界救灾会、澳门抗敌后援会、澳门妇女慰劳会、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等等。其中有些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有些则由国民党参与创设,都对宣传抗日和发动群众起了很大作用。
1937年8月12日成立的澳门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以下简称救灾会),是当地爱国报纸《朝阳日报》《大众报》等发起组织的。从1937年初起,《朝阳日报》《大众报》等经常报道各地抗日救亡消息,刊载宣传抗日的文艺作品,成为读者了解抗日动态的主要媒体。这个救亡团体汇集了传媒、教育、艺术和文体的力量,举办活动有声有色,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从当年9月至11月,它就组织了五期筹集抗战赈灾经费的募捐活动,共筹集现款5000多元,全部送交内地政府用作抗战赈济。此外,比较活跃的爱国团体还有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澳门妇女慰劳会、妇女后援服务团、妇女互助社等。
在当时的澳门,每逢“三八”“五九”“七七”“八一三”“双十”等纪念日,爱国团体都会举行大型宣传活动,鼓舞民众的抗日斗志,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救亡宣传活动形式多样,较多以义卖、义唱、义舞、义映及粤剧、游艺会、话剧、女伶演唱等形式进行,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爱国热潮。这中间,也涌现出不少规模较小的文化团体和组织,如前锋剧社、绿光剧社、起来剧社、晓钟剧社、前哨读书会等。它们积极开展新闻、文学、戏剧、歌咏、美术等活动,传播团结抵御外侮的主张,发动同胞支持内地抗战。
这些救亡宣传,在社会上伸张了民族正气,激励了居民以间接或直接的方式参与抗战。一位名叫姚集礼的商人向驻扎顺德大良的抗日游击队捐献银元1000元和手枪两支,改善了游击队员的生活和武器装备。还有一批知识青年报考广东等地的航空学校,掌握驾驶技术后成为空军飞行员,参加了保卫祖国的对日空战,其中林耀、蔡志昌在作战中壮烈捐躯。救亡团体组织的几批回国服务团中,也有不少青年拿起武器随着当地正规军或游击队,走上与日寇殊死搏斗的战场,多人英勇牺牲。
襄助难民不遗余力
因为是“中立区”,澳门成了抗日战争时期广东地区部分民众躲避战火的首选之地。1937年底,当日军入侵中山县三灶岛时,当地一些居民纷纷逃至澳门。1938年入夏后,随着日寇的加紧侵略,广州及附近地区最终沦陷,大批难民涌入澳门。一时间,小城需要应付和安置的难民多达25万人。广州政府还将澳门列为学校疏散区,自内地迁入的中学、中专达30余所,流寓澳门的教育界人士又与当地天主教会创办了不少新学校,收容内地来澳青年入学。据有关资料统计,1939年,全澳共有中学、中专36所,学生3万余人;小学140余所,学生约4万人。
面对大量流离失所的难民,澳门各界伸出援手,千方百计予以安置和照拂。1939年8月,澳门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发起纪念“八一三”两周年的“献金运动”,组成10个宣传工作队赴各处宣传,举行茶楼义唱、戏院义演、歌姬义唱等活动。福隆新街的伶娼也上台义演,还纷纷捐出珍藏的珠宝首饰。仅三天的活动,便筹得善款折合国币10万元。澳门同善堂依靠社会各界的捐赠,持续不断地向难民施粥、施药、施棺。镜湖医院的病人比过去多了好几倍,病床不足,人满为患,幸得有殷商发起捐赠病床活动,又有澳门妇女会卖花筹款,才可以应付大量的诊疗需求。其时避难澳门的著名画家高剑父、关山月、司徒奇、何磊等人,也多次举办画展,将多幅作品义卖,所得收入悉数救济灾民和赈济难童。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在日军猛烈攻击下,香港18天后失守,一大批滞留的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危在旦夕。中共中央南方局发出指示,粤港澳党组织展开全力营救,将大部分人安排乘船先抵澳门,由在镜湖医院工作的地下党员柯麟负责,再转往斗门、台山等非敌占区,从陆路回到桂林等后方地区。
著名学者梁漱溟便是其中一位。他在1942年1月26日写下《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一文忆述:“承一位朋友的好意通知我们,说是有一只小帆船明天开往澳门,船主曾向日军行过贿,或可避免查问。船费每人港币60元,此友已预定五个人的位子。我们当下付过钱,约定次日天明于某处见面,有人领我们下船,并嘱咐我们改换装束,少带行李。”从香港驶往澳门,“船行全赖风帆之力。风若不顺,或无风,那便走不动。所以一时风力好,则船上人都色然而喜;一时无风,便人心沉闷,都说今天到不了澳门”。并且,“在途中曾遇有敌机盘旋而过,又有敌艇自远驶来,好似追我们的。船上水手和客人均慌起来,各自将珍贵财物掩藏。实则始终没有碰到敌人,或伪军土匪。我们一路无事,于夜晚十时,便在澳门登陆。”此后,梁漱溟一行先赴台山县城,再经开平、肇庆、梧州等地,终于到达属于“大后方”的桂林。
“中立”背后的谍影暗战
四周弥漫着战争的硝烟,澳门这座“孤岛”自然也不平静,不可能独善其身。澳葡当局为了恪守“中立”的立场,既要应付来自占领邻近地区和香港的日本势力,又要维系与内地国民政府以及中共武装部队的关系,使澳门好似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那样的“间谍之都”,各方人马折冲樽俎,明争暗斗。
对于这个“中立区”,日方和其他政治势力也会加以利用。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监察委员、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战时服务团团长的姜豪,在上海沦陷后通过时任伪维新政府教育部督学的朱泰耀等刺探日伪情报,但于1939年5月事泄被捕,后获日本军部设在上海的小野寺信机关保释。其时,日本特务影佐祯昭正在主持“汪兆铭工作”,希图将汪精卫扶植为傀儡,而小野寺信希望抢在影佐之前打通重庆路线。朱泰耀建议姜豪利用这个机会,代表重庆与小野寺接触,试探其“和平”的诚意。姜豪遂到“陪都”重庆向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报告,获得军统头目戴笠指派赴港与日本人接触。
姜豪到港后,先与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会谈,随后他熟识的日本特务吉田东佑到港,但恐受到港英当局监视,当天即乘船转到澳门继续会谈。涉及的内容,包括日方提出要求日华和平的障碍蒋介石下野、两国经济合作以日方为主开发中国的资源、和平后聘请日本顾问以及共同反共,等等。吉田东佑为安全起见,还花大钱请澳门警方保护他。这场非正式谈判,在日本高级特务今井武夫少将的回忆录中也有记载,被称为“姜豪工作”。这桩旧事说明:当年的澳门,无形中提供了两个交战国派员私下接触、相互摸底的平台。
由于历史的缘故,澳门的国民党组织力量较大,澳门支部下辖多个分部,人员众多,在抗战开始后组织和支持救亡团体的宣传活动不遗余力,成绩显著。太平洋战争开始不久香港沦陷,使得澳门的地位更加突出,日方也加紧了针对抗日力量的残酷打击。身份暴露的国民党组织负责人行动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老资格的国民党员梁彦明,既参与澳门支部的领导,又担任了多个救亡团体的职务,遭日伪势力的忌恨,于1942年底的一天,在街头被日本特务枪杀。国民党澳门支部另一负责人林卓夫,曾任中山县长,抗战爆发后移居澳门,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发表揭露日军暴行的演讲,也在1943年2月1日演讲当晚回家途中,遇刺身亡。日本特务的魔爪所到之处,“中立区”照样笼罩在恐怖的阴影中。
距离澳门不远,在中山的五桂山区活跃着一支中山抗日义勇大队,那里的抗日根据地较为巩固。澳葡当局出于遏制土匪和日伪势力的需要,有与之建立合作关系的愿望。抗日义勇大队向上级请示后,决定利用澳门的特殊地位拓展珠江三角洲的敌后空间。1944年初,澳门天主教堂的安神父到五桂山区的贝头里石门路教堂传教,抗日义勇大队大队长欧初与他多次交谈。安神父返回澳门时,欧初派员护送,并修书托安神父转交给澳葡政府。澳葡政府则通过在澳门居住的中山籍人士黄槐与欧初联系,要求派人面谈合作事宜。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批准中山抗日义勇大队先后派出梅重清、郭宁、黄乐天等人赴澳,与澳葡政府警察厅代表、秘书慕拉士达成协议:一、双方互相协作,打击骚扰澳门的敌军、土匪,共同维护澳门治安;二、澳葡当局同意五桂山部队到澳门进行不公开的活动,包括发动爱国人士进行募捐、收税、筹集抗日经费;三、同意五桂山部队在澳门购买部分物资,如弹药、医药及其他设备;四、双方建立一定的合作关系。根据协议,中山抗日义勇大队在澳门设立秘密办事处,为部队开展募捐筹款,筹集军需给养;还送少数伤员到澳门救治,得到镜湖医院医护人员的悉心医护。同样根据协议,游击队员还先后捉拿了在澳门打单勒索、搜集军事情报的“老鼠精”(化名)、汉奸特务黄公杰,并移交澳葡政府收押。
表面“中立”的澳门,其实并不平静,演绎着与别处不同的抗战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