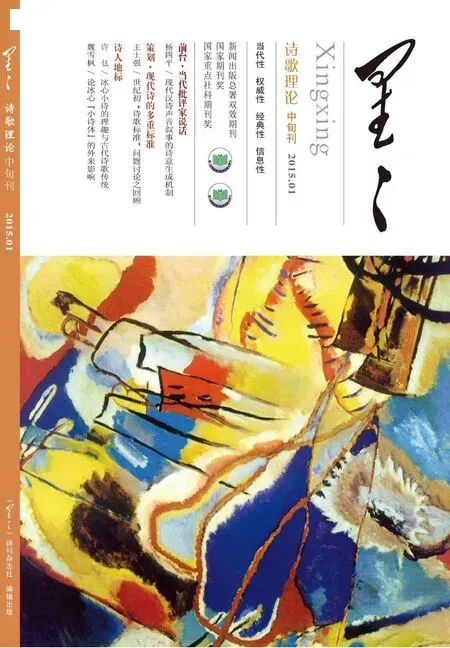诗歌的乡愁
2015-10-27常金秋
常金秋
诗歌的乡愁
常金秋
乡愁是中国诗歌中一个悠远的母题,几乎在每个时代关于它的吟唱都没有停止,随着社会的发展,它不断变化,涵盖了更广阔的内容。它可以是一种地理意义上具体的“离乡”之痛。就像谷禾在《居通州记》中的漂泊者——一个在偌大都市生存的异乡人,怀揣着对“山那边”的梦想,走出生长于斯的故土与父母殷殷的目光,这种如切断血脉的隐痛可能要伴随一生。城市里有摩天大楼、耀眼霓虹,在诗人眼中只有“补丁大小的蓝天,指甲盖儿大小的云彩”,呈现的不只是对故乡的怀想,还有对城市生活的隔膜。也许每个漂泊在外的人都做过海子的美梦,希冀有一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所在,但现实中也许它总是“在水一方”。“通州”作为诗人现实中的栖居地,能抚慰其“无根”之殇的,只有“风筝”、“鸽群”、“小蚂蚱”和“草叶”绵绵的情话,然而这一切也都注定如“露珠”般短暂。诗歌中这一个个统一而微小的意象,不仅唤起了对家乡的记忆,也将思乡的感伤推向了高潮,但是诗人仍不罢休,结尾处是震撼人心的,“在通州,我还有三千里的思念夜夜穿过母亲的针眼儿/它无限大又无限小/我有臃肿起来的身体,我有悬空的/泥土之心。它被轰隆隆的钢铁一次次撞击着/碎成了齑粉……”城市文明中,漂泊者被架空的不仅是肉身,更是精神。至此,我们或许会更深的领悟到诗人从开篇到结尾,不断重复的那几句“我有……”、“我还有……”背后隐藏的悲戚。
诗人的“无根”之痛,不仅存在于地理位置层面,还弥漫在更为宽广深邃的文化场域。刘虹在《当代文学一瞥》中,以诗歌为载体,投射出在市声喧嚣、多元共存的现代文化语境中,当代文学的境遇如“浮萍”般漂泊“无根”的处境。诗人在嘲讽、调侃声中勾勒出当代文学界的众生相。“它的自摸是细腻的,一杯咖啡里出浴隐私/自家一个喷嚏一只宠物,也能洋洋数十万字”,诗人讽刺它搁浅在狭仄的空间内,坐井观天,以兜售自我为乐,以哗众取宠为荣。左右逢源,游走在功利的漩涡中,“它的眼睛向后,深情望着大秦帝国/它的耳朵朝西,瑞典的动静要听仔细”,将其在当代语境中的经历一一勾勒出来,从个人化狂欢到低端媚俗,文学在病态的亢奋中挣扎,在“失根”的焦虑中沉浮,它缺少精神的“高度”,直至走向被掏空与悬置的窘境。在诗歌的最后,诗人写到“让出床位,有人比我们病得更急!”,戏谑中直指其精神变异。诗人的笔锋犀利、尖刻,在猛力批判中,不断触及“当代文学”的“要害”,显示了毫不留情的姿态,这背后蕴藏的其实是深沉的焦虑,一种对文学失去历史与传统价值的忧患。英国学者罗兰·罗伯森将这种现代化进程逼迫下的“焦虑”称之为“文化乡愁”,它不单单在文学中存在,而是蔓延到整个社会进程中,成为现代人的精神症候。
或许,马嘶在《旅行》中的体悟可以作为尝试。现代人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需要一次“还乡”。既然高楼大厦阻断了眺望自然的目光,柏油马路隔绝了对土地的亲近,那么“旅行”是否可以成为一种释放,以此来修复身心的疲惫与苍老?“每次旅行都像告别仪式/今日花开,明天花落,都是分分秒秒的事”,自然不仅是人类初始的家园,也是最后的皈依所在。在充满钢筋水泥的都市,人类日复一日重复着单调呆板的模式化生活,或许在旅行时,在山水中,人类能找回浪漫本真的心性。难得的是,诗人并没有让旅行停驻于花开花落的瞬间与流逝的时光,这些惯常美妙的一面被作者横刀斩乱,赋予了其悲怆的色彩,“虽然是生离,但如同死别,可能永不见面”,很多现代人的旅行,往往变成对形式与内容的强调。徜徉山水间唤起的不仅是自然的亲近,更应该有内心的震撼与美好情愫,“让万物不再流逝,让我们就相爱在那里”,在旅行中收获的还应该有纯粹,这才不愧对自然的给予。
也许人类更要感谢诗歌的陪伴,正因为有它,我们精神与肉体上的“乡愁”才有了安放之地。
(作者单位:天津科技大学法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