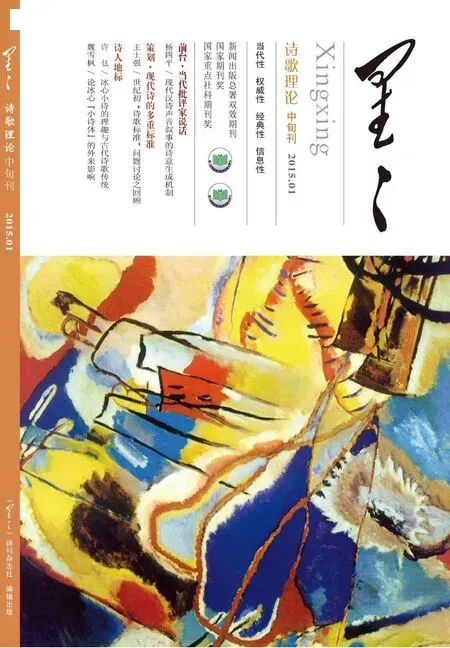世纪初“诗歌标准”问题讨论之回顾
2015-10-27王士强
王士强
世纪初“诗歌标准”问题讨论之回顾
王士强
诗歌标准问题似乎自新诗诞生以来就一直是一个问题,聚讼纷纭,论争不断,从来没有真正地停止过。这在很大程度上和新诗这种文体的“不稳定”、“不规范”有关,同时也和新诗之不受羁绊、追求自由的品质有关。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状况尤甚,关于诗歌人们的争议越来越多而共识越来越少,这大概和网络对于诗歌“生产力”的解放有关,诸多的观点、言论借助网络这个低准入、高效便捷的平台而呈现到公众面前,加剧了诗坛的“分裂”,诗歌在这个时代的确已经失去了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好事,它呈现了更多不同的声音与立场,“理不辨不明”。但同时应该看到,这并不意味着诗歌不再需要标准,实际上对诗歌标准的需求可能更为迫切,更值得讨论。因为,只有在有效交流、充分表达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我们时代关于诗歌认知的“最大公约数”,反思诗歌中存在的问题,推动诗歌的向前发展。
近年以来,“梨花体”、“废话体”、“羊羔体”、“乌青体”等都是诗歌进入公众视野的例子,这自然是诗歌标准分裂、缺乏的一个表征,而关于诗歌标准的讨论在诗歌界内部实际上是更多、更有成效的,这一讨论并没有多少“公众效应”和“爆炸性”,但却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其意义是不应被忽视的。2002年,《诗刊》下半月刊设立“新诗标准讨论”专栏,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分6期发表了50位诗人、批评家、学者的文章,形成了较大的影响。此后数年,《江汉大学学报》《诗潮》《特区文学》《中国诗人》等刊物均就此问题展开过讨论。诗歌标准问题再一次形成热潮是在2008年,理论刊物《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全年设立“诗歌标准讨论”专栏,由诗歌评论家陈仲义主持,全年发表了22篇学者、评论家、诗人的文章,从多个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专门的研讨。在这之后,关于诗歌标准问题的讨论虽然没有此前那么集中,但仍在继续,不时仍有回响。本文拟对世纪初关于诗歌标准的讨论进行一些概观与回顾,希冀由此见出关于诗歌标准问题人们的不同立场、观点,以及其在近年来的若干新流变、新走向。
一
诗歌标准之成为“问题”,是因为人们意识到这个时代没有了诗歌标准或者诗歌标准出了问题。应该说,这个前提性判断是准确的,当今时代所出现的许多诗歌问题都与诗歌标准的缺乏和失序有关,提出这个问题有助于相关人士的自觉、自省,以匡偏扶弊、扬长避短,诗歌标准问题的提出是一种责任感、使命感和艺术良知的体现。当然,正如评论家张清华直言不讳指出的:“(诗歌写作的标准)这个问题确实不能够期望简单化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一般性的呼吁和讨论甚至是没有意义的,它也可以被善良的人们理解为是一种责任感,也可以被不那么善良的人们理解为是试图施以霸权”[1]。这里面的动机与行为方式确实很复杂,不过就主流而言,绝大多数的参加者应该说都还是严肃、认真、理性地讨论这个问题的,这保证了讨论的有效性,也是责任感的体现。
关于诗歌的具体标准,讨论中有许多诗人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但却不可能得出一致性的、所有人都认可并严格遵照执行的结论性规范。《诗刊》社2002年的讨论没有“得出”关于诗歌的具体标准,2008年《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的讨论也不可能“得出”具体的结论。当然,许多具体的标准可能并不一定人人都会认同,但却并不妨碍它能够给人一定的启示和激发,并不代表这种具体标准的提出就没有意义。在这其中,影响较大的观点如陈仲义的“四动”标准:情感层面的“感动”、精神层面的“撼动”、诗性思维层面的“挑动”、语言层面的“惊动”[2],这里面显然有较为完备的、体系化的思考,较有概括力和说服力,当然,没有意外地,它也并没有转化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准则,很多人有着不同甚至激烈的反对意见。但不可否认,他所提出的诸多问题是值得许多人深思和借鉴的。又如,学者王珂由他长久以来对新诗诗体的研究出发,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关于新诗标准的“现实构建策略”:“一体”、“两象”、“三关”、“四要”。其中“一体”指新诗必须重视“诗体”,诗人应该有诗体意识,新诗要建设常规诗体;“两象”指新诗写作,特别是口语诗写作和叙述诗要重视“想象”与“意象”;“三关”指要适度提高行业的“准入”难度,如古代诗人需要有“推敲”基本功和格律常识,新诗诗人应该过“语言关、诗的知识关和诗的技巧关”,“四要”指新诗诗人要重视“学养、技巧、难度和高度”,“四要”也可以称为“四种境界”。[3]这其中的一些具体标准或许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意见,但他所提出的诸多问题无疑是值得讨论、引人思考的。实际上,许多人所提出的具体的诗歌标准都可做如是观,不一定人人都认同(实际上也不可能人人都认同),但是能够引起人的思考,唤起更多人关于诗歌标准的意识,这便是积极的、有益的。诗评家荣光启没有提出具体的诗歌“标准”,而是探讨了有关现代汉诗的三个“尺度”:“新诗其实是一种现代汉语诗歌,我们至少可以从‘现代汉诗’这一概念的角度来谈论,现代汉诗的本体是经验、语言和形式三者互动、纠缠和克服的一种状态,由此,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个体经验的深度、现代汉语的自觉和诗歌形式意识等必要的谈论尺度。”“看看一首诗在现代汉诗的历史脉络当中言说了怎样深刻而动人的经验、锤炼出怎样生动而丰富的语言及呈现出怎样新鲜、合宜又充满意味的形式。”[4]这样的“尺度”比之“标准”更具弹性,但无疑这也彰显了作者所持守的某种标准,同时使得诗歌标准的讨论更具灵活性和可能性。
讨论诗歌标准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求取关于诗歌的最大公约数的问题,但即便如此,仍然困难重重,它更多是一个动态的磋商、协调、修正、妥协的过程。可以看做诗歌标准讨论的另外一个例子是,“诗刊社”2008年初在评选第六届华文青年诗人奖的时候,对候选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结合你在诗歌写作与阅读中的体会,谈谈进入新世纪以来,一首优秀的现代汉语诗歌应具备哪几个方面或者应有哪些特点。”这类似于要求诗人阐述其诗歌观念和诗歌标准,2008年第5期的《诗刊》下半月刊出版“华文青年诗人奖特辑”,刊发了共37位获奖和入围诗人的诗歌作品和关于上述问题的短文。此后有论者曾从:A.心灵性、感动、感染力;B.真诚、说“人”话、抒情性;C.眼泪、疼痛、爱、担当;D.母语、民族文化特征、想象力;E.独特性、创造性、自由等五个方面对之进行了概括[5],虽然不少诗人的观点之间大同小异,但所有这些意见的综合、概括却并非最后的共识和结论,相反,可能没有一个人会完全同意,它要么是大于一要么是小于一的,但却不会等于一。所有这些都说明,已经不可能有一个唯一的、一统的诗歌标准存在,因为这涉及到标准制定者的“权利”和“合法性”的问题:谁来制定?谁有权利制定?这种权利和合法性由谁赋予?等等。标准作为一种规范,一定程度上是压制性和约束性的,而诗人又天生要对抗宰制,崇尚自由,任何人为的、具体的标准都会被视为压迫性的存在而成为应予推翻的目标。而今是一个“多元”的时代,人人都是有“权利”写作诗歌,并制定自己的“标准”的,文化发展中的这种“民主”趋势不可逆转,这也是“进步”的体现。但这里面的问题是,当今时代的人们似乎还没有学会如何“自由”,以致浪费了自由的权利,突破了本应存在的界限、底线和规范,取消了自身的规定性,这实际上也取消了自由本身,正如程光炜所言:“在一个正在走向多元的社会中,尊重文学的多元当然是没有问题。我个人比较担心的就是有人会利用这个‘多元’,将文学一些最基本的精神标准也解构掉了。”[6]如果没有充分的自我意识和自律精神,诗将彻底丧失它的底线,而与非诗沦为一谈,庸诗与好诗的鉴别机制也将完全失效,这对于诗歌的发展而言无疑是极其不利的。故而,仍然需要寻求某种“新诗知识共同体”或者“新诗标准共同体”,如有的学者所言:“于是,如果我们真的试图建立一个新诗的标准——有关什么是诗歌,什么是好诗——我们能够做到的就只能是置身于诗歌知识共同体内的‘协商’、不知不觉中的相互让步:在已有的作品、正在出现的作品和将要出现的作品之间协商,在诗人、读者之间协商,在诗歌艺术和社会情势之间协商。而从常理知道,在这个共同体内协商谈判的各方之间,各方的声音不可能同等程度的大小,而至于什么时候,哪一种声音更洪亮,谁的价值标准占据上风,是作者、文本、读者还是社会甚至某种意识形态,这是无法预测的,它只能是一个时代的艺术时尚、学术兴趣以及社会情势等相互交错的结果。”[7]这种“过程”很大程度上的确比“结果”更为重要。
二
所以,诗歌标准问题讨论的最大意义不在于有没有得出关于诗歌标准的具体结论,而在于敞开了问题本身,探查到当今诗歌创作、评论、研究等的机制内部,对所存在的问题作出富有创见和勇气的表达。这似乎是比字斟句酌于词语层面具体诗歌标准的表述更为重要,也更具“及物性”的,因为它针对现实而发,是作出有效的校正和提高的第一步。关于这一点,有很多的讨论富有质量,比如在《重建我们的诗歌标准》的对话中,几位参加者不约而同谈到了诗歌“环境”,这表面看来与诗歌标准没有直接关系但实际上却关系重大,黄梵说:“在我看来,目前汉诗发展的瓶颈不在创作,而在甄别环境方面。绝大多数批评家似乎已丧失了甄别能力,即没有能力从海量作品中遴选出佳作,或鼓励有价值的创作方向。这就涉及汉诗美学和批评标准的建设问题,目前的真空状态,是造成‘诗歌乱世’的主要原因,也使我们不能更好地理解已有的诗歌。”何平说:“第三代诗人之后,凭借网络强大的传播和繁殖能量,诗歌写作界成了革命家的讲习所。这些革命时代的投机家念念于心的就是破坏和捣毁。我不是说中国这近二十年的诗歌写作没有一点诗艺的进步,但比起破坏和捣毁来说大概是进五十步退一百。极端地说,我们当下的诗歌对汉语白话诗歌美学疆域的拓展比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究竟有多大的进步,都是相当可疑的。”马永波则认为:“中国诗歌写作现场特有的个人情感因素、圈子意识对诗歌优劣判断上不动声色的侵蚀和牵制,中国文化在现代性远远还未完成的情况下,就急于向‘反权威’、‘去中心’的后现代转移,其所造成的价值判断悬置、精神深度消解的相对主义思潮,对汉语诗歌标准的确立更是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8]这样的分析应该说都是深入而到位的,对于“重建诗歌标准”具有重要的意义。又比如,张清华所指出的创作中的“反道德”趋势和“中产阶级趣味”:“我觉得现在的诗歌写作者正在滥用权利,将之演变成了一种权力乃至‘暴力’,这是最危险和有害的。其表现花样是很多的,比如过去我们批判有的写作者假装的‘道德优势’,现在则有了‘反道德优势’,这种假装同样可怕,我是流氓我怕谁?一旦宣布自己是坏人,便成了不受基本规则限制的超人,可以随便骂人,随便讲粗话、脏话,还显得特别前卫。”“职业化和专业化的自视甚高的‘无人文含量’的写作,带着‘纯粹诗歌’面具的自我复制,标举着‘个人化写作’的自恋癖。我把这些问题简单化地称之为‘中产趣味’——是借用了丹尼尔·贝尔批评美国五六十年代文化的一个术语。它是高雅但苍白而缺少力量的,没有精神含量,不见风骨,也无神韵,这是知识界整体的萎靡和堕落的一种表现。这个问题是处在隐蔽层面的。”[9]前者是人人都看到、感受到,但却少有人谈及,似乎是有些“敢怒不敢言”意味的现象,而后者是隐在的,但却丧失了真正诗歌精神的技术性和惯性写作,两者同样都是危害巨大的。指出这样的问题是有创见而有针对性的,显示了批评家的见识和勇气。这样的声音多了,当今诗歌的生态环境才可能更为健康和有序一些,诗歌界才可能建立应有的标准,从而在较高的水准上行进,而不是一直在ABC的初级阶段停滞不前。
抽象地谈论诗歌标准很容易陷入凌空蹈虚的泥淖,只有在历史化的语境中来讨论才可能使问题的讨论更深入、更有效。学者姜涛主张将新诗标准的问题历史化:“期待‘新诗’成长为一个文类概念,从而把握到稳定的语言方式、象征秩序、以至评价标准中,还是将其当作一种与‘现时’剧烈交流的未完成方案,对‘新诗’性质的理解不同,是‘标准’争议背后的重要原因。在这种局面下,与其执着于‘标准’的有无,不如将这个问题历史化,从中探讨新诗内在的历史张力。”“在我的理解中,需要警惕的是一种以‘标准’为名出现的对历史的抽象和固化,而在具体的写作中,‘标准’不是一位小心伺候的‘美学上级’,而更多与一种写作的伦理相关,即:你是否仍将诗歌当成一种卓越的、艰苦的心智劳动,是否能将对生活的想象,转化成有力、准确、优美的语言。”[10]不脱离历史与实际,而又时时坚持对内心标准的执着与趋近,或许是一种较为可取的方案。在由评论家张立群主持的关于诗歌写作标准的对话中,赵金钟与张德明的立场、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强调了诗歌标准之必要性。赵金钟说:“谈论‘标准’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自由诗最大的特点或许是没有‘标准’,没有约束,‘自由’是其精神归宿。然而,我们如果真的这样认为,则又肯定曲解了自由诗。因为,自由诗是‘诗’,它首先必须具备‘诗’的本质属性。这就出现了悖论。不过,无论怎样,‘标准’肯定还是要的,因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标准’也就肯定没有了艺术。”而张德明则指出:“目前的新诗创作整体水平不高,虽然不少诗人在不倦地进行艺术探索,但平心而论,许多探索都是无效劳动,并不能给新诗带来质的飞跃。这就需要有一个相对的创作和评判标准的确立,因势利导,让新诗创作进入正确的前行轨道。自然,我们商讨标准或者制定标准,肯定带有某种程度的主观性,存在‘权力赋予’的嫌疑,甚至还可能导致‘写作霸权’的倾向。不过我认为这并不紧要,紧要的是让诗人的艺术探索和创作实践进入正常的诗学轨道,发挥更大的审美效能。有时候标准苛刻一些,甚至武断一些,这对制止诗歌创作的随意性来说,绝对是利大于弊的。”[11]实际上,对于具体的标准人们往往有不同的意见,但对于“诗歌标准”本身的必要性,则基本都是持正面的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诗歌标准讨论所达成的“共识”。
总体而言,新世纪以来诗歌标准问题的讨论最重要的成果不在于是否得出关于诗歌标准的具体规范,而在于唤起诗人、诗歌评论家和诗歌界关于诗歌标准的意识,打开了相关问题思考、讨论的空间。这一讨论如果能促进个体的自我反思、自我修正、自我提高,建立个人化的诗歌准则,并保持不断创新、提高和反省的能力,那么其作用就已经达到了:它更多是面向未来、启迪未来的,它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注释
1. 张清华:《诗歌写作:标准、权利、难度》,《诗潮》2008年第1期。
2. 参见陈仲义:《感动 撼动 挑动 惊动——好诗的“四动”标准》,《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3. 王珂:《“一体”、“两象”、“三关”和“四要”——新诗“标准”的现实构建策略》,《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4. 荣光启:《“标准”与“尺度”:如何谈论现代汉诗?》,《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5. 参见王士强:《青年诗人心目中的好诗有哪些特征?——对37份“同题作文”的扫描》,《诗刊》下半月刊2008年第7期。
6. 程光炜、张清华:《关于当前诗歌创作和研究的对话》,《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7. 王毅:《新诗标准:谁在说话?》,《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第5期。
8. 何言宏等:《重建我们的诗歌标准》(对话),《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9. 程光炜、张清华:《关于当前诗歌创作和研究的对话》,《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10. 姜涛:《“标准”的争议与新诗内涵的歧义》,《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第5期。
11. 赵金钟、张德明、张立群:《当前诗歌写作标准问题的再探讨》,《中国诗人》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