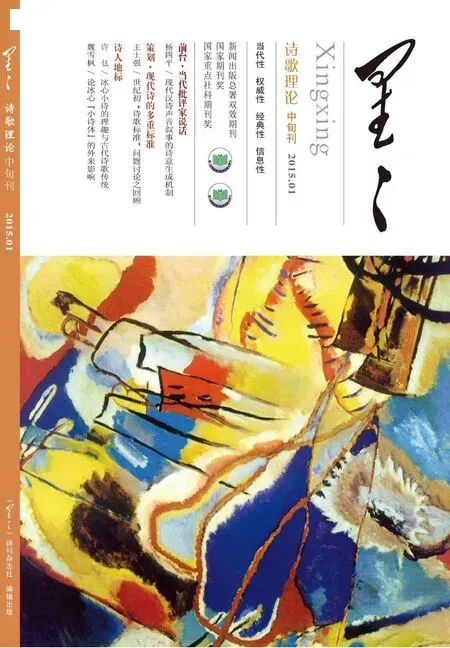化蝶与宿命:关于常英华诗歌
2015-10-27黄桂元
黄桂元
化蝶与宿命:关于常英华诗歌
黄桂元
一段时间,我的手机短信经常会收到常英华发来的诗。这些诗带着体温、气息与脉跳,状如凄美的杜鹃啼血,又仿佛渺远的空谷足音,竟使我一时生出“今夕何夕”的恍惚。我意识到,一种在浮世看来完全属于“无用”的被叫作“诗”的东西,仍在这个喧嚣社会的边缘处顽强生存,闪烁自己的珍稀品质。常英华写诗只有四载岁月,与2011年初冬出版的诗集《寻》相比,《深深的呼吸》有了陌生的变异,岂止是变异,几乎判若两人。这位青年女诗人的禀赋与才情,得益于上苍眷顾,使其迅速与庸常的公共写诗套路分道扬镳,破茧化蝶,独自在一条浪漫悲情主义的诗学坎途坚忍跋涉,渐行渐远。
娱乐至上、游戏狂欢的物质时代,缪斯正在失去尊崇,低到尘埃,被时尚放逐,被世俗嘲弄,这与诗人的门槛已被拆除有关。随便是谁,只要你愿意,并在互联网上经常晒出一些分行排列的汉字口水,或者通过借助冰冷的“自动写诗机”模具制造相关“产品”,都可以自诩为“诗人”。常英华与诗结缘,却不能不是一种宿命。“追求正以卑微的高度行进/却不能选择一条低劣的捷径”(《诗歌令我多么卑微》),这样的卑微激活了她的主体世界,于是不难理解,“强势抒情”何以塑成了常英华近乎任性的诗学姿态,她不断倾诉着所爱所恨,泾渭分明,绝不骑墙,“强光将波澜壮阔的理想蒸发/使我置身绝处,在壅塞狭小的现实中/观一场是非/如同大起之后的大落/生的激情死一样沉静”(《一束强光》),沐浴如此诗之“强光”,读者除了就范,大约别无选择。
常英华属于王国维所说的那一类“以血书者”。诸如爱与恨、情与仇、生与死,这些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永恒母题,被她一一掰开揉碎,置放于澄明而坚硬的诗歌容器,而熠熠发光。她的诗浸透了无尽的生命悲欢,这些无关乎正能量或负能量,却自有不肯流俗、独标一格的质地。借助诗,她蜷缩在时间的城堡,镇痛,疗伤,吟唱,与流逝的光阴博弈。生命的核心问题就是时间,她在时间里迷茫追问,伺机突围,寻求变数。“行走于红尘/注定用脚走出无数条弧线/组成一个轮回/所以,夜游/我需要影子忠诚我的身体/就像脚步忠诚我的心/他们最终以圆的形状汇合/却不一定圆满”(《夜游》),她喜欢写“夜”,却不同于翟永明的女性“黑夜意识”,而是通过“夜”完成一种日的升华,“夜慢下来的呼吸/呼出一串洁净的思想/升华为喧嚣之后的沉默/明媚之后的暗淡/白之后的黑”(《夜的表白》)。她力图借助“夜”的幽暗,孕育昼的梦想。
由“夜”之思抵达“死”之幻,来自常英华的黑色灵感。她把诗歌当做缓解精神危机的载体,并有效地放大了这一功能。“我生,她会用沧桑年轮里深藏的爱/开出最美的木头花,弥漫芬芳/我死,/她会用坚硬身躯的那把骨头/做成装殓我的棺椁,静静超度”(《木头花香》),“生”与“死”是一道诗意的深谷,诗人选择的是浴火重生的飞翔,“那就死一次吧/让深积尘埃的幽灵迸出躯体/将最纯正的爱植进命里/开花、结果,惊世骇俗/人生,我只能交付一颗心去爱/就像只能选择一次出生”(《命与爱》)。凭吊亲人离去,也每每赋予其神来之笔,令人唏嘘,“亲人,你喊着我的乳名去往天国/我没有泪雨滂沱/平静地在你最后的意象中取出暖/等同,在你命运深处挖出煤”(《亲人的煤》),“命运深处的煤”的句子延伸了夜、黑、死亡的隐喻意义,也是常英华诗歌的一个修辞贡献。
像许多严肃的诗人一样,常英华对诗的娱乐化之风深怀警惕,她不喜欢用暧昧的意象表达个人的内心奥秘,也很少用朦胧的词语和甜腻的吟诵描摹现实,而习惯于以率真的叩问直面虚伪的生活,宣释叛逆的冲动。她的处世哲学简单透明,有几分大学校园青春期学子所特有的青涩与纯朴,以及涉世未深的轻狂。“我把一生的美好/都嵌在年轻的额头上/抬头纹占山为王/却败于王者”(《最后的释然》),她对自己的成长既困惑,又自信,“谁来引渡我的欲望/将一种无法释怀变得不留痕迹/将凋零的年轮,葳蕤的情感/变成一个成熟的标识”(《我的圣经》),她所认可的“成熟旳标识”,与世故、圆滑、融通无关,而注定会有难度,“我行走于生活之上/脚印或弯或直,或隐或现/或断或续,或明或暗/随时出卖我的方向——/我来过,且只能来一次”(《唯一的旅行》)。这样的结局她早有预感,心如明镜,却不会轻易与生活和解,同样是宿命使然。
布罗茨基谈到,茨维塔耶娃对世界的反应方式就是“我拒绝”,她的诗句“她等待刀尖已经太久”,正是她的精神写照,也是其灵魂独白。在茨维塔耶娃诗歌的英译者妮娜·科斯曼眼里,这位杰出的俄罗斯女诗人“是脆弱的人类个体存在,她的极其艰难、孤独的命运,如我们所知,源自于她那绝不妥协的生命”,帕斯捷尔纳克也深有同感,“同日常事物的斗争赋予她以力量”。从诗歌发生学的角度说,常英华与之有近似之处。其敏感、脆弱,其大气、强劲,像是一币两面,构成了一道个性鲜明的诗学风景。于是,我们经常可以在她的诗里感受到一种勃勃英气。“我要天地,你只给我一撇一捺/我要永恒,你只给我短暂旅程/我要幸福,你先给我诸多泪/你创造爱恨/令我时而混浊,时而清白”(《哽咽的回声》)。红尘苍茫,世事艰难,她常以凛然之姿凝视苍生,审视自我,直抵被生存表象掩盖着的真相,这个过程中,她的书写绝不会隔靴挠痒,浅尝辄止。
她拒绝自怜自惜,拒绝浅吟低唱,她要借助重金属般的音响敲击尘世,弹奏心曲,死、黑、泪、血、伤、疼痛、挣扎、呼吸、骨头、灵魂、卑微、漂泊、孤独、撕裂、隐忍、墓志铭等词语在她的诗里此起彼伏,斑斓四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把诗人分为“主观之诗人”与“客观之诗人”,这是不同的两种诗歌境界,在我看来,前者“窄而深”,后者则“宽而浅”,无优劣短长之分,各有千秋吧。常英华大约属于前者。人生中不断加剧的疼痛感,反而可以使她拆掉心锁,义无反顾。海德格尔说“当思的勇气得自那在的召唤,命运的言词将一片绚丽”,可以被视为常英华部分诗作的精准写照。“我的人生哟/长不过连绵曲折的燕山筋脉/长不过那条昼夜流淌的滦河/更长不过我魂牵梦绕的思恋/我却驻进记忆悠长的遥望里/被一个无形的力量笼罩/尽情地爱这生和死”(《我记忆的目光里》)。“思”与“在”的深层贯通,使得此诗中的亮色与爆发力浑然一体,交相辉映。
《深深的呼吸》中的爱情自白诗,因其情韵的不同凡俗,而具有近乎撕裂人心的美学力量。“原谅我,独行,是为将你装进更深的梦/就像你的头发短于我的幸福/却长过你的满足/我会手捧你凋落的发丝离去/缅怀那未曾表白的被爱的时光/一根根数着它/解读我们此生相遇的全部意义”(《发丝里隐藏多少爱》)。所谓“有情人终成眷属”,往往只属于世外寓言,“相遇,只在一次长眠后的苏醒中/找到打满补丁的青春里/尘封的彼此”(《无果的相遇》)。无果,无奈,又因死亡而永恒,这个亘古模式令人怆然无语。“你说你的生命虽短,墓志铭很大/大到我再也写不动/而我已在你的枕边,洒下这首诗的余温/那是一个诗人被尘世揉碎的情/是你含在嘴边一生道不出的爱/我要让你永远枕着它,暖暖地睡去”(《道不出》。升华便是诗意的代偿,也指向了爱情的终极意义。
常英华的精神独立与一个异乡游子的漂泊经历有关。她的孤弱身影曾笼罩在陌生城市的巨大阴影之下,“在城市,楼宇是浪/坚厉的牙齿,一次又一次/逼得蓝天节节溃退,高悬/伤口处,彰显着人类的欲望”(《浪》)。她想起了故乡,“我曾希望自己来路不明/那样,就不会在梦醒时分/被想你的眼泪浸泡/就不用在疲于奔命的行走中/缅怀你的温存/我蹒跚学步的世界亦幻亦真/而生活,已惯于我受伤/惯于受伤后将你呼唤”(《回归小镇》)。可以想象,那种彻骨的乡愁曾怎样折磨着她的魂灵,“年终的一场雪/消融了我365个返乡的倒计时数字/我像一条河丢失的一滴水/淌回去的路,淌成了一另一条河……原谅我的贫穷/除了历经沧桑/我备不起一份春天的贺礼/只怀揣诗歌/用断行深情/醉淌一江春水”(《更深的思念不在眼前》),遥望故乡,她并非一无所有,至少她拥有思念。“我这故乡贫瘠的儿女/正用诗歌稀释她富饶的山河/在命途饥渴时/喝下良心和眼泪/交出每时每刻犯下的罪”(《渴》),她的谦卑只献给故乡。只有当她面对故乡的那一刻,才会低下高傲的身段,并祭出一个柔软赤子的忏悔。
即使是一些通常被认为属于应景性质的采风诗,旅游诗,常英华也有能力把所见所闻所想化为葱茏、摇曳的诗句,其冲击力令人惊艳,“南方,是我在北方丢失的一床棉被/盖上就会体验/那茂密椰林对凋零枫叶的思念/那盛开山花对冬眠枯草的真情/……我这北方女儿贫穷得热烈/只为寻一份暖,由北向南日夜兼程”(《为一份暖跋涉》)。常英华的诗也并非完美无瑕,比如,某些句子稍显直白,词语略显生涩,有的诗,过多的直抒胸臆使得本应有的诗意有所流失,等等,显而易见,提升的空间并不是没有。2014年2月10日,我在常英华发来的手机短信里看到这样一句话:“也许写作本身就需要沉寂和孤独,忍耐和苦楚。生活的挣扎和精神的腾飞相生又制约,天分正慢慢输于年轮,输于学浅,输于浮躁。”诚哉斯言。常英华能有如此的诗学自醒,就不会轻易输于未来的挑战。
(作者单位:《文学自由谈》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