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水第三条河岸(五题)
2015-10-21谈雅丽
谈雅丽
沅水第三条河岸(五题)
谈雅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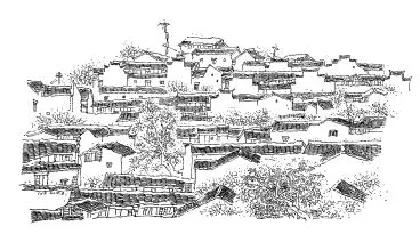
黑天鹅
卡尔·波普尔在“天鹅定律”里面说:“当我们发现一百只白天鹅时,不能定义所有天鹅都是白的。相反,当我们见到一只黑天鹅时,却可以这样命题,并非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只黑天鹅比一百只增加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因为就是这一次使我们的思想开阔了。”
我常用天鹅的哲思隐喻我们所面临的生活,我家族的历史是从谈家河的三兄弟开始,他们是从沅陵深山搬迁进入常德湖区的一支,我所能了解的祖父以上的几代都是农民,习惯于在冉冉升起的阳光中迎接简单的一天,周而复始地用谚语来预测农忙耕种的天气,同时也周而复始地重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大概一百个农民都这样沉浸在对谷子的盼望里,生儿育女,耕地捕鱼,湖区到处都是鱼米的清香,黄昏到处飘荡炊烟,使我的祖辈们即使在最饥荒的年代也没想过要舍弃自己的家园。
最初的那只不安于平淡生活的黑天鹅大概是我的祖父吧,祖父年轻时就具备与众不同的叛逆性格,乡里人是信任道教的,因为车船的不方便,家族中从没有人走出湖区去宗教地朝拜,然而祖父很有胆略,他道听途说慈利县有个灵验的道教圣地五雷山,便预计了一个月的行程,带上干粮,简单的用品以及少许钱财出发朝拜。如果现在从罗家湖的小村子到五雷山大半天的车路即可到达,然而那时没有车没有船,甚至没有行走的基本路线,他依着乡人的信口开河,一路走一路问,大半个月后他胡子拉碴地回来,从此逢村人问起此事便脸上有光,说起五雷山如何五山相连,顶峰一座金碧辉煌的寺庙,又说在寺院的种种经历,大佛像如何神威,道士们又如何一语道中他的心中事。后来我问起父亲这件事,父亲用一句话来形容祖父的沿途:形同乞丐。
就是这趟黑天鹅的飞行开阔了祖父的思路,他想并不是非要依赖平常的生活而一成不变。这之后,他再不安心家里的两亩薄田,而是选择一种非常自由的方式,在沅水河岸做了自由买卖的牛贩子,从乡村收购牛后卖给来来往往的农人或商人,牛生意不好时,他就到有湖的地方看湖。他渐渐远离了祖辈们一向依赖的农田耕作。几年后,他成了村人眼里的客人,他回家时,邻里乡亲看他的目光就与别人不同了,后来他娶了一个远方客家女子做老婆,成为第一个搬迁到小镇做零碎小生意的谈姓人。
以后,谈家河一带才陆续有人出来,其中最出色的是祖父的弟弟,他的腿微瘸,饱受村里人歧视。因为讨不到老婆,祖父将他带在身边,让他跟小镇的师傅学了一门手艺——车柁,以前稍稍讲究的湖区人睡柁床,车柁就是把木料在车床上车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在小镇,他的手艺越学越精,开店子,积累了第一桶金子后,他离开小镇在县城开了一家木器厂。后来,又从县城展翅飞往更辽阔的城市,在市区开着很大的铝合金店,买了高层住宅和小车,彻底地融入都市快节奏的生活。
祖父最初的想法,是在熟视无睹里尝试过另一种生活,他撞击到乡村的听天由命,摆脱祖辈们的约束而奔放不羁,我常想祖父的勇敢,思索着生活有时候真是一成不变的,或者说我们懒于看到他的变化,像波浪一样,我们时刻沉迷于它的风平浪静,一日一日消磨有限的光阴,但现在的我还是渴望触摸到那只梦想中的黑天鹅,渴望看到它飞翔的翅膀摩擦天空的声响,渴望它的飞翔使我们的生活进入风清月明的境界。
旧年的河水
我出生在沅水边一个叫罗家湖的村子,是家里第二个女儿,父母都是乡村医生。据说,我出生时又瘦又丑,本来就重男轻女的奶奶,冷着脸把母亲坐月子的红鸡蛋全部卖掉了。
那年夏天,家里出了一件大事。我的小叔,也是奶奶最疼爱的幺儿,因为赶着回来吃我的满月酒,被建筑工地掉下来的竹跳板砸中脑袋不幸去世,奶奶从罗家湖一直哭到镇上工地,她把事情的根结归于尚在襁褓中的我。十个月后,刚刚被招工的母亲整天忙于工作,她把我和姐姐送给奶奶带,但奶奶绝大部分的爱都倾注在伶俐可爱的姐姐身上。我印象最深的事就是奶奶逢天气不好就坐在后门,对着雨水哭死去的小叔,雨水绵绵,奶奶的眼泪也似乎永远没有尽头。
半年后,我被诊断为三度营养不良,因为拉肚子,造成直肠下垂,而且长了满头虱子。母亲含泪把我接到乡医院,她给我剃了光头,这个又瘦又小的可怜虫,最后只能送到外婆家去养。
沅水分为前后河,外婆舅舅住在沅水南岸的沧浪坪,是前河,奶奶和我父母住在沅水北岸的白鹤山,那里是后河。前河后河民风不同,前河为山区,山民砍楠竹捡茶籽,爱喝擂茶,说安化话,住竹屋木楼。后河的人种水稻、油菜、棉花,家家户户捕鱼种莲,生活条件远好于前河。七十年代,两地间没有汽车可坐,得走大半天水路,从罗家湖出发过湖汊走沅水,再从沅水一直到汉寿附近的沧浪坪河岸,走上两个小时才能到外婆住的大山里。
父母带信让外婆来接我。我三岁,在沅水老码头第一次看到我的外婆,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妇人,外婆那年也许是五十多岁,但头发银白没有一根是黑色的,她穿着对襟开的布衫,一把把我搂在怀里。
这个温暖的老太太,天生慈祥,第一眼就让我喜欢她。我第一次出远门并没有哭闹,只是欢天喜地在船上玩着,肚子饿了,就在外婆怀里哼哼唧唧,外婆带着干粮,没有开水,她就从布袋里拿出一个木勺,一边舀着沅水一边对我说:“丫头,喝茶,喝茶!”河水又清又凉,我高高兴兴地喝了满肚子的河水。
在以后的岁月,我写作与河流有关的文章,总是想着也许从那天开始,外婆就用奇特的方式将沅水喂进了我的胃,流进了我的血管。
山区条件不好,米饭中都煮有红薯和苞谷,外婆并不因为我小而特许我只吃米饭,家里的净米饭只能给外公一个人吃,因为几个舅舅都在外地,外公是家里唯一的男劳力,只有外公吃饱了,家里才能有更多的粮食。饭碗得吃得干干净净,不能剩下一粒饭,如果浪费,可能会被罚饿肚子。
外婆是一个节约的人,她惜小东西,小布头,一小块一小块积攒到百来块时,用线将它们缝在一起做成百种花色的小枕头让我用。撤下来的棉花,一朵朵积下来做我的小背心小棉衣。她惜纸,用坏的挂历是不能丢的,要用来做草稿纸。山区上厕所也不用纸,而是到山上砍竹子,削成竹片当纸用。
外婆上哪儿都带着我,她上山砍柴,我就在山里追着野兔跑;她捡茶籽,我就溜到树上摘酸枣;她去泉边挑水,我就走在木桶前面。
冬天,我去水库的冰面上玩水,她大为生气,但并不大声责骂,而是在水库边要我一直玩,直到我冻得向她求饶,并发誓再也不到河边玩了,她才把我带到火炕边烤着。她教育我的方式就是,让我尝到做坏事的苦果。我偷偷拿了邻居家的小皮球,她就让我自己还回去,让我意识到什么是羞耻不能做的事。
外婆脾气倔强,也使我变成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野丫头。她从内心让我感觉到她的好,小时候她最喜欢给我唱她编的儿歌:“娜娜乖,娜娜好,娜娜有钱买手表!”手表是山村最值钱的东西,娜娜就是我的小名,她把美好的愿望都唱给我听。外婆喜欢让她的孩子读书,两个舅舅一个师范,一个当兵提干,母亲是山里唯一读过卫校的女中专生。外婆常常一笔一画叫我写下她的名字:王心一。这是她唯一认得的三个字。
我六岁那年,因为山区没有一所像样的学校,父母决定接我回后河上学。当他们到山里来时,我已经不认识他们了,听到外婆说要送我回去,我一溜烟地爬上树顶,一直到吃饭也不肯下来,父母站在树下,眼泪哗哗地流。
我们要乘船沿沅水返回了,我记得那天傍晚,外婆牵着我的手上船,她的手又大又暖,她一路叮嘱了很多话给我听,比如要听父母的话,要好好读书,不要调皮捣蛋,不要想外婆。船渐渐地离岸了,她的手一直在河岸上挥动着,我闷闷地坐在船舱看着她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远……忽然,从河堤上传来压抑不住的大哭,我银白苍苍外婆的哭声,满满笼罩暮色中的沅水河。
如今,外婆已经仙逝多年,但旧年的河水仍在我的脑海流淌,我记得谁说过一句话:“人生的每一次离别都是暂别——”
愚舅移山
我想说一个愚公移山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桃花溪,这条溪是沧浪水的源头,沧浪水于汉寿汇入沅水,桃花溪流经的那个乡叫沧山乡。
小溪清清浅浅,日夜叮咚,春来野桃花落进溪水,就有满满当当的桃花水流。溪水绕山而过,满山楠竹,青翠欲滴。山里每个村子都叫着冲,桃花溪流经的村子叫桃花冲,杨姓在隔壁村占据大半,隔壁村就叫杨家冲。再往上走就是安化县,盛产黑茶。我外祖父是地地道道的安化人,民国时将祖屋从安化移到桃花溪下游,外祖父的第一个木屋就在那里建成。
据母亲说,在桃花溪的半山腰建筑木房时,全家大大小小都参与,砍树的砍树,扎架的扎架、平禾场的平禾场,最小的孩子也帮着照看木料。山里的木房和湖区的不同,中间的堂屋是敞开的,不设门,只零散摆几张长条凳,便于躲雨的人休息。四缝三间的大屋建成,房子坐北朝南,清香的板壁,高高的屋顶,是大户人家的好房子,全家人都舒了一口气。
房子风水好,我的大舅杨行武当兵提干成了部队指导员,从此很少回乡。小舅杨次东师范毕业后回山乡办起一次性竹筷加工厂,是村里响当当的人物,但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此后,小舅受困于山乡,他结婚后生了三个孩子,不幸病死一个,使他受到很大打击,竹筷加工厂也因管理不善而倒闭。桃花溪有个奇怪的现象,乡人虽然越来越少,但是楼房却越修越多,打工的子女把钱寄回来,家里的父母亲就帮着修房子,家家都动心思拆木屋修楼房。
失意后的小舅想凭自己的力量修一幢楼。小舅没法到外面干活赚钱,因为有三个留守的孙子孙女得让他带着。山里主要收入是楠竹和木材,却没有卖到山外去的路,表哥打工钱少,小舅手头也没有什么钱,但他有山里汉子的倔劲,他决定修楼所有的工都自己动手。
夏天我去山里,一眼就看到穿得破破乱乱的小舅在大太阳底下忙碌,他已经用自己的挖锄平掉半个山头,正在用一种最简单的方法滚动石碾,踩实地基。夏日午后,热浪滔天,大汗淋漓的他似乎毫不疲惫。
秋天,广州打工的表哥,终于没能留住他外出打工的媳妇,这变成小舅一家的奇耻大辱,从赫赫有名的大户到如今大哥连女人也没守住,小舅铁了心要建好这幢楼。或者,这也是让村里人刮目相看的办法吧。
冬天我来时,楼房已经修得像模像样了,小舅带领我们看新修的楼,一边走一边说:“这楼所有的土建,建筑小工都是我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一肩一肩挑出来的,我一个工也没有请。”
小舅用最少的钱建了一座他心目中的大楼。
此后每年我回乡,都能看到这座大楼的变化,今天是楼的左耳边多出二间木屋,明天右耳又多建了一个偏房,老屋先是拆除,后来又重修,小舅每年都在想办法修缮他的大厦。
他一年比一年老了,因为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修楼建房上。修了楼房他又劈山修路,他的脸晒得焦黑,身上从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爸爸的夹克、大舅的旧军装都是他劳动的衣服,他变得越来越不修边幅,头上乱乱地围着一条黑毛巾,他已经由一名文弱的师范生变成一个倔强的老山民,任何人都无法劝阻他停下劳动。
最初修筑老屋的山被他的锄头开成一块很高的平地,平地周围建房子,种板栗、橘子、桃树,果园下面挖了一个池塘养鱼。果树还要等三年才能挂果,鱼塘的水清悠悠的,山气清冷,抛下去的鱼苗并不见生长。
山里一座座楼房不断拔地而起,无论是建筑规模或是装修风格都远远超过小舅含辛茹苦修成的大楼。桃花溪从小舅的楼前穿行而过,到达沧浪河,再到达沅水,一路不知道走过了多少弯曲。有时候,我能理解小舅的执着,外出打工的儿女只有过年回来后才在大楼住上几天。对他而言,守着房子就是守着最后阵地和净土,他挑来桃花溪的水把孩子们养大,听着桃花溪的水声把他们送走。当月光升起时,他会不会在夜里抽一根旱烟,想想自己一生的辛苦呢。
有些人一辈子轻轻地走过了,有些人一辈子重如大山般地经历。这一切只有溪水知道。或许,整座被愚舅移平的山就是他对时光做的一个永恒记号。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毫无意义,但对于移山人自己来说,却意义重大。
妈妈的爱情时代
我的妈妈年轻时是方圆几十里少见的美人。
四十年后,有一天姐姐在医院给公安局的老干体检,遇到一个风度翩翩的老人,老人慈眉善目,知道姐姐姓谈,便异常亲切,打破砂锅地问姐姐是不是菊清的女儿。我妈妈叫菊清,老人是她的崇拜者之一,当年穷追猛打后却只能失魂落魄,四十年后见到长得像妈妈的姐姐依然长吁短叹,悔之无及,可见我妈妈当年的魅力。
我童年翻箱倒柜,无意中找到爸爸的日记,偷偷来读,满满一个日记本上全是古体诗,我只读懂其中一首:“松风明月荷塘夜,菊花清茶捧手来。”所捧的大概就是我妈妈。风流才子遇佳人,最后的结果是妈妈远走他乡,来到爸爸生活的后河农村扎根生女,个中的甘美与酸涩或许只有她自己能深切体会。
一晃多少年就过去了,爱一世,终成圆满。
妈妈出生在农村,开明的外婆让所有的子女都上学,两个舅舅中专毕业,我妈妈是全大队唯一出来读卫校的姑娘。在她的记忆里,天没亮就要赶十里崎岖山路去读书,所幸妈妈有两个哥哥陪着,放学邀了一同回家。学校有个好留学的数学老师,经常等到天黑才让他们回家,习惯走夜路的妈妈从不以为苦,妈妈学习努力而且人很聪明,河伏卫校招收医生,妈妈是第一批考上的佼佼者。
爸爸也在那年考上,当时他长得十分矮小,进学校时坐在前面第一排,妈妈高,坐在最后一排。中专三年,爸爸个头如春笋般往上蹿,等到中专第三年,爸爸长到一米七五,就和妈妈一起坐在最后一排了。说起他们的情史,其中必定有递小纸条、写情书诸如此类情节,如今无法深究,只是从当年的数本情诗可见一斑了。
妈妈一生最大的优点和缺点就是固执。中专毕业后,爸爸分到后河当上吃城市粮的医生,妈妈也可以定向分配到前河,端上公社的铁饭碗,但她不顾外婆极力反对,义无反顾跟随爸爸到罗家村当了一名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是农村户口,只能领少量钱,农闲时在村里给农民上门打针治疗,农忙时还得下地干活。农村活累,听奶奶说,怀孕的妈妈大着肚子去除草,我差点就被生在水稻田里了。
生了两个女儿后,奶奶的脸色就不太好看了,妈妈怀了第三胎,临产时爸爸正在石公桥开会,因为难产,新生儿一出来就窒息,抢救不及时,妈妈永远失去她唯一的儿子,奶奶把责任全推在妈妈身上,她常常拄着拐杖,在妈妈面前指桑骂槐,她们的关系迅速恶化,爸爸也为难,然而他最大的法宝是对谁都不偏不倚,吵得最凶的时候,他就沉默,却奇迹般缓和她们的矛盾。
小时候我常常妒忌妈妈对爸爸的爱。爸爸是全天下爱好最多的人,妈妈支持他一切的爱好。他养鸽子,妈妈就给买玉米;他喂金鱼,妈妈就吩咐我们到浅水沟舀沙虫;外公是治蛇名医,爸爸想学独门绝技,妈妈就软硬兼施,逼外公打破传男不传女的规矩,破例将看家本领传给了外姓人;爸爸爱酒,每次酒后,妈妈都要泡上蜂蜜水,陪在身边照顾他,只有一次喝醉的爸爸被人用担架抬回来,妈妈大发雷霆,和爸爸大吵一顿,说他不要命了,两个人差点动起手来,那场风波后爸爸饮酒才稍有收敛。
我高中毕业那年,遇上下海潮,爸爸并不安于小镇风平浪静的生活,他受聘区卫生局到海南创办湘琼医药公司,任总经理。海南的创业经历,大概是爸爸一生事业被拔高的虚空巅峰,初期没有钱启动,妈妈找亲戚到处筹钱,湘琼医药良性运转,作为总经理的爸爸被周围的人奉承,每年过年爸爸回家,家里都有川流不息的客人,有人求工作,有的介绍医疗业务,有人拜年,妈妈安静地忙碌。爸爸让她干脆辞退乡医院的工作(妈妈已转为正式职工了),妈妈顽固地拒绝了:“两个女儿还在读书,我让你安心在外创业。再说,我这里也是你最安全的大后方,万一你以后生意失败,随时都可以回来。”
那年,爸爸回来找资金,除了扩充湘琼医药,他还想创办一个碎石场。经济浪潮成了泡沫经济,公司签不到合同,一夜之间,合资人偷偷开走所有的碎石机,不知去向,留下大量的债务,无度的支出使爸爸必须承担其中亏损的百分之二十,一百万,一笔巨款快要压垮了我的父母。但妈妈及时充当了爸爸的后方:“债务我们慢慢还吧。”
新修的房子迅速卖掉,爸爸在桥南市场开药材批发门市,他对于账目管理糊涂,妈妈就去舅舅那里,哭着请求:“哥哥,无论如何,你要借钱给我,请你去帮大毛管账,你还要帮我一年。”我舅舅在桥南的药材门面一干三年。
若干还债细节已经淡漠,我印象中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看到门口站着一个气势汹汹的人,他是我爷爷的二弟,他一边指着妈妈一边骂道:“杨菊清,你今天要是不还钱,我就不走,大毛是大骗子,骗了我的钱。”当年一些亲戚拿钱入股到碎石场,想赚钱,没想到钱投入没多久,碎石场就倒了。亲戚的恶劣态度使我当时就哭了,妈妈默默端来一碗饺子放在他面前,随后拿出那个月的所有收入五千块钱,放在饺子旁:“你每个月来取吧,我会还清的。”
有那么一天,天空很蓝,我们还清了所有的债务。
或者妈妈还经历过感情路上的悬崖,但她都坚强地挺过来了,妈妈哪儿都不去,当年她有机会进修并调到县医院,她不去;她可以去海南当阔太太,她不去;深圳有医院每月一万元请她主持妇产科,她不去。她在猴子巷度过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她在慢慢变老,头发渐渐花白。
在那个最寂静的小镇,爸爸和妈妈退休后开了一间私人诊所,后来我们一起在最繁华的路段修了一座镇上最大的新楼。

沅水女人
大姑的一生可以写一本书。她是依河而居沅水女人的缩影。她的命运坎坷,但她懂得微笑面对生活的磨难。她勤劳、质朴,有很好的耐受力,就像一粒草籽,播种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
年轻时,大姑住在谈家河边。谈家河是沅水的一条支流,这条清澈的小河灌溉了方圆几十里。平原上的农人种植水稻、棉花、甘蔗等南方作物。大姑是家里的长女,没读几天书便辍学了,她从小在田里地里干农活,十岁就做全家人的饭,十三岁时是家里主要劳动力,而且有一双巧手,会刺绣、做花鞋垫、黑棉鞋,也会织网捕鱼。
大姑一辈子生活在湖边,没有去过山区,河水洗亮她的眼睛,使她既有辣妹子的风风火火,也有水上女人的柔情蜜意。她是当地的美人,日晒雨淋却仍然白白净净,一对又黑又粗的辫子一甩,勾住了许多年轻人的心。
姑父在新疆部队当兵,有一回到谈家河走亲戚,看到大姑,美丽少女一双毛茸茸的眼睛一下就迷住这个路过的青年。少女时大姑的理想是开一个小店或当裁缝,然而家里的农活让她连这个小小的理想都难以实现,部队青年的一身军装对大姑有很强的吸引力,那威武的光环仿佛为渔家少女打开一扇崭新的大门。
沅水的两条支流,谈家河和苏家吉河分属鼎城、汉寿两相邻县,两河经过沅水相互连通,七十年代陆路不方便,大姑出嫁时,载着嫁妆的机帆船从谈家河码头起身,大半天才走到苏家吉,满怀憧憬的大姑被接到另一个同样贫穷的农屋。
姑父在部队服役,大姑陪着婆婆在苏家吉撑起了半边天,她插秧种棉花种油菜,家里户外都是一把好手,她陪嫁时有一台凤凰牌缝纫机,晚上回到家里,她摸索着学会了缝被子、补衣服,整天忙里忙外,然而大姑并不觉得苦。没多久,姑父从部队复员回到地方,分到汉寿第一酒厂,领着不多不少的工资。他们聚少分多,一个是农村户口,一个是城市户口,彼此有代沟,才知道生活并不如当初想象的美好。有一天,大姑和县城回来的同乡闲谈,同乡无意说起的话让大姑吓了一跳:“大妹,你不知道吧,你家贵池有大动静。”原来,因为厂里派系斗争,姑父并没有和大姑商量,就一气之下辞职离开酒场,准备和一个走南闯北的人到外地植种。
姑父好高骛远,自认为在部队见多识广,想做什么,立马行动。他从内心瞧不上几乎文盲的大姑,所以做事很少和她商量。大姑感到事态严重,她从小倔强、极有主见,第二天一早,她收拾好行李,决定以后姑父到哪里,不管吃多少苦,她都要跟到哪里,她要维持一个完整的家。
大姑不顾婆婆的极力反对离家寻夫,那年西洞庭湖开始声势浩大的填湖运动。在目平湖上围堤退水,填土造田,乡村部分年轻人应征加入造田队伍。姑父是第一个响应的,他带着大姑来到围堤湖,姑父文化水平较高,负责围堤湖的测量和设计上的细活,大姑在食堂帮工。没有地方住,突击队就在围堤湖边搭了上百间草房子,用黄麻杆做篱墙,屋顶是芦苇,吃大食堂,糙米粗粮,大姑却怀上了孩子。
她把婆婆从苏家吉接到围堤湖的黄麻屋里,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女儿燕子出生在简陋的窝棚里,没有接生的医生,出生时只有四斤,体质也差,三度营养不良,几次在死亡边缘挣扎,围堤造湖结束后,他们一家四口又重新回到苏家吉,村里分了田土,但农田收入却很少。一年后,大姑怀上第二个孩子,他们一心想改善贫穷的生活,两个孩子都上学,学杂费也贵,他们种了几亩地的甘蔗。种甘蔗是笨重又不讨好的事,施肥浇水,砍甘蔗运甘蔗,再把甘蔗用小船运到德山卖,上千公斤甘蔗用独轮车拖到船上,她和姑父一个掌舵,一个拼命划船,逆沅水而上德山,几千公斤甘蔗靠两人一桨一桨划到德山的河滩,甘蔗卸到河滩后,用简陋的雨布搭成棚子,烧水做饭,等待甘蔗贩子收购。
大姑和姑父不想让孩子重复他们的命运,所以一心想让他们读书远走高飞,一儿一女,家里的农活一点不让插手,他们想了很多办法,卖甘蔗、包鱼塘、种黄麻,姑父在酒场当过技术员,办谷酒厂。两人跌跌撞撞地找出路,生活却并不富裕。
孩子们逐渐拉扯大了,女儿进技校到广州打工后外嫁,儿子考上大学,却被检出是乙肝可能面临退学,大姑在家里哭了一天一夜。像当年寻找四处漂泊的姑父一样,大姑从乡里直接到城里照顾儿子,田地荒废了,一个两手空空的女人在陌生的城市学会了生存。为了专心照顾儿子,她在学校附近租了小房子,炒瓜子、卖甘蔗,给周围的学生补衣服,一切所能找到的谋生技能都用上了。一直到儿子分配工作,找媳妇,她才松了一口气。
大姑是那种农村妇女,到哪里都笑嘻嘻的,从来不亏待任何人,别人对她一分好,她便要还十分。她就像沙漠里的刺棘草,随便在哪儿,都能凭借顽强的毅力,生出绿盈盈的草,带给人无限的生机和希望。
这也是我在沅水流域行走时,看到沅水女人想要用自己的力量改变命运的一个美丽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