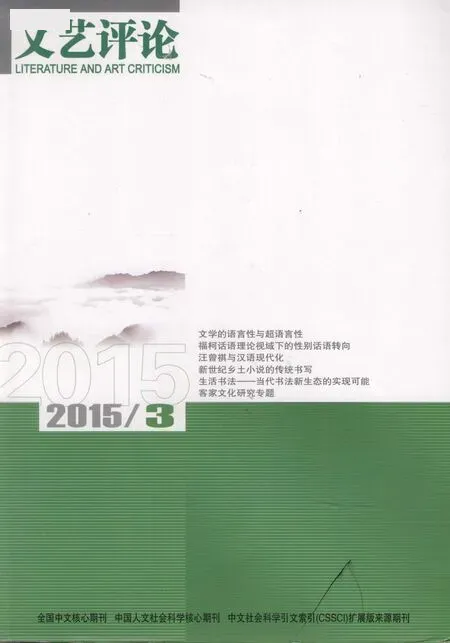文人画中的“语-图”并置艺术
2015-09-29李秀霞徐超
○李秀霞 徐超
文人画中的“语-图”并置艺术
○李秀霞 徐超
宋以后,文人逐渐开始参与到绘画中来,为绘画注入了更多的文学意境和元素,形成“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文艺最高审美境界,而最主要的视觉表现形式便是诗与画在物理层面相结合的文人画。因而,文人喜好的山水画、花鸟画逐渐取代以宣教为功能载体的人物画,一跃成为中国画的大宗,并且“凡有制作,往往与诗文为缘”,“甚至取士之法,于诗文论策外,兼试以画,开从古未有之局……(绘画)于笔墨之外,又重思想,以形象之艺术,表诗中之神趣为妙,诗中求画,画中求诗”,自此以后,中国画“盖已入文学化时期”①。它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据历史主流地位,并历明清至今近八百年而不改——这即是“所谓的‘文人画’,它积淀了中国绘画的基本精神和特色,成为中国绘画的传统核心。”②以诗词介入画面的文人画,使中国传统绘画发生了巨大转折和变迁,也改变了以往(主要是先秦至隋唐时期)的传统绘画图像对经、史、子、集等文字文本语言的单一模仿(即图像叙事),而质变为语言(诗词)与图像(绘画)并置同一物理时空(画面)的语图有机结合形态——这种有机结合形态(文人画)成为宋元及以后语言与图像关系的主流,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文人画是诗与画、语与图从内容到形式协调一致并走向融合的典型代表,它“把诗意画和题画诗揉合到了一起,诗中有画意,画中有诗意,在形式上和内在意蕴上最大程度地实现了诗与画的交融”③。但是,文人画又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诗画组合,它本身的画面无论是笔墨形式还是内在意趣,都蕴涵着诗意,这种诗意一方面通过题诗得到彰显,另一方面它与题诗又形成了呼应”④。在内涵上,文人画家自身要有较高的诗、书、画等文艺方面的学识修养,他们大都以“善诗文或有诗人的高雅逸事记载、学养兼优的艺术家为主”⑤,所创作的文人画要求“熔各种艺术(如诗书画印)于一炉”⑥,他们这种内在的文化气质通过外在的物质媒介载体和表现手段而被置于同一物理时空,便呈现出了内在(心理)与外表(物理)两个层面高度有机结合的语图关系。可见,在文人画中语图的有机结合不仅达到了内在精神层面上的对话与交流,而且在外在物理层面上,也由于语言以书法形式的介入而成为画面构图中的有机组成要素,达到语图结合的最高境界。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文人画都是“题诗+绘画”的表现形式,本文为了论证文人画在物理层面上语图关系的有机结合,仅选取“题诗+绘画”形式的文人画作为研究对象,即画面上有题诗的文人画。
一、语图实现平等对话
由于语言具有很强的叙事功能,在早期的中国画中,图像始终作为语言的附属物而存在。如《洛神赋图》,用画去表现人物故事情节,“竭力效仿文学的叙事功能,为文学故事详以图解,以图配诗,服务于诗”⑦。语言高于图像、指导图像,图像作为对语言文本的模仿或翻译,处于语言的从属地位且没有独立性。图像对语言的模仿主要是发生在先秦至隋唐时期,先秦的绘画多是对上古神话故事传说的图像化。汉代由于统治者重视图像的宣教功能,绘画基本上是以描述经史文本为主——把文本语言翻译成图像,完成图像对经史故事的叙事和模仿。魏晋至隋唐是中国佛教绘画的繁盛时期,此时的图像主要以宣扬佛法为主,按照佛经旨意用绘画进行宣教传播,将佛经图像化。从上古到隋唐这个漫长的时期里,图像始终承载着沉重的语言翻译(宣教)功能,从属于语言,不论是“晋唐的人物画,乃至三代秦汉的绘画,‘周公辅成王’、‘荆轲刺秦皇’、‘二桃杀三士’、‘鸿门宴’、‘女史箴’、‘洛神赋’、‘历代帝王’、‘竹林七贤’,包括佛教的本生故事、佛传故事、因缘故事、经变画,几乎每一种图式,都有一件相应的文学作品”⑧。图像内容基本上是叙述历史故事或是宣扬教义,因而人物画长期占据着绘画史上的主流地位。在画面表现形式上,即使有语言与图像共置同一物理时空的,从表面上看似乎语图平等,但实则不平等,因为有些语言文本描绘的是不可模仿的物象或情节,图像对此则无法进行翻译和模仿。因而,即使语言与图像并置同一时空,语言仍起到主导作用,图像只是传达语言叙事的工具。语图的对话关系也仅是单向的“语言→图像”,而非双向的“语言↔图像”。
宋以后,伴随着文人画登上历史舞台,语言与图像的地位也发生了改变。文人崇尚自然的纯真朴实,注重内心的主观情感表达,绘画的兴趣从人物转向自然,使绘画不再一味地模仿和翻译故事情节,渐渐脱离了从属诗歌的地位,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结束了语主图从的不平等对话。文人画中的“语”,“是语言的变形,它离开了口语和一般的书面语言,成为一种特异的语言形式”⑨,即“诗语”、“诗歌”、“诗”。文人画中的“图”,随着山水、花鸟等题材的象征意义在文人画中被固定下来,图像本身对语言的依赖程度也逐步减弱,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尤其到了明清,笔墨成了画面的主要表现对象,使图像的独立性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加强。
文人画的语图关系之所以能够实现平等对话,是因为诗与画在精神上存在着沟通的桥梁——意境,二者通过意境达到心理层面的共鸣。诗与画所要求的最高境界,乃是以真实、具体的形象表现艺术家的强烈感情,将诗升华,以激起观众的想象和联想,产生艺术魅力,使观众在心理上达到共鸣,回味无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便是为了使观众接受其思想所达到的意境。“意境是艺术的灵魂,是客观事物精粹的集中,加上人的思想感情的陶铸,即借景抒情,经过艺术加工,达到情景交融的美的境界、诗的境界”⑩,而这个境界也正是过去文人苦苦追寻的最高艺术,诗与画相融的至高点。
唐代是我国诗歌的鼎盛时期,“意境”概念在此时已初具雏形。诗人王昌龄最早在《诗格》中提出了“诗有三境”,即“物境”、“情境”与“意境”。晚唐的司空图也有“思与境偕”的观点,北宋梅尧臣提出“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也就是说如果能够把物象之外的“象”(即意境)写得明白如画,其意蕴味之不尽才属于佳作。南宋普闻在《诗论》中提出“得意句之妙”就在于“意从境中宣出”。南宋姜白石在《白石道人诗说》中也认为诗歌要“意中有景,景中有意”。而严羽在《沧浪诗话》里更进一步阐明“诗者,吟咏性情也……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⑪诸如此类的论述,皆是对诗歌艺术的意境阐述。
对于绘画的意境,唐代张璪最早提出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观点,这个提法是对“意境”概念的模糊认识。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便明确使用了“境界”一词:“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境界已熟,心手已应,方始纵横中度,左右逢源。”⑫“境界”即“意境”,郭熙清楚地阐明了诗与画高度相融相通的关系,并提出山水画家要画出诗意。继而明代李日华对意境作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一切形象都是象征境界。”⑬“凡画有三次第:一曰身之所容。凡置身处非邃密,即旷朗,多景所凑处是也。二曰目之所瞩。或奇胜,或渺迷,泉落运生,帆移鸟去是也。三曰意之所游。目力虽穷而情脉不断处是也。然又有意有所忽处,如写一树一石,必有草草点染取态处。写长景必有意到笔不到,为神气所吞处,是非有心于忽,盖不得不忽也。”⑭
诗与画虽属不同的艺术门类,但在各自的领域里所追求的最高审美标准都是意境,二者在这个共同的追求上相通、互补,打破了诗与画的界限,可以说意境是诗与画在各自领域至高点的交汇,架起了语与图之间沟通的桥梁。有了这个桥梁(意境),诗歌(语)与绘画(图)才可以实现双方的互通有无、平等对话。
二、有机的章法构图
文人画中诗歌语言以书法形式介入画面,成为构成画面的组成元素,意味着语言不再仅是单一的信息传达媒介,而具有了双重身份——语言和图像,它既作为内容外在表现形式的诗语存在,同时又作为画面的构成元素存在。在这种特殊的画面中,语与图、诗与画的关系既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在内容上互为引申和阐发,在形式上彼此不同却相通,使语图关系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体共生。文人画中诗歌语言题写的位置及用笔技法等因素对语图物理层面的结合意义重大,⑮对评判一幅文人画作的优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章,即整体也。《吕氏春秋·大乐》中说:“合而成章”。文人画的语图章法是互为依存、互为补充的有机构成,即语言的题写是画面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其题写位置和自身艺术性与整个画面构图形成统一的和谐整体,如宗白华所说:“在画幅上题诗写字,借书法以点醒画中的笔法,借诗句以衬出画中意境,而并不觉其破坏画景”⑯。
语图二者在文人画中的有机结合,体现于画面构图章法的合理性与整体性,画面上的各个构成元素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连,位置经营合理恰当,画面整体协调一致。“语”即画面上的文字、诗歌,传递作者的内心表达,但同时也是画面表现的构成元素,它具有既是内容又是形式的双重身份。“语”与“图”的外象表现在画面形式上互相协调与关连,在内容涵义上互为阐发和牵引,他们之间既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同时又向对方的领域不断延伸与演变(以“语言→图像”为主)。那么,此时文人画的语图有机结合并非是表面上“语+图”(即1+1=2)的简单关系,而应当是“1+1>2”的语图结合效果,从而“达到一种具有再生能力的和谐状态”⑰,这个“再生”便是文人画中语图有机结合的中心所在——“语”非原来的“语”,“图”非原来的“图”,而是在原有的“语+图”基础上达到一个新的领域(即1+1>2),实现语图有机结合再生后的“和谐状态”。
据《宣和画谱》记载,南唐后主李煜为《春江钓叟图》题诗,自此开创了在画作上题诗的风尚。宋元以后,画面上有了“语题于画”的语图结合形式,即题写诗文介入画面。题诗的语言进入画面便真正开始了语图在物理形式层面的结合,诗文与图像并置于同一画面中,就画面构图而言,语与图双方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合而成章”有内在联系的机体融合。继而语言以书法形式介入画面形成的有机构图章法样式中,语言起到了重要作用。姜今在《画境:中国画构图研究》一书中对此作了详细的阐述,主要归纳为七个作用:1.平衡。语言的题写可以解决画面构图的平衡问题,包括各组成元素的空间大小、墨色浓淡、横竖格局等协调性;2.连续。题写的语言在画面形式上可以把上下左右空间元素连接起来,贯通画面气势,景物布置有序,使画面灵活而不散,分而不断;3.衬托。语言文字的墨色浓淡、线块表现、风格样式可以虚拟、衬托图像之美;4.虚实。语言文字的墨迹虚实可以与画面景物互衬、互补;5.呼应。语言文字介入画面,使画面各个元素在形式上既相互联系呼应又增加了画面的生动性;6.笔致。在技法上画家追求“书画同源”的书、画笔法一致,画面上题写语言的笔法与绘画笔法一致,其同样能传达出画家的情感寄托;7.装饰。从画面整体性看,语言文字在画面构图的章法、字形的大小、奇正等起到一种装饰效果的作用。⑱如唐寅的《孟蜀宫妓图》,画面纵向构图,并从上下正中间一分为二,四位宫女(图像)位于分割线以下部分,题诗(语言)位于画面上部的整个空白,语言文字起到了平衡画面的作用;宫女形象的刻画采用精细的工笔重彩技法,以突出女性的优雅与纤细,而上面题诗的书写风格也采用了纤细羸弱、流畅工整的字体,以便与图像相互呼应,达到和谐统一的整体效果;题诗的内容“莲花冠子道人衣,日侍君王宴紫微。花柳不知人已去,年年斗绿与争绯”,作者感叹如花似玉的宫女们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早已不在人间,但大自然中的花柳年年盛开争奇斗艳。题诗语言中传达的情感与画面中身着华丽服饰的宫女落寞的神情正相呼应,共同表明了画面所传达的哀叹青春涵义。作者不仅把题诗作为画面空间的重要补充,并且把题诗的书写风格纳入到画面构图章法的整体性来考虑。绚丽的画面色彩、人物神情落寞的刻画以及诗歌语言的题写等诸多元素在构图章法上和谐统一,突出了文人画中诗与画、语与图的有机结合关系。
宋元之后,语言与图像在画面构图章法上的结合,完成了文人画中语图二者在物理层面上的有机结合。而到了明清,语图之间更深层次的结合——笔墨一体的高度融合,加深了语图之间的互化。
三、笔墨一体的语图高度融合
明清时期,绘画转向本体化是与笔墨高度融合分不开的。“对于中国画的传统来说,物象、心境、笔墨,三者缺一,便不足以构成具体的创作。”⑲然而,明清人更钟情于笔墨的抒写,“对于描法、皴法名目的总结,井然有序的程式,正是作为笔墨内容所赖以表现的基本形式。至此,作画便与书法无异,在书法,是书写一个一个的文字符号,在绘画,则是书写一个一个的形象符号。书法的内容,不在所书写的诗文文字,而在书写这些诗文文字的笔墨,同理,绘画的内容,也不再在所书写的形象符号,而在书写这些形象符号的笔墨。笔墨这一内容,既不是属于客体的,也不是属于主体的,而正是属于绘画本体的”⑳。笔墨在画面中被拆解为一个个书法方式用笔的点线造型,语图双方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体共生境界。这也正如丰子恺所说中国画的特色是“诗与画的内面的结合,即画的设想,构图,形状,色彩的诗化”,㉑这里所说的“诗与画的内面的结合”,正是针对明清绘画语图在物理层面的融合,即笔墨一体的语图高度融合。而石涛更是将笔墨融合提高到了哲学高度,提出了“一画之法立而万物着矣”的“一画”论,认为画面上任何一个笔墨点线都不仅仅是物象的轮廓线,而是与作者的灵魂、心灵、情感等因素有着对应关系的神秘笔墨符号。他说:“一画明,则障不在目而画可从心,画从心而障自远矣。夫画者,形天地万物者也,舍笔墨其何以形之哉!墨受于天,浓淡枯润随之;笔操于人,勾皴烘染随之。古之人未尝不以法为也,无法则于世无限焉。是一画者,非无限而限之也,非有法而限之也,法无障,障无法,法自画生,障自画退,法障不参,而乾旋坤转之义得矣,画道彰矣,一画了矣。”㉒
绘画技法由“画”到“写”的转变。文人画家主张作画的笔法以“写”代“画”,甚至创出了各种皴法、描法,使笔墨元素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北宋郭熙的山水造型变化多端,以幽奇神奥取胜,画中山石形如“鬼面”,皴如“乱云”,写瘦树枯枝,状如“蟹爪”、“鸦爪”,并在晚年独创了“卷云皴”。米芾、米友仁父子开创了“米家山水”风格,并善于运用积墨、破墨、渍染、渲淡等多种技巧以达到云山空蒙、烟云变幻的效果。南宋梁楷书法多飞白遒劲之势,后人称之为“折芦描”或“钉头鼠尾描”。这些笔墨线条甚至被程式化为绘画基本的“描法”,如“十八描”等等。
元代的山水画家如黄公望、王蒙、倪瓒等等,均在笔墨技法的运用上成就显著。黄公望的山水画风平淡天真,笔墨以疏体见长,如《富春山居图》以披麻皴为主,兼以卷云皴、折带皴、解索皴等多种皴法,笔墨多变,或横拖,或直折,或斜行,或屈曲,或挺健,枯湿浓淡等笔墨变化。王蒙山水笔墨则以密体见长,用笔变化多端,皴法丰富,厚重繁密,如《清卞隐居图》运用披麻皴、斧劈皴、牛毛皴及解索皴等多种手法,层层积累。此时绘画的关注点倾向于本体的笔墨形式,笔墨线条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在绘画观念上,文人画家“不屑称作画之事为画,而称为写,写则专从笔尖上用工夫。当作画时,不以为画,直以笔用写字之法,写出其胸中所欲画者于纸上”。柯九思谈画竹技法:“写竹,干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汤垕谈绘画技法:“画梅,谓之写梅;画竹,谓之写竹;画兰,谓之写兰,何哉?盖花之至清,画者当以意写之。”而赵孟頫更明确提出了以写代画的笔法:“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㉓以书法的写作技法直接运用到作画当中,形成了以“书写”代替“绘画”的文人作画风尚。此时,文人画的笔墨点线获得了更为独立的时空。
语图在笔墨层面融合的进程中,具有实质性推动意义的则是明代画坛大家董其昌提倡的南北宗论。他崇南贬北,实则是“反对笔墨技法的造型能力。董其昌捏造历史的实际目的是反对明代的工笔山水人物画家和被称为‘浙派’的山水人物画家。因为他们的笔墨技法还保持了具有相当水平的传统造型能力。例如他们都能描绘有真实感的人物形象”㉔。董还明确提出“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的以笔墨为中心的绘画言论。在董其昌的影响下,文人画家们纷纷响应并身体力行,使笔墨脱离传统造型能力而转向书法性绘画,笔墨的独立性更加进一步增强。
清代画风受董其昌的影响颇大,他们发展并延续了以笔墨为中心的书法性绘画,如“四王”吴历、恽南田“最大的成就是在运用干笔枯墨的方法方面”㉕,他们作画,并不是希望从真实生活中获得真实地再现客体的灵感和相应的笔墨形式,而是希望从真实生活中加强对绘画本体笔墨、程式的认识,因而,他们笔下描绘的并非真山真水,而是以各种技法以表现笔墨和线条的半抽象画。如清人画树的技法:“各种名目的点叶法,个字、介字、胡椒、鼠足等等,无不是符号化的、程式化的,相比于宋人树法的真实性和多样性,其目的显然是以此作为笔墨内容的载体‘形式’,正如书法的创作是以一个个固定的文字符号作为笔墨内容的载体‘形式’。”㉖再如郑燮的兰竹画,“竹节、竹叶、兰叶、兰花,横、竖、点、撇、捺、个、分、介等等,无一不是书法文字的点画符号”㉗,把物象简化成一种准文字符号来进行书写。至此,笔墨形式的独立性已完全确立。
清代完成了绘画向书法靠拢、以书代画的进程,对绘画本体笔墨点线的重视程度已远远超越了绘画物象本身的形象性因素。不仅画面中的物象是笔墨一体,就连画面上的诗歌语言也是以书法为表现形式的,这些因素使语图在此时达到了物理层面的高度融合。
(作者单位:常州大学艺术学院)
①㉓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228-229,319。
②徐书城《中国画之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3。
③④刘晔《中国传统诗画关系探究》[D],南京:南京艺术学院,2004:45-46。
⑤了庐,凌利中《文人画史新论》[M],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2002:2。
⑥李福顺《关于“文人画”一词》[J],社会科学战线,1982 (4):36-39。
⑦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277。
⑧徐建融《从古典到现代——中国画学文献讲义》[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97。
⑨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
⑩⑫⑭周积寅《中国历代画论》[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607,612,613-615。
⑪韩林德《境生象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64。
⑬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43。
⑮李彦锋《中国绘画史中的语图关系研究》[D],上海:上海大学,2010:113。
⑯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23。
⑰滕守尧《文化的边缘》[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28。
⑱姜今《画境:中国画构图研究》[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82:76-78。
⑲⑳㉖㉗徐建融《传统的兴衰》[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61,59,66,74。
㉑丰子恺《中国画的特色——画中有诗》[A],郎绍君、水天中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623。
㉒[清]道济著,俞剑华注释《石涛画语录》[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4。
㉔㉕王逊《中国美术史》[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448-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