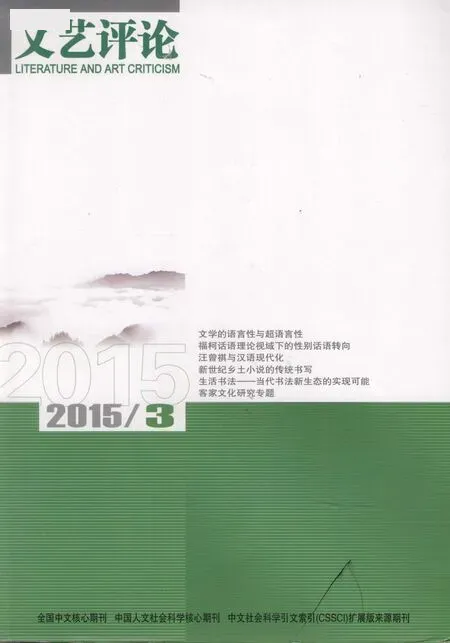颂圣诗文与汉魏文学观
2015-09-29张志勇申慧萍
○张志勇 申慧萍
颂圣诗文与汉魏文学观
○张志勇 申慧萍
颂是我国一种古老的文体,具有独立的文体特征与社会文化价值。《毛诗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①这指出了颂的文体功能是通过形容状貌来赞美盛德。后来刘勰《文心雕龙·颂赞》:“四始之至,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容告神明谓之颂……颂主告神,义必纯美。”②刘勰认为颂在风、小雅、大雅四者之中,是诗理的极致。刘勰的观点就是对《毛诗序》的继承。清代方玉润在《诗经原始》:“颂之名,自商始有之。”③《诗经》三颂之后,从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直到唐宋元明清,颂的传统不断。颂在汉代以后各时代的文学发展中,均被认为是与诗歌、散文等相并立的一种文体,完全可以独立写成一部颂体文学史。
颂的题材很广,繁杂多目,外在的表现形态也各有不同。题材方面如盛徳大业类、封禅类、丰年类、祥应类等;外在表现形态方面,有诗颂、辞颂、秦刻石文和佛颂。这些类目中,以盛徳大业类的颂圣诗文最为突出。如蔡邕《祖德颂》、曹植《孔子庙颂》《列女颂》、王肃《宗庙颂》、傅嘏《皇初颂》以及何晏《瑞颂》等,数量多,质量好,代表着这一文体在这一阶段的文学成就。
为什么在这一时期颂圣诗文的创作表现突出?我们认为,研究的切入点,除了着眼于其时代的政治文化与颂圣诗文创作的关系外,还需要从颂圣诗文发展史的通变关系来看,这主要有两个基本的角度:一个角度是从颂圣诗文本身来看其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变化,研究其在哪些方面是沿承前代的;另一个角度则是从汉魏文学观来透视颂圣诗文,找出影响这一时期颂圣诗文创作的一些因素。
通过研究发现,我们不能将颂圣诗文之受《诗经》三颂的影响,简单化为其时代的政治文化(经学传统)这一层面,而忽略多方面的内涵与表现,特别是其和当时的文学观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一方面表现为群体性的思想、愿望与感情是其基本内涵,主题内容完全是表达对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与圣主贤臣的追求意识,凸显道德教化与礼法治世这样几类;一方面表现为颂圣诗文自身发展的通变关系,表现对象明显地从简单概括转为重史述赋写,甚至通过前序描摹万象。汉魏时期的文学自觉是为浸润、引发这一转变的主要因素。
一
《诗经》中的《商颂》和《周颂》主要用来祭告祖先和礼祀天地,《鲁颂》稍有不同,则用来颂美在世的统治者(此被后人视《鲁颂》为“变颂”)如《》是歌颂鲁公养马众多,注意国家长远利益的诗;《泮水》是赞美鲁公战胜淮夷以后,在泮宫祝捷庆功,宴请宾客的诗歌;《閟宫》则是歌颂鲁僖公能兴祖业、复疆土、建新庙的诗。据此可以看出虽然此时已有咏物颂的出现,但是“美盛德、告成功”却是这一文体的主要功能。此后虽有上博简《李颂》与《楚辞·橘颂》,但仍不是颂文的主流。秦时李斯八篇刻石的创作缘由仍为:“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④刻石的目的很明白,理由很充分,也很堂皇冠冕。以《泰山刻石》为例:
皇帝临立,作制明法,臣下修饬。
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
亲巡远黎,登兹泰山,周览东极。
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
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
大义箸明,陲于后嗣,顺承勿革。
皇帝躬听,既平天下,不懈于治。
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
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
贵贱分明,男女体顺,慎遵职事。
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昆嗣。
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⑤
不仅交代了嬴政平定天下、东巡泰山的经过,还有对秦皇功德的歌颂,四言古体,描绘不多,简练肃正。
刘汉王朝结束秦末战乱,统一全国,丰功伟绩自然要扬之四海,《诗经》三颂之旧体不能适应新生王朝需要,此时蓬勃兴盛的汉赋的铺排藻饰的形式,逐渐被颂的创作者吸纳,汉颂由此迅速成长、成熟。颂扬先祖圣德功业类的作品仍是主流。如刘向的《高祖颂》、班固的《高祖颂》、傅毅的《显宗颂》、崔骃的《明帝颂》、史岑的《出师颂》、蔡邕的《祖德颂并序》、王粲的《太庙颂》等,内容全为对祖先神灵的佑护,功业伟绩的颂美,这里以刘向的《高祖颂》⑥为例:
汉家本系,出自唐帝。
降及於周,在秦作刘。
涉魏而东,是为丰公。
颂为两句一韵,四言古体,不求文采,简练干净,是对《周颂·青庙之什》的有意继承,刘勰誉为颂之正体。再如东汉末年蔡邕的《祖德颂并序》,表面虽然有了一些变化(有前序),但是美盛德的颂圣主题没有变化:
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祸乱,至于成王,太平乃洽,祥瑞毕降。夫岂后德熙隆渐浸之所通也?是以《易》嘉“积善有馀庆”,《诗》称“子孙其保之”,非特王道然也,贤人君子,修仁履德者,亦其有焉。昔我列祖,暨于予考,世载孝友,重以明德,率礼莫违,是以灵祗,降之休瑞,兔扰驯以昭其仁,木连理以象其义。斯乃祖祢之遗灵,盛德之所贶也,岂我童蒙孤稚所克任哉!乃为颂曰:
穆穆我祖,世笃其仁。
其德克明,惟懿惟醇。
宣慈惠和,无竞伊人。
岩岩我考,莅之以庄。
增崇丕显,克构其堂。
是用祚之,休徵惟光。
厥徵伊何?於昭于今,
园有甘棠,别斡同心,
坟有扰兔,宅我柏林。
神不可诬,伪不可加。
析薪之业,畏不克荷。
矧贪灵贶,以为己华。
惟予小子,岂不是欲。
干有先功,匪荣伊辱。⑦
蔡邕是陈留圉人,《史记·管蔡世家》载周文王第十四子蔡叔度生蔡仲明,受封于蔡,其后嗣遂以蔡为姓。至汉代,蔡氏已发展为一个忠孝素著的名门望族。这样的家世,正如上文中所称的“世载孝友,重以明德,率礼莫违”。对于先祖功勋懿德,他骄傲宣称:“岂是童蒙孤稚所克任哉?”
此颂四言结体,分别押“人”“光”“林”“华”等韵,言辞敬畏端直,典雅庄重,王国维言:“颂之声较风雅为缓。”⑧此颂是为代表。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颂前的散体序文,引经据典,比较注重注重遣词修饰,在典重中以求醇雅,有着一定的文采。
二
在数量上,《诗经·三颂》为40题篇,战国至三国90题篇,其中颂圣类占30%强;再看字数上,秦代李斯刻石基本都在180字,曹植的《孔子庙颂》954字(前序734字,颂诗220字),韦诞《皇后亲蚕颂》320字,傅嘏《皇初颂》351字,何晏《瑞颂》172字,文字数量上均比五十字左右的《诗经·三颂》要多得多。
探究篇目、文字数量的增多,以及前文的注重遣词修饰的原因,我们发现,一方面是受到两汉政治文化背景下的经学传统所影响。由于汉代儒学独尊,《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崇高的法定经典,也成为士子必读的经典。继之的东汉对礼乐建设也相对重视,据《后汉书·儒林传》载:“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⑨又据《后汉书·光武帝纪》:中元元年,东巡狩,封禅,“初起明堂、灵台、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图谶于天下”⑩。作为国家礼乐盛典组成部分的颂文,因而享有重要的地位。王充《论衡·须颂》云:“夫颂言,非徒画文也。如千世之后,读经书不见汉美,后世怪之。故夫古之通经之臣,纪主功令,记于竹帛;颂上令德,刻于鼎铭。文人涉世,以此自勉。”⑪在这种情况下,文人具有较为强烈的作颂垂名的意识,视作颂为崇高的事业。而由于《诗经》自西汉就被经典化,经学对颂文更重要的影响是在文中注入经学的价值观和政治理想。所以,“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解释,成了后世创作时不约而同的认定。
这种不约而同的认定,与作家的群体性意识也有着很大的关系。由于真正有价值的思想感情,只存在于群体之中,所以,出于对言语方式之颂和颂圣功能的一致理解,社会功能指向明确的颂,在人类生产力发展程度相对低下的上古阶段,基本不能抒发纯粹的个体性的感情,它必须服从于社会、群体的政治、宗教等方面的需要,所表达的主要是群体的情感与思想,主题内容完全是表达对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与圣主贤臣的追求意识,凸显道德教化与礼法治世这样几类。这种群体性的意志需要,决定了美颂所表达的都是高、大、上的美好事象,反映社会大众所期待的政治理想、审美情趣与伦理观念,就如同《尚书·尧典》的“诗言志”中的“志”,不能简单理解为体的思想感情或精神追求,而是一种经典化的东西,其具体的内涵是礼义、道、道德、政治及外交意图等。⑫这种对政治教化的诉求,即便存在于个体的心中,但却非个体所独有,而通用于群体而言。
就《诗经》而言,“国风”是典型可塑的个体形态,“三颂”与“大雅”,是典型的群体形态。所以,同为《诗经》的三个部分,国风中诸多诗歌的发展,因其个体各异的情感能够相对自由的抒发,最终形成各具特色的诗人、诗作。可以说,自两汉起,各种题材、体式、风格的诗歌洋洋大观,中国也被誉为诗歌的国度。但是颂圣诗文的创作自《诗经》后,却没有和诗歌的发展同步,千百年来的变化基本不大,作家、作品以一种“控制”的姿态坚守着颂诗所强调的“美盛德、述成功”的文体功能,弘扬儒家的王道理想,崇尚礼乐教化,注重“节制”“形式”等,用以避免情感的过度自由或泛滥。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对“颂”的使用,就是如此。《周本纪第四》中有:“(成王)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⑬宋时裴骃集解为:“何休曰:‘颂声者,太平歌颂之声,帝王之高致也。’”⑭这里司马迁视颂与功成、美政为一起,裴骃的集解也是如此。挚虞认为颂与“功成治定”密切相关,且颂的对象是“圣帝明王”或“王之圣德”,所以他对后世的“或以颂形,或以颂声”(咏物铺排),这种远离古意的颂产生不满。后来的刘勰与挚虞持同样的观点,特别是对马融《广成》《上林》等以赋体创作颂,更是言辞尖锐:“何弄文而失质乎!”⑮
三
当颂圣诗文在内容上不容改变时,自发创作或受命创作所留给作家的空间都是有限的。于是汉魏时期的文学自觉,为当时的颂圣作家提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
由此,颂圣诗文发生变化的原因的第二个方面,就是相对于《诗经》的那种回环反复的节奏感和音乐性,以及章节的回环复沓,对于汉魏作家来说,不能再简单的因循,所以颂体文学其内容由先祖而至于当世人事、事功,主旨由简单概括式的颂德、祈福,扩而为史述赋写,内容扩展。首先是对辞彩的追求。如马融的《东巡颂》(222字)有“展圣义于巡狩,喜圻畴而咏八荒。指宗岳以为期,固岱神之所望”⑯。这说明巡狩封禅的合理性,同时也宣扬了东汉经学家一贯提倡的德政。又“散斋既毕,越异良辰。棫槱构,烈火燔燃。晖光四炀,焱烂薄天。萧香肆升,青烟习云。珪璋峩峩,牺牲洁纯。郁鬯宗彝,明水玄樽。空桑孤竹,咸池云门。六八匝变,神祇并存”。言辞较《诗经三颂》华美,整齐和谐,神盈气足。此颂以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篇章较长,全面地反映了帝王出巡时的规模浩大、气势壮阔。再如曹植的《孔子庙颂》中:“煌煌大魏,受命溥将。并体黄虞,含夏苞商。降厘下土,上清三光。羣祀咸秩,靡事不纲。嘉彼玄圣,有邈其灵。遭世雾乱,莫显其荣。褒成既绝,寝庙斯倾。阙里萧条,靡歆靡馨……”⑰联系前面所引蔡邕的《祖德颂》,以及被《后汉书·崔骃传》誉为“辞甚典美”⑱崔骃的《四巡颂》,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颂圣诗文创作有着追求辞彩华美的涌流。
其次是史述赋写的重视。由于颂圣的礼文性质决定了这种文体颂德与纪功并重,因此颂文又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史家记载的特点,以发挥其纪功颂德之功用。如崔骃《南巡颂》:“建初九年,秋谷始登,犹期加时,举先王之大礼,假于章陵。遂南巡楚路,临江川以望衡山,顾九疑,叹虞舜之风。是时庶绩咸熙,罔可黜陟。”⑲《东巡颂》:“伊汉中兴三叶,于皇维烈。允迪厥伦,缵王命,彻汉勋,矩坤度以范物,规干则以陶钧。于是考上帝以质中,总列宿于北辰。开太微,敞紫庭,延儒林,以咨询岱岳之事。于是典司耆耇,载华抱实……”⑳事件的缘由、发展交代得较为清楚,立义选言,多依经树则,附圣居宗。有着转受经旨,以授于后的清晰动机。它如刘苍的《光武中兴颂》,颂扬刘秀的中兴之业,崔骃的《明帝颂》,傅毅作《显宗颂》十篇,都用以追美明帝。班固《安丰戴侯颂》颂美大将军窦宪,史岑《出师颂》颂美邓骘,《和熹邓后颂》颂美邓太后。甚至曹植的《孔子庙颂》、韦诞《皇后亲蚕颂》,都对颂主有着较为详细的叙说。虽然挚虞《文章流别论》说:“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挚虞指出班固等人的颂重在形与声,是对古颂的变体。甚至刘勰《文心雕龙》也说:“若夫子石之表充国,孟坚之序戴侯,武仲之美显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拟清庙,或范那,虽浅深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㉑这意为这些颂圣诗文沿的是《鲁颂》“变颂”的道路前行,但是,在文学自觉的汉魏时期,其注重叙事,讲究征实,让读者区详而易览的一面不容置疑。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认为自先秦到汉魏时期,颂圣诗文的文体意识较为明确。在汉魏文学自觉的背景下,颂代表了文人文学最早成熟的文学方法之一种,同时也是最早追求圣德的一种审美理想。一方面群体性的思想、愿望与感情是其基本内涵,表达对大一统王朝的政治维护,和对圣主贤臣的殷殷追求意识,凸显道德教化与礼法治世;一方面表现为颂圣诗文自身发展的通变关系,这些变化表明颂文体的功能性不是在削弱,而是不断地在拓展。随着时代的风尚走向骈俪,声韵的和谐与字句的对仗也开始在颂作中不断出现,这些使得颂的文学性日益突出,唯美化的追求不断增强,颂也终成为审美价值较高的美文学。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安徽省阜阳师范学校)
①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②⑮㉑[梁]刘勰著,詹锳《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13页,第327页,第324页。
③[清]方玉润《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43—644页。
④⑤⑥⑦⑯⑰⑲⑳[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21页,第122页,第335页,第874页,第571页,第1144页,第713页,第713页。
⑧王国维《观堂集林·说周》[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1页。
⑨⑩⑱[刘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45页,第84页,第1718页。
⑪[东汉]王充著,刘盼遂《论衡》[M],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404页。
⑫曾守正《战国时期“诗言志”的双重观念》[A],韩国慕山学术财团资助东亚人文学会《东亚人文学》第2辑。
⑬⑭[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3页,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