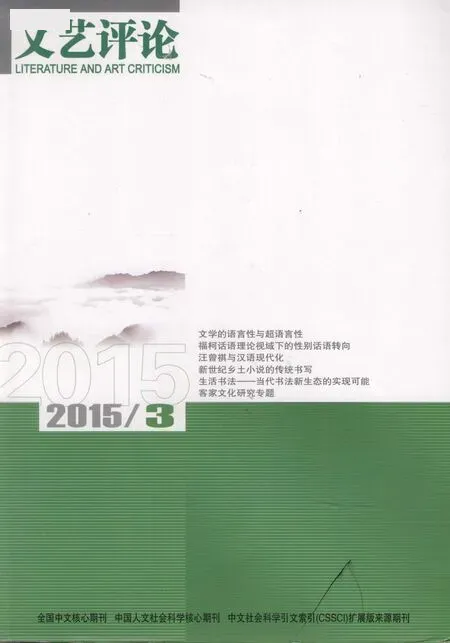福柯话语理论视域下的性别话语转向
2015-09-29王慧
○王慧
福柯话语理论视域下的性别话语转向
○王慧
当前的性别话语研究陷入了生物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之争的本质主义表征困境。如果说生物决定论是一种生物本质主义,那么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关于生理性别也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的观点让性别的社会建构论承载了文化本质主义的重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福柯的话语理论成为一种新的理论研究方法,影响极大。姚文放教授认为,“福柯的话语理论表现出一种强烈诉求,力图为话语问题提供一种制度化的背景,一种权力关系的基础,在制度化、体制化的层面上将话语视为历史语境和权力关系的表征,并形成一种特定视角,在话语问题上打开一条通往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的路径”。进而认为,福柯的“构成主义表征理论”作为“第三条途径”也许能帮助文学理论打破以往文学本体研究,即总在反映论与主情论、再现说与表现说、“镜”与“灯”之间往复徘徊的魔障。而且此理论对于“后学”的各种新文类来说都具有普遍性的参照效用。①性别话语的研究我们也可以参照此方法,以有效摆脱性别话语研究的本质主义表征困境。
近年来西方理论界出现了“后性别”概念,此概念虽没有明确的内涵指向,但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经由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两极之争,后性别试图消解性别研究的二元对立,解构性别话语背后的权力机制和知识逻辑并消除与此有关的或明或暗的影响,重建多元和谐的性别文化。因为传统性别文化两种性别的分类法已不能反映世界的真实面目。可以说,“后性别”是在“后学”理论思潮中性别话语的后现代走向,是“理论之后”的性别理论走向话语实践的表征。一方面突破人文主义的研究视域,不断拓宽理论的研究空间,在解构传统性别文化的同时积极建构更具包容性、多元化的后性别话语理论体系;另方面更加重视性别话语的实践层面和政治诉求,面对现实积极探索对策和出路,以性别研究为切入口,关注人类生存和生命,最终走向生命政治学。
一、巴特勒的性别话语理论
当代著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朱迪斯·巴勒特在《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中提出著名的“性别操演(performativity)”理论,认为性别只是一种“操演”,是由一整套的文化预期所形成的特征,而不是一种本质。社会性别不断地在一个高度刻板的管制框架里对身体予以风格/程式化(stylization),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固化,产生某种自然存有的假象。这个“整套的文化预期”和“高度刻板的管制框架”其实主要指父权制异性恋霸权的律法制度。福柯早期的话语理论认为权力是一种具有压制性的消极力量,性别成为被动的任由父权制权力/知识压制和规训的对象,性别解放的矛头理所当然指向对父权制特别是异性恋霸权的批判和颠覆。相应地,如今的性别虽然还指性别身份问题,但是性别歧视的对象早已经由“妇女”转向行行色色的“第三者话语”了,亦如卡勒所说,妇女已经成为任何一种背叛父权制话语的概念、假设和结构的激进力量的代名词。
如果说《性别麻烦》致力于揭示社会性别的非稳固性,那么《至关重要的身体》(with Bodies That Matter: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Sex”)则深入探讨了性别的物质性,即作为性别话语表征的身体是如何被形塑的。巴特勒认识到话语的界限并不是到了物质就停止,所以仅仅思考性别的建构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思考性别化身体的话语界限,追问性别话语对物质化身体的隐秘的建构过程。“回到物质的概念,身体不是一个场域或表面,而是一个物质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持续生产边界,固定化和表面的效果,我们要质疑的就是这一过程。”②身体是性别化的身体,它不是天生的,而是性别话语物质性的生成和效果的动态展示过程。
在《消解性别》(Undoing Gender)中,巴特勒重新审视了“性别操演”理论,将对性别的关注点从哲学话语转向现实生活与政治,针对医学、美学、社会与政治等领域对性别话语的各种所谓规范,提出“消解性别”的策略。因为性别规范本身并不是性别事实,它只是一种为性别的戏仿实践设定各种参数的图纸。福柯后期的话语理论认识到权力不只是一种压迫性的负面力量和否定性机制,而是一种是构成主义的、具有生产性和建构性的弥散性力量,对于权力问题的认识应该更多关注权利的技术、战术和战略方面,即权力运作的范围、构成和方法以及一系列运作的机制和效应等方面。性别规范显然承载着这样的权力,和社会律法一道形塑着身体,规训着性别,但它的存在并不说明它就是合理的。巴特勒认为“规范”的主要特性是通过建构一种社会常态来排斥与之不符的社会状况,即社会非常态的一种权利机制,并反过来使之成为主体建构的先在的现实自然条件,并以此为标准对主体的发展设定各种相应的承认、否定、奖励和惩罚的社会制度。于是巴特勒运用了一种独特的解构策略:一方面,消解某些概念的基础性地位,使之成为考察的对象;另一方面,通过理论的创造对这些概念重新赋义,使之能够包容之前不曾包容的意义。③以此开启一场话语的创造运动,通过对性别规范的重新赋义构建一种能够包容新的社会内容和性别实践、与以往话语相勾连同时又能够预防原有知识系统从中无意识作梗的新的性别话语规范。
所以,所谓“消解性别”,并不是要消灭终结性别,而是强调自我形成的社会性以及自我与他者、与社会之间相互缠绕的社会关系。因为我们不是作为独立、封闭的个人生活在世界上,而是作为一个社会性的存在,“生活在与他者之间的种种互动和关系之中”。同时也正是这种不可分隔的密切关系可能会导致某些人或群体不受社会规范“承认”(acknowledge),从而导致“社会死亡”(social death),甚至招致暴力,导致肉体死亡,这是社会规范的潜在压迫性甚至致命性的一面。巴特勒消解性别的实质就是消解传统性别文化规范的“连贯一致性”和是非优劣的等级秩序,“将性别规范中存在的二元对立逻辑和强制逻辑剔除出去”,使那些“被严格绑定在一起的性别气质、性别化身体、性向、快感和欲望等方面”的自由组合“不再被强制冠以女性的、男性的或任何性别,从而真正达成‘消解性别’的要求”④。最终目标是通过重新赋义重建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性别规范,构建新的性别话语理论体系,为性别多元化开启多重可能性。所以,后现代语境中的性别话语研究应该重视其实践层面,更多关注性别话语背后的运作机制及其社会效应,探究历史、社会、政治、文化和科技等各种权力/知识对性别话语的生成和建构。同时使新的性别规范成为一种生产多元化性别的话语机制,并通过身体这个场域不断生成各种性别话语的效应和结果。
然而,性别化身体所固有的肉体生命(bodily life)在理论上毕竟是难以化约的,“超越相对的生理学话语,肉体现实仍旧是一个顽固事实。存在着一个肉体,它在子宫中形成,在生命中演变(变的更好或更坏),死亡,分解”⑤。巴特勒将性别化身体的社会建构追溯到生理性别的分类,的确,生理性别的划分可以进行社会文化建构,但是身体毕竟首先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肉体(lived body)而存在的,有着生物解剖学的意义。我们不禁疑惑,巴特勒对性别话语的解构热情是不是过于乐观了些?正如陆扬教授所质疑的:“生理性别对于我们基因的影响,对于我们身体欲望指向的规束,在文化和社会前仆后继的建构、解构和重构面前,就那么不堪一击吗?”⑥巴特勒在对性别进行解构时,还是忽略了更为物质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生理性别。
二、后人类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化性别
后人类主义性别研究(posthumanism gender studies)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巴特勒的偏颇,主张将对科学技术的批判与父权制文化、性别关系和身份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引导人们在技术科学实践与文化中去探究自然与社会、身体与心灵、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等之间辩证互动与异质缠绕的内在动态关系。它直接对人的自然性进行干预,使人类从自然的专制下解放出来,探索技术科学尤其是生物工程给性别带来的多元化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对社会性别进行了更大程度的解构,实行对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双重消解。
在《类人猿、赛博格和女性:自然的再创造》一书中,娜·哈拉维丰富发展了“赛博”(eyborg)观念。在她看来,赛博“是一个后性别世界的生物”⑦。或者说,赛博代表了后性别社会的一种幻想,特别是在科幻世界里。作为一种有机与无机相结合的特殊混合物,赛博是一个能够颠覆和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性别与政治秩序的全新物种,其潜能就是融合和重构社会性别的界限,使性别、种族和阶级在后性别社会得到整合。赛博神话不仅构建一个多元、界限模糊、元素冲突的社会,而且是一个关于女性的贴切隐喻,赛博终结了女性的焦虑、孤独与恐惧,她们不必作为男性的附庸,生存的意义也不再简单地归之于生育孩子。因为在赛博格社会中,男女两性之间的性别界限将变得模糊,其区分也变得毫无意义。
然而,哈拉维最终无法超越客观视角,给予科学太多的信任,使技科学变成一种新的宗教,而赛博格的后性别社会实际上强调用第三性别,即不男不女的电子人来取代现有的性别分类。后人类主义性别研究本以消除性别差异为出发点来探索性别的多元化问题,却无意间将第三性别(或曰超性别)的赛博格作为自我规范的标准,从而使人的性别成为“他者”,结果反而取消了性别的多样性。所以我们一定要警惕第三性别或无性别带来的性别单一化倾向。科技本身没有性别,但掌握科技的人却是有性别的。人类的性别主义偏见会直接影响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渗透到科技产品之中。福柯的话语理论在方法论上抛弃了说话主体,强调所说出的话和为什么这样说而不是说话者本人,但性别研究则有必要在“所说出的话语中承认主体的在场”,因为“谁在说话”至关重要。男性中心的世界观将外在世界作为征服的对象、异己的存在进行改造,其生产必然更多具有女性化特征,并作为一种镜像规范来印证创造者自身的伟大。就像伊格尔顿所说,人们的性别/性意识及其行为涉及人的幻想与欲望,与社会意识形态密切相连,其理性部分本身便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性别政治。除现实的统治外,男人也需要在想象领域征服妇女,从外部想象她们。⑧后性别必须致力于拆解现实性别行为背后存在的被相对忽略的支配模式,批判文化传统男性精英的优势地位和特权,这也是福柯话语理论的应有之义。特别是性别科技和消费文化的联姻,加上媒体文化这个幕后推手,使当代审美文化构建了一系列女性化的消费规范和准则。拉什(S· Lasch)认为:消费文化是一种自恋的文化,“我们就如演员与观众,生活在镜像的包围中,在这些镜子中寻找我们迷惑别人或给别人深刻印象能力的保证……广告工业则有意鼓励这种对于外表的优先关注”⑨。人们就在社会镜像的参照下,在他者的肯定中确认自我的存在,在这个社会镜像的背后我们不难看到到处晃动着的男权制身影。
后人类主义性别研究面临道德伦理和现实层面的多重困境。如果“文化的调教不能删除生理性别的遗传程序”,那么同样,生物技术的发展虽然可以改变生理的性别,但是却无计消除社会性别的影响。文化具有根深蒂固的思想根源,并不是生理界限一经打破,社会性别就不复存在,或者一个变性手术就能从根本上消除性别不平等。我们在建构世界的同时,世界也以同样的方式建构着我们。那么,我们到底可以允许科学在多大程度上重构我们的身体?或者说,我们的身体还有多大程度是自己的?对“身体是什么”的质疑又和“人是什么”“我是谁”等身份认同问题直接相关,从而身体成为一种极不确定的存在状态。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的失当发展不但会造成道德伦理的混乱,改变社会关系的构成,也极有可能导致身体的消解,甚至使整个人类面临自我毁灭的危险,如同福柯在《词与物》最后一页所写:“人将被抹去,正如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
三、重新审视性别二元论
无论是巴特勒的消解性别还是生物技术的性别改造都没能走出二元论的苑囿,无法真正解决性别多元化问题,况且还有实践层面权力-知识体系对父权制直接或间接的维护。人们往往将身心二元论追溯至笛卡尔哲学(其实它的隐秘起源驻扎在柏拉图哲学中),然而有人惊奇地发现笛卡尔的立场竟是“二元互动”的,他相信在身体和心灵之间其实有着一个密切的互动。尼采将历史设想为狄奥尼索斯和阿波罗这两种原则的无穷无尽的争斗,但他最终认为只有这两种原则成功地结合起来,一个健康的社会才能出现。如果在个体的生命中不能创造出这两个原则的满意综合,就会引发疾病、病态和疯狂。这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二元论。伊格尔顿认为,人们的性别规定性首先由真实具体的肉身来承载,肉身毕竟是我们所拥有的人类存在所赋予的最显而易见的符号,拥有一个身体是一种在世界上工作的方式,我们不能从自己身体的内部领会我们自己的身体。同时这个肉身又与社会权力、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物质与精神、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⑩经过福柯重新考量的“权力”概念不再是某种既定物,而被理解成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它们存在于其运作的领域中永不停止地相互争斗和冲撞,形成诸多不稳定、不平衡和不对称的权力形态。对于后性别话语而言,性别的规定性首先由真实具体的肉身承载,同时又与社会权力、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确如福柯所言,“使人类科学话语从根本上可能的进程是两种完全异质的话语和机制的并置与对立”⑪,那么长期以来性别话语一直在生物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这二元之间的往复徘徊和论争,恰恰可以成为后性别话语得以重构的契机和生长点。所以,后性别话语理论可以吸收“二元互动论”并将之运用于性别话语理论本质主义的争论中,如果说物质和精神是人们存在的两个方面,不能过分抬高任何单方面的意义,那么性别的生物性和社会性也是性别构成的两个方面,我们也不可过分抬高或者任意消解其中任何一方的意义。性别话语的文化建构论必须和性别的自然性融合起来。
四、走向生命政治学的可能
在《身体之重》的导言中,巴特勒明确表示,对身体解构和建构的追问,最终是要重构“值得保护的生命、值得挽救的生命、值得悼念的生命”。巴特勒的性别理论以性别研究为起点最终走向了生命政治学。“巴特勒的性别规范概念,将性别问题提升至一个涉及人生命/生活本身元问题的高度,使我们认清了性别问题不只是社会学诸多分支学科之一,更是社会学的一个元问题,与社会科学的众多预设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⑪《消解性别》的后半部分重点探讨了“Life”、死亡、暴力、哀悼和悲伤等与生命有关的重要概念,直接指向对人的生命和生存的关注。后人类主义性别话语则试图通过对人类生物性别的改造,打破人类生命的局限,无限增强生命力,实现生命的永恒和绝对自由。
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对当下理论只关注性别的趋势表示忧虑,认为未来的理论必须重视人类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公正、道德和死亡等,强调阶级、权力等社会因素的重要性。他将性别视角与阶级分析结合起来的理论和批评实践也让我们认识到,认知策略与学术范式必须与时俱进,理论即使再高深、再形而上,最终也一定要落实到社会现实中,对社会的进步产生实际的推动作用。巴特勒的性别理论和后人类主义性别研究最终都走向生命政治学,直接指向对人类生命和人类存在本身的关切。当然,巴特勒的理论局限在异性恋霸权的框架下,而后人类主义忽略了人类生命的多样性,试图单纯依靠科技来追求生命的永恒,最终走向了统一性的技术化生命。
结语
性别话语从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二元对立走向后性别的多元和谐,这和福柯话语理论的发展相一致,也和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精神相吻合。后性别话语站在更高的人类生存层面和更广阔的社会视域,突破人文科学领域的局限,探讨后性别话语的多元辩证融合,最终走向生命政治学,实现对人类生存生命本身的关爱。当然性别并不是个人奋斗式的“性别操演”,要想达到后性别话语多元共融的动态发展,必须首先改变人们的性别思维模式,还必须通过对性别话语的重新“赋义”来制定新的社会规范,给予社会制度上的“承认”和保证。同时重视性别理论的政治诉求和话语实践,因为父权制的影响根深蒂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作为“权力的眼睛”,构成主义的性别话语仍然会演化为具有一定压制性的消极力量和否定性机制。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人文传媒学院)
①姚文放《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向与福柯的话语理论》[J],社会科学辑刊,2013(3)。
②朱迪斯·巴特勒《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M],李钧鹏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
③朱迪斯·巴特勒《消解性别》[M],郭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
④郭劼《承认与消解:朱迪斯·巴特勒的〈消解性别〉》[J],妇女研究论丛,2010(6)。
⑤布莱恩·特纳《身体问题:社会理论的新近发展》[A],汪民安译,汪民安陈永国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⑥陆扬《论后现代女性主义》[J],社会科学家,2012(3)。
⑦Donna J.Harraway.Simians,Cyborgs,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M],London:Free Association Books,1991.
⑧林树明《论特里·伊格尔顿的“性别视角”》[J],文学评论,2010(2)。
⑨陶东风《消费文化语境下的身体美学》[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2)。
⑩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M],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江苏省普通高校学术学位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KYLX_1324);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青年项目(Q20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