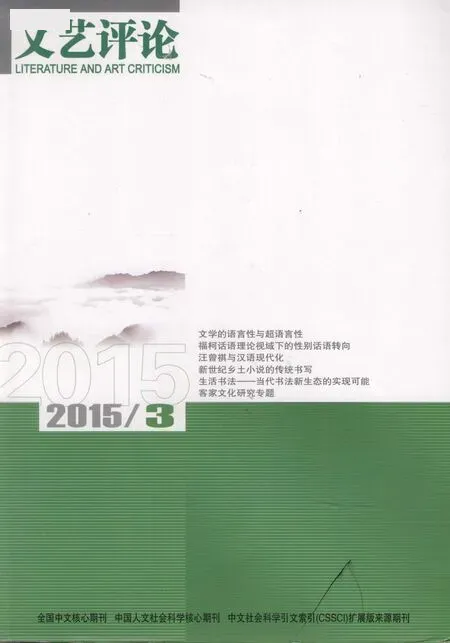论文学的超语言性
2015-09-29白雪王向荣
○白雪 王向荣
论文学的超语言性
○白雪 王向荣
语言与文学关系的探讨是文学理论的传统课题。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结论首先肯定了语言对文学的重要性,同时也区分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不同。然而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它的终极指向一定不是语言所能彻底涵盖的,它是超语言的,尤其是伟大的文学作品,物质媒介必须消失,人们将不再感觉到语言材料存在而进入绝对自由的想象。①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思考。
一、“言”“意”离合的诗学效应
文学是意义的世界,这“意义”不是科学范畴下的知识,而是由语言带来的具有时间性的“信息”与“消息”,②或者说,是与人的生活直接相关的审美经验与价值。这审美经验与价值,与知识的不可脱离语言的性质不同,是与语言相分离的,是历史的超语言的存在。
中国古典诗学很早就点明了言、意之间的这种关系。庄子《外物》中说:“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王弼后来提出“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周易略例·明象》)的说法。刘勰更是意识到了“意在言外”的特征,《文心雕龙》多处论及文外之横生的妙趣。之后的司空图、严羽、叶燮等诗学大家对此都深有体会。这不仅是一种文化诗学现象,更是一种生存与历史现象,是与意义直接相关的生存价值的体现。就如我们欣赏《西游记》不会把它与唐代的历史进行对比一样,《西游记》存在的意义不是让我们想起现实,而恰恰是让我们忘记现实,不是让我们理解语言确定的、实在的内涵,而是让我们享受具有终极意义的审美经验,即透过一个佛教高僧充满艰辛的止欲修行,我们发现,人的存在其实就是当下的方生方死的过程,是在不断否定肉身所代表的物质、欲望的怪圈中朝向辉光、日新的精神圣地的过程。老子讲“死而不亡者寿”(《老子·三十三章》),肉身的生死与精神的存亡在历史中生动地演绎着生命繁衍的盛举,西行之路的象征意义于此可见。诗人瓦雷里为了说明诗的特点,把非文学语言比作走路,把文学语言比作跳舞,尽管都是脚的运动,但前者有外在的目的,而后者的目的就在自身。弱化外在目的而凸显自我、放大自我,其结果就是语言艺术自身广泛意义——“诗意”的产生。伟大的艺术必须超越语言符号的指示功能,以否定自身的方式而成为自身,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文学的世界,不是概念与推理,不是语言确定的涵义,而是某种审美的生命启示,是历史的,更是个别的。
20世纪西方的语言本体论也认为,语言产生“意义”,与“存在”同在,为人类“命名”,并以此确立人们的世界观。在文学上,语言本体论表现为文本本体论,即语言文本包含着文学的功能、价值等全部要素。语言是文学的本体,语言为文学创造了“意义”,这意义不同于现实的世界,是一种更真实的存在。虽说语言本体论中的言、意关系与中国古典诗学中的言、意关系并不相同,一个认为意义与语言具有同一性,一个认为意义是超语言的存在,但意义的超语言性并非是指意义可以离开语言而独立存在,意义永远是语言的意义,而所谓的“超语言性”指的是由语言的形而上的特征所带来的不可确定的思维视域。因此,可以说二者在“意义”层面上的诗学效应完全是一致的,同样是在前科学与前认识的世界里开显原初的生活样貌。“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绝句》)诗人作诗的目的不是让我们认识这些事物,而是让我们从中感受一种实在的、贴己的东西。海德格尔对凡·高的油画《农鞋》做过精彩的分析:
从鞋具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着劳动步履的艰辛。这硬邦邦、沉甸甸的破旧的农鞋里,集聚着那寒风陡峭迈动在一望无际的永远单调的田垅上的步履的坚韧和滞缓……这器具属于大地,它在农妇的世界里得到保存,正是这种保存的归属关系,器具本身才得以出现而自持,保持着原样。③
这段分析给我们的启示就是:黄鹂、翠柳、白鹭、青天、西岭与雪,它们不单单是诗人笔下的景致,而是他独特的审美经验,这里保存着事物在精神的观照中开显出的最真实的属性,丰满而“自持”;它们在空间中占据着时间,是一段早已或正在向未来呈现的“澄明”而光亮的世界。可见,诗人语言的有限性决不能涵养诗意即将彰显的全部“机心”,但它们永远向着这个目标努力。“诗人呈现的是那限制不住的东西,于是我们可以说,诗人呈现了无限。”④
二、超象之境的人生旨趣
中国古典诗学中言、象、意结构的确立,不仅将意义从语言的层面中剥离出来,同时把意义与意象的关系也呈现给我们。《周易·系辞》中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立象尽意,是中国古人处理语言有限性的最佳方式,而“意象”论最终以“意境”说作为成熟态影响着中国古典诗学的历史。也就是说,语言创造的意义世界在中国古人那里是通过“意象”与“意境”两个重要的范畴来完成的。语言、意象、意境,不仅标示着艺术发生的历史性,同时也是艺术精神性的逻辑展示,创意即造境,艺术的意义最终在超语言、超意象的“境”中落地生根。
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记》中提出“境生于象外”的说法,这同司空图的“象外之象”“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与李生论诗书》),如出一辙,都点出了意在“言”“象”之外的重要特征。虽说意境本身是虚实相生的审美境界,但文学的精神与其中实情、实景无多挂碍,而大都赋予了无着无落的虚空之态。“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无论在本体层面,还是在生活层面,“无”永远在“有”之上,因为它无限制、无定形、无约无束,这同样是艺术所追求的超验的世界。“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白居易《问刘十九》)舒适、惬意、友谊与酒,时空纵横处,旨味无尽,这里展示的不是概念与推理,不是事物的属性与功能,不是知识与认知,而是人生的启示与思考:酒、火炉、雪、黄昏,看到这些,就知道这是冬天,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刻,这里有很诗意的人,有一种别样的人生,鲜活、情趣、生命力与创造。法国美学家柏格森的“绵延”曾经神秘地冲击着一个时代,但在文学的世界里,“绵延”其实早就孕养了我们敏感而灵动的心灵。这就是艺术的本质:是一种时间过程,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运动和变化;更是一种直觉过程,自由、开放、永恒而没有界限。充满“诗意”的语言,游走于“绝对精神”的世界,直达生命深处,并主宰一切。正如人生若只如初见,在艺术之境的“召唤”中,我们与诗人一次次隔空相遇,清新而美丽的邂逅是宗教反观的真实,在此,已无言可辨。“不离审美,是艺术,超审美,方是伟大的艺术。”⑤
黑格尔曾把艺术直接推向“死亡”,他认为,艺术最终将走向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宗教与哲学。我们知道,黑格尔讲的不是在时间上实际发生的现象,而是精神上开显的一种先后的逻辑关系,即宗教高于艺术,哲学高于宗教。当然,这里言及哲学与宗教无非是为了说清楚艺术的最高旨意是明“道”于人,而“道”的审美境界我们早在中国古人那里聆听悉受——“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含蓄》)可见,意境之“无”承载的不仅仅是艺术的审美特质,更多的是与生俱来的生命的启示、思考与生存经验,海德格尔后期推崇“艺术真实于生活”的思想与艺术之“无”直接相关。
三、“形而上”语言的“入神”之美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已非日常语言,这一结论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是什么因素使日常语言成为艺术语言而最终涵养文学的存在。这个问题直接关乎语言的一个特殊品质,即语言超越自身的“形而上”的特征。语言是语言的未来,语言一经说出指向的就是永恒无界、深奥未知的世界,这表明,在本体层面语言将进行的是一场生命与生存的“冒险”,不可逆料。语言的这一特征造就了语言艺术“从有到无”的审美品质,同时,语言艺术的审美品质也是语言这一特征的直接放大。
因此,中国古人讲诗要入“神”。关于神,中国古典诗学中多有提及,如:“谷神不死。”(《老子·六章》)“天地并,神明往。”(《庄子·天地》)“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庄子·养生主》)“阴阳不测之谓神。”(《周易·系辞(上)》)“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孟子·尽心下》)“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化,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毛诗序》)可见,“神”作为超验的存在,应是宇宙最深的奥秘。诗入神,就是诗作为有限而表达无限,表达人性与宇宙之道,表达不可企及却永恒朝向的“天地之心”。“诗者天地之心也。”(《诗纬》)说的正是诗作为语言艺术的典范,是对难以认知世界的一种最高的诠释,诗因着“不知”的层面而达于另外的“知”,从而引领我们“进入物象各具其性的内在机枢”⑥,“神人以和”的境界大致如此。
中国早期的诗学提供者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表面上说的是语言的局限性——语言不能表达“道”,语言不能说尽“无”,但仔细想来,语言恰恰是在局促不安与捉襟见肘中始终指向着“道”与“无”。可见,老子的思想是在语言的有限性中完成的,语言向“无”而生,同样是他最深的诗学体会。“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在创生的机制里,“无”永远是“有”的最虔诚的合作者。而语言的活动就是使接受者必须接受语言之外的“无言”,以及其所凝注的物物之间的“原初交谈”,这是未受主体认知“印象”过的“未知之知”的领域,是一切艺术都将分享的美丽之光。“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五十六章》)老子在其思想体系中反反复复地申明“有”与“无”之间的关系,而语言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语言是一切具体而微的“有”,语言又是离开具体而微的“无”,语言在“有”与“无”、在世俗与道之间勾连着人的独特生存。可见,在老子的思想中,语言于人生的重要意义是本体层面的,在此与艺术不谋而合,语言是艺术的“家”,还是艺术是语言的“家”,不可在浮光掠影的生活层面给予简单论断。
文学超越语言,向“神”而生,这使其对人类的精神产生了强大的势能,孔子对此深有体会:“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早已透露出语言艺术于人类心智的重要作用。“兴”“观”“群”“怨”,从感知与认知、个体与群体、情感与理性、对话与宣泄等各个视角来体认“诗”的伟大之处,诗作为语言艺术是整体的存在,对人类而言,它的绽放就如“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般的庄严、瑰丽、妙不可言。可见,文学使人觉醒,使人成长,这一定要放在对宇宙万物的洞察中,对天地自然原初力量的审视中去理解和感悟。因为“语言之用——仿佛一指、一火花,指向、闪亮那物物无碍在沉默中相互指认的世界”。⑦
结语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庄子·寓言》)语言创造意义,但意义大于语言。文学的超语言性不仅是语言与文学关系的问题,也不仅是文学自身的审美形态的问题,而是与人的生存直接相关的“存在”的问题。因为,如果退回到语言艺术发生的起点,我们会发现,它与人类精神的成长从未有过须臾分离,与其说它是精神的一种“保存”,不如说它与精神一起历经沧桑,始终相伴而行于历史的轮回。《论语·阳货》中有段这样的记载: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这可作为以上结论的最形象的解说。
(作者单位: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①傅道彬,于茀《文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②叶秀山《中国艺术之“形而上”意义》[A],《中西智慧的贯通》[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页。
③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54页。
④叶秀山《想起了语言是存在的家》[A],《中西智慧的贯通》[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3页。
⑤张立伟《意境不是诗歌的最高特征》[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第89页。
⑥⑦叶维廉《中国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第56页。
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2522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