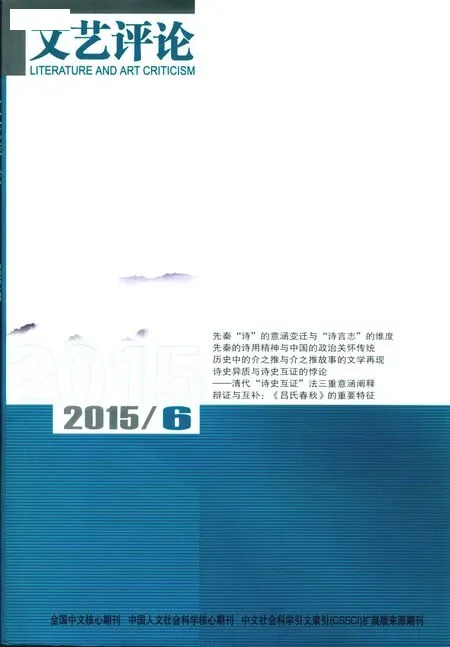《思旧录》中的名士群体特征与心态嬗变
2015-09-29雷斌慧
雷斌慧
《思旧录》中的名士群体特征与心态嬗变
雷斌慧
《思旧录》是黄宗羲皇皇大著中一个特别的存在。它作于黄宗羲晚年,约康熙三十一、三十二年之间。全祖望《梨洲先生思旧录序》评价:“以先生之撰述言之,《学案》、《文案》,如山如河,是录其渺焉者。然先生百年阅历,取精多而用物宏,于此约略见之。”①《思旧录》中黄宗羲追忆昔日师友,以刘宗周为首,以木皙作结,展现了明清鼎革之际名士群体不同的政治价值取向,以及名士生活的审美风尚。《思旧录》中名士群体的书写亦透露了黄宗羲心态复杂微妙的嬗变。
一、《思旧录》中的名士群体政治价值取向考察
“士”之一词源远流长。《说文解字》云:“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为士。”②段玉裁引申士为能事其事者。“名士”最早出现在《礼记·月令》“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③注曰:“名士,不仕者。”蔡氏曰:“名士者,谓其德行贞纯,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也。”④魏晋时期,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江左名士蔚为大观。名士风流亦成为士人的自觉追求与社会风尚。冯友兰先生《论风流》中评价名士风流为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名士传统并不止于魏晋,从竹林七贤到陈继儒、李贽、张岱等,不绝如缕。晚明名士在承继魏晋风流的基础上,浸于心学,染于世俗,清谈诞放,任情狂傲。《四库全书总目》亦评价“隆、万以后,运趋末造,风气日偷。道学侈称卓老,务讲禅宗。山人竞述眉公,矫言幽尚。或清谈诞放,学晋、宋而不成。或绮语浮华,沿齐、梁而加甚。”⑤
《思旧录》追忆明清易代之际的师友,多用“名士”一词。如刘城“戊寅,余信宿其家,四壁图书,不愧名士也。”⑥如刘应期“余尝执笔,名士十数人列坐。”⑦如吴钟峦“知长兴时,刻社稿,名士品不过二十人,而余在其列。”⑧如许元溥“丙子,来越城,张登子大会名士,孟宏与焉。”⑨如管鑨“甲戌,余至其家,其于一时名士,一时堂头皆讥贬。”⑩可见,黄宗羲对自身及师友名士身份的认同。钱基博先生评价:“明末以遗老为大儒者,李顒学究气,独善其身,术未能以经国;黄宗羲名士气,大言不怍,行不足以饬躬。”⑪钱先生虽批评黄宗羲大言不怍,行不饬躬,但明确点出黄宗羲具有名士气。
《思旧录》录明清鼎革之际的名士合117位。黄宗羲谈及《思旧录》的创作缘起“余少逢患难,故出而交游最早,其一段交情,不可磨灭者,追忆而志之。开卷如在,于其人之爵位行事,无暇详也。然皆桑海以前之人,后此亦有知己感恩者,当为别录。”⑫《思旧录》的写作以黄宗羲与名士群体的交往为中心,辐射开去,取精用宏,破爵位行事之旧俗,传不可磨灭之至情。黄宗羲虽表示无暇详记名士之爵位行事,但对他们在明清鼎革之际的政治价值取向多有注明,大致可分为忠贞殉国、遁入佛道、隐居不仕三类。《思旧录》中标示忠贞殉国的名士有:刘宗周、范景文、倪元璐、金铉、施邦曜、祁彪佳、巩永固、魏学濂、徐石麒、朱天麟、沈士柱、麻三衡、赵初浣、金浑、杨廷枢、顾杲、朱大典、张国维、黄端伯、徐汧、彭期生、陈函辉、吴炳、陆培、冯元飏、冯元飇、华夏、瞿式耜、张肯堂、吴钟峦、余煌、熊汝霖、孙嘉绩、王毓蓍、张煌言、吴应箕、韩上桂、陈子龙。《思旧录》中标示因明亡遁入佛道的名士有:方以智、林增智、陆圻、章正宸、张岐然、江浩、熊开元、弘储、奯堂、阎尔梅。考察各小传人物行止及纪年,《思旧录》中心念大明、隐居不仕的名士有:周延祚、李孙之、周茂兰、沈寿民、林云凤、林古度、陈弘绪、徐枋、巢明盛、冯家祯、陆符、万泰、董守谕、余增远、王正中、顾炎武、施博、汪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思旧录》中未明确标示政治价值取向的名士有51位,不足二分之一。在此51人中,黄宗羲未标示其人之行藏出处,实有两大缘由。一方面在于《思旧录》存有大量明亡(即甲申之变)前名士。如文震孟、何栋如、陈继儒、史磐、何乔远、张溥、万时华、张鼐、卓人月、朱荃宰、陈玄素、吴馡、钱禧、闻启详、苏桓、邓锡蕃、姜思睿、严调御。另一方面在于黄宗羲书写上另有侧重。如沈寿国与沈寿民本为兄弟,同是遗民。然而,黄宗羲在沈寿国的书写中,集中笔墨描写沈寿国赠会银一事,“迟明,余始知之,谓治先曰:‘此子会银也,凡人窘则举会,奈何以饷余乎?’治先曰:‘子途中不比余家中也。’”⑬重心放在沈寿国与自己关系的亲厚上,并凸显沈寿国之仗义仁厚。
《思旧录》中黄宗羲对名士政治价值取向的重视究竟有何价值和意义?首先,黄宗羲于抗清失败后,奉母归里,专心学术,不仕清朝,大节无亏。然而,随着清王朝政权的巩固,黄宗羲与清朝的关系趋于缓和,不仅称赞康熙皇帝为圣主,而且与清朝大员汤斌、徐乾学、徐元文、叶方蔼、许三礼等交往频繁,引起世人对其遗民身份的质疑,甚至包括亲弟黄宗会、黄宗炎、好友吕留良等。全祖望《答诸生问南雷学术帖子》亦用辩解的口吻谈到“若谓先生以故国遗老,不应尚与时人交接,以是为风节之玷,则又不然。先生集中,盖累及此。……盖先生老而有母,岂得尽废甘旨之奉。但使大节无亏,固不能竟避世以为洁。”⑭全祖望认为不可对遗民的标准太过苛刻,遗民不仕新朝即可,不必避世,亦不用世袭,黄宗羲为奉母养亲而与清朝官员有适当交往不算有损大节。“先生集中盖累及此”,一“累”字可见黄宗羲对自己遗民身份的苦苦辩解。《思旧录》写于黄宗羲去世的前几年,其对117位名士政治价值取向的关注,以另一种方式诠释了遗民的内涵,并曲折传达出黄宗羲对自身遗民身份的认同与坚守。其次,黄宗羲《谢时符先生墓志铭》云:“故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⑮。《谢皋羽年谱游录注序》云:“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逮夫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坌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⑯《思旧录》以一种另类的书写表达了黄宗羲对遗民的表彰以及对天地间一缕元气的扶持。最后,黄宗羲《户部贵州清吏司主事兼经筵日讲官次公董公墓志铭》云:“国可灭,史不可灭”⑰,表现出为国存史的使命感。《南雷文定凡例四则》亦云:“余草野穷民,不得名公巨卿之事以述之,所载多亡国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稗于史氏之缺文一也。”⑱《思旧录》对明清易代之际遗民的书写,以独特的方式诠释了黄宗羲以文补史的理念。《思旧录》中对名士遗民身份的标记,使得他们少了几分魏晋士人玄谈的清逸,多了一份亡国的沉重,染上鲜明的时代色彩。
二、《思旧录》中名士生活的审美风尚
章国锋《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解读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认为“由交往日常实践编织而成的相互作用之网乃是生活世界——文化、社会和个性——得以自我再生产的媒介,这一再生产过程扩展成为生活世界的象征性结构。”⑲《思旧录》以黄宗羲与名士群体的交往为轴心,辐射开去,编织出明末清初的生活世界,在关注名士群体政治价值取向的同时,亦展现出名士群体的精神风貌与文化底蕴。刘悦笛《重建中国化的“生活美学”》指出“中国古典美学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中国古典美学家的人生就是一种‘有情的人生’,他们往往能体悟到生活本身的美感,并能在适当地方上升到美学的高度。”⑳《思旧录》不仅饱含深情地书写了千姿百态的名士个体,而且整体还原了名士的日常生活,再现明末清初名士群体诗意化的人生境界与审美风尚。
魏晋时期,人物品藻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其源头可追溯至东汉时期的清议。《世说新语》即列有《品藻》、《识鉴》、《赏誉》,表现出对士人形貌、风神、才性的礼赞。宗白华先生评价“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㉑《思旧录》亦重人物品藻。如吴钟峦“知长兴时,刻诗稿,名士品不过二十人,而余在其列。”㉒刘应期“此时谿上多名士,而瑞当裁量其间,不少假借,人亦畏其清议。冯正则曰:‘瑞当亦有疵处,然可件而尽也;吾等非无好处,然可件而尽也。吾等与瑞当,相去远矣。’……余尝执笔,名士十数人列坐,皆无毫发私意,必众论相谐而后定。慈溪冯跻仲有盛名,余以瑞当为首,跻仲次之。跻仲不悦,无以难也。”㉓从以上记载可见黄宗羲与周围师友品藻人物已成风气。黄宗羲不仅为名列吴钟峦品题之名士而自豪,而且亲自加入到品评人物的活动中。冯正则对刘应期与众名士优劣的品评,亦有魏晋风味。在对人物的品评中,黄宗羲对名士的外在音容颇有关注。如范景文“公仪观甚伟,好自标致。”㉔表现出对范景文仪容壮伟的推举。如张国维“送余下舟,声如洪钟。寻死国难。”㉕对其声音记忆犹新,眼前宛然现出一豪迈的硬汉形象。然而,相比于人物的形貌,黄宗羲更关注人物的风神内蕴,并在继承魏晋名士对“清”的推许中,凸显出对“慷爽”的赞赏。如张鼐“已巳,余见之于其家,时先生已病革,卧一坑上,以隐囊靠背而坐,谓余气清,他年远到,勿忘老夫之言也。”㉖张鼐为前辈师友,其人“气清”的赞许,老年黄宗羲仍记忆犹新,可见对“清”的重视。“慷爽”则为慷慨高昂、爽朗洒脱、豪迈大气的英雄气概。如陆符“为人慷爽,能面折人之是非。”㉗,夸赞老友慷爽之性。如张采“意气慷慨,不尽其才而止。”㉘凸显其意气慷慨的神韵。如王毓蓍“为人亢爽不羁,好声色,在先师弟子中,颇为逸群。”㉙勾勒王毓蓍的形象,突出其亢爽的一面。黄宗羲对“慷爽”的推举,浸润鲜明的时代底色。
魏晋名士在日常生活中融入文化品位与独特个性,展示出异于常人的文艺才情与风雅癖好,如服药饮酒,植竹听琴,吟诗歌,善围棋,喜长啸,通书法,精绘画,营造出诗意化的人生境界。晚明名士将之甚至发展为痴癖。如袁宏道《瓶史·十好事》云:“嵇康之锻也,武子之马也,陆羽之茶也,米癫之石也,倪云林之洁也,皆以癖而寄其磊傀俊逸之气者也。”㉚极力颂扬癖好中存俊逸之气,并断言乏味可憎之人皆为无癖之人。张岱《自为墓志铭》亦云:“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㉛将一系列的雅好铺展开来,风流洒脱又不失高雅之致。黄宗羲在《思旧录》的书写中,对师友之诗歌唱和、藏书访书、文人茶事、品曲听琴、斗墨赏画、园林设计等方面表现出十足的关注,流露出一派名士风范。
《思旧录》中记载了大量黄宗羲与师友之间的诗歌唱酬。首先,文人之间的诗酒唱和展现了名士群体对生活中美的敏锐捕捉。如梅朗中行住坐卧,无不以诗为事。黄宗羲曾与其宿观音阁,“夜半鸟声聒耳,朗三推余起听曰:‘此非‘喧鸟覆春洲’乎?如此诗境,岂忍睡去!’薄暮,出步燕子矶,看渔舟集岸,斜阳挂网,别一境界。”㉜正如罗丹所言,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梅朗三因夜半鸟声,而发“喧鸟覆春洲”之叹,谢朓之诗融入生活,灵动亲切,诗人在美的面前的屏息亦让人动容。“渔舟集岸,斜阳挂网”之境宛然目前,让人不禁感叹美是生活,诗不远人。其次,名士之间的诗歌酬唱可探讨诗法,提高诗艺,深化友谊。如苏桓“其寿吾母四十岁诗,仿风雅体为之,甚美。”㉝夸赞苏桓诗歌体式之美。如林古度“余赠诗,有‘痛君旧恨犹然积,而我新冤那得平’。茂之读之流涕。”㉞以诗歌安慰友人,传递友谊。如陈玄素“余时作诗,颇喜李长吉,古白一见即切戒之,亦云益友。”㉟陈玄素的告诫,黄宗羲的益友之评,可见诗人酬唱间广泛涉猎、提高诗艺的自觉追求。最后,诗性乃心性也。通过诗歌,我们可以走进名士深邃隐秘的内心世界,还原面目各异的名士形象。如沈士柱录诗“鹦鹉金笼唤御名,贵妃亲教调郎情。即今苦雨凄风夜,却听鸺鹠四五声。”㊱诗歌从崇祯皇帝好鹦鹉这一细节入手,将“金笼鹦哥唤御名”与“鸺鹠四五声”对照,隐晦传达出诗人对大明王朝的眷恋。如麻三衡“多古诗,后死难,临刑赋诗:‘誓存千丈发,笑看百年头。’”㊲麻三衡长于武事,常以诗酒自豪。后因抗清被杀,临刑赋诗刻画了其为明效忠,慷慨赴死的英雄形象。
黄宗羲曾建立续钞堂,为著名藏书家。《思旧录》中存有不少黄宗羲与师友藏书访书的记载。如黄宗羲提及每至金陵,必借读千顷堂。如钱谦益约黄宗羲为老年读书伴侣,黄宗羲从而得以阅遍绛云楼藏书。如梅郎中“有言某家多古书,余与朗三往观,二更而返。”㊳黄宗羲与梅朗三为访古书,二更乃返,不分晨昏,好书成痴。书不仅是增长学问的阶梯,而且是升华友谊的媒介。如祁彪佳“入公书室,硃红小榻数十张,顿放书籍,每本皆有牙籤,风过铿然。公知余好书,以为佳否,余曰:‘此等书皆阊门市肆所有,腰缠数百金,便可一时暴富。唯夷度先生所积,真希世之宝也。’二冯别去,留余,夜深而散。”㊴祁彪佳藏书丰富,澹生堂名闻江左。祁彪佳以书之佳否询于黄宗羲,“唯夷度先生所积,真希世之宝也”的答语既是对祁氏藏书之精的肯定,又给予其父祁承爜恰到好处的恭维。“留余,夜深而散”透露了黄宗羲与祁彪佳因共同的藏书爱好而升华了友谊。
晚明时期,煮水品茗、斗墨游园、赏曲听琴皆成为文人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文震亨《香茗》云:“香茗之用,其利最溥。物外高隐,坐语道德,可以清心悦神。初阳薄暝,兴味萧骚,可以畅怀舒啸。晴窗榻帖,挥麈闲吟,篝灯夜读,可以远辟睡魔。青衣红袖,密语谈私,可以助情热意。坐雨闭窗,饭余散步,可以遣寂除烦。醉筵醒客,夜雨蓬窗,长啸空楼,冰弦戛指,可以佐欢解渴。”㊵晚明文人将日常饮茶审美化,营造清净恬淡的生活氛围,在精致的茶事中展现士人的超逸之品。如《思旧录》方震孺“时饮六安茶,香色俱佳,因曰:‘此乃真六安,彼暴烈日中者烹之,其色如卤,只堪屠沽饮耳。”㊶福王南京称帝,方震孺上疏勤王,为马士英、阮大铖所忌,放还寿州,死于忧愤。黄宗羲避开此等大事不谈,而独独拈出品茶之细节。六安瓜片汤色清亮,形如莲花,清香鲜醇。茶如隐逸,方震孺比照真假六安,摒弃屠沽之饮,展现了名士对闲适清雅审美之境的追求。有明一代,士人亦热衷于园林建造。如吴履震《五茸志逸》云:“近世士大夫解组之后,精神大半费于宅第园林,穷工极丽,不遗余力。”《思旧录》中亦留下名士经营园林的痕迹。如倪元璐“先生颇事园亭,以方、程墨调朱砂涂塈墙壁门窗。门生鲁元宠为徽州推官,多藏墨,先生索之。间数日,又索,元宠曰:‘先生染翰虽多,亦不应如是之速。’既而知之,以为吾所奉先生者,皆名品,不亦可惜乎!先生导于登三层楼,正对秦望,其两旁种竹千竿,磨有声。”㊷倪元璐书画皆精,黄宗羲此处透露他酷好园林建造的一面。以方程名墨于墙壁间题诗作画,种千竿翠竹于园林之中,倪元璐对园林设计的热衷令人咂舌,其精致风雅亦可见一斑。晚明人还爱好斗墨之戏,如朱荃宰“在留都,为斗墨之戏,皆方正邵格之罗小华名品,方程以下不论也。”㊸古人曾将佳墨比良马,墨作为文房四宝之一,不可或缺。徽墨乃墨之精华,明清时期趋于鼎盛,出现歙县与休宁两大墨派。歙县墨派以罗小华、方于鲁、程君房为代表,休宁墨派以邵格之、汪中山为代表。观朱荃宰把玩之墨,皆徽墨上品。佳墨落纸如漆,色泽黑润,清馨淡远,何尝不是文人坚韧高洁、沉稳厚重人格的写照。《思旧录》还长于在赏曲听琴中细叙友情,弘扬孝道。如董守谕“曾忆与之看戏,有演《寻亲记》者,哀动路人,次公指而谓曰:‘此钱美恭也。其父与此相类,顾忍而为此乎?’盖美恭父钱士鹔仕滇中不返,故次公言之。其后美恭决志入滇;而身无一钱,乃买鼓板一副,市镇之处度曲,卒迎父柩而返。”㊹黄宗羲回忆与董守谕同观《寻亲记》,引出友人钱美恭寻父之艰辛,在戏曲中弘扬孝道,净化人心。
朱光潜先生认为“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㊺,崇尚人生的艺术化。魏晋时期名士的人生艺术化形成中国思想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魏晋士人在清谈玄理时锤炼思维,彰显智慧,在人物品藻中观照自我,凸显“神”“情”,在酒酣中大胆喊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在服药后展现超然物外的魏晋风度。魏晋名士亦品诗论文、赏竹爱鹤、奏琴长啸,将日常生活审美化。晚明政局动荡,世态多变,与魏晋时势有相似之处。在王学的浸染中,晚明名士崇尚性灵,呼唤个性,追求自由。《思旧录》中的名士群体在明清鼎革的巨大时代变迁中,反思王学清谈误国,无善无恶,在最终价值取向上做出了坚定的选择,现实的残酷使得他们褪去了魏晋士人的旷达飘逸,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坚持。《思旧录》同时突破人物爵位行事的套路,将名士群体置于广阔的社会生活与日常行为中,以简净的散文笔法勾勒出名士的立体群像。他们亦在品藻人物、诗歌酬唱、藏书访书、煮水品茗、斗墨游园、赏曲听琴中暂离刀光剑影的庙堂,缓解心灵压抑的苦闷。然而,迥异于魏晋名士在饮酒长啸中对痛苦淋漓尽致的宣泄,晚明名士更多地将苦痛压抑,借助藏书、诗歌、园林、茶事、名墨等建筑人生的精神家园,完成对自我人格的超越。
三、《思旧录》中黄宗羲心态的嬗变
一种心态或曰时代精神,它以一群人甚至一个人为代表。《思旧录》展示了名士群体在明清鼎革之际的艰难选择,还原名士生活的真实场景,探索名士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意蕴,勾勒千姿百态的名士形象。在书写《思旧录》名士群体的同时,黄宗羲的心态亦经历了复杂微妙的嬗变。
首先是华靡背后的荒寒。晚明时期,世风奢靡,以华为美。如张岱《越俗扫墓》云:“越俗扫墓,男女炫服靓装,画船箫鼓,如杭州人游湖。厚人薄鬼,率以为常。……后渐华靡,虽监门小户男女,必用两坐船必巾,必鼓吹,必欢呼鬯饮。下午必就其路之所近,游庵堂寺院及士夫家花园。”㊻《思旧录》中描摹士人明亡前生活,尚奢靡,喜排场,再现末世繁华,在笔墨的逗留和物的铺排中传达出隐秘的眷恋。如陈继儒“侵晨,来见先生者,河下泊船数里。先生栉沐毕,次第见之,午设十余席,以款相知者,饭后,即书扇,亦不下数十柄,皆先生近诗。”㊼《思旧录》笔墨省净,此处却一反常态,将陈继儒一日生活细细铺展,再现这位“山中宰相”盛名下的繁华。如韩上桂“其在五羊,伶人习其填词,会名士呈技,珠钗翠钿,挂满台端,观者一赞,则伶人摘之而去。在旧院所作《相如记》,女优傅灵修为《文君取酒》一折,便赍百金。”㊽步入此境,不觉珠翠满眼,清曲满耳,韩上桂竟以钗钿换一赞,为《文君取酒》馈百金,华靡风流,照应一时。当《思旧录》笔触转入明亡后士人的生活,则褪去温暖,破败清寒,是其荒寒心态的流露。如徐枋“其苦节当世无两,谢绝往来,当道闻其名者,无从物色,馈遗一介不受,半菽不饱,以糠粒继之。其画神品,苏州好事者哀其穷困,月为一会,次第出银,买其画。以此度日而已。”㊾徐枋与沈寿民、巢鸣盛合称“海内三遗民”。黄宗羲透过俗世浮名,真实刻画了徐枋盛年不仕的坚守。以糠粒充饥,靠卖画度日,遗民的生活竟艰辛至此,与明亡前的珠翠环绕、欢声笑语形成鲜明的对照。如余增远“改革以后,居城南破屋,床头屋漏,则以鳖甲承之,担粪灌园,似老农家。”㊿余增远为崇祯十六年进士,官宝应知县。明清鼎革后,竟无钱修补漏屋。《论语》中樊迟问稼,孔子不屑,作为儒家门生的余增远却担粪灌园,似一老农,令人鼻酸。“荒寒”不仅指名士在明亡后生活来源的困窘、居住环境的萧索,更是指经历天崩地坼的亡国之痛后,明遗民埋藏心底的对时代甚至自身的整体荒谬感以及茕茕孑立深入骨髓的孤寒感。如巢明盛“鼎革不离墓舍,种匏瓜用以制器。香炉瓶盒之类,欵致精密,价等金玉,为《大匏赋》以见志。”《逍遥游》中惠子曾叹大瓠无用,巢鸣盛以匏制器,并为《大匏赋》,何尝不是内心荒寒的写照。
其次是逃禅与学隐的碰撞与融合。《思旧录》中记载了名士于明清鼎革之际的不同抉择,如朱朝瑛、陈确等选择学隐,方以智、林增智等则遁入空门。黄宗羲以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的人生轨迹为学隐做了完美的诠释。黄宗羲对逃禅则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如《七怪》将逃禅列为首位,“近年以来,士之志节者,多逃之释氏,盖强者销其耿耿,弱者泥水自蔽而已。……不欲为异姓之臣者,且甘心为异姓之子矣!……亡国之大夫,更欲求名于出世,则盗贼之归而已矣。”黄宗羲认为逃禅乃背儒之举,释氏将销磨强者志气,令其风节委地,其实质比出仕异姓更为严重。晚年黄宗羲在《思旧录》中则给予了逃禅者一份宽容。如章正宸“国亡遁去。骆宾王之遁于僧,名捕之也,羽侯无故而遁,加一等矣。”以章正宸比骆宾王,肯定无故而遁,欣赏其保全志节。又如江浩逃禅,法号义月,黄宗羲仍肯定其“读书略见大意,而胸怀洞达,无尘琐纤毫之累。”欣赏其胸襟与学问。再如阎尔梅逃禅,号蹈东和尚。“余游庐山,遇之,坐五老峰顶,限韵赋诗,月色侵人,三鼓始罢。古古言自华山游返。然观其山行甚艰,人言华险,游者望崖而返,若古古能游,则知余亦不难矣。”据《黄宗羲年谱》,黄宗羲游庐山,遇阎古古,当于五十一岁时。他不仅与阎尔梅同坐五老峰顶望月赋诗,而且细听其述华山游历之事,温馨友情在心中流淌。为什么晚年黄宗羲会对逃禅给予一份宽容?笔者认为,一方面友谊架起了逃禅与学隐的桥梁,黄宗羲虽师从蕺山,但兼收并蓄,交往中亦不乏方外之人;另一方面,阎尔梅、江浩等逃禅者在时光中磨砺自己,在禅门中坚守心性,淡化了逃禅的负面作用。
最后是对晚明“尚奇”趣味的发展。奇常与正相连,本为兵家语。刘勰《文心雕龙》将“奇正”引入文学理论批评,使之具有范畴论的意义。如《辨骚》云:“酌奇而不失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如《正纬》云:“经正纬奇”。如《知音》设六观,其四则为观奇正。晚明时期,“尚奇”成为时代审美风尚,奇服、奇人、奇事、奇言层出不穷。晚明士人以奇凸显自我,张扬个性,表现出对儒家文化的悖离。《思旧录》亦热衷于表现名士之奇行奇事。如方以智为黄宗羲切脉,由关下一尺取之,黄宗羲不觉叹息太过好奇。如钱谦益“是时道士施亮生作法事,烧纸,惟‘九十’二字不毁。公已八十有五,人言尚余五年,亦有言‘九十’乃‘卒’字之草也。未几果卒。”由烧纸推测钱谦益的寿数,充满了一种未知的神秘感与宿命感。如朱大典一节,对其书写只寥寥几笔,大量笔墨却集中在籍籍无名的金无錬身上,细致描绘他在清兵屠城时幸存下来的种种奇迹,此种喧宾夺主的写法实为黄宗羲好奇所致。黄宗羲对晚明“尚奇”趣味的发展在于以通神好梦之奇完成对儒家文化的回归。如孙嘉绩后附章钦臣之妻金夫人。“夫人强项不屈,问官始恐之以斩,再恐之以凌迟。夫人曰:‘吾岂怕凌迟者哉!’磔毕,而行刑者暴死。夫人遂成神,所谓大金娘娘也。余若水作传,其烈古今所仅见者。”颂扬大金夫人不畏凌迟,忠烈成神,以好奇的笔法表现出儒家忠义传统的回归。
要之,《思旧录》为晚年黄宗羲的重要著作,它对所录名士政治价值取向的标记,既展现了黄宗羲对气节操守的重视及自身遗民身份的认同,又以独特的方式诠释了黄宗羲以文补史的理念。同时,《思旧录》还将名士群体置于广阔的社会生活与日常行为中,再现明末清初名士群体诗意化的人生境界与审美风尚:品藻人物、诗歌酬唱、藏书访书、煮水品茗、斗墨游园、赏曲听琴。然而,晚明名士迥异于魏晋士人在饮酒长啸中对痛苦淋漓尽致的宣泄,更多地将苦痛压抑,借助藏书、诗歌、园林、茶事、名墨等建筑人生的精神家园,完成对自我人格的超越。另外,从《思旧录》中名士群体的书写,我们可窥探黄宗羲心态复杂微妙的嬗变:华靡背后的荒寒、逃禅与学隐的碰撞和融合、对晚明“尚奇”趣味的发展。
【作者单位:湖南文理学院(415000)】
①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01页。
②许慎《说文解字》,中国书店1989年版,第12页。
③④朱彬《礼记训纂》(上),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34-235、235页。
⑤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下),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743页。
⑥⑦⑧⑨⑩⑫⑬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㊶㊷
⑪钱基博《钱基博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页。
⑭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6页。
⑱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⑲章国锋《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解读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⑳刘悦笛《重建中国化的“生活美学”》,《光明日报》,2009年8月11日,第11版。
㉑宗白华《中国美学史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页。
㉚马美信《晚明小品精粹》,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2页。
㉛栾保群点校《琅嬛文集:张岱著作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57页。
㊵郭英德、王学太评释《艺事精品》,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183页。
㊺朱光潜《谈美文艺心理学》,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92页。
㊻张岱《陶庵梦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