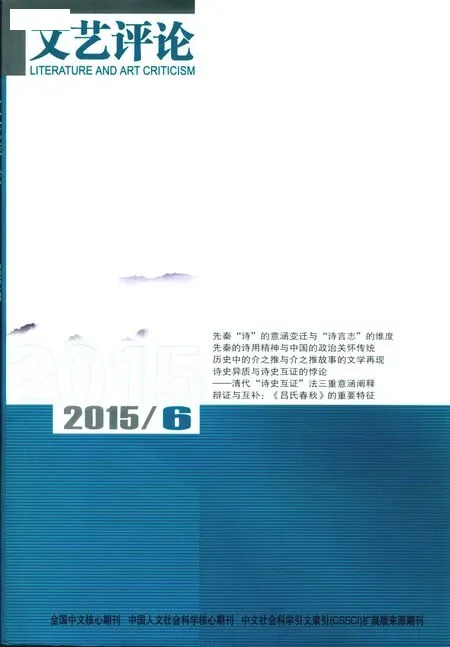中国古代知音现象研究
——以士人为中心
2015-09-29周钟
周钟
古代艺术理论与批评
中国古代知音现象研究
——以士人为中心
周钟
知音①,作为音乐生活中的一种特有现象,很早就被各类文献典籍注意到,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文字记载。虽然就其广义而论,涵盖一切音乐理解现象,但就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及相关文论而言,却主要指文人高士之间由乐而心的交互、印契,乐者与听者以相知故,彼此引为知音。这就是说,知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而是一种有着鲜明特征与特殊意义的高文化的以文人音乐家为主要参与者的交互主体性行为,这就是知音的专指范畴。对其进行专门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士人群体审美价值观及文化生活方式有着较大的意义。
一、立论的前提
音乐,本于人心。唯起心动念,方有指动、声起,音乐兴。关于此,《吕氏春秋》《乐记》《汉书·艺文志》《列子·汤问》等多有论述,后世朱长文《琴史》、李贽《焚书》等做了进一步发挥。嵇康虽造《声无哀乐论》,但未明确否定音乐生于人心。其《酒会诗》云:“但当体七弦,寄心在知己。”又“操缦清商,游心大象。倾昧修身,惠音遗响。钟期不存,我志谁赏。”可见其音乐中确有心志,并渴望知音的出现。由此可知,嵇康之论乃针砭时弊之说,不能作教条理解。现代以来,学界对音心关系的探讨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态势。上世纪上半叶,受西方浪漫主义美学观念影响,主观唯心主义初现;后来主客、心物二元思维流行,唯物唯心观点对立;近十年受西方现当代哲学思潮、中国传统思想复兴影响,视角、观点更加多样。笔者在广泛了解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较为赞同罗艺峰先生基于儒、佛心性思想的心本体论与音心不二论。《思想史、〈中庸〉与音乐美学的新进路》指出音乐本于心之寂然未发,归于心之寂静不动,以心为本。②《音心不二论——仿僧肇笔意》指出:“音心关系只能是‘不二’的关系,心不识音,则音不存。音不表心,则心不显。”③总的说来,就是音乐在乐者(本文代指从事演奏、演唱、作曲等活动的音乐创作者)为自心流露,在听者(本文代指音乐鉴赏者)是自心显现,音心不二,心为乐本。
正是这样一种立足中国古典哲学的音心论,为研究中国音乐哲学美学问题提供了一条可能的思路,并为解决某些西学视野下的音乐哲学历史难题提供了契机。即“在音乐哲学美学研究中,东方哲学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既应是研究对象,其本身也具有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也即,中国哲学可以作为一种研究视界、思维逻辑与学术范式进入我们的学术视野与文本写作。”④笔者尝试解读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知音现象,就是基于这样的立场,特别是借鉴禅宗中的“以心印心”模式来论析知音的发生原理、历史事例及其文化价值,并结合主体间性理论加以佐述。
二、知音现象的发生原理
由于音心本来不二,音乐发乎于心,并必然表现人心,知音现象就有了出现的可能性。在音乐创作表演中,若乐者心中有志,则音存其志,若此心合道,则音亦载道,而言志、载道、缘情正是中国文艺的基本特点。我们可将人心投射到音乐之中的这些意向性存在(以能量、信息的形式)称之为乐心,乐心源自人心,是人心的变现,其实就是音乐所传达的真正意义。听者听音乐,当然也是用心,否则有耳无心,人同木石。倘若听者修养与乐者相当,听时(此处指心、耳直观音乐时)蓦然心动,“透过音乐的现象把握住了音乐中的志”⑤,与乐心产生共振、共鸣乃至心意相通,源源不断地接受、领会、肯定并沉浸在这种意向性中,明白体会到了乐心,若合一契,则此乐心当下即是听者之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则知乐者之心。我们就称这种情况为以心印心,虽是先印乐心,但在印乐心的刹那其实已经印了人心,因为此乐心即乐者之心,两者是不二的关系。正如何艳珊所说:“在这个意义上,知音就是知心,就是知道音乐的表演者和创作者赋予音乐的内在心意。”⑥
印心之后或言之凿凿,心印语证;或妙不可言,彼此心领神会,产生默契。这是一种深度的主体交互性。这种奇妙而欢喜的感觉,正是“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⑦。你知道我,那我就知道了你能知我、已知我,我也知道了你。两个主体心心相印,彼此相知,贴然无间,成为知音。此后,听者与乐者之间很可能还会通过音乐交流,进一步发生情感激荡,相互印发,将音乐创作、表演、欣赏变成一种主体间的共同参与行为。
印心那一刻,听者之所以能蓦然心动、听懂乐者的音乐,如范晓峰先生在《音乐理解现象研究》中所说,是因为乐者的音乐语言唤醒了听者生活中某种经验,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关系质与主体间性。⑧而这种特殊的关系质与主体间性,就是心与心之间的感契印通,其中以音乐的意向性为心媒。由于知音现象中,听者对音乐意象的领会必须明确符合乐者的心,因此,知音行为的发生拒绝解释学的多元结论,这既是知音现象的特殊之处,也是其稀有可贵的原因。也就是说,知音现象虽让人向往,但可遇不可求,其发生有着严格的前提条件。刘勰《文心雕龙·知音》言:“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⑨虽然谈的是文学,但同样适用于音乐。从古代知音事例来看,只有当事人双方同时具有较高的道德修养,相近的性情志趣,且一般在非功利性的适宜的境况下相会,天地间两个孤独的个体才有可能碰撞出壮丽的生命火花。
印心之心,就是当事人的当下一念。恰似禅语“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因此,知音一事与禅宗所谓的直指人心、豁然贯通有相似之处。这是因为在古人的知音行为中,“音乐不是一个可供分析的‘技术产品’”⑩,这一心动而印的过程不同于思维逻辑,应主要是心的整体性的直觉与领悟,乃至心与心之间的自然吸引、契合,非常微妙。这时候若全以思想强会,则说明尚未印心,且容易造成一种知会的障碍。这是由于人在思维时心会变得紧张、分别、有所求,这样听者就与所听之乐、演乐之人形成了主客二元关系,因为主客二元,所以壁垒出现,无法圆合一体、交互交流、融会贯通。只有在心放松、自在、无所住时,才有可能与他者沟通自如。其辩证关系,恰似唐代法融禅师语:“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认为知音的发生对听者的音乐技艺不做必然要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不通音律也不妨碍能听懂,通音律也不一定就能听懂。或者说,听懂音乐与通音律没有必然联系,后者有时会有益于前者,有时会起反作用。至于听不懂音乐就被认为是不通音律的说法更不成立。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却是可能的。这是因为音乐中的意向性存在有时是不需懂得乐理乐法就可以直接把握到的,它直接出于人心,拟人心之态,直接呈现某些生活经验信息。而中国文人音乐往往更以得实忘荃为旨趣,追求超越象而达于道,即《列子·汤问》所说的“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声”⑪,何艳珊博士也指出:“古人所谓的‘知音’并不是在指‘通音律’,因为‘通音律’只是理解了音乐的现象,只是‘知声’。”⑫因此只要听者与乐者有相近的性情志向,乃至在道的层面相合,就有可能听懂。顾逢《无弦琴》云:“只须从意会,不必以声求”,弘一法师云:“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都是此意。借用《文心雕龙》的术语,知音属“妙鉴”,非“俗鉴”,听者在电光火石、以心印心的一刹那间,往往超越音乐形态分析之葛藤,直接观照、体会到音声中的情志,即“应该从最根本处着眼来理解音乐,而音乐的最根本处当然就是赋予了音乐以‘意义’的那个‘志’”⑬。
三、古代知音事例分析
知音现象,说到底就是知音主体之间的心灵感契,有时更会产生一种不随境迁的奇妙连结。这既是音乐的境界,也是人生的境界。从文献记载来看,中国古代知音行为大都非常高明,显示了双方精深的修养,也显示了乐者高超的音乐技能与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有些事例甚至让今人感到惊异,这是因为今人没有此类经验。笔者认为古今差异就在于古代人心质朴、情志纯粹,“思无邪”⑭,因此“古之音指盖淳静简略”⑮,于是如朱长文《琴史·钟子期》所言:“夫志有所存则见于音,君子知其音以逆其志则得焉。或识于斯须之间,或知于千载之下,合若符节。”⑯如今世道人心陷溺,“慆心堙耳,佐欢悦听”⑰,自然无复古人之澄心、明志与清听。
从形式来说,古代知音事例可分为明言与默契两种。
明言,即以心印心后有言语沟通。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吕氏春秋·本味》⑱与《列子·汤问》⑲所载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子期听琴知伯牙志在“高山”“流水”,这既是古代历史上较早的有明确记载的知音行为,也是最为完备、典型的知音现象。由于其境界之高、情义之深,因此后代多有用此典故以明志、寻知音者。
各类文献中有关孔子知音的记载很多,最让人惊异的莫过于《韩诗外传》所载的孔子学琴知文王⑳,其境地高妙,堪称精绝。孔子在自己操缦中会琴声之义,知文王之音,师襄子替文王验证,这是一种特殊的知音形态。又《列子·仲尼》载,颜回援琴而歌,孔子闻之召入,问:“若奚独乐?”回:“夫子奚独忧?”㉑可见师徒相知之深。颜回早逝,孔子非常伤心,这中间除了师生深情,应该还有知音相惜。此外,孔子的弟子曾子亦曾因梦作《残形操》而遇知其音者。
还有一些明言式的知音现象,多产生于特殊情形下,境界参差,又大都只着重于听者的知。如《吕氏春秋·精通》载钟子期夜闻击磬而悲㉒,《说苑·善说》载孟尝君听雍门子周鼓琴知亡国之殇㉓,《孔子家语·辩乐》载孔子从子路琴声中听出其不得善终的结局等㉔。这里有一个特例,就是司马相如以琴歌《凤求凰》向卓文君传情。朱长文《琴史·司马相如》认为司马相如以圣人之器做情挑之事,是玷辱了琴㉕。从官方传统文化的雅正性与文人士大夫的道德规范来看,这的确不是符合古代君子价值观的知音行为。
默契,即心照不宣,只意会,不言传。这种知音似乎更加高明,而其发生于魏晋时期也毫不意外。《世说新语·任诞》载桓子野善为王子猷吹笛三曲,客主不交一言,风度俨然㉖。为何不言?唯因心已相契,言为多余。桓虽身显贵,笛为知音者奏;王若拍手叫好,则大煞风景,枉费桓心。从二人表现来看,确为彼此知音。
白居易不少诗作中涉及了知音现象。在《琵琶行》中,诗人虽与琵琶女有所交流,但默契之味甚深。先是“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为第一次默契;“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是第二次默契;“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是第三次默契;“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是第四次默契;“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是第五次默契;“东船西舫悄无言,惟见江心秋月白”可谓描写知音默契的千古绝句,达到诗人与琵琶女默契之顶点。之后数句由默契而明言,至“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终归于默契。其他诗人诗作中也不乏有默契意味的知音诗。孟浩然《听郑五愔弹琴》云:“余意在山水,闻之谐夙心”,张祜《听岳州徐员外弹琴》云:“玉律潜符一古琴,哲人心见圣人心”,王昌龄《琴》:“仿佛弦指外,遂见初古人。意远风雪苦,时来江山春”皆同此趣。
细细品味,在默契中以心印心的意味似乎更加纯粹。这种心与心的直接契合、沟通、印证,与禅宗第一个公案“拈花微笑”颇有相似处——佛陀以拈花开示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其他人都没有领会,只有迦叶尊者破颜微笑,知其无言的法音。佛陀既没有明示,迦叶也没有直言,但双方却各自心领神会,心心相印。一刹那间,其内涵之丰富,常人无法想象。
知音的要义,在于印心,而之所以说知音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是一种高文化,就在于除了印人心,还有印天地之心、道心的情况。如常建《张山人弹琴》云:“朝从山口还,出岭闻清音。了然云霞气,照见天地心。”孟郊的《听琴》诗,则结合他多年学道的经历,感慨万分地咏道:“学道三十年,未免忧死生。闻弹一夜中,会尽天地情。”白居易《好听琴》之说流传更广:“本性好丝桐,尘机闻即空。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而钱起《省试湘灵鼓瑟》中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虽是诗人的文学想象,但也有一种非常独特的与天地相契的意象。
知音中印道心的情况还有三种特例。其一,是拥有众多后世知音的陶潜素琴实践㉗。其二,是听自然之声而印道心,如苏轼《庐山三诗》中的“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元结以水乐为“全声”㉘也有类似意味。其三,是通过先印道心来知琴心,其代表就是成连先生为伯牙移情的传说。据《乐府解题》等记载,成连“刺舡而去,旬时不返。伯牙近望无人,但闻海水洞滑崩澌之声,山林窅寞,群鸟悲号”㉙,终于感沧溟而领悟寂妙道心,从而理解了成连所传琴心。其奥妙正如李贽《焚书·征途与共后语》所言:“唯至于绝海之滨、空洞之野,渺无人迹,而后向之图谱无存,指授无所,硕师无见,凡昔之一切可得而传者今皆不可复得矣,故乃自得之也。”㉚
四、知音与文人音乐家艺术生命价值的实现
知音是宇宙间两个寂寞心灵的接通与共振。以心会心、以心印心,进而心心相印、惺惺相惜。知音主体通过音乐活动来实现“鉴人”的目的。人生而孤至,死亦孤往。若一生无人相知,更堪悲凉寂寥。而一旦遇到知音,生命便因不孤单而有了一种特殊的光彩与价值,知音而后已,文人音乐家艺术生命价值的实现就在于幸逢知音。
(一)知音之于乐者
知音是对他者的认同,对他者的认同也就是对自我的认同。因此,寻觅知音是古代文人音乐家的一种自我认同的文化心理。而音乐创作、表演的重要目的之一,就在于向听者倾诉,与听者交流,在于期待知音,寻求共鸣。这里出现的反比关系是,人生修养、音乐境界越高,知音越少,愈是阳春白雪,愈是曲高和寡。知音就是缘分,古来圣贤寂寞,高情巨眼毕竟稀有。因此,越是英雄,越是孤独,越缺少认同,正如陈子昂在《登幽州台歌》中的慨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也正因此,一旦见古人、迎来者、遇知音,“于我心有戚戚焉”㉛,则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
知音之幸,也就是知音其难。历史上有知音的故事,也就有似是而非的逆缘。《论语·宪问》所载荷蒉者听孔子击磬曰鄙㉜,毛奇龄《竟山乐录》所载蔡子庄听琴按拍㉝等事例皆属此类。因此,音乐生活的大多数情形中并没有发生知音,而是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所说:“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㉞因此,知音虽妙,却不可强求,也强求不来。也就是说,知知音之理,不必一定有知音其事,得之与否,顺其自然。若得遇知者,实是一桩幸事,故晏殊《山亭柳》云:“若有知音见采,不辞遍唱阳春”。而最具代表性和震撼力的事例还是伯牙摔琴谢知音。
《吕氏春秋·本味篇》载:“钟子期死,伯牙摔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㉟古代话本作家们用文学想象还原了当时的情形,并借伯牙口吟出了“此曲终兮不复弹,三尺瑶琴为君死”,“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㊱等名句。其诗虽为杜撰,但很好地表达了知音对音乐家艺术生命的重要性与知音主体之间的生命张力。也就是说,正是知音子期的出现,才使伯牙的音乐获得了交互主体性与互文性的价值,伯牙的艺术生命才实现了被他者的肯定。也只有在主体间性中,音乐才能实现它的全部价值。子期死后,伯牙用终结自身艺术生命来报答知音,感谢知音。这是因为在钟子期说出“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㊲之时,伯牙艺术生命的价值已经达到了顶峰。所以,士为知己者死,音乐也可为知音者死,死而无憾。这才是艺术生命本有的力度。从此也可看出,“历史上每段知音的往事,总是含有一份悲情。”㊳相遇就意味着别离,相知就意味着思念,它是同情体验与孤独体验的结合。㊴
(二)知音之于听者
文人音乐家艺术生命价值的实现就在于幸逢知音,这里音乐家的所指既包括作曲家、演奏家、演唱家,也包括音乐鉴赏家。因此,伯牙遇到钟子期是幸运的,钟子期遇到伯牙也是幸运的。李白虽叹“钟期久已没,世上无知音”(《月夜听卢子顺弹琴》),薛涛却说“借问人间愁寂意,伯牙绝弦已无声”(《寄张元夫》)。没有钟子期,伯牙的琴声是寂寞的,但钟子期也需要伯牙。或者说,听者逢其知音,听到与之心意相通的音乐同样是难且珍贵的。
鉴赏者寻觅知音之难,古已有之。由于文士饱读诗书,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与古圣贤者通,对于他们而言,总能敏锐地意识到乐道之衰,今不如古,遗憾今人好新声之奇巧浅俗,忘古声之质朴深雅,因此他们也就倍感孤独,“高处不胜寒”。白居易《问杨琼》云:“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唯唱声。欲说向君君不会,试将此语问杨琼”。《五弦》云:“嗟嗟俗人耳,好今不好古。所以绿窗琴,日日生尘土”。苏轼《舟中听大人弹琴》云:“世人不容独反古,强以新曲求铿锵。……无情枯木今尚尔,何况古意堕渺茫”。范仲淹《听真上人琴歌》云:“伏牺归天息千古,我闻遗音泪如雨。嗟嗟不及郑卫儿,北里南邻竞歌舞。竞歌舞,何时休,师襄堂上心悠悠”。刘长卿《听弹琴》云:“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吴筠《听尹炼师弹琴》云:“代乏识微者,幽音谁与论”。徐上瀛在《溪山琴况》“古”况中也指出:“琴固有时古之辨矣!大都声争而媚耳者,吾知其时也;音淡而会心者,吾知其古也”㊵。
在这些文人音乐鉴赏家们看来,音乐不古在于乐心不古,乐心不古在于人心不古,即新声丧失了古乐中的圣贤君子之心。音乐中无心可印,自然没有知音。古代文人音乐家们往往既是鉴赏家又是演奏家,没有知音,只好以自知为乐。此间以白居易最有代表性,他曾尝试“不辞为君弹”,无奈“纵弹人不听”(《废琴》),于是干脆不要人听,自己做琴的知音。《夜琴》云:“自弄还自罢,亦不要人听”,《对琴待月》:“共琴为老伴,与月有秋期”,《船夜援琴》云:“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但他毕竟还是渴望知音的,不能识于斯须之间,只好超越时空的界限,知于千载之下,会古人之心。《对琴酒》云:“只应康与籍,及我三心知”只是嵇康与阮籍毕竟不在身边,前人不知其知,后人也知其不知,因此这种古今知音有一种悲凉与无奈的意味,因其知,更显其寂。无独有偶,朱长文在《琴史·论音》中也说:“安得夔、旷之徒与之论至音哉!”㊶
正是因为时代风气的变迁,文人音乐鉴赏家们的知音越来越少。而与此同时,由于参禅修道与上古君子希圣希贤有极大的相同处,禅道与琴道也颇为相通,僧人道士音乐家却成为了他们主要的知音益友。许多禅师道士品行高尚、修养精深,一旦操琴,自然韵致高妙、不同凡响。李白《听蜀僧濬弹琴》云:“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馀响入霜钟。”吴筠《听尹炼师弹琴》云:“在山峻峰峙,在水洪涛奔。都忘迩城阙,但觉清心魂。”范仲淹《听真上人琴歌》云:“上人一叩朱丝绳,万籁不起秋光凝。……为予再奏南风诗,神人和畅舜无为。为予试弹广陵散,鬼物悲哀晋方乱。乃知圣人情虑深,将治四海先治琴。兴亡哀乐不我遁,坐中可见天下心。”可以说,文人音乐鉴赏家们引僧道为知音,正反映了士人、僧道间特殊的主体间性。高文化的知音现象主要就在这两个群体中延续至今。而今天,由于传统文化、传统文士、传统僧道的式微,且职业音乐家不断走向工具理性、技术主义,其美学趣味不断西化,因此传统意义上的知音现象的发生就更加困难和稀少了。
【作者单位: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210013)】
①文学也有知音的概念,本文主要指音乐范畴内的知音。
②罗艺峰《思想史、〈中庸〉与音乐美学的新进路》,《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4年第1期。
③罗艺峰《音心不二论——仿僧肇笔意》,《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④周钟《近三十年我国佛教音乐哲学研究述评》,《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4年第3期。
⑤⑥⑩⑫⑬何艳珊《高山流水论“知音”——谈古代的音乐理解问题》,《艺术评论》,2012年第10期。
⑦⑨㉞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39、435、437页。
⑧范晓峰《音乐理解现象研究》,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53-75页。
⑪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㉗㉘㉙㉚㉟㊲㊵㊶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增订版),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版,第502、51、654、654、654、223、505、232、506、223、371、536-543、559、552、708、223、223、744、655页。
㉕朱长文《琴史》,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5页。
㉖柳士镇《世说新语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14页。
㉛㉜《诸子集成》第一册,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364、247页。
㉝毛奇龄《竟山乐录》卷四,《丛书集成》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89页。
㊱冯梦龙《警世通言》,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㊳张文浩《声气相求者谓之知音——〈文心雕龙〉“觇文见心”说》,《殷都学刊》,2008第3期。
㊴陈迪泳、梁桂华《“知音”中的同情体验与孤独体验——〈文心雕龙〉鉴赏批评论的美学生命探微》,《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10第2期。
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编号:KYZZ027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