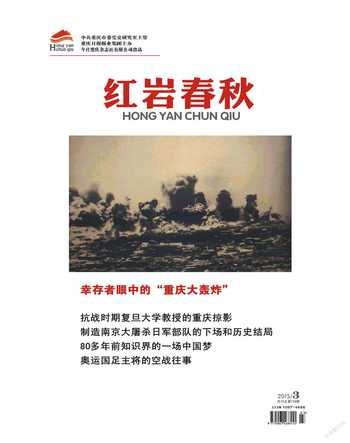上山放牛
2015-09-10朱芸锋
朱芸锋
难得的冬日暖阳,懒洋洋地铺在身上。枕着的草地,间或还有些松针,散发出松油香。三五头牛儿,啃吃青草的声音,顺风飘了过来,一切都那么自然,那么安详。
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小时候最好的时光。每天下午放学回家,匆忙吃过晚饭,小伙伴们都会牵着自家牛儿,上山放牛。呼朋引伴,一个院子、两个院子相互串联,长长的队伍很是庞大,好不热闹。
然而放牛并非字面上那么简单。去年春节,女儿和我一同回老家,看见一头黄牛拴在树边吃草,我便对女儿说:“要不,你去放牛吧?”于是,她把拴着的牛绳子解了放开。这就是她理解的“放牛”的方式,令人忍俊不禁。
醉翁之意不在酒,放牛娃的心思往往也不在牛。一旦将牛牵到山林,任其自由觅草的时候,放牛娃的疯耍时间也就到了。
初冬的山野满眼萧索,在放牛娃们看来却是另一番丰收。三三两两碰头之后,一拨人赶紧四处找干柴禾;另一拨人,则跑到还没有收挖回去的红苕地,干脆利索地将又红又大的红苕一个又一个地刨出。这边的火苗刚刚窜起,挖红苕的人马也就兔子般飞奔回来,上气不接下气,小脸涨得通红也顾不上休息,赶紧将红苕埋进火堆。
马蹬坝是一个四面环山、中间平坝的好地方。从山外吹来的初冬冷风,连打个旋儿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欢腾着的火苗和同样欢腾着的嬉闹,挤得影儿都没有了。放牛之余,小伙伴们就在“哔啵”作响的柴火声中,等待火堆中的红苕烤熟。
移开火堆、扒开柴灰,围拢成一圈的那些脑袋上生动各异的表情,多次在我的梦里浮现。那时的农村,早已远离吃不饱饭的年代,但是不管在家里吃得多么饱,也不管家里的饭菜多么香甜,让这帮放牛娃乐此不疲的,仍是山坡上、野火边、被弄得不伦不类的所谓“野炊”。平淡无奇的红苕,竟然也成为了放牛娃们争相享用的“野炊”美食。
只要有火,就可以烤红苕,还有洋芋、核桃、地瓜,甚至揉成坨的米饭、豆腐。我们还学着小学课本中《森林的主人》描写的那样,用大张的树叶裹着蘑菇、茄子,埋在火堆下烤熟。谁要是再勇敢一点,躲过父母的盘查,偷偷摸摸从家里带出来一口铜罐,那就更会被小伙伴们称赞了。有了铜罐就可以煮汤,配搭带着腊猪肉的油香、泛着糯米亮光的猪肉糯米饭,这就是齐心协力“野炊”成果中的经典之作。
等到品尝成果的时候,却经常落得匆匆收场。有时牛儿跑远了,要去寻找、追回来;有时放哨的跑过来,说某某的爸爸上山来了,大家马上手忙脚乱将火堆熄灭,作鸟兽散;有时,柴禾齐备、瓜果到场,却发现没有带火柴——索然无味地生吞活剥之后,放牛娃的“野炊”只得草草收场。
“野炊”也讲究规则,放牛娃们每次山上开伙都约定俗成,每个人不仅要出力,还必须都得分享“成果”。记得有一次,一个小伙伴到了山上却死活不愿参与,理由是大家要去他奶奶家地里刨红苕。然而当糊里带香的红苕烤熟了,铜罐里清汤寡水豌豆尖也烫熟了,这个小伙伴还是没能逃脱掉——大伙儿一哄而上将他按倒在地,4个人压住手脚,2个人掰开嘴巴,硬生生地给他灌了一通热气腾腾的豌豆尖汤进去。
放牛娃们当年的这些荒唐行为,如今还经常被自己津津乐道。我们甚至都得意地以为,当年即便这么淘气,但因为严格的“保密措施”,一直都没有被哪位家长知道。直到某年回老家过年,一位白胡子大爷拉着我说:“你就是春生吧?你的小孩都这么高啦?你还记得不,你小时候和小洪上山放牛,你们煮铜罐,非要他吃那么烫的豌豆尖,把他嘴皮都烫起亮泡?”
我们煞费苦心隐藏了这么多年的秘密,原来他们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