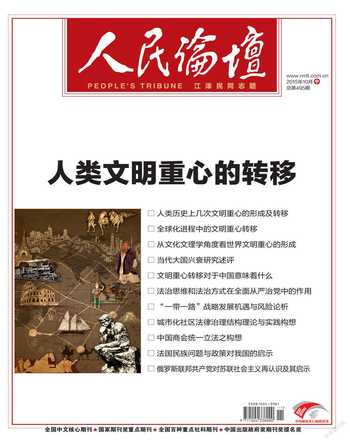葛兰西领导权理论分析
2015-09-10高卫民
【摘要】葛兰西在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探索中,指出发达国家是一种新型总体性国家,并强调了市民社会国家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是对马克思自主性国家观的继承和发展,对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 葛兰西 领导权 国家自主性 政治认同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国家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强大生命力,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指南。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是在现代民族国家成长新阶段对马克思国家理论尤其是自主性国家观的继承和发展,对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借鉴意义。
现代化国家会日益成长为一种总体性国家
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从封建或部落的、分裂或割据的、殖民或半殖民的社会通过中央集权走向主权国家的过程,也是自主性国家构建和成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国家自主性的有无或多少都直接决定着现代国家建构和成长的成败。根据葛兰西领导权理论对马克思自主性国家观继承和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线索,对比分析不同成长阶段的国家领导权及其自主性,探寻现代民族国家构建、成长和治理中的国家自主性表现,可以为后发国家国家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现代民族国家从统治走向治理,国家要从传统的政治国家发展成为葛兰西所说的总体性国家。葛兰西在领导和探索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中,敏锐地感受到传统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区别。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但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相继失败,落后俄国的十月革命反而成功。葛兰西对此矛盾现象进行了反思:“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在西方,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得当,国家一旦动摇,稳定的市民社会结构立即就会显露。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其背后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①通过比较分析,葛兰西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成长为新型总体性国家:“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言之,国家是受强制盔甲保护的领导权。”②政治社会包括行政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传统暴力国家机器,行使强制或镇压功能;市民社会包括教会、工会、学校、政党、家庭等各种组织和团体,行使政治认同或同意功能。葛兰西认为,一方面,十月革命胜利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更多的是能动革命精神的创造,第二国际“机械论和宿命论的经济主义”即庸俗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是错误的;另一方面,简单的暴力革命的苏俄模式不能在西方照搬,发达的总体性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不再是简单的以暴制暴的运动战,首先要加上一场必要的、艰巨得多的市民社会领导权争夺的阵地战,这就为陷入低潮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找到了一条新的革命道路。葛兰西还预计,未来国家的发展趋势是政治社会国家的强制作用日益减弱而市民社会的自愿认同作用日益加强,直到传统的政治社会国家逐渐消失而最终融汇于市民社会国家之中,这与马克思预计的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国家消亡的趋势是一致的。
葛兰西针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欧洲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背景特别提出了文化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但是他在不同场合也强调了政治和经济领导权的重要性,因而葛兰西的领导权是一种总体性的领导权。他认为自己的领导权思想受列宁的政治领导权思想启发,认为列宁在通过暴力革命取得国家政权的建国时期的政治领导权是一种必要的“无产阶级必须在过渡时期依靠政权来改造市民社会”的“中央集权”现象③,并高度称赞其成功和重要性,认为它是对庸俗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的有力批判,彰显了上层建筑国家及其政治领导权的自主性。葛兰西同时也注意到了列宁所实施的新经济政策中的国家经济领导权中的国家自主性,另外他特别批判了西方“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虚幻,揭示了西方国家经济领导权中的国家自主性:“实际上,由于市民社会和国家同为一物,必须搞清laisse-faire(自由主义、放任)也是国家‘干预’的一种形式,通过法律措施和强制手段引进和维持。这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政策,明确自身的目的,不是经济事实的自发和自主的体现。因此放任的自由主义是一个政治纲领……”④所以,现代民族国家的领导权是总体性存在的,国家会在不同的成长阶段自主、辩证地侧重实施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领导权。葛兰西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特别强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内、当时语境下彰显发达国家阶段国家领导权的特点。
现代化总体性国家的总体性领导权与国家自主性
现代民族国家自主性法理上源于国家主权。国家自主性是指国家有能力界定和追求自己的目标并达到其期望的效果,而这一目标又不仅仅是由私人社会利益(尤其是经济力量)为国家所界定的⑤。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所说的传统上层建筑领域的“观念的上层建筑”与新兴市民社会特定的组织机构相结合而物质化为一种新型的市民社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国家由此而成为现代化总体性国家。这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已经不是传统、消极和简单的观念意义上“副现象”和“虚假意识”,而是一种政治社会国家通过市民社会国家共同协调行使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主动、自主的政治实践,目的是获得民众对国家的自愿的政治认同或同意。众所周知,阶级斗争特别激烈时代的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主要是一种工具性国家观,国家被社会经济实力如马克思强调的资产阶级所俘获,成为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工具;但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自主性国家观的开创者,他们强调国家对阶级冲突的调节、对经济发展、社会秩序维护和民众精神素质提高等公共职能的行使。比如,他们用“波拿巴主义”来描述了他那个时代法国和德国的国家自主性现象,“……波拿巴式的半专政就成了正常的形式;这种专政维护资产阶级的巨大的物质利益,甚至达到违反资产阶级的意志的程度,但是,它不让资产阶级亲自参加统治”⑥。当时的“俾斯麦国家的新的德意志帝国”也是这样一种自主性国家:“那时互相斗争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相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⑦正是这样的波拿巴国家促进了当时法德两国经济突飞猛进。波拿巴主义的国家自主性现象在多铎王朝及其以后一段时期的英国(后来资产阶级过于强大使英国曾一度变成马克思所说的典型的工具性国家)、“美国体系”建构时代的美国、后来的传统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国家、当今后发国家中的“发展型国家”或“凝聚性资本主义国家”等国家形态中似乎都以不同的方式广泛存在⑧。实际上,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初期,都有一个确立中央集权和国家自主性的阶段,这一点东西方概莫能外,“权威的合理化和权力的集中,不仅对于统一是必要的,而且对于进步也是必要的。权力的集中对于铲除旧秩序,摧毁封建特权和封建束缚,并为新社会集团的崛起和新的经济活动的发展都是必要的。”⑨对于早发达国家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历史,由于洛克以及后来的休谟和亚当·斯密等英国思想家过分强调社会和市场的作用,且形塑了西方社会科学的古典自由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此语境里从此国家就成为一个被掩蔽的主题,人们尤其忽视了国家在英美等国家早期现代化及其殖民扩张中的国家领导权及其自主性。
如果上述时期国家自主性是侧重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初期国家对经济生产领域的干预,那么后来国家自主性对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分配领域的干预就导致了当今西方民主国家中福利国家或民生国家的产生。因为在当代西方一个凌驾于资本主义经济之上的民主国家内,国家管理者占据了一定的制度性位置,受到了组织性的动机激励,可能会具有相对于资产阶级的“相对自主性”。政府在政治体系中的组织性位置使政府具有高于一般资本家的广阔视野,以及抵制个别商业部门压力的能力。⑩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正是就此在当代语境下重申了马克思自主性国家观:“国家总的说来只是统治阶级的一种简单工具这一甚至整个错误的概念,对于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是毫无用处的。”“国家诚然是一个阶级的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但是,当它作为一个阶级的国家而行动时拥有高度的自主和独立,而且,如果它是要作为一个阶级的国家而行动的话,必须真正拥有这种高度的自主和独立。”
在法德民族国家建构初期,马克思经验性地描述了其政治社会国家如何自主促进经济发展,在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发达阶段,葛兰西则主要探索了市民社会国家如何自主行使意识形态领导权,是国家成长新阶段对马克思国家理论尤其是自主性国家观的继承与发展。而且,在葛兰西眼里,列宁的政治领导权就是西方已经进入发达国家阶段时期,后发的国家如俄国才刚刚建立自己的现代民族国家政权时刻的国家自主性行为。正是受葛兰西强调的市民社会国家领导权的自主性的启发,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波朗查斯才明确提出“国家(相对)自主性”的概念,该概念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回归国家”等学派的重要分析工具,使马克思自主性国家观在当代得以继续发展而成为一种批判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尤其是新(古典)自由主义国家理论的国家自主性理论体系。中国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后发国家,当今社会主义建设是一种典型的国家主导型模式,具有高度国家自主性,从四个现代化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是国家主导提出和推动实施的奋斗目标。
对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农民政治认同问题启示
葛兰西从实际出发探索西方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革命道路,提出了总体性国家及其领导权理论,批判了庸俗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简单的国家阶级工具论和简单的暴力国家论,是对马克思国家理论尤其是自主性国家观的继承和发展,其理论具有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品格。葛兰西时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领导权和经济领导权建设已经相当成熟且步入常规,成为了他重点探索的市民社会国家领导权及其自主性的引而不发的理论和实践前提。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角度看,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总体性国家的总体性领导权和总体性的国家自主性理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成长具有一般性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对刚刚从落后国家行列走出、处于正在向新一轮现代化进军、日渐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一种后发国家的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产物,首先依靠类似于苏俄十月革命的运动战模式获得革命的成功,建立了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国家,然后依靠国家法律、政策和执政党的纪律来整合社会,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和文化,实现了党和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中的强有力的领导。由于中国是一个从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开始构建自己的现代民族国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共和国构建和成长的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可以说农民的政治认同与否决定了这个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命运,这可谓现代民族国家现代化历史中独一无二的最大特色,这一点在新中国政权的获得与稳固、国家经济发展的探索中得到了证实。新中国政权建立和巩固后,“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国家的根本任务就是领导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实践证明,农民政治认同度是国家领导权运行的晴雨表。农民的政治认同程度高的时期,国家领导权就是健康运行时期,否则,就是需要反思和吸取教训的时期。当今我国农民的政治认同有弱化的趋势,基层涉农的群体事件频发,农民用他们的行动来表达对国家治理中一些现象的不满,预示着国家领导权根据现代化的新趋势有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必要。在国家自主性与农民政治认同这一矛盾中,国家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占据主导性位置。但随着基层民主治理的发展,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了变化:在建国初期,国家更多的是靠传统统治型的政治的、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甚至武力的等多种强制性的方式对农民的政治认同进行型塑,但随着国家从统治向治理转型,现代化国家成长过程中政治生活更加民主,农民日常小康生活更加自由,国家对农民政治认同的传统单向度的灌输和压制方法效果越来越值得怀疑;通过提高执政党执政的理论与实践水平,国家通过与农民双向度的平等地协商、交流或沟通的现代化的治理方式来引导和获得农民政治认同的葛兰西式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方式越来越受到重视和推崇,这是一种村民自治的民主治理时代国家试图通过基层社会自治行使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新方法,是一种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嵌入式”的国家自主性的表现。
农民的政治认同问题研究的关键实际上是一个国家领导权问题,是一个如何正确与合理发挥国家自主性、妥当处理好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国家领导权问题,运用制度分析的方法对国家如何自主型塑农民政治认同的制度变迁进行分析很有必要。制度分析研究的对象重点是国家这个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及其自主性、以及其与基层农村社会制度之间的统治和治理关系的变迁,制度分析的方法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传统宏观的制度分析框架为根本和基础,同时结合中观的历史制度主义和微观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等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通过以上制度分析,进一步挖掘和发展马克思自主性国家观并使其体系化,把它用来分析中国基层民主治理中国家领导权主导下的农民政治认同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作为探讨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视角。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层民主治理中农民政治认同的制度分析”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2BZZ003)
【注释】
①④[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94页,第123页。
②[意]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22页。
③[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2页。
⑤[美]卡波拉索,莱文:《政治经济学理论》,刘骥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1~24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09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72页。
⑧高卫民:“国家自主性:认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范式’”,《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3期。
⑨[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114页。
⑩[美]霍尔:《驾驭经济:英国与法国国家干预的政治学》,刘骥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22页。
[希腊]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85页。
[英]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79页。
责编 /于岩(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