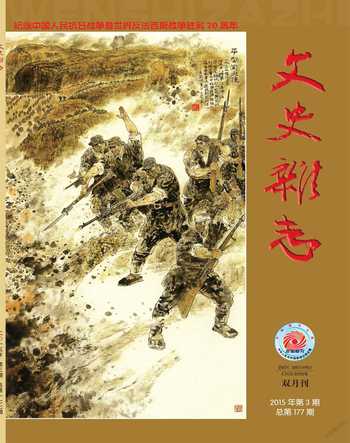话说“涩体”及其他
2015-09-10陶易
陶易
一
在唐代武则天至中宗时期,有位兼任过昭文馆学士的徐彦伯。《旧唐书》本传说他少以文章擅名,文辞雅美,但是“自晚年属文,好为强涩之体,颇为后进所效焉。”据《泔珠集》卷三引《朝野佥载》记载,徐彦伯为文,多好变异文辞以求新奇,他把“凤阁”称作“鶠阁”,“龙门”称作“虬户”,“金谷”称作“铣溪”,“玉山”称作“琼岳”,“刍狗”称作“卉犬”,“竹马”称作“篠骖”,“月兔”称作“魄兔”,“风牛”称作“飚犊”;后进之辈多仿效之,谓之“涩体”。其实就是改用另一种新异说法代替通俗说法,有意造成词语的艰涩难读,以显示其博学古雅。这种标新立异的遣词方法,其实只是“以艰深文浅易”,纯属一种不良文风。
玄宗朝的名相张九龄也曾用涩体调侃学问不高的萧炅。张九龄送了一篮子芋头给萧炅,附言上写明“蹲鸱”若干。萧炅回信说:“损芋拜嘉,唯蹲鸱未至耳。然仆家多怪,亦不愿见此恶鸟也。”张九龄拿着萧炅的回信给众人看,满座大笑。(《唐人轶事汇编》卷十一“萧炅”条)“蹲鸱”一词出自 《史记·货殖列传》,张守节《正义》曰:“蹲鸱,芋也。”因为大芋头形状如蹲伏的鸱鸟(猫头鹰)。萧炅不知“蹲鸱”的出典,把芋头当成了鸱鸮,招致他人嘲笑。其实这不能责怪萧炅不学,谁能都记住古书中那些生僻的典故呢?德宗、宪宗朝的宰相郑馀庆也好用古语,《新唐书》本传云:“其奏议类用古言,如‘仰给县官’、‘马万蹄’,有司不晓何等语,人訾其不识时。”李肇《唐国史补》说:“元和之风尚怪”,当时的韩孟诗派,以及李贺的乐府诗,樊宗师的古文,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涩体”的影响。
“涩体”在两宋时期也不乏仿效者,北宋的“太学体”就以文辞新奇晦涩为特色。又如宋祁重撰《新唐书》,往往把《旧唐书》中的俗语、口语换成雅言,不仅失去了人物原本的精神风貌,有时还把文句改得艰涩难读。清代赵翼《陔馀丛考》卷十一说《新唐书》“造语用字尤多新奇者”,“此皆极意避俗,戛戛独创者,未免好奇之过”。例如其《裴矩传》酒池肉林作“池酒林胾”,《张说传》避暑作“逭暑”。《旧唐书·李正己传》云:“回纥尿液俱下”,《新唐书》改作“矢液流离”。宋人祝穆在《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五“文不必换字”条说:宋祁修《唐史》,好以艰深之辞文浅易之说,欧阳修诗有意讽之,一日大书其壁曰:“宵梦匪祯,札闼洪休”,宋祁见之曰:“非‘夜梦不祥,题门大吉’耶?何必求异如此。”欧公曰:“《李靖传》云‘震雷无暇掩聪’,亦是此类也。”宋公惭而退。按《旧唐书》原作“疾雷不及掩耳”,《新唐书》先改作“震雷无暇掩聪”,后再改为“震霆不及塞耳”,但还是不及原文通俗。清四库馆臣论《新唐书》“文省于旧”之失曰:“唐代词章,体皆详赡。今必欲减其文句,势必变为涩体而至于诘屈。”(《四库提要》卷四十六“正史类二”)
阮葵生《茶馀客话》卷十“文章好奇之弊”条引明末散文家艾南英的话说:“近人作文,好以今字易古字,云出自某书;以奇语易平语,云本自某人。论道理则初无深味,徒令读者缩脚停声,多少不自在。”可见直到明清,一些文人依然好用涩体行文。清初户部左侍郎田雯读书作文好抉拾字句,被讥为饾饤,他却认为奇字是古人所常用,在古诗尤为合适。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田雯致仕归乡,卧病在床,医生所开药方中都是寻常药名,他因此拒绝服药,医生知其所好,就更名不换药,改枸杞为天精,人参为地精,木香为东华童子,并用上等的宣纸开处方。田雯见之大喜,于是乃服药。真是癖好新异,老而愈怪。
二
宋代一些文人还喜好用古人名指代某种事物,如以“刘白堕”指代酒,以“右军”指代鹅等等。《梦溪笔谈》卷二十三“讥谑”类云:“吴人多谓梅子为‘曹公’,以其尝望梅止渴也。又谓鹅为‘右军’,以其好养鹅也。有一士人遗人醋梅与燖鹅,作书云:醋浸曹公一甏,汤燖右军两只,聊备一馔。”又据庄绰《鸡肋编》卷上说:因为王羲之好鹅,曹孟德有梅林救渴之事,因而俗子乃呼鹅为“右军”,梅为“曹公”;并引张元裕说,友人邓雍曾用请柬招他赴宴,柬上写着“今日偶有惠左军者,已令具面,幸过此同享。”张元裕不知“左军”为何物?赴约后才知是鸭子,遂问其得名缘故。邓雍说:“鸭居鹅之下,鹅为右军,鸭自然是左军了。”还说淮西一带都用左军代指鸭子。张元裕讥讽说,俗称老丈人为泰山,遂有人称岳母为泰水,这正好与称鸭为左军配对。
王楙《野客丛书》卷六载宋祁曰:“古人语有椎拙不可掩者,《乐府》曰‘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乐天诗‘杜康能解闷’,潘佑诗‘直拟将心付杜康’,盖祖此意。文士有因其人名遂为事用者,如东坡诗‘独对红蕖倾白堕’,按《洛阳伽蓝记》‘白堕春醪’,自是造酒者,江东人姓刘名白堕。或谓因其能造酒,遂为酒名。”陶宗仪《说郛》卷三十四记载了张耒与苏轼之间的一段对话。张耒有诗曰:“天边赵盾益可畏,水底右军方熟眠”,苏轼说是“汤燖了王羲之也”。张耒戏对苏轼说:“公有‘独对红蕖倾白堕’,不知白堕是何物?”苏轼云:“刘白堕善酿酒,出《洛阳伽蓝记》。”张耒曰:“白堕既是一人,莫难为倾否?”苏轼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杜康亦是酿酒人名也。”张耒曰:“毕竟用的不当。”苏轼笑曰:“公且先去共曹家那汉理会,却来此间斯魔。”阮阅《诗话总龟》记载,张耒作《大旱诗》云:“天边赵盾益可畏,水底武侯方醉眠。”时人以为近乎“汤燖右军”。赵盾是春秋时晋国上卿,赵衰之子。《左传》载赵氏父子为政一温和,一酷烈,赵衰如冬日之阳,赵盾如夏日之阳。张耒就以赵盾作“日头”的代称。诸葛亮人称卧龙先生,张耒用作“龙”的代称。可见苏门师徒亦未能免俗。
清初褚人获《坚瓠乙集》卷三引明代庄昶诗云:“赠我一壶陶靖节,还他两首邵尧夫。”“靖节先生”是朋友给陶渊明的私谥,陶公好酒著名,既然造酒的可用来指代酒,好饮酒的也不妨借用一下。“尧夫”是北宋理学家邵雍的字,邵雍好作诗,这里也就成了诗篇的代称。以古人名代称相关事物,固然也属于借代修辞手法之一,但这种行文方式未免唐突昔贤,且易造成阅读理解障碍,因而不宜仿效。
三
古人行文中还喜欢用古地名、古官名代替今地名、今官名,或以别称代替正名,以显得自己博学古雅。其实这也是一种掉书袋的不良文风,很容易给后人制造阅读障碍。其中官名别称始于汉代,至唐宋而渐盛。洪迈《容斋四笔》卷十五就列举了唐代的多种官名别称,因为“唐人好以它名标榜官称”,这会给年轻人读书带来困难。如《唐摭言》卷三:“大顺(唐昭宗年号)中,王涣自左史拜考功员外,同年李德邻自右史拜小戎,赵光允自补衮拜小仪,王拯自小版拜少勋。”其中的“小戎”指兵部员外郎,“补衮”指补阙,“小仪”指礼部主事(补阙比主事官品高,此“小仪”当作“少仪”,指礼部员外郎),“小版”指户部员外郎,“少勋”指司勋员外郎。这些官名别称,不借助工具书是难以弄明白的。
《日知录》卷十九“文人求古之病”条引何孟春《馀冬序录》云:“今人称人姓,必易以世望,称官必用前代职名,称府州县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为异。不知文字间著此何益于工拙,此不唯于理无取,且于事复有碍矣……此其失自唐末五季间孙光宪辈始。按《北梦琐言》称冯涓为长乐公,《冷斋夜话》称陶穀为五柳公,类以昔人之号而概同姓,尤是可鄙。官职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号而称之,后将何所考焉。”阮葵生《茶馀客话》“文章好奇之弊”条也认为:“大凡地名、官名作文字,都应从今名,不必以古语更易,后世反无所考证。且文之古雅全不系此。”据说明代古文家唐顺之家居日,有人送来新修的《姑苏志》给他过目,他一瞥封面标题,便不屑一顾地说:“不通、不通。”人问之,唐曰:“大明人修《苏州府志》,而标签曰《姑苏志》,不通可知,奚以观为?”
王士祯《池北偶谈》卷十五引唐代孙樵论史云:“史家纪职官、山川、地理、礼乐、衣服,宜直书一时制度,使后人知某时如此,某时如彼。不当以秃屑浅俗,则取前代名品,以就简编”(语见《孙可之集》卷二《与高锡望书》)。王士祯据此说:“此病在唐人已有之,今日钱牧斋(谦益)、艾千子(南英)訾謷沧溟(李攀龙)、弇州(王世贞)本此,非创论也。”杭世骏《订讹类编》卷六中有“官名地名不宜用古”一条,引宋人叶梦得语云:“今人于官名、地名,乐用前代名目以为古,将一代制度、疆宇皆溷乱不可晓,亦是一弊。”又引朱熹语云:“余谓小小撰著若序记等作,不妨以古衔貌时事。若碑志及传,盖所以取信后世者,即与国史一例,断不宜用前代名目。”据《幕府燕闲录》记载,范仲淹为人作墓志,成稿后请古文家尹洙把关,尹看后对范说:“希文名重一时,后世所取信,不可不慎也。今谓转运使为部刺史,知州为太守,诚为脱俗,然今无其官,后必疑之,此正起俗儒争论也。”范仲淹虚心承教,改用了今名。但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仍用“太守”一称,这大约就是朱熹所谓“序记等作,不妨以古衔貌时事”吧!
虽然清代学人对官名地名喜用古称的习惯多致批评,然而在实际行文中仍难免蹈此窠臼。在清代笔记、诗文中,称北京曰“长安”,徐州曰“彭城”,镇江曰“京口”,称巡抚曰“中丞”,道台曰“观察”,知府曰“太守”,知县曰“大令”,翰林曰“太史”,举人曰“孝廉”等等,习以为常,触目皆是。这对当时人来说或许是约定俗成,不致产生误解,但对于后人而言,无疑是设置了障碍,混淆了制度。南朝沈约曾说:“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唐代韩愈虽然主张“戛戛独造”、“词必己出”,但他同时也强调“文从字顺各识职”。面对所谓的“涩体”,以及造成阅读障碍的各种借代手法,今天的读者只有尽量熟悉古籍,勤查工具书,才能解惑释疑,不至于坠入五里雾中。
作者单位:安徽六安市皖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