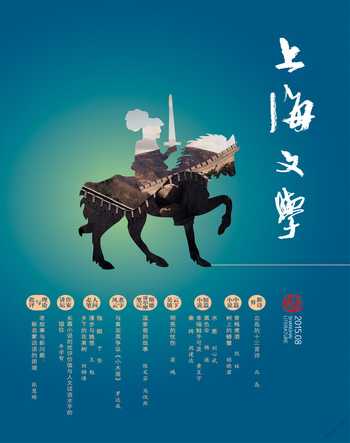老故事与新问题:新启蒙话语的困境
2015-09-10张慧瑜
张慧瑜
2013年作家方方的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发表于《十月》杂志第2期上,立即在早已远离“大众”的文学圈产生热议,小说也很快出版单行本,并荣获《中国作家》和“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2013年度最佳中篇小说奖。赞美者认为这是一部讲述当下青年人个人奋斗失败的故事,写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悲剧”(孟繁华:《从高加林到涂自强——评方方的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批评者则认为这种讨好“现实”的作品只不过说出了“阶层固化时代众所周知的事实”(翟业军:《与方方谈〈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缺乏个人精神层面的反思(曾于里:《只是个人悲伤——对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一点批评》),两种彼此对立的观点并不否认这部作品反映了当下中国的某种“现实”。前些年,方方创作的中篇小说《万箭穿心》发表于《北京文学》2007年第5期,因触及工人下岗、房地产等热点议题同样引发关注(尤其是2012年改编为同名电影之后①)。两部作品的主角农村大学生涂自强和下岗女工李宝莉都携带着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化/社会记忆,他们属于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时代的典型人物,不管是涂自强离开农村走向城市,还是李宝莉从工厂下岗“从头再来”,都与社会改革、体制转型有关。他们是1980年代新启蒙话语所解放的主体,这种以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勾画于1980年代、完成于1990年代,被认为是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径②。方方用这些“老故事”来处理新世纪以来市场化改革所遇到的新问题,涂自强最终没有能够按照1980年代的现代化逻辑留在城里,而自谋出路的李宝莉也没能留住自己的“房子”。在这个意义上,这两部作品既预示着1980年代所累积的新启蒙/社会改革/现代化共识的破产,又呈现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全新格局下所带来的反启蒙困境。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考上大学的农家子弟涂自强,离开封闭的大山来到武汉读书,依靠勤工俭学勉强读完大学,却没能换来城里的美好生活,一步步走向生命的终点,连给母亲养老送终的孝道都没有完成,这种人生悲剧被涂自强自述为“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③。这句话来自于涂自强初恋女友给他的分手诗“不同的路/是给不同的脚走的/不同的脚/走的是不同的人生/从此我们就是/各自路上的行者/不必责怪命运/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这诗如“咒语”般决定着涂自强的人生轨迹。“不同的路”、“不同的脚”并没有让涂自强走出“不同的人生”,他的自强之路就是自取灭亡的毁灭之路。不过,相比《万箭穿心》里没有文化的女工李宝莉心甘情愿接受命运的安排,“天之骄子”涂自强本应拥有“美丽人生”,因为这是1980年代新启蒙话语对个性解放的允诺。
这部小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路遥的经典作品《人生》(1982年),有很多批评家认为这就是新的《人生》。涂自强与三十年前的高加林相似,都面临离开乡村来到城市的问题,这也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人生”之选。《人生》的开头段落就引用了社会主义作家柳青的名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④。这段出自柳青代表作《创业史》(1960年)中的话,既是对《人生》这部作品的解题,也是对高加林的“人生总结”。需要指出的是,从《创业史》到《人生》关于“人生”的选择已经发生了天壤之别。从关于乡村的文化想像来说,这种1980年代启蒙视野下的落后乡村在1960年代的《创业史》中是充满希望和生机的空间。《创业史》把蛤蟆滩这一“五四”以来作为“乡土中国”的封建空间叙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田园,因为在上世纪50—70年代的革命/现代化的实践中,农村不仅不是被现代化所抛弃的他者之地,反而是追求与城市一样的工业化空间,这种农村的“在地现代化”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现代化田园”的想像,既是现代的、工业的、机械的,又带有农村的田园风光,这与西方现代化话语中构造的两种乡村图景“愚昧、落后的前现代”和“诗意的、浪漫的乡愁之地”是完全不同。1980年代的新启蒙话语的文化任务正是把这种现代化田园重新变成落后、愚昧的前现代乡村,《人生》就是这种新启蒙/现代化叙事的产物。
这种封闭的小山村与熙熙攘攘的城市想像被具体体现为一种文化/知识的区隔,也就是用知识劳动与体制劳动的差异来隐喻城乡秩序。就像《人生》里的高加林不仅有文化,而且“修长的身材,没有体力劳动留下的任何印记”。高加林回到农村就面临着每天要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生活,“对于高加林来说,他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已经受到很大的精神创伤。亏得这三年教书,他既不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又有时间继续学习,对他喜爱的文科深入钻研。他最近在地区报上已经发表过两三篇诗歌和散文,全是这段时间苦钻苦熬的结果。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他将不得不像父亲一样开始自己的农民生涯”。涂自强也是如此,一直上学的他从来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如“涂自强自上中学,家里就没让他喂猪。他想接过饲料,母亲却避开身子,说这个活儿哪能让你做?”、“母亲挎着筐,手上拎了根锄,说是去坡边的地里挖点土豆。涂自强说,我去吧,你在家歇着。母亲一闪身,说哪能让我儿做这样的粗活?这不成。”
在这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劳动形式,一种是繁重的体力劳动,一种是写作诗歌和散文的知识劳动,显然,这样两种劳动对于高加林来说是截然不同的,庄稼人的劳动让高加林懊恼和觉得丢人,文学活动则意味着身心的解放和自由。高加林一旦成为县通讯组的通讯干事就从农业劳动转变为“又写文章又照相”的脑力劳动者,他“高兴得如狂似醉”、“一切都叫人舒心爽气!西斜的阳光从大玻璃窗户射进来,洒在淡黄色的写字台上,一片明光灿烂,和他的心境形成了完美和谐的映照”。就连第一次救灾采访,尽管付出了艰辛的体力劳动,但当他听到广播中传出自己的第一篇报道之后,“一种幸福的感情立刻涌上高加林的心头,使他忍不住在哗哗的雨夜里轻轻吹起了口哨”。这种《人生》中随处可见的文化与文盲的二元对立,不仅有效地建构了一种文明与野蛮的修辞,而且这种修辞重构了城市与乡村的秩序。可以说,这种城市作为现代文明与乡村作为落后之地的想像正是七八十年代之交借助新启蒙和现代化叙述建构完成的。因此,从《创业史》到《人生》所展现的乡村故事,与七八十年代之交从人民公社体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有关,这种由社会主义现代化向改革时代的前现代转变的乡村想像就是《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对于大山深处的闭塞村庄的自然化描述的由来。重新把乡村叙述为愚昧、落后的空间不仅为1980年代的启蒙/现代化工程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而且也为1990年代中国大力发展对外出口加工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幸运的涂自强没有成为产业大军中的一员,因为他有文化、考上了大学。
高加林与涂自强离开乡村不仅代表着对城乡二元体制的突破和反叛,还意味着一种自主意志的选择。在这里,可以引入1980年代之初的“潘晓讨论”。1980年夏天,《中国青年》杂志刊登“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呵,为什么越走越窄……》,这篇编辑部集体策划的“读者来信”一经刊登就获得巨大反响。这封信讲述了经历“文革”的“我”从“无私”到“以自我为归宿”的思想蜕变,一方面醒悟到保尔、雷锋等共产主义战士所代表的“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的信仰都是“宣传的”、“虚构的”、“可笑的”,另一方面认识到“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才是可信的人生真谛。最后,信中写到“我”不愿意和工厂里的其他家庭妇女为伍,“我不甘心社会把我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来表明我的存在。我拚命地抓住这唯一的精神支柱,就像在要把我吞没的大海里死死抓住一叶小舟”。从这里可以看出,这封信的重点不在于控诉“文革”伤痕,而是在既有的社会制度下这种追求自我价值、渴望实现作家梦的“人生路”越走越窄。那些人生的拦路虎就是“组织”、工厂式的单位制等体制性力量,这也就是1980年代用个人成功来批判分配制、“铁饭碗”的禁锢与压抑,“体制外”成为一种实现自我认同的“自由”象征。在这里,近三十年之后涂自强的进城之路依然遵循的是高加林的人生路和潘晓的路,不同之处在于,“吞没”潘晓的“大海”经过19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已然变成了真正的“汪洋大海”,涂自强的“一叶小舟”还能扬帆远航吗?
不管是小说《万箭穿心》,还是其电影版,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位豪爽、泼辣而又苦命的武汉女人李宝莉,正是这个人物的出现成为作家方方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1987年方方发表成名作《风景》,这部作品与同一年问世的池莉小说《烦恼人生》一起被批评家命名为“新写实小说”的开山之作。新写实小说作为先锋写作之后最为重要的文学创作潮流,也是少有的从1980年代延续到1990年代的文学现象。新写实小说以相对中性、客观的笔法描写特定历史或现实情境中的人或事,既不同于“现实主义”对现实背后总体社会图景的探讨,也不同于先锋文学对语言叙事、文体形式的实验,恰如方方的《风景》借死婴之眼记录家里人的日常生活,不介入也不批判,其结尾处的一句话“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冷静而恒久地去看山下那变幻无穷的最美丽的风景”。就像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现的“新纪录片运动”,新写实作家热衷于记录平凡人物“一地鸡毛”式的庸常生活,这与1980年代告别革命/告别政治的氛围以及城市改革让每个人浸入“柴米油盐”的琐碎人生有关。更为重要的是,新写实笔下的人物虽然与生活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不适,但是总能找到理由接受现实,因为挣扎或生生不息地生活下去本身就是对人生与社会变迁最好的回答,这也是1980年代以来人道主义人性观在小说中的体现,就像余华的小说《活着》,“活着”成为个人反抗大历史的人性筹码。《万箭穿心》也是一部带有新写实“态度”的作品。
这部小说以1990年代曾经作为工业重镇的武汉遭遇工人下岗潮为大背景,讲述了一位粗粗拉拉、脾气火爆又忍辱负重的下岗女工李宝莉的故事。相比丈夫/知识分子的懦弱和短命,出身城市底层的李宝莉(小市民也是新写实的主角)不管经历多大的变故,哪怕忍着、认命、赎罪,总能找到说服自己活下去的理由,即使最后儿子也不认李宝莉这个母亲并把她指认为杀父凶手之时,李宝莉依然能够想通,“人生是自己的,不管是儿孙满堂还是孤家寡人,我总得要走完它”⑤。小说结尾处,一无所有的李宝莉欣然来到汉正街照样做起女扁担,就像李宝莉的母亲同样经历过“文革”与新时期的大起大落,虽然最终沦落到菜场卖鱼,但是母亲却不在意,只要堂堂正正地做人。这也正是方方所要表达的最“朴实无华”的主题,“唉,人生就是这样。面对生活,大家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思路。当然也就各有各的辛酸,各有各的快乐,各有各的苦痛,各有各的幸福。各有各的温暖,各有各的残酷”(方方:《纵是万箭穿心,也得扛住》,方方新浪博客,2007年6月1日)。
在这里,历史被抽空了具体的意义,变成了“造化弄人”的上帝。这种用坚韧的生命来对抗20世纪分外剧烈的政治/社会变动给个人所带来的伤害和倾轧有其合理性,但是问题在于母亲的“示范”效应,只能让李宝莉逆来顺受。正如父亲看房留下的那句“万箭穿心”的谶语,任凭李宝莉如何不甘地要把“万箭穿心”变成“万丈光芒”,无奈“新写实”的态度或惯例并不是创造奇迹或改变生活,李宝莉只好相信母亲的话“一忍再忍”。这座被楼下的马路“万箭穿心”的房子成了李宝莉的克星(其电影版《万箭穿心》的英文名字为“Feng Shui”)。在1990年代国企改革攻坚战中,下岗冲击波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文学创作领域出现“现实主义骑马归来”的现象,如谈歌的《大厂》、张宏森的《车间主任》等作品为度过社会危机提供“分享艰难”式的想像性解决。十几年后方方写作《万箭穿心》之时,下岗已经成为历史完成式,此时值得追问的不是对李宝莉们所经历的“人生的大劳累和大苦痛”的唏嘘不已,而是为何这间能够看见江水的“福利房”专门与李宝莉过不去,李宝莉为何就该如此宿命般地被“万箭穿心”。
《万箭穿心》最大的叙述动力就是争强好胜的李宝莉一次又一次地遭遇“万箭穿心”,就像苦情戏所必需的一个又一个更大的灾难“宿命般”地砸在弱女子身上,可是李宝莉并没有变成值得同情的、刘慧芳式的好女人/大地之母,因为李宝莉的悲剧完全是她自己一手造成的。正是她的刻薄、粗俗和没有文化,导致做厂办主任的丈夫马学武被搬运工羞辱,如果她听从好友万小景的劝告对马学武好一些,丈夫也就不会出轨,如果她不以向警察告密的方式让警察把丈夫捉奸在床,丈夫也不会重新回车间做技术员,更不会突然下岗,继而去跳江自杀,这一切仿佛都来自于没有文化的李宝莉与有大专文凭的丈夫之间“不幸”的婚姻。这种知识分子/工人之女(按小说的描述,李宝莉母亲成分硬)的“结合”以及文化/没有文化的“苦恋”是1980年代反思“文革”及1950—1970年代革命实践的重要修辞。在这个意义上,《万箭穿心》高度吻合于1980年代的文化、社会逻辑。
在小说中,李宝莉的母亲之所以会从“革委会”主任变成下岗工人,是因为“‘文革’一结束,废掉成分,时行文凭”。或许正因为文凭对于母亲的影响,使得只有小学水平的李宝莉对文凭看得格外重,这也正是她选择跟来自乡下“其貌不扬的马学武结婚”的根本原因,并且坚信“有文化的人智商高,这东西传宗接代,儿子也不得差。往后儿子有板眼,上大学,当大官,赚大钱,这辈子下辈子都不发愁”。果然,李宝莉的儿子不仅学习好,而且考上了名牌大学,并且挣到了大钱。这显然验证了李宝莉把“文化”作为“文革”后“当大官,赚大钱”最大保证的认识。这种对于知识/文化/教育的崇拜正是七八十年代之交“拨乱反正”的产物,只是彼时通过恢复高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来批判“文革”中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荒谬”,而在《万箭穿心》中文化/文凭却成为合理化阶级分化最为重要的意识形态说辞。也就是说,李宝莉与马学武的差距不是文化水平,更是一种阶级身份的差别,这尤为体现在李宝莉与房子的关系上,她这样的下岗女人根本不配拥有一间代表社会更高阶层的房子。
从这种对于文化、知识的理解以及城市与乡村的二元想像中,可以看出方方的书写带有1980年代的文化烙印,或者说这两部21世纪的小说依然是1980年代的老故事。《万箭穿心》处理的是1990年代国有企业破产重组时期的故事,所涉及的房子不是房地产市场化之后的商品房,而是社会主义单位制尚未解体之时的福利房;《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对于落后的乡村与现代化都市的想像也是1980年代典型的现代化叙事,如同《人生》中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来隐喻城市与乡村不可调和的人生落差。不过,讲述故事的年代远比故事所讲述的年代更重要,这些带有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痕迹的老故事遭遇到当下中国的新问题。这与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变是分不开的。相比1980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内部进行社会改革以及1990年代处在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转轨时期,新世纪以来计划经济的旧制度已经消失、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成为主导逻辑。不管是涂自强,还是李宝莉,都变成了自由市场竞争社会中的原子化的个体,他们已经摆脱了乡村、工厂等旧体制的束缚,需要完全依靠个人奋斗或自主创业来生存和发展。而两部小说的敏锐之处在于呈现了这些被新启蒙所解放的“个体”所遭遇到的新壁垒和困难。来自乡村的涂自强在其他城里同学面前根本不具备竞争优势,而出身底层的李宝莉想通过房子来改变自己的阶层命运的努力也是徒劳的。
《万箭穿心》一开始就描述了李宝莉第一次看新房给她带来的“高贵感”、“幸福感”和“电影里贵夫人出行的派头”,她觉得“我是不是一步登天了”。在改编的电影中,也呈现了李宝莉搬进新房第一晚的那份惬意和得意。不过,第一晚还没有度过,马学武就和她提出了离婚,彻底击碎了她的人生美梦,但这些并没有动摇李宝莉对儿子上学“当大官、赚大钱”的认识。当李宝莉第一次搬家到楼下的时候,电影中使用了她的大仰拍镜头,用看不到顶的高楼来对李宝莉形成一种压迫感,也就是说李宝莉从来没有拥有过从楼上往下望的权利,她从来没有真正占有过这间房子。更不用说当李宝莉搬进新房后,产生的是无尽的争吵以及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最终在长大成人后的儿子的“奚落”之下,李宝莉飞奔跑“下”楼梯。而在电影的结尾部分,李宝莉用自己的扁担挑着自己的行李最终离开了这间“万箭穿心”的房子,摄影机镜头从楼上的房子俯视/监视李宝莉推着建建的面包车离开小区,演员表从屏幕下方升起。这个注目礼仿佛是房子对李宝莉的送别,也是死去的丈夫/长大成人的儿子作为房主对女人李宝莉的驱逐。
与现代、整洁的“空中楼阁”对李宝莉的驱赶相比,熙熙攘攘的、低矮老旧的汉正街却是李宝莉的“天下”,不管是她卖袜子,还是做女扁担,只要在汉正街就“满街都能听到她的笑声”,汉正街与高楼对于李宝莉来说恰好意味着两种不同的阶级空间和人生归宿,一个是室内的、学习的、脑力劳动的空间,另一个则是室外的、体力劳动者的空间。喜欢李宝莉的小混混建建就居住在汉正街上,按照小说中的说法,建建始终如一地坚持年轻时对李宝莉的告白“你蛮对我的性格,我恐怕这辈子只会爱你一个人”。小说结尾处,一种少有的乐观喜悦的色彩出现了:“望着乱七八糟、嚣声嘈杂而又丰富多彩、活力十足的汉正街,建建仿佛看到哪里都有李宝莉的影子”。李宝莉还是从隐居高楼之上的中产阶级三口之家来到了学历低的、住在仓库里的建建身边,因为在文化/阶级的修辞学中,李宝莉只配得上建建这样的男人。可以说,李宝莉之所以会遭受“万箭穿心”的天谴,正是因为她试图逾越阶级的鸿沟,贪心找个学历高的丈夫而住上“单位福利房”。从这个角度来说,“祸根”一开始就种下了,李宝莉住了本来就不属于她的房子。在这个意义上,《万箭穿心》如此准确又直白地讲述了作为社会热点的房地产与阶级分化的寓言,这也正是这部作品的意义所在。
1980年代的《人生》故事结尾处讲述高加林返回乡村从事农业劳动,而涂自强则不可能返回乡村了。《人生》依然延续了毛泽东时代对于乡村的正面论述,小说中经常通过高加林的眼睛呈现一个美丽的、自然化的乡村,如高加林在院中刷牙时看到“外面的阳光多刺眼啊!他好像一下子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天蓝得像水洗过一般。雪白的云朵静静地飘浮在空中。大川道里,连片的玉米绿毡似的一直铺到西面的老牛山下”。这种田园化的风景既是一种“文明的”、“现代的”眼光对前现代乡村的回眸,也是一种对土地、乡村和劳动的肯定。当然,这种“希望的田野”与1980年代之初农村改革带来的短暂繁荣是分不开的,这与三十年之后涂自强所面对的凋敝的、被现代文明所遗弃的乡村有着本质的不同。对于2013年的涂自强来说,乡村则变成根本无法回去的地方,就像小说的结尾处,渴望走回头路“拾回自己的脚印”的涂自强却“一步一步地走出这个世界的视线。此后,再也没有人见到涂自强”。这主要是因为小说中的乡村已经变成了没有希望和出路的地方,涂自强走向城市就是一条无法回头的“不归路”。
高加林曾经在意的“文化”优越感在涂自强的时代变得一文不值,这恰好与两个时代所面对的不同问题有关。在《人生》中这种城市的梦想与一种知识性的劳动结合在一起,高加林无法进城的原因在于旧体制的羁绊(第一次是被村干部的孩子冒名顶替,第二次是违反组织原则),而新启蒙/现代化的承诺就是打破旧体制,让有才能的人依靠自己的才能实现人生目标。与这种打破旧体制获得自由的人生路不同,三十年之后的涂自强已然生活在一个以市场为支配性逻辑的社会中。身处这样一个充分自由的世界,涂自强既没有像俞敏洪那样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走出美国梦(如2013年的电影《中国合伙人》),也没有像白领菜鸟杜拉拉那样在职场竞技中实现逆袭(《杜拉拉升职记》是近些年流行的网络职场小说,被改编为话剧、电影和电视剧)。对涂自强来说,这注定是一场徒劳的人生之路。他一直勤勤恳恳地用体力劳动、脑力劳动来养活自己,可是这些在《万箭穿心》中被李宝莉崇拜的大学毕业生/知识并没有转化为市场中的成功优势。
相比高加林的苦恼于无法把自己的知识转变为可以平等交换的商品,涂自强的悲剧在于这种市场化的平等交换再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知识、学历作为象征资本的价值已经无法转换为真正的市场价值。这与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从自由竞争的市场迷梦走向权力垄断与固化的转型有关,正如近些年作为中产阶级后备军的小资、白领在国际化大都市的资本空间中成为“高学历、低收入、难发展”的“80后”、“90后”蚁族。涂自强无法改变自己的宿命,不再是因为城乡区隔,而是他出生之前就已然存在的社会阶级分化的屏障。在这里,涂自强和李宝莉一样,都无法实现阶级的逆袭,只能延续他们命中注定的那条路。不仅涂自强如此,2013年创造七亿多票房的国产青春片《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也同样讲述了一种青春、理想、爱情消亡的故事,以至于《人民日报》发表《莫让青春染暮气》的文章,指出“在一夜之间,80后一代集体变‘老’了”(白龙:《莫让青春染暮气》,《人民日报》,2013年5月14日)。如果说1982年的《人生》可以批判城乡二元体制对高加林这样的知识青年的压制,那么2013年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确实只能是“个人”的悲伤,连可以怨恨的对象都没有。在这个意义上,从高加林到涂自强,中国社会已然完成了“华丽”蜕变,中国文学也从1980年代对新启蒙/现代化的高扬走向了新启蒙/现代化话语的破产。
① 电影《万箭穿心》由青年导演王竞执导、第四代著名导演谢飞担任艺术总监,成为近些年少有的反映当下现实生活的电影力作。
② 贺桂梅在其《“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一书详尽分析了新启蒙话语在1980年代的建构过程,以及新启蒙话语与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现代派、寻根思潮等1980年代出现文化思想论争之间的关系。
③ 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70页,该小说的引文皆来源于此,不再单独标注。
④ 路遥:《人生》,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页,该小说的引文皆来源于此,不再单独标注。
⑤ 方方:《万箭穿心》,《北京文学》2007年第5期,第48页,该小说的引文皆来源于此,不再单独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