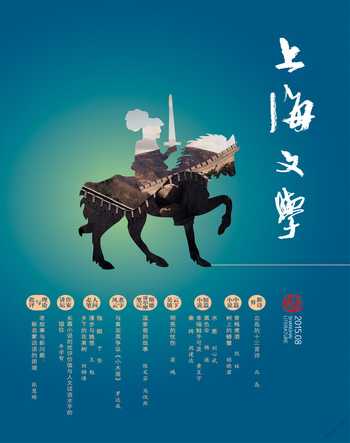乡下的花果树
2015-09-10刘锦涛
刘锦涛
在崇明乡下,把果树称为花果树。杏树、梅树、桃树,都是花果树。时间倒退几十年,小镇的水果摊上,可以看得见的水果大约只有苹果、生梨、香蕉等一些大众品种。这些外来水果,贵不说,经过几百几千里的运输,都有长途跋涉和经风历雨的沧桑感,干瘪、灰暗,无可奈何地躺在水果篓里。偶尔被哪个主顾买去,也是用来看望长辈或者病人的。长辈或病人也舍不得吃,说不定还要转送他人。红颜薄命,越是金贵的水果,其命运越是变幻莫测,最终落入哪个人嘴里的时候,早已失去了原来的容颜和滋味。好在长辈牙口不好,病人胃口不好,水果的滋味好不好无关紧要。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发高烧躺在床上,隔壁邻居送我一个橘子,那个橘子,外表皱巴巴的,失了水分,比原来缩小了一圈,一看就是远道而来、深藏已久的。但那是我第一次吃橘子,算是享受了病人的待遇。即使只吃到了失去水分的橘子,现在想起来,依然口有余香。
相比之下,那些乡下花果,水灵、新鲜,不加打扮,保持了本来面目。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性,一是果型小,杏子梅子,不过核桃大小,一拳掌握。二是口味酸涩,喜欢的人喜欢,不喜欢的人吃得直咧嘴。无论杏子、梅子,还是柑子,其滋味,都是不加任何修饰的本色,酸中带甜,甜得含蓄,却酸得尖刻,如一个土生土长的乡下孩子,未经世面,衣衫随意,做不到礼貌周全,却朴实无华,原汁原味。
如今满大街都是水果,却很难看到乡下花果的影子,大约也是因为乡下花果已经不适合现代人的口味了。有一次发现水果摊上有杏子,比乡下花果树上长的大了许多,买回去一尝,早已不是原来的滋味了,不酸,也不甜,中看不中吃,徒有其表,令人生厌。世道变了,水果的滋味,也被人类弄得不伦不类。
常常要想起乡下花果。乡下的那些花果树,往往长在竹园里,长在宅前屋后的空地上,整片的农田里不会有它们的影子。一些花果树是主人有意栽种的,大多数是飞来的种子,趁主人不备,就在一块空地上“占山为王”了。或许某一天,主人去竹园里挖笋,无意中发现一棵秧苗,是杏树或者梅树的苗,这棵苗命运如何,全凭主人的心情了,要是看不顺眼,一锄头就要了它的命,“王”依然还是人呐!要是主人心情好,手下留情,就留下了,留下也并不代表喜欢,反正长在那个地方不碍什么,不用浇水施肥,不用整枝,就让它长着吧。过了几年,三年或者五年,开花了,结果了。有一天主人把长熟了的杏子或梅子呈现在孩子的面前,换来孩子一脸惊喜,直吃得牙都倒了,第二天不能咀嚼食物。尽管如此,还是要吃。吃那些酸涩水果长大的孩子,似乎从小开始就把人世的酸甜苦辣都尝遍了,脸膛黝黑,身体健壮。
有两棵杏树,长在外婆家的宅沟边上。在我的记忆里,杏树是倾斜的,而且随着沟岸的进一步塌陷,越来越向宅沟里倾斜,根须祼露在外,有的枝干快要贴近水面了,让人感觉这样的生存,是何等咬紧牙关,坚韧不拔。杏树也是老树了,每天在人们的眼皮底下,却熟视无睹,谁也说不清它们的年纪。在他们的记忆里,那两棵杏树历来就是这样长在宅沟边上的,多少年了,除了越来越向沟里倾斜,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杏树尽管倾斜,却不影响年年开花,年年结果。每年三四月份,满树的花,一棵红的,一棵白的。花谢的时候,绿色的嫩叶也长了出来,把一粒粒青杏藏在怀里。每天从树下走过,我都要看一眼那些杏子长大了没有。外婆吓唬我,不可以多看,看多了,杏子就要落了。我趁着外婆不在意,忍不住又看了一眼。甚至,故意使劲盯住某一粒杏子看,第二天再去寻找那棵杏子,还是端端正正挂在叶丛里,心想,啊呀!真是万幸。有时候觉得扫兴,昨天看过的杏子,今天看上去依旧那么大小。
到了五六月份,乡下已是农忙季节,生产队里老老小小,像我这样十来岁的半大孩子,也要下地,或割麦,或插秧。这个季节,也正是杏子成熟的季节。某天傍晚收工回家,正在宅沟里的水桥上洗脚,抬起头来,发现绿叶丛中,黄色的光点刺了一下眼睛,猛然惊醒,啊,杏子熟了!
那一树的杏子,在被你遗忘的日子里,悄然长大成熟。
那个夜晚,成了一家人的欢乐之夜。在这之前,外婆是杏树的“守护神”,坚决不让我们打杏子的主意,只要稍有尝鲜的想法,就要受到凶神恶煞般的责骂。外婆看也不看树上的杏子,就肯定地说,还没熟呢!杏子的熟不熟,全在她的掌控之内。现在杏子终于露出了成熟的笑脸,外婆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完全超越了她这个年纪的举动,一下爬到树上,比我们的动作还灵活。其实,盼望杏子快点熟,外婆的心情比我们还迫切。
那个晚上,一家人都吃了杏子。
那两棵杏树,不在同一时间成熟,西边开白花的那棵果型小,成熟早,口味也比较酸。东边开红花的那棵,成熟晚,但果型大,比较甜。因为有了两棵先后成熟的杏树,整个农忙季节,我们都可以吃到新鲜的水果。
后来,那两棵杏树越来越往沟里倾斜,终于支撑不住,过了几年,死了。
童年时代一眨眼就过去了,到如今依旧怀念那两棵杏树,有了它们,使童年的生活有滋有味。
一个号称“大仙”的算命先生,突然对一个不认识的人说,你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柿子树。听的人吃了一惊,心想你又不认识我,怎么知道我家的院子里有柿子树?继而对“大仙”佩服得五体投地,大仙真是大仙,神机妙算。
其实,“大仙”是一个玩花招的人。在崇明乡下,柿子树是最平常的果树,哪家的宅前屋后没有柿子树?。
有两棵柿子树令我终身难忘。
一棵在外婆家的后门口,挺拔的主干上长满了青苔,树皮爆裂,看上去没有一点活力,主干之上却枝丫伸展,新枝,新叶,在春夏两个季节里扬眉吐气。到了秋天,柿子树不再生机勃勃,树叶黄了,只剩下红的果实,以成熟的矜持,满树城府地等待主人的采摘。冬天来临,柿子树褪尽春光,光秃秃的树干,寂寞地蛰伏一季,等待春天重新焕发生机。
外婆说,这棵树不知道有几岁了。外婆青春年少的时候,它已经有一抱粗细,后来,外婆步履蹒跚了,它依然只有一抱粗细。一棵停留在岁月里的树,不动声色,不再长大。
它至少已是百年老树了。
外婆告诉我,有几年,柿子树春天不爆青了,不长新枝了,以为死了呢。过了几年它突然又活了,变本加厉地,挂满了果实。外婆点着我的鼻子说:“你有吃福呢,它在等你长大,长到能吃柿子的年纪,又结果了。”于是我想,它“死了”的那几年,其实是在静等我出生,静等我长成一个少年。如今,这个少年站在柿子树下,仰着头,望着树上青涩的柿子,期盼它快点成熟。
柿子树,你就是我生命里的一道风景,我相信和你的缘分,要不然,你怎么会这样耐心地等我?怎么会年复一年的,不分大年小年,每年都是丰收,枝头挂满了灯笼似的果实,让我尽情享用?
后来,我离开了崇明。
过了几年,当我重新回到崇明的时候,那棵柿子树已经死了。
我去看它。开始几年,它还站在原地,如一个白发老人,坚信我会来,便耐心地等着我。看望这棵树如看望多年的老朋友,我希望依然能够出现奇迹,只要春风春雨锲而不舍地呼唤,它就能在某个时辰伸个懒腰,悄然醒来。可是,奇迹没有出现,它的枝丫因为失去水分而慢慢枯萎,一截一截地零落,仿佛灵魂已成碎片,纷纷扬扬地飞向远方。
终于有一天,它倒下了。
某年,外婆离我而去,外婆家的老宅也成了废墟。原先柿子树的地方守着荒草,如外婆丝丝缕缕的白发。
另一棵柿子树,在我家,同样在后门口。当年,我的祖父买了一块地,盖了五间房子,供两个儿子娶妻生子。祖父的父亲,即我的曾祖父,为两个孙子各种了一棵柿子树。
等我记事的时候,柿子树已经开始挂果。柿子成熟的季节,父母亲还有我们兄妹三人如花果山上的猴子,争先恐后地爬到树上摘柿子。母亲反复地念叨,是老太太种的呢,老太太说了,给儿孙们种一棵会结果的树,让儿孙们年年有柿子吃。这样的话题,在所有柿子成熟的季节总要重复一遍。
曾祖父早已在我记事之前作古,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我不知道曾祖父长得什么模样,闭上眼睛想像,跳不出慈眉善目,白发苍苍。或许,在我们欢天喜地采摘柿子的时候,曾祖父的灵魂正躲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微笑呢!
如今,那棵柿子树也已年近花甲,每年秋天,却总是挂满果实。望着逐渐苍老的树干,想想我的曾祖父,真是一个有远见的人,每摘下一粒果子,总要让他的子孙后代念叨这个智慧的从未谋面的老人。
我从小在外公家长大。自打学会走路到上学,我就是外公的尾巴。外公养牛,我就骑在牛背上和外公一起走亲戚。外公养猪,我帮外公铡草,猪不但认得外公,也认得我,让我很有成就感。外公在自留地里种菜,我就帮他下种。
那一年,外公种了两棵梅树。两株极细极细的秧苗,托在外公手里,根部连着泥土。从泥土开裂的地方,可以看到一粒半开的梅核,秧苗的根须就从那里长出来。
生命的起源轻而易举,却脆弱得一经风雨就要夭折。外公小心地,把两株小苗种在自留地里,四周用芦苇围上,怕粗心的人踩踏。种完了,浇上水,第二天、第三天,再各浇一次水,就不再管它了,让其自然生长。
到了第二年春天,当我再次跟着外公去自留地里的时候,那两棵秧苗已经长到半人高了,枝丫也多了起来,脆弱的生命在一年的风雨里强壮了许多。又过了两年或者三年,它们就真的长成了一棵树,看上去青春勃发,枝丫舒展,每一片叶子都是水汪汪的。再往后,它们便有了星星点点的花蕊。开花的第一年,没有挂果,第二年,一棵树上结了两个果,后来又掉落了。
从第四年或者第五年开始,小树长成了大树并大量结果。我离开家乡去外地读书的那一年,两棵梅树已经长得高大挺拔,春天满树的花,夏天满树的果实,到了收获时节,一篮子一篮子的梅子,放在家里,满屋清香。
在崇明乡下,常见的花果树还有柑子,尽管都属于柑橘,其口味和现在的橘子相差甚远。桃子,也不是果园里种植的,小而酸,与市面上的桃子大相径庭。前几年,乡下重新翻建了房子,有一个小小的庭园,庭园里种什么?我的要求很功利,种果树。于是,种植了桃子李子杏子梅子,还有在崇明很少见到的外来品种——三棵杨梅、两棵柚子。杨梅树第三年就结果了,可惜小不说,吃起来酸得牙都要掉下来了,和崇明的乡土水果差不多。两棵柚子,一棵死了,另一棵结出了果实,果头大、苦涩、水分少,干巴巴的,但挂在树上,像模像样,远远望去,很好看。
乡下水果的味道,就是崇明乡村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