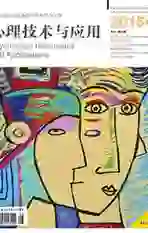成长自己 成就孩子
2015-08-28凌霄张玉霞王茵罗敏杰
凌霄+张玉霞+王茵+罗敏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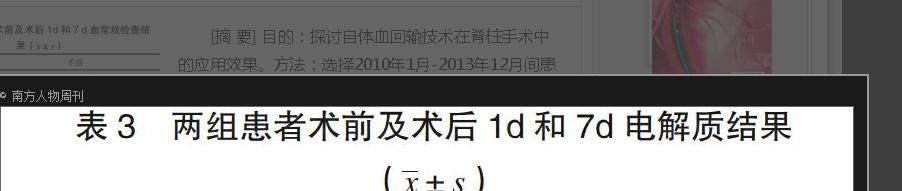
摘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和谐家庭的建立。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和终身老师,其教育的理念、态度和方法将直接影响家庭教育的效果,进而影响子女的健康成长和家庭的幸福。团体辅导已被证实是提高家长素质的有效途径之一,研究采用家长成长团体的形式,通过18次团体辅导,探讨其在改变家长教养态度、改善亲子沟通和家庭氛围上的作用。选取“父母教养态度量表”“亲子沟通问卷”和“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对78名团体成员及其伴侣和子女进行前后测。结果表明:家长成长团体提升了家长家庭教育的素质和家庭建设的能力,将家长成长团体辅导运用到亲职教育中是可行、有效的。
关键词:家长成长团体;父母教养态度;亲子沟通;家庭亲密度
分类号:G444
1问题的提出
1.1亲职教育的意义
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新春团拜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谈到了家庭和睦和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新华社援引习主席的话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的一言一行,不仅影响子女的性格养成,对子女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同样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进而影响子女的终生发展与一生幸福。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手机、电脑、网络无一不在以人们难以预料的速度和方式对家庭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产生影响:家庭民主氛围的提升使过去的权威式教育受阻;孩子看似叛逆的想法与行为既是家庭冲突的制造者,又是家庭教育的显色剂。父母怎么说,孩子才愿意听?父母怎么听,孩子才愿意说?父母如何自信、有力、智慧地履行亲职?父母教育的效能和家庭和谐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2亲职教育的现状
目前我国家庭教育仍存在一系列比较突出的问题。首先表现为“养不教”,一些家长虽然尽了生而养之的责任但未行养而教之的义务。他们以工作繁忙为由,对孩子的教育采取简单粗暴或放任自流的态度。其次表现为“教不得法”,许多父母看重孩子的智力发展,而忽视了孩子的道德教育、生存教育和行为习惯的养成,忽视了对孩子进行思想感情及品德的培养,较少对孩子进行健全人格的培养和心理健康的指导。生活上的过度保护、行为上的过度干涉,使得相当一部分孩子被父母以爱的名义剥夺了个体成长的权利,最后他们不得不以愤怒反抗的扭曲表达方式宣泄精神世界的需要。再者,不少家长苦苦追求“一招制孩儿”的“金科玉律”,而未能充分认识到自身的言行和教养素质对孩子的影响;过多地将时间和精力放在寻求解决孩子问题的技巧和方法上,而忽视了自身在家庭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往往是在教育孩子上花了大气力,但收效甚微。有教育家指出,对儿童青少年进行教育应由以教育儿童为中心转到以父母教育为中心上来(赵阿勐,2006)。孩子的行为是家庭教育的结果,父母的教育观念与态度、教育能力和教育方法才是家庭教育的本源。为此,研究的团体方案除了设计有关转变家长的教育观念、调整教养态度、改善亲子沟通以及提升教育能力的部分,还增加了父母的自我成长部分。
亲子关系在家庭发展的过程中都会面临阶段性的挑战,如果家长能够在挑战中学习,挑战就不会演变成家庭危机,家庭成员也不会深陷问题的泥潭。因此,育人者需先受教育。以家长终身化学习为特征的“亲职教育”(parents education)是双赢的教育,它能协助父母了解自己的职责,提供有关孩子发展的知识,包括正确的教育态度以及调整亲子关系的具体策略,让父母成功成为有效能、有影响力的父母。
1.3父母教养态度
父母教养包括态度和行为两个层次:教养态度是指父母在训练或教导子女方面所持有的认知(知识或信念)、情感(或情绪)及行为意图(或倾向);教养行为是指父母在训练或教导子女时所实际表现出来的行为和做法(王争艳,刘红云,雷雳,2002)。适当的教养态度有助于发挥良好的家庭功能,良好的教养行为以积极正确的教养态度为基础。以往研究提示:科学合理的教养态度是维护亲子关系、促进子女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Lefkowitz,2000;Kroger,1997;姚本先,何军,1994)。因此,对家长过分保护、过度教育、过多限制孩子的教养态度,特别是与之相应的教养行为进行调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4亲子沟通
亲子沟通是指父母与子女彼此之间相互分享情感、交流意见及表达需求的知觉行为,是父母与子女之间信息交流的过程(雷雳,王争艳,李宏利,2001)。亲子沟通对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的发展以及情绪体验、行为模式等心理发展状况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以学习开放式沟通、减少问题式沟通为目标,设计活动方案培养倾听、积极关注、同理等沟通技巧,提高对批评、指责、不一致表达的觉知。
1.5家庭亲密度
家庭亲密度是家庭因素中一个重要的指标,家庭成员的行为特点和交往方式乃至一些不良的行为习惯和心理问题等都是家庭亲密度过低的衍生物(李辉,施江玉,刘春燕,2002)。因此,通过家长成长团体,提高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对和谐家庭关系、增强家庭功能、减少“家源性”身心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1.6亲职教育的形式与剂量
亲职教育的形式非常丰富,包括一般性教育、亲子训练和家庭咨询(治疗)等(曾端真,1994)。每种教育形式都各有利弊:一般性教育的受众广,但针对性较弱,往往由于缺乏后继的指导与反馈而带来新的家庭伤害;家庭咨询(治疗)的针对性强,专业性高,但受众少,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和一定的经费;团体形式的亲子训练兼具了两者的优点,经济高效,同时增加了参与父母的归属感,降低了问题焦虑,获得了团体支持,由游戏体验、角色扮演、小组讨论、作业练习所引起的团体动力也让家长收获了不同的反馈与资源(赵阿勐,2006;刘姿吟,1992)。因此,团结形式成为普遍认可的亲职教育培训形式。
在亲职教育体系中,儿童青少年的父母教育需求最为强烈。特别是在中学阶段,孩子渴望获得尊重与独立,成人感强,挑战威权,情绪化;一方面,他们积极参与同伴群体,想要摆脱父母的控制,另一方面,他们希望获得家人的支持与认可。这些变化经常让父母感到无所适从,也很容易引发亲子冲突和对抗。在这个“青春期撞上更年期”的特殊时期,父母也需要特别的心理关照。因此,针对这一阶段的家长成长团体应运而生。
虽然针对亲职教育培训模式、方案和效果的研究都还处于探索阶段,成果较少,但是已有的研究显示:家长团体辅导对学生家长的亲子沟通水平和教养态度有积极正向的改变(赵阿勐,2006;李辉,施江玉,刘春燕,2002;刘姿吟,1992;王华,2013;刘海鹰,刘昕,2008;李霞,2013)。然而,团体辅导的剂量效应仍不明晰。剂量,即辅导次数,是心理辅导效果研究中的重要变量(Howard,Kopla,& Krause,1986);效果是指在心理辅导中,总体当事人的进步或改善到正常化的百分数或可能性。国外对于个体辅导的剂量研究显示,当事人的快速改变大部分发生在前8次的辅导过程中,而后面辅导期间的改变则较为平缓(秦佑凤,于丽霞,郑晓边,2008;Beail,Kellett,& Newman,2007)。研究表明,剂量效果在个体辅导中遵循的关系在团体辅导中仍然适用(Beail,Kellett,& Newman,2007;Ghebremichael,Hansen,& Heping,2006)。因此,在设计团体活动方案时,通常也以8次作为团体活动次数的参考。在以亲子关系、家庭教育为主题的团体辅导领域,8次辅导可以带来父母教育观念和态度的转变,但在亲子沟通方式、亲子关系和家庭氛围的改善方面仍不理想(赵阿勐,2006;李辉,施江玉,刘春燕,2002;王华,2013;刘海鹰,刘昕,2008;李霞,2013)。事实上,对于心理辅导剂量研究的结果大多来自国外,国内的研究非常有限。国内有研究表明,5次辅导有1/4的当事人达到临床显著效果,9次达到1/2,17次以后将有3/4的当事人得到显著改善(秦昊,2010)。因此,研究还将探讨不同学习时长和次数对父母教养态度、亲子沟通、家庭亲密度改变程度的影响。
1.7研究目的与意义
研究在调查中学阶段家长教育需求的基础上,设计了家庭成长团体的培训方案,通过效果评价探讨:(1)家长成长团体对中学生家长教养态度、亲子沟通以及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的正向改变作用;(2)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亲职教育团体辅导方案;(3)影响父母教养态度、亲子沟通以及家庭亲密度改变的作用机制。
“教育应走在孩子发展的前面”,父母是一种职业,这种职业比其他职业责任更加重大,一旦入职便不能轻易放弃。因此,家长成长团体的意义在于让为人父母者了解现代家庭教育理念和科学有效的教育方法,成功履行父母职责,有效促进家庭和谐,智慧陪伴孩子成长,让每一个家庭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力量。
2方法
2.1对象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半结构式访谈以及家长自荐与班主任推荐相结合的方式,选取武汉市某学校高中家长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自2012年初至今已开展三期培训,共计78名学生家长参与了家长成长团体。成员的筛选步骤如下:(1)宣传招募自愿参加团体活动的家长;(2)通过半结构访谈和开放式问卷的方式选择目标家庭,排除精神疾病、严重躯体疾病者等。
2.2工具
2.2.1父母教养态度量表
采用台湾学者邓玉英(1983)改编自Hereford 1995年编制的“父母态度量表”(Parents Attiude Scale)。量表共40道题,用以测量家长在教养子女方面的态度,包含自信、归因、接纳与了解四个分量表。其中“自信”分量表测的是家长对孩子教养的自信程度,“归因”分量表测的是家长对子女行为的归因倾向,“接纳”分量表测的是家长对子女的需要及子女本身的个人特质的接纳程度,“了解”分量表测的是家长愿意与子女沟通,并借由沟通更了解子女的程度。量表采用五点计分,从“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其中,正向题目15题,负向题25题。各分量表间内部一致性信度介于0.61至0.79之间,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系数为0.85,各分量表之间的相关介于0.39 至0.61之间,各分量表与总量表的相关则介于0.76至0.85之间,所有分量表之间的相关均达到显著,显示各分量表之间具有相当高的相关性。同时,量表修订结果显示,此量表适合在大陆地区使用(赵阿勐,2006;李霞,2013)。
2.2.2亲子沟通问卷
采用Olson McCubbin等人(1955)编制,孙馏英修订(1995)的“亲子沟通量表”(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Scale,PACS)。量表共40道题,采用Likert五点记分,分为开放式沟通和问题式沟通两个维度,各20题。父子沟通问卷α系数为0.76,父子开放式沟通α系数0.87,父子问题式沟通α系数0.46,母子沟通问卷α系数为0.85,母子开放式沟通α系数0.88,母子问题式沟通α系数0.71。同时,量表修订结果显示,此量表适合在大陆地区使用(赵阿勐,2006)。本研究中所得问卷α系数为 0.92。
2.2.3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
采用Olson等修订的“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共有30个项目,包括两个分量表,主要评价两方面的家庭功能: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采用五级评分,分数越高,说明亲密度越高,适应性越好。本量表的中国版具有较高的信效度(李辉,施江玉,刘春燕,2002)。
2.3设计
家长成长团体的目的在于提升父母效能,包括四个方面:(1)明确家庭育人的目标与原则;(2)了解孩子的个性特点和身心发展需求,掌握陪伴孩子成长的方法;(3)运用有效的亲子沟通技巧,帮助孩子社会化;(4)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在错误中成长,不断完善自我(赵阿勐,2006;李辉,施江玉,刘春燕,2002;曾端真,1994;刘姿吟,1992;王华,2013;刘海鹰,刘昕,2008;李霞,2013)。根据设计方案、学校学期安排以及家长需求,家长团体成员接受一周一次、每次120分钟、一期18周的团体辅导。
2.4实施程序
研究实施从2012年3月至2015年3月,分三期进行,成员可在参加第一期后,继续参加第二期和第三期的复训。成员在参加辅导前后完成父母教养态度、亲子关系、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的前后测,同时在每次参加学习后提交家庭作业,并在学习全部结束后完成学习心得。
培训采取以人为中心疗法和家庭治疗的理念,强调体验和积极正向,从系统的观点了解孩子的行为,即不以孩子的行为作为问题的焦点,而是根据子女的偏差行为来审视隐藏的家庭系统的问题,加以修正,恢复家庭的正常功能。当家庭系统能够正常运作时,孩子的问题行为会自然消失。同时,综合Ginott模式(增加父母自我觉察,明确家庭的规则和界限)、沟通分析模式(Transactional Analysis,TA,强调家长的自我成长,帮助父母了解家庭成员的人格结构)、现实治疗模式(自我负责和问题解决取向)以及系统性父母效能训练模式(Systematic Training For Effective Parenting,培养家长积极倾听的习惯,训练亲子沟通方法)等四种成熟的亲职教育辅导模式设计家长成长团体的具体实施方案。需要指出的是,在亲职教育活动设计上研究充分体现“教育性和发展性”,而非“治疗性”的原则,以转变家长家庭教育的观念、调整教养态度、提高沟通水平、增强家庭亲密性和适应性为目标,系统催化成员在子女教育观念和行为上的积极改变。
家长成长团体辅导的主要内容包括:(1)与时俱进的家庭教育观念;(2)青少年的年龄特点和心理特点;(3)亲子沟通的技巧;(4)生活和学习习惯的养成;(5)青春期情感与性教育;(6)家长的自我探索与自我成长;(7)情绪管理;(8)家庭建设的技巧训练等。详见表1。
2.5效果评价
采用自评与他评(伴侣、孩子)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多维评价方式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估。
3结果
3.1成员自评父母教养态度的前后测比较
参与家长成长团体的学员在父母教养态度量表前后测的平均数、标准差以及各分量表的得分差异比较见表2。
图表显示:在成员自评的父母教养态度的四个维度上,后测得分较前测均有非常显著的提升(p<0.001)。说明通过家长成长团体的学习,成员在教育子女上信心提升,变得更有把握;他们将对孩子行为问题的关注和纠偏转移到对自我的觉察以及对自我完善与成长的关注,更多地看到自己在教育孩子过程中应负的责任,把孩子从家庭或亲子冲突中替罪羊的位置上解放出来;接纳不完美,接受孩子有权犯错,允许孩子在错误中学习;更加尊重孩子和孩子的话语权,更愿意倾听子女的想法,重视亲子之间深入的交流与沟通。总体而言:家长成长团体对提升成员在教养子女的自信、归因、接纳和了解方面有积极正向的效果,对改变家长教养态度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促进作用。
3.2子女评价家长成员和伴侣亲子沟通的前后测比较
子女在家长参加成长团体之前和之后对其亲子沟通的状况进行评价,同时评价没有参加培训的伴侣,比较成员和伴侣在亲子沟通上的变化特点。结果如下页表3所示。
数据显示:在子女看来,家长在参加了成长团体之后开放式沟通明显增加,而问题式沟通显著减少(t=5.425,p<0.001; t=-5.677,p<0.001)。这种变化并没有在未参加团体的伴侣的开放式沟通上表现出来(t=0.615,p>0.05)。然而,未参加团体伴侣在问题式沟通上的后测得分较前测也有显著下降(t=-2.546,p<0.05)。这一现象可在成员的家庭作业和访谈中得到解释,几乎所有成员在学习后都会与伴侣分享学习内容,帮助伴侣增加对批评、指责、不一致表达等问题式沟通的觉察。虽然许多成员都表示曾告诉伴侣亲子沟通的方法和技巧,但对方大多一听了之,没有实践;有的尝试几次后,没有坚持。由于子女与父母沟通的方式是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父母偶尔一两次的沟通方式的变化,在大多数情况下,会让子女视为例外,而不认为父母真的变了(赵阿勐,2006;刘姿吟,1992)。因此,让孩子感受到父母沟通方式的变化是一个较长的过程,需要家长的坚持,将更多的“不知不觉”变为“后知后觉”,再转化为“先知先觉”和新常态下的“不知不觉”。学习时间和次数的设置对于这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有影响。一般认为的6~8次团体辅导次数在亲子沟通变量上的作用效应不显著(赵阿勐,2006)。
3.3家长成员、伴侣、子女评价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的前后测比较参与团体的家长成员以及伴侣和孩子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上的前后测得分之平均数、标准差以及各分量表得分的差异比较如表4所示。
比较发现: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方面,家长成员、孩子和伴侣的评分都在家长成员参加团体后显著提升(t=10.258, p<0.001;t =2.075, p<0.05;t =4.427,p<0.001;t =11.279,p<0.001;t =3.698,p<0.001;t=4.546, p<0.001)。其中,成员的改变最大,伴侣次之,子女第三。从家庭治疗的理念来看,当家长不再将孩子的行为作为关注的焦点,而是根据子女的偏差行为来审视隐藏在家庭系统中的问题、调整自己在家庭系统中的位置和角色时,家庭功能就会恢复,家庭便能正常运作,家庭成员的亲密度和面对冲突和危机的适应性都会得到改善。由于在青少年时期,同伴团体代替父母成为子女的重要他人,他们渴望独立,而不是和父母待在一块儿,同时伴侣朝夕相处的时机更多,因此伴侣对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变化的感受高于子女。
3.4学习时长和学习次数对团体效果的作用机制
3.4.1学习时长在父母教养态度、亲子沟通和家庭亲密度上的差异比较在父母教养态度方面,组内变量前后测(2个水平)、父母教养态度(4个水平)与组间变量学习时长(5个水平)构成的三因素方差分析显示:不存在三向交互作用(F=1.054,p=0.401),前后测与教养态度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两向交互作用(F=11.803,p=0.001)。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前后测得分在教养态度的四个维度上均有显著差异,其中,在自信维度上的提升最大(F=146.18,p=0.000),了解和接纳维度次之(F=88.68,p=0.000;F=74.28,p=0.000),归因维度的差异较小(F=58.09,p=0.000),见下页表5。
可见,家长成长团体对成员教养态度的最大改变是是增强了家长教育子女的信心,唤醒了家长对亲子沟通的重视和对子女错误行为更多客观全面的认识,允许、接纳孩子的不完美,让孩子在错误中学习。前后测与学习时长、教养态度与学习时长之间不存在两向交互作用(F=1.639,p=0.174;F=1.727,p=0.063)。此外,学习时长仅在教养态度的自信维度上效应显著(F=3.978,p<0.01)。多重比较发现:学习时长在两年以上的成员教养态度的改变显著高于半学期、一学期和一年的学员(p=0.001,p=0.006,p=0.022),一年半的显著高于半学期的(p=0.021)。这说明学习时间越长,家长教育子女的信心越足。而在归因、了解和接纳方面,家长可以通过半学期的学习达到教养态度的明显改变,与长期学习者的差异不显著(F=0.334,p=0.854;F=1.345,p=0.261;F=1.102,p=0.362)。
在开放式沟通和问题式沟通维度上,组内变量前后测(2个水平)、亲子沟通(2个水平)与组间变量学习时长(5个水平)构成的三因素方差分析显示:不存在三向交互作用(F=1.357,p=0.288),学习时长与前后测和亲子沟通之间均不存在两向交互作用(F=1.204,p=0.343; F=1.150,p=0.365),前后测与亲子沟通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两向交互作用(F=24.006,p=0.000)。简单效应分析发现,亲子沟通在前后测上均有显著差异(F=23.53,p=0.000;F=41.04,p=0.000),前后测得分在亲子沟通上均有显著变化(F=12.77,p=0.002;F=14.27,p=0.001),在问题式沟通上的改善略多。这似乎揭示了家长团体在亲子沟通方面的作用机制是先增加家长对问题式沟通的觉知与行为改变,而开放式沟通的同步提升还需要更多练习与巩固的时机,特别是让子女有所觉察。这也解释了之前研究中,8次活动方案的设计还不足以带来子女对父母沟通方式改变的稳定认知和感受(赵阿勐,2006)。本研究中18次的设置给成员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反思固有的、自动化的亲子沟通模式,学习使用并不断内化新的沟通方式,实现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上,组内变量前后测(2个水平)、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2个水平)与组间变量学习时长(5个水平)构成的三因素方差分析显示:不存在三向交互作用(F=1.811,p=0.136),学习时长与前后测、家庭亲密度,以及家庭亲密度与前后测之间均不存在两向交互作用(F=1.656,p=0.169;F=1.886,p=0.122;F=3.426,p=0.068),学习时长的主效应不显著(F=0.597,p=0.666)。这提示: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的变化可以通过半学期(8次左右)的学习达成。
3.4.2学习次数在父母教养态度、亲子沟通和家庭亲密度上的差异比较在父母教养态度方面,组内变量前后测(2个水平)、父母教养态度(4个水平)与组间变量学习次数(5个水平)构成的三因素方差分析显示:不存在三向交互作用(F=0.643,p=0.804),学习次数与前后测之间也不存在两向交互作用(F=1.791,p=0.140),教养态度与学习次数、前后测与学习次数之间均存在非常显著的两向交互作用(F=2.876,p=0.001;F=6.558, p=0.000)。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学习次数在教养态度的自信维度上有显著差异(F=4.556,p=0.002)。多重比较发现:15次以上的成员父母教养态度的改变显著高于3次以下、3~5次以及8~15次(p=0.029, p=0.010,p=0.001),但与5~8次的相比差异不显著(p=0.052);学习次数在教养态度的了解维度上也有显著差异(F=3.103,p=0.034)。多重比较发现:学习次数在15次以上的学员在了解维度的得分显著高于3~5次和5~8次(p=0.015,p=0.030),同时,15次以上与3次以下和8~15次之间不存在差异(p=0.113,p=0.104),详见表6。
可见,8次左右的学习次数可以给家长带来教育子女自信的显著提升,且与更长学习次数的学习者没有差异,这恰好说明成长团体的形式降低了家长对亲子教育问题的焦虑;团体动力帮助家长从更多视角,更客观、全面地看待子女的教育问题;带领者积极关注、关注积极的态度也提升了成员对教育子女的信心。在8~15次时教育自信的小幅滑落可以在家长作业和访谈中得到解释,当家长转变了教育观念,了解了孩子的年龄和心理特点以及学习了积极倾听、同理、一致性表达等亲子沟通技巧后(8次左右),教育子女的信心大增,同时在练习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和瓶颈,引发了家长对自我的反思,激发了他们想要了解自我、完善自我的渴望。当完成自我探索和自我成长的部分之后(15次左右),家长对家庭教育和对自我的信心同步提升。此外,在亲子沟通意愿和对子女了解程度的提升方面则需要比教育自信增加更长的学习次数(8次以上),3次以下学习带来的提升更多来自对亲子沟通的重视和沟通意愿的增加,对子女了解程度的提升是发生在8次以上的学习之后。
在开放式和问题式沟通维度上,组内变量前后测(2个水平)、亲子沟通(2个水平)与组间变量学习次数(5个水平)构成的三因素方差分析显示:不存在三向交互作用(F=2.493,p=0.091),前后测与学习次数、亲子沟通与学习次数之间均不存在两向交互作用(F=0.436,p=0.730;F=1.985,p=0.150),学习时长的主效应不显著(F=0.809,p=0.505),前后测与亲子沟通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两向交互作用(F=21.284,p=0.000)。
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上,学习次数在家庭亲密度前后测上的三项交互作用不显著(F=1.887,p=0.122)。学习次数在家庭适应性前后测上存在两向交互作用(F=3.901,p=0.006)。不同学习次数的学员在前测的家庭适应性上不存在显著差异(F=0.912,p=0.462),在后测的家庭适应性上差异显著(F=2.742,p=0.035)。进一步分析发现:学习次数在15次以上的学员的得分显著高于3~5次和5~8次(p=0.024,p=0.028);15次以上与3次以下和8~15次之间不存在差异(p=0.087,p=0.704)。8~15次与3~5和5~8次存在临界显著(p=0.06)。这显示,在家庭应对冲突方面,需要8次以上的学习次数才能让成员感到有能力处理家庭矛盾,应对家庭变化。
4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家长成长团体这一亲职教育培训形式在转变家长教育观念、改善父母教养态度和亲子沟通状况,以及促进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方面都产生了积极正向的作用。这种改变不仅使参与培训的家长成员受益,他们的伴侣、子女也同样感受到了父母沟通方式的改变,以及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的提升。家庭治疗的理念和研究数据的分析都说明,培训的效果是显著的。由此可见,采取教育性和发展性的家长成长团体方案来提高父母家庭教育的效能、改善亲子关系是可行的。
4.1家长成长团体的有效性分析
催生这一系列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团体辅导形式本身和带领者的辅导理念。
其一是提供情感支持。团体辅导营造了一种安全、信任、民主的氛围,带领者在活动中积极关注、倾听、同理成员,起到了辅导和示范的双重作用。来自其他成员的自我表露、积极反馈和欣赏、赞美、肯定,让家长成员感到被团体接纳、支持而感到温暖和平静,体验到归属感。访谈中,不少成员表示,每周一次的团体活动不仅让自己获得了心灵的成长,还体会到了回家的感觉。还有家长谈到,大家的赞美与肯定让其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
其二是获得普遍性发现。团体初期,家长成员最大的感受是“如释重负”。“啊!原来有这感觉的不止我一个人啊!”团体分享减轻了成员的心理负担,增强了安全感和解决问题的愿望。
其三是利用团体动力,重塑希望。课前调查发现,家长参与学习的心理是复杂和矛盾的。一方面,期待通过学习改善亲子关系;另一方面,长期低效,甚至无效的沟通模式和关系模式让家长感到挫败,信心明显不足。结果分析发现,与归因、了解、接纳三个父母教养态度的维度相比,家长在培训后家庭教育自信的提升是最大的。原因在于,团体辅导的形式很好地激发了家长的学习动机和改变动机,增强了家庭教育的自信。在分享环节,不同背景的成员在活动中不同角度的分享给每位成员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料和生活经验;目睹他人的成长对成员有所启发,看到身边的成员在努力转变教育观念、调整教养态度、尝试更多开放式沟通,同时亲子关系和家庭氛围慢慢得到改善,这对于有类似问题的成员产生了极大了激励和鼓舞性。成员在作业中写道:“我和他有类似的困难,他能做到,我也能。给自己一些时间,让‘奇迹慢慢发生。”通过直接观察、比较和模仿其他成员积极改变的行为,让成员意识到改变是有可能发生的,我是主动的,我是有能力去创造这些改变的。当家长内心的希望之火被点燃,他们就会更加积极地参与活动体验,努力尝试新方法,不断寻求自我突破。
其四是使用体验的、系统的、积极正向的方案设计和活动实施理念。方案设计以体验式为主,在辅导过程中带领者始终坚持系统的观念和积极正向的引导,帮助成员观察自己说了什么,以什么方式在说;留意自己听了什么,看了什么,有何选择。通过画家庭图谱帮助成员看到隐藏在家庭结构中深层次的、影响家庭运转的问题根源,从系统的角度科学合理地认识问题,并思考解决途径。
追踪整个过程,家长们从最初的解决孩子问题转向自我成长探索,从一开始的混沌无力到主动“内化”行为,从起初的抱怨冲突到温和而坚定,从以往托付他人、一劳永逸的假想到终身学习、主动经营的态度转变……每一次的家长作业记录了这点滴微小的改变和充满惊喜的领悟,家长和子女的改变持续发生。
4.2家长成长团体的剂量效应
研究数据分析显示,8次左右(半学期)的成长团体可以带来家长在父母教养态度的归因和接纳方面的积极改变,而对家庭教育自信和对子女了解程度的显著增加则发生在8次以后(8~15次),亲子沟通状况和家庭氛围的显著改善也需要8次以上的学习时间(8~15次,15次以上)。因此,在设计家长成长团体时,可以考虑适当延长辅导次数(8~15次)或采取俱乐部、网络会议等辅导以外的团体陪伴方式以催化并稳定家长团体的改善效果。这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来探讨。
4.3家长学习动机与学习收获的对比
从课前调查来看,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期望更多注重方法的学习,想要学到“搞定问题孩子”的方法,而不是教育观念的更新、教养态度的调整以及自我的提升与成长,因此容易表现出急躁、失落与挫败。随着团体活动的进行,家长们收获了与时俱进的家庭教育观念,尊重孩子,给予孩子自信、独立、为自己负责的权利;了解了孩子的成长规律与年龄特点;掌握了倾听的方法,学会了无条件的爱的表达与情绪管理。特别是在允许孩子和自己在错误中学习,以及明确了问题根源之后,家长逐渐将关注的焦点从教育孩子转到成长自己,他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亲子关系不是以爱的名义去操控,而是如何做最好的自己,用生命去影响生命。
5结论
(1)将家长成长团体辅导运用到亲职教育中是可行、有效的。
(2)家长成长团体对中学父母转变教育观念、调整教养态度、改善亲子沟通以及和谐家庭关系具有积极正面的作用,全面提升了家长家庭教育的素质和家庭建设的能力。
(3)家长家庭教育自信的稳定树立,对子女的了解以及亲子沟通和家庭氛围的改变需要更长时间。
参考文献:
雷雳, 王争艳, 李宏利. (2001). 亲子关系与亲子沟通. 教育研究, 6, 49-53.
李辉, 施江玉, 刘春燕. (2002). 团体心理辅导对家庭亲密度的促进.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6(7), 480-482.
李霞. (2013). 家长素质提升在父母效能训练中作用的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工程大学.
刘海鹰, 刘昕. (2008). 改善青少年亲子关系的团体实验研究.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53(3), 145-149.
刘姿吟. (1992). 父母效能系统训练方案实施效果之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彰化师范大学.
秦昊. (2010). 门诊心理治疗的效果评价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西南大学.
秦佑凤, 于丽霞, 郑晓边. (2008). 心理治疗剂量效果研究简介.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2(4), 316-318.
王华. (2013). 团体心理辅导改善家庭功能的实验研究. 中国特殊教育, 3, 69-72.
王争艳, 刘红云, 雷雳等. (2002). 家庭亲子沟通与儿童发展关系. 心理科学进展, 10(2), 192-198.
姚本先, 何军. (1994). 家庭因素对儿童社会化发展的研究综述. 心理发展与教育, 2, 44-48.
曾端真. (1994). 现实治疗模式的亲职教育方案. 台湾: 资商与辅导, 78(2), 29-30.
赵阿勐. (2006). 父母效能成长团体对小学高年级学生家长亲子沟通和教养态度的影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浙江师范大学.
栏目编辑/王晶晶 终校/丁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