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电影产业对古希腊神话的开发*
2015-08-22吴冰沁
吴冰沁
( 齐鲁师范学院 文学院,山东 济南,200013 )
好莱坞电影产业对古希腊神话的开发*
吴冰沁
( 齐鲁师范学院 文学院,山东 济南,200013 )
好莱坞一直将古希腊神话当作素材资源库,生产不同片种的神话电影。尤其是近50年来,“大片”以弘大的史诗规模与复杂精湛的电影技法创造了新浪漫神话。它们承载了美国保守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塑造出典型的美式超级英雄,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奇幻景观,并在全球赢得巨额利润。
古希腊神话;好莱坞大片;超级英雄;保守主义;全球利润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5.01.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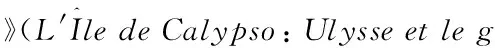
经典好莱坞时代曾是类型片的天下。类型片,如大卫·波德维尔所言,并非存在着超越一切、升华为固定类型的某种影片,是对一种制作模式的归纳,即众多影片共享一些类型化的特色,例如众多影片分享了令人愉快的歌舞桥段,另一些影片则分享了美国西部英雄的传奇*为了精细解读丹麦导演卡尔·德莱叶,波德维尔在其著作之首言简意赅地陈述了对经典好莱坞类型片的见解。参见[美]大卫·波德维尔著,柳青译:《德莱叶的电影》,长春:吉林出版责任集团责任有限公司,2012年,第9页。。在这两大类影片的外围电影,同样体现着大片场时代的电影观念、制片意志和价值模式。作为西方文化继承人的美国在面对希腊神话资源时,从一开始就更多地立足于产业的立场,在衡量古代文化遗产的开发价值时,有着与其欧洲“表亲”不一样的选择维度、改编策略和表现途径。
在希腊神话的汪洋大海中,特洛伊战争以其大事件、大冲突、大级别叙事起点最符合好莱坞向“大处”着眼的趣味、观念和标准。从默片时代直到当代,好莱坞为这场战争多次制片,几十年间陆续出品的《木马屠城记》*Helen of Troy,导演:罗伯特·怀斯。关于这个版本,本着翻译界的习惯,采纳中文通译名,下同。、《新木马屠城》、《特洛伊的妇女们》等同名、异名、相关题材的电影、电视电影片不下数十部*The Private Life of Helen of Troy,导演:亚历山大·柯达,影片制片于1927年或1928年。,如果再将以诸神为名的影片计入,则有数百部之多*在IMDB页面输入HERA(赫拉)或ZEUS(宙斯)等,每项都有近百部长短不一的影片,其他诸神被改编影视亦不少见。。如果说荷马的《伊利亚特》把一场延宕了10年的战争浓缩在最后51天,那么,好莱坞则是将一场战争放到几十年间反复重演,可称之为发生在银幕上的“特洛伊战争”。这场银幕上的战争与荷马的战争有何不同?与两千多年前的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有何不同?
一、亡国叙事与浪漫叙事
默片时代的尾声,好莱坞就有标准长度的影片《海伦在特洛伊的私人生活》。这是神话作为浪漫故事长片的题材在好莱坞的首度亮相,它也为好莱坞探察了一个无限丰富的资源库。1956年,华纳兄弟公司与意大利两家公司联合制作《木马屠城记》,以当时的“大片”规模搬演了这一经典。影片在给出片名Helen of Troy之后是东方风格的音乐、不列颠口音的旁白和特洛伊城自外而内的全景长镜头。好莱坞自经典时代就发现了视听语言中一个重要的技巧——美国口音活泼、清晰,同时又似乎显得不够典雅,缺少古风意趣。因此,每逢制作重大历史题材、史诗或文学经典选题时,不成文的惯例是,演员务必操不列颠口音,以示其“言说”来自欧陆,具有某种“正宗”的叙事意味,在听觉上令人产生“历史大叙事”的印象。*至于英国口音在好莱坞电影中具有“符号化”的价值,此处参照[法]让-卢普·布盖著,严敏译:《好莱坞 欧洲电影人之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木马屠城记》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包括:第一,按照神话的叙事逻辑,冲突的一切根源在于奥林匹斯山诸神的对立及其迁怒于凡人,电影叙事是否还要遵循这一前提?第二,大片场时代的好莱坞并不喜欢真正的悲剧,对这场战争的叙事立场既然立足于特洛伊一方,又该如何处理战争的悲剧性?第三,以美国清教伦理为道德基础,怎样面对帕里斯与海伦的关系?
旁白中的特洛伊——这个“人民勤劳”、爱好“美与和平”同时又城墙高筑的世俗国度,一艘即将起航的船正等待它的主人——特洛伊王子。场景进入皇宫,国王正主持一场议事:重要角色依次发言,但第一个正面镜头却是金发王子帕里斯*好莱坞视听语言经常借助外观造型隐含对人物的判断。头发的颜色具有给人物分等级的功能。依惯例,“金发少年”通常被预置了某种不言而喻的好感,而黑头发则次之。,他俯视正与之争论的黑发表亲,然后镜头才依次落脚于其父王、兄长、王后、王妃(拉辛《安德洛玛克》的主人公)。庙堂之上女人们虽有所言,但与男人们正在讨论的国家大事无关,故可以忽略不计。男人们争论的焦点则在于与斯巴达人的关系:兵戎相见,还是贸易往来?帕里斯——男主人公——坚持后者。这段众声喧哗的开场调度解决了一个基本问题——谁是故事的主人公?以谁的视点切入特洛伊的兵燹?
在《荷马史诗》中,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为了一时之争而分为两派,各选定人类的一座城池下赌注。除爱神、战神和掌管预言的阿波罗神站在特洛伊一方,其他众神对人类毫无感情立场,它们随机地站到了万神之神宙斯、天后赫拉以及智慧神雅典娜一方帮助希腊人,注定要毁灭人类世界中的特洛伊王国。神祇之争,不仅赋予事件以想象的趣味,而且从根本上取消了人类的自主性。当爱情的绚烂与战争的残酷都是神意时,荷马发出了对盲目战争和无辜人类的喟叹。但是,影片却对这种沉重感失去了耐心,它避重就轻,简化了特洛伊沦陷的悲剧前提——“众神的意志”。影片从恋人的角度讲述特洛伊的故事——年轻的王子帕里斯为了稳固王国的贸易安全而出使斯巴达,世俗的缘由导入了历史学家和通俗故事在解释特洛伊战争时所遵循的思路:利害分明、正邪两立的二元叙事。考虑到影片名为HelenofTroy——它应被译作《特洛伊的海伦》,影片定场戏的镜头调度就显得深思熟虑了。按照好莱坞制片的场面调度法则,角色出场方式将确定一部影片的核心人物和叙事框架。辩论的话题和镜头的运动围绕帕里斯展开,传统叙事中的大英雄赫克托尔退居角色群的外围,这表明故事并未依据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原框架作完整讲述。影片还另有侧重——基于尚未出场的重头人物海伦展开,按照角色/演员的关系配置规律,她要尽量迟些出现。所以在影片情节的第二段,帕里斯的破船漂到希腊海滩,在昏迷时刻他见到了从海水中走出的海伦。由此,影片完成了三个功能:其一,在众多标出姓名的核心人物中,海伦最后一个出场,从濒死的帕里斯视角远眺由远而近,这意味着影片的第一明星是海伦;在片尾,破城后的最后一个镜头也是海伦,而且是特写。影片首尾呼应,完全成为关于海伦的叙事;其二,海伦出场于海水,结束于海水,她仿照爱神的出现方式规定了影片的主题*据古希腊的神话,女神阿芙洛狄特自海水中出生,掌管爱情。影片引用这一手法表现海伦,显然有所喻意。:浪漫爱情。其三,海伦无爱的婚姻中的丈夫斯巴达王则偏执地促成希腊联军对特洛伊的大举讨伐,这个直接的人为动机被解释为战争起因。神话史诗中的帕里斯在希腊人的婚礼上拐走了海伦,战争由此开始;本片中二人相遇于身份明确之前,自然发生的爱情似乎优于无爱的婚姻,这就回避了帕里斯的道德尴尬。影片名正言顺地将伦理立场移到了帕里斯一方,并使特洛伊战争的残酷成了海伦浪漫叙事的砝码——古希腊悲剧成了好莱坞的伤感剧。这是好莱坞最受欢迎的片种之一,堪称票房摇钱树。
如果仅有一部《木马屠城记》,我们也许不能断言好莱坞总是将古希腊经典商业化,但是将这部影片中被征引最频繁的镜头画面放到好莱坞类型片中,它在视觉语言体系中的“陈述”特性及美学归属就显现出来:以性感著称的女明星群支撑着好莱坞叙事电影的半壁江山。她们在各类影片中的造型与镜头表现构成了伤感罗曼司类型电影的视觉中心,以至于我们在当时好莱坞影片中无数次看到这些在人物造型与场景方面几乎雷同的镜头。无论它们出自畅销小说、古希腊经典还是莎士比亚剧作,无论它们处于什么时代、什么背景,除了姓名,银幕上的人物都是如此的难分彼此。她们成就、强化的并非文学的经典,而是好莱坞伤感爱情的经典。
对比另一种银幕叙事——现代希腊人迈克尔·柯克杨尼斯以欧里庇得斯的舞台剧为基础执导的影片《特洛伊的妇女们》*Troy women,1971,凯瑟琳·赫本主演,英国、希腊、美国联合制作。,将加深对好莱坞商业操作的理解。对于古典悲剧的意义与价值,柯杨尼斯有着深刻的洞察。早在1960年代,他就以古希腊悲剧导演的身份活跃在欧美电影和戏剧舞台上。其《伊菲吉妮娅》、《伊莱克特拉》分别表现人类的命运悲剧在俄狄浦斯的儿女与英雄奥德赛的儿女们身上的延续,与其《特洛伊的女人们》共同奠定了柯杨尼斯在欧洲艺术电影中牢固的地位。在接受《电影》月刊杂志的采访时,他谈到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与人类战争的愚蠢、屠杀人民的野蛮之间的关系及其本人对这一切的强烈感受。这一切生成了导演诚实而自觉的艺术表达动机和富于独创性的电影语言。1971年的凯瑟琳·赫本出演柯杨尼斯影片中的特洛伊王后赫库巴,一个因亡国、亡子、亡孙而悲痛欲绝的老妇,在她的身边是大名鼎鼎的公主卡桑德拉、王妃安德洛玛克与海伦——她们黑衣褴褛,沦落为奴。影片没有丝毫“造星”的企图,不为女明星们安排任何机会去施展王后的威仪、王妃的浪漫、公主的甜美。它没有一处赏心悦目、讨好卖乖的桥段,不仅使人看到从古到今战争的残酷,更让人回到经典的源头去重新思考古人对其自身愚蠢的反省。这种反省出现在冷战局势日渐严峻的1960-1970年代,更令影片具有与众不同的思想力量。另一位希腊战后著名导演乔治·加维拉斯在1961年导演的《安提戈涅》*Yorgos Javellas,亦名George Tzavellas,1916-1976。本片1961年提名金熊奖,同年获得旧金山电影节金门奖。则依据索福克勒斯同名原作的内容,呈现了荷马史诗主要人物俄狄浦斯王的女儿安提戈涅在个人情感与国王意志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悲剧”,人称“悲剧之后的悲剧”。在讨论悲剧中的女性形象时,诺斯罗普·弗莱曾指出:“在希腊悲剧中,女性通常是悲剧情境的牺牲者而不是发动者,因此,女性增强了悲剧情绪而不是悲剧情节。”*[加拿大]诺斯罗普·弗莱著,孟祥春译:《世俗的经典:传奇故事结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5页。他提醒我们回过头来检验同为希腊神话史诗改编的不同版本的电影《木马屠城记》中的海伦与赫库巴、伊莱克特拉以及安提戈涅等女性形象在各自文本中的表意功能——尊崇悲剧经典的希腊导演们将他们的女主人公置于电影客观的视听语言系统中,在叙事、陈情、达意等不同维度上始终保持着适当的平衡。但好莱坞的海伦则被视听语言推向感官体验的最前端,在进入她的命运陈述之前和陈述的过程中始终强化观众对她的凝视一种视觉的消费,因此海伦不是一个关于人类命运的悲剧,而是一则男欢女爱的伤感小品。将这一影片置于经典时期好莱坞同类型电影群中,海伦的真实身份会因为其“同伴”而更显眼——在由费雯丽、伊莉莎白·泰勒、玛丽莲·梦露挑大梁的好莱坞,银幕上的女性少有能逃脱被观看命运的,明星及其扮演的角色之间的“互文”仅用一个形容词——性感,就足够涵盖她们的价值。
在1956年被讲述之后,海伦又出现在好莱坞后续电视电影等形式的衍生品中。它们不仅延续了1956年好莱坞电影版的同名,同时也继续制作“尤物”。原片又制作为DVD向家庭放映市场发行至今。比较而言,柯杨尼斯的《特洛伊的女人》在上映票房上根本无法冲出《木马屠城记》的合围。不仅如此,早于《特洛伊的女人》的《伊菲吉妮娅》、《伊莱克特拉》、《安提戈涅》以及法国、德国1971合作制片的同名电视电影《安提戈涅》——这些致力于战争、人性问题的严肃思考每每出自导演们长久而独立的思想探索,虽然在文化价值、美学意义上更胜一筹,却因票房上不敌一部娱乐世界的世俗伤感剧《木马屠城记》而纷纷堙没。海伦——这个著名的女性,终于被添加到好莱坞娱乐业的尤物行列,在多种视觉艺术的形态中成为一个被凝视的中心并渐趋稳定。
二、大英雄的降格
作为艺术,古希腊人创造的神谱与英雄传奇形象起初只有一处不同——身份。神是不朽的,而英雄迟早要走向死亡。对人类而言,真正迷人的正是那些终究面临死亡的传奇英雄。希腊人对人的生命(即便他是英雄)有着“一揽子式的”深刻体验和理解:传奇一生注定与惨烈之死捆绑在一起。似乎愈是英雄,其死亡愈是寓意深长;或者相反,一切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都在生命终结时刻被扯平。那么,作为终结的死亡在叙事艺术中究竟有多么重要?古希腊人以赫拉克勒斯、伊阿宋、阿喀琉斯、珀修斯、奥德赛的多种英雄谱给出了参照:他们的传奇叙事遵循着与生命过程基本一致的朴素形态,有始有终。在开端和结局——天平的两端,一端是高贵的血统、力量、智慧、勇气、野心;另一端则是对他人的忽略、自身的贪婪、对权力的欲望和注定而不自知的终极缺陷。后人尽可对神话的完整范式采取任何形式去截取,但这并不表明神话本身怎样,只表明截取者自己的意图和倾向。
就《木马屠城记》断言好莱坞不需要重量级神话并不准确。相反,好莱坞一定要建造属于自己的神话殿堂,借此打造自己的英雄丰碑——以古典英雄的名义。只不过,它一定要供奉美国人心目中的神祇和英雄,要以好莱坞的方式截取英雄神话,建立神谱影像,并持续其祭拜。由此,不同的类型片成为好莱坞式英雄的影像神龛。
在古希腊神话和悲剧中,关于赫拉克勒斯的原始叙事包含着非常矛盾的内容:作为神灵宙斯与凡人的混血后裔,他天生力大无比,但因受到内在的、不可控力量的疯狂袭击,他会有超人的、甚至残暴到可怕的行为,也可能倏忽变得无比虚弱。因而具有盖世神功的大英雄终生在深刻自责。这是只有人类血统才会遭遇的致命的毁灭——在各种传奇后面,神话还紧跟着“后英雄叙事”:如此大英雄竟死于不足与外人道的私人情感纠葛,这就是在他的生命中还注定要经历伊阿宋式的、基于命运的无奈;另外,英雄的后裔则在权力欲望的驱使下彻底放弃了手足之谊,兄弟阋墙,这是神话保留的富有启示意味的完整结尾。
新兴的电影艺术在早期就曾向这位大力神致意。目前可看到的影像中,首先值得瞩目的是1957至1964年间,意大利出品的富有意大利传统古装片史诗风格的《赫拉克勒斯》*它同时还是意大利专为宽银幕放映而制作的影片。以及后续系列《挣开锁链的大力神》(HerculesUnchained,1959)和后来为电视台提供的系列片《大力神挑战九头怪》(Herculesvs.theHydra,1960)、《大力神在鬼蜮》(HerculesintheHauntedWorld,1961)以及《大力神与女俘》(HerculesandtheCaptiveWomen,1961)等影片。它们杂糅了希腊神话中各种英雄叙事,当然也不会缺少爱情戏份,其中《大力神与女俘》就表现了导致英雄意外死亡的故事。在战后意大利,古希腊-罗马神话与历史素材是电影制作的常规选题。这些影片往往有一贯的美学特征:豪华的装饰,壮观的场景,大尺幅时空开阖的故事叙事。似乎不如此便配不上或对不起古代文化遗产。然而遗憾的是,面对这些古典素材的意大利人既不是擅长史诗电影、富有贵族气派的导演维斯康蒂,也不是冷峻内敛的导演安东尼奥尼,更不是锐利而激进的诗人导演帕索里尼。相反,接管这批资源的是电影产业界的意大利投资商人。以其思想和艺术的水准而言,他们无法和本国那些独特而执着的作者、导演相提并论。以其产业运作的魄力和能力更是遇到了强大的对手——正处在1956至1966年古装片制作波段上的好莱坞。但他们使美国人意识到,在古希腊神话与悲剧经典遗产中,大力神早期的英雄传奇充满不可多得的积极力量。比之另一个传奇英雄伊阿宋,他更单纯、更富于青春力量。
既然是一个如此丰富的传奇金矿,美国人就不会袖手旁观,任由这么受追捧的英雄拘于意大利语电影市场上。精明的美国制片人为华纳兄弟公司争取到了意大利影片《赫拉克勒斯》在美国纽约地区的发行权,以英语配音在纽约地区175家影院独家上映。尽管《纽约时报》的影评人理查德·纳森后来不无苛刻地说:赫拉克勒斯的英语配音有着“银行职员腔”,但意大利人的赫拉克勒斯还是在美国市场起到了试金石的作用。当时的纽约媒体认为,观众对此片还是很感兴趣的*影片上映时,《纽约时报》有专版报道。。而且,纳森同时承认,这位来自意大利的大力神有着像美国流行文化中的传奇形象人猿泰山一般的“大块头肌肉”,能战胜一切怪物,这正是1950-1960年代热衷于健美运动的美国人的趣味。事实上,我们很快就能看到这一点:在任何可以引来财富的资源面前,美国人都不会犹豫。影评人纳森之所以认定意大利影片仅够“希腊学生看”*New York Times, July 23, 1959。,原因就在于它还缺少能逗乐美国观众的东西。其实,这位影评人差不多提到了“英雄大力士”在美国银幕上所应具有的一切要素:一个年轻而乐呵的大乖,他要有一连串的英雄行为,能理解足够的幽默并遇到些许的浪漫。于是美国人开始行动,经过重新处理,很快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大力神系列”:《赫拉克勒斯的爱情冒险》、《赫拉克勒斯抗击月亮人》、《赫拉克勒斯漫游圣经》、《赫拉克勒斯与特洛伊公主》——连篇累牍的影视制品冲击大小银幕。无论人们怎样和这位天神胡闹、搞笑,美国观众就像对待西部片的英雄牛仔一样一概热烈欢迎。除了故事之外,美国人还征用了意大利电影的一切:历史传奇、经典、电影感觉、素材、制片厂的电影棚以及电影的资源库。曾执导过《荒野大镖客》、《黄金双镖客》、《黄金三镖客》、《西部往事》以及《美国往事》等片的意大利著名导演莱昂内(Sergio Leone)洞悉了古代神话英雄和好莱坞西部片主人公内在的一致性。他说:“阿伽门农、埃阿斯、赫克托尔是过去的西部牛仔的原型: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独立而英勇,为人不够正直;而西部片中的人物被导演搬进了神话世界……加里·库珀(Gary Cooper)就是赫克托尔。”*[法]洛朗斯·斯基法诺著,王竹雅译:《1945年以来的意大利电影》,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05-106页。
我们先以《大力神在纽约》*Hercules in New York,1969。一片为例。那个后来广为人知的明星阿诺德·施瓦辛格在1969年以健美的“欧洲先生”之名移民美国,凭“发达的肌肉,健美的体型”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赫拉克勒斯——大力神的最佳人选。仅从外形上人们就可以看出美国大力神与意大利大力神的差距,这可是崇尚运动的美国人衡量男性不可或缺的标准之一。大力神将美国人对力量的崇拜从人猿泰山身上成功地转向了人*根据希腊神话和该影片片头的剧情,赫拉克勒斯是宙斯与人类女性阿尔克墨涅的后代。这解释了他的神性和对人类的亲和力的由来。,他挂满全身的肌肉是美国人自信而乐观、强健而坦率的身体式的言说。至于施瓦辛格瓮声瓮气的口音则暗合了赫拉克勒斯在神话中总摆脱不掉的“外乡人”标记——憨厚到略嫌笨拙但不让人厌烦的性格。
赫拉克勒斯首先要“为王位而战”。与希腊神话中很多别的英雄为“夺取”什么而奋战略有不同,大力神是仅凭自己神性的优越出身便要在人世“夺取”一个王位。宙斯的血统加上赫拉的哺乳,这个被神祇遗弃的鲁莽大个子在尘世显得雄心勃勃,超人一等。虽然那些英勇的举动因为“为民除害”而被屡屡冠以“美德”之名,但究其根源,赫拉克勒斯不甘心久做他人的臣民,他是个偶尔被欲望蛊惑得狂暴的野心家,正要夺取王位。在神话叙事中,国王对他虽有无奈的允诺,但也有效地拖延了这一过程,赫拉克勒斯不停歇的英勇行动也证实他对真正的王位反而非常耐心,并没有强取豪夺。因此,他的叙事是一个关于凭借出身自动升格的故事,是朝着奥林匹斯山众神的回归。
可是,现代美国人不会像古代希腊人那样虔敬向神。在电影上,神不仅要按照美国人的意愿和趣味举手投足,如有必要,它们还要被重新规划关系。比如婴儿赫拉克勒斯在神话中先是被自己的母亲丢弃,随后又被赫拉丢弃,而在电影中他却有宽容慈爱的天父宙斯和亲切温和的天后母亲——一个现代美国的理想家庭,一个伦理关系的乌托邦。高贵与世俗的天然对峙历来都是同时在身份域与道德域合并展开的:来自神界的必定高贵,原本凡界的必定鄙俗。大力神在空中飞越一架航行中的泛美航空公司的喷气式飞机,一位老太太惊呼舷窗外惊鸿一瞥中的那个“人”是那么“英俊”、“漂亮”。我们看到了大力神来自神灵的超能力,同时看到与生俱来的诚实、坦率、友善、快乐。这是好莱坞对大力神的品质定位。来到纽约的大力神一再对人说:“我从希腊来”,“我是宙斯的儿子”,“我是大力神”——他非常诚实;纽约人则认为这位大个子“移民”“健壮”而“幽默”。神的高贵使他对人的鄙俗无从觉察,为“坏人使坏”提供了人性化的机会和推进情节发展的动力;同时,在天神的希腊语和纽约凡人的英语对话时,影片又运用了两种语言“错层”交流的小技巧,由此产生了各种有趣的误解与误会,笑点自然引出。无形中赫拉克勒斯变成了一位为凡人——为观众带来快乐的“文丑”。神话中的大力神四处砍杀,一步步走向奥林匹斯山,而电影中的纽约“历险”实质上已然“降格”。
在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希腊神话传奇与经典悲剧中,一些艺术形象已然为当代文化所接管,例如特洛伊战争传奇中的人物群。她们在原典中的凡人身份、悲剧命运和巨大的、爆发式的情感力量引发的是“净化”与“崇高”,这是形象本身的升格,在世世代代的艺术传承中逐渐获得了稳定的属性。凡人安德洛玛克、安提戈涅、伊莱克特拉以及愤怒的美狄亚,她们都有无法更动的情感并因其他人物的行动力在不断累积而被逐步推向毁灭,生命在爆发的瞬间定格,毁灭获得了某种神圣的意味。相反,好莱坞影片中赫拉克勒斯的神性身份规定了他与纽约人的对峙无论如何不会改变对方的属性,天神始终高贵,凡俗也将始终凡俗。无论在纽约胡闹多久,大力神永远像当初到来时那样与纽约凡人相处,接受纽约人心理标尺的度量。天神内心浩浩荡荡的纯洁是凡人无法想象的,但他的孔武有力的外表和思无邪的行动却是可见的,甚至看起来像个令他自己都觉得尴尬的憨大个。这是形象本身的降格;同时,只要制片人乐意,大力神可以随意去往任何一个社区,出现在任何一个街角,起始一段新的、但与上次行动却是等价平行的滑稽叙事。每个章回等价平行,使大力神的叙事不同于人们所熟悉的希腊神话的形象。美国人所选择的大力神必须无忧无虑,只有“给定的性格特征”,他无法实现任何内在的变化,因此可以没完没了地游历下去。票房高,可以接着拍;观众稍有变脸,制片就到此为止。它可以在任何一集上结束整个系列,而每个续集的内容又都可以作为独立单元再次使用。这个最合乎经济法则的制片策略,使好莱坞此后的系列产品圈钱圈到最后一毫厘,如同“超人”、“蜘蛛侠”、“蝙蝠侠”、“忍者”以及“哈利波特”。好莱坞的市场让赫拉克勒斯从貌似英雄的地位降格到喜剧处境中,他彻底沦落成了一个为着世俗的乐趣而存在的大活宝。
大活宝是这样赢得票房的——在最富有操作性的层面上,好莱坞电影技巧发挥了效力。它在个性定位、角色配置、情节设置等方面确保了大力神降格叙事的可爱与呆萌。比较而言,大力神尽管贵为天神之后裔,品行纯洁,但他本身实在缺少讨人喜爱的性格,在喜剧叙事中,其作用仅在于以超人的力量所引发的事端。是这些奇迹事端令人称奇,而不是丰满的人性引人入胜。因此,在他周围必定要有懦弱而善良的“椒盐”、聪颖而美丽的“海伦”、犹豫而迂腐的“教授”与凶残无度的“黑帮”、死皮赖脸的“无赖”、嬉皮笑脸的“骗子”。正是这群个性突出的随行者分立在高贵而憨厚的大力神的正邪两侧,使影片鲜活有趣。如果说在喜剧叙事中大力神是基调和力度,那么喜剧配角们则是精心演绎的音色和旋律。这些尽职尽责的“帮闲”与“帮凶”活灵活现,确保来自“奥林匹斯山众神”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顺理成章地成为最讨美国人喜爱的“英雄”。影片实际是一出欢乐喜剧,一出由神降格为人的杂耍。好莱坞从古希腊经典中攫取的恰恰不是悲剧,而是喜剧。喜剧还发生在明星个人身上。1969年逛遍了纽约的大力神——奥地利移民来的健美运动员阿诺德·施瓦辛格在欧美两地一举成名,成为好莱坞最成功的电影明星之一,也让好莱坞电影产业看到了一种身体崇拜的“强汉”类型电影,而其他形态的影视制作则从大力神身上看到继续衍生的叙事资源,它们都将继续提取神话经典千年不尽的产能。
对大力神资源作日常化提取的是电视业。在1950—1970年代的电影放映业低谷期间,美国电视网需要大量节目填充其各种频道的时间段,人们以赫拉克勒斯为素材拍了多部专供电视播出的电视电影,平均制作周期不足一年,即拍一部放一部,选题之频繁可见人们有多喜欢这位尊神。当然,这些影片并非全部来自赫拉克勒斯的神话,个别影片属于借名,借题发挥。*例如《三丑遇到大力神》(The Three Stooges Meet Hercules,1962)。在这个制作周期里,貌似被“英雄崇拜”推动着的大力神浑然不觉地进入了他的黄金时代。
在讨论歌舞片时沙茨曾指出,所有的类型电影——并且是所有的好莱坞电影,在不同程度上——都含有乌托邦的允诺,并投射出一个可能的、秩序井然的社区乌托邦愿景。*[美]托马斯·沙茨著,冯欣译:《好莱坞类型电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4页。古希腊的赫拉克勒斯传奇是好莱坞一个令人激奋的重要愿景,构成美国文化核心之一的通用观念就是他的人格。被作为产业资源开发的希腊神话要最大程度地契合美国文化观念,让尽可能多的观众易于理解、乐于接受这些视听化的英雄传奇,并将其中的一切价值默认为“自我愿景”。只有这样,这些资源才有可能转化为当代文化的产能,实现产业利益的最大化。至于这种开发是否还能保持原典的文化属性,好莱坞投资方似乎不太予以考虑。如有必要,他们还可以做更大的变动。1994年,哥伦比亚公司出品了电视剧《大力神与亚马逊女人》后,1995至1999年包括联合公司在内的五家美国公司和两家新西兰公司,共七家公司联合制作了80集电视连续剧《大力士的传奇旅程》(Hercules:TheLendendaryJourneys)并由德国公司发行。作为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强大同盟,电视电影的制作周期短,编—导—播过程中完全以观众的收视率为核心。在长达数年的播出过程中,它更加灵活多变,完全摆脱了古典神话的内容、情节,风格随时调整,先后融合了魔幻、探险、言情、神怪等类型片的趣味,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杂耍故事集成的方式,成功地占据收视率上位,随后又凭借英语的传播优势,发行到欧洲,在多国电视台播出。这一制作/播出周期过后,2005年,美国Hallmark Entertainment公司与澳大利亚Photon VFX公司、新西兰Photon NZFX公司(visual effects)和 Digital Post Ltd公司(post-production)再次联手推出电视电影《大力神》(Hercules)并由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三国共同合作发行,其市场直接覆盖整个英语地区。
利润带给投资人的鼓舞是巨大的。1997年迪斯尼推出的动画版《大力神》*即Hercules。香港等地译“海格力斯”,回归之后,一些国外影片的译名有了多种译法,故本片又译《赫拉克勒斯》、《大力士赫拉克勒斯》或《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等,网络上的译名更多,但似更随意。本文依翻译界传统仍用赫拉克勒斯之名。接力续写施瓦辛格启动的大力神“英雄”叙事,并使经典英雄更加美国化了——迪斯尼卡通,它辅以歌舞片的形式处理这一资源,赫拉克勒斯又变成了少年英雄的人格愿景。
卡通所聚焦的,被片中丑角“菲罗斯”一言以蔽之概括为大力神“打怪兽,救美女,回老家”。两部影片同样都遮蔽了主人公在神话原典中冷酷的出身渊源和最终不无悲剧意味的结局。卡通片比真人片来得更温情化:大力神不是神话中那个被亲生母亲遗弃又被妒忌的赫拉陷害的婴儿,而是慈父宙斯与天后赫拉无比宠爱的乖宝宝。只是为了成长的需要,他来到人间,所做的一切无外乎确立自我,取得父母(现行社会秩序与正统观念)的认可,与家人和解。他与宙斯神族所代表的整个世界的和解并非在死后,而是在一系列神勇行动之后立刻得到承认——这本是美国电影最保守、最安全的道德观念和流行文化主题,也是好莱坞商业片欢乐电影的基调。与施瓦辛格真人版赫拉克勒斯比较,卡通版《大力神》绘制出的金发大力神有着更大的蓝眼睛、因为总是乐呵呵的所以咧得更大的嘴巴,那副坦荡少年的做派比演员施瓦辛格更为夸张,除了其符合青少年特征的头高比等要素之外,片中宙斯特别赞叹了他“强壮的下颚”。这一造型几乎将美国人心目中一个健壮青年的体态夸张到了极致,正如对女性凹凸体态的想象被夸张到极致一样,它们(似乎只能用“它们”这一代词,才能传达出视觉符号的“物性”)从人物造型上使叙事转向了成长喜剧。同时,四位配音演员分别精心处理了赫拉克勒斯不同年龄段的声音,其中主演多部普通真人电影的演员泰特·多诺万有意识控制声线,为角色注入了被影评人安德里亚·德亚称为不染“街痞腔”的、“孩子气的”、“纯洁无辜”“大个子”的品质。这些特征恰是好莱坞电影对“好男孩”的基本把握,而不是塑造一个成年人形象的出发点。
在角色配置和造型上,卡通版还特意加强了周边角色——朋友:“神马”与“导师”*好莱坞卡通片最洗练的喜剧手法之一,是配角/丑角的精心塑造和配置。在少年成长主题中,他们/它们一般在自然属性、天然条件方面劣于主人公,但无条件地忠诚,且与主人公同性别或中性,起到玩伴和见证人的功能。即便是异性配角,也至多是建立友谊而不承担性别的叙事意义。。这两个油嘴滑舌、插科打诨的角色一老一少,强化了施瓦辛格版的配角“椒盐”的丑角功能,而且卡通片的视觉节奏使其表情与举手投足更为夸张,喜剧特性更为鲜明。值得一提的还有,在影片的首尾,百老汇歌舞形式出现的所谓“缪斯女神”既取代了经典悲剧的歌队,还取代了故事的传统讲述人(在史诗中讲述人被认为是荷马,在神话中则是全能的第三叙事人,如无特别指出,这个叙事人通常为男性)。九位缪斯的歌声、歌词、舞蹈毫无例外地都在“甜妞”的范式中,如同NBA赛场上的啦啦队一样,她们在每个叙事段落的间歇时间出镜载歌载舞,引吭高歌,为故事穿针引线,为“英雄”喝彩,为影片掌控节奏。于是,大力神的成长叙事在打斗和欢乐歌舞中交替进行,彻底变成了喜剧大神搞笑串烧,强迫观众接受了这个干净得出奇的乖大个儿。没有谁指望这样的影片内容与这个世界的实际经验吻合,但人们还是乐于为这简单而纯粹的欢愉付出钞票——据MTIME网的不完全统计,1997年迪斯尼版本的《大力神》成本8500万美元,北美票房9900万美元,全球票房2.52亿美元——更多的钱是从美国之外挣来的。
大力神在好莱坞的降格到1997的卡通片还没有终止,那些在影院放映时格外有效的视听创造及其产值效应还远未穷尽。1998年,迪斯尼旗下电视公司在此版本的基础上又制作推出了每周六早上播放的电视版卡通赫拉克勒斯系列,这套节目每集时长30分钟,人物与情节继续降格,几近中学生年龄段,并在原卡通电影的基础上延续运作52周以上。不仅如此,美国的泛影视产业——所有使用银幕、屏幕、显示器的媒体,例如单机或联机的电子游戏、电视连续卡通、互联网flash等传播平台都还在继续开发着这一资源,这些产品无不致力于向美国的海外市场拓展。也许,迪斯尼最典型地体现了好莱坞精髓——分明是在借希腊诸神讲述“美国的神系传说”,而且将希腊诸神变成了好莱坞电影“产业神话”的“硬通货”之一。回过头来再看引发了这一切的意大利大力神系列,则显见其产业后续开发能力的不足,其悄无声息,鲜为人知,令人遗憾。当人们无法抵抗好莱坞的强大势力时,只好听任它的快乐,接受它制造的微醺。
三、伊阿宋传奇与被屏蔽的美狄亚
伊阿宋传奇是好莱坞热衷开发的另一个资源,在一系列的开发中被肆无忌惮地注入了美式文化观念。
从神话所铺陈的伊阿宋英雄谱中,人们不难体会到英雄的豪迈和讲述者的敬慕。可这只是伊阿宋传奇的开端,接下去就是美狄亚的加盟和他们一起的砍砍杀杀:杀父,杀兄,杀子,直至那最可怕的事实:夫妻俩先后自杀。从有关伊阿宋的完整故事中,希腊神话和古典悲剧都看到了人类共有的野蛮、粗暴、兽性,它们只是讲述但并不过多评析。这种看似无意义的冷静不仅仅留存在文字中,还与远古的英雄行为捆绑在一起,令人毛骨悚然。人们有理由回避这些被动继承下来的残忍,也有理由对叙事的经典范式作现代化的修改,以适应现实心理诉求。但问题仍然要提出:第一,这些反复重生的资源发挥了怎样的效应?第二,在神话谱系中,老辈的伊阿宋在英雄壮举上原本丝毫不亚于赫拉克勒斯,甚至,在阿尔戈船上,大力神要接受伊阿宋的指挥,可这一切都被美狄亚的发飙毁掉了。假如没有美狄亚的决绝,伊阿宋不会成为悲剧的主人公;在神话那数不清的英雄中伊阿宋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可以断言,由于关联了女性的命运,英雄们的游历在开端时刻越神奇,在结束时刻就越沉痛。似乎英雄之所以历经艰难万险,就是为了那致命的最后一刻——没有这一刻,此前的神勇都失去了美学价值。
伊阿宋与美狄亚的故事数千年来一直是考量艺术家、文学家乃至思想家功底的范本:故事80%的篇幅在讲述伊阿宋神勇的传奇,可以作为喜剧陶醉于此,但它只是在为后面20%做铺垫,由漫长的喜剧导入戛然而止的悲剧。因此,伊阿宋的故事的核心实质上是美狄亚。不将故事最后的美狄亚处理好,就无法正常讲述伊阿宋。现代欧洲电影人中最富有激进个性的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丹麦导演卡尔·德莱叶*“德莱叶是电影艺术的伟大天才之一,如果缺乏对这个人及其影片的理解,任何电影史都是不完整的。”参见[美]吉恩·德拉姆和戴尔·德拉姆著,吉晓倩译:《受难中的激情·前言》,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与拉尔斯·冯·特里尔都曾向这一沉重的老故事发起对话,或像古希腊的天才悲剧家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一样,直接切入英雄故事的真正核心,将美狄亚的生命传奇作为个人生命的自我言说的契机。他们的影像都落脚于主人公传奇的终点——人的内心坍塌——被世界彻底压垮的时刻。在导演的操作层面上,德莱叶和帕索里尼甚至同时想到这世界只有一个人能担当美狄亚,即当时世界歌剧界的第一女高音,墨西哥歌剧演员玛利亚·塔拉斯。塔拉斯“声誉显赫又喜怒无常”,在德莱叶看来非常吻合他对美狄亚“未开化民族的狂野”性格的想象,但是美狄亚绝不仅仅能满足德莱叶对古希腊神话的好奇,她还内在地承担着德莱叶对宗教意义的探索,也由于这份有关灵魂的主题过于深重,直至去世,德莱叶也没轻易动手促成拍摄。*塔拉斯只为帕索里尼一人出演了美狄亚,那是无神论的诗人帕索里尼“神话三部曲”之一。1987年,作为晚生的特里尔接过了德莱叶的剧本将美狄亚带上了银幕——完成了德莱叶未竟的“从美学层面至工业体系——带来的狂风暴雨般的冲击”*[美]大卫·波德维尔著,柳青译:《德莱叶的电影》,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第4页。。无论英雄伊阿宋还是公主美狄亚,都处于命运悲剧的强势逼迫下,无怪乎帕索里尼的美狄亚同样沉闷粗砺得与利比亚荒漠融为一体,凝重得令人难以呼吸,无法忍受。美狄亚的这些影像,将看似约定俗成的伊阿宋英雄传奇带回到真正的荒蛮时空,挑战我们对神话、英雄、悲剧、电影的想象力和理解力。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选定了几种版本,从技术形态、电影类型的角度分别加以考察,比较英雄伊阿宋从1963年到2010年在好莱坞的30年传奇。
较早的电影记忆可以从1963年哥伦比亚公司出品的JasonandtheArgonauts开始*1963年以真人与定格动画混合制作的Jason and the Argonauts在中国本应通译为《伊阿宋与阿尔戈英雄传》,但在互联网上却更多见《杰逊王子战群妖》之名。“杰逊”之译出自港台,近粤语和闽南语发音,考虑到当时港台地区与大陆体制的差异,可推断本片应由港台率先引进,后以此片名流入大陆。1960-1970年代的香港正值功夫片黄金时期,Jason and the Argonauts非常符合当时港人对影片“动作”的趣味。也许在译者眼里片中群雄业绩如孙悟空一般,其历险被译作孩童般的“战群妖”就不奇怪了。。这是哥伦比亚制片方给经典高调的各路英雄的定位:一部B级片。没有人指望好莱坞的B级电影解决任何重要的精神诉求,B级电影不可替代之处就是为人的垃圾状态提供视听填充。毕竟,“整个精神像垃圾一样”的情景,占多数人的多数时间,于是我们看到了这部没有美狄亚发飙的阿尔戈英雄记。与赫拉克勒斯完全一样,推进这一进程的动力是伊阿宋的个人欲望:夺回王位。在奔向王位的途中他要路过各种怪物的领地——奇形怪状的男女老少组成的群妖陆续出现。对主人公而言,这些怪物之间彼此达成的是聚合关系,无论增删哪一个都不会破坏整个历程的逻辑关联,因而每一个怪物都不是叙事的有机组织,伊阿宋和阿尔戈船上的英雄们只是逐一地打败它们。在好莱坞类型电影中,“打斗片”或“动作片”一直没有明确的概念外延。它可以存在于各种题材、主题的影片中,却在电影实践中一直发挥着多元作用。当“动作”本身就是独立的愉快体验、就是观影的目标时,芝加哥的黑帮、丛林里的大猩猩、荒蛮之地的国王,无论其身份怎样、扮相怎样,无论其遭受的是围攻还是逐个单挑,本质上都是在娱乐观众。
如果说1963年的B级片《阿尔戈英雄传》还因为定格动画的妖怪们显得有些天真烂漫,那么,2000年的JasonandtheArgonauts就重复了立意的庸常、结构上的残缺以及制作的粗疏。这部由美国Hallmark Entertainment公司投资3千万美元拍摄的《阿尔戈英雄传》分两集,主要面向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的电视网发行播出并供应DVD零售市场*本片也外销到了中国,曾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出。。与1963年魔斗动作片完全相同的是,它也将伊阿宋一路的砍杀作为视觉主叙事,情节同样截止于伊阿宋获取王位,美狄亚仍然在伊阿宋的命运之外;与老版本路数不同的是,影片在一些细节处理上试图自圆其说,以弥补情感线索上的不足。比如,在关键人物——美狄亚的造型上我们看到导演的用心,它比1963年的版本更有意强调了美狄亚的“异邦”和“蛮族”特征。在美国清教传统下,出现在大众银幕上的主人公要尽量恪守道德规范。这也是制约美国电影艺术范式的力量之一。一般而言,男性英雄同时被处理为道德上的楷模,如有变故,也要以温情或体面的方式将前一则感情变故推成背景,迅速转换成一个新浪漫故事的开端。但是,希腊神话中的伊阿宋在亡子、丧妻之恸中自杀已成铁案,不可能继续演绎英雄美人的完美传奇。所以,在叙事的周延以及节奏的流畅感方面,2000年电视电影版显得犹豫不决,这与它在影片内容的整体走向上的骑墙态度有关。从演员的表情可以明确看到,除了1963年版中浓密的黑发外表之外,新版的美狄亚还被夸张了眉梢和黑眼圈——这是一个隐藏着主观视点的镜头,它突出了伊阿宋直觉上对深肤色的“高加索公主”美狄亚的排斥感。运用冷色调去表现一个恋爱中的女性在好莱坞非常罕见——除非她是一个反派。冷调的偏光包含着创作者对角色的态度,令观众从感官上与伊阿宋对美狄亚的直觉保持一致,为他后来的背叛开脱。这位英雄原本以感情的谎言换取婚姻,以婚姻换取王位,其分裂的人格和悲剧的命运却因为美狄亚的缺席而被屏蔽,一切欲望与幻灭被影片最后一个凝视的镜头阻挡在电影叙事之外。
希腊神话中著名的赫拉克勒斯和伊阿宋都被好莱坞理念重新编码了,重新编码也许是好莱坞的一种不言而喻的智慧:古老的英雄在旧世界被讲述得太久了,他们完全属于历史,属于文化传统,属于古人和一切不属于美国的时空。美国电影需要的是属于美国精神的英雄。
四、《特洛伊》为何而战
人类文明的历史有多久,战争的历史就有多久。不仅如此,战争还与人类自身、与人类的文化一道进化、升级——规模越来越大,杀伤越来越多,似乎智慧水平也越来越高,战争的快意越来越足。同时,战争孕育英雄,大手笔的战场具有无可比拟的审美价值,它张扬着人的意志的宏大豪迈之美。任何人,只要能管束住自己的理智,关闭战争影像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勾连,都可以从中体会到澎湃之气。所以从古老的神话史诗到现代的影像艺术,战争始终是最激动人心的主题之一。

依据荷马史诗的叙事,关于人的一切故事——个人命运或城邦兴衰均与神灵有关,从神灵开始,由神灵决定。特洛伊城的故事也是如此,在《伊利亚特》中,天神之争及随后的天神大战是史诗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从叙事逻辑看来,人类之战只是天神大战的余波。倾听诗人吟唱的世人通过语言亲历永恒的神话故事,看震怒的神灵无动于衷地毁掉哪怕是最优秀的人类,看被毁灭的结局。战争双方所有人类的德操与品行都将化作虚无,盖世英雄在神的笼罩下失去神圣性,活得越壮阔,死得越卑微。这就是悲剧令人战栗的至高境界。然而,美国主流文化一直排斥宿命论、神衍论。毕竟在现代社会,神的绝对性太容易引起人们的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对此,《特洛伊》的编导像好莱坞面对所有古希腊神话、史诗、悲剧经典时一贯的做法一样,同样采取“避神策略”:最大限度地弱化史诗中神祇的力量,只字不提众神为了争夺人类的祭拜供奉而毁灭特洛伊的动机,也绝不像荷马一样泼墨表现它们在战场上的暗中行径和幕后以牺牲人类、毁灭人类城邦为代价的妥协。隐去众神,电影的叙事得以专注特洛伊人和希腊人,他们或远或近,都算神的后裔。在分析《特洛伊》时,美国《芝加哥太阳报》著名影评人罗杰·依波特曾幽默地指出,影片声称改自《伊利亚特》,荷马应该去“投诉”,因为影片尽可能地从神话中脱身,神话叙事降格到电影《特洛伊》的人类叙事。按照弗莱的理论,这是关于凡人的、“次等”的叙事;按照巴赫金的理论,这是叙事的降格,它指向人的虚妄。
影片情节起始于希腊半岛各联邦的明争暗斗,重要角色之一阿伽门农有着强烈的野心和政治谋略,与希腊最伟大的战士阿喀琉斯的英雄性格发生冲突。这与前辈的影片——经典好莱坞叙事以帕里斯与海伦的故事作为起点完全不同。《特洛伊》以希腊人内部战争为起点,以摧毁特洛伊并彻底征服它为终点,看起来应该是不折不扣的战争影片。
市场运作似乎也证实并强化了这一点。从制片方与发行方投放到世界各地的放映海报可以佐证其影片的类型。发行在巴西、德国、日本、韩国、西班牙、意大利、中国大陆以及香港等地的海报取样与旧版《木马屠城记》的海报所显示的影片类型有鲜明的区别:2004年张贴在世界各地的《特洛伊》海报都突出了男明星:布拉德·皮特和他在影片中的决战对手埃里克·巴纳,即便在边角仍保留那一对著名的情侣。有的海报只列出了演员奥兰多·布鲁姆,但他所扮演的帕里斯与海伦的爱情显然不再是影片在发行市场上的核心“卖点”。至于在特洛伊战争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之一——奥德修斯,尽管其扮演者西恩·潘同为大牌,也未被列入海报——影片要突出的是冷兵器时代战争中的砍杀明星,而不是谋略大师。
为了讲述一部伤感的罗曼司“特洛伊的海伦”的故事,1956年的《木马屠城记》要以国家的毁灭作强大而厚重的祭坛,突出渲染一对情侣爱得如何惊天动地,以使他们的私奔成为永恒,所以1956年的影片注定选择特洛伊的情感立场;而2004年的“特洛伊”属于古装战争片。当代好莱坞原本没有义务坚守一方,可以超脱于战争起因的是非判断,也无需对双方的善恶作复杂的阐释,可以说在“特洛伊叙事”上,好莱坞享有 “言说”的自由。莎士比亚就喜欢同时向战争双方投注等份的赞赏和敬仰:在《特洛伊诺斯》等剧目中,他同样地赞美两边的英雄阿喀琉斯与赫克托尔、英雄各自的妻子安德洛玛克和珀涅罗珀、英雄各自的母亲赫库巴与忒提思。从理论上说,讲述者“均分”情感,犹如观看一场无关乎主客场的体育比赛,不必在意一方的输赢、胜败,意味着某种游戏性和纯粹性。如果说没有立场的战争片就是游戏的话,那么没有英雄的战争除了胜败结局的历史意义和阶段性的道德投诉之外,就没有了人格的魅力,它的审美力量将不值一提。但是,好莱坞会制作一部与其经典战争片不同的《特洛伊》以别于《一个国家的诞生》、《西线无战事》、《兵曹乔治》、《漫长的一天》、《M.A.S.H》、《现代启示录》、《黑鹰坠落》,甚至发生在伊拉克的《拆弹专家》吗?
卡尔维诺曾经说,“主控故事的,不是声音,而是耳朵”——这是针对有关马可波罗的叙事而言,但他启发我们解读电影叙事时应有的意识:主控电影的除了眼睛,还有耳朵。无论眼睛或耳朵,都是被设计的。影片《特洛伊》则起始于一张颇有“历史感”的古代希腊地图和一个声音。
古装片的片首出现地图是好莱坞历史片常用手法,它可以给影片带来一种文献性。而那番不乏疑虑的旁白者-叙事者之声则出自影片角色之一奥德修斯之口,他是希腊联军高层的观察者、著名的木马计设计人、特洛伊破城时的亲历者、各种英勇业绩的见证人。呈现特洛伊战争要涉及到众多人物,在希腊联军屡战屡败的核心群体中,奥德修斯的英雄气质并不出众,他甚至可以延迟到影片最后20分钟露面献出计谋。但是,他不仅出现在片首,而且还主持了阿喀琉斯葬礼,是他的声音贯穿了影片首尾。比较影片中几个主要人物的语音可见,西恩·潘所扮演的奥德修斯在音高上的低音点明显多于皮特所扮演的阿喀琉斯、考克斯扮演的阿伽门农、巴纳扮演的赫克托尔,更不必说由奥兰多扮演的帕里斯。其发音的音节在时长上少于其他人,音域相对偏窄,甚至与彼得·奥图尔所扮演的老国王普里安相比,潘的语调波动幅度上也明显偏小,更趋于自然语流。这个声音塑造了奥德修斯深谋远虑、不动声色的个性特征,也让旁白远离了剧场式发音的语感,具有纪录电影冷静镇定的语音特征,它与影片开端精准的古希腊地图共同形成了某种“历史感”。在电影中,“历史感”,归根到底是真实感,是一种能让人物“活在其中”的时空。可以说,影片的基调就是脱离神话形而上的飘渺,也远离中立者的坐席,以擅长察言观色的奥德修斯的角度逼近其同伴,包括英雄阿喀琉斯。
如果说伊阿宋与赫拉克勒斯的英雄业绩“斗怪兽”、“战群妖”、“杀巨人”属于个人历险的英雄神话的话,那么挣脱了神话胞衣的电影《特洛伊》则要讲述一个无比尴尬的“史实”:出现在特洛伊战场上的英雄面对的是不折不扣的人类同伴——阿喀琉斯的对手们并非“异类”,而是自己的邻邦;迎接自己刀劈、箭射的人们就住在海岸对面,一些人或者还不乏往来,彼此仰慕已久甚至联姻结亲。在讲述的结构上,大力士和阿尔戈英雄的个人历险叙事只要不断变换场景和鬼怪们的外形,以线性的时间历程承载一次次传奇就足够了。而希腊-特洛伊的人们则需要复调式的戏剧冲突结构,在人伦组织中建立持续发展的对位关系,以完成其人物形象的塑造。《伊利亚特》中的阿喀琉斯的心理变化和个性特征处于同一平面,除了砍人还是砍人,除了勇敢,还是勇敢,战士的品质自始至终未曾变化。而电影《特洛伊》则将其定位在性格发展上,被逐一战胜的每个对手都与他形成了动态的复调关系,直到他战胜那个最强大的对手——他自己。
《特洛伊》中的阿喀琉斯究竟是怎样的英雄?必须把他放到几组形象中考察。
第一组是帕特洛克罗斯与布里塞伊斯。从柏拉图开始,人们早已认定前者是阿喀琉斯的“伴侣”,荷马史诗中当然描述过两人深挚的感情,但好莱坞主流电影历来对此类人物关系非常审慎。在阿喀琉斯出场的第一个场景中,影片《特洛伊》有意强调了他身边存在的异性,但没有相关发展线索。而帕特洛克罗斯首次出现时被降格为阿喀琉斯练习打架、打斗、砍杀的玩伴,两人造型非常接近,仿佛阿喀琉斯“身体游戏”的凡人化镜像。这些细节意在模糊、淡化阿喀琉斯与帕特洛克罗斯的同性关系,模糊、淡化并不是删除,只是使之不那么显著,让谙熟文化传统密码却持保守态度的多数观众心领神会地接受。在随后的场景中,两人的关系仍然顽强地延续着,镜像注定要破碎,变为真相:阿伽门农抢了本该归阿喀琉斯的女俘,即“美颊的布里塞伊斯”,阿喀琉斯拒绝参战,眼看无数希腊战士惨死沙场而无动于衷——“我不是战争的奴隶”,他说,并掉头离去,仿佛阿喀琉斯的“取向”“不成问题”。但是,影片设置了一个“巧合的”场景:布里塞伊斯来到阿喀琉斯帐中的同时,帕特洛克洛斯战死。在《伊利亚特》中,布里塞伊斯是太阳神庙祭司的女儿,是阿喀琉斯与阿伽门农之争的焦点,但并未指出她同时是特洛伊王室公主。影片将布里塞伊斯处理为王室成员、帕里斯的堂妹,这位性感的、“美颊的”女俘作为近身角色被添置到与阿喀琉斯有关的情节中。但女祭司的神圣和公主高贵本来就不该成为欲望的目标,所以作为“帐中人”,她的嵌入完全出自影片对阿喀琉斯的塑造所需:在戏剧结构上平衡冲突双方的力量,使阿喀琉斯的叙事与帕里斯对等——他们都爱上了“彼岸的”女性(事实却是一位来自王国疆域的彼岸,一位来自精神的彼岸,但后者在镜头中热辣性感的身躯非常容易让人忽略这一点,而它恰恰是影片想要的效果),于是阿喀琉斯帐中发生的不是对一位女性的酒神之爱而是女祭司对他的精神救赎——云端对话激发了后者沉思自省——后者坚定了自己真实的人格,确认自己何以“为战争而生”。激发了阿喀琉斯战场上的血腥复仇——从这一刻开始,用他对手下人的话说,特洛伊是“属于我的战斗”。因此,真正打破两位男性之间镜像关系的不是杀死帕特洛克洛斯的赫克托尔而是布里塞伊斯。阿喀琉斯返回战场——为帕特洛克罗斯复仇,之后,一个无比阴鸷的暗夜*这个场景与其他表现希腊联军场景的光效影调均不同,且是全片影调最低的段落:夜,内景,无明显人工光源。它应是阿喀琉斯个人“帐内”情形的视觉化呈现。,阿喀琉斯放生老国王、女俘并为死去的赫克托尔休战12天。其非凡的英雄气质所产生的吸引力有效地转移了人们对其“性别动机”的追究,至于奥德修斯在片首喟叹英雄们所谓的love究竟指什么影片却含糊其辞,观众就这样被悄悄地蒙过去了。
与阿喀琉斯有关的另一组对比人物是阿伽门农与普里安国王。荷马史诗中非常明确的是,战前阿喀琉斯本人与特洛伊人之间并无冲突,上战场只是他作为希腊人的“雇佣兵”履行职责。冷兵器时代的英雄,如果不是像阿伽门农这样处在统帅位置,通常就是单兵英雄,依仗非凡的体力和勇气赢得战场英名。但在希腊联军内部,阿喀琉斯与人发生强烈冲突,对手是统帅阿伽门农。对手的身份与级别衡量英雄成就的高低。两人的个性、脾气同样激烈、狂暴,战争期间为女俘势不两立,阿喀琉斯拒绝参战,希腊联军因二人对立而深陷危机。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世纪,德国学者谢尔曼的考古工作已经得出了让世人认可的结论——特洛伊战争结束后阿伽门农死去时大约在35岁,与阿喀琉斯同为青壮年。为了筹拍《特洛伊》,华纳兄弟制片方组成了庞大的学术团队,为了追求细节的真实感甚至固定在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做深入的专业调研,他们必定掌握这一有关阿伽门农身份的学术结论。影片中阿伽门农也提到过与阿喀琉斯共同作战无数,这是一种非常模糊的表述,并不说明他们的年龄差异有多大。可是,从导演设置的角色造型上来看,他们却被鲜明地塑造为两代人。阿伽门农充当了“粗暴的老朽”,与特洛伊老国王普里安一起参与了阿喀琉斯叙事——作为老人世界的象征,他们是“双面父亲”组合,修正青年阿喀琉斯性格的发展。前者,阿伽门农,一个恶老,为着自己的野心,堂而皇之地借国家使命敦促阿喀琉斯出战,将一个年轻人送上战场。同时,影片不仅格外突出阿伽门农无休止的野心和狂野、残暴的性格,而且着意表现其因为年老而愈显丑陋的外观。与阿喀琉斯对待布里塞伊斯的态度完全相反,其对待女性贪婪变态而充满恶意,令人不禁从感官层面完全排斥,进而在道德上否决他;“父辈组合”中的后者,特洛伊国王普里安则被塑造成一个为国家自卫而献出儿子的开明国王、一个捍卫儿子的爱情的慈父、一个赞赏“美少年游戏”的审美者。普里安是影片为阿喀琉斯对抗阿伽门农所增添的重要参照,他与阿喀琉斯的关系潜在地开辟了发生在特洛伊的另一场战争,一个发生在阿喀琉斯内心的弑父战争,阿伽门农就是那个即将成长为英雄的年轻人必须战胜的精神敌人。对阿喀琉斯而言,精神上战胜阿伽门农比武力上战胜赫克托尔更重要。这样,影片《特洛伊》得以被好莱坞改写成青年成长主题的影片,阿喀琉斯的战场因此成为他自己成长考试最后交答卷的地方。
第三是阿喀琉斯与赫克托尔的组合。两个人脾气迥异,是坏脾气的顽童与温和的模范儿童、小弟与兄长、坏男人与好男人的对比关系。影片将伊利亚特的故事浓缩到三段日夜交替的场景中。首战,阿喀琉斯非常不情愿地替他所不屑的阿伽门农出战,在赢得特洛伊神庙战役时,与赫克托尔第一次相遇且有一番对话。他挥手请赫克托尔离去,并对手下人说“现在杀死王子还太早”——固然这是古代战争的规则,但布拉德·皮特微妙的讥讽表情和嘲笑帕里斯的语调同时阐释了阿喀琉斯游戏化的心理秘密。随后,阿喀琉斯为帕特洛格罗斯之死向赫克托尔发起挑战,这是为自己而战。作为战士,他们惺惺相惜;作为英雄,他们都要通过对方确认自己非凡的英雄气概,甚至以生命相互辨认。所以用刀剑对话的“对手”赫克托尔是阿喀琉斯的另一种镜像。为彻底超越自我而战的阿喀琉斯有着天神般的盛怒,被动自卫的赫克托尔最终战死。但获胜后回到帐中的阿喀琉斯并无快意,直到老王普里安的到来“以父亲的身份讨回儿子的遗体”。走下战场的阿喀琉斯终于暴露出真正致命的精神缺陷——面对死去的赫克托尔的遗体,这个游荡在生死之间、无父无家的孤儿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他跪下掩面痛哭,预约了此后见面:“兄弟,我们将很快见面。”这是他们第三次谋面,精神上的胜败显然急转直下。经历了反抗老朽、重置爱情、战胜对手之后,影片以赫克托尔的家破人亡为代价,阿喀琉斯向着他的精神父兄致敬,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
现在我们要连接起影片首尾的旁白者——奥德修斯的意义出现了:作为阿喀琉斯故事的见证人,奥德修斯的视线贯穿全片,始终追随着这位青年英雄,并讲述了他关于勇气与爱的真正故事。至此我们发现,这部发生在古代战场上的故事片的核心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战争,而是一个青年人心理的变迁,他所亲历的伤害——无论对人对己,无论是遗失还是获取,都是“成长叙事”的符码。
以胜利者姿态回顾二战的美国人巨资制作过战争片《漫长的一天》、《虎虎虎》等影片。开阖的叙事线索、宏大的战场、英雄主义的精神迅速形成了有关二战电影的史诗美学特质:酒神式的深度狂野、武神的大尺幅张扬、战神呼啸天地的速度,正是其他艺术形式和素材所欠缺的审美特性,也是人们所期待的。在好莱坞,战争景观的现代经典首现于越战题材的电影制作中,例如直升机编队在天空中播放着瓦格纳的歌剧执行大轰炸任务、轰炸机投放长达数公里的燃烧弹焚烧整个沿海滩涂*此情景出自F·F·科波拉导演的《现代启示录》的开始部分,该片1979年获金棕榈奖。。这类场面和镜头段落曾经令当时的观众兴奋不已,有效地培育了人们尾随而来的视觉欲望,给后人的战争镜像以丰富的启示,由此催生了好莱坞电影的新理念:没有大场面运作的镜头就不再是战争大片,至少不再是值得关注的、令人兴奋的战争片,或者说人们不再执念于对战争作道德与情感的诉求,但战争片必须满足某种异乎寻常的视觉诉求。同时,战争片的兴起与后现代文化进程比肩并行,在全球信息化背景下,战争不仅仅作为人类社会重大事件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地伴随在当代历史进程中,更多的是作为新闻事件的影像出现在传播网络——电影、电视、互联网视频中。对大多数与战争事件无直接关系的人而言,那些跨越千万里空间被媒体推送到眼前的碎片化战争信息往往只是填充在播出时间内被观看的特殊景观,它们不需要受众作出道德判断,不向受众吁请情感的投入。如果说它们有什么效应,那就是让人们熟悉、习惯战争事实并将其游戏化、愉悦化,降格为大众的视觉快意资源。
在电影技术水平高度发达的今天,一切并非为着审美而发生的战争却统统可以被包装制作成奇特罕见的景观,最大化地实现战争的特殊效用——似乎只有发生在人类成员之间的大规模暴力、高端技术的暴力才能释放人所渴望的快意。产生于这种文化中的战争影像,其审美价值完全取决于战争场景的大小、叙事空间的宽窄、暴力级别的高低。于是,战争片的叙事往往追求从宏观到微观的全面性,这些属性同样适用于冷兵器时代的古装战争题材,古装的希腊-特洛伊人就是唤醒视觉奇观的战争片实践者之一。以希腊人第一次出征特洛伊场景为例,影片以长达近一分钟的段落模拟一个运动的、拉开的、上升的全景镜头,表现希腊人的海上舰队的规模。镜头从单船底部开始到高空俯瞰整个舰队的上千条战船,近30秒的长镜头,用数字技术模拟完成。这是传统电影技术无论如何不能实现的视觉效果。在这长达近30秒的时间内,观众的视点被牵引着自下而上地升腾,直达百米以上的高空,蔚蓝色大海铺满整个画面,此番壮阔的空间绝对不是其他任何艺术形式所能拥有的,而电影也只有借助数字技术,才能让观众分享这个天神般的主观镜头,发出海天如此辽阔的惊叹,为随后到来的英雄传奇预先垫付浪漫的情绪。
战争的核心在于征服,与征服相呼应的是杀戮的快意。在营造历史氛围、虚拟现场、“真实再现”方面,好莱坞能胜任任何具有“现实感”的视觉效果,罕有哪个国家的电影能与之媲美。它以这样的制作态度和能力来营造战场形象,包括影片中的武器技术及其他器具,战场便获得强大而丰富的质感:当它要通过杀戮的快意直接唤起观众肾上腺时,对阵双方冷兵器的铿锵之声、血肉之躯搏杀的呐喊,通过立体音效能达到最强;单兵执冷兵器格杀之后的肝脑涂地、残肢跃动、血脉贲张、脏器蠕动,这些靠超级制作才能提供的视觉奇景将观影体验直接引向了感官快意,特别是那些被着意渲染、放大的细部、延长时值的镜头,脱离了人物的命运,也无助于人物的性格特征,但它们强烈刺激着观众神经,与其说出于人物形象塑造的需求,不如说为了遵循动作片的类型,惯例性地满足技术时代的观众对战争片的预置诉求,就像伊阿宋与赫拉克勒斯的成长必须一次又一次地砍杀巨人、怪兽和妖魔一样,变成了其所属类型的必备构成模块之一。好莱坞的电影语言所具有的强大视觉优势可以吞噬一切。至此,战争本身的意义已经所剩无几。
为了使战争审美进一步获得人性化的支撑,《特洛伊》制作方排出了豪华的实力派与偶像派明星联盟,演员名单中有多位欧美实力派演员加盟。首先,收起美国腔、临时换上英国口音的布拉德·皮特扮演阿喀琉斯*参照其主演的《搏击俱乐部》、《无耻混蛋》等片可以明显听出其有意识地改变语音,以适应不同角色的特征。,刚刚完成《黑鹰坠落》的澳大利亚硬派明星埃里克·巴纳饰赫克托尔。两位偶像派明星分别在女性青年观众和男性青年观众中有着极高的票房号召力;同时,主演《卡拉瓦乔》、《亨利八世》、《王牌对决》的英国明星西恩·潘饰奥德修斯,这是一位每个瞬间都有戏的实力派演员;而两边国王的扮演者则分别来自英国莎士比亚公司和皇家莎士比亚剧院*英国的“莎士比亚剧专业演员”是表演艺术界对一个演员的功力不另需验证的评价。饰演阿伽门农与普里安国王的分别是来自英国的布莱恩·考克斯和来自爱尔兰的老牌明星彼得·奥图尔。前者在戏剧舞台上名声堪比安东尼·霍普金斯,后者则因主演《阿拉伯的劳伦斯》(1962),并在《末代皇帝》(1990)一片中扮演溥仪的外国教师而闻名。;扮演阿喀琉斯母亲的英格兰演员朱丽叶·克里斯蒂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饰演过《日瓦戈医生》中的女主角“拉拉”,又在1996年版的《哈姆雷特》中出演王后;因出演《指环王》的精灵王子而名声鹊起、资历最浅的偶像演员奥兰多·布鲁姆在片中扮演的帕里斯王子也表现出足够的层次感——明星们的功底确保了他们对人物性格准确、细致的刻画,特洛伊这个战神与爱神齐飞、人类与神祇共愤的故事与当下的观众有了贴近感,使英雄个个鲜活而观众与之遥相呼应。明星联盟——好莱坞制胜法宝——保证了在希腊联盟出征特洛伊之前,电影《特洛伊》已经征服了观众。至于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如何分段讲述、各段落之间的视觉效果如何转换、衔接的问题,在观众看来都显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建立了一种处于科幻战争(例如“星战系列”)和现实战争(例如“二战”素材的影片)之间的战争视觉范式:在时空上重返古代,在规模上标明史诗的印记,在细节上声称有真实化追求,而这些史诗化的视觉空间与偶像级的血肉之躯合力推出的则是美国文化中的“青年核心”精神。
影片投资约一亿七千万美元,票房接近5亿美元。其中美国本土收入仅占26.8%,大额收入分布在全球的院线及衍生市场。这表明不必向“荷马”或任何希腊人购买版权的电影《特洛伊》所开发的全球市场有多大,也表明它的视听效果多么深入人心。我们已经不能想象有关特洛伊战争的电影由同样居住在那个地方的现代希腊人和土耳其人来讲述了。现在如果问,世界上谁是拍摄《特洛伊》的最佳选择?答案似乎是惟一的:只有好莱坞。在这场由特洛伊战争引发的世界电影市场大战中,票房收入归好莱坞,美国趣味归全世界。
五、众神的3D时代
奥林匹斯众神为电影提供了不同规模、幅度、格调的叙事资源,如何将神话有效地转换为电影产业的制片资源往往与投资成本、制片方所在国家的文化艺术传统有关。有时较低成本即可完成一部轻喜剧风格的影片,而完成史诗规模的影片则要求较高成本。以1935年德国的Ufa-Atelier制作的片长105分钟的故事片《安菲特律翁》*Amphitryon,1935,又译《东道主》,德国乌发公司制片,导演Reinhold Schünzel。为例,这部取材神话的影片基于莫里哀经典喜剧而拍摄,影片以珀修斯之子安菲特律翁-宙斯-赫拉克勒斯的神话核心为背景,剔除了包含在神话中叛乱-弑父-复仇、人与神背叛-通奸的原型,以喜剧品格将故事落脚于当事人安菲特律翁夫妇与宙斯之间,表现年迈的宙斯风流时刻的尴尬、难堪之处境,成为影射资产阶级家庭的客厅里常见情景的世俗剧。此后仍有对此神话感兴趣的人——但在法国,它则是另一种继承——1993年,戈达尔再次光顾这一神话,《安菲特律翁》选题几经辗转,最终在现代时空的伪装下,以《悲哀于我》之名进入电影*[法]让-吕克·戈达尔《悲哀于我》(Hélas pour moi 1993),主演: 杰拉尔·德帕迪约。。与德语版电影不同,按照个人的电影美学理念,戈达尔的用意不在于讲述漂亮的神话故事,而是将此神话故事整体性地用于隐喻:现代社会和宙斯的世界同样错综复杂,不可理喻。两部影片一部轻松愉快,一部严肃认真,无论德语或法语的《安菲特律翁》,它们都属于低成本制片,所追求的并不在票房多少。
但是,1980年代卷土重来的好莱坞产业显然需要“更大的手笔”。派拉蒙预算150万的《诸神之战》*1981年的Clash of the Titans,另有《泰坦之战》、《世纪对神榜》等译名,由劳伦斯·奥利弗出演片中的宙斯,派拉蒙出品。将故事的中心放在这组“人物关系”的上一级——安菲特律翁的父亲珀修斯与宙斯的身上,并将他们称为Titans(巨人),意指他们是巨神(Titans一词本来是指较宙斯等更古老的神族)。以今天被“大片”培养起的“重口味”观影习惯来看,这个版本确实显得安静斯文,通篇不尽其瘾,但当时的它却赢得了4100万以上的美国票房和1400万以上的海外票房*http://www.imdb.com/title/tt0082186/ 此处可见其票房成绩,为下一轮投资所埋下了伏笔。。剧作家比彻姆说:“整个希腊神话比较吸引我的,是他们把为人熟知的人类斗争史放在一个虚构的故事环境里,从而说明一些平常无法解释的事情。比如说英雄救美,那能有多困难?你必须打败恐怖的怪兽才能救出美人。想寻找自我价值?你必须走到世界的尽头再回到家乡才会明白。想反抗你的父母?但你的父亲是天神,看看你有多大能耐跟他叫板。”法国导演路易斯·莱特里尔由此得出了对希腊神话的深刻见解:“希腊神话不会像其他国家的那些幻想故事那样拘泥于一些规则,‘Chaos’(混乱)是关键词,那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国度,很多不可能的故事情节,在希腊神话里都是可能的。宙斯之子所遇到的那些强大的敌人,还有他们彼此之间的恩怨,都是非常吸引人的元素,而这也给我们的电影版本带来不少的灵感。”他承认:“1981年版的《诸神之战》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也是我观看的第一部魔幻电影,我绝对被它震住了。所以,有机会拍摄我自己的版本简直令我欣喜若狂!”他甚至自称对老版本的每一个镜头、每一个场景、每一句对白都烂熟于心。电影制片人巴兹尔·伊万尼克记得自己11岁时,为买票看1981年版本的《诸神之战》排队2个多小时:“对我来说,那是最棒的电影周末之一。里面的猛兽,决斗,公主和佩剑的勇士让我大开眼界,以前我可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以上从剧本作者到制片人的访谈参见http://movie.mtime.com/89637/behind_the_scene.html#text_5。当代好莱坞一线的技术“大咖”们无不受到雷·哈利豪森的想象力的启蒙,至今行内人还对泰斗级人物雷·哈里豪森设计的众神模型和随处可见的特效记忆犹新。也许恰恰就是这些技术手段,使上述制片人、编剧、导演对这个神话的更多可能性念念不忘。正是他们——1981年版《诸神之战》培养起的一代电影人,组成了2010版的主创团队,将这种爆棚的想象力放进了新版《诸神之战》*Clash of the Titans,2010年,时代华纳公司出品。预算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截止到当年11月的票房为四亿九千万美元以上。http://en.wikipedia.org/wiki/Clash_of_the_Titans_(2010_film)与http://www.boxofficemojo.com/movies/?id=clashofthetitans10.htm。以及希腊神话系列大片里。我们可以因此将“巨人”之“巨”理解为影片投资的“鸿篇巨制”和相应的“弘大叙事”、影片中诸神与凡人的造型比例、景观的纵深与开阔程度、行动的张阖尺幅、放大的时空以及这一切所带来的震撼力。某种意义上说,影片实现了这一切,新版本的《诸神之战》引爆了奥林匹斯神族的大片时代,接踵而来的有《波西·杰克逊与神火之盗》*Percy Jackson & the Olympians: The Lightning Thief,2010年出品。神话中伊阿宋的故事混搭进了美国青少年生活。、《惊天战神》*Immortals,2011年由美国Relativity Media等三家公司联合出品。导演Tarsem Singh致力于将影片打造成一部有着卡拉瓦乔风格的、《搏击俱乐部》式的动作片,应该说有自己个性化的追求。该片预算$75 million,票房$226,904,017。、《诸神之怒》*Wrath of the Titans,2012年作为《诸神之战》的续集,由Legendary Pictures等公司出品。预算$150 million,总票房$305,270,083。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Wrath_of_the_Titans。、《赫拉克勒斯传奇》和《赫拉克勒斯》*The Legend of Hercules与Hercules,两片均在2014年出品。前者由Millennium Films公司制片,放映后受到广泛的批评且票房惨败。后者由Flynn Picture Company制片,米高梅与派拉蒙两家发行,主攻包括中国在内追捧3D片的海外市场。预算$100 million,总票房$243.4 million,与前者相比算是收支平衡。参见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7/27/us-boxoffice-iduskbn0fw0kr20140727。等一系列直接来自神话或穿越神话的影片。
自《阿凡达》之后,3D技术已经被媒体炒作为观影要素之一、电影放映“标配”之一而风靡全球,成为所有神话影片制片时不可或缺的技术支撑。这必定抬升了每部影片的制片成本,在投资上亿美元的《诸神之战》中,数字技术果然完成了雷·尼古拉斯在上世纪所不能想象的奇观:万丈峭壁上轰然坍塌的宙斯巨像、大洋上狂飙突起的海怪、恐怖狰狞而委颓于珀修斯剑下的女妖美杜莎以及万众聚集的奥林匹斯神殿和国王富丽巍峨的皇宫。在加入3D效果和强大而细微的声效后,每一个场景都产生了不可思议的景深空间,在细微与波澜壮阔之间创造了过去的技术所不能实现的视觉感受空间。其豪迈的想象、逼真的质感和自由的时空流转成为影片的重中之重,呈现了想象中的远古神话的世界,成就了前所未有的奇观神话和票房神话。但是,多变的奇观美学并不能改变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同样,好莱坞慷慨的预算投资和激进的技术探索并不意味着影片在内涵上也具有相应的开拓性,同时它们也并非只是以神话完成的特技秀或者是“好看、刺激的动作片”。
希腊神话中的众神在各个故事中的性格特征和所承担的叙事功能并不一致,但唯独宙斯的好色与赫拉的妒忌是一贯的。他们的性格对立共同决定了其他人与神祇(包括珀修斯、赫拉克勒斯,也包括奥德修斯的漂泊在内,都与两位天神的性格大战有或长或短的因果链)的身世、命运、神力以及最终向着神界的归宿,因此即便不作为故事的第一主角,他们的关系模式也足够关键。1981年版的《诸神之战》对待诸神尚且客观,尤其在道德判断上相对中立,各角色之间的戏份比例相对均衡,与神话精神较为一致。其中大名鼎鼎的巨星劳伦斯·奥利弗扮演了戴面具的宙斯,而赫拉则由1930年代出生在英国的著名演员克莱尔·布鲁姆扮演。在与诸位女神讨论如何处置宙斯的私生子时,她细微地表现出天后赫拉恼怒而无奈的心理和隐忍而强悍的性格内涵。这一对作为神祇之首的夫妻,其恶劣的关系和反复无常的性格规定了珀修斯、赫拉克勒斯的命运曲线。但较之1981年的版本,新版《诸神之战》诸神传奇仍然因循着保守观念,顽固地坚持父系权威在一切英雄叙事中的神圣性、唯一性、不可撼动性。导演莱特里尔*该片主创团队来自好莱坞神话电影的核心,导演路易斯·莱特里尔虽来自法国,却是卡通系列片《圣斗士》与《黄金圣斗士》的忠诚粉丝,因此难怪他们能将神灵的一切复杂性简化到少儿所能理解的程度。http://movie.mtime.com/89637/behind_the_scene.html#text_5。甚至彻底省略了旧版中赫拉与宙斯在神庙里的亘古之争,将宙斯改写成一个“深爱着人类”的“众神之父”的形象。这一处理,当然使叙事更为集中,也似乎解决了旧版“散”的问题,但遗憾的则是缺少了一版再版的同题神话本来有机会获得的可能的深度。值得重视的是,这似乎已成为英雄叙事的一种结构模式,当夫妻关系(宙斯-赫拉)与男性行为(宙斯那边却不断出现私生子)的冲突背景在2014年的《大力神》一片中再次被触及时,该影片直接将赫拉的心理力量做了恶魔化处理——两条绿色巨蟒从她的眼睛中爬出,加害婴儿赫拉克勒斯,这一针对女性角色的恐怖片手法极度夸张了赫拉的恶意,同时有效转移了观众对宙斯的“恶德”背景的追究,使“神圣之父”的原型功能再次安全地进入英雄叙事,因而2014年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只有沿着1970年代施瓦辛格奠定的基调继续重演美式“超级英雄”成长记。如此,无论10年前的阿喀琉斯、珀修斯或几十年来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他们的“杀怪”、历险、成长、乃至回归奥林匹斯上的所谓“救赎”就毫无悬念地获得了“以父之名”的使命并归顺于神圣父权了。
当然,今日好莱坞对电影语言的驾驭早已炉火纯青,被神化了的超级英雄例如珀修斯在出生时就做了程式化的视觉润色:这个原本“来路不明”的男孩像后世的救世主耶稣一样成长于年轻母亲和年迈父亲组成的“父严母慈”之家,而其余那些角色——赫拉、海神*改编所依据的原稿之一中,海神曾经被设想成“来自苏美尔的死亡与毁灭之神”的形象。见原作者Louis Leterrier 与Tim Roth在2008年Universal Studios Home Entertainment DVD 中的访谈,转引自http://en.wikipedia.org/wiki/Clash_of_the_Titans_(2010_film)。、冥王、鲁莽的人类国王与王后只能在这个秩序前提下参与搅局。观众尽可以跟随核心情节迅速进入萨姆·沃辛顿*萨姆·沃辛顿主演过《终结者2018》、《阿凡达》等好莱坞大制作,是目前银幕上最炙手可热的男影星之一。所扮演的珀修斯大战众神怪的场面,其中包括翱翔于苍穹间的飞马、珀修斯砍下美杜莎那著名的蛇发脑袋并以之退却海神巨怪的情景,陶醉于奥林匹斯世界的奇幻。但暗藏着好莱坞的秩序和美国文化中的“神圣父系”核心观念也无形中植入幻境之中,在古老神话中那个因德行不佳而饱受诟病的宙斯与他的个人标志——美国白头鹰所象征的父权威仪又一次征用了英雄叙事。这使得希腊神话中的诸神与英雄和《星际穿越》等科幻影片中的英雄一起,组成了一个富有神圣意味的国度——那是一个浸润了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好莱坞影像之国。
Exploitation of Ancient Greek Mythology by Hollywood Film Industry
Wu Bingqin
(School of Literature, Qilu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250013)
Nowadays, myths and stories of ancient Greece are still a database of material resources for Hollywood films to turn out various genres of films. In the last five decades, the so-called blockbusters have given birth to a new romantic myth oa grand, epic-like scale and with sophisticated and exquisite film techniques. Bearing the core values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they have licked into shape typically American super-heroes, presenting an unprecedented fantastic landscape, and getting hold of huge profits of the whole globe.
ancient Greek myths; Hollywood films; super hero; conservatism; global benefit
2014-12-21
吴冰沁(1963—),女,江苏无锡人,齐鲁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J905.712
A
1001-5973(2015)01-0137-20
责任编辑:李宗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