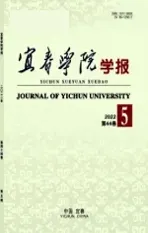论《史记·陈涉世家》现代重写文本中阶级斗争意识的表现
2015-08-15宋先红
宋先红
(肇庆学院 学报编辑部,广东 肇庆 526061)
与《史记·项羽本纪》被改写后出现多种话语形态很不相同[1],司马迁的《史记·陈涉世家》虽然在现代作家那里也是以很高频次地被重写,但其重写文本在其思想上表现出的“阶级斗争意识”却惊人的相似。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考量的现象。
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中以“陈涉起义”为线索记录了秦末各地反秦力量的风起云涌的社会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赞扬了陈涉的首义之功。秦末之所以有陈涉起义,而陈涉起义在当时又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司马迁认为是秦国统治者仁义不施的结果,并没有或者不可能从阶级论意义上解释陈涉起义或秦末农民起义。但是,由于陈涉作为“农民”的身份和陈涉起义的影响之大,却成为了中国现代作家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并用于指导写作的一个有力证明。从1929 年至1948年,以《史记·陈涉世家》为底本的重写文本一共有出自四位作家的五种文本,他们分别是:孟超在1929 年写成的《戍卒之变》和《陈涉吴广》、茅盾1930 年10 月6 日写的《大泽乡》、宋云彬的1937 年前写的《夥涉为王》和廖沫沙写于1948 的《陈胜起义》。细细研读这些文本,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出现是跟当时中国社会现实和中国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引入息息相关的。
用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对中国民众进行启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目标,但是“觉醒之后怎么办”也是一个迫切需要启蒙者回答的问题,所以先进知识分子对社会现状的思考随着西方学说的不断被引进很快从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反思走向关注现实政治斗争的层面。这个转变和影响在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中得到体现,也是现代历史小说所表现的时代思想层面之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自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被引入中国后就成了中国文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与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被进步的现代作家用来解释文学现象,尤其是将这种文艺理论用于古代的农民起义来应和当时的红色革命运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被史书记载并作为正面书写的农民起义并不多见, 《史记·陈涉世家》就是这少数中的重要一份子。正因为如此,《史记·陈涉世家》就有在短时间内获得了被反复重写的机会。 《史记·陈涉世家》的反复重写不同于《史记·项羽本纪》的多角度地被重写, 《史记》中陈胜、吴广的寥寥话语在5 篇重写文本中被扩充成洋洋大篇的阶级斗争词语,陈胜不同于其他秦末起义领袖的出身成了现代作家们进行阶级斗争阐释的绝好切入点,也正是这一切入点让《史记·陈涉世家》所有的现代重写文本拥有如下共同的书写特征。
一、明晰的阶级对立形势
所谓的“阶级斗争”一定有两个利益和权力截然不同的阶级的出现并呈现明显的对立形势。《史记·陈涉世家》记叙的是以陈涉等各地武装奋起抗秦的经过,其中当然存在着“强秦——诸侯”的对立,但是《史记》在记叙过程中重视的是经过,而不是对立。但是在孟超的《戍卒之变》、《陈涉吴广》、茅盾《大泽乡》、宋云彬的《夥涉为王》和廖沫沙的《陈胜起义》中,两种阶级的对立形势一直围绕着故事情节的发展。
孟超的《戍卒之变》中就说出了“秦始皇”与“楚民族的亡国贱民”、 “秦”与“六国的人民”、“新的力量——农民的,奴隶的”与“统治势力”、“卫兵们”和“戍卒”与“二世皇帝”等几种势力的对立;孟超在后来的《陈涉吴广》中还是延续了《戍卒之变》中的对立形势,只不过强化了陈涉吴广在起义之前的思想过程,更加细致地写出了强秦酷政之下六国人民不堪忍受的生活:“然而如虎如蛇的苛政,横征暴敛的重税,伤人不眨眼的律令,早已使閤天下的人民,虽是战栗在他那'腹诽者族,偶语者弃市'的钳制言论的手段之下,但蕴蓄在心里的,哪里不是怨气冲天?哪里不是鬼哭神嚎?……”[2]
写作时间略后的茅盾《大泽乡》中这种阶级对立意识更为浓厚,而且非常明显地将这种“闾左”和“闾右”的对立说成是“阶级”的了:“……他们是将门之后,富农世家,披坚执锐做军人是他们的专有权,他们平时带领的部卒和他们一样是富农的子弟,或许竟是同村的儿郎,他们中间有阶级的意识做联络。然而现在,他们却只能带着原是'闾左贫民'的戍卒九百。是向来没有当兵权利的'闾左贫民',他们富农所奴视的'闾左贫民',没有一点共同阶级意识的'部下'!”、“到渔阳去,也还不是捍卫了奴役他们的富农阶级的国家,也还不是替军官那样的富农阶级挣家私……”、 “他们若祖父血液中的阶级性突然发酵了”、 “统治阶级的武装者的他们俩全身都涨满了杀气了……”。因此在《大泽乡》中,两位军官就成了“统治阶级”的代表和陈胜、吴广他们这些“闾左贫民”就直接有了面对面的尖锐冲突,最后以这九百人的爆发而成为这阶级冲突的正式开始。小说中两种叙述话语的交替成为不同阶级群体话语的范本。茅盾选取了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的一段过程,小说一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以统治阶级的代表——两位军官为叙事视角叙述了他们在听到“陈胜王”之后的想法,而第二部分以农民阶级――九百戍卒为叙述人叙述了“闾左贫民”的觉醒,第三、四部分就写以上两种对立开始激化,最后终于爆发了“被压迫的贫农要翻身”的大起义。在这里,我们听到的不是军官或陈胜、吴广作为个体的声音,而是两个不同阶级集体话语对抗,而“阶级”二词频繁地出现在小说中,这就是茅盾对“陈胜起义”所作的阶级论的的解释,也是小说采取交替变换叙述人的原因。
宋云彬的《夥涉为王》表现得更为清醒,他似乎看透了中国历史上“成者为王”的把戏,他把阶级论的思想应用于整个封建社会,当然也包括陈涉、吴广等农民出身的反抗者。他着重写了成为大王的陈胜最终住着“沉沉”的宫殿,甚至杀掉当初一起“庸耕”的朋友的事情。从更广义的层面写出了封建社会的两个阶级的对立,中国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从根本上不是为了改善劳动人民被压迫的现状,不过是谋求一家一姓的富贵而已,如果不认清这种根本意义上的两种阶级的对立,劳动人民只能永远生活在被欺压和被欺骗的境况之中,所以宋云彬在这里揭示的是一种超越特定朝代的一种阶级对立。可以说,他把中国整个封建历史都置于小说的批判之下,而这种批判也是对一种新的思想、新的社会制度的欢迎。
廖沫沙的《陈胜起义》应该是最朴素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民在毫无意识地情况下被征兵、又被逼造反的经历,但这里从陈胜主动辞工当兵,又被逼杀掉军官造反两件事情看出这里也存在着“雇农-地主”、 “壮丁-军官”的对立,而这种对立从根本上讲也是阶级的对立。
从一个人的勇敢到两个阶级的对立,甚至到贯穿整个封建历史的的阶级对立,这不能不说是当时作家开始用新的视角、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来重新打量历史事件的结果,不能不说是当时中国思想界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这些思想和主义随着人们的宣传进入了文学作品,又进入了更多的人的心。
二、清醒的农民阶级反抗意识
如果说这些重写文本中的阶级对立反映了人们如何认清社会形势的话,那么作品中共同出现的农民阶级清醒的反抗意识则说明了当时社会形势发展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地步,而老百姓更有了奋起反抗的行动意识,这在为无产阶级革命进一步营造声势。
在孟超的《戍卒之变》和《陈涉吴广》中,“反呀,反呀!”“反!反!反定了!” “那末只有,只有反了!”这样的词语反复出现,它是一种无法遏制的激情弥漫在大泽乡的九百民戍卒的心中:“……使他们——尤其是这九百多个远戍的屯夫——都明明白白了这样的一种感念,就是不但认为这个的时代——暴虐的秦家天下,快要到了灭亡颠覆的时候,而且已经断定了一个新的时代快要到来……”,“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是奴隶们抬头的时代啊!这个时代是拿锄头的造反的第一次的开展!”。反抗的声音从陈涉那里发出,很快得到群体的共同回应,并且给了这个群体无限的希望。
茅盾《大泽乡》里把农奴们的反抗意识比作“洪水”和“地下火”。 “但是'闾左'贱奴们的洪水太大了,太大了,咸阳城不免终究要变成大泽乡罢!” “地下火爆发了!从营帐到营帐,响应着'贱奴'们挣断铁链的巨声。从乡村到乡村,从郡县到郡县,秦皇帝的全统治区都感受到这大泽乡的地下火爆发的剧震。即今便是被压迫的贫农要翻身!他们的洪水将冲毁了始皇帝的一切贪官污吏,一切严刑峻法!”很明显,茅盾在这里已经是站在农奴阶级群体的立场来写陈胜起义了,一种新的力量和认识被注入到历史事件中,写的就是当代史。
宋云彬在《夥涉为王》中甚至把成为“大王”的陈涉也当成了农奴们反抗的对象,说明当时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对阶级和阶级的对抗已经有了很深刻的认识,宋云彬的《夥涉为王》选取了“陈涉庸耕”、“发配渔阳”、“夥涉为王”三个片断来写陈胜,表面上看,通过陈胜起义前后对待农民的态度似乎揭露了历代起义为王者最后还是成为统治阶级的真面目,是将陈胜放在和刘邦、朱元璋等通过农民起义最后当上皇帝与农民对立的平台上一起批判,揭示出在旧的时代即使陈涉最后起义胜利了,但历史还是免不了堕入胜者为王的循环怪圈,真正属于人民的解放还是属于新思想照耀下的新的时代。所以最后年轻农奴的声音让我们明白孟超写“夥涉为王”虽然与以上的角度不同,但是还是宣扬了农民起义的正确方向:“……陈涉已经不是我们的同伴,而是我们的仇敌了!他出卖我们,要用我们的骨肉和血来造成他自己的崇高的地位!他心目中只有权位利禄,没有劳苦大众!我们不要他的欺骗!我们应该团结起来,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去争取一切应享的自由和权力。打到一切压迫我们,剥削我们的敌人!打倒一切反叛我们,出卖我们的敌人!”这完全就是现实题材小说中受马克思阶级理论教导的农民共产党人的呼声。反抗的深刻和反抗的决绝也由此而见,这种深刻和决绝绝不是中国古代历史学家们能具有的,是一种新的思想被引进中国的有力见证。
廖沫沙的《陈胜吴广》写于1948 年,虽然取的是《史记》的题材,但是因为人物语言和对历史事件的改动,我们完全可以将陈胜、吴广的故事当现实题材的小说来读。小说首先虚构了陈胜在地主家做事的苦闷日子,将陈胜被征发渔阳写成陈胜不堪地主的虐待而主动当兵,最后因为当兵无望才被迫造反,这难道不是现实题材小说中中国农民在当时的出路和选择吗?他们的造反的意识虽然不像以上小说中那样的强烈和清醒,但是在朴素的语调中他们造反的经过确实一步步走来,水到渠成,很符合现代中国农民走上反抗道路的事实。
在这些文本中,反抗的声音和反抗的行动在少数人那里开始,最后得到了一个群体的响应和拥护,这就是当时中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事实。中国现代作家将对现实的认识融进历史文本的重写之中,历史和现实被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了,铸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文本。
结 语
从上文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在哪一种重写中, “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的对立和“农民/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意识一直是被突出和强调的。这里多个文本表现的相似和《史记·项羽本纪》被重写后的多义虽然一样耐人寻味,但并不是不可以解释的。那就是现代文学从时间段上仅仅只有三十年的时间,但在这短短的三十年中,是中国历史风云变幻的时期,也是中国思想界有主流也有百花齐放的时期,作家们在这三十年中在思想上经历了太多的变动和起伏,这种变动和起伏都生动地记录在他们的历史小说的写作之中。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在二三十年代作为西学的一种被引进中国,被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诚如王富仁在评价孟超的《陈涉吴广》时说:“中国现代以中国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的结果。”[3]而四十年代由于中国国内阶级矛盾空前激化,陈涉起义这样的农民起义题材历史小说就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了。因此,司马迁的《史记·陈涉世家》从陈涉的身份、事件的经过和影响都为这些重写提供丰富的空间。它是历史,但是是可以容纳现实的历史。而《史记·陈涉世家》中“大泽乡起义”这一段被反复选择、改编和扩充,是作家的想象力与现代意识的一种融合和再创造,是中国历史文化在现代的一种再生和升华。
[1]宋先红. 论《史记o 项羽本纪》被改写后的多种话语形态[J]. 宜春学院学报,2012,34(3):94-97.
[2]王富仁,柳凤九.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大系[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3]王富仁.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大系·代序[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