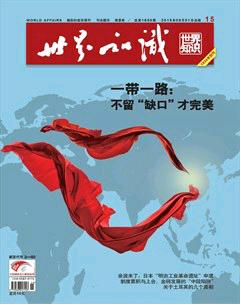妥协的艺术
2015-08-12湘溪
湘溪
7月14日,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终于达成,长达12年的谈判终于画上句号,协议因此被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形容为“历史性的大交易”。而在种种惊叹与赞誉声中,《金融时报》的观察视角与众不同,它认为伊核协议的最大意义在于一个国家首次通过外交而非战争方式摆脱了经济制裁。
的确,经济制裁始终是近代以来大国特别是美国推行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1919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就在演讲中明确提到:“遭受经济制裁的国家就是一个即将投降的国家,……制裁是和平、无声而又致命的手段。”不过,现实似乎与威尔逊开了个玩笑——自国际联盟成立以来,经济制裁一用再用,但其结果常常事与愿违,其中不乏引发战争的案例:1935年~1936年国联对意大利的制裁并未阻止其入侵埃塞俄比亚,1940年后美国对日本实施的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的禁运更是成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重要诱因之一。冷战期间西方对苏联及经互会成员的战略物资禁运也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经济制裁的“效果”始终与它的“目的”相关联。大部分制裁的目的其实并不是“让制裁对象屈服”,而是削弱对手的力量,从而为军事颠覆做准备。美国在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前,对伊实施了长期的经济制裁;1999年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前,南联盟也遭受了经济制裁;冷战期间美国对古巴的长期封锁、制裁显然也是在为“拔除眼中钉”做准备。这一类制裁,其目的就决定了它不可能通过外交方式被解除。
与之相比,另一类制裁则属于“表明态度”。美国学者拉斯·戴维斯指出,“经济制裁是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一种国际关系行为”,对于一些国际危机,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介入过深,但面对议员、媒体和民众的压力又不得不做出反应,所谓“战不得、和不能”,介于其间的经济制裁就成为“最佳选择”。乌克兰危机之后,美国对俄罗斯一轮又一轮的制裁就是现成的例子。
不过,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经济制裁的确能够起到“规范制裁对象行为”的作用。与军事打击相比,经济制裁既能让对手遭受损失,又能做到“程度可控、行动可逆”;就像美国国务院官员所说的,经济制裁的核心是“杠杆作用”,也就是让制裁对象“做选择题”——是继续承受制裁带来的损害,还是调整行为从而获得解除制裁的收益。正是这种杠杆原理,让经济制裁有可能成为妥协的催化剂,促成双方的“战略交易”。从2013年11月达成临时协议以来的伊核问题各方就是这样逐步实现了妥协。美国国务卿克里7月14日接受采访时称:“制裁让他们(伊朗)回到谈判桌前,制裁伊朗就是为了重启谈判。”
当然,克里说的只是“一半事实”。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始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迄今已有36年之久。至少是在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前,美国并没有将制裁作为“妥协杠杆”的意思,而是像对付米洛舍维奇、萨达姆那样,实实在在地为推翻伊朗政权做准备。2002年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就明确将伊朗列为“邪恶轴心”,公开宣称要用武力颠覆,而这也正是让伊朗产生“拥核自保”念头、导致伊核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
然而十年之后,经历金融危机和阿拉伯世界剧变、中东战略一再受挫后的美国,对伊朗制裁的目标确实发生了转变。一方面,美国国力下降,而伊朗在中东的大国地位越来越明显,此消彼长之下,奥巴马政府意识到要更迭伊朗政权越来越力不从心,事实上也不太可能;另一方面,伊朗遭受多年制裁,特别是2012年以来严苛的金融制裁,国内经济和国际贸易受到破坏性影响,通过伊核谈判打破外界的封锁、突破国际孤立逐渐成为伊国内政治共识,这也是“温和派”鲁哈尼在2013年大选中当选的大背景。
恰恰是在2013年,持续了十年的伊核谈判迎来了转折点,自11月达成临时协议以来,尽管最后期限“马拉松”式地一拖再拖,但这反而说明双方都有诚意——毕竟涉及各自重要利益,岂能不进行顽强的讨价还价。
而不论过程有多曲折,就像俄罗斯《观点报》指出的,伊核协议意味着“一个可能在海湾地区引发战争的隐患排除了”,它让世界松了口气;更重要的是,通过合适的对话机制,经过多方共同努力和不断协商,伊核谈判最终达成历史性协议。协议的达成为国际热点问题的妥善解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和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