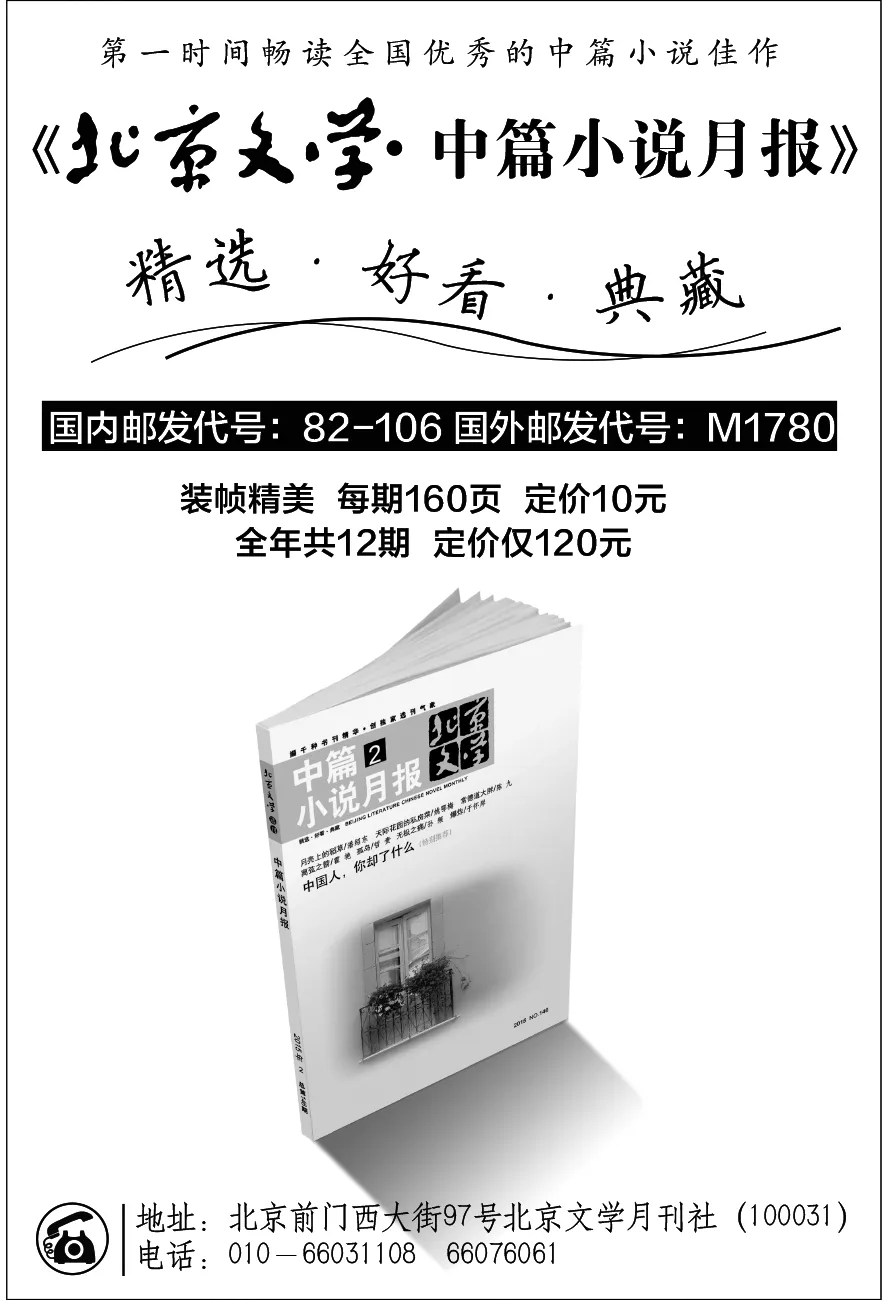出售哭泣的人
2015-08-01刘荣书
刘荣书
出售哭泣的人
刘荣书
她知道这世上的很多东西都可拿来出售,比如物品,比如身体——有人出售身体中的血液,有着细水长流的笃定与淡然;有人出售自己仅有的肾脏,像沉陷于一场惨烈的赌局;还有的人,用性器拿来交易,为人销魂又遭人唾弃——她想不到,当她进入不惑之年,却会拿自己的哭泣用来出售,使自己深陷一段生理上的困境。
从十六岁进剧团,她所饰演的角色,大多是丫鬟媒婆之类的配角——不是她不求上进。她是从农村出来的野丫头,幸运被剧团选中,自然知道怎样努力。她记得刚入剧团那会儿,每天早晨四点钟起床,吊嗓子,劈叉。除熟练掌握自己的演出业务之外,主角的唱词,都被她默记下来。主角在台上的举手投足,也被她谙熟于心。她天资聪慧,又肯吃苦,许多年下来,已在剧团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却难能有出头之日。
究其原因,是因她的嘴巴有点大——按民间的说法,她的五官有点苦相,只可演悲情的角色。但剧团鼎盛那几年,传统剧目被打入冷宫。那些新编的现代戏,全是胡编乱造的闹剧和喜剧——她的嘴唇不但翘,还有一些上翻,不开口便已破坏整个面部造型的美感。鉴于她的唱功出色,当年剧团的一位副团长,曾一度举荐她担当主角,但在每次的评审会上,都被团长以及文化局的领导一票否决。
多年的龙套跑下来,她也便渐渐松懈了自己。结婚生子。感情上又经历了一次波折。她的丈夫,那位退任的县人大办公室主任的公子,那个在生活中风流成性的男人,当初就是被她的嘴巴迷住的。每次和她亲热时,他都会给她的嘴唇留下些难能忍受的痛楚……后来,她的嘴唇便再不能吸引他了,他在外面乱搞,最后撇下她和女儿,同一个比自己小很多岁的富商之女私奔了。据说那女人有一张很小巧的嘴巴,戏剧美学上俗称的 “樱唇”。
工作上的不顺,以及生活中的种种际遇,起初还能让她保持从容的心态。她领着微薄的工资,却也足够她们母女打点生活了。她在剧团跑着龙套,靠以前打下的功底和积攒的人气,也能做得游刃有余……本想生活可以这样平淡地持续下去,女儿初中、高中,及至大学毕业,结婚成家,她也就能卸下身上的担子。或许再找个聊以抚慰的人,走完后半生也算个圆满结局。
命运发生转折之时,她未曾想到会得到剧团的重任——女主角忽然辞职了,和情人去了深圳。主角的人选一时成了空缺。领导焦头烂额,主角的丈夫不但来找他闹事,还要顶住上面的压力——演出是硬性任务,必须要完成的。她对领导说,要不我来试试?
她临危受命,却处变不惊,并不认为自己抓住了机遇,从此会迎来人生的某个拐点。她在台上唱着,不经意间朝台下看去时,见观者寥寥。剧场内的昏暗,并不能因几名老年观众的痴迷而变得熠熠生辉。她不去在意,觉得上天的垂怜,总该在这样的突变与落寞中发生……只是好景不长,几场重要的演出任务结束之后,剧团忽然解散了——她艺术生涯的短暂辉煌,其实是一种病入膏肓般的回光返照。
她积蓄不多,甚至可以说没有积蓄。那不多的积蓄被她存进银行,存折用一块手帕包起来,压在箱底。和那存折放在一起的,还有女儿满月时爷奶送的银镯子,还有一枚袁大头的银元,那是母亲送她的陪嫁。她清楚它值不了多少钱,但每次翻弄出来时,都会用指尖捏住镍币的一端,嘟起嘴巴吹一口气,快速将镍币移至耳边,便会听到风声颤抖的余音……对财富的淡漠,其实大都是自欺欺人。这是她在女儿上大学之后的那几年里得出的结论。
缴了学费,把必需的生活费打到女儿银行卡上,买完出行的衣服、皮箱,到准备去买两张远程车票时,她便感到捉襟见肘。为此她偷偷哭过一次。但她必须要送一送女儿,而手里的钱,恰好只能买下一张单程的卧铺车票。从车站回来,她谎称卧铺票卖完了,只能买两张硬座车票。为此她感到庆幸——买完硬座车票之后,竟能余下她的另外一张返程车票。硬座也没关系,我们可以轮流睡觉,两个人的座位,完全能抵得上一张卧铺了。物美价廉。她这样心虚地对女儿说。
她或许应该感激她的父亲,得知女儿要上大学之后,脚步蹒跚赶来县城,塞给她八百元钱。也多亏了这八百元钱,她不知道,到了大学之后,还会有另外的花销,还有她独自返程时,睡过了车站,还需补上一张短程车票。还要谨防在人流密集的售票大厅,有小偷割了她的行李,只是钱被她放在贴身的内衣兜里,才能保全自己这初次的长途旅行。
接下来的日子,她完全陷入到一种惶恐不安的境地之中。每天一睁眼,便要绞尽脑汁,想怎么去挣女儿的生活费。自己每天的花销,她曾在一个本子上记录过,大不了是油盐酱醋花了多少钱,买米买面花了多少钱,电费卫生纸花了多少钱。看那将近三年的记录,看不出她买肉买菜花了多少钱,买衣服买化妆品花了多少钱。除去必要的开支之外,她省略了所有不必要的花销,甚至每次来例假,用掉大量的卫生纸,她都会认为是一种罪过。那微薄的工资,不到万不得已她不敢去动。待到两三个月过去,存折上有了一定的积蓄,她才敢松口气,才敢让自己感冒一回。将自己放倒在床上,睡上一天一夜的懒觉。但等第二天天气晴好,身上又有了力气时,她又会为那无端浪费掉的一天而深感不安……每当压力不能解脱,她便躲在家里,放声大哭。因为是一个人,所以便哭得放肆,毫无顾忌。有时抱着枕头哭,像抱着另一个自己;有时对着镜子哭,像以前在剧团工作,对着镜子练功一样。待哭过了,心里也舒服了。车到山前必有路,她会这样安慰自己。
即便这样,日子仍旧捉襟见肘。说不准什么时候,她会接到女儿打来的一个电话,告诉她学校里又要缴什么钱了。她惊慌失措,却故作镇静,告诉女儿,妈这就去给你汇钱。女儿每次给她打电话时,她都能从女儿的口气间听出她的诉求,听出她的羞愧与不安。她会恍然大悟说,是不是又快没钱了?女儿这才压低嗓音 “嗯”一声。她会瞬间崩溃,她能想象到女儿的窘迫,因俭省而在同学面前生出的自卑。握话筒的手止不住簌簌发抖。她在电话里不停地责备自己,脸上流满了泪水。你看,妈这记性,这几天事多,忘了快到月底了……放下电话,她仍旧会大哭一场。她不是为自己而哭,而是心疼自己的女儿,她觉得亏待了女儿,使她不能像别的女孩那样,穿漂亮衣服,用时髦手机,节假日结伴去想去的地方旅游。
那几年,她想过做生意,却苦于没本钱,无门路,只能想想作罢。做不了生意,只好去出卖体力。其间她做过保洁,当过保姆,干过钟点工。确乎所有能挣到钱的行当,她都去尝试过。最窘迫时,她甚至想过要把母亲送她的银元卖掉,虽知道换不了几个钱,但她却想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办法……女儿钱要得急时,她想过去卖血,但医院已不再做这种生意;即使能卖,也只能暂解燃眉之急,而仍有后顾之忧。生活曾让她一度产生了消极的情绪,不去想事情积极的一面,而总是将任何事都推入悲观的虚构。她总是想女儿生病了怎么办?女儿大学毕业,要找工作怎么办?或者某一天出了意外,急需一大笔钱,她这个做母亲的,又该怎么办——那就去卖肾好了,她如此决绝地想。甚而留意过如何将肾脏卖掉的途径。她又曾无耻地想过,不行干脆就去做妓女算了,虽人老珠黄,但她却知自己尚存几分风韵。她身材保持得不错,靠着多年做演员的经验,风月场上还是会迷倒众生。至少迷倒那些一夜暴富的乡下土包子,肯定不在话下。
每每在走投无路的设想中,她会放声大哭。泪水的宣泄就是这样奇怪,每次哭完,她总会找到一种心理及生理上的平衡。
若不是出现了一次转机,她真的说不定自己会走到何处去了。
那段时间她给人看摊,偶遇一位剧团的前同事。他本来已从她的摊前走了过去,她也并没看到他。但冥冥中他却走了回来,眯了眼打量一件挂在衣架上的衣服。直到相互砍价时,她才认出了他,叫了他的名字。他照旧眯了眼看她,直到认出她来,眼睛才睁得老大:何红英,怎么会是你!
他说,你老多了,老得我都不敢认了。
两人倚着柜台,相互打听去向不明的那些同事。有的发了财,有的离开了这个小小县城,过上了一种让人无法想象的生活。有的年纪轻轻便撒手人寰,去了另一个世界……两人发过一通感慨之后,又相互交流起各自的境况。
何红英,我真想不到你会干这个!
她面颊微红,羞赧地低着头,轻声说,我不如你们,我一个人拉扯孩子,孩子上大学,需要花钱啊!
凭你的本事,再怎么落魄,也不至混到这份儿上,简直大材小用啊!赶紧辞了算了,跟我走,我带你去……不说挣大钱,也比干这个收入多好几倍。
她心内一喜,觉得抓住了救命的稻草。这才知道,这个当年籍籍无名的剧团乐师,如今已是一位民间乐团的经纪人了。周边乡下的婚丧嫁娶,都有他的生意。
自此,她便做了一名 “哭丧女”。
她知道这世上的任何东西都可拿来贩卖,诸如物品,诸如身体——她想过去卖血,想过去卖肾,甚至想过去做妓女,但她终究没有想到,有一天她会拿自己的 “哭泣”用来出售。
第一次去 “哭丧”,她也曾犹豫过。但却不得不拿出百分百的热情。哭一次丧,能得两百块钱,时间只不过是短短的四十分钟。如果你觉得不适应,三十分钟或二十分钟也可以,但不能低于二十分钟。前剧团乐师这样对她说。那两百块钱,对她有着莫大的吸引力。相当于她打工三到四天的收入,如果能抽出时间,她下午或晚上还能兼职一份工作,这样算下来,每月她将会有一笔可观的进账。生活中的难题将迎刃而解。
她第一次的 “出演”,面对的是一个相对简朴的乡村葬礼。死者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从她随乐师赶到葬礼现场,便再次感受到初次登台时的那分压抑与紧张。死者的亲人们穿着白花花的丧服,红漆棺材停放在狭小庭院,上面罩着硕大的凉棚。案前放着贡品,燃着香烛。她也曾留意过死者的遗像,试图从那陌生的面孔中找到一丝亲切之感。她知道她所要扮演的角色,是死者的某个女儿,或是她的某个侄女。她要代表她们,用动人的方式,演绎出对故去亲人的思念……但这种试图却毫无成效。她仍旧感到紧张。当她换上一身白色素服,头上缠着孝布,外面鼓乐声已止,主持葬礼的人用清亮嗓音,宣布葬礼的下一个程序。一支唢呐发出婉转呜咽,以完成她 “哭诉”前的声音调试……她仍旧万分紧张,手心出汗,大脑一片空白。乐师看出她完全不在状态,凑近前,轻声提示了她一下。
寂静是开演的前奏,无论是曾经的舞台还是如今这个简朴的乡村葬礼。乐师的话让她醍醐灌顶,她真就把那口红漆棺材当成了舞台上的道具,把那些跪倒在棺材周围的人,当作了群众演员。她的左右,还需两位服丧的女人将她搀扶,以体现葬礼的肃穆与隆重。而实际上,葬礼的主人是把她当作自己的一个亲人来看待的,没有任何雇佣间的淡漠与轻薄。她肩负众望,以使这人间最后的聚会,赋予更多抒情的色彩。而那两个搀扶她的女人,必是死者的女儿或媳妇,她们羞于表达,而心甘情愿做了她的陪衬——她们是配角,是她以前在舞台上常演的角色。
她毫无争议地成了这个舞台的主角。单支唢呐吹响,仿佛舞台上铜锣的开场。她完全入了戏,用婉转的唱腔,哭出对亲人思念的道白。围观的众人在棺材前面围起一条甬路,从甬路开端,到棺材摆放的位置,只不过数米的距离,却被她走得波澜起伏。她一步三跪,以头伏地,先是哭诉死者一生的不幸与劳苦,而后表达亲人对亡者的思念,其后绕棺材一周。观众们泣不成声。而那些她所代表的亲人,竟在 “哭丧”中途,便开始大放悲声,最后抱住她,错将她当成一位异姓的亲人。
她初次的表演,便进入到物我两忘的境地。这是戏曲表演中最高的境界。她的脸上流淌的是喧嚣的泪水,竟然在“哭丧”结束之后,仍旧发出不由自主的抽噎。让迅速从情绪中摆脱出来的观众,甚或死者的亲属,认为她一定刚刚经历过亲人逝去的伤痛,或是遭遇了什么愁闷的事情,从而才会在别人的葬礼上,有着这样真挚的宣泄。
她渐渐爱上了这份职业。由于表演真挚,她渐渐得到了众人的认可。很多死去亲人的家属,甚至点名要她。他们说,你看你看,她是动了真情的,她的泪水不是伪装出来的……她那个乐师同事,为了照顾她,一天会为她安排诸多场次的 “演出”。钱来得非常容易,她再也不用每天早上醒来,绞尽脑汁去想怎样赚取女儿的生活费了,再也不用等女儿打来催促汇款的电话,揪心而愧疚地跑去银行汇款了。她专门为女儿准备了一张银行卡,把不定期的收入,不定期地存入进去。除此之外,她家里的那张存折上,也有了不少的盈余……但这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她内心的感受。她似曾找到以前在剧团工作时,那种气定神闲的感觉。每次为陌生的死者哭过之后,她都会得到一种心理上的安慰——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她想。就像以前有压力时,她都会用哭泣来寻求缓解一样。而现在,她再不用被动地去哭泣了,而能在一份所谓的工作中,让泪水顺其自然地释放。
生活稳定之后,她也并不是没有了烦恼。她要面对更多的压力与烦恼,比如同事间的竞争。比如女儿在电话里问她:妈,你现在做什么?怎么会给我汇这么多钱?我花不了这么些钱的,你不要太辛苦……每当遇到这样的追问,她都会略有踌躇,她不想让女儿知道自己干着这样一种营生。直到女儿暑假回来,见她早出晚归,对自己所做的 “工作”支支吾吾,便尾随跟踪她,这才知道她的母亲做着这样一种职业。女儿躲在葬礼的外围,听到扩音器里传来的母亲悲戚的声音,不由得泪流满面。
除了觉得愧对女儿,她也会在父亲的面前略有羞愧。父亲是个老戏迷,终生为她骄傲。剧团解散之后,父亲便得了脑淤血,脑子变得有些迟钝了。每次回家,父亲都会语焉不清地问她最近又唱了什么戏。她羞于撒谎,对父亲和家人说自己加入了一个民间乐团,就是那种别人娶亲或庆寿时去参演的剧团。她唱的是主角,演出任务不累,收入却还不错。
父亲便频频点头,含混不清说,等我做八十大寿,你就把乐团带过来,也给爹唱一场大戏。
她微笑着点头,连连称是。
他们这个行业,以前不知道,原来竞争也会如此激烈。乐师管辖下的民间乐团,像她这样的 “哭丧女”,共有三位,还有两位为男性。而在城市周边,零星散布着很多这样的民间乐团,自然也有更多 “哭丧女”存在。如果单从业务能力上来说,她不惧怕她们。她们没有与她竞争的实力。但她们各有各的招数,比如那两位 “哭丧男”,其中一位给乐师不定期地送过烟酒之后,另外一位显然更有头脑,他干脆和乐师谈妥了每次从中抽取提成的商业构想,并从此形成这个行业内不成文的规矩。每个用眼泪赚取钞票的人,都要给乐师一份提成。但竞争却不会因此结束…… “哭丧女”就不用说了。那位年轻的 “哭丧女”,干脆做了乐师半公开的情人。自收入稳定之后,乐师对她显然没有了最初的热情。这也情有可原,他必须掌控乐团内业务的平衡。但在别人的竞争下,她觉得对乐师多了一份人情上的亏欠。她也曾从自己的收入中另拿出一份,准备送给乐师。但乐师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我们在一口大锅里吃过饭,不帮你帮谁呀!乐师这样说。他们之间有过一番推让,在动作的磕碰中,乐师攥住了她的手腕,并拍了她的肩膀,让她感知了某种 “情色”的暗示。这没有什么,她不会因做了乐师的情人而感到屈辱。她对他颇有好感。在谈婚论嫁之前,她曾把乐师当过最合适的人选。只是在前夫强大的攻势下,当时穷困潦倒的乐师知难而退了。
两个已近不惑的男女,对这种事自然没有多少困惑。但乐师 “情色”的暗示却隐晦不明。他似乎在等着她主动投怀送抱。她错把乐师每次不经意的玩笑,或一个眼神,都当作了 “情色”的暗示。她竟然在自己的想象中,可笑地爱上了乐师。从而在乐师面前,多了些期期艾艾的怨情。
那次乐师打电话通知她,明天去赶赴某地的葬礼时,她撒谎称:我发烧呢!
严重吗?
起不来,一天没吃饭了。
那赶紧去医院。
家里就我一个人,况且天都黑了……
乐师很快赶了过来。见她果然躺在床上,鬓发散乱,衣衫不整。
起来吧,穿衣服,我送你去医院。
她期期艾艾看着他。
乐师愣了,误解了她的意思,冲她笑笑,说,不方便……我到外面去等。
她向他伸出手。
乐师不知她想要表达什么,懵懂地伸出手,回应了她。
她把他拽到床上,抱住了他。
乐师被动地由她抱着,却没有任何举动,脸上是一副惊讶的表情。她有些羞恼,问他:嫌我老了?
乐师忽然笑起来。他笑着对她说,做了这种事,以后就没办法打交道了。我们还是做兄妹吧。
她彻底误解了乐师,起初还心存疑虑,担心乐师会不会因此而冷落自己。但乐师待她一如从前。一次喝醉时,乐师对她坦白了自己身体的隐疾,他得了病,房事不举。他不是不想做男人,而是做不成了。乐师以一种调侃的语调说。她 “咯咯”笑起来,笑过之后,一切的疑虑烟消云散。
她过起了一种闲散的生活。每当心情很好或不好时,她把以前积攒起来的戏曲碟片翻找出来,调至音乐伴奏功能,重温一段曾经再熟悉不过的戏曲唱段:
听谯楼打罢了一更时分
薄命女张翠鸾好不伤心
冒风雨受饥饿心酸难忍
思想起生身父滚下泪痕
……
对唱腔的把握她仍旧驾轻就熟,却很难融入到剧情规定的氛围中去。她记得以前在剧团时,每唱到这一段,不需情绪上的任何调度,泪水便会潸然湿了眼眶……她不以为意,只是把它当作了一种消遣,却在这种消遣中得到一些启示。再次去 “哭丧”时,她便动用了戏曲表演中的手段,比如动作上的闪转,比如唱腔上的委婉。她将普通的念白与哭诉用戏曲的方式演绎出来,从而在撕心裂肺的氛围中,多了一些可观赏性。她还会在 “哭丧”临结束时,扑到死者的灵柩前,抱住死者的遗像,将人间的离别与不舍演绎得淋漓尽致。几次三番,她在搀扶者的规劝中将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
她竟然将 “哭丧”这一职业做得如此完美,好像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对戏曲艺术钟爱的一种表达,并在现实中为这种钟爱找到了恰当的接口与延续。她以假乱真的哭泣,俨然成了生理上一种必须的需求。
在一次 “哭丧”表演即将开始时,她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那是她的哥哥打来的。她掐断,手机又响。她不得不去接听,哥哥在电话里已是泣不成声,告诉她,她八十三岁的老父亲,因心脏病突发,忽然辞世了。
她不能推掉迫在眉睫的表演。唢呐已吹响前奏。她仓促上阵。那是她最不成功的一次表演,僵硬、呆板,完全不能融入葬礼的氛围。恍惚中她错把陌生的死者当成自己的父亲,却处处感到隔膜。她内心真正的悲伤,容不得半点伪装。她应付了事,而后匆匆赶赴在奔丧路上。
父亲与她最亲。初进剧团时,父亲披星戴月去县城看她,怀揣家里刚刚打下麦子后新蒸的馍。家里的杏树上结了果子,父亲也会给她送来几枚。她离婚,父亲揪心扯肺地惦记。女儿上大学,他将卖玉米的几百块钱偷偷塞给她,那可是他半年的生活费呀。她在路上边走边哭,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强烈地折磨着她。
等赶到家里,父亲的遗体已停放在灵柩里。远远见红漆棺材安然停放于庭院,棺头翘起,仿佛一艘准备驰往天庭的木船。家里的亲人们身着白色孝服,在院内走动,或静守在棺材两侧……她手扶院墙,哭不出声来,只能在心里大放悲声。但情绪的不能释放,终究会像决堤的洪水,使她的身体没了一点力气。她一步三晃,踉跄向院内迈开步子,却忽然放出一声凄怆的念白:我苦命的爹呀!这正是她在诸多次 “哭丧”中的一句标准念白,随着这声念白的脱口,她的泪水破堤而出,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里,她一下子进入了角色。
她哭诉着父亲的苦命,用念白的方式,回忆了父亲披星戴月,给她送去新蒸的馍,以及成熟的杏子。在他的眼里,她始终是他最疼爱的姑娘;在他的眼里,她永远也长不大,永远让他操心。她追悔自己婚姻的不幸,让父亲不能安然度日,她隐去父亲私下里送她钱的事,那是因考虑到哥嫂的在场。如今日子好过了,还没等女儿孝敬你,爹呀!你就撒手去了,你让做女儿的怎么活下去……听到她的哭声,嫂子和侄女赶忙跑过来,搀扶着她。其他的亲人白花花跪倒一地,这更契合了表演中的某种情境,使她不能自拔。她一步三跪,以头伏地,在亲人的拉拽与劝解间,动用了戏曲表演中的身段,几次向父亲的遗像扑去……从院门口到父亲灵柩的停放地,只不过短短数十米的距离,却被她走得波澜起伏,肝肠寸断。
只是在靠近父亲遗像时,她身体内部的某根神经忽然出现剧烈的反应。耳膜在震荡,那个依附在她体内的幽灵,脱壳而去,她被迅速打回原形,瞬间愣怔在原地。
那张黑白遗像不知父亲什么时候拍的,是她再熟悉不过的面容,却比她印象中的父亲要年轻许多。表情依旧是平常所见,温厚、木讷。但她却分明看见他的嘴角微微翘起,仿佛暗含了一丝微笑。在嘴角的牵扯下,生硬的面部起了微妙变化,她竟然从父亲那双和善的眼睛里,读出了一丝嘲讽。她仿佛听到父亲用半开玩笑的语气在对她说,至于吗,闺女?
哭声与念白戛然而止,她这才意识到这是自己父亲的葬礼,而非某个陌生人的葬礼,而非某个她通过表演手段、能赚取到钞票的葬礼。在这样最为素朴的葬礼上,眼泪不可以用来出售。所有的念白,所有的哭诉,都显得异常做作。
内心的喧嚣轰然隐去,她终是感到了强烈的自责,甚而羞愧。她本该站在亲人们中间,默默地流泪,静静为父亲守丧。她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一点过,自己在父亲的葬礼上,仍在表演。偷偷瞟一眼周围的亲人,长辈和晚辈们都以惊讶的目光看着她,由于悲伤挂在脸上,那惊讶便显得异常冷漠。站在她身边的嫂子,甚至轻蔑地撇了一下嘴角。
她彻底安静下来,为自己的虚情而感到深深的懊悔。她向来是一个崇尚本真的女子,容不得丝毫伪装……从此整个葬礼上她一言不发,像一位看客。甚而讨厌着别人的哭诉,觉得那是一种可笑的伪饰,是做给别人看的。特别是父亲下葬时,哥嫂几次扑进坟坑里,阻止掘墓人用土掩埋。她甚至轻蔑地想,人活着时你们不孝,人没了,做这些样子给谁看呢?
但让她感到奇怪的是,随着情绪的克制,眼泪竟化为了空气。她不是不想流泪,不是不想对父亲的离世有一个自然而真切的表达。但她却最终失却了这种能力,她怕一张口,便重回表演的老路上去……越是有着这样的担心,心里便会有一个声音在时刻提醒着她:眼泪是不是真实的?你是不是又在表演?她觉得所有的看客都在盯着自己看……这种莫名的情绪,让她在整个葬礼上疲惫不堪,显得无所适从。悲伤不能化作泪水,便全部变成一种雾状之物,箍在脸上,使她的脸像戴了一层面具。她神思恍惚,面部表情略显僵硬。在别人看来,好像她在父亲的葬礼上负气着什么,又好像她对哥嫂安排的葬礼深怀着不满。
直到回到家里,她才放声大哭了起来,哭得真切而自然。哭过之后,心里才好受了些。回想起自己在整个葬礼上的表现,一前一后简直判若两人。她怪异的举止,肯定会引来众乡邻的耻笑。如果父亲活着,会不容置疑地为她申辩,会说她是最惦记自己的孩子,哭不哭的又怎么样呢……想到这儿,她又大哭了一场。像是对父亲的哀悼,又像是对自己的谅解。
父亲去世半月之后,噩耗再次袭来。她身体一直不太好的母亲,猝然离世了。
她赶回家中奔丧。由于有了前车之鉴,她再不敢轻易将自己的情绪自由地宣泄,不敢有任何的念白与哭诉,只想跪在母亲的灵柩前,默默地流泪。颇为奇怪的是,别人只见她面部抽搐,却看不到她流下的半滴泪水。她也感到不解。本来努力地哭着,却只是干哑着嗓子发出几声呜咽,仿佛野兽的悲鸣,却感觉不到有一滴眼泪润湿了眼眶——这才知道,眼泪作为生理表达上最常见的一种特征,于她已是稀有之物了。
母亲离世后的半个月,哥哥又因车祸去世。
她在哥哥的葬礼上不哭,不诉,亦不流泪。
起初她不以为意,认为这只是一种生理上的失调,就像偶尔的感冒,就像如期而至的月经。如今它们出现了紊乱,等过段时间,便会不治自愈。她仍旧奔赴于各种葬礼,专心做着她 “哭丧女”的职业。只是每次在陌生死者的面前,她都会倏忽想起那些逝去的亲人,恍惚中仿佛又看到父亲遗像中那嘲讽的表情,甚而会听到他半开玩笑的话:至于吗?闺女……每当这时,她都会感到一种由衷的羞愧,绷紧的神经顿时松懈下来,本来蓄积的饱满情绪,也像溃败的潮水,一蹶不振。
眼泪成了一种久违的东西。起初她不以为意。她对待自己的工作,从此却很难有一分专注,难以付出更大的热情。每次的哭丧,都被她做得潦草、应对、敷衍了事。
她开始彻夜失眠,面色黑黄,体重下降。起初她仍旧不以为意。
她知道自己的病因所在,只是不能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如果能够大哭一场,真正地大哭一场,将心里的负面情绪排泄出来,身体便会不治自愈。为此她开始为 “哭泣”寻找各种途径。每次“哭丧”开始时,她都会像以前在舞台上等待开演那样,闭目静息,调动内心的情绪。她会把每个陌生的死者想象成自己的父母,但这种努力却难见成效。夜里她还会躲到护城河边,面对黑暗中静默的流水,想象这世上众多的悲苦齐聚一身,不由发出凄厉的呜咽,等待眼泪夺眶而出,让夜游人误以为她是一个走投无路的自杀者。她甚至罪恶地想过,女儿出了车祸,先她而去。在自己家里,她对着一面镜子,披头散发,像一个即将崩溃的疯子。她还会偶尔自残,用针尖扎破自己的皮肉,切菜时故意用刀划伤自己的手指,看疼痛能不能使自己流出眼泪,却往往会收到相反的效果——自残只会让她兴奋,却难能感受到一点点悲伤的氛围。她还看过各种悲情剧,看过各种煽情的节目,想借助别人的悲伤,唤醒自己沉睡的眼泪。但不管屏幕上的人物哭得多么凄惨,命运如何曲折,却不能让她有一点点触动。
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得了一种病,一种不能哭泣的病。
那年女儿从南方休假回来,发现了她精神上的异常。
她形销骨立,一双凹陷的眼睛仿佛干涸的池塘。在女儿的追问下,她才道出困扰她已久的病情: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害怕与人接触。每次去街上,会觉得那些迎面相遇的陌生人,穿着白色孝服,脸上戴着面具……他们以亡人的名义,在她的现实世界中游走。她正常的生活,俨然成了一场庞大的葬礼。
女儿听得心惊肉跳,起初怀疑她得了抑郁症。想想母亲这些年独处,供她读大学,找工作,直至结婚,其间经历了怎样的艰辛!她或许是在极端的压力下,才染上这种病的。母亲所经历的种种痛苦与磨难,似乎都与自己的拖累有关。想到这里,女儿失声痛哭,坚决要带她去看心理医生。
面对女儿的哭泣,她反倒微微笑了。
她对女儿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就是觉得憋屈,不能流一滴眼泪,不能痛痛快快大哭一场——这要去看医生,还不被人笑话!
听了她的话,女儿也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人不能哭泣,不能流泪,听上去确实有点莫名其妙。
女儿背着母亲,还是偷偷去找过心理医生,但医生并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
休假临近结束,女儿和她商量,决定带她去南方生活。
她有些抵触。但后来又想,离开这个糟糕的环境,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况且那时女儿已有了三个月的身孕,需要人来照顾。
她喜欢南方,喜欢它的明丽、湿润、干净。她去时北方已近初冬,身上穿了御寒的衣服。但经历了一天一夜的旅程之后,仿佛一下子从料峭的寒气里,步入一个天然的花园。那种经历好像做梦一样。
南方的生活让她感到新奇,情绪却仍时时处于一种消极的状态中。特别是独处时,特别是走在陌生的街头,周围全是她听不懂的话音,她便会再次有了一种想 “哭”的冲动。她会用完全想象的方式,为自己安排一场虚拟的葬礼,她会在葬礼上任意挥霍自己的情绪,却不能使自己真正地开心起来。
好在有女儿的陪伴,她也不敢太任性地放纵自己。每见她落寞时,女儿便会俏皮地问她:妈,是不是想家了?
她为难地看着女儿,像个不更事的少女。
女儿便调侃她:你对我来说,便是家;我对你来说,也是家。我们在一起,就是在家里。你还想什么家呀!
为了转移她的注意力,女儿会为她安排很多零碎的事情去做。比如买菜、做饭、洗衣服、拖地。在母亲面前,她又会故意放大着自己妊娠期的反应,她在她面前撒娇,做出痛苦的样子,对她百般依赖。
她依据自己怀孕时的经验,给女儿以安抚。她会说,实在不好受,你就哭一哭,哭出来就好受了。
女儿抬抬睫毛,眼泪便轻易滑脱眼眶,在脸颊上滴淌——这是女儿生理上最正常的一种反应,也是她让母亲如此的辛劳、所表达的一种歉疚。
但她感觉不到女儿的良苦,只会惊讶于那些泪水。她痴迷地看着它们。那些在光线中变得晶莹剔透的泪水,最终在她目光的触摸下,变成稀松平常的液体。
对于新生儿的期盼,让她得到了暂时的解脱。她盼着他早日降生,猜测他是男是女。她愿意是个男孩,女儿却极力反对。她更希望是个女孩,甚而对她重男轻女的思想作出批判,责问她是不是在她降生之际,便失望过。她苦笑。她们又开始为那婴儿的名字争论不休,男孩叫什么,女孩又叫什么。女儿嫌她起的名字土气,而她又反驳说女儿起的名字像一个外国人。最终她们会在名字的争端上达成妥协——如果是男孩,便由她来起名字;如果是女孩,便由女儿说了算。她去商场买来各种柔软的布料,给新生儿做小衣服。女儿嫌那些衣服土气,却不去说破,故意放纵她的慈爱。只是在她开始找各种旧衣服、准备孩子的尿布时,女儿才会善意地制止她:妈,现在谁还用尿布啊!现在都用尿不湿、纸尿裤了!
由于忙乱,她的情绪开始变得节制而正常起来,似乎又回复到以前的状态。
孕产期的前十天,她陪女儿住进了医院。
婴儿的出生很不顺利,像不甘心轻易来到这世上一样,又好像要故意折腾他的母亲,以烘托他隆重的出场。一波一波临产前的阵痛,让女儿在产床上哭叫、呻吟,汗水往往会浸湿了床榻。她心疼得要命,甚至想代替她经历这 “幸福”的痛苦,但实际上却帮不上一点忙。除了尽心照顾、安慰她,她开始在女儿与医生之间跑来跑去。她询问医生,女儿会不会遇到难产?会不会出现什么不测?她饶舌的询问一度让医生感到心烦。
直到女儿被推进产室,她才安静下来。
在那个清晨,她终于听到了破涕的哭声。
哭声嘹亮,犹如针刺,在她心头扎了一下,却没有任何特殊的感觉。
待她走进产室,看到新生儿的面容。世界仿佛最初的样子。是一个男婴。在护士的协助下,她生疏地将他抱在怀里,走到女儿床前,想让女儿初尝一下为人母的喜悦。
女儿从床上欠起身子,脸上汗津津的,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女儿看了新生儿一眼,目光却忽然停留在她的脸上。
妈,你哭了!你流泪了……
女儿这样惊喜地对她说。
责任编辑 梁智强
刘荣书Liu Rongshu
河北省滦南县人。作品见于 《江南》、 《山花》、 《中国作家》、 《人民文学》、 《天涯》等杂志。有作品被选刊选载并入选多种选本。著有长篇小说 《一夜长于百年》,中短篇小说集 《追赶养蜂人》、 《冰宫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