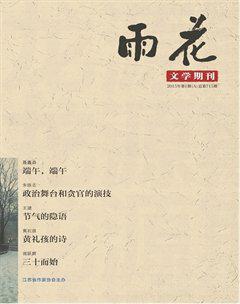雨催花发
2015-07-20王德安
■ 王德安
雨催花发
■ 王德安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就与当时江苏省唯一的文学刊物《雨花》结上了缘。江苏省作家协会每月一次的例会,我认识了主编章品镇,编辑曾传炬,也认识了一些江苏的作家和诗人,如《狠张营歌》的忆明珠、《水乡行》的沙白、《我是煤我要燃烧》的孙友田、《静静的水杉》的丁汉稼,还有赵瑞蕻、杨苡、白得易、鲍明路、王鸿、黄东成等等。这些作家和诗人都是我们这些业余作者仰慕的人,以前只是在报刊杂志上见过他们的名字,现在是近距离的交流,真有一种“受宠若惊”如沐春雨的感觉。
那时的编者和作者不懂吃请送礼这一套,好长时间我只知道《雨花》编辑有个叫曾传炬的,也是位诗人,常看到他在报刊上发表的诗。他在退稿信上的落款是:传炬,甚至是:弟传炬,那时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年轻人。他的退稿信写得很认真,一首诗好在什么地方,还有哪些地方欠妥,都分析得头头是道,书信往来神交已久。我常常按照他的意见修改诗稿,一直把他当作“催花的春雨”。直到1963年秋天,我才见到他,不过没见到脸,只见他伏案午睡的样子。那时没有电脑,甚至电话都很稀有,那天我是把改好的一首诗趁午休时间送到编辑部的。当时的《雨花》编辑部在总统府内,叫省政协大院。我推开门,只见一位中年人伏在办公桌上午睡,门卫告诉我,那就是曾传炬。我估计他刚刚入睡不便打扰,就将稿子放在桌上,悄悄地走了。
后来,他在省作协的例会上认出了我。他说那天你怎么不叫醒我?原来他正想告诉我一件事,我的那首题为《家书》的诗已经在《雨花》10月号上登出来了。《家书》一诗是9月16日写的,那天收到受灾家乡的一封报道丰收的信,我激情于怀一气呵成写下了这首诗,在一个小型朗诵会上我朗诵了这首诗,《新华日报》留下准备发表,怎么会发在《雨花》上了?他告诉我《雨花》第10期缺少振奋人心的好诗,就到《新华日报》副刊部找稿子,发现了这首《家书》,按当时的话说“兄弟单位协作”,把稿子要了下来。他觉得稿子很好,很有激情,特别是结尾:“信上每个字,/哪个没经汗水泡,/哪个不比糖甜蜜,/……小小的一封家书啊/写着我那穷困的家乡/正一步步走向富裕。/一个字就是一滴油啊,/我要把它加在/我那机床的油眼里……”他一边背诵一边感叹:写得有工人味、有工人味!他说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对描写家乡遭灾的那一段作了小改动,原诗是“春二月要水不下雨,/三伏天要晒决了堤。/咱要走社会主义,/老天爷肘(zhou)着扭着不同意!”“肘着扭着”大概是你们家乡方言,就是不让你顺心的意思。但发表出来怕很多人不懂,我把它改成了“扭着脖子不同意”。他说得那么诚恳,又那么详细,让我好感动。
一篇作品从写好到发表在刊物上一般是三个月,比如一月份的出版了,二月的稿子应该在校对,三月份的正在发稿。而我这首诗从写成到刊登只花了半个月。这在那铅字排版的时代恐怕算一个奇迹。其间曾传炬老师为这首诗跑报社、跑印刷厂,抽稿子,换稿子,编辑、校对,稿子刊登后还组织几位诗人写点评,所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
从此他成了我的良师益友,成了我心中的偶像。他的这种敬业精神也深深影响了我。他曾说过:“作品就是作者生的孩子,关心他的孩子就是对作者的尊重。”我至今保留着上世纪60年代《诗刊》《人民日报》《上海文学》等报刊的三十多封退稿信,其中《雨花》杂志的就有十四封!
后来我也当了编辑,我给自己订了一条规矩,来稿必复。虽然以后电话普及了,虽然那时有铅印的退稿信,但我觉得应该向曾传炬老师那样,尊重作者的劳动,用亲笔书信来与作者交流,当一阵催花的春雨。
我所在的杂志是一个以女性读者为主的综合月刊。女性的许多生理和心理上的问题需要向你倾诉,请你帮助解决,杂志就开了个“莫愁信箱”,虚拟一个“莫愁大姐”,大家一致推选我来担纲,对外保密!否则人家知道“莫愁大姐”是个大老爷们,谁还敢把那些隐秘的话告诉你?把作品当孩子,把读者当亲人,我努力写好每一封回信,这都是从“催花春雨”那儿学来的。一封封信或劝诫、或指点、或鼓励、或释疑,乃至为寻找一个药方或一种治疗方法,要向多位医生咨询。曾有过为帮助一位读者治疗肝病而满山遍野寻找垂盆草的事。那段时期“莫愁大姐”的名声大振,不少读者在得到“莫愁大姐”的指点后,经过努力走出了困境,大老远背着家乡土产来答谢“莫愁大姐”。这时编辑部的女同事都会“挺身而出”替我“隐姓埋名”。
《雨花》杂志当时有个专栏叫“雨催花发”,是作家和诗人对发表的习作评点的园地,那“雨催花发”就成了“传道、授业、解惑”的园地。对于诗歌的评点有个子栏目叫“拾贝人说诗”,我很有幸,就是上面提到的刊登在《雨花》1963年10月号上的《家书》被署名“杜子微”的诗人“说”了一回。
杜子微评点道:“更难得的是最后三句。它把作者的许多言语和心情,集中在短短三句,十分形象化地说了出来。既体现了作者工人的身份,比喻也很切当,又充分表达了思想感情,生动、鲜明、凝炼,使人一读难忘。”同时也指出诗中的问题在开头表达“家乡的好年成”的几句:“三千亩碱地上打的粮,/二十里苇塘捞的鱼,/新添的那台拖拉机,/才下的葱白小叫驴……”他说,碱地总是会打粮的,问题是打多打少;苇塘也总是可以捞鱼的,下了一头小叫驴也不一定说明年成的好坏。新添的拖拉机虽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这些句子表现“好年成”还远远不够。他指出“大概是由于作者没有深入挖掘、慎重选择的缘故吧!”
这样的点评真是一针见血,其实我根本没有农村的生活体验,难得一次下乡帮助收麦子,那感受也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这些句子都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这以后几十年的文学创作中始终记住“深入挖掘、慎重选择”,记住了这一阵催花的春雨。“杜子微”的笔名也就是帮助你杜绝漏洞,弥补不足的意思,他是谁?好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杜子微”就是沙白。
文革时,《雨花》停刊,作家们都受到冲击,我那时也像发疯似的卷入造反狂潮,和一批青年作者办了个造反刊物《红雨花》,扬言“铁笔横扫旧世界,锦绣河山我当家”。文艺界批判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把李进、章品镇、亚明押上台批斗,我也上台对着他们举拳头喊口号,在污蔑他们的大字报上签过名。造反狂潮使人性中邪恶的东西都翻腾出来,我觉得我在《雨花》上发表得太少,就编了顺口溜:“雨花雨花,高围墙铁篱笆,水难泼,针难插……”本应感恩春雨润花,倒过来说成是风雨摧花。
文革中我也没能逃脱被批斗、关押的命运,在阴暗的地下囚室里痛定思痛:那些被批斗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难道不都是和我一样,被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编造出来的吗?此刻我虽然当了这场浩劫的运动员,但同时也是个帮凶呀!
运动后期,我被宣布“平反”,把抄没的财物又发还给我,其中最珍贵的莫过于保存完好的三十多封退稿信,展信重读,更感到那上面的话殷切衷恳,字里行间体现了园丁护花的苦心。从此,又多了一分对“雨催花发”的深情。
1962年我曾把一组八十多首写百货商品的咏物诗《百货谱》投寄编辑部。退稿信是这样写的:“《百货谱》短小精悍、含蓄隽永,有一定哲理性。但你是个工人,应该反映火热的斗争生活,这类题材不宜多写,追求过甚,恐有误焉!”当时我还认为编辑部不识货,既然含蓄隽永为何不刊用?后来文革中把我的诗上纲上线,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批判《百货谱》,说它是和流沙河《草木篇》一样的大毒草。
例如:《花瓶》“你骄傲地站在窗前/欣赏窗外的风雨雷电/依靠那一注活命的水/托捧一个短暂的春天”(批判:《花瓶》影射社会主义是花瓶,攻击社会主义是短暂的春天)
例如:《摇头电扇》:“扇凉了别人,烧热了自己/你把感情都扩散在风里/暑热的人由衷地将你赞赏/你摇着头,始终那么谦虚”(批判:宣扬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只顾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
后来我才明白,在那个极左思潮的特定时期,编辑老师出于对文学青年爱护而发出的忠告,是提醒我规避枪口,不要重蹈覆辙。这和文革时一些有识之士为了保护文物古迹,在外面涂上油漆、糊上水泥有异曲同工之妙,退稿信上是护花的良苦用心啊!
1985年大概是5月份吧,省作家协会和《雨花》杂志联合举办“朱红、赵恺、王辽生诗歌研讨会”。就在开会的午休时间,《雨花》主编章品镇约我陪他出去转转,到哪儿去呢,他说到朝天宫吧。
昨夜因下了一场小雨,今天的空气格外清新。我们这一老一少就沿着北京西路翻过上海路的坡子走到莫愁路。我们一路上谈作品,谈文学和历史典故,我几次想把话题转到文革中我们办《红雨花》批判他的事,他都是淡然一笑:“年轻人都会冲动嘛!你现在就是要好好写点作品”,又把话题转了过去。
莫愁路两侧正在挖管道,在翻起的泥土上,章老眼睛一亮,捡起一片破碗底。我说要这个有啥用?他抹去碗底上的泥巴,一个青花款赫然显露出来:“大明成化年制”。哇!这是500年前的东西!这不就是古董吗?章老看我对此颇有兴趣,就跟我聊起了瓷器:3500年前就有了原始青瓷,然而最有文化内涵的还是元明清三朝的青花瓷,它上面的纹饰有人物故事、灵兽花鸟、山水楼台、诗词铭款等等,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审美趣味、风俗民情,甚至帝王意志都会在瓷画上体现出来。从一枚瓷片上能读到一段兴亡史,能发现一次兵燹之灾。历代都有失手打碗之人,青花瓷片就是历史散落的记忆、无言的证人。
他看我也对捡瓷片跃跃欲试,就让我先到他家去参观他的瓷片。研讨会一结束,我就到了他在青云巷的家。他家地方不大,但床边案头摆满了瓷片,特别是写字台上摆着他自制的青花瓷片吊挂。那是一块明代弘治年的碗底,画着东方朔偷桃献寿,章老将它修磨过,又为它镶了金属的边,吊挂在红木的支架上,俨然一个有文物意味的小摆设。还有那嵌在镜框里的成化年“携琴访友”,画得生动传神,韵味十足。章老又将在纸箱里的瓷片一片片拿出来给我讲解,年代特征、画意故事,那一天听得我如痴如醉。久蓄心头的历史文化磷片,被章老擦燃了。
章老告诉我:古代南京城内人稠物穰,只要动土挖坑肯定有青花瓷片出土。临走又关照我,雨后天晴你到工地上去,必有收获,因为小雨将瓷片冲干净了,你容易发现,这也叫“雨催花发”。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
从那以后,我成了章老家的常客。章老青云巷的蜗居成了“传道、授业、解惑”的课堂。捡到的瓷片让章老鉴定断代,讲解瓷片所属窑口的前世今生。捡到画意好的瓷片,我就写点解读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到章老家时也把文章带给他看。他看到《解读巨龙抖落的鳞甲》的文章时,连连叫好,说这是对捡瓷片这个活动形象生动诗意的概括。
有一天《周末》编辑部打电话来,让我到章老家去一趟。出什么事了?我急忙赶到青云巷,只见章老板着脸很不高兴,劈头就说:“你捡到柴窑的片子,拿来看看吧!”原来我在《周末》一篇文章里说章老带我在工地捡瓷片,几大名窑的残片都有: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和柴窑。章老说:柴窑创建于五代后周为周世宗柴荣的御窑。周世宗规定御窑瓷的釉色:“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文献中记载五代柴窑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馨”的描述,可以说柴窑是瓷中之最。《格古要论》里有一句:“柴窑最贵,世不一见”!可是柴窑至今未发现实物及窑址,柴窑有无的争论一直是陶瓷界的一大疑案。章老说:陶瓷研究和考古鉴定,不像写诗可以夸张渲染,而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学问,你可以随随便便说捡到了柴窑瓷片?一席话说得我面红耳赤、冷汗淋漓。我想我又遇到一位护花润花的“杜子微”。
章老长期编辑生涯,也像捡拾瓷片那样,在江苏文坛,除高晓声外,还捡到了陆文夫、方之、沙白、忆明珠……他们各自写出光彩夺目的作品,活跃于中国文坛。江苏作家群中的的陶瓷爱好者,顾尔谭、池澄、赵本夫、陈咏华,乃至现在的《雨花》主编李风宇等等,不知是不是也受到他的影响。而最早的捡拾者却隐身在幕后,章老是名副其实的伯乐,也是润花催花的春雨。
我也是他捡的瓷片,确切地说我是跟他学的捡瓷片。在以后的十多年里,我们在他的感染下,团结起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和社会上一批热爱陶瓷文化的瓷友,成立了江苏省古陶瓷研究会。“陶瓷研究考古鉴定要经得住历史考验”,章老的话言犹在耳,我们将它归纳成“求真、求实、求索”的行动纲领。我们捡瓷片、跑窑址、搞鉴定、赢官司、办网站、编图录、出专著,把一个古陶瓷的研究课题变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江苏“瓷片族”闻名遐迩,殊不知章老就是这“瓷片族”的先行者、肇始人。
去年我将新出版的一本解读青花画意的书《青花写意》送给他,他从病床上坐起来,翻开书连说“好、好!”指着上面的婴戏图说这几片很好,我也有一片和这个差不多,范曾看了赞不绝口呢,还为我画了一幅婴戏图。然后又说:“我那时自制了一个捡瓷片的夹子,背了个布口袋在工地上搜寻,你看像不像古时候敬惜字纸的老人?”说完他闭上眼睛微微笑着。此时此景,仿佛远处有一阵儿童颂诗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不论是写诗还是玩瓷,我都真诚地感恩“雨催花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