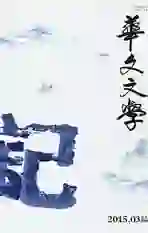宗教、政治与文化:索隐派与来华传教士的易学研究
2015-07-01王宏超
王宏超
摘 要:索隐思想是一种神学阐释方法,认为世界各民族都本源于基督教,后来的人类历史也都在《旧约》中有所预示。利玛窦在华建立了“适应”的传教策略,希望在原始儒家文献中找到基督教的痕迹。利玛窦重视儒家经典,尤其是《四书》,其“适应”策略可视为中国索隐派之先声。中国索隐派由白晋建立,傅圣泽、马若瑟、郭中传等人是核心人物,他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易经》上,希望从中解释中国古代的上帝信息。因为礼仪之争,耶稣会在华传教在清中期中断,到晚清才由新教重续其业。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理雅各以译介中国经典而著名,他对于《易经》以及其他中国古代典籍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这些书籍中的“上帝”,即是基督教的God。理雅各的思想可视为中国索隐派之后继者。易学研究在西方的兴起,与这些来华的传教士,特别是中国索隐派有密切之关系。
关键词:索隐派;《周易》;利玛窦;白晋;傅圣泽;理雅各
中图分类号:I05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5)3-0037-08
西方传教士来华,是中西文化交通史上的大事件。不论是唐代的景教、元代也里可温教,还是明清之际的耶稣会,以及后来的新教,其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毫无疑问便是宣扬基督信仰。但面对和西方文化有极大差异的中国,选择何种方式作为切入点,是诸多传教士最为关切也是最为焦虑的问题。而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也形成了不同的传教策略。本文所关注的来华传教士的“索隐”思想,便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传教策略。狭义的中国索隐派(Figurists),是指以白晋、傅圣泽、马若瑟等人为核心的传教士,以《周易》为研究中心,希图从中找到上帝的讯息。由于中国“索隐派”非常关注对于《周易》的研究,有时被径直称为“易经派”。关于传教士的易学研究,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①本文的重心在于说明,白晋等人之前,以利玛窦为代表传教士,主张“适应”策略和学术传教,强调中西文化间的融合与对话,尽管他们没有明确提出“索隐”思想,但他们可以视为索隐派的先驱者;而白晋之后,以理雅各为代表的一些新教传教士,继承了索隐派的传教策略,继续从中国经典,尤其是《周易》中阐扬上帝的信息,可以视为索隐派的后继者。
一、《圣经》阐释与索隐思想
索隐思想乃是天主教对于《圣经》的一种阐释方法,认为《旧约》隐含着神秘的、象征的意义,基督徒要以揭示其中的寓意为要旨。而且,基督教乃是唯一的信仰,其他宗教或真理,都是上帝的另一种显现形式,都可以通过寓意的阐释,找到共同的源头,即基督教。索隐思想由来甚久,最初的形态可追溯到犹太人寓意释经传统。这一传统最初在希腊后期犹太宗教与希腊思想相调和的氛围出现。如公元前150年左右逍遥学派犹太人弗洛布洛斯(Philobulus)献给国王托勒密·菲洛曼托(ptolemaeus philometor)关于《圣经》前五卷注释著作中,就“试图表明旧约的说教和希腊哲学家论点的一致性,断言希腊人(奥尔弗斯、荷马、赫西俄德、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曾经从犹太经典中吸取知识。”②在公元前100年左右一位犹太作家所著的《阿里斯底斯的使徒书》中,亦先于斐洛用寓意法解释旧约律典。③将这一寓意释经法推至极致的是希腊化犹太教思想家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约公元前25-公元50年)。
斐洛希望调和犹太教信仰与希腊哲学,他采用寓意方式解释圣经,认为《圣经》和柏拉图哲学并无矛盾,本质相同。他希望用“犹太的普世主义”来统纳希腊哲学,认为“柏拉图和他的学园派学者,其年代远在摩西之后。可以认为正因为他们学贯古今,也必然接触过犹太人的《圣经》,他们学说中的精华也正是从《圣经》得来的。”④斐洛之本意在于阐明犹太教乃一种普遍之宗教,能够吸引并赢得“所有人的关注,野蛮人、希腊人、陆地和岛屿上的居民、东方和西方各民族、欧洲和亚洲,从这头到那头的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⑤
继承此一犹太释经传统的是亚历山大学派,其代表人物为克莱门特(Clement)和奥利金(Origen)。克莱门特也着力调和基督教真理与希腊哲学真理之关系,并成为这两大思想“综合的范例”⑥。他认为“上帝把哲学赋予希腊人,与赐律法给犹太人,具有同样的目的,那就是起着一个使女的作用,把人们引向基督。再者,哲学就是上帝与希腊人订立的约,而且——就像犹太人有他们的先知一样——根据这个约,上帝赐给了荷马,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这样的人以灵感。真理只有一个而且都源于上帝。”⑦克莱门特亦遵循斐洛的亚历山大犹太主义之寓意方法,认为解读《圣经》必须能够透过字义(literal sense)看到背后的比喻(parables)、隐喻(metaphors)和寓意(allegories)。克莱门特的思想,使得“异教哲学与《圣经》得以贯通。它成了整个历史的统一原则,特别是‘新旧二约的统一原则。”⑧
在斐洛和克莱门特等前驱的影响下,克莱门特的学生奥利金形成了关于圣经阐释的系统理论。奥利金提出了《圣经》经文的三种意义:somatic(文字上的)或语文学上的意义;psychic(心理上的)或道德上的意义;pneumatic或属灵的意义。尤为重要的就是第三种意义,“一般说来,神秘的意义与文字上的意义有区别。神秘的意义通过一种寓意的方法而发现,这是一种发现在文本后面的隐藏意义的方法。”⑨
除了源自犹太传统的寓意解经传统外,其他类似索隐派理论的学说还有原始神学(Prisca Theologia)和12世纪的喀巴拉(Cabala)。其共通之处是,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都有基督教的痕迹,可以通过对《圣经》的解读,发现其中隐藏的神秘意义。特别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喀巴拉被重新发现,基督教徒希望以此促使犹太教徒归信基督。⑩
在文艺复兴时期,索隐派思想在费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那里得以复兴,他“试图从埃及象形文字中解读出世界和神的深奥真理。”{11}继起者有伯里耶(Paul Beurrier,1608-1696)和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伯里耶同其他索隐派学者一样,也认为非犹太教的异教徒曾得到过来自上帝的启示,值得注意的是,伯里耶第一次指出,中国也是得到这一启示的民族。他在其著作《基督教之镜,从自然规律、摩西和福音之法律三方面讲》(Speculum christianae religionis triplici lege naturali,mosaic et evangelica)(1663)中指出:“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如同《旧约》中的先祖们一样拥有对创世、亚当的诞生、人类始祖的罪恶、大洪水、三位一体、天使和恶魔,以及惩恶扬善等等的认识。”{12}
被称为“最后的一个文艺复兴人物”{13}的基歇尔在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基础上认为,洪水之后,诺亚的后代统治着世界,中国的文字始于洪水泛滥后约三百年左右,创造者为当时的帝王伏羲,而伏羲是从诺亚的后代那里学到的。其实,中国人乃是埃及人的后裔,中国文字也是来源于埃及的文字。{14}基歇尔有关中国文字的看法完全与提供其资料的耶稣会士卜弥格的看法相反,且具有“来自欧洲人的偏狭观念和基督教沙文主义”{15},但却是当时欧洲索隐派思想的重要体现。
二、适应策略与学术传教:
中国索隐派之先驱
索隐派思想,一方面生出狭隘的基督教中心主义,如前所述的基歇尔;另一方面,也使得基督教对于其他宗教和文化有了几分尊重与宽容,并积极对异教和异文化加以“适应”,以图从中发现基督教的痕迹。尽管其目的最终还在于归化异教徒,但这份理解与尊重却有着超越宗教的意义,在异文化沟通之初期,显得尤为难得。晚明耶稣会来华之初,秉承的即是“适应策略”(accommodation),其代表人物就是利玛窦。
耶稣会士的“适应”传教思想直接来源于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of Loyola)。“不是要他们必须像我们而是相反”,这句话成了早期耶稣会士遵奉的一句格言。{16}利玛窦所遵照的是保罗所说的“在什么样人中成什么人”的教训,以此作为其在中国传教的根本依据。利玛窦的思想被徐光启概括为:“易佛补儒”。{17}利玛窦之“补儒”,并非将儒学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而是区分了“先儒”和“后儒”,区分了“经”和“疏”。他“尊先儒,反后儒”,尊经而斥疏。具体来说,就是批判宋明理学对于经典的阐释,而转向儒家经典之原本。在《天主实义》中,他多次批驳“俗儒”、“腐儒”、“今儒”等,其具体所指即为程朱理学,认为他们从源初儒学的有神论走向了无神论或泛神论。利玛窦认为,古代中国已经知道上帝的信息:“从他们历史一开始,他们的书面上就记载着他们所承认和崇拜的一位最高的神。”在古代经书中已有体现的上帝的信息,在后来的儒者那里被逐渐遗忘,新儒学“全部哲学都是有负于这些古代哲学家的。”{18}今日之急务乃恢复古经书之真相,宣告中国人,“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19}
在《天主实义》中,利玛窦“以中化中”地引用中国古代经典来论证中国自有天主之精义。利玛窦特别重视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书,尽管据说他著有《八卦与九宫之变化》{20},但对于《周易》似也无特殊的看法。倒是中国学者与之探讨儒耶关系时,常把话题转到《周易》上来,或会使利玛窦及其他传教士逐渐意识到《周易》在诸经之中占据着首要地位。利玛窦虽然没有对《周易》进行专门研究和译介,但其著述中所体现的“易佛补儒”的思想以及在儒家典籍中寻找基督教信息的做法,实则开启了后来索隐派研究中国古代典籍尤其是《周易》的序幕。
金尼阁可能是《周易》最早的翻译者。他继利玛窦翻译“四书”后,又将“五经”译成拉丁文,在明天启六年(1626)在杭州刊行,惜乎译本佚失。{21}再后的卫匡国在其著述中涉及到了《周易》。他在《中国上古史》(1658)中提出了中国历史纪年问题。以公元前2952年伏羲称王作为中国历史的开端,而据当时公认的《圣经》年代学,上帝造人在公元前4004年,诺亚洪水在公元前2349年{22}。卫匡国的说法对于欧洲年代学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卫匡国认为,伏羲不但是中国历史的开端,而且是八卦和文字的发明者,《易经》是中国最古老的书籍,伏羲通过《易经》规定了“由天及人数学模式”,《易经》自诺亚时代起一直传播不绝。{23}卫匡国继承了适应策略,也对中国历史知识和思想在欧洲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柏应理等人撰写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也是利玛窦开创的适应策略的延续,此书被誉为“在耶稣会适应政策下产生的最高学术成果。”{24}此书是“四书”中的《大学》、《中庸》和《论语》的翻译和注解。但和利玛窦不同的是,《中国哲学家孔子》的撰写者们对《易经》持批判的态度。原因有二:一是他们把伏羲当做传说中而非历史上的人物,由此,被耶稣会士认为是伏羲作品的《易经》,其地位也令人怀疑了;二是他们认为新儒学中无神论和唯物论的倾向源自《易经》,最重要的证据便是“太极”的概念。{25}也因为此,他们没有参照朱子的《四书集注》,而是采用了张居正的《四书直解》。虽说张居正对于朱熹的注疏有所批评,但其思想还是在理学范围之内的,耶稣会士夸大了张居正和朱熹之间的分歧,并以此作为贬斥新儒学的凭借,并以此作为回归原始儒学的途径。
三、“发现”上帝:中国索隐派与易学研究
尽管利玛窦对于“四书”、“五经”都非常重视,但其最为重视的却是“四书”,其后的金尼阁、柏应理等人亦是如此。至白晋来华,开始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周易》,并以此建立了中国索隐派。
如前所述,索隐思想在欧洲渊源有自,在文艺复兴的气氛中,这一思想得以复兴。在基督教与异教及异文化的接触过程中,索隐思想成为了理解和吸纳异教徒的一种重要手段。早期来华耶稣会士自觉地运用“适应”策略,虽说不能等同于索隐派,但却和索隐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可视作中国索隐派之先驱。后来的白晋自觉地把索隐思想运用到了在中国的传教实践中,成为了中国索隐派的创立者,他对于《周易》的研究,也开启了西方易学研究的新局面。
白晋很早就听说过利玛窦和中国,在1673年入耶稣会之前就决定献身中国使团。南怀仁委托柏应理回法国招募科学传教士,白晋最终作为“国王的数学家”之一来华,开始了其在中国的传教生涯。白晋之转向《周易》研究,曾经历过一段探索过程,但索隐思想早隐然于心。在开始传教之前,他就设法了解关于暹罗的宗教和经书的知识,并认为:“在这个国家的宗教信仰中可以找到我们宗教的一些踪迹——这个国家对上主的认识看来无疑是在时间流逝中被泯灭了,以至于他们对上主变得一无所知了。”{26}如若熟悉白晋后来有关中国宗教和《周易》的著述,就很容易看出其对于暹罗的看法和后来对中国的看法一脉相承。
白晋来华之初虽历经一些挫折,后来却被偶然选中进宫为康熙皇帝讲授数学、天文学、几何学等科学知识。传教变成了“教书”,白晋对此颇有不满之处,认为这是其传教生涯最为艰难的时刻,但尽责的白晋颇受康熙赞赏,康熙由此还在1692年3月22日颁布宽容圣旨,允许传教士在中国各地自由传教。白晋由此也对宫中传教方式兴趣大增,寄望于康熙一日归信,举国也将仿效入教。
白晋入宫之事虽有偶然的因素在,但就后来的效果看,此举也昭示着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的一次大变革。耶稣会士一改利玛窦着力结识士大夫精英的学术传教方法,转而围绕皇帝展开传教。白晋“国王的数学家”的身份,已经表明了其所在的宗教团体所效忠对象从宗教转向了国家。随着法国这一时期在欧洲地位的上升,政治和宗教的关系已经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其显要例证就是,在国家主义思想的刺激下,葡、法传教士在欧洲和中国发生了很多的冲突。随着世俗权力的强大,君主在国家事务和宗教事务中的作用增加,白晋转向效忠“太阳王”路易十四和中国皇帝康熙,就是基于这一背景的变化。与《四书》和士大夫的道德理想相关联类似,对于《周易》的强调,似乎更为切合注重儒学正统性的清初黄帝的口味,“在白晋看来,《易经》既是联结中国与欧洲的一把思想钥匙,又是获得满洲皇帝青睐的一把政治钥匙。”{27}由此看来,白晋的索隐思想,既是对利玛窦适应策略的继承,也是根据传教现实加以改进的结果,由士大夫走向了皇帝,由《四书》走向了《易经》。
白晋之所以转到索隐思想路向上来,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28}礼仪之争使康熙皇帝对传教士的态度逐渐改变,对康熙归信抱有乐观态度的白晋,意识到必须做些什么来扭转局面。后来成为在华耶稣会最高领导者的严当在1693年3月26日发布一道牧函(Mandatum seu Edictum),强调要维护天主教信仰的正统性,反对中国宗教的礼仪传统,其中明确反对“《易经》表达的是一种杰出的道德学说”{29}这类说法。白晋的索隐思想,与礼仪之争密切相关,他不赞同教宗有关中国礼仪的禁令,希望通过对《周易》的研究,使得世人明瞭中西宗教和文化的同源性,他认为自己有关索隐思想的理论“是前途渺茫的传教事业唯一的希望所在。”{30}
在1697年8月30日的一封信中,白晋首次提出了索隐派观点,{31}并在其后三十多年的生命中,不断加以阐释和补充,形成影响深远的中国索隐派。白晋以《周易》为核心的索隐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经和传、注、疏剥离,剔除对于经的解释部分,认为这些注释中有“大量错误和一种纯属迷信的占卜”。由于历代的错误解释,使得中国人逐渐忘却了《周易》本来精义所在。白晋自己对《周易》进行了注解,其工作的核心就在于揭示其中所包含的基督教信息。
二、揭示《周易》中暗含的数学信息,认为伏羲创造了由抽象符号阴爻和阳爻组成的八卦和六十四卦,其中包含了有关自然界的科学原理和神秘信息。白晋和莱布尼茨有关《周易》的通信,就是以这方面内容为要点。白晋更是将伏羲的数学体系和柏拉图、毕达哥拉斯联系起来,认为他们三人的数学体系是相同的。
三、文字问题。汉字这一象形文字(Hieroglyphen),曾引起过许多传教士的注意,索隐派也把对中国象形文字的研究作为研究重点之一。和前述基歇尔不同,白晋认为汉字和古埃及象形文字并不一样,汉字更富寓意。汉字产生于大洪水之前,是伏羲按照日月星辰创造的神圣符号,“它们反映的是上主和救世主对过去和将来规划的奥秘”。{32}《易经》就是这些文字最为重要的载体,“包含着象形文字智慧(Hieroglyphenweisheit)的完整体系且描述了过去和将来直到世界末日所有的变化。”{33}同属索隐派的傅圣泽认为,“易”由“日”和“月”两字组成,“日”代表圣父,是光明之源,“月”代表的是“天主圣言的人性灵魂(圣子)的形象”,“易”由此可看作是圣父和圣子的合一(Hypostatische Union)。{34}
在白晋周围形成的索隐派,包括郭中传、傅圣泽、马若瑟等,另外樊西元、聂若翰、卫方济等,也被认为与这一派思想相关。
作为法国耶稣会士中对“索隐主义最忠心不贰的拥护者”{35},傅圣泽曾作为白晋的助手一起研究《周易》,他的观点与白晋相互启发,尽管在主要观点上看法一致,但傅圣泽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索隐主义体系。其与白晋显要的区别是,“当白晋将注意力集中在《易经》中的算术和几何成就时,傅圣泽却因其对道教的兴趣而超越这一点。”{36}他认为中国古典文献源于天启,典籍中的“道”即代表天主徒的上帝,“太极”也代表着相当于“上帝”和“天”意义上的“道”。{37}自利玛窦对佛道两家持批判态度后,后来的耶稣会士对传统中国思想和宗教的认识也着眼于原始儒家,专注于儒家的经典,而傅圣泽扩大了对古代中国关注的视野,把目光投向了道家,认为其中也包括圣教真意。傅圣泽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其在回到法国之后,与当时诸多思想家交往,传播了索隐主义思想,这份名单包括:伏尔泰、圣西门、孟德斯鸠、拉姆塞、德·科蒙、布罗斯、傅尔蒙和约瑟·斯彭斯等。
马若瑟是索隐派另外一位代表人物,他曾称自己花了20年时间研究《易经》及其评注,笔记就有八大本之多。通过研究,他“越来越确信《易经》是一本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书”{38},他说:“如果我们不明白什么是寓言,我们也就不会理解‘经,特别是寓言的源头《易经》。这些书因为其譬喻和象征的特点而区别于其他的中国经典。《易经》一书以天、地和神秘事物为创作原型,是一部象征主义作品。《诗经》和《尚书》的教旨与《易经》中象征性地展示出来的教旨一样。这部书谈论圣人,所有的象征暗示着圣人的标志。最基本的象征为天与地,日与月,君与臣,夫与妇。”{39}马若瑟很重视泰卦和否卦,认为中国人对这两个卦的诸多解释都没有领悟到其真正的涵义,即:“世界由于亚当的原罪而遭到破坏,又因道成肉身而得到恢复。”{40}马若瑟很重视通过汉字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如他透过六书体系,认识到这些基本的规则把汉字指向了共同的神圣的来源,“六书体系是打开隐藏在这些预言中的神秘钥匙。这种观点成为了形成马若瑟自己独特的中国索隐派观点的基础。”{41}
尽管马若瑟曾经与白晋发生过对立,但就中国索隐派来说,最为核心的成员仍是白晋、马若瑟、傅圣泽和郭中传四人。白晋终其一生都希望教皇和罗马传信部相信索隐派理论对于在华传教的价值,但中国索隐派的理论“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地被投入到实践当中去。”{42}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是因为中国礼仪之争造成的耶稣会在华传教的中断。中西间新的交往,重启于晚清新教传教士来华。理雅各以一人之力翻译多部中国经典,其中就包括《易经》。就其对于《易经》及中国宗教的看法来看,理雅各的许多看法都类似于索隐派,可视为中国索隐派之后继者。
四、维多利亚时代的东方朝觐:
中国索隐派之后继者
新教来华传教士常把自己在华的传教当做是明清耶稣会事业的继续,他们遵循着类似于利玛窦的“适应”策略,强调对于中国文化的尊重和适应。首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就强调借助于科学和知识等“工具”,并强调中国具有和希腊、罗马一样丰富的历史和文化。
理雅各作为对于中国传统研究最为深刻的新教传教士之一,对于耶稣会士的“适应”传统,也有着更为全面的理解。1873年理雅各在参观天坛时,和同行者进行了一次即兴的礼拜仪式,尤其富有意味,即如吉瑞德所言:“理雅各在天坛上的行为,显示出与早期耶稣会士之间的某种联系,这些耶稣会士适应调和了中国传统仪式,他们的行为,曾经让17、18世纪的更多正统天主教传教士和教皇感到反感和愤怒。”{43}
理雅各以翻译《中国经典》而闻名,曾翻译过《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尚书》、《诗经》、《春秋》、《礼记》以及《庄子》、《道德经》、《佛国记》等中国古代经典。理雅各对于儒家的看法前后有些变化,但从他关于中国宗教和《周易》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坚持的主要观点是,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上帝的存在,中文中的“上帝”就是基督教的God。这一观点曾造成极大争议。理雅各认为,“传教士想要改变一个人的信仰,必须先要屈尊去了解他们将要改变的人和他们将要改变的宗教。”{44}理雅各关于中国古代宗教的看法,和白晋等人的索隐思想很接近。
理雅各曾在1854-1855年间翻译过《周易》,但他觉得,虽然完成了翻译,但他认为对于这部书并不甚理解。他于是把初稿放在一边,希望并相信有一天灵光乍现,让他得到一条线索,指引他洞悉这部神秘的经典。{45}直到1874年,理雅各才意识到自己可以把握到《周易》的秘密而开始重新翻译。其“朝向正确理解的第一步”是把经传分离理解,只用经本身来理解经。把经传分开的做法,是索隐派解读《周易》最基本的策略,理雅各之举,可看做是对索隐派做法有意无意的继承。
理雅各解读《周易》以及其他中国典籍另一主要主张是,认为中国典籍中的“帝”、“上帝”就是基督教的God,由此还发生过著名的“译名之争”。理雅各认为,中国古人用“帝”表达了基督教用God表达的意思,他认为“帝”就是God。理雅各以“上帝”与God进行对译的做法缘起于19世纪50年代初期,对于具体的理由,理雅各通过两篇论文进行了论述:《论“上帝”作为Elohim和Theos在中文中的适当翻译语:对于文惠廉主教所持“神”的观点的批判》(An Argument For Shang Te as the Proper Rendering of the Words Elohim and Theos, In the Chinese: with Stricturres on the Essay of Bishop Boone in Fovour of the Term Shin, 1850)和《中国人的上帝观和神灵观》(The Notions of the Chinese Concerning God and Spirits,1852)。{46}
在理雅各翻译的《周易》中,把“帝”、“上帝”译作God的例子所在多有,略举几例如下:
1.《履卦·彖》:“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Its subject)occupies the God (given) position, and falls into no distress or failure;——(his)action will be brilliant.(p.223)
2.《豫卦·象》:“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The ancient king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composed their music and did honour to virtue, presenting it especially and most grandly to God, when they associated with Him(at the service)their highest ancestor and their father.(p.287-288)
3.《益卦》六二:“王用享于帝吉。”
Let the king,(having the virtues thus distinguished),employ them in presenting his offerings to God, and there will be good fortune.(p.150)
4.《鼎卦·彖》:“圣人亨以享上帝。”
The sages cooked their offerings in order to present them to God.(p.255)
5.《涣卦·象》:“先王以享于帝立庙。”
The ancient king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presented offering to God and established the ancestral temple.(p.341)
6.《说卦》:“帝出乎震。”
God comes forth in Kǎn(to his producing work).(p.425)
“凡在中国古籍中出现的‘上帝,他一概译为God。”“中国古籍里的‘上帝就等于是基督教圣经里的‘耶和华。”{47}这种做法使得许多传教士集体写信给把理雅各所译《周易》收入著名《东方圣书》丛书中的麦克斯·缪勒,这些反对者认为,中文的“上帝”只能译作Supreme Ruler、Supreme Emperor或Ruler(or Emperor)on high等。缪勒则坚定地站在理雅各一边,认为“将God译成中文,没有比‘上帝更恰当的词。”{48}译名之争背后,彰显的是对于中国宗教以及儒耶关系的看法。理雅各译的《周易》在很长时间都是西方的标准译本,他的思想也因此得以广泛传播。
虽然理雅各接受了用God对译“上帝”,但他并非如同时代“汉学中国——印欧传统”那样,采用“一种强迫性的不加控制的胡乱愚蠢比较”方法,坚守着“一种有关起源的类似《圣经》一元发生学理论”,而是在比较的视野中,坚持一种人类文明起源的多元论,主张站在异文化的立场上看待文化与宗教的差异。{49}理雅各的立场代表着一种变化,即代表着从传教士汉学到专业汉学的过渡。一方面,理雅各延续着利玛窦、白晋以来的索隐传统,认为中国文化初期有着一神信仰,有上帝信仰的证据,只是在后来这一传统衰落了;另一方面,他自觉地运用比较的视野和方法,赞成文化的多元起源论。这样的看法更接近于一种纯学术的立场,也开启了后来对于中国文化的新的研究范式。
五、结语
来华传教士对于《周易》的研究深受源自《圣经》解释学的西方索隐思想的影响。利玛窦采用“适应”策略在华传教,认为原始儒家文献与基督教至为契合,其中包含有大量的上帝信息。利玛窦虽没有明确标举索隐主义,但他实可视作后来中国索隐派之先驱。白晋是自觉把索隐思想运用到中国传教实践和中国典籍研究中的传教士,他把传教对象的重点从士大夫转向皇帝,把研究文本的重心从《四书》转向《周易》,标志着传教士在华传教策略的一次重要转变。此一策略虽可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国家主义兴起背景下融通之举,但更是其一贯坚持的索隐主义之体现。白晋建立了中国索隐派,傅圣泽、马若瑟、郭中传等人均是中坚。这一派虽因中国礼仪之争而受挫,但他们所坚持的异文化、宗教间融会共存的理念,实是中西文化交通史上的重要经验。因礼仪之争所中断的在华传教事业,由晚清新教传教士重新开启,初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亦持适应和尊重的传教策略。新教传教士理雅各译介了包括《周易》在内的诸多中国经典,其关于中国宗教和《周易》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典籍中之“上帝”,即为基督教的God。这一观点曾引起过著名的“译名之争”。理雅各关于《周易》的观点,与索隐派思想有契合之处,实可视为中国索隐派之后继者。
《周易》作为中国的“群经之首”,一直以来在西方学界都颇受关注,西方之易学研究一直方兴未艾。而这一研究传统,实由来华传教士所开启,中国索隐派作用最大,由其所开创的易学研究模式,对于后来西方的易学研究,亦有持久之影响。
① 关于来华传教士索隐思想的研究,见:[美]魏若望著,吴莉苇译:《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德]柯兰霓著,李岩译,张西平、雷立柏审校:《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卓新平:《索隐派与中西文化认同》,见王晓朝、杨熙楠主编:《沟通中西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古伟瀛:《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对中国经典的诠释及其演变》,李明辉编:《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二):儒学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等。关于传教士有关易学的研究,见:阎宗临:《白晋与傅圣泽之学〈易〉》,见阎宗临著:《中西交通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林金水:《〈易经〉传入西方考略》,《中外关系史学会通讯》,总第6期,1985年(《文史》,第29辑,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王东亮:《易经在法国》,《周易研究》,1991年第3期;李贻荫:《易学在西方》,《读书》,1991年第10期;凡木:《周易西行》,《读书》,1992年第1期;沈延发:《周易——国外研究者点滴信息介绍》,《周易研究》,1992年第4期;罗丽达:《白晋研究〈易经〉史事稽考》,《汉学研究》(台北),第15卷第1期,1997年;任运忠:《理雅各、卫礼贤/贝恩斯〈周易〉译本比较》,《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2期,2008年4月;吴伯娅:《耶稣会士白晋对〈易经〉的研究》,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西初识二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杨宏声:《明清之际在华耶稣会士之〈易〉说》,《周易研究》,2003年第6期(总第62期);郭汉城著:《西儒卫礼贤易论举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李雪涛:《卫礼贤〈易经〉德译本的翻译过程及底本初探》,见氏著:《误解的对话——德国汉学家的中国记忆》,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等等。近年来对于传教士易学这一论题进行较为系统性研究的是韩琦和张西平,见以下文献:韩琦:《白晋的〈易经〉研究和康熙时代的“西学中源”说》,《汉学研究》,第16卷第1期,1998年6月;韩琦:《科学与宗教之间:耶稣会士白晋的〈易经〉研究》,陶飞亚、梁元生主编:《东亚基督教再诠释》,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2004年;韩琦:《再论白晋的〈易经〉研究——从梵蒂冈教廷图书馆所藏手稿分析其研究背景、目的及反响》,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张西平:《〈易经〉研究:康熙和白晋的一次文化对话》,见氏著:《传教士汉学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张西平:《〈易经〉在西方的早期传播》,见氏著:《传教士汉学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张西平:《梵蒂冈图书馆藏白晋读〈易经〉文献初探》,见氏著:《传教士汉学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张西平著:《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张西平著:《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等等。
② [美]梯利著,[美]伍德 增补,葛力译:《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31页。
③ [德]E·策勒尔著,翁绍军译,贺仁麟校:《古希腊哲学史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275页。
④ [美]胡思都·L.冈察雷斯著,陈泽民等译:《基督教思想史》(第一卷),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⑤ 斐洛:《摩西传》(Ⅱ,20),转自[英]罗纳尔德·威廉逊(Ronald Williamson)著,徐开来、林庆华译:《希腊化世界中的犹太人——斐洛思想引论》,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⑥⑨ [美]保罗·蒂利希著,尹大贻译:《基督教思想史》,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页;第58-59页。
⑦⑧ [美]胡思都·L.冈察雷斯著,陈泽民等译:《基督教思想史》(第一卷),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85页;第194页。
⑩{12}{26}{29}{30}{31}{32}{33}{34}{42} [德]柯兰霓(Claudia von Collani)著,李岩译,张西平、雷立柏审校:《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第11页;第19-20页;第31页;第61页;第345页;第141-142页;第97页;第64页;第213页。
{11} [美]孟德卫著,陈怡译:《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135页。
{13} 《简明不列颠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3-174页。
{14} [德]阿塔纳修斯·基歇尔著,张西平、杨慧玲、孟宪谟译:《中国图说》,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389-393页。
{15}{22}{23}{24}{25}{27} [美]孟德卫著,陈怡译:《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142页;第269页;第121页;第124-126页;第286-290页。
{16} [日]柯毅霖著,王志成、思竹、汪建达译:《晚明基督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
{17} 徐光启:《泰西水法序》(1612)。
{18} [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9-102页。
{19} 利玛窦:《天主实义·解释世人错认天主》,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20} 沈延发:《周易——国外研究者点滴信息介绍》,《周易研究》,1992年第4期。
{21} 萧若瑟:《圣教史略》,中法大学出版社1931年版,第419-420页。
{28} 见李天纲著:《中国礼仪之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5}{36}{37} [美]魏若望著,吴莉苇译:《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页;第185页;第190页。
{38}{39}{40}{41} [丹麦]龙伯格著,李真、骆洁译:《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第131页;第161页;第189页。
{43}{46}{49} [美]吉瑞德(Norman J. Girardot)著,段怀清、周俐玲译:《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1页;第35页;第126-127页。
{44} Helen Edith Legge,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05,p.231.
{45} The I Ching(The Book of Changes), Translated by James Legge,“Preface”,Dover Publications, Inc.,New York,1963.
{47} 《中国人对神的称呼》,[英]麦克斯·缪勒著,陈观胜、李培茱译:《宗教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167页。
{48} [英]缪勒《宗教学导论》,第166-167页。
(责任编辑:庄园)
Religion, Politics and Culture: the Figurists and the Study of The Book of Changes by Foreign Missionaries in China
Wang Hongchao
Abstract: The idea of Suoyin(searching for the hidden)is a theological method of explication that holds that all the nations in the world originate with Christianity and that subsequent human histories have been indicated in the Old Testament. Matteo Ricci established a missionary strategy in China that was“adaptive”, hoping that Christianity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the original Confucian documentation. Matteo Ricci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Confucian classics, particularly The Four Books, including The Great Learning,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whose“adaptive”strategy can be regarded as a harbinger of Chinas Suoyin Pai(the Group of Figurists). Core members of this group, Bai Jin(Joachim Bouvet), Fu Shengze(Jean-Fransois Foucquet), Ma Ruose(Joseph de Prémare)and Guo Zhongzhuan(Jean-Alexis de Gollet), focused their studies on The Book of Changes, hoping with it to explicate Gods in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s a result of the fight about the rites and rituals, the missionary activities by the Society of Jesus were interrupted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it was not till the late Qing that they were resumed. Famous for his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Li Yage(James Legge), a Protestant missionary in the late Qing, had an important view on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the ancient classics of China that“God”in these books was the Christian God. James Legges thought can be viewed as a successor to Chinas Figurists as the rise of the The Book of Changes studies in the Wes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issionaries who came to China, particularly to Chinas Figurists.
Keywords: The Figurists, The Book of Changes, Matteo Ricci, Joachim Bouvet, Jean-Fransois Foucquet, James Legge